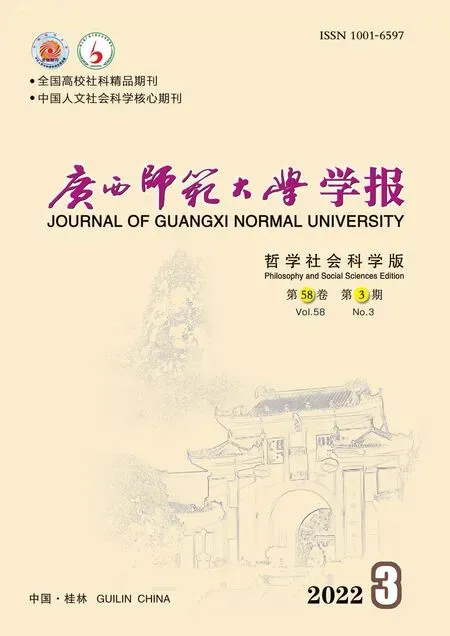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
——从“强制同化”到“新的阐释”
2022-02-26李栋
李 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后西学的输入在中国并未掀起波澜是因为“政教一体化”的王权主义维系着传统的“夷夏观”,国人囿于文化心理的定势思维对其进行排斥的话[1]232—241,那么,洋务运动三十年,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并认识这些知识时,其影响效果依旧有限,就不得不引起思考了。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西学传播内容的多少或传播方式的优劣,而主要涉及这背后中国人对西学这种舶来知识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即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评价心理”。
以往学界对西学东渐中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史实经验层面,侧重于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介绍他们都说了什么以及所说内容前后发生的变化,而缺少对于这些史料背后所涉相关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本文在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认知—评价心理”为分析框架,试图解释上述问题,以期深化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一、中国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
(一)“强制同化”:朝野知识分子的认识心理
首先就认知心理而言,根据主客二分的相关理论,人作为认知的主体,会自然而然地从自身的角度看待外在的客体或外部世界。按照已有的研究,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将人们对外部客体对象的认知过程类型化为两种:同化(assimilation)机制和顺化(即顺应,accomodation)机制。
前者指的是,“把外界元素整合于一个机体的正在形成中或已完全形成的结构内”[2]429。这即是说,当主体认识外在客体时,主体常常需要利用自己已有的认知,将外在之物“翻译”过来,让其成为主体原有认知的一部分。在此种“同化机制”中,对外在客体的存在和刺激,认知主体通常会将其放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理解,其本质上是一个外在客体融入主体已有认知结构的过程。
后者则指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对于外在客体,主体在认识其过程中,发现从自身知识结构出发,无法认识、“翻译”它,其内容和意义完全超越了主体原有认知结构,因而,认知主体必须主动改变或更化原有的认知结构,以顺应外在客体的刺激。
由于后者能够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因而具有开放性;而前者主要适合于主体对外部世界周而复始、循环出现的熟知对象迅速加以处理、分类和编码,因而对新鲜事物或异质事物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倾向于保守[3]34-35。对此,皮亚杰指出:当同化胜过顺化时(就是说不考虑客体的特性,只顾到它们与主体的暂时兴趣相一致的方面),就会出现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2]432。
如果以此为据,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由于缺乏异质文明的冲击以及对自身典章制度的自信,中国传统的认知心理大体上应属于同化机制。当他们遇到新事物、新知识时,惯常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从旧有词库中寻找相近术语进行表达,而不会另辟蹊径,通过建构或发明新概念完成这一任务。如他们将西方的“炮船器具,声光化电”用古语“奇技”“机巧”来表达,将国与国之间的“通商贸易”用古语“互市”“通市”来概括,将英美的议会政治用古语“议礼明堂”“议政乡校”来比附。
这种“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一方面很容易使来自于西方的新事物、新知识被中国人归类到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转化为中国人可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形态,甚至构成一种接受西方知识的权宜“策略”,“展现了冲破文化隔阂或拘囿的努力,为求弥合而诉诸本土话语,为异域法律文化寻找‘适当’的本土表述,蕴含着对西方法律的引介之策与推广之术”[4]307。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由于这种“强制同化”发生在认识主体对新事物的客观性特征和本质属性尚未充分认知以前,因而,认识主体也就失去了对其进一步辨识、理解的机会,必然表现为一种不真实或者说一种扭曲的认知,其结果必然导致观念与现实的背离,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皮亚杰的认知心理理论等于提醒我们,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理解近代中国的“刺激—反应”可能并不恰当。因为一个“刺激”之所以能够引发“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有机体首先能否“感受”到这个“刺激”。如果不能采取“顺化”的认知,而采取“同化”的认知,那么,由于缺乏对外部的“感受”,何谈“刺激”,哪有“反应”呢?
(二)“圣学投影”:朝野知识分子的评价心理
具体到认识主体的评价心理,按照既有的研究,人们评判和取舍外在客体或事物,需要遵照一定的标准和尺度。而评价标准和尺度的来源,大致存在两种方式:(1)归纳综合有关事实的信息,提出假说,然后考察这一假说能否说明全部事实,并通过比较事实与假说,进而修改、补充和丰富这一假说。这一过程是在不断试错、修正过程下完成的,其最终结果一般会发展或者反思原有标准或尺度。(2)以某种先定的信条、原则、规范及外在的权威命题为前提,并从这些前提中演绎出针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尺度和取舍标准[3]44。就差别而言,后一种以类似演绎逻辑的方式将新事物纳入先验性的权威系统进行评价;而前一种则有归纳逻辑的意蕴,即新事物构成了原先先验性知识的“源头活水”。
从理论上讲,评价心理虽不同于认识心理,但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从诠释学的角度讲,认知主体在认知心理的模式选择过程中已经“前见地”持有某种价值倾向。申言之,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认识心理的“强制同化”,必然会对其评价心理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所恪守的先验性权威原则就是“尧舜孔孟之道”。这些先验性权威原则意味着人世间万事万物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世间一切都只是这些权威原则的“投影”。如果用权威原则的“投影”无法投射,这类事物就一定是旁门左道、异端邪说。而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境,都被归结到对权威性原则的偏离,因此,解决方式就是重归圣人之学。
二、“西学中源”与“中本西末”: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具体表达
按照前述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介绍,其处理西学的思维过程可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他们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归类;第二步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评价。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在洋务运动时期呈现为两种具体的观念或者说范式:“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
(一)“西学中源”说:认知心理“强制同化”的具体表达
就涉及认知心理的“强制同化”来说,无论是居庙堂之上的洋务派士大夫,还是处江湖之远的早期维新派文人,为了认知、接纳西方异质事物,都在秉持“西学中源”说。
先说洋务派,该派之所以坚持“西学中源”说主要是为了对抗守旧派,为洋务运动开路。与洋务派所坚持的功用主义不同,面对西学,保守派则表现得更加敏感,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样一套西学知识会不会破坏中国人亘古不变的“人心”及其整套的价值体系。面对保守派的指摘,洋务派必须回答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申言之,洋务派面对的困境是,一方面他们与保守派一样也是孔孟之道的拥护者,恪守道统,不能逾越雷池;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谋求变化,接受西学,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于是,我们看到“强制同化”的认识心理在洋务派这里发生了作用,他们不去客观地辨识、理解中国和西方,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西方纳入中国,寻求一种正当性。需要强调的是,洋务派鼓吹“西学中源”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借用在明末清初朝野上下已经形成共识的“西学中源”理论。实际上,李鸿章早在1865年为了论证派人赴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反固有传统时,就开始主张“西学中源”说:
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5]14
洋务派后期的代表曾纪泽也是如此认为。他在光绪五年(1879)二月廿三日的出使日记中就认为西学涉及的政教、器物皆来自于“上古之中华”[6]177-178。
总之,洋务派“西学中源”说为他们“师事夷人”进而“采西学”作了合理性辩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西学中源”说不仅是洋务派所坚持的,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也对此深信不疑,并在此基础上将“西学中源”说的范围从“声光器电”扩展到“礼乐刑政”。
长期接触西学的王韬在《原学》篇得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的结论,并用大量篇幅予以溯源,他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7]89-90
薛福成对“西学中源”说的表述更为极端,不仅器物层面的各种“制作”是“西学中源”的,而且西方的宗教、工商、政制亦是如此[8]252。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陈虬(1851—1904)也认为议院之名虽不直接来源于中国,但其法则却是中国的。他说:
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则固吾中国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乡子产不毁乡校,其知此义矣。[9]917
此外,早期改良派集大成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卷一《道器》篇中,也说到今日中国之西学不过是“流徙而入于泰西”的结果,接着在《西学》篇中详细列举了“西学中源”种种表现,认为学习西学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并据此批评保守派反对西学,恰恰是不明中国固有古史的表现[10]111。
光绪十六年(1891)还未出仕的汤震甚至明确提出西方各门学科、各种技能源自中国古籍:
余若天文、物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重学、矿学、兵学、法学、水学、声学、医学、文字制造等学,皆见我中国载籍。[11]511
由是观之,“西学中源”说构成了前述朝野知识分子践行“强制同化”认知心理的主要方式。这其中既有他们对明末清初官方确立“西学中源”说的知识方面的接受,同时也有其应对保守派策略上的考量,但主要的还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心理。这一点可以从早期改良派拓展“西学中源”说的范围得以验证。至于为什么早期改良派会将“西学中源”说的范围扩大至“礼乐刑政”,则涉及他们对于“中本西末”观的不同认识。
(二)“中本西末”说:评价心理“圣学投影”的具体表达
就涉及评价心理的“圣学投影”来讲,实际上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在对待、评价西学知识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坚持“中本西末”说。
既然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在认知心理上坚持的是“强制同化”,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那么,中西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即中国的“圣学”是放之四海的,而西学只是“圣学”在泰西之地的延伸。因而,评价西学的标准自然是“圣学”,“圣学投影”就成为一种评价心理。“西学中源”说只是在文化源头上作了解释,而“圣学投影”需要进一步在文化的性质上明确中西之间的全部关系问题。于是,“中本西末”说就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评价心理“圣学投影”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学界一般认为,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中本西末”说皆来自1861年冯桂芬(18091874)《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冯桂芬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因而他很可能读过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所译、所编西书,故而提醒国人不能夜郎自大,应注意这些西学文献。接着他提出了“采西学”的顺序以及所涉范围: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12]56
由此,我们看到冯氏将西学的范围限定在数算地理、声光器电等自然科学领域,但同时,他又主张尽可能多地“鉴诸国”,凡是“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有帮助的,都应该了解。“鉴诸国”秉持的原则立场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目标是“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12]57。这里,冯桂芬明确地提出了“中本西辅”说,且西学仅作为辅助中国富强的功用。“伦常名教”作为“圣学”之本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以反对保守派得名,但在坚持“中本”还是“西本”这个问题上,两派并未产生分歧,皆将“圣学”奉为圭臬。李鸿章在1864年致函总理衙门时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13]卷二五,9-101865年他在《置办外国铁矿机器折》中明确提出了“中本西末”的观点:“中国文物制度”是不可动摇之本,而西学“犹如急病之方”,是末,且“末”对“本”而言,有“补救”之功效[14]卷九,35。
曾纪泽甚至认为,种种西学的内容,中国圣人“于数千年已曾道破”,其内容不曾超出中国经典所言[6]228-229。
可见,洋务派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开门”接纳西学,前者以一种功用的态度,认为西学可以“补救”“中本”;而后者则恪守“夷夏大防”,完全“堵塞”西学,生怕西学之末的引入会最终腐蚀、消解“圣学”之本。然而,两者却在是否应该固守“圣学”之本这个问题上态度完全一致,且不容分说。
洋务运动时期另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表现是,早期的改良派在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心理也是“中本西末”说。
对于“中本西末”说,王韬认为:“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7]13,且本末应同时兼顾,由本及末。在此,王韬不仅明确了“本”是“中国之政治”,“末”是泰西诸国“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而且批评了洋务派徒袭西人皮毛而不固国本的问题。王韬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一再重申“中本西末”说,其中的“本”就是中国固有的“圣学”,“末”是西学,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相辅而行之”[7]246。
由此,我们看到早期改良派中的王韬虽然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之“末”,但对应坚持中国之“本”并无异议,相反,他还提醒洋务派在学习“西末”的同时,更应该提升“中本”,且后者更为重要,纲举才能目张,“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7]29。
作为早期改良派的集大成者,郑观应也明确地坚持“中本西末”说,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0]112。与前述王韬一样,郑观应的“中本西末”说也建立在“道器论”的基础上,凸显了其坚守“中道”圣学的立场。他说: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10]18-20
由是观之,“中本西末”说构成了前述朝野知识分子践行“圣学投影”评价心理的具体表达。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这种认知—评价心理决定了他们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及西学在这一时期在中国被接受的可能性。对此,有论者认为这些朝野知识精英基本来自上层,而“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15]141。
先说保守派。该派适用这一心理机制的逻辑大体是,从认知心理上,甚至无须刻意地“强制同化”,直接将西方的一切归入未曾开化的“夷情”范畴,进而在评价心理上,在“圣学投影”“夷夏大防”的演绎下,直接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此种逻辑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关于“同文馆”设立之争和关于“海防”的争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再说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他们在适用这一心理机制时,一开始在认知心理上,用中学的固有概念和表达,在“西学中源”说的指导下,“强制同化”新出现的业已在中西交往中显示出无可辩驳之实际威力的西方事物;接着,在“圣学投影”的逻辑演绎下,以“中本西末”说为具体展开公式,以一种包容性的姿态,以西末“补救”中本。
因而,按照上述认知—评价心理,西学在洋务运动时期,要么像保守派那样彻底否定,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那样有限地接受,其接受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置换掉中国固有的“圣学”传统。
这样一种认知—评价心理的结果,要么像保守派那样,呈现出一种近乎迂腐般的盲目乐观情绪,进而滋生一股虚骄、排外之气;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那样,随着对“西末”了解、接受程度和广度的提高、加大,在思维层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观念与现实的极度混乱和悖离。实际上,早期改良派中的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这一点。
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的有限突破
尽管从整体上讲,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强制同化”的作用,影响有限,但是这些新鲜西学知识的传入反过来也会对上述的认知—评价心理产生一定的冲击。这里,笔者试图再以“中本西末”说为论说的重点,展现早期改良派虽在整体上坚持“中本西末”观,但由于受到上述西学的影响,他们后期的“中本西末”观在内容方面已经与洋务派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前已述及,“中本西末”观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评价心理,也是一种逻辑演绎范式,似乎一切新鲜知识、新奇事物都可以毫无扞格地放进这个既有的公式中进行逻辑推演。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里的西学是一套全新文明的产物,是一套用固有“圣学”所无法涵摄的新知识;同时它还是一整套既包括“奇技淫巧”,还包括“政教文化”的完整知识。因此,“中本西末”在早期改良派那里,到了后期还有另一种表达,构成了对于其既有认知—评价心理的某种有限突破。
(一)中西各有本末
总体说来,洋务派所说的“中本西末”观,指的是西方的一切“船坚利炮”“声光器电”,甚至包括后期利用“西学中源”所“强制同化”的“政教文化”,都属于“末”的范畴。中国当下学习它,只是为了修补、拱卫“中本”。“中本”与“西末”是在一个大框架下的,是可以相互修补的。至于到底是“由本及末”,还是“由末及本”,抑或是“本末并行”,并不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本”已经由中国的先贤圣人规定好了,且这个“本”本身是至当的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便“西末”中有涉及“中本”的内容,那也是“中本”很久之前传入西人那里的,现在的学习充其量算是“礼失而求诸野”。申言之,西人要么无“本”,即使有“本”也是中国固有之“本”,“本”只有一个,那就是“圣学”。
对于此点,郭嵩焘在接触了西学,尤其是作为公使出使英法之后,发生了改变。1875年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提出了西洋也有本末的观点: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16]345
并且,就本末之关系而言,他认为要因时制宜:“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16]340
既然西人也有“西本”,那么,他们的“西本”又是什么?这个“西本”是否只是“中本”的投影呢?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对此问题,郭嵩焘1877年在考察完英国政制之后,得出了如下认识:在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君民共主,民主之治矣”的其他文明政治模式,而这种“君民共主”的政治模式是西洋富强、文明的根本所在,即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17]156。需要注意的是,郭氏甚至还拿西洋“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制度参照、反思了中国陈陈相因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治恰与西洋“君民兼主国政”相反[17]407。由此观之,郭嵩焘不仅认为西人亦有本末,而且西人之“本”完全不同中国之“本”,甚至西人之“本”可能是优于中国之“本”的。因而,中国学习西人应从“本”开始,徒学西人之“末”是存在问题的。这些观点不仅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观相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颠覆了洋务派的观点。
(二)中“本”亦可变
按照洋务派“中本西末”观的理解,中“本”乃圣王之学,是万古不变之常经,这个“本”是不能变的。即便西学中存在诸多涉及“本”的内容,按照“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在“西学中源”的逻辑下,西学之“本”也是从中学之“本”得来的,因此,说到底这个中“本”是静止的、永远不能变的。
然而,随着西学知识的传入,早期改良派不仅开始意识到“中西各有本末”,而且随着这种认识的加深,中“本”亦可变的观念开始产生。这其中以薛福成、钟天纬表现得最为明显。
从法政思想来看,薛福成的思想以出使西洋为界,大体分为两段。前期薛福成的思想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法政观念,仍是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对传统制度的补苴,而出使后才认识到了西洋法政的利弊,以及中国可资借鉴之处。例如,1865年他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用传统治世“治标”和“治本”的观念,最早使用了“中体西用”这一概念,但其实质上并未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富有洞见性地将练兵、通商等也列为“体”[18]20-22。
薛福成有感于保守派因循守旧、阻挠洋务,也觉察到洋务派徒学皮毛、效果有限,因而提出“变法”主张,即“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甚”[18]52,并极具洞见地概括出天下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转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8]88。
由此,薛福成主张应“大变”,认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18]89。同时,他还认为:“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18]89他甚至突破了洋务派“西末”的观念,认为西法不仅不是“西末”,相反西法得“风气之先”,中国应主动学习:
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年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18]89
在这段表述中,薛福成已经承认中国在作为“本”的“风气”方面已经不如西方,并希望通过学习,以期在未来“更驾其上”。他在1893年借出使随员之口,讲出西学之“本”最重要的五个方面,即“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他认为:“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8]803
既然承认中学之“本”不同于西学之“本”,甚至不如西学之“本”,那么,中学之“本”是否应该变?对于这个问题,薛福成回答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主张中国之“本”亦可变是必须的。如他在出洋之后还坚持说:“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虽伊、吕复生,管、葛复生,谓可勿用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濬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9]卷六但是,在另一方面,薛福成又在很多时候坚持“独三纲之训,究逊于中国”,强调“中本”的优先性[8]273。
而对同一问题,在1880年前后,同样出过洋并长期与西人接触、从事中西翻译工作的钟天纬则表达得更为明确和深刻。他首先认为西人之“本”在于“政教修明”的政教制度,以及君主对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法律至上性的遵守[20]21。接着,他指出,西方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不同于中国之“本”,进而带动了各种“目”,纲举目张,实现了大治[20]21。对这样一种良善的“西本”,钟天纬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贫弱源于“本源之地,受病最深”所致。他说:
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由于堂帘太隔,太阿独操,所以易治者以此,所以易乱者亦以此。望君门如万里,则壅蔽日深,操政柄于一人,则民心日涣,虽有九州十八省,实则家自为政,人各有心,不啻瓜分为百千万国。如此则国势安得不削弱,君民安能关痛痒乎?于此而欲谋挽回补救之方,原自有在,特不从大本大原处着手,而仅就外面张皇,不揣本而齐末。则如遣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非不竭力经营,仍治标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苴,终无救于存亡之大计。[20]21
因而,钟天纬在字里行间已经表露出用西方政教修明之“本”,来改变中国“独操为政”之“本”的想法,可谓走向了“中本西末”的反面。当然,像钟天纬这样极端的表达在当时只能算是“先知先觉”,更多的早期改良派依然试图在“中本西末”的范式内表达其不同于洋务派的主张。
(三)“中本”中的“大本”
随着对西学了解、认知的深入,早期改良派不仅认识到西学一样“有本有末”,而且西学之“本”有其良善的一面,甚至产生了中学之“本”亦可变的想法。但是,囿于时代之风气、教育之背景以及不得不考虑的政治压力的影响,他们陷入了既想突破“中本西末”,引进“西本”,又不敢公然革新“中本”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十分无奈地提出了一些奇特的主张。这其中以郑观应所提出的“大本”最具代表性。
前已述及,郑观应亦是“中本西末”观的代表性人物,其代表性表达即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0]112。然而,如果认真品读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中《西学》篇的论述,实际上,在这段表达“中本西末”观的文字中,还有一个“大本末”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达是:
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10]112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郑观应一方面“分而言之”,认为西学也是有“本末”的,“本”就是格致、制造等学,后来也包括政教之学,“末”则是语言文字等;另一方面,就中学与西学关系而论,他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那么西学这个“本”与中学这个“本”是什么关系呢?对此,郑观应提出了“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的观点,即是说中学这个“本”较西学那个“本”来说,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是“大本”。
那么,这个“大本”具体包括什么呢?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道器》篇给出了明确的说明,他说:
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为而道不可变者。[10]20
可见,郑观应对中学之“大本”作了明显的限制与收缩,仅将其定位为抽象化的尧舜周孔“圣学之道”。这也就是说,除去这个抽象化的“圣学之道”以外,可以说都是“末”,哪怕是涉及西学之“本”的种种制度和知识。
通过这种转换,我们看到,一方面,郑观应在政治立场层面,坚决贯彻了“中本西末”这个清廷和社会舆论所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大本”的提出,使中学之“本”在内容上被缩小了,这样更多的西学之“本”,可以通过这种转换,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因为说到底它们还是“末”。关于这一点,郑观应在该篇的另一段话表露得更加明显: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所得,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10]19
在这段论述中,类似“开下议院”这样涉及根本性政教内容的西学之“本”,也被认为可以作为“末”,来辅助中国之“大本”。这样一来,在早期改良派的世界里,“中本西末”这个评价心理公式已经与洋务派有了绝然的不同。在早期改良派那里,“西末”的内容不断扩大,而“中本”的内容不断缩小。这也解释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为什么早期改良派会将“西学中源”说的范围扩大至“礼乐刑政”,其中学之“本”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洋务派。
事实上,这一时期为了弥合中学之“本”与西学之“本”同时存在的尴尬,与郑观应提出“大本末”类似的是,周采提出了“末中之本”和“本中之本”的概念:
今之天下,欲弥外患非自强不可,人能知之;而自强之要之本,人固不能尽知也。简器、造船、防陆、防海,末也;练兵、选将、丰财、利众,方为末中之本;修政事、革弊法、用才能、崇朴实,本也;正人心、移风俗、新主德、精爰立,方为本中之本。得末中之本者尚难勉支强敝,得本中之本者足以永奠苞桑。[21]卷4,23
这里朱采对中学之本末和西学之本末进行了杂糅,按照四个序列进行排序,即洋务早期所提倡的“坚船炮舰”和“声光器电”被认为是最低等的“末”;洋务后期所讲的练兵、丰财、利众等内容被认为是“末中之本”;而早期维新派所提倡的西方的“政教制度”被认为是“本”;而中国传统“圣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本中之本”。对此,他解释道:“人心何以正?躬化导、尊名教,其大纲也。风俗何以变?崇师儒、辨学术,其大要也。”[21]卷4,23
总之,尽管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在评价心理上都秉持“中本西末”观,但基于立场和认识的不同,早期改良派语境下的“中本西末”观在很多方面已经与洋务派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早期改良派接受西学知识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的“中本西末”从根本上并未突破“中本”的限制。因而,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西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有限的,法政知识连同背后的西学一起是中学之“大本”之外的“本”或者“末”。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争后,当维新派变法改制的思潮席卷中国时,他们反而噤若寒蝉的原因所在。
四、朝野知识分子认知—评价心理背后的原因
前已述及,洋务运动时期尽管西学在中国的输入较之鸦片战争前后已有明显不同,朝野知识分子对于它的态度已不再是冷漠与排斥,而是以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对待它,并将其具化为“西学中源”与“中本西末”这样的认知—评价心理,甚至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后期的某些朝野知识分子心里出现了某种有限的突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朝野知识分子仍给泱泱华夏几千年来固有传统的内核留下了位置,不仅没有彻底否定它,甚至连怀疑它都缺乏勇气。因此,无论“中本西末”也好,别样的“中本西末”也罢,“中本”这一核心本身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而言,仍是具有正当性的。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显然是传统的力量。传统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存在,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思想,更是一套特定场域下人们日常洒扫应对的信仰。用美国学者麦金泰尔的话讲,传统并非是笛卡尔以降,尤其是启蒙思想家笔下那种“未经反思的智慧”,相反,它不但不违反理性,其本身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即“传统的合理性”[22]457-466。作为一种传统存在的中国,历经几千年,并在鸦片战争前,在泛东亚地区构建形成“朝贡体系”,这都不能不促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其传统保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并对其内在典章文物的良善性深信不疑。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残酷的现实,促使生活在传统中的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他们在兹念兹的这个传统,于是,才有了上述类似“中本西末”这样的表达。正如前文所述,尽管这一时期朝野士大夫开始反思甚至更化这种传统,但其本质仍是在“绝对主义”哲学思维框架下对待传统的,亦即传统的典章文物仍被看成是“大本”,看作是绝对的、不容更改且优于其他传统的存在。
按照麦金泰尔的理论,一个传统之所以称之为传统,并具有合理性,其自我发展、更化的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起相关的信仰、经典和权威,而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第二个阶段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传统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或“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这对传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尚未找到克服或补救的方法;于是在第三个阶段,经过努力,对于上述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那种神圣的权威因此会在这一过程的进展中免遭否定,但其话语当然可能重新阐释”[22]464-465。这即是说,经过第三个阶段,尽管传统的内核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人们在此过程中对那个过去牢不可破的传统进行了新的解释。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新的解释也不能给予太高的估计,因为从本质上讲,这种新的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或者解构传统的核心部分,而其核心部分在这种新的解释下不仅更贴近“原教旨主义”,而且更具活力。
具体结合本文,可以看到,清末自海禁大开以来,当传统受西学的强势冲击,遭遇麦金泰尔前述提及第二阶段的“潜在威胁”,开始朝第三个阶段转化时,传统中国为了赓续传统,自然会对传统进行反思,看看自己的传统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探究为什么会这样,该如何应对。很明显,两次鸦片战争之前,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社会不会主动产生这些想法,相反,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上述表达与实践,实际上都在说明他们在对被冲击的传统做着“新的阐释”。当然,与过去历史不同的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朝野知识分子的“新阐释”所依凭的和所面对的都是传统农业文明所不曾遇见过的工业文明全新且不同质的知识。当然,借助这套新知识所给出“新的阐释”,如“西学中源”“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等,显然是过去不曾有的,但是这套“新的阐释”的框架仍然未超出传统。“新的阐释”探究的最终依据还是来源于历史经验,强调的仍然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这种特殊性,而非西方笛卡尔出发点式的探究,也非黑格尔那种终点式的探究。
中国社会对待传统这种探究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仅使得传统具有某种延续性,陈陈相因,自成一体;而且使得任何赓续传统的努力具有某种正当性,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然而,这种探究传统的方式也是存在问题的。申言之,当这种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通过“新的阐释”能够应对危机,即通过前面麦金泰尔提到的第三个阶段的工作使得传统重新获得活力时,传统还能得以维系和继续。但问题是,当这个传统即便通过“新的阐释”无法应对问题时,这种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呈现出“认识论危机”[22]473。
“认识论危机”不仅意味着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无法维系,被迫承认他传统存在的“相对主义”哲学思维框架;而且在“相对主义”哲学思维框架下的固有传统和他传统也并非是相互平行、无法比较、不分优劣的。相反,当一个传统遭遇“认识论危机”,它必须借助于他传统帮助其“续命”,这一过程就使得两种传统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在这一时刻它们在价值上是存在优劣的。这即是说在“认识论危机”之下,不仅任何自认为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传统无法继续“绝对”,被降格为“相对主义”意义上的存在,而且这种“相对主义”意义上的存在如果还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借助另一个有生命力的他传统,在批判、质疑原有传统内核的基础上,彻底改变自己。
同时,“相对主义”者的哲学命题(每一种传统必须永远按照那些标准来得以维护,因为它提供自己的合理性证明标准)也就跟着破产了。尽管在这里麦金泰尔注意到他传统与旧传统之间应具有连续性,但他特别强调克服“认识论危机”的新理论和概念结构“绝不会从那些早期的立场中派生出来”,是与传统发展第三个阶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本质区别的。更为重要的是,从价值上来看,这种帮助旧传统“续命”的他传统是“更有洞见的”,它一方面使旧传统“得以幸存和繁荣”,另一方面,它凸显了他传统在何时何地较旧传统而言才更具意义。
以此为据,我们认为:前述所概括抽象出的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知—评价心理及其所出现的有限突破或者说尴尬的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没有认识到清末之变实际上是中国固有传统遭遇了“认识论危机”,仍旧采取传统的应对危机的方式对待之的缘故。
面对“华夷隔绝之天下”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的现实,当时尽管不乏薛福成、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发现了此一变化不同于以往,但是他们尚无力从更为深入层面和更具理论化的角度阐释此种变化,因而,他们注定只能从麦金泰尔前述所说传统发展第三个阶段所使用的方式思考它、应对它。笔者这里并不是苛责古人,只是想表达他们的阐释在当时不仅是符合时代的,而且也是注定的。甚至国人对此认识的茫然无知,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时期,即梁启超所概括的“器物—制度—文化”。这一过程因为无法预计,所以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固有方式、努力的不断受挫,即通过时间才能感悟和获得。
因此,这也就注定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朝野知识分子在面对西学时,一方面他们无法摆脱“绝对主义”的思想框架,站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去正视它们、理解它们;另一方面,在无法意识到“认识论危机”的情况下,更无法用他传统的知识去质疑或者从根本上置换掉关涉固有传统中核心的部分,并论证这种质疑和置换本身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