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女儿
2022-02-26[比利时]让·马克-图林
[比利时]让·马克-图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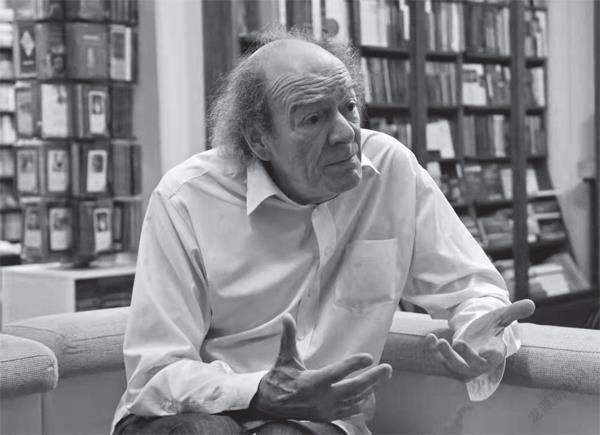
那时希奥朵拉十五岁,住在三角洲的平原上。
1934年夏天,那天很热。她穿上最美的珠光裙,黑发如中国的水墨泼洒至臀部,更显得肤若凝脂。母亲和姐姐在卫生间里帮她梳妆,给她戴上金银首饰、项链,往她发间插上珠花,手腕上套上镯子,脚腕上系细链子,再戴上金耳环。父亲决定让这个最小的女儿嫁给好友的儿子,一个她从没见过,或者说不熟悉的人。父亲的好友是一个傲慢的人,贪恋权势,事事躬亲地掌管着自己的家族以及依附于这个家族的人,他认为正是他人格的伟大,他所经营的事业,才能买下带地皮的房子,方便养马、停放小拖车。希奥朵拉要离开这片营地,离开祖辈开辟的道路,离开驯化的贫穷,离开无忧无虑、幸福、排斥、屈辱、乞讨、流动商贩式的迁徙,在那阳光明媚的早晨,她亲赴的是盛宴,还是葬礼?婚礼结束后,她就嫁进了丈夫的家族,他二十岁,是个有名的驯马师,他叫瓦西里,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傲慢有时让他无缘无故的暴力。
为此,他的刀破损了不止一次。瓦西里有一副斗士的体魄。姑娘们被他的悲剧气息深深地吸引,嫉妒希奥朵拉。瓦西里表现得像个领导人,马和人都由他管。他信命运,命中注定他就是母亲的好儿子。婚礼上充斥着各种舞蹈、音乐,各式的菜肴和酒精,大量的酒。瓦西里终于可以碰他的妻子了,他当众拥抱她。婚礼持续了两天。瓦西里的朋友们都想见识一下。美丽的新娘拥有一对明艳的猫眼,葡萄柚一般丰盈的胸,饱满而充盈的唇,跳舞时曼妙的臀。对了,还有感化马儿的笑声。“瓦西里,快跟我们说说。”瓦西里拉长着脸,卷发挡不住脖颈上轻微的划痕。他使蛮力要逮住她的时候她大吼:“别再来了啊!否则我杀了你!”婚礼第三天是家族聚会。音乐与欢歌中,亲人们笑着抹着泪,一一道别。在多瑙河与一片松林间广袤的草原上,木篷车隔出婚礼的场地。用于骑兵乐的马已经备好。孩子们围着新婚夫妇团团转。骑马的宪兵隔着距离在观测、监察着婚礼活动。
希奥朵拉面无表情。喝得东倒西歪的人群中,只有她的母亲读出了她眼中的悲伤。她油蓝的双眼仿若冬日的天。新婚之夜,母亲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勉强的婚姻带来的磨难。父亲从未征求母亲的意见,关系到家族繁荣的婚姻问题都由男人做主。希奥朵拉曾向祖母倾诉:“我不要嫁给瓦西里,我并不爱他。”祖母驳斥她:“没人能左右你父亲的决定。你得接受并且服从。最重要的,你得为你丈夫生个儿子。没有儿子,他根本不会正眼看你。”
她实在听不下去,那些谏言害苦了身边多少女人,蚕食了她们多少的美梦,害得她们只剩飘零的支言碎语还要不断重复,害得她们没有退路却不问缘由。她突然地伸出左手,示威地说:“你看看我手上这条女人的河,你看到了什么?”
老太太看都不看一眼。丝绸般的姑娘却总是急急躁躁,成天灰头土脸弄得一身脏。“你总是胡言乱语地对未来指指点点,你嘴里那些话你自己都不会信。将来等你有了孩子也够你受的。”
老太太扇了小孙女一耳光。“是时候找个男人驯服你了,我看你快变成一个荡妇了。你全身上下都魔怔了,我看都不想多看一眼。你不听话,有你好果子吃。我们说的话,你要敢不从,绝对会做出些伤风败俗的事,我看得很清楚。规矩不需要白纸黑字地写下来,规矩是一路穿越时空约定俗成的,那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骄傲和荣誉。在我们这儿,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爱他们,对他们忠诚。你没有哥哥,没人好好地引导你。你丈夫会好好管教你的。一直以来你父亲就是太放纵你,没看好你。”
那天夜里,小希奥朵拉问母亲:
“你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像我一样,像父亲逼迫我的那样,你也是被父亲逼迫着嫁给一个陌生人吗?”
“都是一样的。后来我爱上了你的父亲,我知道你正经历什么。”
希奥朵拉走出大篷车,心里一阵苦涩翻涌。无与伦比的璀璨星光下,她的双眼溢满泪水。
新婚的早晨,希奥朵拉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让他碰我。”同房让她浑身是伤。新婚夜里瓦西里强行挺入她身体三次。希奥朵拉观察她的丈夫。他大口喝酒,大声喧哗,手舞足蹈。她在宴会的人群中搜寻阿拉丹的眼睛,阿拉丹是她的朋友,比她稍大。一直以来他们总是在一起,并且偷偷地相爱了。阿拉丹正和一个女孩跳舞。他把手风琴丢在一边。小希奥朵拉喜欢看他演奏时与乐器合一的样子。跳舞时她感觉到了阿拉丹投向自己的目光。他演奏了一首告别曲,那是为她写的歌。阿拉丹是族群中唯一能读会写的人。有位老师特别喜欢他,放学后总是带他到家里单独授课。希奥朵拉真希望从婚约上踩过去,回到过去,让时间倒流。回到湖蓝般无忧无虑的小时候,回到满月时冷冷的夜里,躺在阿拉丹的怀中,再次地赤裸相对。她想起那天,把婚讯告知阿拉丹后,眼泪沾湿了他的肩头。阿拉丹说:
“只有一条出路,离开。”
“上哪儿去?到陌生城市的街头浪荡吗?行尸走肉吗?我没那个勇气。我既不会读,又不会写,靠什么赚钱?和你私奔又会害了你,我父亲和瓦西里绝对不会放过你。走遍天涯海角他们都会把我们找出来。”
“学着阅读,学着书写,赋予自己力量。自己争取的独立没人能夺走。拒绝改变,拒绝质疑统治规则的民族不可能进步,更不可能进化。”
阿拉丹家中有九个孩子,三个男孩、六个女孩,阿拉丹排第四。他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在四人乐团中担任匈牙利扬琴手。他让家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常常组织家庭游。
阿拉丹父亲的四人乐团跑各种商演,旅馆、市镇庆典、私家婚礼都在他们的行程里。没有宗教、市政元素的婚姻,婚礼是最基本的仪式。十三岁起,阿拉丹便开始了三地往返的生活:家里的大篷车、多瑙河支流中央一座小岛的小木屋、邻村老师家后方的小棚屋。
阿拉丹与老师结识的过程很普通。九岁的时候,阿拉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然后就等在学校门口,向老师表示希望跟随他多学一些知识。老师喜出望外:“太棒了!茨冈人的孩子渴望学习!”老师遵守了诺言。上完学校的课,便在家中等他,教他閱读、写作和算术。几个星期后,善良的老师让阿拉丹带一些书回家。
一双强劲的手从身后扣住希奥朵拉的腰,将她举高。希奥朵拉吓得大叫。瓦西里放声大笑,抱着她跳了几步,将她抛向弟兄姐妹和朋友。在场所有人为新婚夫妇的幸福干杯,为美丽的新娘干杯,祝他们子孙满堂。希奥朵拉知道,下一步该洞房了,再然后……满场的玩笑、恭维她充耳不闻,她满脑子只想狠狠地咬下去,狠狠地挠,她的下腹疼得厉害,一心只想钻进地缝,顾不上规划未来。瓦西里摸上了她的胸,拿捏着尺寸。他在享受自己的战利品。他是毋庸置疑的主人。男孩、女孩将新婚夫妇团团围住,嬉戏、打闹。大摆的红裙旋转、飞扬。女孩们手腕的镯子叮铃作响,翻飞的帽子一顶一顶又被接住。纱巾滑落,发型也乱了。音乐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即兴表演,他们总是节庆最耀眼的存在,让人惊艳。女人们唱起了歌。酒瓶子传到希奥朵拉这里,希奥朵拉对着瓶口喝了。大她两岁的姐姐邀她跳舞。她压低声音问她的初夜。“瓦西里的那玩意儿硬吗?持久吗?”问完自己笑了起来。希奥朵拉不说话,没人能撬开她的嘴。她望着晚霞的红光披挂在树梢,微微侧着脸看他。希奥朵拉幻想着阿拉丹邀请她跳一支舞,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即便她知道他不会,那会激怒瓦西里,阿拉丹不能冒这个险。如果他拥她入怀,她能掩饰无以抑制的欲望吗?不行,阿拉丹从没学过格斗,而且他已经离开了宴席。他骑马走了。小希奥朵拉恣意地跳着,曼妙的舞姿围绕一个又一个男人。瓦西里引她入怀,久久地吻她。他的酒气逼得她往后退。瓦西里笑,打了她屁股,又笑。然后又喝了起来。
夜幕降临。
瓦西里跳舞时摔了一跤。他点燃一根烟。希奥朵拉坐在火炉旁的木头,翻来覆去的一个疑问在她胸中翻滚,仿佛一块巨石压在心上。“为什么?”她徒劳地搜寻着母亲的眼睛。幼时抱她入怀安抚她的女人在哪儿?那时她还小,蜷缩在母亲的怀中,听她唱现在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她的周围围着几对跳舞的恋人,希奥朵拉不离火炉半步,茫然地盯着快要熄灭的火焰,眼里写满疑问。瓦西里看到了她,走到她身旁。他令她生厌。她起身,朝留给他俩的小篷车走去。
老希奥朵拉睁开黯淡无光又空洞的眼睛,睡时干瘦的手蜷缩在裙裾。蒂波的演奏舒缓。老希奥朵拉细声说:“当时我不能上鸟岛找阿拉丹。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阿拉丹在河中央的木屋。他按自己的品味改造了三角洲一间渔民的老房。很多时候他在那儿阅读,拉手风琴。他把马留在草地,划小船上岛。婚礼上的歌舞环绕着我,我想象着阿拉丹的手风琴声轻轻柔柔地晃。”
希奥朵拉不知道,鸟岛不叫鸟岛了。为了纪念当年排水工程的茨冈苦役,人们叫它“镣铐岛”或者“酷刑岛”。死去的冤魂激荡着大河,直至黑色的大海,阴风阵阵中苦苦地呻吟。希奥朵拉的祖母告诉她,奴隶主放狗追捕逃跑的苦役,脚踝上戴着铁球镣铐的苦役白天黑夜地躲在多瑙河边的沼泽里,寻找着一线生机。一旦被发现,茨冈苦役或者被狗咬,或者被打。奴隶主很清楚,不听话、拒绝奴役甚至妄图自由的毛病是人的瘟疫,那比麻风病可怕多了。
老太太不说话,双眼又慢慢地合上了。蒂波停止演奏。橙色的光切近地面而来,泼洒在树上和房屋的正面。蒂波说,天烧起来了。希奥朵拉转过头,她看不见却仍然看向记忆中熟悉的色彩。
“我不喜欢‘燃烧’这个词,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罪恶。起风了?”
“风很小。”
“帮我准备轮椅,该上城里去了。”
她笑了,布满皱纹的脸焕发光彩。“今天上公墓那儿。你如果有事的话,把我留在那儿,之后再来接我。一个人静静挺好。”
蒂波把轮椅停在一棵椴树下。公墓年久失修了,花草野蛮生长,覆盖了坟头、小径,与塑料假花混为一体。
老希奥朵拉轻抚盖过阿拉丹棺材的土,又将一捧土装进果酱瓶里,双手握住瓶子,放在腿上。希奥朵拉睁着眼睛,脸庞的肤色、发丝的银映着落日余晖的铜色。睡意来袭她就睡一会儿。一个小女孩坐在她脚边,背靠着轮椅的轮子。一根青草在她唇间翻来倒去,她穿了一条齐肩的褪色破裙子,光着脚。有一会儿,老希奥朵拉的手落在小女孩缺乏营养的枯发间。仿佛诊断出疾病一般,她错愕地缩回手。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睡了。小女孩看着她,耸了耸肩膀。
妻子隆起的肚子成了瓦西里的新骄傲。他向亲朋报喜,向集市、酒吧的陌生人报喜。一个男孩儿,那可是他的儿子,他所有的寄托。他为他规划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夜里的月亮骗不了他,他会为每一个儿子规划远大的前程。他的儿子将纷纷成为成功人士,成为企业家。他们将平等地享有大多数人应有的权利,受人敬重。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成为战士,他们也一定会成为战士。瓦西里远眺,风谲云诡如万马奔腾,人世也如此,拒绝卑微的人理应用尽一切手段为荣誉而战。“瞧瞧,马多尊贵,它绝对不会容忍羞辱。马接受规则,而不是不公。”
希奥朵拉帮她婆婆干活儿,帮她公公干活儿,帮姑嫂干活儿。当然,帮她丈夫干活儿。希奥朵拉就是干活儿的。起早贪黑地干活儿,直到她失踪不见。她不说或者少说。她已经学会了骂不还口,学会了不要大惊小怪。原先她还躲着哭,后来她不哭了。婚礼后阿拉丹再也没有出现。五个月了,肚子里的孩子都会动了。夜里躺在床上,她便由着瓦西里摸她的肚子。因为他想,她是他的所有品,她服从他。这一个冬天格外的漫长,霜雪让人们屈就于逼仄的生活空间。孩子们总是喊饿。多少做母亲的跑到服务区向农民讨吃的。春夏时,她们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户外劳作重启时,她们所做一切并不计算在内。没有保暖的衣物,孩子们冻僵了。没条件便创造条件,瓦西里经常离开营地上城口的集市去。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结婚的开销过大了,得想办法赚钱。瓦西里的商业头脑算是打磨出来了,他父亲帮了很大的忙,教他算计,在马匹的数据上作假。他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很多人愿意听一听他的意见。父子俩名下的马匹越来越多。瓦西里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周围到处是财富,怎么就不能属于他,怎么就不能再估算?
每到深夜的时候,希奥朵拉就问自己,生孩子能带来幸福吗,勉强的婚姻让自己成了自己不愿成为的那种女人:彻底地屈从于男权。尤其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尤其女孩。希奥朵拉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反抗的能力,这个疑问让她总是头晕,躺在自己丈夫的身边,她心中充满了各种矛盾,一夜又一夜地辗转难眠。有一天夜里,瓦西里醉了,总觉得自己被一个买家骗了,他粗暴地弄醒希奥朵拉,要跟她做爱,强硬得还想打她。希奥朵拉不从,他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两天后,希奥朵拉流产了。瓦西里要希奥朵拉和上帝原谅自己。特别是上帝。接下来的几周,母亲和姐姐训斥希奥朵拉,瓦西里总是站出来维护她。他还特别关照她要多休息,不让她干重活。希奥朵拉看不出他的变化有多真诚。祖母那句话“你得服从他”不断地反复,仿佛悬崖边不断撞击的惊涛骇浪。夜以继日地回荡在她脑海。
春天时瓦西里的妹妹安吉丽卡要结婚了。瓦西里的妹妹十五岁,新郎帕维尔十九岁。帕维尔跟着瓦西里做买卖。一天夜里,两个年轻女子坐在炉火边,希奥朵拉告诉安吉丽卡,自己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但是安吉丽卡可以保护自己,不再重蹈覆辙。
“瞧瞧我,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认为我幸福吗?”
“我和你不一样,你冷漠,永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男人们的目光在你身上停留,因为你长得漂亮。他们想要你,我哥哥要你。但你的身体不是为男人而活。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你就没有任何欲望?一点都没有吗?我的身体告诉我,它需要一个男人。我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我的男人,我要满足他的欲望,当然也要让自己开心。我的乳房是他的,我的腹部,我的双唇全都是他的。我还年轻,年轻是我的资本,这也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要生活,我想要被爱。”
安吉丽卡并不在意希奥朵拉的眼神,反而笑了。她的笑洋溢着肉欲。她还说,“至于我的心,没人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又是什么做的。但是如果没了人,就像老话说的,世界就要变荒漠了。我倒要说说你,希奥朵拉,你浪费了你最好的年华。”
希奥朵拉气得直哆嗦,“瓦西里全家都是这么看我的,其他人呢?阿拉丹呢?”想到这儿,希奥朵拉心痛得快窒息了。她可以不在乎其他人,但她不能不在意阿拉丹,他不能这么看她,不能像安吉丽卡说的那样看不起她。内向的阿拉丹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次,她心里反反复复一个疑问折磨得她痛不欲生——“他没出现的时间都和谁在一起?”她嫉妒自己想象出来的女人。夜梦中阿拉丹被多少滚烫的爱人身体烘热著。梦见阿拉丹的夜里,她让瓦西里抱紧她,要她,吞了她。
责任编辑:丁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