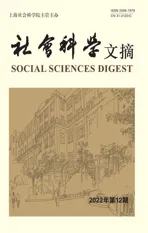“鲁迅文学”:20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
2022-02-23汪卫东
文/汪卫东
“鲁迅文学”的提出
本文提出“鲁迅文学”,意在描述和彰显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作为起源性与标志性的存在,“鲁迅文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回顾和总结“鲁迅文学”,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鲁迅,也意味着适时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甚至一窥鲁迅文学想象与中国文学现实的距离。
无疑,“鲁迅文学”集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现代文学的优秀资源,从传统、现代、启蒙、革命、政治、艺术等多种维度去描述它,都可以找到阐释的可能,但任何单一维度都不能穷尽它的存在。
鲁迅不认同载道与游戏的传统文学观,不屑于现代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文学,又与现代的“纯文学”与“艺术”保持距离。他前期投入小说创作,申明并非将小说引入“艺术之宫”,后来放弃富有别才的小说转向杂文,对于他人的劝阻不以为意,甚至断然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以文学为志业,但屡屡宣称文学是无用的,戏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临终留下“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遗言。
他与文学之间,构成了一种情到深处一言难尽的关系。特立独行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定见?鲁迅很少正面谈及他的文学观,我们能否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立场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不是以作品,而是以一生的文学行动,展现了“鲁迅文学”的存在。留日时期引介“摩罗诗人”,揭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意向,此后终其一生以文学为促进现代转型的行动。文学在他这里,是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社会行动,是追问自我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是有限自我与大时代共存亡的方式,其文学外在切入现实,同时内在切入自我生命,既反抗外在的黑暗,也反抗内在的绝望,在鲁迅文学中,个人与时代、现实性与内在性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
从小说、散文诗到杂文,鲁迅在行动中赋予文学以意义,所到之处,不断展现新的文学景观,拓宽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因其示范效应,小说由边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杂文更是几乎凭其个人的努力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镇。在他这里,文学性不是从过去时的“文学概论”来的,而是由文学者的当下行动赋予的。
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已然超越诸多现行文学理论的界定。以艺术和审美为宗旨的现代纯文学观,无法穷尽鲁迅文学的复杂性,以文本为中心的现代阐释观,顾及不到作品背后更大的文学者存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单一维度,也看不到鲁迅文学现实性与内在性的深刻关联,将文学的现实关怀简化为“感时忧国”并打上不够“现代”的标签,更与中国和鲁迅相隔。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必须溯源到更为本源和整体的、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
弃医从文:救亡理路与文学自觉
弃医从文背后有文学的自觉,与苦心孤诣的救亡理路相关。创办文学杂志《新生》中途流产后,鲁迅有两个重要行动,一是在《河南》杂志发表系列文言论文,二是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弃医从文的内在理路,就在这两个文学行动中。
五篇论文的动机来自先觉者共同的问题意识:近代中国的危机及摆脱危机的出路。面对“扰攘”不休的“新学之语”,鲁迅对洋务派、维新派甚至革命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提出批判,并展开系列追问。如果说《人之历史》追问什么是“进化”,《科学史教篇》追问什么是“科学”,《文化偏至论》追问什么是“文明”,那么,《摩罗诗力说》追问的则是:什么是“文学”?鲁迅超越构成“国”与“群”的“国民”层面,拿出“立人”方案,所立之“人”,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己”,将作为“个”的现代主体作为“兴国”的基础。五篇论文追寻的就是能激活“己”的所在:“进化”之“能”—“科学”背后的“神思”“理想”“热力”“道德”“圣觉”—“精神”与“个人”—“诗”(文学)。“诗”(文学)成为最后的落脚点。《摩罗诗力说》将文学与应用性知识相比较,展示文学的“不用”性。“不用之用”暗含着这样的指向:只有发现前面那些“用”无用之后,文学之“用”才显现出来。《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也含有卓越的文学想象,引进东欧、北欧及俄国等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展示了深刻的人性力量。
青年鲁迅的文学自觉背后,是中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自系统内自发的价值重估正在发生,传统僵化的和现有确定性、规范化的话语,无法承担激活“心”的使命。“诗”终于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出现,在转型的历史关头,它能通过还原生命与现实,打破物欲掩盖的平和,颠覆僵化的界定,释放生命的活力,激起“上征”的意向,化为再造文明的行动。痛感中国“诗人绝迹”“众语俱沦”,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展现“摩罗诗人”的“诗力”,宣告“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
以“新文化”为指向的“第二维新”呼吁,远接十年后“五四”的风雷。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历史选择,鲁迅“精神”与“诗”的孤寂思路才得以对接。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中,可以说,世纪初鲁迅个人志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起点。
救亡—“兴国”—“立人”—“己”—“心声”—“诗”(文学),这是鲁迅的文学自觉,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个人起点。
危机洞察与小说中国
五篇论文没有任何反响,《域外小说集》也少有人问津,个人挫折加上现实失望,累积成长达十年左右的隐默。在“金心异”劝说下,才有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22年底鲁迅将14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并写了《自序》。在这篇名文中,鲁迅第一次回顾个人经历,对于寄居S会馆的六年用墨颇多。在他的笔下,S会馆的独居岁月神秘而恐怖,成为十年隐默的最深点。
当周树人在S会馆隐默的时候,《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钱玄同来会馆拉稿,遂发生有关“铁屋子”的对话。通过将希望与绝望之争置换到时间之维,鲁迅将原来作为行动前提的希望放到“将来”,确认了希望的“可有”。
选择重新开口,内因还是主要因素,十年中对现实与历史的洞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近代危机的本质和重启行动的必要。《狂人日记》标志着鲁迅打破隐默,重启文学行动。“呐喊”并非自我表达的需要,而是为文学革命者助威,采取的是边缘姿态。
小说的文体特点是鲁迅中期选择小说的一个原因。小说虚构一般包含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的叙事层级。对于采取边缘姿态的鲁迅,小说正好可以隐藏自身。选择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现代小说的性质相关。18世纪小说开始加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致力于对现实真相的全方位展现,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又转向以内在真实构造整体世界图景。鲁迅同时面对的是19世纪现实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两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性和史诗性,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相结合,构成了现代小说具有整合性和寓言性的特点。
《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采取极为精巧的象征结构,揭示出封建文化的“吃人”密码。以《狂人日记》为主导,《呐喊》展示弱者被“吃”的“无事的悲剧”,揭示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病苦”。《阿Q正传》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也是一篇极具整合性和寓言性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性,但典型论阐释难以揭示其丰富的思想性。“序”强调找不到给阿Q作“传”的传名,意味着阿Q不能被传记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系统所接受。这可能是阿Q悲剧的最深点。找不到传名是否意味着,面对现代中国,传统的史传已经失效?从小说“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才找到阿Q的传名,又是否意味着,现代小说开始取代传统史传成为写照现代中国的最有效手段?“序”宣告了史传传统的式微和现代小说的来临。
小说书写隐藏了周树人,推出了中年小说家“鲁迅”,以“现代小说”写照“现代中国”,忧愤深广而深文周纳,成为现代中国的传记和寓言。
《彷徨》与《野草》:反抗绝望的生命行动
《阿Q正传》后,《呐喊》的写作速度明显加快,写作者似乎失去虚构的耐心。1922年12月,鲁迅作《自序》,回顾第一次文学行动挫折后的“无聊”“寂寞”“痛苦”。而此时鲁迅已处在第二次行动的挫折中,对彼时绝望的描述,叠加了此时的感受。
1923年鲁迅又一次停止创作,并且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两件事:一是周氏兄弟失和,二是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前者让前期家庭生活告一段落,后者则拉开此后人生的大幕。这一次沉默并不长,1924年初鲁迅打破沉默撰写《彷徨》,9月又开始写《野草》。打破沉默的秘密,就在《彷徨》与《野草》中,这是梳理自我、冲决绝望的尝试。
《在酒楼上》中吕纬甫的回乡是为两件“无聊”的“小事”,但结果都没有办成!两件事都来自母亲的指令,一个问题也就问出:如果这个“母亲”不存在了,其结局会怎样?答案就在一年零八个月后写的《孤独者》中。小说开始,魏连殳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祖母去世了。小说以祖母的死亡开始,以连殳的死亡结束。连殳开头迸发的大哭,既是为祖母,也是为自己,祖母之死,敲响了连殳的丧钟。如果说《在酒楼上》写的是绝望的最后状态,《孤独者》写的就是绝望后的崩溃过程,二者堪称姊妹篇。两篇结尾都安排了悲剧目击者“我”与悲剧主人公分开的相似情节,显出试图超越悲剧自我的意向。写于同时期的《伤逝》是爱情悲剧。据许广平回忆,其时二人刚决定携手一生,鲁迅的现实人生与《伤逝》悲剧也拉开了距离。
《野草》以更为内在的方式切入自我,是第二次绝望中生命追问的过程,是突破绝望的生命行动。《野草》将长期缠绕的矛盾一一打开,试图探究矛盾背后的存在,每一篇都面对矛盾,并将其推向终极悖论,最终形成生与死的难题。从《影的告别》到《过客》是追问的第一个部分,《影的告别》宣告走向死亡,到《过客》化身为走向“坟地”的“过客”,并提出“走过那坟地之后”的问题,在以“我梦见”开头的七篇中,向死的意向又遭遇生的挑战,直抵死亡的追问却最终发现,“本味”永无由知!《颓败线的颤动》中,此前所有矛盾汇集整合并于“老女人”的绝望中发散。《死后》之后,终于回到生的主题。一年多后,鲁迅为《野草》写下《题辞》,像久病初愈发出新生的呼喊,生死的辩证,意味终于穿透死亡获得新生!
杂文的自觉:文学行动的最后抉择
与内向型的《彷徨》和《野草》同时,新的外向型写作已悄然开始,随着卷入女师大事件,鲁迅的杂文越写越多。《彷徨》尤其是《野草》的追问解决了自我的难题。论战的杂文说明,一个以杂文为武器的行动者鲁迅,已经产生。
鲁迅杂文结集始于1925年,该年编有《热风》《华盖集》,此后越写越多,成为晚年最主要的文体。杂文对于鲁迅,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鲁迅放弃小说转向杂文,常引起人们的惋惜和非议。在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中,他不时回应,并自觉地与“创作”“文学概论”“文学史”等拉开距离。可见转向杂文背后有着不想明言的定见。
《野草》追问的终点,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野草·题辞》宣告第二次绝望的克服,同时宣告杂文时代的来临。鲁迅完成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矛盾背后的不矛盾自我并不存在,自我就在矛盾之中,自我价值就在于对每个“当下”的争夺,只有以有限的自我与大时代碰撞,投入每个当下的行动,才有个人与时代的未来!
行动,成为最后的落脚点。《野草·希望》对核心矛盾——希望与绝望——进行集中处理,层层设置障碍,又层层突围,最后落脚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之上。既没有站在“希望”一边,也没有站到“绝望”一边,而是站在“虚妄”之上。否定之后什么留了下来?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而是行动!
第二次绝望后确立的行动,与走出第一次绝望时有别。作为“可有”的“希望”属于他人,行动也是为了他人,这次行动基于“虚妄”之上,为他人与为自己的矛盾得以解决,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和解,自我以真实的身份直接出击,投入与时代的互动。现实取代虚构,成为文学发生的直接场所。
鲁迅最终确认的文学行动,就是杂文。这是“生命的泥”委弃于中国“大地”的产物,“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这是穿透死亡后的发现,是作为“行动”的鲁迅文学的最终抉择。
晚年《且介亭杂文·序言》道出“杂文”的本意。“杂文”的命名不是现代文学上的文体归类,而来自传统的文章编年法,编年的“杂文”,不在于“揣摩文章”,而在于“明白时势”。每一篇“杂文”,都是“攻守”当下、“感应”现实的“神经”和“手足”;作为整体,则展现为行动的轨迹和人生的历史,杂文写作是让每个当下成为“现代史”的行动。以杂文为武器,鲁迅最充分地发挥了文学参与历史、介入现实的功能,鲁迅杂文不仅是最出色的个人传记,而且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份“野史”,并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见证。
文学就是行动!终其一生,鲁迅以文学为促进现代转型的行动,经历了留日时期的文学自觉、“五四”时期的小说自觉及20年代中期开始的杂文自觉,遭遇两次绝望。在这复杂的文学之旅中,我们看到战士鲁迅、哲人鲁迅、小说家鲁迅、杂文家鲁迅的丰富面影,这些都归属到现实战斗与生命挣扎相互交织的文学行动中。只有将“鲁迅文学”还原到整体的文学行动中,才能得到合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