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绕三灵”的本相阐释
2022-02-22邢莉张翠霞
邢莉 张翠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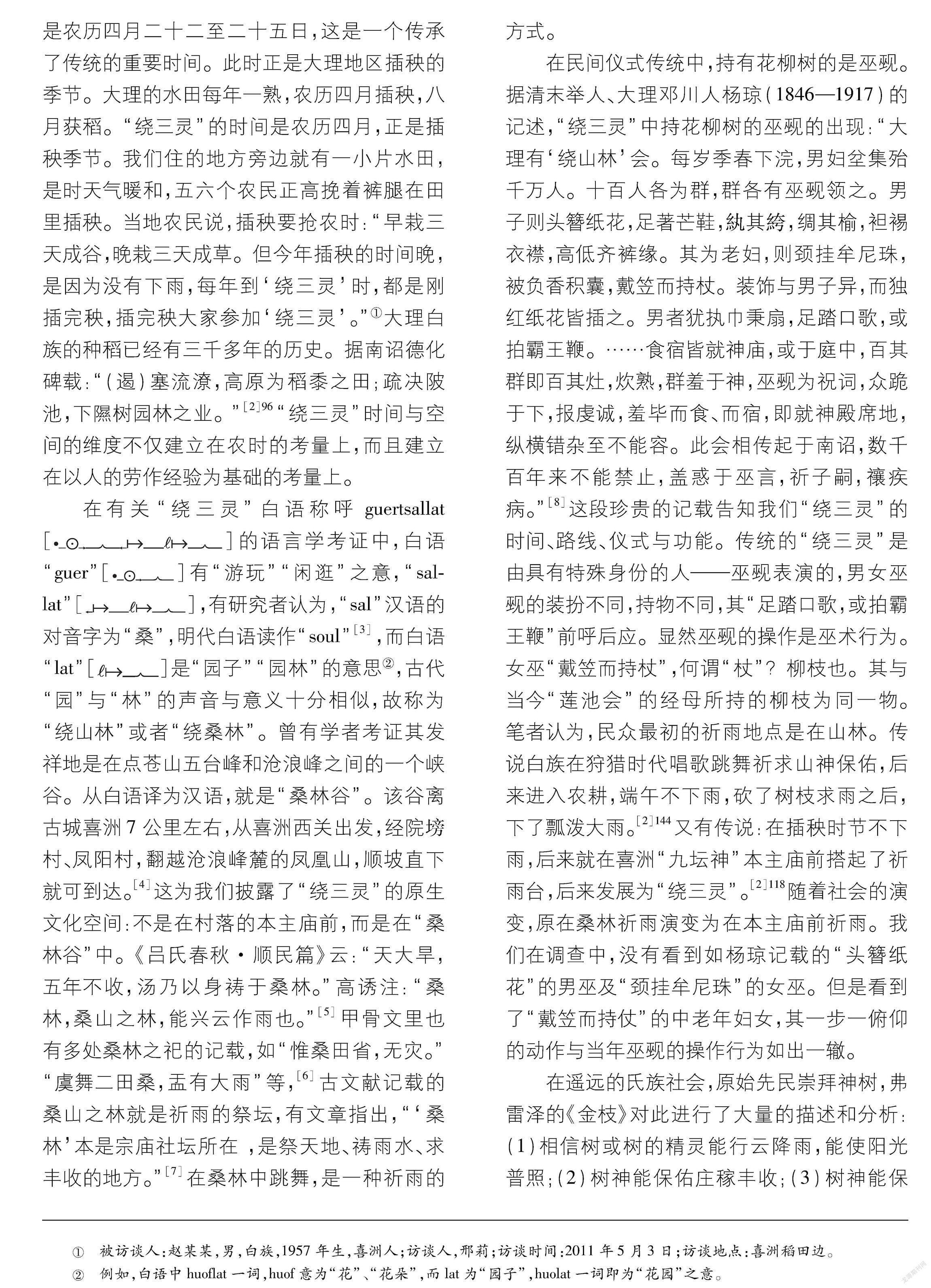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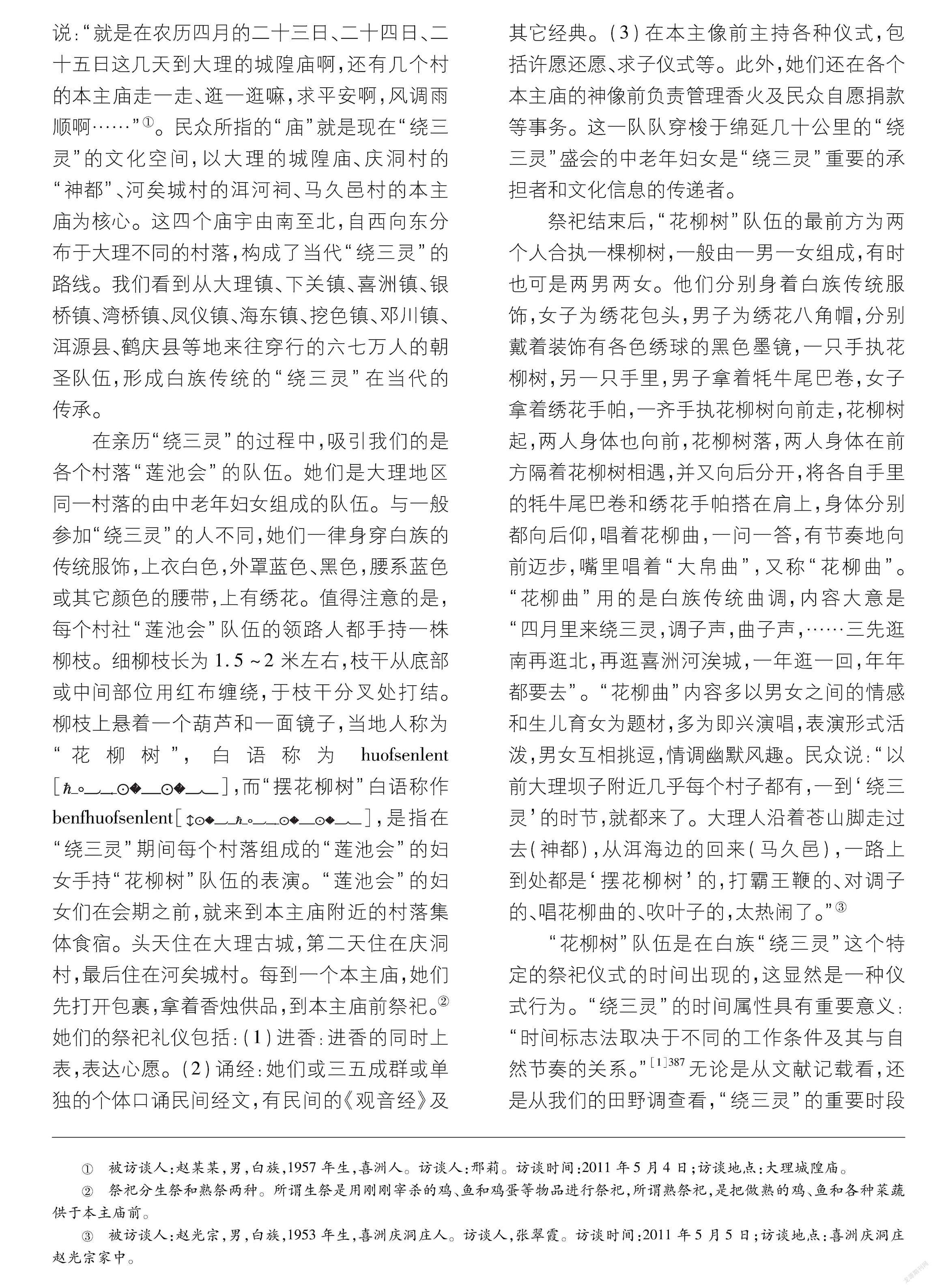
摘要:“绕三灵”是大理白族稻作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征。通过田野考察,从“绕三灵”的时空维度与大理白族稻作文化的关系可知,出现在“绕三灵”过程中的舞蹈、对歌、接送金姑等仪式表述的文化本相是祈雨。在“绕三灵”节日的“阈限期”内,婚外性行为可能存在,其构成了巫术祈雨功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原始文化思维的遗留,显示了“绕三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白族;“绕三灵”;本相;祈雨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2)01-0024-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2.01.004
大理白族“绕三灵”,白语称为[guertsallat]也称作“绕山林”“绕桑林”等。“绕三灵”起源于白族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和风俗传统。
2011年“绕三灵”前后,我们跟随当地民众足迹在大理镇、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等地进行了为时14天的田野考察和访谈:①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晨,村民到达古城的城隍庙,沿着点苍山麓向北,然后到佛都崇圣寺三塔祭拜,再行16公里,到达苍山五台峰下的朝阳本主庙祭祀,此为“南朝拜”;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向北到称为“神都”庆洞村的圣源寺,祭拜圣源寺和庆洞的本主庙,②这里供奉的是大理最大的本主,民众称为“北朝拜”;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从庆洞到洱海边河矣城村的洱河神祠,这里民众称为“仙都”,晚上有规模较大的对歌;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从河矣城村向南到大理城北洱海边的马久邑村,祭拜本主保安景帝。
一、“绕三灵”中“摆花柳树”的功能是祈雨
何谓“绕三灵”?我们在访谈中求解,民众说:“就是在农历四月的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这几天到大理的城隍庙啊,还有几个村的本主庙走一走、逛一逛嘛,求平安啊,风调雨顺啊……”被访谈人:赵某某,男,白族,1957年生,喜洲人。访谈人:邢莉。访谈时间:2011年5月4日;访谈地点:大理城隍庙。。民众所指的“庙”就是现在“绕三灵”的文化空间,以大理的城隍庙、庆洞村的“神都”、河矣城村的洱河祠、马久邑村的本主庙为核心。这四个庙宇由南至北,自西向东分布于大理不同的村落,构成了当代“绕三灵”的路线。我们看到从大理镇、下关镇、喜洲镇、银桥镇、湾桥镇、凤仪镇、海东镇、挖色镇、邓川镇、洱源县、鹤庆县等地来往穿行的六七万人的朝圣队伍,形成白族传统的“绕三灵”在当代的传承。
在亲历“绕三灵”的过程中,吸引我们的是各个村落“莲池会”的队伍。她们是大理地区同一村落的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队伍。与一般参加“绕三灵”的人不同,她们一律身穿白族的传统服饰,上衣白色,外罩蓝色、黑色,腰系蓝色或其它颜色的腰带,上有绣花。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村社“莲池会”队伍的领路人都手持一株柳枝。细柳枝长为1.5~2米左右,枝干从底部或中间部位用红布缠绕,于枝干分叉处打结。柳枝上悬着一个葫芦和一面镜子,当地人称为“花柳树”,白语称为huofsenlent[],而“摆花柳树”白语称作benfhuofsenlent[],是指在“绕三灵”期间每个村落组成的“莲池会”的妇女手持“花柳树”队伍的表演。“莲池会”的妇女们在会期之前,就来到本主庙附近的村落集体食宿。头天住在大理古城,第二天住在庆洞村,最后住在河矣城村。每到一个本主庙,她们先打开包裹,拿着香烛供品,到本主庙前祭祀。祭祀分生祭和熟祭两种。所谓生祭是用刚刚宰杀的鸡、鱼和鸡蛋等物品进行祭祀,所谓熟祭祀,是把做熟的鸡、鱼和各种菜蔬供于本主庙前。她们的祭祀礼仪包括:(1)进香:进香的同时上表,表达心愿。(2)诵经:她们或三五成群或单独的个体口诵民间经文,有民间的《观音经》及其它经典。(3)在本主像前主持各种仪式,包括许愿还愿、求子仪式等。此外,她们还在各个本主庙的神像前负责管理香火及民众自愿捐款等事务。这一队队穿梭于绵延几十公里的“绕三灵”盛会的中老年妇女是“绕三灵”重要的承担者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者。
祭祀结束后,“花柳树”队伍的最前方为两个人合执一棵柳树,一般由一男一女组成,有时也可是两男两女。他们分别身着白族传统服饰,女子为绣花包头,男子为绣花八角帽,分别戴着装饰有各色绣球的黑色墨镜,一只手执花柳树,另一只手里,男子拿着牦牛尾巴卷,女子拿着绣花手帕,一齐手执花柳树向前走,花柳树起,两人身体也向前,花柳树落,两人身体在前方隔着花柳树相遇,并又向后分开,将各自手里的牦牛尾巴卷和绣花手帕搭在肩上,身体分别都向后仰,唱着花柳曲,一问一答,有节奏地向前迈步,嘴里唱着“大帛曲”,又称“花柳曲”。“花柳曲”用的是白族传统曲调,内容大意是“四月里来绕三灵,调子声,曲子声,……三先逛南再逛北,再逛喜洲河涘城,一年逛一回,年年都要去”。“花柳曲”内容多以男女之间的情感和生儿育女为题材,多为即兴演唱,表演形式活泼,男女互相挑逗,情调幽默风趣。民众说:“以前大理坝子附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到‘绕三灵的时节,就都来了。大理人沿着苍山脚走过去(神都),从洱海边的回来(马久邑),一路上到处都是‘摆花柳树的,打霸王鞭的、对调子的、唱花柳曲的、吹叶子的,太热闹了。” 被访谈人:赵光宗,男,白族,1953年生,喜洲庆洞庄人。访谈人,张翠霞。访谈时间:2011年5月5日;访谈地点:喜洲庆洞庄赵光宗家中。
“花柳树”队伍是在白族“绕三灵”这个特定的祭祀仪式的时间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仪式行为。“绕三灵”的时间属性具有重要意义:“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奏的关系。”[1]387无论是从文献记载看,还是从我們的田野调查看,“绕三灵”的重要时段是农历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这是一个传承了传统的重要时间。此时正是大理地区插秧的季节。大理的水田每年一熟,农历四月插秧,八月获稻。“绕三灵”的时间是农历四月,正是插秧季节。我们住的地方旁边就有一小片水田,是时天气暖和,五六个农民正高挽着裤腿在田里插秧。当地农民说,插秧要抢农时:“早栽三天成谷,晚栽三天成草。但今年插秧的时间晚,是因为没有下雨,每年到‘绕三灵时,都是刚插完秧,插完秧大家参加‘绕三灵。”被访谈人:赵某某,男,白族,1957年生,喜洲人;访谈人,邢莉;访谈时间:2011年5月3日;访谈地点:喜洲稻田边。 大理白族的种稻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南诏德化碑载:“(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 ”[2]96“绕三灵”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不仅建立在农时的考量上,而且建立在以人的劳作经验为基础的考量上。
在有关“绕三灵”白语称呼guertsallat[]的语言学考证中,白语“guer”[]有“游玩”“闲逛”之意,“sallat”[],有研究者认为,“sal”汉语的对音字为“桑”,明代白语读作“soul”
[3],而白语“lat”[]是“园子”“园林”的意思例如,白语中huoflat一词,huof意为“花”、“花朵”,而lat为“园子”,huolat一词即为“花园”之意。 ,古代“园”与“林”的声音与意义十分相似,故称为“绕山林”或者“绕桑林”。曾有学者考证其发祥地是在点苍山五台峰和沧浪峰之间的一个峡谷。从白语译为汉语,就是“桑林谷”。该谷离古城喜洲7公里左右,从喜洲西关出发,经院塝村、凤阳村,翻越沧浪峰麓的凤凰山,顺坡直下就可到达。 [4]这为我们披露了“绕三灵”的原生文化空间:不是在村落的本主庙前,而是在“桑林谷”中。《吕氏春秋·顺民篇》云:“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高诱注:“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 [5]甲骨文里也有多处桑林之祀的记载,如“惟桑田省,无灾。”“虞舞二田桑,盂有大雨”等,[6]古文献记载的桑山之林就是祈雨的祭坛,有文章指出,“‘桑林本是宗庙社坛所在 ,是祭天地、祷雨水、求丰收的地方。” [7]在桑林中跳舞,是一种祈雨的方式。
在民间仪式传统中,持有花柳树的是巫觋。据清末举人、大理邓川人杨琼(1846—1917)的记述,“绕三灵”中持花柳树的巫觋的出现:“大理有‘绕山林会。每岁季春下浣,男妇坌集殆千万人。十百人各为群,群各有巫觋领之。男子则头簪纸花,足著芒鞋,紈其絝,绸其榆,袒裼衣襟,高低齐裤缘。其为老妇,则颈挂牟尼珠,被负香积囊,戴笠而持杖。装饰与男子异,而独红纸花皆插之。男者犹执巾秉扇,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食宿皆就神庙,或于庭中,百其群即百其灶,炊熟,群羞于神,巫觋为祝词,众跪于下,报虔诚,羞毕而食、而宿,即就神殿席地,纵横错杂至不能容。此会相传起于南诏,数千百年来不能禁止,盖惑于巫言,祈子嗣,禳疾病。”[8]这段珍贵的记载告知我们“绕三灵”的时间、路线、仪式与功能。传统的“绕三灵”是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巫觋表演的,男女巫觋的装扮不同,持物不同,其“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前呼后应。显然巫觋的操作是巫术行为。女巫“戴笠而持杖”,何谓“杖”?柳枝也。其与当今“莲池会”的经母所持的柳枝为同一物。笔者认为,民众最初的祈雨地点是在山林。传说白族在狩猎时代唱歌跳舞祈求山神保佑,后来进入农耕,端午不下雨,砍了树枝求雨之后,下了瓢泼大雨。[2]144又有传说:在插秧时节不下雨,后来就在喜洲“九坛神”本主庙前搭起了祈雨台,后来发展为“绕三灵”。[2]118随着社会的演变,原在桑林祈雨演变为在本主庙前祈雨。我们在调查中,没有看到如杨琼记载的“头簪纸花”的男巫及“颈挂牟尼珠”的女巫。但是看到了“戴笠而持仗”的中老年妇女,其一步一俯仰的动作与当年巫觋的操作行为如出一辙。
在遥远的氏族社会,原始先民崇拜神树,弗雷泽的《金枝》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和分析:(1)相信树或树的精灵能行云降雨,能使阳光普照;(2)树神能保佑庄稼丰收;(3)树神能保佑六畜兴旺,妇人多子。[9]在原始信仰里,树神信仰时常会与行云降雨联系在一起。对于“花柳树”有两种解释,一是“花柳树”代表树神,而持“花柳树”的人一俯一仰的动作为祈雨的仪式;另外一种解释是,“花柳树”代表最高之神天神。徐嘉瑞认为:“大理各村本主往神都时,其行列亦以树枝为先导,……男女各扶一树枝,似与巫教之杉、松、柿,同为代表最高之神。” [10]这里所说的最高之神就是天神,表示向天祈雨。白族学者认为:“白族自古以来的神树,通常由巫师来扶持,也是有巫的祈雨之意。”[2]90柳枝成为祈雨的象征物。人类学家认为:“象征有如隐喻,它或者借助于类似的性质,或者通过事实上或想像中的联系,典型地表现某物,再现某物,或令人回想起某物。”[11]在民间仪式中,自然物的树已转换为社会化和信仰化的树。人与树的关系由人与物的关系也变为人与神的关系, 并反映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 概括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社会生活内容,它会唤起强烈的信仰感情和功利愿望的联想。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巫觋是沟通人界与天界的媒介,他既代表人界向天神祈求雨水,又代表天界授意向人间降雨。 “有些巫术是公共行为,背后存在着公共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说,在巫术仪式中,整合社会环境都是激动的,部分祈雨巫术就是公开进行的。”[12]
在我们亲历“绕三灵”的过程中,手持花柳树的人行进在各个村落“莲池会”的队伍之中,也就是说,大理的周边有多少村落就有多少手持花柳树的人。花柳树又有社树之意。一自然村为一社。社既为土地又为掌管土地之神。《说文》解释“社”为:“土主也,从示土。”这里的“社”不是泛指的土地观念,而是特指这个村落的土地之神,即“立社建祠”之“社”立木是“社”的标识,花柳树又称“社树”。据白族学者考证,“古代生活于苍洱之间的白族先民有自己的丛社和神木。大体上以今天以大理城为中心的氏族或部落的‘所宜木是松,白语的对音为xout[ou];以太和为中心的氏族或部落的‘所宜木是柳,白语对音是[senen];以周城為中心的氏族或部落的‘所宜木是袥,白语对音是[sou]; 以喜州为中心的氏族或部落的‘所宜木是桑,白语对音是[sou],以后变音为[sa]等。”[4]大理白族的“绕三灵”是起源于古代氏族社会的祈雨文化。手持花柳树的人是代表种植这块土地的人向天神祈雨。白族学者认为“绕三灵” “民间也叫祈雨会”。[2]144在现代的“花柳树”队伍的仪式中,再现了古代文献中“桑林祈雨”的文化记忆。21世纪进入田野调查的学者,只能从“绕三灵”的衍生态,追溯其文化本相。
二、 “绕三灵”中的性表述与祈雨
遍及大理各个村落的本主庙是大理白族日常生活的神圣空间。村落“莲池会”“摆花柳树”的表演是在神圣庙堂前进行的。在庆洞神都、河矣城洱河祠、马久邑村这三个本主庙前,我们还看到不同村落多个“莲池会”的妇女队伍在“绕三灵”这个特殊的情境中展演的是花柳曲舞、霸王鞭舞、金钱鼓舞、双飞燕舞等舞蹈。霸王鞭舞是舞者用金钱鼓击打身体的某部位,“霸王鞭舞”是手持二尺长的霸王鞭在本主庙前的舞蹈。霸王鞭是用直径大约3厘米的、长约66厘米的木棍,上缠画纸,棍上拴有铁片,哗哗作响。 我们看到,跳舞的妇女用霸王鞭拍打着各个部位,眼看着霸王鞭上下翻飞,目不暇接,伴随着舞者尽兴尽致、酣畅淋漓的表演,鼓面上的铜钱有节奏地哗哗作响,身体的各个部位主动迎合。一位被访问者说:“敲、碰、靠、扣、划等打法,或与他人互打,都要做到背靠背、心合心、脚勾脚,……马虎不得。”被访谈人:赵光宗,男,白族,1953年生,喜洲庆洞庄人。访谈人:张翠霞、邢莉。访谈时间:2011年5月5日。访谈地点:喜洲庆洞庄赵光宗家中。 “霸王鞭舞”的动作是拍手接臂、拍足接踵、拍头接颈、拍腰接股。“最基本的动作是脚勾脚、心合心、背靠背等”,“白族民歌形容这种舞蹈动作‘像邓川(地方)乳扇脚绞脚,如姜寅红糖心连心”[2]8人们往往以“欢快”“跳跃性强”来描述“绕三灵”的舞蹈,并其视为艺术。不可忽视的是,霸王鞭舞等舞蹈在“绕三灵”特殊的时空维度中,是在大理地域的本主庙前展演的,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娱乐,而属于祈雨的仪式范畴。前面所说的柳枝是神圣的树崇拜的象征,这种背靠背、心合心、脚勾脚的肢体动作是世俗表演的象征,其象征符号后面具有寓意。
世俗的象征符号还出现在“绕三灵”的对歌过程中。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来到喜洲庆洞村神都本主庙后面的山坡疏林,观看到两两对歌的情境。敬完了各庙的本主之后,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本主庙后边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这里树木并不茂密,但是偶有阴凉。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或者一个女子走着走着,停下来敞开嗓子,放声唱歌,接着就有一个男子或者女子应答,这样就结成了对歌的伙伴关系。曲子是人们平时生活中熟悉的白族调,而歌词却完全是即兴而起,即兴而唱,唱山则情满山、唱水则情溢于水。有一对歌手,年青的男子一出口,年纪稍大的一位女子马上应答,唱四时物候,唱农田耕作,唱男女情爱,其问得快,答得疾,既有情有义,又幽默风趣,两方均绞尽脑汁,努力压倒另一方,而另一方又往往妙语连珠,压倒对方,巧妙的问答,博得周围人的声声喝彩。访谈过程中,当地人称对歌要有“肚才”,别人最后一句没唱完,你要应答的歌词就胸有成竹了。这就要求演唱者既要会唱,熟悉各种曲头韵律,更要才思敏捷,有生活知识。对唱中多有衬词,衬词的“呀”“嚒”等不仅使得声调高低错落,还使唱词显得悠扬绵长,给了对歌者思考的间歇。我们观察到,对歌是在一男一女异性之间进行的,没有看到同性男女两两对歌的情境。对歌人的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不等,但是歌手的年龄并不一定匹配,有的男大女小,有的男小女大。对歌似乎有一个程式,男子称女子“小妹”,女子泛称男子为“阿哥”。男子想邀请一个女子对歌往往以“小妹小妹你听着”开头。如前所说,歌词的内容非常丰富。与一般的情歌不同,对歌出现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婚外情内容。例如:
男:小妹呀,想你想你想死我啊,今晚遇着嚒小妹你呀,唱完调子跟你去啊,
小妹你要啊招待我。
女:阿哥呀,这句话来说对喽呀,唱完调子嚒跟我去呀,我家的老哥多贤惠呀,
出来的时候交代妹呀。
男:小妹呀,我想你来嚒你想我,想起小妹睡不着呀,唱完调子嚒跟你去啊,
快到你家嚒你安排我。
女:阿哥呀,这句话来说对喽呀,唱完调子嚒跟我去呀,快到我家嚒我安排 。
再有一首:
男:小妹呀,小妹的人才实在好,小妹仁义嚒又贤惠呀,把我小哥嚒到你家呀,
你把小哥嚒安排好呀,只要我俩心连心呀,我还不怕你老公呀。
女:阿哥呀,既然小哥这样说呀,大胆跟我去我家呀,快到我家嚒我安排呀。
我们访谈了在大理湾桥南庄住的一位50多岁的妇女,她开朗、热情,而且还脱口唱出了婚外恋的情歌。我们问她为什么会有婚外恋的情歌,她说:“这些歌,就是这个时候唱,平时是不唱的,這个时候可以唱,……这么大岁数,竟唱那个,……不好意思嘛,我就带个墨镜。”当问到她的爱人是否支持她唱的时候,她爽快地说:“他知道嘛,可以嘛,就是在‘绕三灵的时候耍一耍嘛。”被访谈人:段某某,女,白族,50多岁,喜洲庆洞庄人。访谈人:张翠霞、邢莉。访谈时间:2011年5月9日。访谈地点:段某某家中。 与婚外恋的对歌相呼应,在神都的墙壁上有当地文人撰写的对联:
看苍山青翠,洱滨柳荫,正好绕山穿林,唱起俚曲山歌,大家及时行乐; 际熏风解愠,纪野陶情,何妨吟风弄月,鼓舞风流韵士,须知盛会难逢。
绕山又绕林,看红男绿女,一路花飞蝶舞,歌唱互答,极尽赏心悦事;胜迹传胜会,彼游人香客,满载风流豪兴,陶醉欲狂,诚为悦目大观。
神都墙壁上的对联是世俗男女陶情风流的表述,不排除在绕山又绕林期间相恋的内容。明代李浩《三迤随笔》中有《蒙段时俗》记载得非常明确:“时男女不分老少,唱曲游山玩水三日。日间群游各觅佳侣,入夜双栖双宿,苟且之事。河蛮之俗,合欢会夜,男女萍水共宿,多一夕之会而孕育。当事者一夜鸳鸯,故不知子属于谁,多有人在。故古河蛮之陋俗,沿至蒙氏。”
[13]我们考察,“绕三灵”对歌的内容纯属口头戏谑,并没有婚外性关系的发生,但是并不能说明历史上没有这种社会情境。当地文化学者认为,“‘绕三灵男女情人相会互称对方为‘活恩尼,其他人也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他们。……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活恩尼在特殊的时间和场合,可能被白族的社会道德所默许。”[2]99白族学者承认,在“绕三灵”期间可能出现婚外性行为的社会事实,对此文化现象出现了多角度阐释。有的认为,这是研究古代婚俗文化的活资料;有的认为这是以求子嗣为目的,以野合为现实手段的活动。有认为,“绕三灵”是白族的情人节,是旧时代婚姻不自由的追忆,而在“绕三灵”期间可以与相恋的情人会面(参见杨宴君、杨政业主编:《大理白族‘绕三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115页、186页)。
我们认为传统的“绕三灵”出现的“活恩尼”的情境与祈雨存在必然的联系。弗雷泽在《金枝》中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巫与巫术,他把“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列为单独的一章论述。他特别谈到,在新几内亚西端和澳大利亚北部之间的落蒂、萨马他等地域,地球作为女性的本源,要有男性的太阳给女性的地球受精,地球才能生育繁殖。而神圣的无花果树是降临太阳的天梯。届时“男男女女都一齐纵情狂欢。太阳和大地的神秘的交合就这样公开地在歌舞声中,在男男女女于树下真正进行的性交活动中戏剧性地体现出来。听说这种节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向太阳祖宗求得雨水,求得丰富的饮料和食品,子孙兴旺,牲畜繁殖,多财多福。”[1]138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认为:在农业的节日里,世界各地都有男女性交的例子。如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任何禁止女人淫乱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图和观念都会危害农业丰产。[14]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在原始社会,男女性交并不是单一的性行为,而是另有巫术的功能。白族先民为了实现渴求雨水、获得丰收的目的,以男女交合促进天地交合而激发甘霖的降落。弗雷泽认为,无论是模拟巫术还是接触巫术都属于交感巫术,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相互作用。[12]140 “绕三灵”中的性表述不是古代婚俗制度的遗留,更不是由于过去时代婚姻不自由而产生的情人节,“绕三灵”中性行为的目的在于求雨。“绕三灵”的祈雨与祈子构成同位同构,互促互生的关系,这是“以自己的心理互渗出集体表象的世界。”[15] “绕三灵”的集体仪式是公共表征的符号,它代表心理意愿的文化逻辑,属于民众的信仰层面,“如果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语汇,这应该是不同于现代人的思考习惯的一种理性,是另类的,但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16]
随着社会的演化,原始社会的文化基因逐渐被遮掩淡化,表现在:一是“绕三灵”的求雨空间从田野山林置换到本主庙;二是求雨的对象从天神、山神、树神转化到各个村落庙的本主;三是随着时间的演化和社会的变迁,杂糅了当代社会求平安、求财、超度亡灵等内容。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出,在现代“绕三灵”民间实践行为中还存在鲜明的祈雨文化的因子,目的是希冀稻谷丰收。在“绕三灵”的传承中,可以追溯到原始巫术行为的遗存。“绕三灵”是大理地区稻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征。
与祈雨仪式相对应的还有关于祈雨口头传说的不断建构。在我们的调查中,搜集到10多个流传至今的祈雨传说。包括:(1)向山神祈雨;(2)向皇帝祈雨;(3)向龙祈雨;(4)县官向段赤城祈雨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传说,也见到散见的文字资料。详见张云霞:《金姑的背影——大理绕三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189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绕三灵”经历了从自然神崇拜到人神崇拜的过程。在当代传承的包容性很强的本主信仰中,仍旧有祈雨文化因子的遗存。祈雨传说的存在不仅表达了传统的需求,同时又活态地建构了当今的社会现实。大理人在农历四月末插秧后期望雨水而求得稻谷丰收,这就是“绕三灵”的文化本相。
三、镶嵌在“绕三灵”中的金姑传说、仪式与祈雨
在阐释与日常生活相区别的仪式生活的时候,范热内普对“边缘礼仪”的界定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阈限性” (liminality),对于节日、仪式、庆典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范热内普提出的“边缘礼仪”或“阈限礼仪”认为从一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过渡进程分离或降低于正常社会活动。[17]无疑,参与“绕三灵”的白族民众在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进入了一个“阈限期”[18]96。在这个“阈限期”内,村民暂时离开了自己日常的村落生活,参与了集体的具有规模的仪式,特别是民间组织“莲池会”的中老年妇女暂时脱离了日常生活,进入了“阈限期”或称“反结构”状态。在访谈中得知,白族传说中的历史人物金姑与驸马也参与了“绕三灵”,即他们也进入“阈限期”。
大理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金姑为大理喜洲白王张乐进求之爱女,因被父亲责罚而离家到苍山保和寺被巍山来的猎人细奴罗搭救,遂嫁给他为妻。白王被观音点化,得知实情。由于金姑的丈夫细奴罗文武双全,被选为新王。金姑驸马回大理娘家探亲,金姑独自回喜州看望父母姐妹,细奴罗在保和寺等候一时,没有等到金姑的细奴罗独自先回到巍山,之后大理人送金姑回到巍山,二人愉快地生活。民众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接送金姑驸马”传说,并且把这个传说的展演纳入到“绕三灵”的仪式之中。
有否金姑其人?无文献记载。在公元7世纪中叶,白族的大姓张乐进求、仁果的家族先后建立“大白国”“拜国”“建宁国”等古代酋邦性质的国家。对此《南诏野史》有载,《南诏图卷·文字卷》还有文图并茂的展示。传说金姑是张乐进求的女儿,与细奴罗成亲。传说有历史的影子,而传承至今的“迎送金姑”及“送驸马”的活态仪式反复呈现,反复强调金姑驸马“真实”存在的历史传统。我们研究的不是传说与历史的对接,人类学和民俗学要探讨的是历久弥新的传说在当下生活中存在的缘由。
金姑与细奴罗与神都供奉的本主段宗牓一样在大理白族的本主信仰之行列中。据《僰古通记》记载,段宗榜牓南诏中期统帅,曾任南诏国清平官。“绕三灵”节日核心地点被称为“神都”的圣源寺奉祀的主神“灵镇五峰建国皇帝”即是段宗榜:被奉为大理最高本主“中央皇帝”。 在马久邑村的本主庙中,我们看到金姑娘娘的塑像;其面目清秀,身着白族的传统服装,发饰装扮是典型的白族少女。金姑像前有供品和香炉纸花之类,表明当地人对她的尊崇。金姑呈现了世俗与神圣两种身份。一方面,她被大理村民认同为出嫁的闺女,为真实的人;另一方面,金姑又被崇拜為本主,是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神。民众说:“金姑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后来嫁到巍山去了,每年她都要离开驸马,回娘家看看。金姑可善良了,平时有事情,比如生病啦,妇女要想生孩子啦,求求她,可灵验了。”被访谈人:段某某,女,白族,50多岁,喜洲庆洞庄人。访谈人:邢莉、张翠霞。访谈时间:2011年5月9日。访谈地点:段某某家中。 “绕三灵”中出现的每年一度的拟真实性的游神巡演,就是人与神沟通的最佳时机,此阶段,接送金姑驸马的民众也同时处于神圣与世俗交替的时空之中。
时间和空间的选择是解读“绕三灵”的重要关键。“绕三灵”的关键时段是3天,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开始就拉开序幕,大理白族妇女前往大理巍山垅圩图山的金姑庙迎金姑的塑像回大理,至农历二月十五日迎到下关七五村本主庙,二月二十六日迎至大理湾桥,二月十七日回到庆洞神都。农历三月三日先送金姑的丈夫细奴邏回巍山,四月二十五“绕三灵”结束后,送金姑回巍山。金姑从婆家——娘家——婆家的行程贯穿了“绕三灵”的全过程。在“绕三灵”中,对于金姑来说从巍山(婆家)到大理(娘家),再回到“巍山”(婆家)是一个“阈限期”。这就使得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即社会结构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 (旧有形式)中分离出来。[18]95,而农历四月末的“绕三灵”,只是“金姑娘娘”传说实践体系中的一部分。即“四月修行二十三/善男信女去烧香/合会弟子来朝贺/送金姑娘娘”。
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个“过渡礼仪”或称“阈限期”之内,驸马没有见到娘家人,在保和寺等候不到金姑,细奴邏独自先回巍山。也就是说,金姑与驸马之间有一个分离期。为了造成金姑与驸马的暂时分离的合理性,民间传说有三种解释。一说驸马长得丑,不愿与金姑一起回去;二说驸马认为自己未经金姑父母同意,就与金姑婚配,觉得无脸面对金姑父母;三是说驸马公细奴罗已经是南诏王,张乐进求禅位于他,但是相见之后岳父要对他行君臣之大礼,细奴罗觉得不过意,拒绝与金姑一起回去。以上三种不同而又都符合道德伦理的解释,在被视为“真实”的民间传说中,反复强调金姑在回娘家的日子参与“绕三灵”,均在于说明,在“绕三灵”期间,金姑与驸马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分离期,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分割的过程,也就是处于“边缘”的境遇中。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阈限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金姑与驸马同时参与了“绕三灵”仪式,进入了仪式的阈限期;另一层是金姑与驸马暂时分离,他们各自进入了自己的阈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