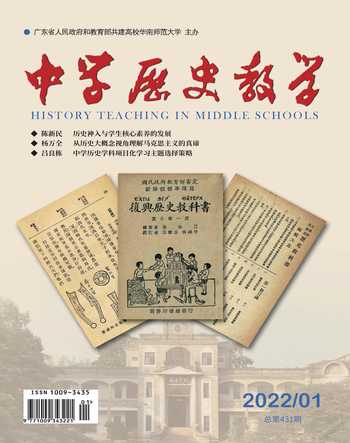关注新教材的隐性主线
2022-02-14张兆金
张兆金
新教材以史事发展形成叙事框架,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中交相辉映,但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如何讲完、讲好一课时的教学任务不免令人焦虑。应对新教材,教学要有新思路。崔允漷教授认为,新课程要求教师必须提升教学设计的站位,即从关注单一的知识点、课时转变为大单元设计,实现教学设计与素养目标有效对接。[1]笔者认为,大单元设计的核心是抓住串联知识的主线,尤其是应关注新教材的隐性主线,并把所学知识迁移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以中国古代史为例,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实,这两条主线的背后,都隐含着民族关系的发展与民族政策的演进。如果在教学中发掘并与主干知识相关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一、两汉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与民族交融
战国后期,匈奴在众多游牧民族中脱颖而出,占据河套地区。秦统一后,秦始皇派蒙恬率领30万大军把匈奴赶出河套地区,并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修筑了西起陇西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
秦末汉初,匈奴卷土重来。“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2],对西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白登之围”后至公元前133年以前,西汉被迫实行“和亲”政策。此后的十余年间,汉武帝对匈奴发起了大规模的武力反击。为了抗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密切了与西域的联系。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又实施盐铁专卖、收归铸币权等措施。汉宣帝时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确立了西汉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但有一点要讲清楚,西汉一直严格奉行禁止少数民族内迁的铁律,少数民族被牢牢地限制在秦长城以外的地区。
东汉初,匈奴再度崛起并控制西域。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为减少匈奴南下侵扰造成的损失,省并了北方八个边郡,将官民迁入长城以内。另一面打破铁律,允许少数民族内迁。尤其是48年,匈奴分化为南北两部,对南匈奴主动附汉的请求,“因其故俗”以资安置。少数民族得以迁入长城以内和黄河流域一带居住。汉明帝非常重视儒家教育,推动匈奴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教化。匈奴与汉族杂处,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使其原有的文化风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匈奴本有“贵壮健,贱老弱”,使“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习俗。[3]入塞后接受了中原汉人“孝”的风俗思想。91年前后,北匈奴在东汉的征伐之下彻底溃败,但出乎意料的是助推了鲜卑的兴起。
二、三国至两晋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与正朔之争
三国至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内迁。如三国时期,鲜卑迁到了辽宁、陕西及河套地区。到了西晋末年,氐族由西向东迁入陕西关中,匈奴和羯族,则由北向南迁到山西一带。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南下,河套以南地区已成为羌胡的天下。[4]少数民族为什么要内迁?竺可桢认为,三国到六朝时期中国正处于长期的低温期,这与北方各族内迁中原的时间节点一致。[5]此外,从曹魏至西晋,中原地区人口锐减,为了补充劳动力和扩大兵源,大量少数民族被迁入内地。一个是主动内迁,一个是被动内迁,讲清楚这两点,教学更通透。
280年西晋实现了统一。内迁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腹地靠近,甚至距洛阳不过百里,此时的民族关系成為西晋最为棘手的问题。一些官员主张“徙戎”,即把内迁的各民族一律迁回故土。三国、西晋虽沿用了秦汉的政治制度,但在民族政策上没有与时俱进,西晋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内迁的少数民族成为士族大地主的佃客,遭受剥削,并承担了西晋沉重的赋役、徭役,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内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相处,文化交融,形成同源共祖的华夏认同。“八王之乱”后,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乱华”的局面。西晋灭亡后,各族趁乱纷纷建立政权,将自己视为正统国家的代表,采用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借鉴汉族的典章制度,统称为十六国。东晋建立后,一大批中原士族“衣冠南渡”,自诩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至此,中国进入历时270余年的大分裂时期,起初是东晋十六国,之后是南北朝的对峙。当时,无论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汉政权都将自己视为正统国家的代表,一度产生正朔之争。
此时的北方,活跃着魏晋时内迁而来的鲜卑拓跋部。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孝文帝改革是民族关系发展中的适时革新,缓和了民族矛盾,顺应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民族交融是双向的,理解其深刻内涵是教学的重点。孝文帝之后,北方经济持续发展,南北文化趋向一致,为北方最终统一南方奠定了基础。
三、隋唐实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
隋朝建立时,东北的契丹、秣褐,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谷浑,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尤其是北方草原的突厥最为强大。突厥尚武,风俗特别,一是采用火葬,二是在墓前立杀人石。突厥击败了多个强大的对手,统一了草原。583年,隋朝趁突厥内讧发动北伐,致其分裂为东、西两部。这为隋朝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隋朝奉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如隋炀帝时强调“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隋朝诸族一家的民族开放思想。[6]“华夷之辨”为基调的民族思想,逐渐被“华夷一家”的主流思想取代。这是民族政策走向成熟的表现。
隋朝末期,突厥人趁乱进入中原。唐朝建立时,当时甚至出现“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的局面。[7]突厥成为唐初的最大威胁。630年,唐朝歼灭东突厥汗国,后又联合回纥灭西突厥。唐继隋制,也实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当然也有创新。如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护府下的各州,唐朝均任用当地部族首领。实行册封制度,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典型。唐朝传统的民族观念逐渐被“中华”所取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初认同得以实现。唐太宗曾自信坦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8]陈寅恪说的更形象,即“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9]要理解隋唐的盛世,了解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十分必要。
隋唐的民族政策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受鲜卑、突厥等族的影响,收继婚盛行,改嫁成风。隋唐汉族女子服饰吸取了胡服衣身较窄的特点,显露出女性的曲线美。可以说,隋唐制度的革新正是适应了民族关系的发展,由此带来了盛世局面的出现。
四、宋元时期由并立到统一
辽宋夏金元对峙局面持续了400余年。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汉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一体化的趋势增强,但对宋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因奉行重文抑武,重内轻外的“祖宗之法”,导致拥有强大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处于下风。宋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甚至为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不惜以钱、物的赏赐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也是贯穿整个古代史的一条主线,应力戒汉族中心论和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影响。[10]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吸收中原制度和文化、协调民族关系的同时保留自身特色,其开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并视自己为轩辕的后代。辽占据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其治下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了实行有效统治,辽官分南北,因俗而治。凭借强盛的国力,辽与北宋以及后来的西夏长期并立。原本臣服北宋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党项族也认为与汉家同为炎黄子孙、夏后氏的苗裔,将自己建立的皇朝命名为夏国。西夏的政治与典章制度基本模仿北宋,官职名称却保留本民族的称呼。西夏也推行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为命题范围,考生不限地域,唯才是举。如此一来,北宋落榜的考生便纷至沓来,促使北宋广开取士。1115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金国,打破这一并立的局面。在50年内相继灭辽和北宋,臣服西夏,与南宋对峙。金朝在地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又沿袭隋唐以来的科举制,青睐汉族官僚知识分子,以及南宋出使金朝的官员。女真皇帝禁止将女真族称为“边塞”民族,表明他不愿意人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11]尽管统治者力图保持民族特色,但绝大多数女真人说汉话、穿汉服、用汉姓,与汉人通婚,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实现了由并立到统一。面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现实困境,该如何有效治理呢?其一是设立十个行省,强化了对边疆控制。其二是设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吐蕃地区,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加强对西域的管辖,还设置澎湖巡检司,经略台湾。元朝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唐朝“所谓羁縻之州”,到元朝“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2]在大一统之下,融合形成回族的前身——回回,全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然而,元朝将全体百姓分为四个等级制度,具有民族歧视和压迫色彩,与大一统相比,元朝呈现出汉化迟滞的特点。蒙古族也因此在元朝以后长期保持自身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五、明清时期民族政策更加成熟
明朝面对少数民族数量多、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等问题,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如对蒙古族采取防御的政策,沿着原幽云十六州北境修建了坚固的长城,设置九边重镇。为了削弱女真族的力量,一方面实行分化政策,设立努儿干都司负责管理女真族,另一方面进行安抚,在经济上互通商市。
清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更加成熟。清朝统治者秉持“华夷一家”、“中外一体”的民族与国家理念,对内地采取行省制,边疆设置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物,对西南则实行改土归流。通过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置驻藏大臣、金瓶掣签和颁布法律等,明确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对西北则在康熙时平定蒙古准噶尔叛乱,在蒙古地区设立盟长、旗长;乾隆时平定维吾尔大、小和卓叛乱,在新疆地区设立伊犁将军,总领军政事务。对此,雍正曾豪言壮语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13]“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策对清朝稳定边疆具有重要意义。
关注并寻找新教材的隐性主线,这是上好历史课的关键。其实,隐性主线往往隐藏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学识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如此,才能让知识在隐性主线的架构之下变得灵动而有意义,从而推动深度学习。
【注释】
[1]崔允漷:《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上海教育科研》2019年第4期,第1页。
[2]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50页。
[3]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9页。
[4]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第36页。
[6]《隋书·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69页。
[7]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8]《资治通鉴(198)·唐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7年,第6247页。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10]徐蓝、朱汉国主编:《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86页。
[11][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12]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2页。
[13]《清世宗實录》卷83,转引自刘晓东:《“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