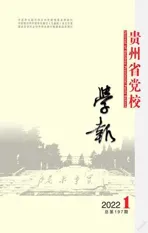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体系化思考
2022-02-13王雪梅
摘 要: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了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基本框架,因此有必要对分级干预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制度体系建构做一整体性思考。本文首先从分级干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总体格局的历史形成这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对罪错少年进行分级干预;其次,对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原则、根据、措施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再次,从法律制度和相关机制的完善视角对分级干预制度体系化建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罪错少年;罪错行为;分级干预;儿童福利;保护处分;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92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2)01 - 0119- 10
一、问题的提出
罪错少年并非正式的法律概念,是指出现了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而需要进行教育矫治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指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其健康发展的行为,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对少年罪错行为的分类和具体表述有很大不同。比如:美国少年法中的越轨行为大体相当于罪错行为,包括身份犯行为(违法或违规)、犯罪行为;日本将罪错行为分为三类,即虞犯行为、触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我国也有论者建议将罪错行为分为少年犯罪、触法行为、虞犯行为与违警行为。[1]根据2021年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其中,不良行为指未成年人实施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行为。这类行为具有自害性,如果不加以及时纠正有可能发展成为危害社会的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指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法规定但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的治安违法行为。
从上文的概念解读可以看出,少年罪错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触法行为和治安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基于这些行为人的特点(年龄及身心发育不同),以及行为性质的不同,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处遇措施,因此,分级处遇(干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是,干预或处遇的性质,以及如何干预则是存在争议的。关于“干预”的性质到底是保护性治疗措施还是惩罚措施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干预”更接近处遇、矫治、介入,带有少年司法的特色。那么,针对罪错少年不同程度的罪错行为和个体特点,如何进行矫治和康复就成为解决犯罪预防和促进其正常社会化的归宿。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罪错行为和不同个体采取何种具体的矫治措施,比如心理矫治等;二是基于罪错行为的不同性质要有一种体系性思考和设计,采取分级干预的体系建构也是本文的落脚点。本文所谓分级干预体系,是指根据不同年龄和罪错行为,针对罪错少年的心理偏常程度、人身危险性,采取不同级别的个别化干预方式,以促进未成年人完成社会化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对于罪错少年分级干预问题,国外关于罪错少年矫治的理论、实证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建构相关制度体系提供借鉴。从总体上看,国外的相关研究强调教育的自由与人本理念,对罪错少年矫正多基于帮助其重返社会,采用非监禁手段。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但是,总体而言,研究多集中于刑事法制和行刑社会化方面,而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以制度体系为视角所做的研究尚比较欠缺。况且,具体的国情不同也宜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罪错少年分级干预涉及的价值、目的、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将对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法律制度完善,以及相关机制构建提出建议,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罪错少年分级干预体系。
二、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价值和因由
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冲动性等特点,以及少年司法追求的特别保护、促进其全面发展和复归社会等价值目标,揭示了对罪错少年进行分级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所展示的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格局,进一步強化了分级干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少年司法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分级干预的必要性
对目的和价值的追问,关系着该制度的整体风貌,制度变革无不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在思考为什么要对罪错少年进行分级干预的时候,必然涉及对其价值的思考。罪错少年分级干预作为少年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其价值考量不能脱离少年司法的价值追求。[2]除了与少年司法有着一致的价值追求之外,罪错少年分级干预制度也有其具体的目标价值,主要集中于预防犯罪和促进罪错少年顺利社会化。儿童社会化是儿童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个体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儿童在不断地与周围的人或事物等发生相互作用中,形成了积极的自我认知,发展与他人之间有效的交流能力并顺利实现了社会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一定概率会出现儿童心理行为偏常,其中就包括攻击性行为、偏常行为等罪错行为。此时,他们的社会化遇到了障碍,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促进他们正常实现社会化。[3]因此,对出现罪错行为的少年如何进行干预矫治就成为少年司法独立发展以来的重要课题。
尽管“有错必纠、有罪必罚”符合一般的正义观念,但是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进行惩罚(制裁)既缺乏正当性,通常来说也无效,这已经为科学研究和少年司法实践所证明,所以,刑罚对罪错少年应当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应更多地采取教育矫治措施,特别是在“错”的阶段及时尽早介入,以防止进一步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当然,分级干预制度并非一味强调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之所以要采取分级干预的模式,是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性质的罪错行为不应当采取一体的保护模式,特别是对于其中年长的犯罪少年在进行积极矫治的同时,让其承受一定的惩罚亦有其必要性。比如,美国少年司法中的移送管辖制度的设定,除了矫治以便助其回归社会之外,还有社会防卫方面的考量。当然,这里的社会防卫与单纯以惩罚为目的的古典社会防卫有所不同。法国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的“新社会防卫论”,主张通过保护犯罪人实现保护社会的目的,以教育方法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通过人格矫治促进其重新社会化。[4]少年刑法中的保护主义理念是安塞尔“新社会防卫论”的最大特征之一。[5]因而,教育矫治、人格调查、多种非刑罚措施一体运用等,目的是促使罪错少年顺利社会化,这既是对少年的保护,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二)儿童发展理论及差异性理论揭示了分级干预的可行性
儿童发展理论不仅揭示了儿童个体之间的不同特点,还揭示了儿童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儿童发展是遗传、神经生理成熟、气质等个体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等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儿童发展形成的不同特点不仅有生物学的根据,也有社会学的根据。儿童的环境敏感性不同,从而受到环境影响的大小就不同,而且儿童成长面对的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形成了儿童的多样性发展。[6]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有大量的发育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加以论证。总体而言,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顺序具有一致性。[7]特别是皮亚杰(Piaget)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揭示儿童在每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的不同特点。[8]关于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相关权利保护,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的若干一般性意见也有解释。比如,委员会指出,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积极和扶持性的机会,可用来抵消幼儿期遭受伤害所造成的部分影响,并培养能够在今后减轻伤害的适应能力。因此,委员会要求父母以符合儿童不同时期接受能力的方式提供指导和指引。差异性理论也揭示,儿童作为向成年阶段发展的必要人生阶段,也必然带有自身的特点而与成年人存在差异。有关神经科学研究证明,儿童在向成人过渡的过程中,青春期是大脑与心理行为逻辑相关联的区域迅速发育期,形成了青春期少年特有的心理行为特点,比如,规划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弱、冲动和冒险行为、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等,由于青春期少年不成熟和可塑性强,对其偏差行为和心理进行矫治能够对其后的发展产生不断的影响。[9]此外,有关少年犯罪的研究也发现,实施犯罪行为的大多数少年常常有不良行为甚至严重不良行为,对这些不良行为如果不趁早及时干预,会逐渐恶化为更严重的违法行为甚至犯罪。
综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及差异性理论揭示了对少年罪错行为应当及早干预、及时干预、分级干预。儿童发展理论和差异性理论的研究,为处置少年罪错行为提供了重要指引:一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不可忽视性。儿童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警示我们,对儿童行为和心理的正向引导,不能仅仅关注罪错少年甚至采取刑罚的措施,而需要优化其成长的生态环境,修复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促进亲社会行为,成长为守法公民。二是未成年人的偏常或越轨行为的爆发具有阶段性的特点,集中在身体发育迅速和心理发展不稳定的青春期,有些越轨行为的发生率在成年后可能会急剧下降甚至消失,但有些罪错行为如果不给予及时干预,对塑造其健康人格将带来负面影响。
(三)少年司法发展展示出分级干预的总体格局
广义的少年司法不仅包括少年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狭义少年司法制度,还包括以矫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为核心的犯罪预防法、研究犯罪行为的犯罪学及少年矫正法。少年司法的广义性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的突出特点,是建构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观念基础,从少年司法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治理而形成的分级干预格局。
在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诞生之前,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一直被像成年犯一样对待,无所谓分级干预。19世纪末叶,人们对儿童和不良少年这一群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认识到制裁的威慑力对那些分不清对错的少年没有作用,应当免除年幼孩子的刑事责任,对于困境儿童和少年罪犯来说,社会是有责任的。于是,1899年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无人照管、忽视及罪错儿童处遇和监管法令》出台,同时,美国芝加哥成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这个机构当时是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刑事司法体制中转处的替代物,解救困境儿童是少年法院的初衷,其教育矫治措施不具有惩罚性,旨在改变罪错少年的不良心理与行为,并促进其个体发展与增进其未来福祉。就此点来看,少年法院实际上成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监察失败家庭儿童的移管和处遇,并辅之以学校教育、童工改革、母亲津贴等福利措施,实现防止少年罪错和无人照管的目的。[10]33-41可见,少年司法建立之初的目的,意在救助失足少年、矫治不良行为和预防犯罪。美国独立少年司法改革运动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少年司法的发展。比如在英国,尽管像美国一样,各司法辖区关于少年司法的改革进程也有差异,但一般而言,少年犯罪案件由少年法院管辖,对极其严重的犯罪,则移送至刑事法院,对罪错少年处置结果也以照管令、警告、训诫令等为主。[10]493-523在欧洲大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少年司法中各种“替代性制裁措施”(观护、教养院、社区服务)越来越多地被警察、控诉机关和法院使用,有超过一半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这也体现了欧洲大陆少年司法的福利特征。比如,德国法律在预防少年罪错行为方面,重视少年成长环境的优化等,其《少年法院法》强调“以教代刑原则”,处置措施包括:管教措施(指令、监护管教、教养院管教),训诫措施(警告、强制性义务),少年禁闭,缓刑,少年刑罚。但是,就罪错少年案件处理程序而言,与美国相同,少年法院是必经程序,只有少年法院放弃管辖才能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11]而在亚洲的日本,深受美国少年法院的康复理念和国家亲权理论的影响。日本《少年法》规定对罪错少年采取“保护处分优先原则”,保护处分成为替代刑罚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护观察、解送救济院、儿童商谈所、少年院等。这些措施主要是对罪错少年进行教育和指导。日本的少年法院系统(家庭法院)审理三种类型的案件:14—20岁的严重违法者,虞犯未成年人(离家出走、屡教不改等),以及触犯刑律但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12]因其不满14岁,根据《儿童福利法》交给政府建立的儿童辅导中心监护。在家庭法院中,以保护和矫治为重点,缓刑官则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最终移交检察官接受刑事审判的比例非常小。[13]
从少年司法诞生和发展的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少年司法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矛盾冲突的总体特征。首先,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这其中可以看到不同思潮、理念、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少年司法改革中,其实行的策略往往為了顾全少年司法的福利性和惩罚性而采取二元性的定位,即把少年司法定位为既是为儿童福利的、治疗性的、非正式程序性的,又为社会安全的、惩罚性的、需要正当程序的。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的法律观念造就了少年法院在福利机构和刑事司法机构之间徘徊。其次,观念上的游移不仅影响到少年司法模式的形成,也影响到对罪错少年采取怎样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单独设立的少年司法机制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各国做法不一。少年司法设置大致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是“社会化的少年法庭”模式(或福利模式)。大多数美洲国家都采取这种模式,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儿童福利委员会模式。这种模式的少年司法制度更加重视儿童福利,意欲摆脱刑事程序对少年的伤害。其二是“修正的刑事法院”模式(刑事司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普通刑事诉讼规则处置少年案件。再次,尽管在少年司法中越来越强调一种司法模式色彩,但少年司法在建构之初所带有的福利“基因”依然无法改变,其与普通刑事司法在基本理念及运作程序上仍体现出各自的特征。总体上,少年司法的独特理念和特征依然在其一般性原则以及具体的少年司法程序性规则(原则)中得到体现。少年司法不仅仅指少年刑事司法,还包括以犯罪预防为主的对不良行为、违法行为的矫治,因此呈现出对罪错少年的分级干预特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与调整少年罪错行为相关的立法、司法机构,强调犯罪预防,在对罪错少年的干预中,提倡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理念。由于分级处遇的理念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当前各国司法制度所普遍追求的处遇个别化目标,尤其适用于尚处于身心发展阶段且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罪错少年的矫治中,因此也被认为是对罪错行为进行有效治理的最重要原则和依据。[14]
三、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基本问题:原则、根据、措施
为了预防犯罪,矫治罪错少年的偏常行为和心理,有必要根据不同原则及其个性化特点,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帮助罪错少年顺利社会化的目的。然而,如何分级和怎样干预,不仅涉及分级干预原则,还涉及分级根据和干预措施等问题。
(一)分级干预的原则
当犯罪预防纳入少年司法体系后,少年司法显然不是仅限于刑事司法,或者说主要不是指刑事司法,而更多的是针对不良行为、违法行为采取一系列保护处分和矫治措施,那么,所遵循的原则也必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坚持儿童最大利益、非歧视等总体原则的基础上,尤其需要具体注重下列一些原则。
1.分级处遇原则。分级处遇既是一项原则,也可以看作是干预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条将分级处遇确立为一项原则,符合少年成长发育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成长是一个不断犯错和纠错,最终达到心理和生理成熟的过程。不同年龄、个体之间因成长环境不同而身心发展差距巨大,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当尊重其成长规律,进行分级处遇,才能助其顺利社会化。
2.早期及时干预原则。早干预即在少年行为还处于“错”的阶段就介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第三、四章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做出了规定。对于少年罪错行为的规制,各国立法采取家长主义立场,认为诸如逃学、饮酒、赌博等不良行为,以及盗窃财物、吸毒等轻微的违法行为,如果不加以及时干预,有可能演变为犯罪,更不利于少年的健康成长,这已经为少年发展理论和犯罪学研究所证实。关于早期及时干预的范围,依法限定于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大多数仅具备“身份性”“自害性或轻微害他性”“犯罪倾向性”[15],仅有少部分行为属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因此,有必要及早干预和矫治,防止发展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3.个别化和专业化原则。个别化原则不仅是少年司法独立发展的根基,也是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原则和依据。[16]个别化处遇要求专业化的配合才能实现,专业化是实现个别化原则的前提。对心理和行为偏常的未成年人进行简单的惩罚被证明没有效果,还易导致重新犯罪,应当引入专业人员,采取有针对性的专业方法,因人施治。少年司法系统之所以越来越关注保护服务专业性的特殊重要性,概因其中涉及的问题大多都需要专业性的指导,如果专业化介入不足,家庭支持力度不够,必然会削弱早期及时干预的效果。
4.隐私保护原则。隐私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因为罪错少年的分级干预要避免周遭人群的不必要的关注,进而给该少年及其家庭带来社会交往和融入的困境,隐私保护在罪错少年分级干预中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影响到干预的效果,还涉及去标签化问题,进而影响罪错少年的顺利社会化。
(二)分级干预的根据
分级处遇的理念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少年司法制度所普遍追求的干预措施个别化目标,尤其适合身心发展都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少年矫治,因此也被认为是对少年罪错行为进行有效治理的最重要原则。就其分类根据来看,有论者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一是根据适用对象的分级,即根据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恶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等因素进行分级。在法律上将年龄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主观非难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的关键因素。二是根据适用范围的分级,即根据罪错少年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分级。行为因素体现了行为的法律性质和人身危害性,是采取何种处遇措施的根本因素。[17]这两种分级也是各国少年司法通行的做法,但我们还注意到,在少年司法的发展和实践中,对少年个体及其生长环境的全面理解,也是少年矫治的考虑要素,因此,对罪错少年分级处遇的根据,也应当包括个体要素。下文将从主体因素、主观要素和行为要素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根据主体特点考虑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主体特点涉及群体性特征和个体性特征,前者对分级干预具有指导意义,而后者则对采取何种干预和矫治措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主体特点也可以看作是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根据。从这个角度,分级干预制度意在矫治而非惩罚,也可以看作是关于行为人的制度设计。主体特征主要包括主体的生物学特征和人格特征。生物学特征是比较显性的特征,人格特征则表现得十分复杂,因此产生了各种探讨人格特征的理论。人格理论关于人的心理、行为,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罪错少年的分级处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根据主观要素的不同而采取的分级。如果说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指考察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有无而确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罪错少年的干预则需要考察一般意义上之辨控能力的强弱来进行分级介入,因此,这里的主观要素也可以理解为依据行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程度,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辨认控制能力,以及一般辨认控制能力强弱的各相关要素。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作用、后果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控制能力指行为人通过是非判断而产生约束力,从而采取某些行为而不采取其他行为的能力。一般情况下,只有对事物的性质有正确的判断,才能有效地支配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也就无所谓控制能力,有判断能力而缺乏控制能力,行为及其后果并非行为人真实意思表达,也不能将行為人看作是有责任能力的。[18]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视角解释少年刑事责任能力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很难解决个体判断问题。我们都知道,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表达即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12—14岁作为推定能力阶段,14—16岁为限制责任阶段,16—18岁为完全责任阶段。这些规定是对一个群体的判断,却无法解释低于法定年龄而实际具有辨控能力的儿童的刑事责任问题,或者让其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问题。二是可能导致与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相冲突。辨认和控制能力说以古典学派道义责任论和报应主义为背景,以这一学说来解释少年刑事责任问题必然导致报应主义,单纯考虑等价报应必然会引起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诉求。因此,也有论者主张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是一种刑罚适应能力,要追究犯罪少年的刑事责任,除了考察少年的行为能力外,还应当考察其刑罚适应能力。[19-20]对少年刑法适应能力的关注在解释罪错少年分级干预问题时也有其价值。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目的是帮助其正常社会化,因生理与心理特殊性导致少年受刑能力低,对受刑能力低的少年采取监禁刑,不仅对其身心发展产生副作用,还会造成“交叉感染”,犯罪预防效果下降,无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因此,现代少年司法主要是基于受刑能力低而在责任方式上改用强制教育措施。近代刑事实证学派的社会责任论则是从社会防卫的视角考察行为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对于实施犯罪的幼年人,因不具备刑罚适应能力,给予保安处分或其他保护性措施,而非刑罚。
需要说明的是,以辨控能力作为判断非难可能性标准仅在判断罪与非罪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作为辨别和控制能力的法律表达——刑事责任年龄,则在承担罪责方面发挥了界定作用。尽管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并不符合人格发展形成的渐进性,但是,这样的推定却为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必需,因此各国法律往往将年龄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主观非难可能性的关键因素。对不同年龄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比较清楚地呈现了罪错少年的分级干预制度,因此,年龄也可以看作是分级干预的根据。大致来看,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通常有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最高刑事责任年龄之分。一是未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段的儿童,分不清对错,以及缺乏受谴责的能力,其罪错行为应予宽宥。[21]21-32不构成犯罪的,由儿童福利、保护部门或者由家事法庭、民事法庭处理,适用儿童福利法或者家事法等,采取具有强制性的福利措施或者家事法措施。各国最低责任年龄大多规定在6—15岁之间。二是已达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未达最高刑事责任年龄段。由于该阶段未成年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原则上不适用刑罚,因此应采用符合其身心特点、成长规律,以及促进其改过自新的干预措施,必要时还应对其进行机构矫治。例如,根据法国1945年2月2日发布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的规定,法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3岁,13岁以下年龄者为绝对推定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阶段,对于10—13岁之间的少年如果犯有比较严重罪行的,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需要由法官裁断,并采取相应的行政拘留或教育性惩罚措施[10]554-555;而对13—18岁罪错少年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推定则不是绝对的,一般情况下,只能采取教育性惩罚措施,特殊情况下,可适用刑罚,但以减轻和从轻为原则[22]。三是已满最高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原则上可以适用刑罚,但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如果根据情况适用非刑罚措施更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的,可以不适用刑罚。但是,以年龄作为分类标准在对罪错少年采取具体矫治措施中还是显得过于粗糙,因此,结合罪错行为作为分类根据就成为各国少年司法比较通行的做法。
第三,根据罪错行为不同严重程度分级。根据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分级,既直接决定着少年行为的法律性质,也间接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是决定对未成年人采取何种处遇措施的根本要素。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大致采取此种分类。从美国少年法院对不同罪错行为的管辖权中,也可以看出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采取相应措施的分级干预制度。美国少年法院对18岁罪错少年案件有原初性管辖权,根据各州不同情况,大致管辖6—18岁之间的少年越轨行为、身份犯、受虐待等案件,而对年长少年的严重犯罪行为,则根据移送管辖制度交由刑事法院审理。[21]276-296
(三)干预措施的保护性及程序的专门性
分级的目的是有利于采取个别化的处遇措施,而具体的矫治措施则将最终决定着少年司法制度在解決罪错少年问题上的能力和效果。[17]针对罪错少年的主体特征、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年龄而采取的干预措施,由于决定机构不同、程序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的性质也不同。在世界范围内,针对罪错少年的干预措施具有康复治疗性,而不具有纯粹的惩罚性。具体表现为:(1)强制性福利措施。预防犯罪、未达责任年龄儿童的一般性不良行为,比如交由家长管教、心理辅导等。(2)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保安处分的基础上设置“保护处分”的措施对罪错行为进行干预与矫治。如日本的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机构等,又如法国对罪错少年的保护处分措施等。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尚无保护处分的规定。而现有的处遇措施仅为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学校管教、公安矫治教育、专门教育、犯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社区矫治、少管所服刑,后两项是刑罚的执行,前面的几项也不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功能,不能阻断刑罚的二次干预。(3)刑罚。从理论上来说,犯罪少年经过审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都有可能接受一定程度的刑罚,但针对罪错少年适用的刑罚仍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刑罚种类的限制;二是基于教育优先于惩罚的原则。对少年采取刑罚措施的谨慎概因严厉的刑罚会阻断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的正常进程,刑罚中的一般预防功能在少年群体中亦很难实现。因而,对罪错行为不能追求单纯的刑罚,而通过保护性的矫治方式,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权保障为前提的犯罪控制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儿童的最大利益。
另外,根据罪错少年行为和年龄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决定和适用,与专门的程序设计和专门的办理主体有关。在国外都有根据不同案件中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龄和所涉嫌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而有不同的程序设计,比如有的国家针对少年罪错事件的处理设立有违警法院、预审法官、少年法庭和少年重罪法院。这些都体现了少年司法的专业化特征,也是罪错少年分级干预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四、分级干预的制度框架
罪错行为不仅在概念上与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警行为、犯罪有责行为形成了逐级发展、逻辑严密、衔接有致的概念体系,而且因处分和矫治对象的不同特点,有必要采取不同的犯罪预防、干预、处分和矫治措施。我国对这一问题之所以缺乏有效的干预,概因少年司法的独立价值及对罪错行为性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法律定位不明确,以及之前的收容教养制度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均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过程中暴露出来。因此,建构罪错少年分级干预制度,除了清晰了解上文涉及的概念、原则等基本问题之外,有必要做体系性思考,至少明确其制度框架,以便于这项制度的有效运行。
(一)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目前与此相关的立法既分散也不成体系,立法比较粗糙,专门性立法还需加强。我国关于少年罪错行为及其处遇散见于多部法律,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法》和《监狱法》等。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些法律也形成了一定的以主体、年龄划分和行为性质为主的分类处置体系,但分散的立法模式必然导致分级及其干预措施之间的衔接错位,缺乏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加强专门性立法。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制定一部法律来规范少年司法所有问题的做法未必可行,但专门立法有必要,也有可行性。除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之外,特别需要制定解决罪错少年处遇之程序问题的《少年事件处理法》,以及解决失依儿童和受害儿童保护问题的《儿童福利法》等重要法律。这样,从罪错少年分级干预的视角,在立法上将形成一个以儿童福利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前期保护和预防犯罪为主的第一级干预,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实体规定的第二级干预,犯罪后进入少年刑事司法的案件则维持目前的《刑法》规定。但是,少年案件处理的程序性问题,包括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程序性问题,则急需一部《少年事件处理法》加以规定,这样形成一个衔接有致的罪错少年分级干预法律体系。因此,从立法角度,可以考虑从如下方面完善和加强。
第一,根据行为主体特征及其行为性质,进一步完善对罪错行为的分类。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旷课、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属于身份犯行为,交由监护人和学校监管,国外一般采取福利性和保护性教育措施;严重不良行为内部组成则比较复杂,既有治安违法行为,也有触法行为。对于治安违法行为,基本采取训诫、限制自由、禁止行为等矫治教育措施,而对于触法行为则采取送专门教育机构的惩罚性教育措施。那么,将这两类行为性质和处遇措施不同的行为放在“严重不良行为”之下就显得不够严谨了,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规定12—14岁未成年人犯杀人和严重伤害行为的,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负刑事责任,但是对核准没通过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少年怎样纳入专门教育进行矫治,刑法并无具体规定。这些方面的内容,显然与治安违法行为采取的保护教育措施不同,因此,从分级干预的视角,对触法行为有必要考虑单列,以便对其中涉及的具体处置和矫治等问题做进一步的规定。
第二,处置措施的种类相对少,缺乏衔接,不系统,可操作性不强。根据预防犯罪法,不良行为干预措施除了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之外,学校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训导、要求遵守行为规范、要求参加专题教育和校内服务、接受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等教育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满足了教育措施多元化的特点,但还存在两方面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偏严;二是不够明确,给落实造成困难。比如,预防犯罪法对两类性质不同的严重不良行为做出了具体规定。然而,从行为性质上看,治安违法行为绝大多数仍属于自害性行为,应当采取教育性矫治措施,更适合在社区进行矫治;而触法行为则属于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的犯罪行为,应当采取具有一定教育性的惩罚措施。一般情况下,具有犯罪行为的少年通常可能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更可能采取半机构或机构矫治的方式,但目前法律关于送专门学校矫治的具体措施和程序上的衔接等都缺乏具体的规定,这种不加区分的笼统规定,将不利于法律的进一步执行。
第三,分级干预措施的程序性问题也急需解决。少年司法处遇尤具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中表现为少年事件处理的专门制度和案件移送管辖制度,这些制度也是少年司法独立发展的基础。故而,对罪错少年采取分级干预的各级决定或裁决为何种性质,以及决定或裁决的机构、具体程序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另外,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性质、程序、效力,以及专门学校对罪错少年移送和封闭管理问题、在触法少年的矫治中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分工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二)相关实施机制的建构和完善
仅从完善法律制度角度思考罪错少年分级干预体系建构显然是不够的,就目前情況看,有必要推进儿童福利制度、少年保护处分制度和少年社区矫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建构。从总体上看,这三项制度的推进尤其需要强调专业化原则的保障,不仅涉及少年警务、少年检察、少年法院等人员和机制的专业化程度,还涉及一系列的专业化措施的应用。
其一,推进儿童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建构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的同时注重儿童福利制度并行发展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从少年犯罪预防的视角看,家庭支持系统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从少年司法建立的初衷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不仅包括触法行为的处遇,更多的是将不良行为、违法行为纳入进来,这也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形式。少年司法的发展脱离不了儿童福利机构,特别是对于流浪儿童、弃儿、无人照管儿童的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的矫治,需要依靠福利机构和相关寄养家庭等的配合,同时要对家庭提供支持,考虑家庭教育令的可行性及经济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冲突解决和协调等。另外,少年罪错的预防机制包括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和家庭外部支持系统,前者发挥家庭养育和教育功能,后者则发挥教育、少年福利、少年司法等社会的积极作用。只有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力量,形成系统、科学的应对格局,才能不断地改善罪错少年的微观环境,协助其顺利社会化。另一方面,从少年司法制度体系视角看,需要纳入儿童福利制度,以更好地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尤其是从少年司法的发展路径来看,我国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成立少年法庭之初,其定位就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这一定位使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纳入不良行为、违法行为和触法行为的规制,增强保护处分和矫正色彩,压缩减少刑罚措施,逐步靠近并走上现代少年司法的发展道路。
其二,保护处分机制的建立。从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推导出对待罪错少年要尽量避免刑罚惩罚,但亦不能一放了之,要设计完善的刑罚替代措施进行干预和矫治,这种刑罚替代措施正是保护处分。[1]保护处分是现代少年司法的核心内容,从性质上,保护处分兼具惩罚和教育的属性,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刑罚的报应功能,也可以起到预防再犯的作用。保护处分制度立足于少年福利本位,在各国少年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从国外立法规定看,在保护处分适用上形成了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德国将保护处分作为少年犯罪的刑罚替代措施,日本将保护处分适用于少年犯罪、触法行为和虞犯少年,美国也将保护处分适用于少年犯罪、触法行为、少年虞犯和违警行为。在我国,由于实行违法犯罪二元处罚机制,对违法等行政处罚措施勉强可以看作是一种保护处分措施,但缺乏对于少年轻罪的替代刑罚措施。因此,对其性质的界定是保护处分机制建构的立足点。如果将其看作是刑罚替代措施,则可适用于犯罪行为;如果将其界定为矫治措施,则可适用于触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我国适用于罪错少年的保护处分措施主要包括:一是专门教育措施,二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警告、罚款、拘留等),三是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措施(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这些措施中有些显然过于严厉,比如拘留。保护处分应当以非限制自由为基本要求,尽管保护处分包括机构性保护处分和非机构性保护处分,但从世界范围对保护处分的适用看,无不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而以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23]因此,有必要严格限制甚至废止拘留等机构化措施的适用,这类措施带有较为浓重的监狱化色彩,也就必然带有监狱监禁的弊端,与世界范围所倡导的非监禁化运动相背离,不利于罪错少年的社会化。此外,保护处分应当遵循处分法定原则。保护处分措施的合法性离不开其程序的正当性,如果作为刑罚替代措施,保护处分适用的决定权应归于少年法庭,并按照司法化的程序运作。
其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我国《社区矫正法》设立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问题,对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及其职责、被矫正的罪错少年权利和义务、社会组织的参与等问题有特殊规定,但总体上,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施。毫无疑问,社区矫正的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更生和保护的目的。我国少年社区矫正一直发展缓慢,这与我国对社区矫治性质的限制有关系,也与少年司法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体系有关系。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社区矫正被规定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而在国外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刑罚替代措施(或刑种)。对社区矫正基本功能的认识差异带来制度适用的局限性,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外犯罪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国外被规定为犯罪的轻微行为和违警行为在我国被看作违法而非犯罪,而国外绝大多数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行为就是违警罪和轻微刑事犯罪。二是从社区矫正的渊源看,天然地带有促进越轨者更生、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社会福利性质,其思想基础在于少年的可矫治性,这也暗合了以少年司法教育矫治为主促进复归社会的性质。三是国际上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适用广泛,成为针对少年犯首选适用的措施;其二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利于罪错少年社会化。总体上,少年社区矫正更加强调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福利化。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孙鉴.触法行为干预与二元结构少年司法制度之设计[J].浙江社会科学,2017(4):41-45.
[2]王雪梅.论少年司法的特殊理念和价值取向[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5)45-53.
[3]马乔里·J.克斯特尔尼克.儿童社会性发展指南:理论到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3.
[4]康树华.新社会防卫论评析[J].当代法学,1991(4):66-72.
[5]泽登俊雄.新社会防卫论[J].法学译丛,1987(3):49-50.
[6]王振宏,王笑笑,李彩娜.儿童发展的不同环境敏感性:理论与实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36-47.
[7]王彦,苏彦捷.5至8岁儿童心理理论各成分的发展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639-640.
[8]刘鹏飞.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研究综述[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7):141-143.
[9]劳伦斯·斯滕伯格.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02-107.
[10]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等.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孙云晓,张美英.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德国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61-220.
[12]齐文远,刘娥.日本少年法理念与日本少年司法晚近变革[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2):37-42.
[13]孙云晓,张美英.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日本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60-170.
[14]杨飞雪.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探索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8.
[15]姚建龙,李乾.论虞犯行为之早期干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51-64+146-147.
[16]盛长富,郝银钟.论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2(4):76-80.
[17]宋英辉,苑宁宁.尊重未成年人司法规律建立分级干预体系[N].检察日报,2019-02-11(3).
[18]陈兴良.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1999(6):68-74.
[19]侯国云,么惠君.必须将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区别开来[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5):76-82.
[20]李川.从刑罚论视角看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正根据与适用[J].环球法律评论,2021(4):100-115.
[21]巴里· C.菲尔德.少年司法制度[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22]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07-412.
[23]姚建龙.犯罪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J].法学论坛,2006(1):32-42.
Systematic Thinking on the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Wang Xuem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Law on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of China has defin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do an integral thinking on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n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swers the reason why the juvenile delinquents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rom i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as well as the vie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juvenile justice. Secondly,it analyzes the basic problems on the principle,basis and treatments concerning the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Finally,it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systemat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classified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system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s improvement.
Key words: juvenile delinquents;delinquency;classified intervention;child welfare;protective treatment; community correction
责任编辑:刘有祥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