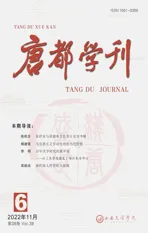论儒家之“义”的三重维度
——兼论儒家理想人格的尚义特质
2022-02-10姜波
姜 波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合肥 230039;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1131)
义是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由此引申出的“见利思义”“舍身取义”“君子喻于义”等人格品质浸润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尚义品格是塑造人们道德伦理的价值导向。然而,在儒家思想仁义对举的过程中,仁的价值历来被充分观照,自孔子至近代思想家、乃至现当代学者,多有专论仁学的著作彰显于世,相形之下,儒家之义的内涵则有所遮蔽,或曰隐而不彰,换言之,儒家在理想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崇仁的一面往往被视为主流和重点,而尚义的一面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不仅如此,受《中庸》思想影响,在对义之内涵诠释的过程中,突出了义之为宜的层面,将儒家之义释为适宜、恰当抑或道德地本然,已成共识,然而“仅仅把它(义)理解为道义,或是单纯解说为正义,出现了对儒家义学的误解、误读”[1],也就是说,儒家之义,除了被诠释为“适宜”外,应还有其他意涵隐而未彰,否则孟子就不会大为表彰义,将其提升与仁同等价值的层面,并列入四德之次。故而,对于儒家之义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拓展传统义德的研究论域,对于彰显儒家理想人格的尚义特质,培育新时代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义”的本质内涵
《易传》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455的说法,意思是说:天者,有阴阳之对立统一;地者,有刚柔之相磨相荡;而人者,则有仁义之相辅相成。那么,仁义是否如阴阳、刚柔一样,为相互对举的概念呢?关于这一问题,诸多学者意见不一、众说纷纭。按照通行的解释,仁为爱已不成问题,即使到宋明儒家那里,将仁释为生,也与爱意内在契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义”作何诠释。周桂钿说:“儒家常说仁义那个‘义’字,我们了解它的通义‘宜’就可以了。”[3]8此种说法显然受到了张岱年的影响,张先生说:“寻求字义,主要是了解其通义,不一定寻求本字。”[4]将“义”训为适宜、恰当、当然之则等意思,已是学界共识。但是,《易传》何以将仁义与阴阳、刚柔并列使用?庞朴认为:“根本地说来,儒家道德学上的仁与义,也就如它的政治学上的德与刑。或者说,这两对范畴,正是统治阶级应有的两手政策在儒家学说的两个领域中的表现。它们都是对立而又同一的。这是应该时刻把握的基本要领。离开这个要领去轻信儒家自己所作的种种虚假表白,去看待仁义关系和义的内容,都将无法了解儒学的本相。”[5]庞先生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儒家的仁与义本是对立的范畴,如阴与阳、柔与刚一样,处于对举的关系中;二是对儒学的理解,应当充分观照到义的内涵及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仅仅将义释为宜,将无法全面把握儒学的真相。
为了说明义与仁有对立的意思,庞朴通过大量的考证指出:作为通义的“宜”本义为“杀”,即在祭祀中要杀牺牲和俘虏以祭天神,由此宜带有了“血腥气味”,不利于凸显儒家伦理追求合适、美善的形式。加之义、宜同音,义之威仪可容纳宜之杀戮的意思,故而在战国中后期的孟子及其弟子手中,实现了以义代宜,并因此与儒家倡导和谐融洽关系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但同时也掩盖了义之本义中倾向于制断、肃杀的一面。此论被李泽厚、张立文所赞同,而张岱年则表示反对:“上古时代的祭祀,都是杀牲以祭,杀俘以祭。但杀牲杀俘都只是祭祀的部分内容,祭的主要意义还是向神祈祷。近人‘宜之本义为杀’,就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了。”[6]周桂钿也指出,将“儒家的‘义’解释为‘杀人’,是不严密的。”[3]8以上论争牵涉到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相关问题,此不展开。但是从诸多的文献记载来看,将义字仅仅释为合宜、适宜的“善善”的表达并不能完全揭示其本来面目,义的本质内涵也有“恶恶”的一面,即裁制、截断甚至割弃之义,朱熹就有“义是肃杀果断底”[7]245“杀底意思是义”[7]246,这与庞朴的说法基本一致。而周桂钿“朱熹这些历代儒学大师的一切言论中,看不到任何一处把‘义’释为‘杀’的明确说法”[8]的论断,显然缺乏对史料的全面观照。故而,事物要想适宜就必然要经历一个剪裁的过程,“裁制”是使事物“各得其宜”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义之内涵首在裁制、断制,重在合宜、适宜,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
要之,儒家之义包含裁制与合宜两个层面,即“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9]24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云:“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美善同意。”[10]639而这里的“由中断制”即是“由心断制”,是指人内心的决断能力,属内;而“与美善同意”则是指行为的效果,属外。换句话说,儒家在这里将义解释为“心之制”,乃“事之宜”的根本所在,如果将义释为“宜”“事之宜”是通行的解释,那么将义释为“制”“心之制”则是最本根的解释。
二、“义”的形上依据
知晓义的本质内涵之后,必然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义缘何而来、从哪而发呢?这即是义的形上依据问题。孟子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1]259朱熹也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9]247二者都认为,义同仁一样,是天理内化于人心的德性,是内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质言之,义源于人之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而其根本上则源自天理。
关于义之来源于天理、天道的问题,传统儒家中有两处重要论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2]483“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12]由此看出,义之合理性是由天道推衍出来的,其形上依据则来自于颠扑不破的天理。换句话说,孔子用“礼义”来定义人间的伦理关系,从天地万物的相交相生的源头,顺衍出人间伦理的开端,为人间之义找寻到了本体依据,这对于后来的宋明儒家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就说:“义者,天理之所宜”[13],为儒家之义找寻到了天理本体的依据,以理行之,就是为义,这是对传统儒家义学的提升与发展。对此,杨国荣也指出:“新儒学之以理规定义,更多地着重于为义的至上性提供本体论的论证。”[14]而有关义之心性依据的问题,孟子最先提出义是人心固有善端,并以此说明了人、兽之根本区别。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80朱熹在注解此段时指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9]289-290端为头绪、开头,借着人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的表现,则能看到仁、义、礼、智之性的本来状态。具体到义来说,即羞恶之心是显露出来的义,而隐含在其中的义,则关联着性之本然,换言之,对于人的本性而言,如果具有羞恶之心,并不断扩充提升,就可以达至义的状态。由此可知,义作为人之四德之一,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的根本所在,荀子也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5]
然而,明晰了儒家之义的天道、天理依据,清楚了人禽之间的根本区别后,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来源于天地万物之一理的人性,为何会导致人的不同特质呢?为何会有慈爱与断制、善善与恶恶、贤能与不肖、聪明与愚笨的区别呢?关于此,孟子有“牛山之木”比喻:“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11]263孟子认为,人与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而终点未必一样,其根本区别在于有的人能扩充仁义礼智四端,而有的人不能扩充此四端。能扩充者,就能不断强化和完善自己的德性,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趋于完美人格、人性;不能扩充四端者,善端就会越来越褪色,越来越靠近动物性,最终丧失人性而同于动物性,甚至还有连禽兽都不如之人。为了具体说明这一问题,宋明儒家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从人之气禀各异的角度揭示此种差异的缘由。因“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7]205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朱熹接着说道:“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7]205由此可知,朱熹引入了五行的理论与五德相互诠释,认为禀得金气多的人,则有个清峻刚烈的性格,做事果断、嫉恶如仇、善善恶恶,这即是义多之人的外在表现,即“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9]282此差别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与天地运行、四季更替等自然因素有关,“日月清明气侯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7]198如此看来,儒家人性之气禀思想与其天地万物之生成的本体思想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皆奠定了儒家义德的形上学基础。
三、“义”的伦理价值
为了脱离动物性,彰显道德性,塑造理想人格,人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需要义作为价值指向,也只有以义为价值坐标,才能具有道德的自觉性和人格的尊严感。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6]39告诫我们义、利之辨乃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点,以义为价值导向,则能成为君子,而以利为价值追求,则会沦为小人。儒家理想人格中尚义特质十分突出,其生发出的见利思义、舍生取义、集义生气等理念,为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
(一)见利思义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不贪利”等思想妇孺皆知,然而,如果据此就认为儒家反对追求利益,而一味地崇尚仁义,甚至发展到谈利色变、以利为耻的地步,这显然是对儒家义利思想的曲解。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6]71后世轻利者往往舍其“不义”二字,渲染“富贵如浮云”的片面观念,并冠以圣人之名获取其正当性。孰不知,这是对经典的断章取义,也是对儒家传统义利思想的误解。如果说孔子没有对义利之辨展开充分论述,没有对取利的重要性予以抉发,那么到了孟子那里则明确地指出:义不贪利并不是杜绝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完全流入清静无为、无欲无求的境地,孟子只是反对“不辨礼义”的贪利和“以利为利”的小利,他所极力主张的是“合乎礼义”“以义为利”的大利。在见梁惠王之后,孟子明确提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11]1,认为一味地追求利益,则国将不保;反之,如果上下皆以合乎仁义之道行于世,则未有不王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280。宋明儒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将利区分了公利与私利,即“公私之辨”,前者“以利为利”之利是私利,这当然是危险的,需要摒弃;而后者“仁义相接”之利则是公利,应予以大力提倡,对社会的进步有积极意义。近来,有学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义、利二字进行了分析,发现“两个字都有用刀切割东西的含义在其中,只是行为的对象略有不同。故而在原始意义上义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更近于本与末的关系”[17]51。这也是对义利统一性解释的合理路向。
《孟子》还有一处典故,可看出他对待利益“当受则受,当辞则辞”权衡取舍的态度。有一次,孟子推辞了齐王的一百镒黄金,却接受了宋王的七十镒和薛王的五十镒黄金,学生陈臻十分不解,问其缘由。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11]93孟子认为,宋王的七十镒是送远行之人的盘缠,薛王的五十镒是让我购置兵器以防不测用的,所以都是符合道义的钱财,没有理由不要;但是,齐王送我的黄金则没有任何的缘由,这就等于用钱来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被钱财货物收买的呢?所以不义之财不能要。由此看出,孟子在利益的权衡取舍之间自有一番道理,而这道理不是别的,应该是以义作为价值标准的仔细考量,只有因义取利才是正道,而见利忘义终会误入歧途。所以,孟子将此正道定义为义路、正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1]267明代中叶,商业文明繁荣阶段的诸多思想家的义利观都是在见利思义、利不忘义的维度展开的,清代的徽商商帮素有贾而好儒、见利思义的美名,也与此层面的义利思想有根本关联。
(二)舍身取义
中国人十分注重生命意义和身体价值,道家有重生、贵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观念,儒家也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说法。所以,单纯从身体、生命的角度而言,先秦各家的思想基本一致。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11]301这也就是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重身(生)观念。然而,儒家和道家的重身(生)观念存在根本差异,借用上文公私、义利之辨的讨论来看,杨朱对身的理解完全出于私利,即使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愿意,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视天下苍生于不顾的自私观念;儒家虽也重视生命的价值,但儒家重生却不恋生,当个体生命与道德仁义、苍生社稷发生冲突需要抉择取舍时,儒者认为生命与身体的价值就要让位于道德价值,小我的私利就要让位于大我的公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11]265这里需要明确,孟子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倡导“舍身(生)取义”,而只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才需要做出抉择;具体来说,在人生之常态(也是大部分状态)下,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修养身心,以俟长寿,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对家庭、家族以及国家、民族有利,毕竟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身(生)为根本的,没有了生命和身体的存在,一切都是空谈。然而,纵使有生命和身体的存在,儒家也十分重视身体的强壮和生命的质量,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6]176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所戒,这是身体保养、生命延长的法门,也是农业文明下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基点,从这一点上看,儒道思想具有注重养身(生)的共通性。然而,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当一己之身与社会道义发生矛盾时,或者苍生社稷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救国救民时,儒家就趋向于舍去一己之性命,成就仁义与道德,舍身取义换取更大的利益。
古往今来,儒家舍身取义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众多仁人志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多次从危难中转危为安,成就辉煌,靠的就是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义凛然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义担当,这些志士仁人不仅名垂青史,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接续奋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断贡献力量。众所周知,庚子初,荆楚疫,举国同抗击,白衣天使、社区干部(其中不少都是共产党员),舍小家顾大家,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一句“不计报酬,不论生死”道出了多少逆行者为民立命、为国分忧的道义担当。这些都是典型的儒家式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也是浸透于中国人血脉中的家国情怀,从根本上体现了舍身取义的道德良知。
(三)集义生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道教有气功说,儒家也有浩然之气说,然其本质不同。道家、道教之气纯粹是从养生的角度而言,甚至后来有神秘化倾向;传统儒家之气,虽也从修养之气出发,但终点并不止于养生,而是有道德价值层面的追求,其目标指向是蕴含道义(义理)的精气。朱熹说:“气,只是一个气,但从义理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气;从血肉身中出来者,为血气之气耳。”[18]1711质言之,血气之气等同于感性与冲动,义理之气则蕴含着理性与智慧,前者纯属生理反应,凡有生气之动物(包括人)皆有,后者则多了一层良知的自觉与道德的反省,只有外显为饱含浩然之气的人所独具。
对于如何涵养孟子的浩然之气,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熹在注解“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11]62时说:“配,合也。义者,人心节制之用;道者,人事当然之理。馁,不饱也。气由道义而有,而道义复乘气以行,无异体也。得其所养,则气与道义初不相离,而道义之行,得以沛然无所疑惮者。若其无此,则如食之不饱,虽欲勉于道义,而亦无以行矣。气者,道义之成质,故必集义乃能生之。集义,犹言‘积善’。”[18]1728朱熹这里牵涉了集义的概念,这也是他修养工夫论层面重要的思想。所谓集义,就是事事都要合道义而行,偶然做某一件事符合道义,即所谓的义袭,并不能真正地养出浩然之气;只有将众义积集既久,浩然之气才自然而生,这是一个需要终身行之,而非偶尔行之的道德自觉。“凡事有义有不义,便於义行之。今日行一义,明日行一义,积累既久,行之事事合义,然后浩然之气自然而生。”[18]1735显然,这与他格物、致知的为学功夫具有内在一致性。儒家理想人格塑造过程中具备集义生气、重知重行的重要特质,而具有此种特质的人则能养出浩然之气,并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1]141,其“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1]141,具备了入世与超世的双重品质,同时,无论在何种人生境遇中,他都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1]141,如此之人,即具备了孟子眼中超越了一己之私、将小我融入大我、顶天立地于人世间的大丈夫品格。
综上所述,儒家之义包含有“心之制,事之宜”的双重内涵,且“心之制”是“事之宜”的基础和根本,这是研究儒家义德首要明确的本质内容,唯有此才能弥补义德诠释的不足,全面把握传统伦理道德的多元价值。不仅如此,儒家之义还应超越伦理层面的价值导向,明确其具备天理、天道和心性层面的哲学依据,有其形上之维的价值支撑,且从气禀的角度看,义德充沛的人有刚毅果敢、当机立断的品格,这是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一环。儒家的义德在价值论层面倡导见利思义、舍身取义、集义养气等人格修养与品格特质,强调担当有为的道义精神和主体自觉的独立品格,这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社会,重新唤醒儒家伦理的尚义品格,明晰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小大之辨的价值内涵,对于弘扬道德理想、培育健全人格、增强文化自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