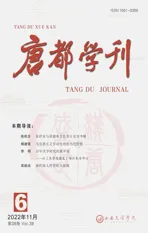百年关学研究的新开展
——以《关学思想史》增订本为中心
2022-02-10李明
李 明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安 710063)
关学研究自挣脱传统理学的樊篱步入近现代学术视野以来,已涌现出诸多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视域既涉及张载的宇宙论,也涉及张载的认识论、心性论和道德修养论;既涉及关学创始人张载的生平及思想研究,也涉及关学史上诸多学人的行实、思想的个案研究。但是对于关学一些带有总体性、系统性的问题,则歧异较大。分歧较大的问题,似乎需要在对关学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系统考察中才有可能得到明晰的说明。近读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增订本)(1)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增订本)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20&ZD033)成果。,原先心中的诸多迷雾渐为驱散。
一、为关学正名
关学概念的内涵向来颇具歧义。这既源于关学思想史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也与思想学派得以形成的一般性要素和机制有关,更与研究者考察学派问题的方法论和眼光密不可分。大凡学派的形成与流变,“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1]自古以来,历代学人也正是基于上述缘由对关学的理解莫衷一是。究其大端,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是狭义上学界普遍认同的理解,即指“濂洛关闽”并称而为北宋道学之主流的张载及其弟子之学。此一具有师承门派意义的关学一度兴盛而“不下洛学”,但自张载殁世之后,却因“再传何其寥寥”(2)参见《宋元学案·序录》。而后继乏人;又经“完颜之乱”以致“儒术中绝”而学统断隔。师承意义之关学衰落的原因除了张子门下本身少英才大儒而学脉乏力以及冯从吾、全祖望等人强调“亦由完颜之乱”的社会根源之外,还与王夫之所言张载“素位隐居”又无当时“巨公耆儒”政治上的支持有关(3)转引自赵馥洁《论全祖望的关学观》一文,收入《浙东学术与中国实学——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是以有“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之说[2]。
第二是泛指关中地域性文化与学术的“关中之学”,即“凡是集中在关中地区讲学的名儒和他们的学术成果,可以统统纳入到‘关学’这个体系当中”[3]。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所谓关学,有两层意义,一指张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指关中地区的学术思想。”[4]刘学智先生也认为“民国时期宋联奎主持编纂的《关中丛书》就是以此为基点”[5]。
第三是广义上指宋元明清时期的关中理学。从明代冯从吾首撰《关学编》到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名儒先后续编,直至民国初年四川成都双流人张骥编撰《关学宗传》,皆持此说以成著述之事。这也是当今学界认同度相对较高的观点。陈俊民先生说:“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6]赵吉惠先生认为,“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理学(儒学)。”[7]赵馥洁先生指出:“关学是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至明清时代仍然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学派。关学从张载创立到李颙终结,历时 700年之久。”[8]
第四种观点则为赵吉惠先生所谓的“泛义关学”。他在界定狭义和广义的关学之余,还提出“泛义关学”之说,即“宋元明清时期或出于关中,或不出于关中,但继承张载气本论哲学传统的哲学思潮”[9]138。他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宋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形态的宋明理学有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三大学术派别,而在张载之后,凡“断断续续有关中或外地学者继承和发挥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所形成的思想传统即为“泛义关学”,其中“宋代的李复、明代的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就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和发扬者”[9]142-143。相对这种着眼于“学承”而跨地域性泛化界定方式,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论者就指出,“能继承、发扬张载关学的大儒也还是有,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但王夫之并非关中学者,与关学也无授受关系,并不属关学范围之内。”[10]
第五种观点则否定统一的关学概念。林乐昌教授认为,要准确地理解关学这一概念,必须综合考虑“地属”-“学属”-“学传”这三大基本要素,即必须兼顾其“地属关中”“学属理学”以及“学术传承”三个维度[11]315,或又谓“‘时间’、‘空间’和‘学传’这三重维度”[12]。作为一个学派,关学有一个从北宋“单一的独立的”形态向明清“多元的并生的”形态变迁的过程,从而“谋求定义一个统一的能够有效解释宋元明清各代‘关学’的概念,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学’概念”[11]317。因此根据基于不同时代和学承具体情形所发生的意涵差异,关学应有不同的称谓,如“北宋(张载)关学”“明代关学”“清代关学”。
上述对关学概念诸多异见纷呈的理解,可以透映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涉及关学学派的学理性、源流性、地域性、时代性、多元性、统绪性、独立性等诸多问题上的摇摆和犹疑。这一方面呈现出现当代关学研究的观念开放性、思维多向性、方法多元性、理论多样性等繁荣发展的态势与活力,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使关学学派的很多理论问题和历史演变逻辑及其具体开展显得更加模糊不清,甚至在特定程度上遮蔽抑或消解了关学的历史生命力与学派的存在真实性,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凝聚必要的学术共同体以开展富有成效的团队协作研究。直到《关学文库》这一重大文献整理项目开始实施,就把解决关学概念之认同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凸显出来。为此,课题组负责人刘学智先生在长期理论探索和不断深度反思中,既拓宽了上述对关学的第一种狭义界定,又收紧第四种广义界说而予以调适中和,提出了自己持之一贯又日益明确的新“狭义关学”概念,即“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5]5。这一界定既从关学与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有机关系中凸显了关学概念之地域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又从以“生命”为中心、“以价值论为特征的境界形上学”这一中国哲学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精神传统出发,注意到由学脉传承之直接性与间接性以及一源多流等因素导致的关学演变之复杂性、多样性问题;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关学学统在源流演变中实际表现为精神宗风之相通性与学脉源流之统绪性一体两面且学行不二的双重历史开展方式。
事实上,就关学学派传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而言,刘学智先生主张“关学”是一个兼顾学脉上一贯性与宗风上相通性的多相性概念,并在21世纪初明确提出张载学脉的传承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论域诸如“气论”的思想传续,还应包括学术宗风或精神宗旨的一脉相通即精神传承[13]。陈俊民先生则在师承与学承之间更突出了后者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在‘关学’及整个宋明理学的传衍中,每个理学家的学承,实际要比其师承更重要。”[14]而赵馥洁先生又在关学多变的历史传衍中揭示出学术传承与精神传承的非同步性,并强调了后者相对的历史稳定性和连续性,认为“尽管关学在传衍过程中,学术观点屡有变化,但张载培育的治学精神却有其前后的一贯性特征”[8]。
此外,在“地属”-“学属”-“学传”三维兼备、一脉与多元统一、“师承”与“学承”变通以及学术传承与精神传承并重的基础上,刘学智先生也主张与上述第三种大致相同的“广义关学”概念,即“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5]5。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就明确了关学在其根本精神上源流一贯的连续性,也看到了关学在复杂的阶段性演变与多样性分途开展中的统一性,更是自信地肯定了关学在历史流变中与其它学派交流互动、相向渗透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总之,基于综合观照、历史洞察和学理辩证,刘学智先生坚信“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5]5。这一判断不仅成为当今学界的主流观点,而且也遥契于自明代以来编修关学史的冯从吾、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张骥等历代大儒对“关中道脉”的学脉认同与精神信念。
二、为关学续史
作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关学自北宋鸿儒张载(1020—1077)创始以来,其思想主题、理论体系、学术渊源、历史流变、地域分化、道脉统绪、思想特征等问题一直为古今学者持续关注。其中,自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1556—1626)撰著《关学编》以使“横渠遗风将绝复续”[15]1,又经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以至清末民初的张骥等历代学人发扬“编关中道统之脉络”[15]65的宏愿与学术使命,至今已经形成了四百多年编修关学学派专门史的传统。而《关学思想史》(增订本)可谓今人担当与弘扬续写关学史学术传统和精神使命的当代力作。
在关学的学术渊源问题上,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对此,刘学智先生在该著中梳理了“申侯开先说”“高平门人说”“洛学渊源说”“《易》学渊源说”“《四书》渊源说”以及李源澄“多本渊源说”、钱基博“祧老祖《易》宗《中庸》说”、陈学凯“主源《中庸》说”等诸多代表性观点,给我们呈现出为关学探源索隐之一个深邃又广阔的历史空间。进而在平章众说又综合评析的基础上,刘学智先生提出:“研究张载关学的学术渊源,应该考察其思想形成的综合因素。”[5]22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张载关学之渊源的“如实知”(唐君毅语),而且有助于尽可能准确又完整地把握张载的思想体系以及整个学派的学脉与宗风之所在。
针对现当代学人在关学发展史的下限节点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刘学智先生修正了前辈遗留的北宋亡后关学“衰熄”说,也否定了金元时期关学中断说,又进一步突破了明清之际李顒终结说。书中一方面充分论证了张载身后一些关学学人为了传承道学而入洛从二程学,但并没有放弃张载的“关学学脉”和“关学宗风”,甚至吕大临还“守横渠说甚固”,关学没有“洛学化”。该书认为,关学在张载身后一直在传承和发展,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作者认为关学的传承不是对张载一些具体观点的坚守,而主要表现为对张载所奠定的关学文化精神的传承。即使在金元时期,关学也没有中断,只是此时“关中学人从宗张载的关学而走向了宗濂洛关闽之理学,尤推崇程朱之学,这成为关学在元代的一个新动向”。可见,此时关学已融入“濂洛关闽”的理学大潮中,如奉元之学等亦“阐关、洛宗旨”[5]237就是明证。“他们基本上忠实于张载关学的学术宗旨”,并“保持着关学力行践履、重于实践和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宗风”[5]212-213。到了明代,“三原学派与吕柟的‘关陇之学’,以及冯从吾等所代表的晚明关学,都保持了关学躬行礼教、崇真务实、笃行实践、崇尚节气的宗风。”[5]242
在此基础上,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增订本)中对关学“下限”问题提出了富有新意的看法,不仅突破了学界长期以来的“明清之际”(李二曲)下限说,也打破了刘古愚下限说。该书通过对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以及刘古愚、柏景伟等人的研究,以翔实的文献证明“明清之际”说是站不住的。至于关学的下限问题,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在清末关学出现了多元的走向,大约同时的贺瑞麟、柏景伟和刘古愚,从不同的思维路向上把关学推向终点。但如果从关学的时代转型来说,刘古愚是关学向新学转向的代表;从对张载“关学正传”(唐文治语)的意义上说,柏景伟是其代表;而从恪守程朱之学的意义上说,贺瑞麟则是其代表。贺瑞麟所代表的清麓一系一直到民国时期仍有传承,而牛兆濂作为清麓一系的最后传人,直到1937年才过世。故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有效的论据证明,“作为传统理学在关中的最后一位守护者,牛兆濂是传统关学在清末民国终结的标志”[5]565,并强调“张载开创的关学学脉没有中断,关学学风也一直在被传承弘扬”[5]5。
这样一来,由北宋张载开创而终结于民国牛兆濂的关学,就有着八百余年的传承史。在此期间,关学发展演变虽晦明有时、历尽沧桑,但其学脉宗风与精神价值却始终绵延不绝。其中究竟固然可以且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和综合考察,但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那就是关学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拘泥门户、囿于一隅而自我封闭的思想流派。该书通过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分析,揭示了关学吸收异地学派思想的同时又能坚守关学本色的秘密:“由于张载的这些思想在此后的发展中为程朱或吸收或发挥,所以后世关学学者多以承传濂、洛、关、闽之理学的路径,使关学继续得以传承和弘扬。”[5]423正是通过与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思想流派如洛学、闽学、河东学派、东林学派、甘泉学派、阳明心学等不断展开广泛的交流、互动、会通与融合,关学才得以适时顺势地在一脉相承与多元开放的张力中、地域全国化与全国地域化双向互动中,形成了风格独特、历时久远、影响深远并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的流变演进史。该著在此意义上相应地对关学与其它学派交往互动的具体情形予以全面、深入地历史考察,不仅有助于凸显张载在关学乃至全国主流思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也有助于考察、审视关学在关中地域文化变迁史以及宋明理学发展史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贡献。
此外,刘学智先生对关学的通史研究中总是把关学学统的历史一贯性与具体时代的阶段性结合起来,把关学的主脉与地域性分流结合起来,从而在常与变、断与续、一与多的辩证统一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立体多维、动态开展的关学演变图景。比如关于明代关学历史演变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线索问题,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增订本)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有明一代,关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明代前期,以段坚、周蕙等人为代表,恪守河东之传;第二阶段从弘治年间开始,关学大致有两条发展路向,一是以王承裕为代表的三原之学,二是以吕柟为代表的河东之学,此外,还有在渭南传播阳明学的南大吉兄弟;第三阶段则在万历年间,以冯从吾、张舜典为代表,其特征是以心性之学为主,融合程朱、陆王。”[5]由此可见,明代关学的阶段性发展和形态变迁的主旋律,是两股重要思潮即朱子学和阳明学先后在关中的传播,并与本地原有学统宗风交互影响而渐臻融合的过程。所以对关学与朱子学及阳明学交流、互动和会通的具体情形及其本质关系的研究,是考察和把握明代关学思想内容、逻辑进程和精神特质的基本线索。
可以说,增订本《关学思想史》是八百多年的关学思想通史性著作。因其具有跨时代研究的时间连贯性特点,又具有“学脉”“宗风”一以贯之的特点,谓其为关学通史性著作毫不为过。
三、为关学定位
关学既以谦恭务实的态度融入理学大潮之中得以发展自身,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异地诸学派互动并相互融通,从而使关学以强大的生命力发展传承八百年之久,其不仅在关中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着广泛的影响,成为宋明理学重要的一翼。这就意味着对关学予以如实又公允的历史定位显得尤为必要。
增订本《关学思想史》首先对张载关学在思想史上做了这样的定位:“张载所创立的关学为孔孟儒学在宋代的重建和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张载也因此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张载不仅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者。”[5]自序1这一说法,为张载及其关学在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上给予了比较合理而明晰的历史定位。其次,该书是对张载关学的本体论做了新界说。以往学界在讨论张载的宇宙论时存在着“气本论”和“太虚本体论”的不同说法,前者以张岱年为代表,后者以牟宗三为代表。双方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张载“太虚即气”这一命题,张岱年将之理解为“太虚是气”,牟宗三将之诠释为“太虚不离气”。该书认为“虚是从形态而言的,气是从实体而言的”,其实“太虚与气是统一而不可分的”[5]94。基于对“太虚即气”的这一理解,书中提出张载关学是“虚-气”本体论,这一观点与1929年谢元范先生所提出的宇宙是“太虚一元之气”“‘虚’与‘气’,实二为一者也”[16]的宇宙论相吻合,也与早年范寿康所说“横渠以为宇宙的本体,乃是太虚一元之气”[17]的说法相一致。再次,本书首次揭示了张载“诚明”论在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明诚”(或“诚明”)是张载关学的重要命题,是张载对《中庸》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故张载去世后弟子私谥他为“明诚夫子”。书中不仅指出张载的“自诚明”与“自明诚”是“两种成圣之路”,更指出“朱熹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发挥了‘自明诚’即由穷理而尽性的路向;而陆九渊之心学则发挥了‘自诚明’即成圣而穷理的路向”[5]137,张载本人更主张“自明诚”,说“某今亦窃希于明诚”,故该书谓“张载所谓‘自明诚’‘先穷理而后尽性’的认识论意义在于:他承认达到天人合一境界需要以客观认知为基础,这也许正是朱熹‘即物穷理’思想之滥觞。”[5]111这就从工夫论证明了张载为宋明理学开创者的地位。最后,该书提出《西铭》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具体来看,第一是从“天人一体”立论讲“民胞物与”;第二是儒家的“仁孝”伦理;第三是“存顺没宁”所彰显的积极进取和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这些都是颇有创新的。
其对关学学派的新认识以对关学学者身份的反思和检讨最为突出。冯从吾的《关学编》及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的《关学续编》、张骥的《关学宗传》等前现代的关学史普遍坚持“以地系人”的原则,且其属地即为王心敬所说“关中产也”。本书则突破了这一狭隘的地理阈限,并通过历史的考索和思想的分析,认为作为“关中理学”的“关学”其学人其实并不限于陕西域内的“关中”,一是因为“关中”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并不仅指陕西的关中平原,它是一个“大关中”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甘肃的陇右地区在内,还可能包括关中平原之外的陕南或陕北某些地方。特别是关学与陇右理学就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关学不能排除对陇右之学的研究。二是陇右的诸多理学家与关学学者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将甘肃的段坚视为明代重要的关学学者,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段坚身上躬行实践的特质颇具关学气象”“他继承和坚守着张载关学‘学政不二’的为学特点及反佛老的立场”[5]278,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明代关学支派河东之学的重要传人,正是受段坚的影响,才形成了以薛敬之、吕柟为代表的“河东之学”在关中的传衍。吕柟是把关学推向中兴的重要学人。再者,该书因跳出传统的“关中”地域之囿,也将贺瑞麟的大弟子、在陕西传承关学达四十年之久的山东人孙乃琨,也视为清末“关中理学的重要传人”。其原因一是孙氏之学“恪守清麓宗旨,惟程朱是从”,又“承继横渠遗风,躬行实践”;再者孙氏“通过近四十余年在陕西的生活,已经深度地融入关学之中”[5]547-549。该书对关学学者身份的反思和检讨,不但突破了古代关学“以地系人”本位思想的藩篱,也突出了关学学派学术传承的脉络,这也是符合现代学术研究规范的。
关学宗师张载强调学人应当“以天下为度”,治学应当“多求新意”。《关学思想史》对关学学者思想和关学学派认识的“日新又新”,不只是学术研究“与时俱进”的表现,亦是对“关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四、为关学研究示范
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传统关学终结于民国,到现在约百年之久。这时分析关学由盛到衰的发展历程,探究其升降浮沉的历史原因,适逢其时,这也是刘学智教授撰写《关学思想史》(2015年初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作者不断补充资料,继续思考,尝有增新,遂于张载千年诞辰之际完成并出版增订本《关学思想史》(2020年增订本)。作为现代学人撰写的第一部关学通史,此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对今后的关学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该书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单就其中的任何一个方法来看,都非作者原创,但就其综合使用及取得的成果来看,实属方法上的创新。
第一,义理与考据相结合。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阐发义理,但需要运用考据方法。思想史研究运用考据方法是为了证明证据的可靠性,从而增强论证的有效性。本书运用考据方法的突出表现是,在对吕大临著作考辩的基础上对其著述分期和思想划分阶段,从而辨明吕大临由关入洛的思想立场,最终证明吕大临在接受洛学思想的同时,又坚守“关学学脉”和“关学宗风”。在由考据提供的可靠且充分的史料基础上,经过合乎逻辑的论证,吕大临“守横渠说甚固”的观点便被夯实。再如,该书对乡约作者为吕大钧而非吕大忠或“吕氏诸兄弟”的考证,关于《张子全书》形成过程的考索,关于《西铭》与《正蒙》关系的辨析,关于张载一些弟子如游师雄等从学张载时间的考证等,这种将考据与义理的结合,为关学思想史的成立增色不少,从而使本书成为“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关学信史。
第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按照史华慈的理解,“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18];这样对思想的研究就必须紧密结合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做到“内外兼顾”。本书在分析关学学者的思想时,注意考察每一位学者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张载思想的分析,将其放在宋代前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环境中考察就非常重要。韦政通说:“一部接近理想的思想史,最好是做到内外兼顾。”[19]运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本书写作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体验与思辨相结合。中国古典哲学的认知方式是直觉体验,而非概念思辨,关学也不例外。对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人而言,既要保持哲学的民族特色,又要追求哲学的现代品性,那就不得不“以思辨之力,推广体验之功,使二者能兼资互进”[20]。本书对关学思想的研究,普遍使用体验与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因为作者也“主张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不必将西洋哲学的方法简单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5]11。《关学思想史》(增订本)正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方法。
J.W.汤普森说:“历史可以被看作跨越时间的洪流、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的一座巨大的桥梁。”[21]《关学思想史》是一座联结关学的过去和现在的巨大桥梁,桥的一端通向关学学派的悠久历史,另一端指向关学史研究的前进方向。随着保存在陕西各地的关学文献不断被发现,将来关学史研究可依据的史料会越来越丰富,关学史的研究也会越来越细致;但是《关学思想史》依然具有借鉴的价值,因为这座联结关学过去与现在的巨大桥梁是现代人学习和研究关学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