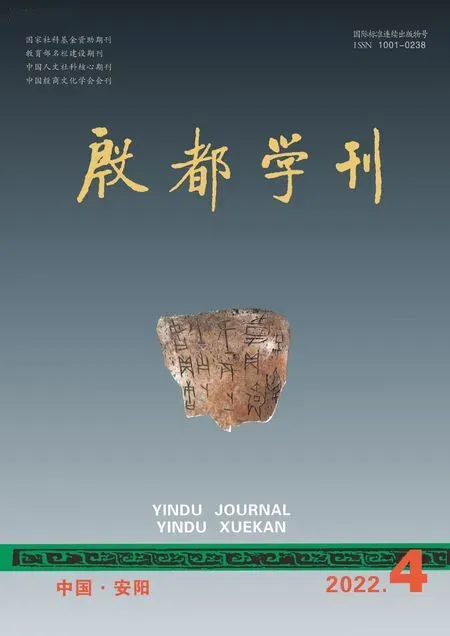豫北晋语语法研究概述
2022-02-09马静
马 静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豫北晋语的形成,是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及历史移民等多方面因素积淀的结果。豫北地区处于太行山与黄河故道相夹地带,自战国时期便隶属同一行政区划河内郡(1)路伟东:《河内郡始置于战国》,《历史地理》1999年第1期。。元朝末年,由于战争、天灾、徭役等原因,中原地区人口锐减,有些地方甚至“十不存一”。根据裴泽仁(1988),明初山西百姓多次移徙豫北,几乎持续了整个有明一代。明季豫北方言基本上是在山西泽潞二州(今山西晋城、长治)方言的基础上,融合原有土著方言形成的(2)裴泽仁:《明代人口移徙与豫北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一)》,《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由于移徙到彰德府、怀庆府和卫辉府(今豫北西部)的山西百姓人数占优势,“且呈墨渍式”(3)康国章:《晋人南迁与豫北晋方言的语言变异》,《殷都学刊》2012年第4期。分布于豫北地区,因此豫北西部的方言受山西晋语影响较大,至今仍保留喉塞韵尾。豫北地区封闭的自然环境及相对统一的政治统治为移民方言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
一、豫北晋语的分区
“晋语”由李荣先生率先提出,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4)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河南省北部有入声的方言归入晋语区。豫北晋语指分布于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包括安阳、安阳县、林州、鹤壁、汤阴、淇县、卫辉、辉县、新乡、新乡县、延津、获嘉、修武、武陟、温县、焦作、博爱、沁阳、济源19县市,即晋语邯新片中的获济小片。(5)沈明:《晋语的分区(稿)》,《方言》200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张启焕、陈天福、程仪编《河南方言研究》(1993)(6)张启焕、陈天福、程仪:《河南方言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与《河南省志·方言志》(1995)(7)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省志·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豫北晋语的划分趋于一致,都包含上述19县市,前者将河南方言分为五个片区,豫北有入声的地区划为以安阳话为代表的第四片区,称为安阳片;后者以安阳方言的音系为代表将豫北有入声的19个县市划为河南方言安沁片。
随着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学者对豫北晋语所含区域有了新的认识。支建刚(2018)(8)支建刚:《河南延津方言的入声今读及归属》,《语言科学》2018年第2期。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从延津方言高元音后增生衍音现象和周边方言入声调与阴平调调型调值相近两方面论证指出,延津县只有西北部的部分村镇保留入声,绝大部分区域的入声已经消失,应归入中原官话郑开片。笔者曾于延津县僧固乡大布村、县后街实地调查(9)随导师辛永芬至延津县僧固乡大布村做实地调查,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YY041)“河南境内中原官话与晋语边界点方言语法研究”研究内容。,也未发现有入声现象。史艳锋(2013)(10)史艳锋:《豫北晋语单字音与变音现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提出,孟州至今仍保留有独立入声调,应归于晋语区。此观点尚有争议,笔者以为入声韵消失,仅保留入声调,也是入声舒化的一种情况,应属中原官话。因此,研究认为豫北晋语包含除延津以外的其他18县市。
二、豫北晋语语法研究的现状
豫北晋语区别于中原官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有入声,其语音研究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尤其是入声问题和变韵问题。目前,豫北晋语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音层面。建国初期至2000年前后,豫北晋语的研究主要是为配合国家推普工作而编写的以学习普通话为主要目标的普及实用性材料,其对豫北各地方言语音的记录较为浅显粗略,未展开深入研究,但仍不失为后期研究的珍贵语料。2000年以后,形成以陈卫恒、陈鹏飞、支建刚、史艳锋等青年学者为研究主体的主力军,全面系统而又细致深入地探讨了豫北晋语的入声、Z变韵、D变韵、儿化等语音问题。可以说豫北晋语的语音研究已较为完善和深入,而其语法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单点语法的研究,还是区域性比较研究,都显得十分薄弱。
豫北晋语的语法研究从时间上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00年以前的全面描写阶段,主要成果是对变韵现象的提出;二是2000年之后的描写与解释并重的阶段,出现了运用语法化理论、跨方言比较、历史比较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新方法对虚词和变韵现象进一步深入分析的成果,推动了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也为后期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
(一)2000年以前的全面描写阶段
2000年以前的豫北晋语语法研究,主要是对语法现象的全面描写,包括对河南方言语法的概要描述和对豫北某地特殊用法的描写两方面,较少展开对语法现象的深入探讨和解释。主要成果是贺巍先生对获嘉方言各类变韵现象的详尽描写与分析。具体如下。
1.对河南方言语法的概要描述
张启焕、陈天福、程仪编《河南方言研究》(1993)(11)张启焕、陈天福、程仪:《河南方言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0—421页。系在20世纪60年代方言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增补完善而成,书中将河南方言分为五个片区,其中豫北有入声的地区划为以安阳话为代表的第四片区,称为安阳片,这是第一次将豫北有入声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书中介绍了安阳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及其与普通话的异同,虽有词汇和语法例句,但是从河南整个区域描写的,并没有在不同表述之后标注地域。而《河南省志·方言志》(1995)(12)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省志·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260页。描写了安阳方言的声韵调系统,例举河南地区的常用词并概述河南方言的语法特点,也未区分各方言点语法面貌的差异。这些成果涉及的语法描写,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豫北晋语的语法面貌,有助于了解河南方言各片区句法方面的轮廓,为后继者提供了重要材料参考,但并不利于作比较和深入研究。
还有少量论文描写了豫北方言中较为特殊的语法现象,如赵声磊《安阳方言的儿化现象—— 安阳方言琐谈之一》(1981),崔灿《豫北方言的文白异读》(1981),郭青萍《安阳话里的特殊语法现象》(1988)、《安阳话中的音变》(1990),宋玉柱《林县方言的几个语法特点》(1982)。这些论文注意到安阳方言同普通话有差异的一些语法现象,如儿化、“圪”头词、子尾、儿尾、音变、形容词的生动形式、结构助词“的”“了”“着”等特殊用法。这一时期是对豫北方言语法全面描写的阶段,较少比较、分析和溯源,但是发现了豫北晋语中区别于普通话和周边中原官话的特殊用法,为后学系统深入研究豫北晋语提供了材料参考和研究方向。
2.变韵现象的揭示
贺巍先生自1979年始,陆续在《方言》《语文研究》《中国语文》等权威期刊发表一系列关于获嘉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论文,如《获嘉方言韵母变化的功用举例》(1962)、《获嘉方言的连读变调》(1979)、《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1980)、《获嘉方言韵母的分类》(1982)、《获嘉方言形容词的后置成分》(1984)、《获嘉方言的轻声》(1987)、《获嘉方言词汇》(1989)、《获嘉方言的语法特点》(1990)等,并在此基础上出版《获嘉方言研究》(13)贺巍:《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一书,是豫北晋语单点研究的典范之作。贺巍先生首次提出获嘉方言中存在的变韵现象、合音现象及形容词的后置成分、表音字词头,细致地描写了儿化韵、Z变韵、D变韵中基本韵与变韵之间的对应关系,归纳总结变韵的条件、规律以及表义上的功用。其研究引起了学者对变韵现象的重视,为其他地区的方言调查提供了参考范本,指引了豫北地区方言研究的方向。至今豫北晋语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仍然集中在变韵层面。此外贺巍先生的《济源方言记略》(1981)(14)贺巍:《济源方言记略》,《方言》1981年第1期。描写了济源地区的声韵调系统、Z变韵、D变韵以及简要的词汇、语法例句,大致呈现了济源的语言面貌。
(二)2000年之后描写与解释并重的阶段
自1979年学位制实行,方言学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充壮大。众多硕士和博士加入到豫北晋语语法研究的队伍,推进了语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0年后,豫北晋语语法研究逐步系统深入。一方面出现了对单点方言语法进行较系统描写的成果,另一方面出现了运用语法化理论、跨方言比较、历史比较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新方法对虚词和变韵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成果,将研究从全面描写的阶段逐步推向描写与解释并重的阶段。具体如下。
1.对单点方言语法的系统描写
相较于2000年之前的普及性方言语法概述,此阶段出现了对单点方言作较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王芳《安阳方言语法研究》(2021)(15)王芳:《安阳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对安阳市区方言的词缀、重叠等构词法以及词类、体貌、处置句、感叹句等句法项目19类进行研究,着力描写了安阳方言中特色较为鲜明的代词、副词、语气词、疑问句等,追溯特定用法的历史来源,探索其语法化的历程,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呈现出安阳地区的语法面貌。穆亚伟《辉县方言语法研究》(2021)(16)穆亚伟:《辉县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从词、短语、句子三个层面对辉县方言的语法现象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与总结,每一章按照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描写辉县方言的语缀、重叠、副词、助词“叻”、“X人”结构、比较句、疑问句、被动句、处置句等用法。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解豫北方言的基本面貌提供了参考,也为后继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对照材料和研究框架。但是,以上成果较少展开与周边方言的横向比较,未描写出某一语法现象在地域上的过渡变化,也未总结出特色用法的历史继承和发展规律。
2.深入探讨虚词用法
豫北地区的虚词用法较为特殊,成为语法研究的热点。此类论文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周边方言作比较,并考察历史文献,运用语法化理论探索某一虚词的演变机制和路径。
(1)探讨普通话“了”的发展与演变
安阳、林州一带相应于普通话“了”的成分有不同的语音变体——“咾、啦”,多位学者就此展开深入探讨。如王琳《河南安阳方言“咾”》(2010)、《安阳方言中表达实现体貌的虚词——“咾”、“啦”及其与“了”的对应关系》(2010),陈鹏飞《豫北晋语语音演变研究》《林州方言“了”的语音变体及其语义分工》(2005),谷向伟《河南林州方言中表可能的情态助词“咾”》(2006)、博士论文《林州方言虚词研究》(2007),王芳博士论文《安阳方言语法研究》(2015),都通过方言中相应于“了”的成分的语音形式、句法分布、语法意义探讨了普通话中“了”的语法化过程,一致认为动词“了”经历了“完成动词→结果补语→动态助词”的虚化过程,方言中的相应成分“咾、啦”是虚化程度不同的同源成分并存于一个共时系统的现象。豫北晋语中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了”虚化演变的各个阶段,这对更清晰地认识普通话“了”的用法很有启发性。
(2)运用语法化理论探讨时间词“动、动儿”的虚化过程
陈鹏飞《河南林州方言的相对时结构“X”动》(2018)、王芳《河南安阳方言的时间助词“动儿”》(2014)、谷向伟《河南林州方言的“动”和“动 了”》(2007)都分析了“动、动儿”的结构特点、句法分布和语义功能,并通过与晋方言各地区“动、动儿”类结构的比较,探讨其语法化的过程,比较“VP动/动儿”与普通话“……的时候”的不同。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溯源两方面深入分析“可”“也”“连”等虚词的用法,如王琳《安阳方言中的副词“可”》(2009)、《安阳方言将行体助词“也”及其溯源》(2010)、《安阳话“当么”与“敢”的语法化及主观化》(2009 ),王芳、冯广艺《表处置义“连”字句的语义特点、语法功能和语法化途径——以豫北安阳方言为例》(2015),谷向伟《林州方言的“V 来/V上来”和“V 来了/V 上来了”》(2007)等。
3.变韵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继贺巍先生首次揭示变韵现象,后代学者在厘清方言中基本韵与变韵之间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运用语法化理论、实验语音学和历史比较等新方法,深入探讨变韵尤其是Z变韵的形成、演变与发展。牛顺心《河南武陟方言的子变韵及其形成与发展》(2008)(17)牛顺心:《河南武陟方言的子变韵及其形成与发展》,《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从跨方言比较的角度看武陟方言中子变韵的形成与发展,认为由于基本韵母与子变韵演变速度不一致,造成了基本韵母与子变韵的对应纷乱复杂。王临惠《晋豫一带方言变音源于“头”后缀试证》(2013)(18)王临惠:《晋豫一带方言变音源于“头”后缀试证》,《中国语文》2013年第4期。一文通过方言比较认为集中分布于河南北部、山西东南部及西南部的变音现象不是从“子”尾演变来的,而是从“头”尾演变来的。赵日新《豫北方言儿化韵的层次》(2020)(19)赵日新:《豫北方言儿化韵的层次》,《中国语文》2020年第5期。指出以往所说的Z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进而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的其中三个层次:[uou]层,[]层和[]层。支建刚《获嘉和济源方言Z变韵的形成与演变》(2021)(20)支建刚:《获嘉和济源方言Z变韵的形成与演变》,《现代语文》2021年第3期。在王洪君(1999)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法对获嘉和济源Z变韵的合音过程进行补充论述,并对比获嘉、济源Z变韵近几十年来的变化。认为表面上不规则的Z变韵可能是在更早期的单字韵基础上形成的。几十年间获嘉和济源方言的Z变韵都在发生由长音节向正常音节的变化。甘于恩、董一博《河南新乡方言子变韵的语音类型》(2020)(21)甘于恩、董一博:《河南新乡方言子变韵的语音类型》,《方言》2020年第2期。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将子变韵分为融合型、拼合型、鼻音型、长音型。这些研究都是语音层面上的深入探索。截至目前,Z变韵的合音过程仍未达成一致。
师蕾《辉县方言Z变韵的语法功能及其语法化》(2013)(22)师蕾:《辉县方言Z变韵的语法功能及其语法化》,《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从语法层面展开论述,认为Z变韵具有丰富的语法功能——派生、名词化标记、缩小词义或转义引申的标记、表达嫌弃厌恶的感情色彩,是古汉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法化的结果,并论述子变韵的语法化过程。
4.深入探讨子尾的语音分化和表义功能
5.挖掘出新的考察点——对形容词尤其是“老AA”式的初步考察
济源、焦作一带形容词尤其是“老AA”式用法较为丰富和特殊,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并不深入,没有出现较有影响力的成果。现有研究多是对形容词的适用范围、语音特点、句法特点、语用表达等方面的描写,还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语法研究外,还有郭艺丁、吴早生《河南新乡方言句末语气词“不咋”的主观义及其句法语用制约机制》(2020),穆亚伟、汪国胜《河南辉县方言的比较句》(2017),乔全生、鲁冰《论豫北晋语反复疑问句的过渡性特征》(2016)。其中,乔全生、鲁冰(2016)(23)乔全生、鲁冰:《论豫北晋语反复疑问句的过渡性特征》,《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以整个豫北晋语为考察对象,详细描写了豫北晋语区不同地理位置反复疑问句的分布类型,并归纳其过渡性特征,提出豫北晋语正逐渐向强势方言中原官话演变的观点。
综上可知,2000年之后豫北晋语的语法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逐步深入,由原来的全面描写逐渐向描写与解释并重过渡。但其与山西晋语、临近中原官话相比,研究力量十分薄弱,代表性成果也很少。
三、豫北晋语语法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豫北晋语语法研究的不足
1.各地区的语法研究不平衡
从研究成果上来说,豫北晋语所含18县市(不含延津)中,获嘉、安阳、林州、辉县地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对语法现象的描写也比较充分,但仍有一些地区,如汤阴、淇县、温县、沁阳等地成果寥寥,几无参考语料。此外,对豫北晋语语法进行整体考察的成果也很少。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现有语法研究集中在某些特殊用法的考察上,如多是零星地对变韵、代词、副词、形容词、语气词等词法以及“特色用法”“特殊句式”等句法的描写和讨论,研究面相对较窄,语法中的体貌、时制、语法化等领域鲜少涉及,缺乏全面、系统的描写。
2.语法研究以描写为主,缺乏横向比较和纵向溯源
目前豫北晋语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较少横向比较和深入挖掘,也未考察语法现象的成因及其语法化过程,研究还不够深入。
(二)对豫北晋语语法研究的展望
由上文可知,豫北晋语的单点方言研究和区域性研究都较为薄弱,尤其是区域性研究。目前各单点方言系统、全面的语法著述很少,也未出现有代表性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今后还需要更多学者倾注更多精力,开发和挖掘豫北晋语中蕴含的语言矿藏。在此,我们提出对豫北晋语今后发展的一点展望。
1.依托团队合作,对各县市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
在今后的发展中,如能树立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依托团队合作,深入地对各单点方言进行大面积系统调查,豫北晋语的研究将向前推进一大步。在此基础上,出版类似于山东、山西方言志系列丛书或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亦或对一种语言句法和形态作全面描写的参考语法系列丛书。各单点方言的全面深入调查,不仅可以促进各单点方言研究走向纵深,还可以为区域性研究提供珍贵的语料参考。
2.深入挖掘豫北晋语中有特色的语言现象
在全面系统描写各单点方言的基础上,总结豫北晋语区域性语法的共性及差异,由点到面展开方言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溯源,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系统探讨豫北晋语的演变路径和发展方向,搭建起研究豫北晋语和周边山西晋语及中原官话过渡性演变的桥梁,揭示现象背后的原理。以此填补豫北晋语区域性研究的空白。
3.重点考察豫北晋语中的虚词用法
虚词在豫北晋语中的用法较为丰富,往往以不同的语音形式对应不同的语法意义,还处于语法化的较早阶段,对于研究虚词的语法化过程很有帮助。现有成果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如较多文章涉及虚词“唠”“啦”“动、动儿”。此外,助词“哩、着、了、来”的分布与演变、“圪”头词的构词差异、人称代词领属结构的表现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豫北晋语是山西晋语与中原官话接触融合的产物,是典型的过渡性方言,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其单点研究以及区域性研究有待更多学者投入更多精力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