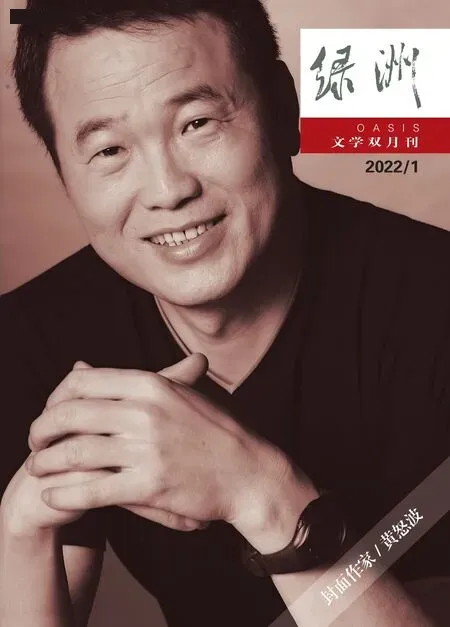哑巴娘
2022-02-07潘文
潘文
1
村里有个哑巴,住在我老家屋场的东南角。如果他能说话,站在我家的屋檐下就可以喊答应。哑巴父亲去世得早,哑巴和他娘就孤儿寡母过日子。
一个人不能说话,是莫大的苦寂。可对一个哑巴而言,得无条件接受。哑巴除了不会说话,还有些呆傻。笑是他最多的表情,但没有声音。哑巴或许并没觉得怎么样,一天到晚懵懵懂懂地过着日子,但是却难为了哑巴的娘。
哑巴出生的时候,虎头虎脑,样子极为可爱。没有人会想到他要遭受说不了话,且呆愣的这份罪。哑巴慢慢长大,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却总也说不上来。随后,大家又突然发现哑巴不仅说不来话,而且憨得很。哑巴娘开始紧张起来。四处寻医问药,虔诚求拜菩萨,单方也吃了无数。这样坚持数年,却毫无收效,只得认命。
哑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篾匠,为人善良,从无多言。听说哑巴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也乐了一阵子。后来见哑巴如此,一声长叹,又回归寂然。我们在屋场乱窜时,也常会越过天井,跑到他家里去。每次都看见他坐在挨近天井的矮凳上,低着头,默默地编织着各样的篾器:凉席、撮箕、篾篮、竹篾,哑巴就在旁邊坐着,将手拢在袖子里。看到薄薄的竹篾在父亲灵巧的手中不断翻飞,他便傻傻地笑。彼时,哑巴娘就在屋内或屋外,洗衣、做饭、挑水、喂猪和鸡鸭。每次经过天井,都会有意无意地望向哑巴。
母亲说,哑巴娘年轻时是很好看的。哑巴娘刚嫁过来时,整个村子就数她最漂亮。一连几天,都有外村人专程赶过来看她。快五十岁了,哑巴娘仍有着姣好的身材。只是她的皮肤已失去了光泽,干涩里透着暗黄。她穿着斜襟的衣裳,旧而黯淡,但也素雅洁净。从天井洒下来的阳光落在她灰黑的发上,也落在她发亮的眼眸里。她的目光柔和地在哑巴身上游移,带着一抹温存的笑意,还有不易觉出的轻叹、遗憾和担忧。
其时,哑巴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了。他并不是除了傻笑就什么都不做,有些时候,他也会帮着父亲把竹片从屋子外抱进来。只要父亲扬扬唯有手中剩下的篾片时,他就会立马没了笑容。然后慢慢把拢在袖子里的手抽出来,磨磨蹭蹭地走出去,再磨磨蹭蹭地走回来。即便再不情愿,回来时他的怀里还是会多上一捆篾片。
哑巴长得高大,一捆篾片抱在怀里,显得有些大材小用。但哑巴显然不太高兴。有时,他会把篾片往地上一丢,又继续把手拢进袖子,一屁股坐下来。听到声响,哑巴娘一个箭步从里屋窜了出来,扬起巴掌,朝哑巴脸上抽下去。
我们一惊,想跑出去,却又站着不敢挪动脚步。在心底里,我们其实很想看看哑巴到底会不会哭,会不会和他妈妈对打起来。只是从没受过巴掌的我们,看到哑巴娘的凶狠,都不寒而栗。哪个妈妈不疼崽?我们不知道哑巴娘为什么能下得了手去。
哑巴疼得很。手掌落下去,他的脸上立刻就留下了深红的手掌印。哑巴不哭也不闹,只是瞪圆了双眼,手捂着脸冲出屋去。哑巴父亲放下手里的活,两只手在青灰的围裙上搓了搓,然后猛地站起来,也跟着冲出屋子去。
哑巴娘的眼圈“嗖”地一下红了,眼泪噗噗往下掉。她伸出刚刚落在哑巴脸上的手掌,又紧紧捏成拳头,朝胸口狠狠擂了几拳:“你留下来的时候也不多了。你要走了,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他不学着做事,以后我老了,他怎么养活自己?”
哑巴娘的喊叫夹杂着哭声,从天井里飘散出去。那声音越来越小,慢慢地似乎就只剩下了无奈和苍白。而那个时候的我们,五六岁的孩子,并不曾知道那个家庭里难以言说的悲伤。我们看到哭喊过后的哑巴娘,在她默默坐下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只剩下木然。
不久后的某一天夜晚,寒风四起。冬日夜晚的凄冷,把村子里的人都关在了各自的屋子里。我们也是。屋子里唯一的一盏煤油灯明明灭灭,更添了一丝寒意。屋场外一片静寂,只有风夹着几声狗叫在村庄的上空回旋。
突然间,屋场东南方向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声。凄楚的哭声一声高过一声,整个村子瞬间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这是哑巴娘的哭声。娘说:“亮叔走了。病了好些年,走了也解脱了。”然后又幽幽地说:“可是懵古怎么办?就靠着他娘了。不容易呀。要是之前生的那两个带成了,总还不止如此。真是命苦的人。”
那日,我方才知道,哑巴娘曾有过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都夭折了。说这些的时候,母亲搂着我和妹妹肩膀的手愈来愈紧,直到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那一刻,我们被黑暗笼罩着,也被莫名的悲伤笼罩着。
2
但日子还得过。此后,哑巴娘每天出去做事都带着哑巴。挖土、砍柴、种田、栽菜……但凡别人家里要做的,哑巴娘都要做,一项也不肯落下。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哑巴就像一只影子,总是紧紧跟在哑巴娘的后面。
日子久了,村里的人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似乎慢慢忘记了哑巴娘的那些辛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村子里的人渐渐离哑巴娘远了。见了面也就是匆匆打声招呼,然后又急急离去。村里新来的媳妇更奇怪了,她们总是一看见哑巴娘和哑巴就绕道走。
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躲避着什么,就像在躲避一场瘟疫。
哑巴娘起初还主动和人家搭讪:“他婶,我明天要到山里砍柴,你一块去不?”“我去买点盐,家里没盐了。要我带点回来不?”
哑巴娘咧开嘴笑着,热情地朝人家迎上去。但没有人愿意让她带。一看到哑巴娘身后的哑巴,所有人就目光躲躲闪闪,疾速而去。哑巴娘说出的话,就好像是从嘴里飘出的一缕空气,一离开温热的唇,就立即消散了。
之后,哑巴娘就变得沉默了。如果不是碰到要紧的事,她就不太开口。她的性格开始乖戾起来,脸孔总是绷得很紧,走起路来像一阵风。她的肤色从暗黄变成黑黄,皱纹从眼角嘴角爬上了额头。原来盘起来的头发,也变得凌乱了,风一吹就飘了起来,像飞在空中的茅草。
村里头的孩子却都只怕哑巴,尽管他的笑善良而单纯。哑巴从未吓唬过任何一个小孩,可是大人们都再三地叮嘱自己的孩子离他远一点儿。我的父母虽然未曾交代我们莫走近他,但我见着他也是怯怯的。若是在路上遇着了,也先要远远停下,然后突然撒腿就跑,或者是躲起来。
娘说:“不要跑,他不会打人的。遇到他,你可以叫他叔,或者朝他点头微笑,他能够懂的。”而我却总有些担心,总觉着他的笑里藏着很多让人害怕的东西。
村里的其他孩子更怕。“再哭,再哭就叫哑巴把你背过去!”只要一哭的时候,大人就这样吓唬他。小孩子一听,哭声马上小了。他们将哑巴描绘成了一个让孩子们避而远之的恶人,凶巴巴的。
可小孩子们对呆傻的哑巴又充满了好奇。于是,常常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远远跟在哑巴后面,不时地故意“招惹”他。
其实,哑巴只是呆傻,他的心地并不坏。或者说,他心里藏着很多善念。所以,我们几乎没看见他对谁凶过,尤其是对小孩。相反,只要看见小孩,他的眼睛里立刻就有了些柔和。
几个孩子凑到一块的时候,总是想搞点恶作剧。“哑巴,哑巴,又呆又傻。只会砍柴,不会说话……”也有胆大的孩子,只要看到哑巴娘不在他身边,就笑话他,还向他扔石子。突如其来的袭击,常常让哑巴躲闪不及。但他从不还手,只是露着洁白的牙齿,傻傻地笑。
匆匆赶上来的哑巴娘却很尴尬,也很心疼,她总是拍着哑巴的肩,提着嗓门喊:“你就会笑,你就会笑。走,赶快做事去!”哑巴娘的话有些重,但我们都知道她不是骂哑巴,她是心疼又心酸。
哑巴娘没有带哑巴同出来的时候,只要遇见小孩,就会很热情的迎上来:“伢崽,有空就到我家去吃旱茶啊,懵古不会打你们的,懵古心地善着呢。”哑巴娘唤哑巴为懵古,但语气中满是怜爱。
虽然我们很怕哑巴,但是我们都很喜欢哑巴娘。哑巴娘会做很多花样的旱茶,还会浸萝卜、菜梗、番薯片,夏天还常常摘了屋后的凉粉坨做凉粉。这些村里大多的婶婶们也能弄,但是味道总是差了那么一点。也不晓得哑巴娘藏着一点什么小窍门。
很多时候,哑巴娘会从衣兜兜里掏出一包旱茶来。她小心翼翼地捧着,慢慢松出一只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然后又一层一层将洁白的手巾打开,再捧到孩子们面前:“伢崽,吃吧,先解解馋,好吃得很呢。往后再到家里吃。”
起先大家都不敢拿,你推我搡。哑巴娘又说:“都拿些去吃吧,莫要告诉家里就是。”于是,大家一哄向前,拿过自己喜欢的旱茶后又一哄而散。
“记得不要怕懵古,他不会打人的,你们也莫要拿石头打他,会很疼的。”哑巴娘立在那里,扬了扬手中的白手巾,声音似乎焦躁不安。孩子们乐滋滋地吃着旱茶,一阵风,把哑巴娘的声音吹跑了。
但大多时候,哑巴娘是和哑巴一同出来的。在哑巴面前,哑巴娘的模样和神情似乎都有了些变化。他们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每次哑巴娘都走在前面,和箩筐或者背篓或者其他农具一块横在哑巴的前面。哑巴娘的身躯在那一刻似乎魁梧了起来,模样也威严了起来。
而哑巴,就跟在娘的后面,东瞅西望。哑巴出门时的装束基本上是不变的,头上用旧得发白的手巾扎了一圈,腰上捆着粗粗的秆绳。衣服是破旧的,一补再补,但丝毫不显得邋遢。
有哑巴娘在,哪怕是胆子大的孩子,也是不敢捉弄哑巴的。我敢断定,哑巴其实也是期望看见小孩的,哪怕是欺负他的小孩。他的世界过于单调,过于平淡,他也期望千姿百态的生活。而哑巴娘却不这样想。
3
因为孤儿寡母的,哑巴和哑巴娘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
田里地里,粗活细活,屋内屋外,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啞巴娘一手一脚去做。哑巴也能吃苦,但只能做些呆活。挑水、担谷、扛柴,每次出去,总是沉沉地压了一肩。
哑巴不晓得累,三十二岁的光景,哑巴有的是力气。一大捆的柴,哑巴轻轻地就能拎起,好像拎着一只小鸡。哑巴娘似乎也不知道累。她常常光着脚在地里劳动,冬天才穿上鞋子。她总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从没有停歇。为了省下时间,到山上或地里干活,他们便带上简单的吃食和茶水,一干就一整天。
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常常能看到哑巴和他娘猫在地里,挥舞着锄头或者镰刀。哑巴娘的衣衫总是很旧,很多地方开了口子。手腕上被撕开的那一片,跟随着镰刀一块晃动,哑巴娘也懒得去管,只有哑巴,指着那片飘动的布嗤嗤地笑。
有时,哑巴娘会不停地使唤:“懵古,有什么好笑,把这堆草抱走。懵古,你把土挑到那边去……”哑巴娘一只手扶着锄头把,一只手不停地比画着。起先有些吃力,慢慢就娴熟和简单起来。
也有些时候,哑巴不听使唤。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或者干脆躺倒在地。随便扯下几根草,滋滋有味地在嘴里嚼着。哑巴娘叫不动,也便由着他。割草、挖土、挑粪……她在地里来来回回,很少停歇。
偶尔,哑巴娘也会坐下来。她拿拳头锤锤腰腿,然后麻利地从一旁的布兜兜里拿出一个米饼,掰一小口放进自己嘴巴,余的全塞给哑巴。哑巴立刻把饼塞进嘴里,傻傻地笑。他的笑里有些虚弱。哑巴娘一手抚着哑巴粗糙的脸,一边用手擦了擦眼角。
一个晚上,刚吹灭煤油灯,我们和母亲正要上床睡觉。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随之屋场的狗也一阵一阵地叫了起来。我有些害怕,紧紧拉住母亲,不肯让她去开门。会有谁呢?母亲安抚好我和妹妹,重新点上灯盏。
“菊华,懵古浑身没劲,又呕吐,我该怎么办?他一定是生病了,你帮帮我。”是哑巴娘的声音,她的语调总是又急又快,这会就更急促了。
母亲并非医生,但因为教书,备受村子里的人敬重。家家户户有些难解的事情,总是会先想到母亲。哑巴娘也不例外。见她着急,母亲先是安慰着。粗略问了些情况后,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小药瓶,拔腿跟着哑巴娘过去了。
母亲出去了一会,又急匆匆回来了。她一边唤我们起来,一边端着煤油灯进了灶房。等我们穿整齐衣服,母亲已经把两碗热气腾腾的面端出来了。我正不解,她又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竹篮,里面盛着半篮鸡蛋。娘说,哑巴是饿着了。
就着零星的月光,我们端着面条,拎着鸡蛋进了哑巴娘的屋。哑巴娘见着,反复推辞,不肯接受,见母亲态度坚决,方才默不作声。母亲说:“去吧,给懵古吃点,会好些。”哑巴娘似乎才反应过来,赶忙点点头,端起一碗面朝哑巴房里走去。母亲拿着灯盏,紧紧跟着。
哑巴斜靠在床上,看起来没有一点儿气力。漆黑的屋里突然有亮光,他似乎有些不适应,下意识地往里蜷缩着。但他似乎又闻到了某种特别的香味,带着葱、姜的清香,还有浏阳豆豉特有的味道。
他的脸刚侧过去,又立马扭转过来,逐渐发亮的双眼充满着期待。哑巴娘在床沿坐下,一只手扳过哑巴肩膀。然后将筷子插进碗里,快速转一圈,面条便紧紧缠在筷子上了。哑巴娘将带着面条的筷子伸进哑巴的嘴里时,自己也微微张开嘴,然后又咂巴着嘴唇。橘黄的灯光给她的脸抹上了几缕红晕。
很快,一碗面吃完了。哑巴娘又端起另一碗。
母亲想要阻止,又有不忍。哑巴吃得很开心,昏暗的灯光下,他憨憨的笑容又一点一点从他那粗黑的脸孔上冒了出来。
哑巴娘喂着面,也轻轻地啜泣着。她时不时的将拿筷子的手抬起来,用袖口擦着眼角。
娘看得有些心酸:“张婶,莫要再喂了,多了反而不好。懵古只是饿了,今天砍柴又淋雨了。你也吃点,过两三年你也是六十的人了,身子骨不经老这样折腾。那点鸡蛋,能够吃几天,你们都要补充下营养。”
哑巴娘放下碗,站了起来,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她的眼里闪着晶莹的亮光:“菊华,你对我们孤儿寡母真好。大家都把我们看成扫把星,你却不嫌弃我们。实在是没办法,青黄不接的,家里也实在揭不开锅。但凡有我吃的,也不会让懵古饿着。”她说着,又流下泪来。
那个夜晚后,哑巴娘见着母亲就分外亲切起来,丝毫没有了先前的拘谨。母亲见着她,总是隔着好远就朝她扬手,或者大声叫唤:“张婶,又到地里去呀?”哑巴娘于是轻快地应着:“是呀,那番薯还不挖要烂在地里了呢。”如果旁边有人,哑巴娘便会停下来,故意将声音拔高几分:“菊华,有空到我家去坐坐啊。”
日复一日。村里的人不再那么害怕哑巴和哑巴娘了。遇着了,也会打招呼。哑巴娘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是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又开始生动起来,衣衫又慢慢齐整起来。
4
“摊上这样一个儿子,又能怎样?总不能扔下不管吧?”哑巴娘时常在我娘面前这样感叹,“只有认命,就是不晓得以后我老了他怎么办?”哑巴娘最担忧的恐怕就是这个。
我娘只是默然,无以安慰。有时,她会留哑巴娘在家里吃口饭。她们在厨房一起做饭,也说笑。听到哑巴娘的说笑声,我也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开心。
“钉板也要生得好。你看,生在你们家多好。天天都有油吃,亮晃晃的,不像我们家的干枯的很。”哑巴娘揶揄。
我娘便笑,又像无奈。
空闲的时候,娘就领着我和姐妹上她家坐坐。每次去,总要拎上一点什么。有娘在,我们是不怕哑巴的。哑巴娘也格外小心,见我们去,就将哑巴叫开:“去,去,到那边去。”
哑巴就听话地走到厅屋天井的那一头去了。我们坐在饭桌前,吃哑巴娘为我们端上的旱茶。这个时候的哑巴娘特别高兴,似乎还有点兴奋:“吃,吃,莫要嫌弃,我都洗得很干净,干干净净的。”
在娘的默许下,我们姊妹就不再客气,一个劲地吃。平素见我们这样,娘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哑巴家,娘似乎特别的宽松。
愈是这样,哑巴娘就愈是高兴。哑巴似乎也很高兴。他听话地站在天井的那头,倚着屋子的门框,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憨笑着。我们每吃一会,就转过头去,朝他扮个鬼脸,他笑得更开心了。笑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往前挪挪,但马上又缩了回去。
这样的时候,娘会悄悄暗示我们,要我们招呼哑巴也坐过来吃。我们起先不太情愿,但也惧怕娘柔和里的严厉。于是我伸出手,朝哑巴招了招:“哑巴叔,你过来吃东西呀。”
看到我招手,哑巴眼睛一亮,立刻兴奋起来。他刚刚迈出一步,哑巴娘即刻呵斥道:“懵古,出去喂牛!”哑巴立刻局促起來,眼光瞬间暗淡了。他不安地看着他的娘,好像犯了很大的错一样。然后又低下头,快速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从侧门出去。
哑巴慌乱和不安的眼神让我有些难过,但哑巴娘显然更加亲热了。她一个劲地将吃的往我们手中拿,还不断地夸着:“真是读书人家的孩子,真是好孩子。”临走时,哑巴娘还往我们口袋塞上几把旱茶。
哑巴娘家里没有小孩,客人也不见多,但她的咸旱茶做了一昙又一昙,做了给谁吃啊?我们问娘的时候,她笑而不答。哑巴娘也偶尔给我们做布鞋,纳鞋底,她的针线功夫真好。
因为娘的缘故,哑巴娘对我们极好。渐渐地,我们去哑巴娘家的时间多了起来,每次去,我都欢喜得很。哑巴娘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的点心也愈发精致了。农活不是很忙的时候,母亲也邀村里的大婶、姨婆们一起去,小孩们也跟着。
见旁人去,哑巴娘有些局促不安,紧张得双手直直地往围裙上擦。慢慢也就回过神来,忙里忙外,端茶倒水,脚步都轻盈了许多。大人们说说笑笑,小孩儿跑跑跳跳,哑巴家里瞬间亮堂起来。
从那以后,她做的布鞋也渐渐穿在村里老人们脚上。人们都说:“张婶是个好人呢,都是命不好。”大家在数着哑巴娘的不幸时,也常常会感叹万分。还有的说着说着就会掉下些泪来。
村子里打了鱼捞了虾的,树上摘了新鲜果子的,杀了过年猪的,即便不多,也还是会给张婶留一小份。农忙时,各家都会挤出些时间到哑巴娘的地里帮衬。这种似乎也成了村子里约定俗成的事。
久而久之,我们也不怕哑巴了。哑巴见着我们就会咧着嘴笑,有时候打打手势。虽然我们并不懂得那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他是友善的。村子里的孩子们也都一块慢慢长大,不再有人捉弄哑巴了,这于哑巴娘更是个安慰。
几年后,我们全家离开了那个屋场,离开了那个村子。曾有一度,哑巴和哑巴娘慢慢淡出了视野,慢慢淡出了记忆。哑巴一直未婚。因为带着哑巴的缘故,哑巴娘也未曾再嫁。始终如一的守护在哑巴旁边。
我们偶尔会回一次老家,但因为匆忙,也很少能见上。一年春节,娘说不知道张婶怎么样了,于是绕进去看看。快七十岁的哑巴娘显得老了,脸上的皱纹很是明显,但她的背丝毫都没有驼,依然直挺。哑巴似乎也有些老了。我们刚要进去的时候,哑巴娘和哑巴正要出门,依然是一前一后,依然拎着背篓。尽管有些衰老,但是只要能够劳动,生活依然会继续。
娘说,张婶活得真是不容易。此后,每次回村,娘都会去看哑巴娘。悠长的岁月里,哑巴娘顽强地生活在村子里,像一棵老树,撑起一片母爱的天空。又过了几年,村里人说哑巴娘的日子好过些了,因为党的好政策,哑巴娘不用再为她与哑巴儿子的生计而奔忙。娘听了,心里欢喜得很,我也特别欣慰。
前些日子,我们回乡下,突然惊喜地看到哑巴家的屋子翻新了。乳白色的墙,干净敞亮的屋子。院里种了些花草,用木栅栏围着。屋后的一角辟出了一畦菜地,辣椒一串串的,红得正欢。另一角则圈了几只鸡鸭,都藏在树荫里了。九十六岁的哑巴娘坐在院子里剥豆角,微微仰头,嘴角都是笑意。
责任编辑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