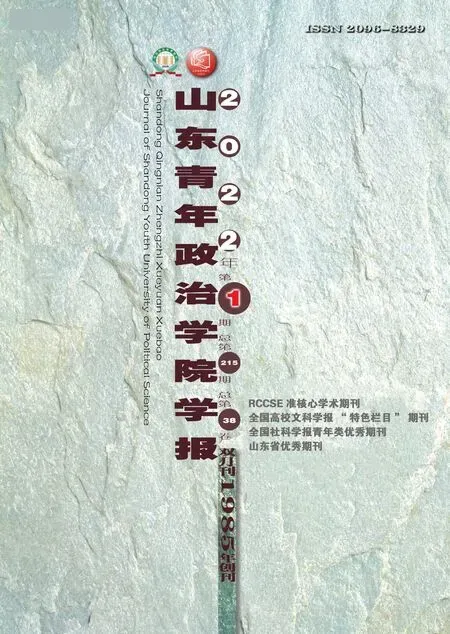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与相关问题探赜
2022-02-05郑威
郑 威
(广西大学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南宁 530000)
两汉之际的时间范围,“始于西汉哀平之世,终于东汉明帝时期”[1],共计82年。两汉之际,是两汉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同时亦是两汉学术文化、思想风尚发生显著嬗变的时期。奏议文是记载汉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引用《诗经》的问题,蕴含了两汉之际经学与文学发展的宝贵信息。本文通过梳理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的材料,力求细致归类并了解其规律性,探寻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所反映出的相关诗经学史问题与文学问题,故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讨论。
笔者依据《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和清代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两部总集,勾稽和梳理两汉之际奏议文的文献材料。两汉之际包含三个历史时期:哀帝、平帝时期,时间范围是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引诗用诗的奏议文是6篇,共计引用《诗经》17次。王莽时期,时间范围是从居摄元年(公元6年)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引诗用诗的奏议文是3篇,共计引用4次。自王莽被杀至刘秀即位于千秋亭,中间数年(公元23-25年)是群雄逐鹿的大混战时期,更始政权、建世政权次第建立,皆有称帝之实。故臣子向这些新立君主呈递的进御奏议,亦应纳入到两汉之际奏议文的讨论范围内。这数年引诗用诗的奏议文是1篇,引用《诗经》1次。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是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始,至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止。这一时期引诗用诗的奏议篇目和引用次数,较上述两个时期为多,引诗用诗的奏议文共是12篇,引用《诗经》13次。汇总而言,两汉之际奏议文共计22篇引用《诗经》,引诗用诗总数为35次。
一、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特点
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的特征,关涉语义变化、选诗倾向、引用形式三个方面的问题。探究并解决以上三者,是厘清和把握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特点的关键。
(一)以直取诗之义为主,较少断章取义
从语义的契合来考察,奏议文引诗用诗时涉及到三个意义对象:奏议作者的使用意义、所引诗句的意义和《诗经》篇章的整体意义。其中,所引诗句的意义既是《诗经》篇章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即将进入奏议文的意义体系中,起到连接两端的桥梁作用。当奏议作者在遵循《诗经》篇章整体意义下引用诗句,同奏议文的意义表达相贴合,这是直取其义。但是,所引用诗句在离开《诗经》篇章的语境时,其本身的字面意义或者说独立意义便立刻由隐匿到复现。当奏议文作者引用诗句进入到新的语境中,只摘取字面的语词义,不顾《诗经》篇章的意义,而以证己见、以圆己说,则是断章取义。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主要分为直取其义和断章取义两种情况。其中,直取其义计29次,占比总引用次数的83%;断章取义涉及5篇6次,占比总引用次数的17%。
直取其义之例,如孔光《上书对问日蚀事》所引“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句,出自《周颂·敬之》,是君臣戒成王之诗,希望成王敬畏天道、慎保周疆。孔光征引此句时直取其义,告诫哀帝当敬畏日蚀异变,总正万事、补察时政,在语义上是两相契合的。又如班彪《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引《大雅·文王有声》之“贻厥孙谋,以宴翼子”句,建议当为皇太子、诸侯王选配通习政事的名傅贤臣,以使他们接受正向教导,继承祖宗的优良智慧,以得为君之道。所引诗句,意为贤明武王遗留下治国良策、庇荫子孙,恰与奏议文的意义表达相合。断章取义之例,如鲁匡《上言令官作酒》,所引“无酒酤我”句出自《小雅·伐木》。据《毛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2]可知,该句表现的是饮酒宴会、亲友和谐欢洽的场面。鲁匡在引用时为证己说,只摘取“酒”“酤”之义,引申为“酒酤在官”,弃置诗篇的整体意旨,乃断章取义的典型表现。
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时较少断章取义,这与奏议文的公文属性①是有密切关系的。奏议文是一种应用型公文,要求文义表达和观点陈述要真实、平易。刘勰《文心雕龙·奏启》云:“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3]指出明辨通畅乃奏议文写作的首要任务。奏议文引诗用诗多直取其义,直露明晰,较少采用断章取义这一朦胧隔膜的意义表达方式,能够降低理解奏议文的难度,提高处置朝廷事务的行政效率。
(二)以引《雅》《颂》诗为主,选取带有积极的、赞美的感情色彩的诗篇
从两汉之际奏议文所引用诗篇在《风》《雅》《颂》诗中的分布来考察,多引《雅》《颂》,少引《风》诗。共征引了《大雅》10篇14次,《小雅》8篇9次,两者合计18篇23次,占比总引数已近七成;征引《颂》诗6篇8次,占比二成多;引用《风》诗3篇4次,其中《召南·甘棠》2次,《曹风·候人》《曹风·鸤鸠》各1次。两汉之际奏议文以引《雅》《颂》诗为主,只是一个整体取向。若深入细究会发现,它有着更为具体、细化的引用倾向。主要撷取二《雅》中带有积极的、赞美的感情色彩的诗篇。即使所引篇目以讽刺性、批判性为主,亦属于反用,来证明己说或称美君主。故两汉之际奏议文的总体艺术风格是纡徐、和缓,多是经生醇儒之言,与东汉中后期多任气批判之作大不同。
对于《雅》诗而言,鲁匡《上言令官作酒》所引的《小雅》之《伐木》,宴饮欢乐之诗。刘歆《孝武庙不毁议》所引的《六月》和《采芑》,美宣王北伐、南征的中兴之功。王莽《言立官稷》所引的《甫田》、钟离意《谏起北宫疏》所引的《大田》,诗中回荡着庄稼长势喜人、庆祝五谷丰登的满足之情。李寻《对诏问灾异》所引的《十月之交》、张竦《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所引的《小宛》、朱勃《诣阙上书理马援》所引的《巷伯》,三首皆是刺诗。但第一首是借灾异指出当前政失之由,鼓励初即位的哀帝变革前政,焕然一新;第二首是用来称赞王莽温和恭谨的品性;第三首乃说明谗害马援之人的可恶,希望王德圣政而不忘功臣。李寻《对诏问灾异》所引的《大雅》之《文王》《皇矣》、张竦《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所引用的《大明》、王莽《言立官稷》所引的《绵》、张纯《奏宜封禅》所引的《下武》、班彪《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所引的《文王有声》、杜林《上疏议郊祀故事》所引的《假乐》,皆是正雅之诗,格调高亢,洋溢着对西周初期的君主接续开拓基业、积极进取的美赞情感。张竦《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这一长篇颂章,还引用了《烝民》《抑》《瞻卬》三诗:《烝民》是赞宣王与贤臣仲山甫之诗;《抑》虽不乏灰色格调,但作诗的主要目的仍是劝诫和激励平王重振君威;《瞻卬》全篇充斥着国衰民困的怨愤之情,引用此诗之句强化了傅太后逐斥王莽的负面效果,表达了对王莽重新掌权后霍然四除、更为宁朝的赞叹之情。
《颂》诗,美盛德之形容,是颂赞先公先王的宗庙之诗,感情倾向本就昂扬向上。刘苍《世祖庙乐舞议》所引用的《周颂·清庙》、孔光《上书对问日蚀事》所引用的《周颂·我将》和《周颂·敬之》、窦融《封皇子议》所引用的《鲁颂·閟宫》,分别颂文王、诫成王、赞僖公。所引《风》诗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和倾向。在所引4例中,《召南·甘棠》引用2次(刘苍《上书谏猎》《上疏归职》各1次),其美召公德行的诗旨受到了奏议文作者的偏爱。鲍宣《上书谏哀帝》所引用的《曹风·鸤鸠》,是“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专一”[4]之诗,赞美君子的品行坚贞如一。刘苍《上疏归职》所引的《曹风·候人》,刺君主疏远贤君子而亲近小人,刘苍引用此篇之句是为了自谦以辞受明帝恩宠。
综上可知,两汉之际奏议文在多引《诗经》之《雅》《颂》诗的倾向下,于其中选取具有积极正向感情色彩的诗篇之句入奏议。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诗经》中的贤君(主要是周文王、武王、成王)、贤臣(如召伯、仲山甫等)、贤君子(具有坚贞专一的美好品德)被高频次地征引到奏议文当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奏议作者试图为帝王树立良好的典范榜样,引导帝王励精图治而增强国力的良苦用心。
(三)以常用的引诗用诗的结构形式为主,但又有新的变化
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的结构形式多是以“诗云”“诗曰”为引用标志词,援引诗篇原句,入奏议文中。如张纯《奏宜封禅》“《诗》云:‘受天之祜,四方来贺’”。这一引用形式属于直接引用,计有27次。
另有7篇9次,其引用形式不同惯常,属于化用,可归为4类。一是引诗篇名,代称全诗之旨。如鲍宣《上书谏哀帝》“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引用了《曹风·鸤鸠》篇名;二是摘取诗句之字词,代称全句之义。如杜诗《荐伏湛疏》“是故《诗》称‘济济’”,摘取了《大雅·文王》“济济多士”一句中的字词;三是改造所引诗句的文字,嵌入、融合进奏议文的语句中。这种改造,包括对所引诗句的文字进行拆分、调序、整合以及添加无意义的结构助词等。如刘歆《功显君丧服议》“是以殷有翼翼之化”、“今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分别化用了《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句与《周颂·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句。又如刘苍《上疏归职》“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化用《曹风·候人》“三百赤绂”句;四是依据所引诗句义,更换表述方式。如严尤《谏伐匈奴》“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化用了《小雅·六月》“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句和“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句。需要说明的是,刘苍《上书谏猎》引《大雅·抑》,虽然在引诗时是以“《诗》云”开头,但所引诗句是由首章前两句“抑抑威仪,惟德之隅”与第二章末两句“敬慎威仪,惟民之则”并引而成,不是直接引用,故亦归类探究。
两汉之际奏议文,其引诗用诗结构形式的新变,在汉代奏议文引诗用诗形式的发展中,起到的是过渡、铺垫的作用。表现在两点:第一,从变化类型看。4种化用《诗经》的类型,相较于成帝时期,不仅类型更加丰富,而且运用时更为纯熟和舒展;相较于东汉时期,已基本上不出这4种类型。第二,从使用频率看。9处化用的例证,已占总引用数的四分之一,较成帝之前,频数已大大提高。相较于东汉明帝之后的诏奏占比一半的“化用”现象,确如大雨前的惊雷,已轰隆作响。综合以上,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形式的嬗变,对于后代奏议文,进而扩展至其它文体的引诗用诗的结构形式,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在语言上,《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富于韵律、节奏鲜明,吟诵时回环跌宕;奏议文则是以散句为主,语句长短不一,注重语言的灵动性与阅读的顺畅感。引用《诗经》之句入奏议文,两者在语句上具有差异性和互斥性。奏议文作者通过这4种类型的引用形式,将《诗经》规整的四言句融合入奏议文中,使两者在文字上完美相契,在节奏上顺畅和谐,反映了他们对于《诗经》的谙熟于心与巧妙运用。
二、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折射的诗经学史问题
两汉之际奏议文所引用的诗句,并不专主一家诗,而是齐、鲁、韩、毛四家诗均有所引用。同时,两汉之际三个历史时期,奏议文引用《诗经》的次数,亦并不均衡。从汉代经学发展史的角度观照这些问题,可以发现它们折射出丰富的诗经学史信息。
(一)引诗用诗的四家诗归属与两汉之际《诗经》的传播、接受
比勘两汉之际奏议文所引诗句与《毛诗正义》,在所有35处引用中,计有13处,在文字上异于今本《毛诗》。汉代传《诗》四家中,鲁、韩、齐诗相继在文、景时期立为博士,《毛诗》后出,未得立。两汉之际奏议文所引用的诗句,判断和明确其归属于四家诗中的哪一家,能够为管窥两汉之际《诗经》的传播、接受状况,提供重要的材料。
清代学者在三家诗辑佚与疏证方面成果迭现,范家相、徐堂、阮元、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等,均做了艰苦而卓越的工作,而又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为集成之作。王先谦在辑佚过程中,对涉及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共计8篇10次,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诗家归属断定。其中,5篇6次引用《齐诗》,1篇2次引用《鲁诗》,2篇2次引用《韩诗》。
因三家诗多亡佚,加之文本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校改、讹误等,对于我们从作品的角度来判断每一条引诗的来源造成了障碍。除从作品本身去探求外,还可以转换思路,从作者角度来切入。作品是作者制造的文字产品,作者的主观情志和思想倾向,往往直接投射到作品中,知人论世、文气说等古代文论,已有精到阐述。汉代的文学家族注重家学的传扬,后世子孙所受到的知识教育以及他们的文学创造,打上了鲜明的先辈印记和家学特征,这为我们从作者角度判断两汉之际奏议文所引用诗句的来源,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如刘歆《孝武庙不毁议》所引诗句,“至于太原”之“太”字,“啴啴推推”之“推”字,“勿鬋勿伐,邵伯所茇”之“鬋”“邵”字,《毛诗》作“大”“焞”“翦”“召”;“荆蛮来威”,《毛诗》作“蛮荆来威”。另据上文,其《功显君丧服议》,是在语词和语义上化用了“商邑翼翼”与“遭家不造”句。刘歆上述引用,当皆是《鲁诗》。据《汉书·楚元王交传》载:“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为元王诗,世或有之。”[5]自其先祖刘交开始,这个家族便有研读《鲁诗》的浓厚绵远的文化传统。刘歆的曾祖刘辟彊亦好读《诗》,父亲刘向善文辞,堪称博学,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代诏宦者署,为黄门郎”[6]。由以上所举字词之异,加之其家学渊源,可断刘歆《孝武庙不毁议》《功显君丧服议》所引用诗句乃《鲁诗》。
又如张竦《为陈崇草奏称莽功德》所引诗句,“不侮鳏寡”之“鳏”字,“邦国殄顇”之“顇”字,“惟师尚父”之“惟”字,“时惟膺扬”之“惟”“膺”字,“亮彼武王”之“亮”字,“亡言不雠,亡德不报”之“亡”字,《毛诗正义》分别作“矜”“瘁”“维”“维”“鹰”“凉”“无”字。《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曰:“(张)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然政事不及也。”[7]又《谷永杜邺传》曰:“(杜)邺少孤,其母张敞女。邺壮,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以孝廉为郎。”[8]从彼此的亲属辈分推断,杜邺与张竦乃表亲兄弟。再据《谷永杜邺传》:“初,邺从张吉学,吉子竦又孤弱,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9]可知杜邺曾跟随张竦之父张吉学习,张吉之子张竦又曾追随杜邺学习。由杜邺现存《灾异对》《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等奏议文的内容看,以阴阳灾异推论政治,嘉瑞、阴阳、日蚀、地震等词密集出现在奏议文中,当是《齐诗》的思想路数。杜邺之子杜林奏议文中引诗用诗的线索,也可作为佐证。因而,杜邺研习《齐诗》的可能性较大。学于杜邺的张竦,便亦可能传承的是《齐诗》之义。另外,该奏所引“夙夜匪解”句,《鲁诗》与《韩诗》皆写作“懈”,唯《齐诗》与《毛诗》作“解”字。这一字句异同,亦是张竦习《齐诗》的旁证。综上,张竦《为陈崇作奏称莽功德》所引诗句,当来自《齐诗》。
奏议文所引用诗句的意义内涵,是一篇奏议文完整内容意义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被包含—包含”的关系。同时,奏议文在引诗用诗时,有时也会对诗意加以阐述。因此,通过解读奏议文篇章的内容与所引用诗句的意义,来辨别引诗用诗同哪一家诗的诗意阐释相合,是判别诗家归属的第三个角度。
有的应当是《齐诗》。如杜林《上疏议郊祀故事》曰:“《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杜林对所引该诗句的阐释,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郊语篇》曰:“《诗》云:‘不骞不忘,率由旧章。’‘旧章’者,先圣人之故文章者。”[10]可见,杜林对此句引诗的意义阐发,与董仲舒如出一辙。清人研究三家诗的著作,均将董仲舒列入《齐诗》学派。虽有当今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我们不宜先入为主地将董仲舒的《诗》学划归到《齐诗》的范围内”[11],但“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12],确带有《齐诗》学的典型征象。故杜林奏议所引,应推断为《齐诗》。同样,其《请徙张步降兵疏》引“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句,亦当为《齐诗》②。
有的应当是《韩诗》义。如鲍宣《上书谏哀帝》所引《曹风·鸤鸠》篇名。《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载,曹植奏议文有“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13]句,乃是源自《曹风·鸤鸠》的征引。曹植作品多引《韩诗》,故其意义解说,应为《韩诗》义。鲍宣奏议文所引《鸤鸠》,表达的正是均平养长、抚育百姓之义,与曹植相同。故鲍宣所引,类推亦应为《韩诗》义。另有刘苍《上书谏猎》用《召南·甘棠》之篇名,似为《韩诗》③。
有的则为《毛诗》。严尤《谏伐匈奴》这篇奏议文所化用的《小雅·六月》之句,当出自《毛诗》。原因之一,关于《小雅·六月》的主旨意义,《毛传》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14],《谏伐匈奴》便有“当周宣王时”之说。原因之二,《小雅·六月》“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一句,据《郑笺》释义曰:“匪,非。茹,度也。镐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猃狁之来侵,非其所当度为也,乃自整齐而处周之焦获,来侵至泾水之北。言其大恣也。”[15]《谏伐匈奴》“猃狁内侵,至于泾阳”与之隼牟相契。原因之三,《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句,《毛传》释云:“言逐出之而已。”[16]孔颖达疏曰:“不言与战。经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强,猃狁奔走,不敢与战,吉甫直逐出之而已。”[17]另,李山《诗经析读》亦云:“史言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大原当是周朝领地。善战的王朝军队乘胜逐北之时,却只是将敌人赶出境外,表现得十分有节制。”[18]《谏伐匈奴》“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可谓是此句句义的同等转换。综上,严尤《谏伐匈奴》所引用诗句的含义,与《毛诗》高度相符,当断为《毛诗》。此外,有两篇引诗,只能权且归为《毛诗》,难下定论。如窦融《封皇子议》所引“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句与张纯《奏宜封禅》所引“受天之祜,四方来贺”句,所引为《毛诗》的可能性较大。
基于以上三个角度,我们对多数引诗用诗的四家诗归属问题,作出了判断。但是,由于四家诗对诗义的解读难免存在趋同之处,这为我们遽断其属于某一家,带来了难度。对于这些材料,不妨本着谨严的态度而权且存疑。如鲁匡《上言令官作酒》所引“无酒酤我”句,释“酤”为“买”之意。《说文解字》曰:“酤,一宿酒也,一曰买酒也,从酉,古声。”[19]“酤买”之说,四家诗义均同,难以明确其归属于哪一家诗。钟离意《谏起北宫疏》所引《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句,并释义为“君臣相济,上下同忧”。齐、鲁、韩三家诗都有例证表明与这一释义相合,《毛诗》义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四家诗同义,故存疑不断。此外,有一个引诗用诗现象值得注意。李寻《对诏问灾异》中“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李淑《上疏谏更始》中“思隆周文济济之美”句与杜诗《荐伏湛疏》中“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句,这3篇奏议文引诗用诗的共同特征是或直引或化用了《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句。所引用的诗句,在奏议文中已经浓缩为举荐人才、重视人才的意符,在西汉哀帝、更始帝、东汉光武帝三个不同的时期,表达着相同的含义,形成了相对凝练和固定的意义表达。在这样一个意象含义中,难以明言其是四家诗中的某一家。总之,以上4篇奏议文难以确定诗家归属情况。
经过上述全面地研判,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三个现象。
第一,两汉之际《诗经》的传播与接受,仍然是以三家诗为主。《毛诗》虽有传授,但并非主流。两汉之际引诗用诗的奏议文作者中,引用《齐诗》的计7人次8篇,《鲁诗》计有2人次3篇,《韩诗》计4人次4篇,而《毛诗》则仅有3人次3篇,窦融与张纯奏议之引,还只是权且归为《毛诗》。
第二,《齐诗》在西汉末年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较另外三家诗更为突出;《韩诗》则在东汉前期显露出勃兴的征兆。对比两汉之际三个历史时期引用三家诗的奏议文数量,可以发现西汉哀、平时期引用《齐诗》的奏议文篇数为3篇,多于引鲁(2篇)、韩诗(1篇)之奏。并且,东汉前期有5篇奏议文引用了《齐诗》,超过引用韩、毛诗的篇数,造成了一种《齐诗》在东汉初期兴盛的表象,但实则不然。伏湛、杜林、班彪均是由旧朝进入到东汉政权管理体系之中的,其诗学接受本在西汉末年而非东汉初年。出身于诗学世家的他们,在作于东汉的奏议中引用《齐诗》,恰恰说明的是《齐诗》在西汉末年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较另外三家诗更为突出。同时,西汉末年仅有1篇奏议引用《韩诗》义,而东汉前期却有3篇。尤其是刘苍,在《上书谏猎》《上疏归职》两篇奏议文中均能熟练运用《韩诗》义。刘苍皇亲国戚的尊贵地位在东汉光武帝、明帝两朝的辐射力不容小觑。其习尚《韩诗》的标杆作用,似已成为《韩诗》在东汉勃兴的征兆和风信。
第三,出现一人可能兼习几家诗的情况,如刘苍兼习《韩诗》和《齐诗》。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专习一家诗说的奏议作者会更多。毕竟,仅有刘苍一人兼习,是依据现存的文本材料、并在判断诗家归属时采用推测方法的基础上而呈现的结果。
(二)上行下效与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的影响因素
如前所言,王莽时期历时18年却仅有3篇奏议文引用了《诗经》。《全汉文》所辑王莽时期的奏议文,不少为残篇断章,难以看出每篇引用典籍的全貌。但以现存文本看,多援引《尚书》《春秋》《礼记》《论语》等,这一现象背后的因由,值得细究。
王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掌权者。检《全汉文》所辑录的王莽诏令,所援引的典籍主要为《周易》《尚书》《礼记》《春秋》《周礼》等,征引《诗经》的诏书寥寥。这种对《诗经》的冷遇,与官吏奏议极为巧合地相互应和。而这种上行下效,正是奏议文偏尚引用某一种、几种典籍和引用数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王莽诏令之引,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与他以周公自居、意图篡位的政治野心有关。《汉书·王莽传》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20]王莽勤学《礼记》,并以合礼行为获得了广泛赞誉。他对《周礼》《礼记》之礼仪典则,可谓运用自如。王莽以周公自居,周公摄政辅成王、成周道,王莽居摄奉孺子、安汉朝,成为他居摄掌权的基本逻辑依据,“周公在汉”是他最深刻的身份标识。《周易》《尚书》可谓恰好契合了这一人设特征,因而成为其诏令之引的重要来源。孔子从周,循周礼,故《春秋》《论语》等多被引,缘由自明。
奏议文是上呈君主的议政文本,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政治制度下,臣下依附于统治者而得以获得进身之阶。普通官吏面对最高统治者所表现出的卑弱型人格,使得他们效仿、迎合君主的思想宗尚以及在诏令中的引用偏好,这是他们的心理定势和行为惯性。况且,君主是奏议的阅读者,臣子撰写奏议的目的是让君主接受己说,借重典籍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被接受的可能性和容易度。所引典籍语句作为奏议文作者观点表达的助推剂,投君主所好以便减少接纳阻碍,是自然的且必需的。
当然,奏议文引用何种典籍,必定要受到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但事实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为水乳交融,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崇,往往由上而下地引发、主导着当时的文学风气,成为社会热潮。奏议文作者既受到君王在政治上的影响,又受到君王引领的文学风气的浸染。可以说,奏议文是否引用《诗经》及引用数量,往往受到君王自上而下的影响。
三、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透露的文学问题
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是一种文学现象。由这一文学现象为切入点,循此路径挖掘其背后深层的文学问题,是本文重要的目的和归宿。
总的来说,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问题,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体:诗与文。所谓的“引诗用诗”,即是将属于“诗”体的诗句引入到属于“文”体的奏议文当中,两种文体的差异转化为和谐的状态。再作进一步地思考,这种引用能够表现出一体和谐,说明《诗经》与奏议文在诸多文体要素上具有直接、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诗经》的特质和精神内涵,与奏议文具有共通性,是两汉之际奏议文引诗用诗的深层原理。
第一,《诗经》尤其是《雅》《颂》诗,乃卿大夫所作的政治之歌,多指向天子与国家政事,与奏议文的言说对象与言说内容相同。《雅》《颂》诗表现了对天子的劝诫、引导和颂赞,与奏议文言说的内容区域多有相合之处,奏议文引诗用诗以助己说,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小雅·十月之交》由灾异频现、天降凶兆之象,怨刺执政者弃贤用恶、贻害国政。李寻《对诏问灾异》籍此劝诫汉哀帝面对水出地动、星辰日月失常的灾异示警,应当博求英才、闭绝私门,两者在内容上毫无违和之感。《周颂·清庙》在虔诚雍容的情感氛围下颂赞文王的光辉美德,表达对文王功绩的仰慕之情。刘苍《世祖庙乐舞议》引用《周颂·清庙》,以真挚肃穆的语调回忆了光武帝中兴汉室、廓平四宇的巍巍功德,其对光武帝盛大武功的称美之情,与《清庙》之诗别无二致。
正《雅》与《颂》诗对于周文王、武王、成王等贤君的德行、功绩由衷赞叹,奏议文作者援引此材料,树立为当朝君主的品德模范和为君榜样,作为正向引导;变风变雅之诗对于昏君、佞臣无情讽刺、鞭挞,奏议文作者引用此诗句,警示、劝谏当朝君主以史为鉴,勿要重蹈覆辙,作为反面教材。《汉书·儒林传》载,王式为昌邑王师,自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21]可见《诗经》篇章、语句,可作奏议;同理,奏议文援引《诗经》语义、成句入文中,亦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由是,奏议文在言说对象、内容上与《诗经》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第二,《诗经》主文而谲谏,与奏议文委婉讽劝的进谏思路相一致。所谓“主文谲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语言与文风,语言措辞要有文采,注重形式,文风肃雅端庄。其次是进谏方式,刺上的方式应当委婉含蓄,以积极正向的情感表达为主。奏议文作者皆是博学之士,用语必反复斟酌考究。其借助《诗经》阐发己说,也同时为奏议文增添了文采英华。他们在奏议文中引诗用诗,不但使得奏议文风端庄雅正,而且使得奏议文的语势更为顺畅,气脉更为流动通达,故汉代奏议文多有文学佳品。同时,臣子与君主之间存在等级地位的差别,委婉讽谏是士人们默认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展现出了高妙的进谏艺术。
两汉之际奏议文的作者,大多数是通过温柔敦厚的言语叙述、逐步引导的方式姿态、积极正面的情感表达,来完成进谏的。即使如鲍宣《上书谏哀帝》这样的痛心疾首之作,也是如此。这是两汉之际引诗用诗的奏议文中最为激切直言的进谏。鲍宣直陈哀帝私养外亲、独宠董贤的错误行为,任意封赏、所用非人的恣意行径,淆乱制度、昏于执政却幻想天说民服的不切实际,可谓是开门见山、直陈君过。但在激切的言语中,我们仍旧发现鲍宣循循善诱、逐步劝说哀帝任用贤臣、屏退奸邪的苦心孤诣。引《曹风·鸤鸠》之诗,明示哀帝应当臣民一体、视之如一,恳切希望哀帝善养百姓、励精图治。文风愤而不怒,怨而不颓,于直言中可见鲍宣忧虑政事的高尚情怀。除此之外,其它奏议文多委婉讽谏,于揭露现状、陈述己见的同时,夹杂有革新现状的愿望以及对君主的歌功颂德。在王莽时期政治复古的彩色幻想中,臣子的奏议文皆以颂君德、引周说为显著特征。而在光武帝、明帝时期中兴汉朝的蒸蒸气象中,臣子之奏表现出一派去旧立新、重整乾坤的积极气魄,呈现出昂扬自信之态。由是,奏议文与《诗经》在进谏方式上具有相同的特质。
第三,《诗经》热切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奏议文参政议政的文体功能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属性相同。《诗》三百篇,无论是出自下层民众、普通官吏之手,还是上层贵族之作,从言说成康之治、平王东迁、幽王时期百姓流亡的内容中,从赞美抵御外敌、批判任用奸臣、哀悯百姓疾苦的情感表达中,我们无不感受到《诗经》作者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切。奏议文的文体功能是参政议政,可以说,国家政事与民众疾苦,就是奏议文的两大基本主题。
《诗经》与汉代奏议文一样,都鲜明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现实批判精神。孔子《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22]《诗经》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伴随着《诗经》经典化进程而展现出愈来愈强大的影响力。所谓“怨”,历代对其含义的阐释,或曰怨刺上政,或曰怨而不怒,无不表明了《诗经》具有批判时政、抨击现实的精神,其针砭时弊、观照现实的诗教作用,建构起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国家时政的牢固纽带,在包括奏议文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直接传承或间接显现。
两汉之际奏议文的作者在身份上是国家政治的管理者和国运兴衰的见证者,又受到了包括《诗经》在内的众多典籍的濡染,因而他们满怀着忧国忧民的使命感,秉持着“文死谏”的精神,自觉分君忧、辅君政、纠君过。天有日蚀,紧接着傅太后崩逝,极大地冲击了汉哀帝的心灵,孔光以《上书对问日蚀事》予以纾解。奏议文中引《周颂·敬之》《周颂·我将》两诗之句,谏哀帝应当敬畏天变,进贤良之臣、退贪婪之徒,施惠于百姓,自然会销祸兴福、永葆宗庙,在分君之忧的同时也为哀帝指出了一条成为贤君之路。五庙而迭毁,亲尽而宜毁,众臣认为世宗孝武皇帝庙应毁。刘歆则上《孝武庙不毁议》之奏,援引《召伯·甘棠》之诗,由思召伯而不伐其树的历史借鉴,力排众议,建议不毁武帝宗庙。以有理有据的奏议文字,统一意见,为哀帝所采纳,顺利转化为国家政令。东汉明帝于盛春农忙时节外出游猎,误农时、废民力。刘苍及时上呈《上书谏猎》指明君过,在徐缓不疾的语言表述中,引《大雅·抑》之句,劝导明帝树立君德、约束己行,成为民众的榜样和标准。两汉之际奏议文的作者既有重臣贵戚,也有普通官吏,作为庙堂之臣,在他们深层的思维观念中,是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为其提供着动力和底气,支撑强化着他们借助奏议文参与国事、辅弼朝政的行为举动。由是,奏议文在精神属性上与《诗经》具有共同的内涵。
总之,在两汉之际三个历史时期更迭的背景下,文学生态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在经学兴盛的时代文化氛围中,《诗经》的传播与接受状况是两汉之际文学发展的重要缩影。奏议文作为载录两汉之际包括政治、历史、文化在内的社会情况的可信文本,其引诗用诗的特点和所反映出的相关诗经学史与文学问题,对于理解这一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发展、衍化,文化思潮的动向、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注释:
①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专设“公牍文”一节,认为“公牍文,指古代朝廷、官府通常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他将章、奏、表、议、疏、启、剳子、弾事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归为“奏议”类,总称臣下给帝王的上书。见《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杜林在此奏中认为,连年大雨、阴阳失所,乃侵陵之兆,劝谏刘秀留意灾异示警,徙张步降兵。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详审其文意可得,董仲舒与杜林对该句的阐释是相同的,故此奏议文所引用的诗句,当为《齐诗》。
③《诗三家义集疏》载《韩诗》说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烝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韩诗》说的不愿叨扰百姓、听民断而“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勤于耕桑这三个信息点,与刘苍此奏的意义相合。但《齐诗》说也有一定的意义关联性。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