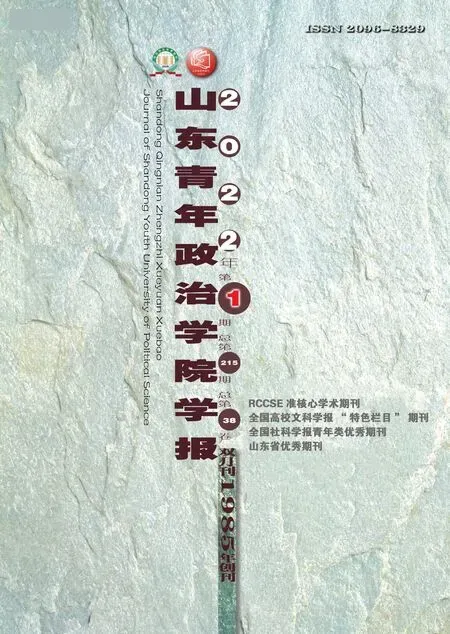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省的实证调查
2022-03-01韩钰
韩 钰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济南 250024)
2021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快推动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城市分级名单,一、二线城市共49个,三到五线城市288个①,中小城市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如何提高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质量,提升中小城市治理水平,对完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起着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急剧的社会变迁又使得很多社会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比如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严重、买房难、看病难、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居民对社会进步和城市发展的信心。城市发展信心指数可谓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是重要舆情的“风向标”,及时了解中小城市居民的城市发展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了解小镇青年的城市发展信心可以为规划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未来发展前景提供依据;了解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提升社会信心的方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心理氛围,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根据百科释义,所谓“信心”是指对行为成功及其相应事物的发展演化犹如预盼的信任程度。在社会学学科中,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社会信心。国外对社会信心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研究是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展开,后来逐渐发展为对政治、经济等具体领域或事项的信心,如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1-2],还有不少研究是与社会信任的研究交织进行的[3],但对社会信心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国内对社会信心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不少学者都依据自己的研究侧重点给出了相关界定,但并未形成学界的统一认识。王丽萍[4]将社会信心界定为“社会成员在当前和之后一段时间内对于整个社会的态度和看法。”李汉林和魏钦恭[5]认为“社会信心主要指的是公民对于社会整体和个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未来状况的一种预期和判断。”丛玉飞[6]认为“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认知而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自我与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期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意向的综合评价和反映。”刘程[7]认为“社会信心主要是指代社会基于当下现实客观情况的一种未来预期。”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社会信心界定为社会成员对某种具体社会事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演化达到个人预期程度的判断,本研究关注的社会事项为城市发展。
当前关于社会信心的研究并不多,从研究维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社会整体、国家/政府、个人/家庭,有些学者关注单一的维度,有些学者从多个维度同时展开。王丽萍[8]从社会总体评价,对社会公平、社会诚信、社会保障的评价,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对城市居民社会信心现状的描述和探讨,其关注的是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丛玉飞[9]对上海市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的研究,主要从即期生活满意度、预期社会信心和社会行为意向三个方面进行,涉及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张彦[10]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维度分析国人的社会信心。雷开春[11]以青年群体为对象从个人层面的阶层地位信心展开分析。张洪忠[12]等以网民为对象,以国家维度为重点,分析了经济前景、政府清廉、政府政策执行力、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道德六个方面的社会信心。初奇鸿、毕文芬[13]以国家维度为重点,从城市未来发展、国家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医疗体制、人才教育、和谐社会、反腐败、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梦”实现、国家和平崛起等十个方面测量社会信心。
整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社会信心的研究更加侧重从国家和政府职能的角度展开,就研究对象而言,除了全体居民或城市居民外,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主要是青年群体、外来白领群体或网民。对近年备受关注的“小镇青年”群体,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消费、身份建构、生存状况等方面,缺少对其社会信心的研究。然而,了解小镇青年的社会信心尤其是对城市发展方面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剖析中小城市在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速释放中小城市活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
(二)研究假设
就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信心的影响,有些学者[14]从生活压力的视角分析住房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也有些学者[15]直接从社会地位视角分析,雷开春指出社会地位(教育、职业、收入、党员、户籍、住房)、家庭背景(父亲教育、职业、户籍)和社会体验(生活改善度、贫富差距感和社会公平感)是影响阶层地位信心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收入和住房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毕文芬[16]和初奇鸿[17]在两篇文章中依次分析了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收入(同时分析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和教育获得(同时分析腐败感知的调节效应)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分配公平感相比,客观的收入差距并不影响社会信心,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低于基础受教育者,但降低民众腐败感知对提高高等受教育者社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从前面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并不是影响社会信心的单一因素,反映相对剥夺感的社会体验和社会公平感变量也是影响居民社会信心的主要因素。张彦等[18]还专门将相对剥夺感作为反映社会景气状况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对社会信心的抑制影响,刘程[19]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此外,丛玉飞和刘程还注意到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信心的作用,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和情感性支持对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丰富的社会资本是获得“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事项信心”[21]。
基于以上研究文献,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三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在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中,教育、职业和收入经常被作为反映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关键变量,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他们依靠个人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较少面临各类社会问题和生存压力,所以他们对城市发展的信心会比较高。较多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较多的社会资本,小镇青年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工具性和情感性交换,减缓生活压力,提高城市发展信心。而感受到的社会不平等越多,意味着相对剥夺感越强,会带来悲观的情绪和态度,更容易降低其对城市发展的信心。此外,在毕文芬和初奇鸿的研究中,尝试将社会公平感作为收入影响社会信心的中介变量,并用相对剥夺感理论进行解释,虽然最终并未证实中介效应的存在,但却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有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等社会资本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22],所以我们推测社会资本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可能会通过社会公平感发挥间接效应。
本文的研究假设具体表述如下: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小镇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城市发展信心越强;
假设1.1: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镇青年;
假设1.2:从事中产职业的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高于不从事中产职业的小镇青年;
假设1.3:收入更高的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高于收入低的小镇青年;
假设2(社会资本假设):小镇青年参与的社会活动越多,城市发展信心越强;
假设3(相对剥夺假设):小镇青年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城市发展信心越低;
假设4(相对剥夺感中介效应假设):社会资本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相对剥夺感发挥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小镇青年”为对象,重点分析其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及其影响因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小镇青年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信心研究”调查数据库。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第一阶段在S省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13个三线及以下地级市中抽取4个地级市,第二阶段在各个地级市按照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案抽取最终的被访者。在调查过程中,本研究对“小镇青年”做如下界定:目前生活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的18-35周岁青年。本研究并未将那些出生在“小镇”但目前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青年纳入研究范围,对于这部分群体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比如针对城市新移民的研究和“蚁族”的研究。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57份,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布详见表1。在下文的分析中,这些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形成统计模型的基准模型。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表
(二)主要分析变量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即对当前居住城市未来3年各方面发展情况的信心指数。具体包括工资收入、医疗保障、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住房条件、文化娱乐设施、城市绿化水平、居民素质、社会治安水平、工作与就业机会等十个方面。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以上方面按照五分总加量表打分,将非常没信心赋值为1,比较没信心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比较有信心赋值为4,非常有信心赋值为5。在最终的统计模型中,将以上十个问题的得分求和,得出城市发展信心的最终得分。其最小值为16,最大值为50,均值为31.89,标准差为5.207。
解释变量包括三个维度,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其中社会经济地位维度选择了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收入等级三个变量,前面两个变量都被处理成虚拟变量,即是否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是否从事中产职业(企业主/个体老板、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2。收入等级分为8个等级,依次为2000元及以下、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1-6000元、6001-7000元、7001-8000元、8000元以上,从1到8赋值,作连续变量纳入统计模型。

表 2 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分布表
对社会资本维度的测量主要从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展开,包括同乡/校友/战友聚会、居委/物业等社区组织开展的活动、宗教聚会、兴趣群体的活动、志愿者活动,从未参与赋值为0,然后按照参与频率从很少到经常从1到5赋值。在最终的统计模型中,将以上五个问题的得分求和,得出小镇青年社会资本拥有量的最终得分,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均值6.009,标准差4.959。
所谓相对剥夺感,主要反映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相对位置和相对得失的感知。“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人们感知到的社会公平度低时,会更加认为自己比他人处于更低的位置,产生更多的相对剥夺感。本研究主要通过社会公平度感知来反映相对剥夺感,即由研究对象对当今社会的公平度进行打分,完全公平赋值为1,比较公平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比较不公平赋值为4,完全不公平赋值为5,分值越高,小镇青年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均值为3.246,标准差为0.832。
三、分析结果
(一)小镇青年的城市发展信心现状
根据表3的统计结果,S省小镇青年对居住地所在城市的发展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所有类别的信心均值都在3分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在所有分项的信心评价中,评分在4分以上的比例高于评分在2分以下的比例。就城市发展信心总分来说,均值为31.89,标准差为5.207,最小值为16,最大值为50,这表明S省小镇青年对所在城市发展信心的评价处于“及格但不优秀”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S省中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成果离青年的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

表 3 小镇青年的城市发展信心描述统计表
具体来看,信心评分均值比较高的是住房条件、社会治安水平、居民素质和城市绿化水平。这与S省大力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密不可分,文明城市的评选对市容市貌、市民在公共场所的道德表现、市民的交通意识、公共场所人际互助关系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各地以创城工作为契机,部署安排了大量惠民、利民的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举措,包括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和棚户区改造工作,违法违规建筑整治工作、园林工程、四德工程建设和乡村文明行动等。
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信心平均分的第二梯队是对工资收入、文化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信心,从标准差来看,这一梯队的信心分值差异也是相对较小的一组。这表明小镇青年对S省中小城市在增进收入、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方面取得的成效感受相似。相关部门需要切实提出更多惠民举措并落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扩大医疗保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图 1 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不同维度得分均值分布图
小镇青年信心评分均值最低的城市发展内容是工作与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文化娱乐设施。S省中小城市在以上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确实与大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小城市和乡镇因为经济体量小,所以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并且与大城市相比,偏向于熟人社会,很多工作机会需要靠关系介绍。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其他部分的统计结果,只有21.36%的青年享受五险一金的社会福利,29.08%的青年不享受五险一金的任何福利,享受3-5项的比例也仅有11.13%。小镇青年通过自己常用的交通工具到达离自己最近的体育馆、展览馆和文化中心用时在一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是22.8%、32%、27.4%,半小时以上的比例均超过50%。
(二)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因素
因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城市发展信心是取值介于16-50的连续变量,且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本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来拟合模型。为清晰说明不同解释变量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本研究共构建了5个模型,其中模型1是仅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至模型4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纳入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变量,用于检验三个研究假设;模型5是纳入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全模型,以初步判断各解释变量的组合效应。本研究对5个模型都做了显著性检验,F检验结果显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总体显著,即我们用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恰当的。此外,所有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3,这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详见表4。

表 4 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控制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和大城市生活经历的情况下,三个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对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均有显著影响。调整后的R2从0.045提高到0.153,这意味着三个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可以单独解释城市发展信心差异的10.8%。从事中产职业的青年比非中产青年的城市发展信心高1.347分;收入等级每提高1个级别,城市发展信心会提高0.891分。假设1.2和假设1.3均得到证实,这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小镇青年对城市发展的信心。但是教育程度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却是负向的,与假设1.1相反。所以生存压力理论在解释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时并不适用于教育水平,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的生存压力小于非高等教育青年,但却不能提高其城市发展信心,反而会降低其信心。社会期望理论可以对这一结果做出合理解释,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高等教育青年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城市发展抱有极高的社会期望,当城市发展现实未达到其预期时,就会降低其信心。
模型3显示,在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小镇青年拥有的社会资本每提高1分,其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就会提高0.103分。从R2的变化来看,社会资本变量可以单独解释城市发展信心差异的0.7%。虽然其解释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相比较低,但是就提高的难易程度来看,肯定是比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容易。所以在未来的工作过程中,可以针对小镇青年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组织活动,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可以扩展他们的社会资本,增加社会支持,减缓生活压力,提高城市发展信心。
模型4显示,在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小镇青年的相对剥夺感每提高1分,其对城市发展的信心就会降低1.19分。如果社会的公平程度比较低,那么小镇青年一旦遇到生活压力就会产生更多的悲观情绪和态度,其社会发展信心也会受到影响。相对剥夺感变量可以解释城市发展信心差异的3.3%。
此外,对比模型5和前面几个模型结果,当同时纳入控制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相对剥夺感变量时,职业类型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但依然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社会资本变量的显著性却消失了,这表明社会资本变量对城市发展信心的作用确实受到了相对剥夺感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4,我们进一步展开中介效应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将社会资本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大城市生活经历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检验结果详见表5。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检验步骤,模型1的系数显著,可以做进一步的检验,模型2中社会资本对相对剥夺感的系数和模型3中相对剥夺感对城市发展的系数均显著,同时模型3中社会资本的系数明显比模型1小,且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在社会资本对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中,相对剥夺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60.64%,假设4得到证实。

表 5 社会支持影响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主要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S省小镇青年对居住地城市发展信心的评价处于“及格但不优秀”的状态。S省在中小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在住房条件改善、社会治安水平、居民素质和城市绿化水平提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工资收入提高、文化教育公平和医疗保障力度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此外,在工作与就业机会、社会福利保障和文化娱乐设施方面与大城市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切实增加就业机会并保证就业人员应享的社会保障权利,增加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
就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因素来说,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感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用生存压力理论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中的职业类型和收入等级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减少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提高城市发展信心。但是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青年是个例外,他们会因为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对城市发展有更高的社会期望,现实与期望的差距降低了他们的城市发展信心。社会资本对城市发展信心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降低相对剥夺感发挥间接作用,小镇青年在参与各类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对社会公平度的认识,从而减少悲观情绪,对未来城市发展水平充满信心。所以在未来的工作中,除了切实提高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解决民生问题外,从丰富社会组织活动入手,降低青年的相对剥夺感,也是提高城市发展信心的重要手段。
注释:
①https://www.maigoo.com/news/5502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