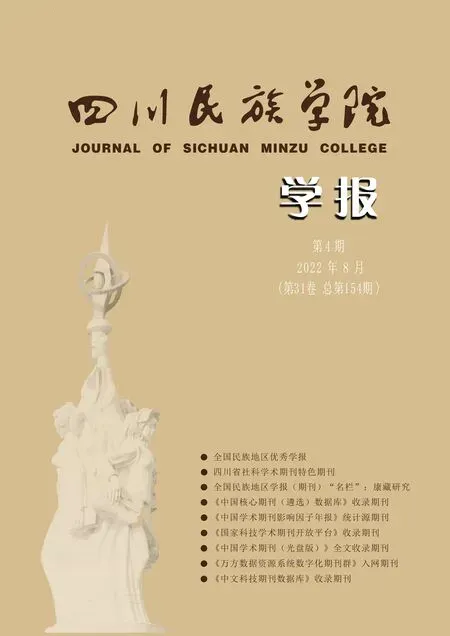康熙皇帝学弹《普庵咒》考释
2022-02-04吴跃华
吴跃华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美国学者史景迁著的《康熙自画像》一书中提到意大利传教士徐日昇教康熙弹奏《普庵咒》一事,国内有学者依此称“康熙自述”:“徐日升教我在羽管键琴上演奏《普庵咒》的曲调和八音音阶的结构”[1]39。其实这所谓的“自画像”,作者史景迁在著作中已清楚地交代是自己模仿康熙口吻所作的[2],也就是说,这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或许是因为此,宫宏宇觉得史景迁这著作“最可读”[3],但由此便大赞这本书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这不仅并非康熙真正的“自述”,上述说法还存在“八音音阶的结构”这明显不够准确的说法。其实,徐日昇在《律吕纂要》中的用词是“六音音阶”。遗憾的是,《康熙自画像》一书的国内中文译本不仅没有更正,还这样写道:“是徐懋德教我(康熙)在大键琴上弹‘布延州’(笔者注:这是《普庵咒》音译)的曲调和八音阶”[4]。这不仅是“八音阶”一说沿用史景迁的不准确说法,还把“徐懋德”错误地当成“徐日昇”。那么,《康熙自画像》以康熙名义所说“徐日昇教我弹《普庵咒》一事”又是否属实呢?对此,一些来我国的外国传教士确实有类似记录[5],此外,康熙宠臣高士奇在其《蓬山密记》中也描述了他亲见康熙“亲抚《普庵咒》一曲”之事[6]。美国学者梅文诗与其华人丈夫蔡金冬撰写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纽约Algora出版,2004)[7]一书第二章“音乐的航程”,在谈到康熙想学拨弦键琴时甚至说:“康熙学会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普庵咒》”[8]。看来这确有其事,但关于康熙所弹的《普庵咒》,正如魏廷格先生最早在其1981年的文章《中国钢琴曲创作概论(1915-1981)》中所说:“(康熙)在古钢琴上弹奏《普庵咒》,这必定是一种移植、改编曲。可惜,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皇帝移植、改编的具体情形”[9]。这种“可惜”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笔者就此试作一专门考释。
一、徐日昇教康熙弹的《普庵咒》实质上是类似于音乐的启蒙教材
葡萄牙学者称一些耶稣会报告中提到:“中国皇帝康熙曾和卑微的耶稣会士并肩坐在古(钢)琴之旁弹一个曲子”[10]。确实,与徐日昇同时服侍于清皇宫的法国传教士白晋(1656-1730)也是这么说的:“康熙还和徐日昇并肩坐在古琴前‘弹一首曲子’”[11]。按说,谁也不敢跟皇帝“并肩”而坐,除非皇帝应自己需要特许。但这“特许”总得有个理由,难道是“四手联弹”吗?一般认为,16世纪英国作曲家卡尔顿创作的《供两架维吉那琴或管风琴四手联弹诗曲》是最早的四手联弹[12]。因此,从“四手联弹”史看是有这种可能的。但徐日昇还不至于敢主动选择一首四手联弹曲子来要求跟康熙“并肩”弹奏。再说,“四手联弹”至少也得在单人弹有点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弹吧!因此,这“并肩”弹应该不是“四手联弹”,而是像现今儿童刚学琴时教师坐在旁边给予辅助弹奏的那种。
笔者作出这样的推测可从《普庵咒》流传本身得到间接印证。关于《普庵咒》有好多研究成果,这原是一首佛歌,尽管康熙皇帝父亲顺治信佛,也有说康熙也信佛,但康熙弹此曲应该不是源于佛事。康熙知道徐日昇是耶稣教徒,他也不至于非得用这佛歌来为难徐日昇,况且,徐日昇也不可能主动选择一首佛歌来教。实际上《普庵咒》到了康熙年间,已普遍成为独立的《古琴曲》和各种器乐曲了。且这实际上已演变成一首具有象征意义的乐曲,发挥着祈福“平安”的功能,因此《普庵咒》也被称为《平安乐》[13]205,并广泛运用于清宫礼仪用乐之中,如清宫用乐之吹打乐中就有《普庵咒》[14]。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万岁爷请皇贵太妃逛百子门,中和乐伺候……午正三刻十分进膳,吹打《普庵咒》[13]265;咸丰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延春阁伺候《普庵咒》;[15]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着郭喜于九月十九日起,每日早晚上去教成嫔娘娘下小太监刘进福随焰口上吹打《普庵咒》鼓,有差毋庸上去[13]250;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敷春堂承应《普庵咒》[13]256,等等。作为清宫常用礼仪乐曲,康熙一定很熟悉。且选用已作为文人“古琴曲”的《普庵咒》,也不失文人儒士的身份。尤其作为康熙老师的徐日昇,他也应该懂得,从康熙熟悉的曲子入手教学容易有效果。徐日昇是有教学经验的,他在被召来皇宫之前,在澳门圣保禄学院教授过(约)两年人文课程[16]。此外,法国传教士白晋说:“康熙皇帝希望学习西洋乐理,为此他请来了徐日昇神父。徐日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律吕纂要》)”[17]29。我们还可从徐日昇给康熙所编的这教材看出其懂教育。如,他非常善于运用易于教学的形象化手段,他用“圭多掌”来教圭多的“六声音阶”中的各音(乐名)音高的记忆方法[18],就是典型一证。“圭多掌”是在以前纽姆谱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纽姆”这种记谱法原本源于东方,希腊语的意思是“手势标记”,但“并不指示音高或音程。这些标记只表示旋律进行的方向,非常模糊地指示旋律的起落”[19]78。但“圭多掌”开始指示具体音高,它用左手代表所有音域各音的手掌图表,来辅助唱名法教学。音阶中的每一音对应于左手的各个关节,教师用右手指着左手各个关节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牢记圭多之手的含义后,对音程和音阶便能“了如指掌”了[19]79。显然,这“圭多掌”犹如我们熟悉的科尔文音阶手势,但比科尔文音阶手势要早多了。
此外,该书对乐音时值的介绍更形象,他用“睡、卧、坐、游、行、趋、飞、不见”等人体姿势来“代表八种音符的时值长短”[20]。徐日昇将“最长”音符名为“睡”;比“最长”稍短音符名为“卧”;比再稍短音符名为“坐”……[21]。这如同当前流行的达尔克罗兹体态律教学法和奥尔夫教学法中的做法,但这比后者要早得多了,这种方法还被汤普森运用于他编写的著名钢琴启蒙教材《简易钢琴教程》中来教授休止符。因此,这完全是儿童启蒙音乐教育的一种教法。
但康熙可已是成年人啦!徐日昇为何用教儿童的形象化手段来教康熙呢?其实,康熙虽然是成年的皇帝了,但在西洋音乐面前仍然还是个“儿童”,徐日昇用儿童教学善用的形象化手段来编写教材,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更便于康熙理解,好在其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学出效果来,这一点他比利玛窦要聪明多了,利玛窦助手庞迪我之所以教了一个多月没教会宫廷乐师,无疑跟利玛窦选曲没考虑到学习者的可接受能力有关。徐日昇应该是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为懂教育的徐日昇,他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的教学条件和教学效果,康熙肯定没那么多时间来学习这音乐,如果康熙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不出效果来,那风险就大了,至少对接下来想通过康熙进行传教很不利。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想教好康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徐日昇编的这教材真可谓是费尽心思,连教法都进行了精心选择。倘若徐日昇只是为了显摆西洋音乐理论的“科学”性,他没必要用“睡、卧……”这些简单的方法来编写乐理教材。尤其这首曲子还真是个著名的启蒙曲子,据杨荫浏在《古琴曲汇编》中说,此曲原本就是用于歌唱伴奏的,目的是帮助学习梵文的发音用的,后来才成为独立的器乐曲,如古琴曲、琵琶曲等[22]。因此,徐日昇选这曲子作为教材,或许也是受到此曲本身具有的启蒙功能的启发。这不仅是康熙熟悉的曲子,也是吉祥的曲子,更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曲子。因此,选这为第一首曲子来教康熙弹奏就再适合不过了。
那么,这推论是否能经得起检验呢?笔者再作如下分析。曾住清宫13年的意大利人(大清宫廷画师)马国贤,在他著的《中国学院(又名圣家书院)成立史》中说:“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但)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钗或古钢琴(epinette[23]756),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中国宫廷所奉行的过分地溜须拍马,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24]。那时法国来华服侍于宫廷的传教士白晋也含蓄地批评说:“康熙帝……对西洋乐器练习不够,技法生疏……如果他能在处理国务之暇,经常摆弄一下我们的乐器,那他也一定能够娴熟地进行演奏”[17]6。或许马国贤、白晋的言论带点个人偏见,但这毕竟是当事人的言论,因此,这总要比我们现代人猜想要靠谱。马国贤这里指出那时的中国有“奉承”“拍马”风气,应该不是个人偏见,传教士罗明坚更早时就已发现了这个“规律”,他还把这经验传授给其他传教士,他说:“(在中国人面前)谈到别人时要用赞美的口气;说到自己时要用谦卑的词句”[25]。但即便在这喜欢“奉承”的氛围下,高士奇的描述也只是“亲抚《普庵咒》一曲”而已。如果康熙的演奏水平真的很高,那高士奇绝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奉承”皇帝的好机会。
与中国学者普遍赞誉康熙的音乐才能是多么高不同,外国学者一般“点赞”得较少,如法国学者裴化行甚至说:“(庞迪我所教)这四名太监……很有可能,他们演奏起来就像一百年之后的著名康熙帝那样……他弹起来是只用一只手指头”[26]。笔者认为,康熙“单指弹”这一说法或许更可靠,证据可见徐日昇为康熙编写的教材《律吕纂要》。该乐理教材对“配合作乐”的演奏是这样说的:“相合五音内一、五、八为最合,配合作乐时,将此三音,每人各执一音而奏。”如此,这“并肩”弹奏就是康熙弹一个声部音,徐日昇弹另一个声部音的配奏。因为,正如沈知白说康熙弹的古琴曲《普庵咒》里有“四度、五度、八度音程”[27]42。顾梅羹在其《琴学备要》中对《普庵咒》的演奏提示到“右手重在齐撮,全曲共用到217个之多,来取得两弦同度或四度、五度、八度的和声音程,使音响更为宽洪和协”[28]。笔者查阅《北京琴会谱》溥雪斋演奏谱,最常见的是八度,五度次之,四度较少。八度的转位其实就是一度。但还有一个诸多专家没提的大三度音程(见该曲倒数第24、25、26小节)。如此,这曲子的演奏非常符合徐日昇所要求的“配乐”演奏方式。且该曲中出现的“音程”之“一、五、八”度属于徐日昇所谓的“最合”,“三度”属于“次合”,即便在徐日昇的理论中认为“四度”是不谐和的,徐日昇认为用得好也反而“更妙”。也就是说,该曲几乎完全符合徐日昇所编教材“配乐”的音程协和规则。因此,《普庵咒》应该就是这理论实际运用的教学案例。如此,马国贤等的批评就能解释得通了。这“单指弹”对外国人来说当然约等于“一窍不通”,但对那时国人来说也说得过去,因为我们国家的音乐文化就是重在“单旋律”,即便把古琴曲《普庵咒》那些所谓二声部的“一、四、五、八度”配音去掉在键盘上弹也无妨。
有人可能仍会怀疑,这《普庵咒》哪像启蒙音乐啊?确实,对于古琴弹奏来说,该曲或许弹奏难度较大,因为这涉及音准控制。但对于古钢琴来说,根本无需考虑音准控制,该曲弹起来反而简单多了,只要照着音符对着键盘单指“敲”就能行。再加上左手的二声部是徐日昇辅助弹奏,因此,尽管《普庵咒》看起来很长(其实也可分段弹),但即便儿童学起来,这种用单手在键盘上弹《普庵咒》也并不是困难的事,何况康熙呢!试想想,康熙这么忙,又怎么可能有大量时间练习古钢琴呢?但音乐演奏是需要技术的,没有时间练习是不可能达到演奏程度的,因此,把康熙弹奏解释成“单指弹”就比较合情理了。康熙通过学习,怎么也能“敲”出个单旋律《普庵咒》吧?那么,按照徐日昇的配法,仅用“音程”来伴奏真能有效果吗?德国学者曾这样说,用“音程给某一首歌曲配作和声以后,甚至可以催人泪下,所谓可以直接对灵魂说话了”[29]。这说法是否夸张暂不论,但徐日昇教康熙确实是重点考虑到了使用哪个音程来“配乐”效果最好,其次是用哪个音程次好,即便“最不合”的不协和音程四度音程也有其“妙用”。
二、对徐日昇《律吕纂要》的重新解读
正如上文笔者认为的,徐日昇教康熙弹《普庵咒》依据的是其所编教材《律吕纂要》之“配合作乐”法。遗憾的是,国内对这本教材也存在不少误读。因此,要充分认识徐日昇教康熙弹的《普庵咒》,还得对这部教材做一番辨识。
(一)对《律吕纂要》性质的误读:是乐理教材还是理论“著作”?
德国学者称赞徐日昇撰写的《律吕纂要》是“第一本中文撰写的西方音乐理论著作”[30],美国学者也这样认为[31],甚至国内学者也认为“这是一套很有使用价值的音乐理论著作”[32]。倘若按照“理论著作”的标准来衡量《律吕纂要》,这或许涉嫌“抄袭”。因为,中国科学院学者王冰通过该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分馆”)[33]69-81的中文“稿本”和“抄本”(还有满文本[34])比对,发现该书内容“主要取材于《音乐全书》(基歇尔)第 3 ~ 8 等卷中的部分内容”[33]69-81。但第一个发现该书的民国学者吴相湘认为该书是“第一部华文西洋乐理书籍”[15]222,现今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介绍“西洋乐理”的教材,台湾许常惠还把这一结论编入《音乐百科手册》(1979)。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中称这为 The Elements of Music(《乐学初步》)[23]629。这或许是最客观的,但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称之为Musica practica etpeculation(《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23]629)(有学者认为应译为《音乐的理论与应用》[35])不大准确。如作为初级乐理教材,那该书不但不涉嫌“抄袭”,还确实是近代存留后世的“第一本”西洋乐理教材。
不过,王冰说该书主要来自基歇尔的《音乐全书》(日本学者称《普遍音乐》(1)2013年8月刊,菊池赏翻译。,中国学者译成《音乐宇宙》[36]《音乐泛论》《世界音乐》《音乐世界》《音乐学概论》《音乐学通论》《关于声音协和于不协和的技巧》[19]79)也不尽然。尽管有确凿证据表明《音乐全书》那时已传入我国[37]220,南怀仁就曾明确表示想致力于将基歇尔的书有选择地翻译出来[38]221。但在《音乐全书》中找到相似的内容不代表就是来自这本书。因为作为基本乐理教科书,许多知识一定是公共的,比如,该书介绍的六声音阶理论,这是圭多“发明”的理论,也是自圭多以来的宗教音乐中一直沿用的理论。再如,该书介绍的五线谱,在15世纪时就已逐渐定型为“五线”的谱表了[38]16。16世纪时,“欧洲各国(更是)统一确定(使用)五条线的谱表”[39]。这些基础知识,作为传教士且很有音乐素养的徐日昇甚至可能在学校就系统学过。相反,基歇尔的著作倒有跟不上时代的地方,如徐日昇教的五线谱的音符符头是“圆形”的,但基歇尔1650年出版的这本《音乐全书》(Musurgia Universalis)竟然还仍在使用“方形符头”。这是西方最初的音乐符号即被称为“纽姆”(用来指示音调在何时升高、何时降低)的乐谱就用的记号[40]20,其实五线谱的符头由方形变成圆形早在16世纪[41]为了书写乐谱的方便[42]就已经出现了。不仅如此,基歇尔的书还有很多不可靠的内容。笛卡儿称他为“七分骗子,三分学者”[43]。
(二)对《律吕纂要》内容的误读——是音乐实践理论还是乐律理论?
正因为这是初级乐理教材,所以,徐日昇编写这本书主要解决的是音乐两大最为基础的要素即音高与时值的记谱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因此,全书上篇主要讲述五线谱基本知识及其对音高的记谱方法和六声音阶体系理论。下篇主要讲述乐音的时值关系及其有量记谱方法[44]。所谓“有量”,其实“就是给每一个音符以各自明确的长短。”[45]遗憾的是,有学者却误读说该教材“前半部分介绍西方乐理知识,后半部分为中国传统乐律理论”[46]。
该教材实际上受圭多的影响比较大,其编写风格符合13世纪以来的由圭多形成的理论教学特征。在圭多之前,所谓的音乐教学其实就是思辨的音乐理论教学,其基本内容是教乐律方面的知识,这是毕达哥拉斯带来的影响。西方中世纪的“七艺”之所以重视“音乐”而不重视“美术(绘画)”就是因为“音乐”属于“数学”。但圭多开始扭转这样的教学局面,圭多教学重视音乐实践。因此,此后一阶段的所谓“音乐”理论教学,其实就是教人怎么唱歌,教演唱多声部音乐的人如何即席发挥,即兴“创作”多声部音乐应该遵守哪些规则。后来的“音乐理论教学”才逐渐演化为技术写作教学[47]。徐日昇的书籍是紧密围绕实践进行教学设计的,如在阐述协和与不协和音程时不停地用“配乐”来叙述,这就是圭多以来形成的强调实践的音乐理论教学特征,而不是以往只是乐律学教学,也不完全像我们今天的乐理课让学生重在去计算音程的度数。笔者断定徐日昇沿用圭多的方法的依据,不仅有徐日昇书中介绍“圭多掌”,还有该书“上篇”论述的圭多的“六声音阶体系”。其实,此时16世纪时比利时人威尔兰特(Waelrant)已补加了音阶的第七音si[48]。显然,徐日昇没有采用。当然,徐日昇著作不是圭多的四线谱教学,已使用五线谱。以上分析的就是《律吕纂要》,遗憾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引进了“和声学理论”[49][27]41,其实不是,徐日昇编写的这教材主要阐述的是音程协和理论,根据其阐述的内容判断,该教材采用的是“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徐日昇称这是“配合作乐”法。这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即兴伴奏”编配。只不过相较于今天的“即兴伴奏”大都是运用和弦来配伴奏而言,徐日昇是运用那时的“音程协和理论”来配“音程性和声”的伴奏。总之,这教材非常初级,是根据康熙这位初学者的实际需要编写的。
三、徐日昇教康熙“音程性和声”伴奏本质上是遵循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徐日昇是因音乐才能突出被特召进宫的[50],关于徐日昇的音乐水平也是有证据的,如见证人之一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在其书信中曾提到康熙考核徐日昇的事,“(帝)召乐师若干人,帝亦自取一乐器而奏。日升不仅能默记歌曲,且能用中国音符名称录出,并记中文歌词[51]405”。见证人之二南怀仁对此事的记述更详细,称康熙用满语称“徐日升神父有如此非凡的才华,实在是令人钦佩!”[37]219-220。这称赞故事还被记述在“杜赫德于1735年于巴黎出版的一本《中国概览》[1]38中。有学者甚至说这轶事在欧洲作家的笔下广为传播[1]38。杜赫德甚至吹嘘说:“康熙皇帝大声说道,欧洲音乐‘是无与伦比的,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够与这位神父(指徐日昇)相匹敌”[1]38。那么,如此有水平的音乐专家徐日昇,为何选一个已过去近三百年的音乐理论即14世纪的“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来教康熙,而不是选择最能代表西方先进性的扎利诺“大小三和弦”的和声理论或“数字低音”来教呢?笔者认为,徐日昇这是继承利玛窦“文化适应”传教策略使然。为了能让康熙很容易学会,进而选择康熙非常熟悉的宫廷用乐《普庵咒》来教,因《普庵咒》一曲本身就存在中国的“音程”现象,进而又选择适合解释这一中国“音程”现象的西方音程协和理论来编写教材。如果徐日昇选择了更贴近时代的扎利诺的音程协和理论就跟《普庵咒》所体现的中国和声观念不吻合了,更不要提选择扎利诺的“大小三和弦”的和声理论和那时的“数字低音”了。显然,徐日昇选择的理论是为了来迎合解释中国音乐的,这是徐日昇因遵循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使然。
但从该教材之“配合作乐”法要求“最合之音必以继续之音雷同为戒”(笔者注:即平行一、五、八度是禁止)一语可见,徐日昇的观念与我国的音乐观念在声部进行方面是有些差异的。对于这样的风格问题,不知徐日昇是怎么处理的? 对此,笔者推测认为,或许徐日昇在实际配弹中迁就了中国古曲文化习惯。康熙帝确实很热爱西方文化,也很喜欢西方音乐,费赖之书中提到是南怀仁因康熙于1671年向他询问欧洲音乐的情况下后才想到举荐徐日昇的[37]221,按理,徐日昇直接教西方曲子才是,但徐日昇并没有直接选择西方曲子来教康熙。显然徐日昇这行为绝非寻常,只能用“文化适应”策略来解释。徐日昇虽讲的是西洋乐理,但其所教乐曲却是中国的,其所选择的理论也是跟中国音乐基本相匹配的。在他看来,如何让中国皇帝容易接受并高兴才是主要的,因为这会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开展传教活动,而传播最新、最科学的音乐理论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正因为此,后来德利格在其后续编写的《律吕正义·续编》中删除了徐日昇的“音程性和声”内容。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倒退”,其实不是,德利格的音乐才能远远高于徐日昇,德利格还有在中国创作的音乐作品存世[51],他是有作曲才能的。因此,徐日昇用于特定教学目的选用的“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对他来说太浅显了,至少远远跟不上时代,或者说,这已经被淘汰的理论,必须删除。认为这行为是“倒退”的许多学者,实际上是不明就里。由于懂教育的徐日昇所选教学乐曲《普庵咒》适当,教材(配合作乐法--西方“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适合,因此很有教学效果,最终赢得了康熙的赞许。徐日昇也充分利用了康熙对他的好感,如1670年“山东教案”发生时,正是徐日昇请求康熙帝才得以化解的[52]。因此笔者推测,既然选择教弹的曲目都有遵循“文化适应”的目的,那么他对“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所要求的“平行进行”的禁忌或许也不会那么严格执行了。
综上所述,徐日昇教康熙弹的《普庵咒》,是康熙弹主旋律,徐日昇配以音程性和声的“配合作乐”曲。类似于今天的四手联弹(实际两个人只用两只手弹),也类似于今天的即兴伴奏(只不过运用的伴奏和声是14世纪“新艺术”时期的音程协和理论而非“和声学”)。此曲弹奏并非像有些人描述得那么夸张,认为康熙弹奏该曲说明其很有音乐才能。其实际意义在于徐日昇实施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很成功。对于今天来说,这种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以及康熙努力学习西方音乐文化的行为,即这种平等文化交流正是当前“一带一路”倡导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