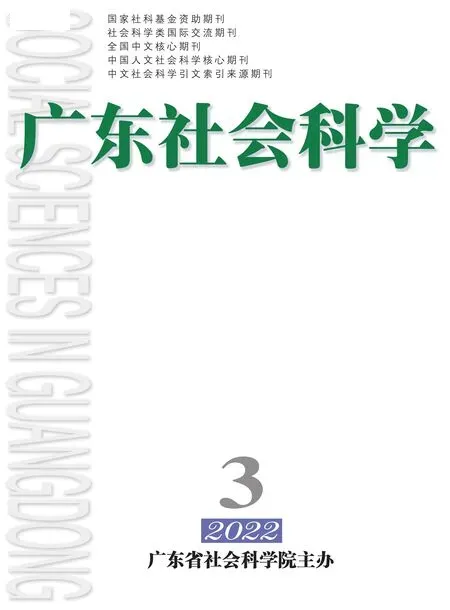1913年谭延闿“阻郭入湘”与民初政局
2022-02-03高航
高 航
1913年二次革命中南方各省落败,北洋政府势力大举南下,袁世凯派遣议员郭人漳入湘查办,而作为湘督的国民党人谭延闿则联络总理熊希龄,共同谋划“阻郭入湘”。(1)“阻郭入湘”一词,意即为阻止郭人漳作为查办使进入湖南,防止其染指湖南善后问题。该词频繁出现在《谭延闿集》中谭氏致熊希龄的电文标题里,参见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谭、熊、郭同为湘人,郭人漳与国民党有旧怨,熊希龄隶属进步党,熊、谭联手“阻郭”,体现出民初政争中地方意识与党派观念互相纠葛的复杂面相。因南北实力悬殊,谭延闿为求自保,亦为湖南稳定善后,不得不允许北洋势力入湘,来换取“阻郭”成功,最终代表袁世凯政府的汤芗铭接任湘督。
谭延闿本人向来重视湖南一省的命运,这是他在独立问题上态度摇摆的原因,同时也是他力争拒郭的根由。因此欲全面探究谭延闿“阻郭入湘”的来龙去脉,需要将视角向前延伸,回到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对比南北势力彼此间的不同观感,展现出谭本人在革命过程中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既往关于二次革命时期谭延闿的研究,多是依据报刊、回忆录来描述他在这一时期的决策与行动,很少利用一手材料勾画其内心世界,更未见有论著探讨“阻郭入湘”一事。(2)相关论述参见成晓军:《谭延闿评传》,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03—123页;刘建强:《谭延闿大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01—115页;贺永田:《谭延闿三主湘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62—74页。
有鉴于此,笔者拟重点利用1913年间谭、熊二人的往来电报,(3)上海图书馆藏的熊希龄档案中,有一批谭延闿与熊希龄往来电报,其中1913年间的内容多为商讨湖南问题,这些电报均已整理,分别参见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并同时辅以日记、报刊、文集、时人函电等其他各色史料,深入研究二次革命后包括谭延闿在内的各方关于“阻郭入湘”的谋划与博弈,同时展现出谭延闿纠结的心路历程,揭橥出民初政局中南北之争、地方意识与党派政争互相交织的多元图景,以期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史和民初政治史的相关研究。
一、二次革命期间谭延闿的心路历程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于上海被刺。两日后谭延闿得知消息,关切宋之生死,遂遣人赴沪探访。(4)《谭延闿日记》,1913年3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22日清晨宋教仁去世,他的死在湖南各界引起公愤。(5)《湘人为宋教仁被剌案之公愤》,《申报》1913年4月5日,第6版。谭延闿也屡屡电告北京,请迅速查拿凶犯。(6)《为请严拿宋案凶手再致大总统等电》(1913 年4 月3 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391—392页。因宋案证据公布,孙中山开始筹划反袁,与此同时“善后大借款”也引发风潮。
5月5日,由国民党人出任的四省都督联名发电,请政府停止善后借款。(7)《湘赣皖粤四都督联名反对大借款通电》(1913年5月5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7页。8日,袁世凯谴责四督越权行事,指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粤督胡汉民或有误会,而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虽身处近省,却对此事懵懂不知。(8)《命国务院致电副总统黎元洪等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7—448页。随后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致电四督与黄兴,分就宋案和借款予以调和。(9)黎元洪:《致长沙谭都督、南昌李都督、安庆柏都督、广州胡都督、上海黄克强》,《黎副总统政书》卷20,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第14—16页。5月底,黎元洪领衔的十七省都督、民政长联名发电,反对四督通电,支持政府借款。(10)《十七省督反对推翻借款电》(1913年5月3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7—371页。
众多疆吏表态支持后,袁世凯开始动作频频。先于6月9日罢免赣督李烈钧;14日,粤督胡汉民转任西藏宣抚使;30日,皖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11)《免李烈钧本官交卸来京候用令》《任命陈贻范胡汉民职务令》《任命柏文蔚职务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5、39、99页。天津《大公报》对谭延闿持论与其他三督有所区别,将湖南的反对声归咎到他人身上,“现反对中央者为粤、湘、皖、赣四省……惟湘省尚未定有何办法……因谭督系为拥护中央之人,与三省不同,其主张反抗者系为都督府外之人,必当另订别项办法云。”(12)《筹议对待湘省办法之碍难》,《大公报》1913年6月20日,第1张第6版。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媒体,一开始对于谭延闿的态度均有别于其他国民党都督,这表明在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中,谭延闿一向与北方关系较为和缓。但随后也有笔名为“无妄”的人指出,谭在湖南势难久留,继任湘督不知为何人。(13)无妄:《赣粤皖湘之四都督》,《大公报》1913年6月27日,第1张第4版。《谭延闿日记》,1913年7月26日、27日、3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同时长沙省城也风声鹤唳,7月3日城中旅馆发现炸弹;7日湖南军械局发生大火,大批军火化为乌有。(14)《谭延闿日记》,1913年7月3日、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程潜在回忆录中称湖南军械局的大火是袁世凯指使向瑞琮、唐乾一放的,见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91页。湖南省议会向北洋政府发去公电,意在表明民意,希望谭氏依旧担任湘督。(15)《湘议会挽留谭都督》,《大公报》1913年7月11日,第3张第1版。
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誓师,二次革命开始。(16)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页。14日,谭延闿针对赣事发电,希望袁世凯开诚布公,呼吁黎元洪与各省都督排难解纷,维持大局。(17)《就赣军独立讨袁发表通电》(1913年7月14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396—397页。次日,谭接江西来电,方知江西已正式宣布与中央断绝关系。(18)《谭延闿日记》,1913年7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黎元洪电告谭延闿,因为江西方面率先攻击,自己已无斡旋余地。(19)《湖南独立前黎元洪由武昌致谭延闿电·武昌电一》,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第333页。随后,江苏、安徽、广东、福建等省也纷纷宣告独立,江西讨袁军频频电催谭延闿尽快独立,会师北上。(20)《南昌欧阳武李烈钧致谭都督及谭人凤之发兵捣武汉电》《欧阳武致谭都督等促誓师电》《欧阳武谢国昌致谭都督告捷电》,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4辑,第337—338页。
《申报》称谭延闿素来圆滑,“揣其意,殆欲周旋于两方面”。(21)《湘中对于赣事之态度》,《申报》1913年7月23日,第6版。其实谭延闿本人确实难以抉择,独立并非易事。二次革命发生之前,北洋政府便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南方的国民党势力,二次革命使得南北双方矛盾激化,兵戎相见。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正是北洋势力一鼓作气全面南下的时机。谭延闿自然明白此中利害,是与其他独立省份共同联手抗袁?还是选择倒向北洋政府?究竟哪种策略才能保全湖南?国民党人的身份也增添了他内心的纠结。
接下来,谭延闿与湖南军政要员连续数日商议,19日至军事厅与诸人议事,20日议出师之事,21日开政务会议。23日,谭延闿终于决定牺牲自己来以保卫湖南,但又觉得家人无辜,遂遣人送家人赴沪。25日,谭延闿正式宣布与北洋政府断绝关系,湖南独立。(22)《谭延闿日记》,1913年7月19日、20日、21日、23日、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独立次日,谭延闿便与僚属商议出征,忽闻江西讨袁失利,湖口失守,僚属中便有人反对,出征之事难以落实。到了7月底,督署中多人请辞。(23)无妄:《赣粤皖湘之四都督》,《大公报》1913年6月27日,第1张第4版。《谭延闿日记》,1913年7月26日、27日、3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进入8月,战争形势更加对南军不利,部分省份已取消独立。“日来消息殊不佳,多颦蹙者,或故作壮语”,谭延闿夜闻上海战况,深感焦虑。8月3日,谭人凤告知谭延闿,黄兴已遁走。随后谭又听传闻黄兴噩耗,决定派人前往宁、沪打探。恰巧黄兴副官黄孟养来湘,称黄兴虽离开南京,但军队未败。谭延闿对此颇为疑心。(24)《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2日、3日、4日、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谭延闿致袁世凯自咎密电》(1913年8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2页。其实7月29日南京战事失利,黄兴已乘日舰离宁赴沪,随后又由沪赴港,前往日本。(25)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01—405页。
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程潜后来回忆道,赣军失败使谭延闿心神不定,得知陈炯明潜逃又大为恐慌,遂与程潜密商,打算请黎元洪担保取消独立,并将罪责一人承担。(26)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92—93页。其实谭延闿的内心转折并非是听闻陈炯明潜逃。7日,原皖督柏文蔚遣长沙人易坤来湘见谭,双方详谈许久,谭在日记中记道:“谈甚久,知孙中山种种谬举,此番皆为所误,可叹!”(27)《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至此,谭延闿或才打算取消独立,重新归附北方政府,不过改旗易帜仍需契机。
袁世凯对于谭延闿也较为宽容,之前对四督的责令中,湘督最为轻微。湖南宣布独立后,袁仍对谭延闿网开一面,将其与其他湖南要员区别对待,把罪责归咎于程潜、谭人凤等人,依然承认谭延闿的湘督身份。(28)《褫革并通缉程潜等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88页。袁世凯之所以如此处理,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湖南革命阵营自行分裂,但这同时也与谭延闿的出身及行事大有关系。谭延闿父亲谭钟麟于晚清迭任封疆,“谭钟麟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系拜把兄弟”,民初宋教仁甚至有召谭氏入京,利用谭、袁世谊调和府院关系的计划。(29)仇鳌:《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183页。谭延闿于清季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投身立宪运动,民初在焦、陈事变后担任湖南都督,积极响应袁世凯政府的裁军号令。(30)成晓军:《谭延闿评传》,第19—23、37—42、48—57、74—78页。1912年仇鳌回湖南改组国民党,积极拉拢谭延闿,谭延闿才加入国民党。9月改组成立国民党湖南支部,谭任支部长,在立宪派与国民党之间调和斡旋。(31)刘建强:《谭延闿大传》,第100—101页。因此谭延闿本人并不是激进的国民党人,而是趋向于中间路线,所以当时报纸中才会频频出现谭延闿被革命党胁迫宣布独立的消息。(32)《湘省附和独立之内幕》,《申报》1913年8月3日,第6版;《湘民痛恨暴徒之呼吁》,《大公报》1913年8月11日,第3张第1版。
二、谭延闿、熊希龄谋划“阻郭入湘”
袁世凯问罪湖南的命令发布当日,谭延闿也致电同为湘人的故交熊希龄,希望即将出任总理的熊氏可以出面斡旋,不使中央政府对湘用兵,“湘事维持别有办法”。(33)《致熊希龄电请斡旋以维持湘局》(1913年8月10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398页。11日,谭延闿密电袁世凯,将湘事归咎于自身,同时也表明苦衷,眼下湖南局面已稳定,当尽力维持,不过此电请政府暂勿发表。(34)《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2日、3日、4日、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谭延闿致袁世凯自咎密电》(1913年8月11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2页。做完这些布置后,谭延闿于12日告知旁人打算取消独立,围绕此事湖南军政高层意见不一,但当晚谭已草拟归附中央的告示文稿。(35)《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京专电》,《申报》1913年8月17日,第2版。当天,他还电告黎元洪湖南取消独立,自己听候处分,请中央遣员来湘接替。(36)《黎元洪调停湖南独立电》,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4辑,第339页。
13日,湖南在经历了不到二十天的短暂独立后,重新归附北洋政府,谭延闿在布告中称自己已电告中央,静待处分。(37)《谭延闿取消独立布告》(1913年8月13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第762—763页。同日,黎元洪也向谭延闿表态,“湘与鄂无二体,洪与公犹一人”,一定会竭力为其斡旋。(38)黎元洪:《复长沙谭都督》,《黎副总统政书》卷26,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第5页。当天黎氏便上书袁世凯,称谭在独立前因形势危急曾遣人向黎代达苦衷,黎劝其暂做权宜之计,表面附和,湖南军队开赴岳州事先亦与黎协商,故湖南虽独立,却始终未出兵与北军交战,而当下取消独立,也见谭延闿的维持之功。(39)《黎元洪致袁世凯为谭延闿辩解电》(1913 年8 月13 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第763页。
谭延闿在湖南独立前到底是否如黎元洪所言,目前尚无法坐实。但纵然谭延闿态度反复,黎元洪始终对其多有庇护。(40)刘建强:《谭延闿大传》,第112页。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黎元洪坐镇武汉,其实相当于北洋政府在中南、西南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统筹、指挥北军前方将领。(41)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9—280页。但另一方面,黎又和谭私交甚笃,二人均于武昌起义后分别出任两省都督,谭延闿在辛亥之际遣军援鄂,襄助黎元洪,此后也函电往来甚密,每逢要事互通讯息。(42)成晓军:《谭延闿评传》,第108页;贺永田:《谭延闿三主湘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73页。这也是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为谭延闿说项的重要原因,可见政治立场的歧异并未影响到两人的私谊。在接下来“阻郭入湘”的过程中,谭延闿的助力除了黎元洪,还有内阁总理熊希龄。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人谭延闿的两位好友,均是进步党中的重要人物。
湖南取消独立当日,熊希龄复电谭氏,愿意从中斡旋,但湖南善后不能托诸空言,需详细告知方案。(43)《就湘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8月13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9—210页。16日,袁世凯下令解散湖南省议会;17日,饬令谭延闿继续督湘,处理善后事宜。(44)《解散湖南省议会令》《饬国务院致湖南都督谭延闿电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330、338页。然而袁世凯也不愿将湖南事务继续全盘交给谭,他令籍贯湖南的众议员郭人漳担任湖南查办使南下入湘。(45)《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京专电》,《申报》1913年8月17日,第2版。
郭人漳过去曾于清末的起义中背叛革命党。(46)参见高拜石:《郭人漳参加革命始末》,《古春风楼琐记》第9集,台北:台湾新生报社出版部,1979年,第101—117页。同盟会改组后,郭人漳加入国民党。1913年3月5 日,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郭人漳在老家湘潭被人行刺,所幸无事,传闻其被刺与议员选举有关。(47)《郭人漳险遭炸毙》,《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6版。《请接洽公举代表致武昌黎副总统电》《乞指导黎尚文等调查湘事上黎副总统函》(1913年8月26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26、227页。4月上旬,郭人漳脱离国民党,并带走一批追随他的议员,影响了国会选举,湖南国民党人对其行径大为不满,甚至有人扬言要赴京暗杀,幸亏谭延闿居中调停。(48)《北京电》,《申报》1913年4月17日,第2版;《北京电》,《申报》1913年5月3日,第2版;《议员之危险》,《申报》1913年5月25日,第6版;《张继独为陈家鼎剖白耶?郭人漳危矣》,《申报》1913年6月1日,第6版。早在7月上旬便有郭人漳“运动湘督一席”的传闻,郭对此或许筹划已久。(49)《湘人之挽留都督忙》,《申报》1913年7月5日,第7版。
8月19日,袁世凯接到黎元洪关于湖南善后方案的电文,其中强调谭延闿不得立即辞职,善后事宜当由湘鄂两省协商处理。(50)《关于湖南方面反正后之消息》,《大公报》1913年8月20日,第1张第6版。当天下午,袁世凯又与人密议,商谈湖南善后问题,以及湘督是否需要更替。(51)《政府对于平乱善后之计划》,《大公报》1913年8月22日,第1张第5版。
25日谭延闿电寄熊希龄,具体言及善后规划。谭计划在自己辞职后,最好由同为湘人的滇督蔡锷来继任;若行不通可先另设民政长;对国民党人不应过苛,不宜使郭人漳任查办使,“湘尚意气,郭素不惬,来恐报复”。(52)《致电熊希龄陈湘中局势及解决之办法》(1913年8月25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0—401页。
熊希龄立即向袁世凯反映,袁世凯称是因为湖南暴徒尚多,恐谭被掣肘,故派遣查办使。熊希龄告知谭延闿:蔡锷一时难来,湘督仍需谭担任;拟派无党见的朱树藩、张学济来湘襄助;郭人漳已启程南下,只能待其到鄂后设法留住。(53)《为湘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8月25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24—225页。
谭延闿对于朱、张表示欢迎,并询及民政长人选,仍希望蔡锷能来湘继任。(54)《为请阻止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8月26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2页。次日,谭又听闻郭人漳已带军队南下,更加惊惶,请熊希龄务必将郭留在湖北,善后事务可由自己与黎元洪商议,随时可与中央商办。(55)《为请阻止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 年8 月27 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2—403页。《谭延闿集》中将此电系为8月26日,但依据“昨发宥电”可断为8月27日所发。28日晚,谭延闿向熊希龄再去一电,表示湖南已开始裁军撤兵,“郭来实属有碍”,并非抗拒中央命令,而是不愿涂炭生灵。(56)《为请阻止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 年8 月28 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3—404页。《谭延闿集》中将此电系为8月27日,但依据谭氏日记及此电内容,可判断为8月28日所发。
北京城内部分湖南议员对于郭人漳南下也非常不满,公推欧阳振声、黎尚雯赴湘调查,熊希龄请黎元洪对二人“遇事曲加指导”,意在为湘弭事。(57)《郭人漳险遭炸毙》,《申报》1913年3月14日,第6版。《请接洽公举代表致武昌黎副总统电》《乞指导黎尚文等调查湘事上黎副总统函》(1913年8月26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26、227页。此时袁世凯亦有任命郭人漳为湖南民政长之意。(58)《关于湖南方面善后之计划》,《大公报》1913年8月26日,第1张第5版。另一方面,谭延闿荐蔡代己的计划也在运作,有报道称袁世凯密电派蔡锷兼任会办湖南全省军务。(59)《关于湘赣方面乱后之消息》,《大公报》1913年8月29日,第1张第5版。熊希龄也致电蔡锷,称湖南安定后谭便将引退,自己和同乡都推举蔡锷督湘。(60)《就湘滇事务致云南蔡都督电》(1913年8月30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33页。
29日,熊希龄告知谭延闿,袁世凯已令郭人漳暂驻湖北,同时也在商讨蔡锷离滇赴湘之事。(61)《就湘中用人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8月29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29页。《就平息湘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9月4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42—243页。谭大为宽慰,但又得到黎元洪消息,闻郭来意甚坚,“复大忧”。(62)《谭延闿日记》,1913年8月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他催促熊希龄尽快宣布朱、张担任湖南宣劳使的任命,以抵消郭人漳查办使之名。(63)《致熊希龄电告知萧礼衡暂难离湘等事》(1913年8月31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4页。熊也告知谭,郭人漳决不致来湘;另外中央拟任命驻扎湘鄂边境的旅长伍祥桢为岳州镇守使,询问湘军能否退驻长沙,将岳州让给北军。(64)《就国军镇守岳州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8月31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35页。
有人阻郭来湘,也有人助郭来湘,进步党湖南支部就曾电催郭人漳尽快赴湘查办。(65)《进步党湘支部电催郭查办使赴湘》,《亚细亚日报》,1913年9月1日,第3版。有趣的是,熊希龄本人名列进步党名誉理事,黎元洪是进步党理事长,但两人均助谭拒郭,体现了进步党内部的分歧。郭人漳本人也积极运作,9月初他呈报中央,称李烈钧已逃往湖南,暗中招兵,反对中央遣使及北兵入境,谭延闿“毫无主权”。(66)《询问李烈钧入湘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9月4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42页。此电尚是影射谭延闿暗中勾结李烈钧,而9月8日的电文则更加露骨:
谭督曾电中央,力阻遣使入湘,且称对于叛徒如何惩治,均易为力,今竟纵虎出柙……人漳奉命查办,义无容忍,应请大总统电饬江西李护军使迅派兵队,向萍乡出发,堵匪回窜,并电副总统派拨军舰载运曹军、漳部,克日入湘,切实查办。如湘省独立真已取消,则南北军队同电中央,决无误会冲突之可虑。倘系阳奉阴违,或受逆党胁制,正可声其罪状,一鼓聚歼。(67)《湖南查办使之电告》,《大公报》1913年9月11日,第1张第5版;《湘省之隐忧未已》,《申报》1913年9月16日,第6版。
二次革命后,谭延闿尽力保护在湘的国民党人,谭人凤、程潜等人均受其庇护,谭也因此被告发。(68)刘建强:《谭延闿大传》,第115页。据李烈钧回忆,他在兵败离赣后,确实在长沙秘密会见过谭延闿与程潜。(69)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谭延闿拒郭入湘,主要原因便是惟恐其到湘后为报私怨,惩办国民党人,引发湖南新一轮动荡。不过这样一来,未免更加授人口实,令自己进退两难。谭延闿也急于为自己辩护,谎称李烈钧并未来湘,“郭欲急进”,故言多污蔑。(70)《致熊希龄电陈湘中剿逆等情》(1913年9月7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7页。
熊希龄为此大伤脑筋,他力主和平解决湘事,但郭人漳一派频频告状,甚至有报纸称自己派往湖南的朱、张为乱党。因此他向谭延闿提出四点建议:一,湖南本地各司长官应尽快公布人选,杜绝郭人漳染指之心;二,岳州湘军迅速撤回,以免与入境北军冲突;三,张、朱等人来湘,以热河卫队护送,消解谗言;四,国民党在湘支部解散重组。(71)《就湘中用人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8月29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29页。《就平息湘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9月4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242—243页。
对于四点意见,谭延闿一一回复,只是湖南国民党重要人物均已远逃,完全解散颇感为难。(72)《为维持湘省局势等事复熊希龄电》(1913 年9 月6 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5—406页。与此同时,谭延闿也草长电向袁世凯报告湖南情形,称自己并未被挟持,并从事实角度辟谣湖南二次独立之事,请袁世凯拣选有道德、无党见之人来湘彻查。(73)《为辟谣湘谋二次独立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上旬),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9—410页。此电同时寄发袁世凯与国务院。 黎元洪:《上大总统》,《黎副总统政书》卷29,第6页。当时社会舆论亦知郭、谭不和,袁世凯下令郭、谭二人以国家为前提,和衷共济,不可意气用事。(74)《关于湘赣乱事善后之消息》,《大公报》1913年9月13日,第1张第5版。
就在谭延闿为善后阻郭之事头痛不已之时,长沙城又添乱象,9月5日密谋兵变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人被捕,7日省防守备队二、六两营部分士兵哗变,不过当晚即被平定。(75)此次事变前后过程参见《谭延闿日记》,1913年9月5日、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兵变一事正好再次给予郭氏攻讦谭延闿的把柄,谭的处境可谓是雪上加霜。平定兵变后,谭便迅速致电中央,报告事变情形。(76)《致大总统等电陈湘省缉匪情形》(1913年9月8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7—408页。为了消解内忧外患,从10日到15日,谭延闿向熊希龄连去七电,其中内容大抵为三点:一,欢迎张、朱二使与伍祥桢来长沙,与其让郭糜烂湘局,不如请伍率军前来;二,袁世凯已令郭人漳进驻临湘、新堤一带,可否设法挽回,使其勿入湘境;三,自己在湘已难久任,蔡锷若不能来,可否先简选民政长。(77)《致电熊希龄询张、朱检查使来湘日期》(1913年9月10日)、《为伍旅长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0日)、《为阻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0日)、《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1日)、《为阻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1日)、《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4日)、《为阻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15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11—414页。
以上诸多电文的中心就是“阻郭”,为此谭延闿甚至愿意让北洋军进入长沙,以显示自己并无二心。虽然湖南善后最好是由蔡锷前来,但如果做不到,至少也应当阻止郭人漳入湘,防止其染指湖南,再酿祸患。因此为了“阻郭”成功,谭延闿只好退让,同意北洋军队入湘。这也为汤芗铭南下埋下铺垫。袁世凯已令郭人漳于9月13日入驻临湘,(78)黎元洪:《上大总统并致参陆海三部》,《黎副总统政书》卷29,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第1页。熊希龄亦难使袁收回成命,他称郭驻临湘尚无危害,劝谭延闿全力整理湘政。(79)《就郭使驻扎临湘、新堤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522页。依据电文内容,此电时间当在1913年9月中旬。但这时袁世凯对郭人漳也有不满。(80)《政府对于各省善后之计划》,《大公报》1913年9月14日,第1张第5版。
此前在江西、安徽等地成功“平叛”的海军次长汤芗铭被调来长江上游,其意在针对重庆、湖南。(81)黎元洪:《复芜湖汤次长》,《黎副总统政书》卷29,第1页。汤芗铭并非北洋嫡系,但他是进步党领袖汤化龙之弟,故袁世凯对其予以重用,以向进步党示好。(82)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令汤芗铭率军舰协助北洋陆军共同镇压南方军队。汤芗铭于14日抵汉,黎元洪密商袁世凯,重庆已取消独立,岳州以上军舰不便行驶,“拟即分驻武、岳、长沙一带”。(83)《为辟谣湘谋二次独立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上旬),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09—410页。此电同时寄发袁世凯与国务院。 黎元洪:《上大总统》,《黎副总统政书》卷29,第6页。此时谭延闿应该已和黎元洪暗中沟通,为了抵消郭人漳查办之名,不惜使汤芗铭和伍祥桢带兵进入岳州、长沙。20日,黎元洪电告已经合师一处的汤、伍,湖南诚心归附中央,并无可疑,请二人迅速抵岳,以息谣言。(84)黎元洪:《致新堤伍镇守使、汤次长》,《黎副总统政书》卷29,第12页。
三、郭人漳入湘失败与汤芗铭顺利入湘
关于二次革命后的湖南善后之局,谭延闿本来谋划使蔡锷入湘接替自己,来抵御“北人南下”,这样既可拒郭,又可防止北洋势力进入湖南。但因为长沙兵变等外在因素,使得袁世凯更加不信任自己,眼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以允许北洋势力进入湖南来换取“阻郭”成功。郭人漳与湖南国民党人有旧怨,且为人刻薄,来湘后必然反攻倒算。而北洋势力入湘,或许在谭延闿看来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湖南稳定,而且汤芗铭与进步党关系匪浅,黎元洪和熊希龄又分别是进步党的理事长和名誉理事。
在这种局面下,汤芗铭正是“代郭”的合适人选,加之谭延闿已表示北军军舰可以进入长沙,黎元洪也极力促使汤芗铭入湘。21日,汤、伍至岳州,“湘渐安稳,闿当急行”,谭延闿再次陈请辞职,意在尽快使熊希龄公布湘督人选,瓦解郭人漳的谋划。(85)《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1日)、《为请辞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2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15—416页。
北京城中熊希龄尽力斡旋,终于在9月下旬确定了蔡锷拟担任湘督之事,并定于10月初公开。(86)《就郭使驻新堤再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522—523页。电文开头称“个、养电均悉”,时间当在9月22日之后。蔡锷督湘并不只是谭、熊的私人意见,且是湖南人心所向,“湘人大部分多希望调蔡改任湘督”,“湘人多数均希望滇督蔡锷调往”,甚至有报纸称蔡锷即将督湘。(87)《关于川湘军事善后之种种》,《大公报》1913年9月24日,第1张第5版;《关于湖南方面善后之消息》,《大公报》1913年9月28日,第1张第5版;《北京电》,《申报》1913年9月27日,第2版。
为了保证郭人漳尽快退出,谭延闿直接提议可否以汤芗铭顶替郭人漳任查办使,郭人漳的目标就在于湘督,湘督一日不定,“彼一日不安”。(88)《为请辞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4日)、《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4日)、《为裁兵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4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17—419页。28日,袁世凯批准滇督蔡锷请假,令其来京调养,或许是为任命湘督做铺垫。(89)《准蔡锷请假来京调养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536页。谭延闿闻讯颇慰,称自己与汤、伍接洽甚欢,催促熊希龄尽快公开湖南民政长任命。(90)《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10月3日)》、《致熊希龄电表示欢迎汤来湘》(1913年10月5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20页。但令谭延闿想不到的是,相谈甚欢的汤芗铭会在坐稳湘督之后迅速清算国民党,在湖南引发新一轮祸患,“代郭”的行动虽然完成,但“阻郭”的真正目的却未达到。
郭人漳此时也在积极营造湘事“非郭不可”的舆论氛围,一方面他运动同党,使其联名致电袁世凯,欢迎郭来;(91)《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9月24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18页。一方面又尽力争取湖南方面的支持,陈请袁世凯免予解散湖南省议会。(92)《郭查办使电保湘议会》,《申报》1913年10月11日,第6版。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当天,熊希龄电知谭延闿,湖南民政长将任命王瑚署理,此外他还听闻郭人漳拟暗杀伍祥桢,“嫁祸于湘”,已将此事转报袁世凯。(93)《告知王瑚署理湘民政长事并嘱严防郭宝生祸湘及办湘团练用人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322—323页。无独有偶,谭延闿也从湖北方面听到这个消息。(94)《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10月3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20页。《汤芗铭署理湘督之由来》,《申报》1913年10月27日,第3版。至此,郭人漳急功近利的阴鸷手段暴露,他对于袁世凯而言再无利用价值,郭的入湘计划也间接等于宣告破产。
随后,袁世凯便打算将将郭调回,并取消查办使。(95)《关于各省军事善后之计划》,《大公报》1913年10月8日,第1张第6版。黎元洪也电请取消郭的职位。(96)《电商取销湘查办使》,《申报》1913年10月16日,第6版。《大公报》通报内幕,称国民党曾与郭人漳有仇,恐郭来湘后复仇,与政府和平路线不合。(97)《郭人漳撤消查办使之原因》,《大公报》1913年10月14日,第1张第6版。其实这并非深层原因,郭的去留主要取决于袁世凯的对湘策略。过去袁世凯对湖南心存疑虑,意在利用郭人漳与国民党的旧怨,使其入湘后压制国民党,但不料遭到阻挠;各方均能接受的汤芗铭顺利抵达长沙,北洋势力已直接入湘;另外郭人漳暗杀计划丑闻的曝光,使他成为袁世凯的一枚弃子。
谭延闿盼望王瑚早日南下,一再催问任命蔡锷何时公布。(98)《为湘中人事安排致熊希龄电》(1913 年10 月12 日)、《为湘中人事安排致熊希龄电》(1913 年10 月14日)》、《为阻郭入湘等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10月16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21—423页。熊希龄称王瑚即将到任,蔡锷月底到京,大约11月初赴湘;汤芗铭已被任命为查办副使,郭人漳决不可能入湘。(99)《为湘省人事更替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 年10 月18 日)、《为湘省军队调动等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年10月18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342—344页。20日,形势又有变化,蔡锷11 月中旬方可到任,因此政府将以汤芗铭代理湘督;袁世凯希望谭卸任后北上京师。(100)《为湘省人事安排及路股抵押借款事致长沙谭都督电》(1913 年10 月20 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四),第347—348页。因王瑚一再推辞,不愿南下就任,黎元洪又建议以汤芗铭暂署湖南民政长。(101)《关于湘督更替之种种》,《大公报》1913年10月28日,第1张第6版。24日,袁世凯连发数道命令,一面将谭延闿与郭人漳免职,令二人来京;一面以汤芗铭署理湖南都督,兼湖南民政长和湖南查办使。(102)《命谭延闿郭人漳调京候用令》《任命汤芗铭职务令》《任命汤芗铭兼职令》《任命汤芗铭兼职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109—110页。
上述变动体现出袁世凯手段的高明:在北洋军队抵达长沙后,方公布汤芗铭署理湘督的命令;黎元洪曾建议以汤为湖南民政长,谭延闿曾表示希望汤担任湖南查办使,袁世凯的任命也算是承二人之请;由于汤芗铭与进步党的紧密关系,又与黎元洪同属鄂人,因此熊希龄、黎元洪均不会对汤的任职表示异议;同时将谭、郭二人免职调京,对外显示自己不偏不倚;至于之前同意蔡锷督湘的任命,或许只是针对熊希龄的缓兵之计,毕竟此时袁世凯急欲集权力于中央,对地方推行“削藩”政策,自然不愿仍以湘人治湘。不久后兼任鄂督的副总统黎元洪也被调往北京,失去实权。
郭人漳最早领命查办,但“终不得一履湘境”。(103)《检察使到湘后之郭人漳》,《申报》1913年11月1日,第6版。谭延闿、熊希龄希望以蔡锷督湘,此举正遭袁世凯猜忌。汤芗铭入湘后“湘人颇表示欢迎”,而且汤随时向袁密报湖南情况,颇合袁世凯心意,袁便顺水推舟。坊间也称袁世凯对于各省都督不欲任用本省人,“蔡为湘籍,虽为湘人所欢迎,而与所定政策不合,故汤芗铭之署理亦为事实上之所偪成”。(104)《为阻郭入湘事致熊希龄电》(1913年10月3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20页。《汤芗铭署理湘督之由来》,《申报》1913年10月27日,第3版。后来蔡锷到京,再次有人称袁世凯不愿本省人担任本省都督、民政长,“湘赣尤为紧要”。(105)《蔡滇督调任湘督之未定》,《大公报》1913年11月4日,第1张第7版。
汤芗铭初到长沙时,公开发言称湖南自取消独立后当维持现状,不致地方糜烂,此后“决不有所根究”,故湖南各界心中颇为放松。(106)《汤次长来湘后之评议》,《申报》1913年10月20日,第6版。不料谭延闿卸职之后,汤为投效袁世凯,立即开始清算,湖南审计分处处长易宗羲便在谭延闿离开长沙之日被逮捕,都督府秘书吕劬生本拟随谭离湘,但被汤强行留下,以备质问。(107)《湘省党人之厄运》,《申报》1913年11月10日,第6版;《谭延闿日记》,1913年10月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随后,汤芗铭在湖南大肆逮捕、迫害国民党人,开启了他的“祸湘”之旅。(108)《汤都督穷治党人纪》,《申报》1913 年11 月17 日,第6 版;《湘督惩创国民党之霹雳手》,《大公报》,1913年11月18日,第3张第1版;《湘督惩创国民党之余闻》,《大公报》1913年11月19日,第2张第2版;《汤督对付党人之严厉》,《申报》1913年11月21日,第6版;《湘督惩创国民党之余威》,《大公报》1913年12月1日,第2张第2版;《湘省又破获党人机关》,《申报》1913年12月2日,第6版。
1913年10月29日,谭延闿被要求登上军舰,离开长沙。11月2日至武昌拜会黎元洪,随后在汉逗留半月有余。(109)《谭延闿日记》,1913年10月29日、11月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17日,谭延闿得知他与熊希龄一向看重的萧礼衡、杨德邻均被汤芗铭枪毙,心痛不已,决定立即进京。(110)《谭延闿日记》,1913年11月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为湘省涉嫌参与二次革命人士说情致熊希龄电》(1913年11月16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一),第428页。
但此时的谭延闿远离湖南,纵然入京见了袁世凯,也是无可奈何,况且自己也已自顾不暇。12月12日,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谭延闿本应依照刑律处以四等有期徒刑,但念其功劳予以特赦,裭夺陆军上将衔。(111)《特赦谭延闿裭夺军衔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416—417页。
1964年,谭延闿长子谭伯羽为其父编写年谱,于谱中记述谭延闿“阻郭入湘”一事:
乡人某素跅驰,不齿于乡评,旧岁规代湘督,已得请矣,乡人合力拒之,因改任汤芗铭。(112)谭伯羽:《茶陵谭公年谱》,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7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79页。
年谱中所言“乡人某”正是郭人漳,不过其湘督任命从未“得请”。汤芗铭能任湘督,主要还在于北洋势力强大,以及他与进步党的特殊关系。谭延闿为拒郭,为湘省善后,不得不迎合袁世凯意愿,以北洋军队入湘。汤芗铭在湖南倒行逆施,很快便于1916年的护国运动中被驱逐,谭延闿二度督湘。(113)刘建强:《谭延闿大传》,第124—136页。
结 语
近代中国迭遭变局,地缘上的南北之争成为动荡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南人北上”与“北人南下”的情况时有发生。太平天国军兴之后,湘淮系势力崛起,李鸿章掌印直隶,两江总督自曾国藩之后常为湘系把持,均可视作“南人北上”的重要表征。辛亥鼎革之际南北双方罢兵和议,进入民国后袁世凯政府亟欲掌控全国,随之开启了“北人南下”的进程。二次革命后南方落败,北洋势力大举南下。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在此后的南北之争中常常兵连祸结,以至于后来从湖南兴起了席卷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114)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219页。
民初南北之争的背后,地方意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默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提出,“省籍认同、乡土观念、南北之别”只是地方意识中的一部分,推进地方意识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史事。(115)陈默:《地方意识与区域政局——以护法运动时期粤军“援闽”之役为例》,《暨南学报》2019年第7期,第106页。二次革命爆发前夕,作为国民党人的谭延闿,与其他国民党人共同发声,反对袁世凯。革命爆发后,谭延闿从宣布独立到重新归附北洋政府,中间经历了纠结矛盾的心理变化,可见他维护湖南的地方意识终究强于作为国民党人的党派观念。不管是谭氏响应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还是后来谋划阻止郭人漳入湘查办,包括举荐蔡锷督湘等一系列措施,其最初目的均是为了抵御北洋势力对湖南的渗透。但由于南北势力悬殊,虽然由总理熊希龄施以援手,但“阻郭入湘”依然进行得颇为艰难,其根源仍是取决于袁世凯的对湘态度。谭延闿为自身计,为湖南计,同意北洋势力入湘,来换取“阻郭”目标的达成,二次革命后的湖南善后终以汤芗铭入主湘政而结束。
“阻郭入湘”一事亦可视作谭延闿后来倡导“湘人治湘”,推动湖南自治运动的一次预演。在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中,熊希龄也积极响应谭延闿。(116)1920年谭延闿第三次主政湖南时,率先宣布湖南自治,背后仍旧与熊希龄的建议和支持分不开,参见:何文辉:《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 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4—27页;刘建强:《湖南自治运动史论》,湖南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77页。被谭延闿多次引为奥援的熊希龄虽是北洋政府总理和进步党人,但同时又是湖南人,乡缘因素便显得极为重要。(117)熊希龄本不愿担任内阁总理,在袁世凯的敦促下方才出任并组阁,终因与袁政见龃龉而辞职,参见周秋光:《熊希龄传》,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404页。陈明的研究也揭示了熊希龄内阁时期时期府院之间的微妙关系,参见陈明:《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历史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39—56页。不过他们眼中的治湘之人,绝不可是对湘不利的湘人,这也是他们联手抵制另一个湘人郭人漳的原因。最后进入湖南善后的汤芗铭是进步党汤化龙之弟,同属进步党的熊希龄和黎元洪便不再出面斡旋,后者甚至积极支持汤芗铭入湘。围绕“阻郭入湘”展开的多方博弈,充分体现了民初政局中党派政治与地缘政治互相交织的复杂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