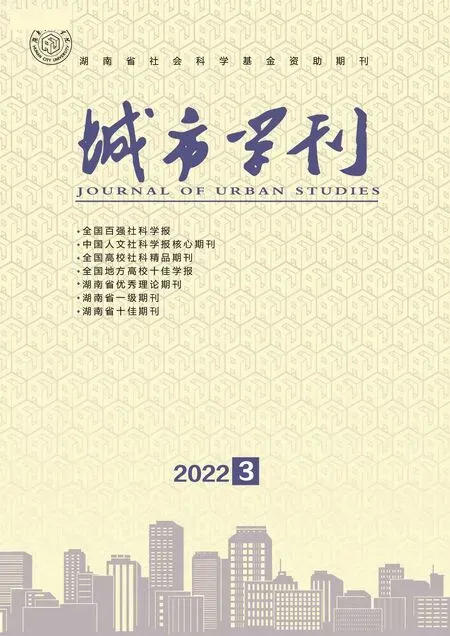圣旨、奏疏与明末时事小说的生成
2022-02-03杨志君
杨志君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长沙 410005)
天启、崇祯二朝是明朝最后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十分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以顾宪成为领袖的东林党之间的党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天启七年(1627),赋税和徭役负担过重,加上天降的旱灾,陕北发生了农民起义,后来在李自成等人的率领下,推翻了明朝。
社会矛盾的激化,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时事小说的创作,诞生了诸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等一大批作品。崇祯、天启两朝,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皆渐趋式微,英雄传奇更是了无踪影,而世情小说由于《金瓶梅词话》刊刻较晚,到清初才兴盛起来。这时,时事小说却迅速崛起,在明末章回小说中一枝独秀,与冯梦龙、凌濛初的拟话本,成为明末通俗小说中最为兴盛的两类体裁。
据陈大康先生《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可知,自崇祯到明朝灭亡之前,时事小说按刊刻时间先后依次有《辽东传》(1623—1624年间)、《警世阴阳梦》(1628年6月)、《魏忠贤小说斥奸书》(1628年9月)、《辽海丹忠录》(1630年)、《皇明中兴圣烈传》(崇祯初期)、《平虏传》(崇祯初期)、《放郑小史》(崇祯中期)、《大英雄传》(崇祯中期)、《新编剿闯通俗小说》(1644年完稿)九种。[1]其中《辽东传》已失传,而《放郑小史》《大英雄传》二书检索不到,或为佚书。剩下的六部,《古本小说集成》中皆有收录。而这六部小说中,皆含有大量的圣旨与奏疏。本文以稗中文为视角,拟对圣旨、奏疏与明末时事小说的生成关系加以阐发。
一、时事小说中的圣旨与奏疏
《警世阴阳梦》等六部时事小说中包含书信、评论、檄文、吊文、赋、揭等多种文体,但数量最多的文体是圣旨,其次是奏疏。笔者对《警世阴阳梦》等六部时事小说中的文体分布情况做过统计,它们共包含204则文章,其中圣旨、奏疏就占了183则,约占文章总数的90%,可见其在时事小说所含各文体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从稗中文与故事情节的融合度来说,《警世阴阳梦》等六部小说中的圣旨、奏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平不高的作品,其圣旨、奏疏以照录为主,圣旨、奏疏大多只是简单地罗列,与故事情节并没有怎么结合起来,这一类作品以《皇明中兴圣烈传》为代表;一类是水平较高的作品,其圣旨、奏疏以改写为主,圣旨、奏疏能较好地融入故事情节,这一类作品以《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为代表。
从《皇明中兴圣烈传》中文章的文体分布情况来看,其中的圣旨、奏疏主要集中于最后两回。该书第四十七回“籍没魏崔客氏群奸”含3则奏疏、19则圣旨;第四十八回即最后一回 “圣天子覃恩四记”含1则奏疏、22则圣旨;这两回的文章共45则,约占总数(58则)的78%,可谓分布极不均衡。而事实上,最后两回几乎就是奏疏、圣旨连缀而成,如最后一回开篇:“十一月初七日,刑科杨文岳谨奏为恳乞圣明查清无辜之狱,并除奸媚之臣,以广圣仁,以彰乾断事。奉旨:这本说清刑狱一事,着法司将二三年来,经厂缉拿,深深重拟者,从公会审,务情法两相合,具奏无罪牵连者,与审实开释,其奸恶巨魁,人命重情,律有明条,不得滥开,余俱有旨了。博平侯郭振明母崔氏一本,圣明乾照事。圣旨:崔氏系皇妣贞皇后生母,皇考临御日浅,恩泽未加,孤寒靡栖,朕所深念,籍没官房,准与一所,朕体恤懿戚至意。礼部一本……”[2]405-407这一段先呈示刑科杨文岳奏疏的概要,再录出皇帝针对此事而下达的圣旨。接着是崔氏的奏疏概要,再录出皇帝针对所奏之事而下的圣旨。后面又是礼部所上关于圣泽覃恩等事奏疏的概要,再录出皇帝针对此事而下的圣旨。整回便是如此这般的奏疏概要加圣旨的连缀,可谓连篇累牍。这些连缀而成的奏疏、圣旨,相当于未经作者加工的素材,很显然未能融入该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这是该小说最大的败笔,也是史传传统“实录”精神在时事小说中的体现。但我们也要看到该小说前46回,一共只有13则文言散文,其数量是比较少的了。尤其是前29回,没有一则文言散文,其叙述主要依据的是当时的传闻及编撰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原创率是比较高的。只是编撰者非士大夫出身,文化水平并不高,不仅出现了魏忠贤是狐狸精奸淫其母而生的荒诞之说,而且经常在回末故事结束的地方附上一些诗歌,如卷三“士民祷祝杨琏生还”:“且听下回分解,有诗一首付(当为‘附’)录:耿耿孤忠不可移,矢心血诚有天知。荼苦脐甘宁啮药,草堤萋萋为君悲。”[2]239这很明显是狗尾续貂,不顾及故事情节的连贯与流畅,是一种类似于史家的“存诗”观念;其最后两回大量圣旨的连缀,其实也是史家“存文”观念的体现,因而该书整体艺术水平并不高。《剿闯小说》也明显体现了史传“存诗”“存文”的观念,如第二回后半部分的《重纪越郡三忠死难实录》《重纪马素修先生死难实录》《重订死难名臣籍贯姓氏》及所附录的“四忠诗”;第四回在回末附录的评论,第五回附录的《贼事奇闻》(即关于李自成的轶事奇闻)、第六回附于回末的《宫娥出禁词》《美女叹二首》,皆未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为小说的冗余部分。
相比而言,文人陆云龙编创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的圣旨、奏疏能较好地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陆云龙不同于其他时事小说的编撰者,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对邸报中的圣旨、奏疏会加以适当的增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首先,对于篇幅过长的奏疏,陆云龙会对其进行删略,尽量保留其大意而不显得冗长,如第八回有一则杨琏弹劾魏忠贤述其二十四大罪状的奏疏:“大略道: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皇上念其服役微劳,拔之幽贱。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既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票拟托阁臣,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真伪谁与辨之?乃公然三五成群,逼勒讲嚷于政事之堂,以致阁臣求去,罪一也。……(引者省略)走马御前,上射杀其马,贷以不死,乃敢进有傲色,退有怨言。罪二十四也。伏乞敕下法司逐款严讯。”[3]125-130这一段文字,见于《颂天胪笔》卷五等,原文长达3 813字,《皇明中兴圣烈传》卷三“杨琏论逆珰二十四大罪”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占了32页的篇幅。而陆云龙将这则奏疏进行了删略,仅用了923字,不到原文的四分之一。这里略作分析,看陆云龙是如何删略的。其一,他省略了原文数落魏忠贤罪状的“前引语”:“左副都御史杨琏题为逆珰,怙势作威……(引者省略)仅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为皇上陈之。”[4]卷五这一段文字共 268字。其二,他对每一条罪状进行了删减,如《颂天胪笔》关于魏忠贤第一条罪状的原文为:“忠贤原一市井亡(疑为‘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劳,拔之幽贱,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其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乃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既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疑为‘尽’)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自忠贤等擅权,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讲嚷,政事之堂,几成闹市,至有径自内札,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眇小?以致阁臣郁闷,坚意求去,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大罪一也。”[4]对比上引《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杨琏奏疏文字,可以发现陆云龙删去了原文中“非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其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几成闹市,至有径自内札,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眇小”等句子;且将“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删减为“真伪谁与辨之”,将“以致阁臣郁闷,坚意求去,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删减为“以致阁臣求去”。其他二十三条罪状,陆云龙皆以此法进行删改。其三,在“罪二十四也”后面省略了原疏于此之后的全部内容,即“凡此逆迹,皆得之邸报招案……(引者省略)惟皇上鉴职一点血诚,即赐施行。”这一段文字长达1 062字。而陆云龙删略之疏的最后一句“伏乞敕下法司逐款严讯”,为作者根据前后语境所添。由此,我们可知陆云龙做的删略主要是“掐头去尾”,以及对中间内容进行删减与概述,这突出了编撰者的主体性,是章回小说文人化的重要表现。同回还有一则也是以“大略”领起的奏疏:“臣见忠贤所营坟墓,制作规模……(引者省略)曾不闻蒿目先帝陵工之费无措。”[3]130-131这段文字见于《玉镜新谭》卷五等,原文近300字,这里仅125字。同回一则圣旨,即“借言渎扰,狂悖无礼,廷杖一百为民。”此为删改自《玉镜新谭》卷二,原文140字,这里只有17字。其他较长的奏疏,大多作了类似的删略。
其次,对过于简略的奏疏,陆云龙会略做增补。《国榷》卷八十八中贾继春的一则奏疏:“保圣躬,正疏体,重爵赏,敦名义,课职业,罢祠费,开言路,矜废臣。”[5]《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三十四回增补为:“(贾继春)那本更说得利害:一曰保圣躬,道是食息起居之际,时存睥睨非意之防,深闱邃密之中,亦怀跬步弗缓之念。一曰正疏体,道是善则归君,归重厂臣,已堪食不下咽。章称上公,更为语不择音。一曰重爵禄,道是黄口孺子,不应坐膺侯封。一曰敦名义,道假子亲父之称,何以施面目于人间。一曰课职业,道是门户封畛不可不破,奈何不问枉直,以凭空混号为饰怒之题。一曰罢祠赏,道是生祠广建,笑柄千秋,撤以还官,芳徽后世。一曰开言路,道是高墉可射,不当袖手旁观。一曰矜废臣,道是先帝创惩颇僻,原非阻其自新。”[3]392-393陆云龙对贾继春所陈“八事”逐条作了具体解说,让原本干瘪的奏疏变得血肉丰满,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同回还有一则陆主事所上的奏疏:“竟上一个本,开陈四款,直指时事。第一款是正士习,说台省不闻廷谏,惟以称功颂德为事。第二款是纠奸邪,说崔呈秀安忍无亲。第三款是安民生,说宜罢立枷之法,缉事专归五城。第四款是足国用,说省事不若省官,今各处俱建生祠,是以有用之财,靡无用之役。”[3]391-392此疏虽检索不到来源,难以确证原文,但其句式与前面增补的贾继春的奏疏基本一样,只不过贾继春的奏疏每条陈述后,是以“道”字领起,而这里是以“说”字领起,因而大致可推测该疏原文当为:“正士习,纠奸邪,安民生,足国用。”而陆云龙对此亦逐条做了具体解说。
由此,我们可知《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的文章,大都经过编撰者的加工处理,使其较好地融入故事情节,既不显冗长,也不过于简略而让读者不知所云,具有较强的文人色彩。
二、时事小说中圣旨、奏疏的来源
纵观明末时事小说,其中圣旨、奏疏的数量是最多的。根据时事小说的序跋、凡例等资料,大致可判断这些圣旨与奏疏应出自当时的邸报。吴越草莽臣(即陆云龙)在《斥奸书凡例》中陈述其撰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经过:“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是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3]卷首足见邸报是其主要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其奏疏的主要来源。乐舜日所作的《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也陈述其创作经历:“读邸报雀跃扬休,即湖上烟景,顿增清明气象矣。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2]卷首更是明确交代《皇明中兴圣烈传》中关于魏忠贤等逆党的罪恶行径大多来自邸报。而吟啸主人在《近报丛谭平虏传》的序中说:“近报者,邸报;丛谭者,传闻语也。”在每章回目后皆用小字注明“邸报”或“丛谭”或“报合丛谭”,显然它是作者“坐南都燕子矶上阅邸报”,并据南来“燕客”所告之传闻而撰的。[6]
虽然天启、崇祯朝邸报现存很少,但其圣旨、奏疏大多仍能从当时据邸报而成的史料性著作中检索到。这里以刊刻于崇祯初年的《皇明中兴圣烈传》为例,对其中圣旨、奏疏来源加以说明。《皇明中兴圣烈传》包含58则圣旨、奏疏,其中有38则来自《颂天胪笔》《玉镜新谭》《圣朝新政要略》《三朝要典》《两朝从信录》等史料性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根据明代邸报编撰而成的。如明代金日升辑的《颂天胪笔》,其《凡例》曰:“始自初元,迄乎兹岁。珥笔所纪,授梓无遗,用彰喜起之风,弥显离光之照,不无脱简,咸本邸钞。”[4]卷首可见其材料辑录来源主要是邸报。而朱鹭在《颂天胪笔引》中也说:“日升贫而好游学,不仕而时品邸抄,年来见圣作物睹,每捶案欢呼,于改元初政及谕旨召对,纂述咸得精要”[4]卷首亦道出金日升《颂天胪笔》中的“谕旨”(含219道)、“召对”(含10通)等文献主要来自邸报。又如明人朱长祚编撰的《玉镜新谭》,这是一部汇辑天启时期魏忠贤等阉党与东林党斗争的书籍,其《凡例》:“录用章奏,字字俱从邸报、邮传,不敢窜易一字以欺人。”[7]可见其中的章奏全部来自邸报。而外史氏辑的《圣朝新政要略》,主要是关于天启间阉党的史料,其《凡例》曰:“是编翻阅邸报,备录圣天子新政者有关亲贤远奸”“是编或有疏无旨,有旨无疏,以金陵邸报原多未备,无从查考”“是编依邸报相连纪录”。[8]再如明代沈国元编撰的《两朝从信录》,叙述泰昌、天启两朝史实,其自称“悉本邸奏,非同剿说”,[9]而翰林院学士陈懿典在《两朝从信录序》中也说:“草泽所闻朝家故实,一凭邸抄,而省直流传,详略已异,其他遗散,益复无纪。”[9]576-577可见,不仅是沈国元编撰《两朝从信录》时依据邸报,民间的私人著史基本上都是凭借邸报。虽然《皇明中兴圣烈传》中圣旨、奏疏还有20则查不到来源,但根据作者《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中“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之语,可以推测也应是从邸报中抄录的。
而《警世阴阳梦》12则奏疏中,有9则见于《玉镜新谭》,1则见于《两朝从信录》;4则圣旨中也有2则见于《玉镜新谭》。此外,《警世阴阳梦》还有1则评论、1则谕令、6则谀词、3则俗赋,皆见于《玉镜新谭》。可见“录用章奏,字字俱从邸报、邮传”的《玉镜新谭》,不仅仅是《警世阴阳梦》奏疏、圣旨的来源,还是其他实用文体乃至俗赋的来源。从稗中文的角度来说,《玉镜新谭》对于《警世阴阳梦》的意义,几乎就相当于《三国志》对于《三国演义》以及《通鉴纲目》对于《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意义。有学者考证,《警世阴阳梦》是作者在大量抄录和改编《玉镜新谭》的基础上写成的,[10]可见《警世阴阳梦》的作者不只是从《玉镜新谭》中“借用”奏疏、圣旨等文章,连故事情节都是主要依据《玉镜新谭》。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15则圣旨、8则奏疏中有10则见于《玉镜新谭》,4则见于《颂天胪笔》,2则见于《圣朝新政要略》,1则见于《三朝要典》,1则见于《三朝野纪》,1则见于《国榷》,1则见于《启祯两朝剥复录》,1则见于《明季北略》,1则见于《明朝通纪会纂》。这些著作,大多收入了明朝的邸报。这其中虽然有些是清代才刊刻的,如《明朝通纪会纂》《启祯两朝剥复录》《三朝野纪》,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见于其中的奏疏、圣旨,可能也是它们参考明代的邸报而引录的。《辽海丹忠录》中的11则圣旨、9则奏疏,有13则见于《两朝从信录》,1则见于《国榷》,1则见于《度支奏议》。而《剿闯小说》中的6则奏疏、1则诏书,有3则见于《国榷》,2则见于《中兴实录》,1则见于《甲申纪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时事小说,基本上都是据邸报而创作的,尤其是其中的圣旨、奏疏,几乎全是来自邸报。
明末邸报的盛行,有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那就是洪武中期朱元璋下旨停修《起居注》与《日历》,之后各朝因循此例,使得当代史的编纂失去了可靠的史料基础。大概在汉代以后,中国就形成了当朝人不修当代史的治史传统,这从二十五史绝大多数都是后代史官所编可见一斑。从古代的目录学著作来看,“实录”先在宋代官修目录书《崇文总目》中出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还保留着,之后便在目录学著作中消失了,这表明自宋代以后,“实录”类史书便不提供给人们看了。一方面是明朝停修《起居注》与《日历》,一方面是“实录”类史书不提供给人们看,而时事小说是以叙述当朝要事为务,由于距离叙述对象时间较短,其处境便与私自撰写本朝历史的文人一样,没有可靠及充分的史传文献作为依据,能依凭的也只能是当时的邸报。
三、时事小说中圣旨、奏疏的叙事功能
《警世阴阳梦》等六部小说中的圣旨、奏疏,其功能首先是承担政治叙事的任务。对于时事小说的作者而言,由于没有正史、编年史等作为依据,而他们所叙述的又都是当朝重要的事件,在相关文献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从邸报中抄录圣旨与奏疏来表现当时的政治状况。如前引《皇明中兴圣烈传》卷三“杨琏论逆珰二十四大罪”中杨琏所上的奏疏,陈述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包括魏忠贤擅权,废票拟而旨意多出传奉,破坏明朝二百年来之政体;魏忠贤勾结孙杰,剪除忠义之臣;魏忠贤逼迫礼臣孙慎行、宪臣邹元标离职等,一定程度再现了明末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以及阉党种种的政治劣迹。
其次,圣旨、奏疏也能提高文本的真实性。邸报上最重要的文体是圣旨,其次是奏疏。圣旨是由封建社会中权力最大的皇帝发出,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而奏疏是大臣上给皇帝的折子,陈述的都是有关政治、军事的大事。大学者顾炎武曾谈及其欲根据邸报而撰写《两朝纪事》之事:“昔年欲撰《两朝纪事》,先成此卷,所本者先大父当时手录邸报,止纪大事,其迁除月日,多有未详。别购天启以来人家所藏报本,岁月相续,几于完备。”[11]而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迁为编撰明代国史《国榷》,曾大量借阅并采摭邸报,其在《北游录》中对此有记载:“丁丑,过王倪生,已授长芦盐运司知事,饭我。是日,吴太史借旧邸报若干,邀阅,悉携以归。戊寅,展抄邸报,棼如乱丝,略次第之。”[12]从中可见邸报是《国榷》的重要史料来源。而大学者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也是他在弘光年间邸报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顾炎武、谈迁、黄宗羲等学者之所以在其史著中大量采摭邸报材料,就是因为邸报上的文献比较真实可信。邸报虽没有正史或《资治通鉴》那样崇高的地位,但相比道听途说,无疑要可信得多。在正史等文献缺乏、消息闭塞的晚明,邸报上的圣旨、奏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而时事小说的作者引录邸报上的圣旨、奏疏,亦如《三国演义》引录《三国志》《后汉书》一般,也能提高文本的真实性。
再次,圣旨、奏疏还是时事小说的作者们关心国家命运的媒介。陈大康先生有言:“时事小说的作者对于国家政治、军事等领域各种重要事件的发展极为关注,然而并不具备参与朝政的条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在野之忧亦久矣’的士人。这些自号‘草莽臣’‘孤愤生’‘西湖义士’的作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但没有条件或机遇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他们便将对国事发展的忧虑以及无法对此干预的愤懑寄托于创作之中,同时也希望广大百姓一起来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13]总之,时事小说的作者确实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科举或仕途的失败者,这从时事小说编撰者署名“长安道人”“吴越草莽臣”“吟啸主人”“西湖义士”“孤愤生”“西吴懒道人”等可见一斑。他们有急切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却没机会得到统治者赏识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只好将其政治抱负寄寓于时事小说的创作中,正如草莽臣(即陆云龙)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序》中所说:“龙飞九五,若禹鼎成而妖魅形现,雷霆一震,荡然若粉齑,而当日之奸,皆为虚设。越在草莽不胜欣快,终以在草莽,不获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隐恨。然使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唯次(当为‘斥’)其奸状,传之海隅,以易称功颂德者之口,更次(当为‘斥’)其奸之府辜,以著我圣天子之英明,神于除奸诸臣工之忠鲠,勇于击奸,俾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则犹之持一疏而口阙下也。是则予立言之意。”[3]8-12作为一名科举蹭蹬的文人,陆云龙没有机会参与晚明朝政,只好借小说“斥其奸状”,达到“俾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的“立言之意”。亦如陆云龙替其胞弟陆人龙之《辽海丹忠录》所作之《序》所言:“顾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14]可见,陆云龙认为其弟创作《辽海丹忠录》也是为了表达其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而这种关心,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时事小说对邸报中圣旨、奏疏的引用上。
除了以上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的功能之外,《警世阴阳梦》等六部小说中的圣旨、奏疏,由于保存了当时部分重要的史实,因此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后世撰史者所参考的对象。明代自洪武中期后,由于朱元璋下旨停修《起居注》与《日历》,之后各朝因循旧例,使得明朝当代史的编纂失去了可靠的史料文献。而邸报出自朝廷,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况,故而时事小说将其采撷,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当时的史料——若没有时事小说的保存,明末不少圣旨、奏疏无疑会失传。从《警世阴阳梦》等六部小说中不少圣旨、奏疏见于清初的《国榷》《明季北略》《三朝野纪》《明朝通纪会纂》《启祯两朝剥复录》等史著来看,这些史著中应有一部分圣旨、奏疏参考了时事小说。如果说这还只是推测的话,那么如侯忠义先生所言,清初时事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多录入当时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富有文献价值,且多被《明季北略》《平寇志》《小腆纪年》等书所采录”,[15]大概也能说明时事小说中圣旨、奏疏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