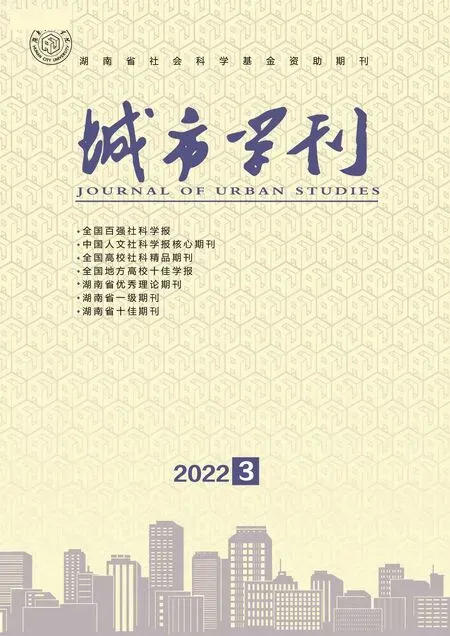当代城乡居民社区感的特征及其提升路径
——以福建省八城市的数据为例
2022-06-28林巧明
林巧明
(阳光学院 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福州 350015)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社区正代替传统村落、街道片区、单位大院成为人们主要的居住模式和基层管理的新单元。但受到需求对标不准、动力激发不足、参与渠道较少等问题的困扰,[2]社区场域内的一系列集体行动遇到困难,如以属地为单位的疫情管控、居民退休后脱离单位的信息交流或体育休闲。这给当前自上而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提出了问题——人们还需要社区吗?实际上人是社会性的生物,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支点构建了一种自下而上、自然天成的结构秩序和认知起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人社会”中个体对稳定性和确定感的心理需求。同时当前政府行政职能的下沉和资源整合,强化了城乡公共服务的社区嵌入和管理升级,从乡土地域联系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需要倚重社区来实现“脱域”后社会需求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感是人们依托社区关系而产生的情感或意识,是对存在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依赖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的感知,[3]它对公共参与、社区认同和社会幸福感等有显著正性影响,[4]可分为宏观社区感(对社区整体的认同感)和微观社区感(对社区内部小群的认同感),[5]能够起到整合社区力量、凝练社区共识和锻造社区共同体的作用。然而,以往对此的研究多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想象的“共同体”来引导社区政策制定和实行公共管理,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供给上较少从需求侧的视角出发,忽略了城乡居民作为社区主体的内生力量和关系性存在。因此,不论采取怎样的治理策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社区中,在需求者主动亦或被动的生活中思考社区的发展。
一、研究假设与模型
社区是城乡居民社会行动与互动的重要场域。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用自我的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其他环境进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感知。[6]因此,这种属性就将身体与地方、他人的关系对应呈现出来,构成了无可回避的共生关系,[7]但这种依存关系是一种被动关联。人们开始真正在社区里生活是源于两个时期,一个是疫情期间,另一个是退休之后(看病、锻炼、广场舞),这是因为生活半径减少了,人们在社区里浸润的时间更长了。否则就如卡特和莫麦戈得里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所言,[8]成年期的个体会有更丰富的生活空间,比如单位、学校或是外出旅游、购物。为此,研究拟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将社区感作为可资影响的结果变量,探究当代城乡居民社区感的样态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中社会性变量的作用。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1:当代城乡居民对居住的社区存在一定的感知和意识。人类合群的社会属性为社区的构成和生活打下了群居的印记,个体生活与社区的具象生活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会形成共同的要求、感受或情绪,弥散在社区中导致自觉或不自觉的集体行动,[9]这必然会对个体宏观社区感的产生和形塑发生影响。
假设 2:不同户籍、年龄和社区类型在社区感上存在差异。社区作为一个凝炼共享意义的表达空间,不仅体现了对社区整体共同性的理解,也包括了对社区内部多样性的认知,无论人们是否满意所在社区,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里都是社区现状的经历者和参与者,以地域背景、世代类型和生活场域等社会元素作为载体来构建对当前社区处境的微观体验和感知,[10]进而可操作为户籍、年龄和社区类型进行表征。
假设 3: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对社区感有正向影响。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体会以身体为中心,结合社会结构发展出一些抽象的位置概念,所以有了阶层上层、中层和下层,把上面的、接近的视为积极,把下面的、远离的视为消极,这就为嵌入环境的身体同空间临近的环境互动提供了社区感知的认知框架。[6]而生命周期理论也提供了一个远、近的时间位置框架,即每个个体都是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安排当下的生活,以此预见个体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完善并改变相应结构,[11]这就包括了与之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当代城乡居民社区感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图1)。

图1 当代城乡居民社区感的研究模型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以福建省莆田、厦门、三明、漳州、南平、泉州、福州和龙岩等8个城市的城乡社区居民为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施测起止时间为2021年1月至3月。问卷总计发放597份,回收597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22份。调查对象平均年龄36周岁,其中男性172人(41%),女性250人(59%),城镇人口177人(42%),农村人口245人(58%)。
(二)调查工具及变量说明
1.社区感量表
LA Jason,E.Stevens和D.Ram编制的量表共9个项目,包含自我(身份和对自我的重要性)、社会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实体(一个群体的组织和目的)3个因子,采用 6级评分制,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社区感越高,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23,分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33~0.904。[12]本研究测得该数据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33,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未来预期和社会阶层变量
采用赵德雷等人编制的未来预期题目,一共有2个条目,分别是代表近期时段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代表长远时段的“下一代生活预期”,采用5级评分制,1表示差很多,2表示差一点,3表示说不清,4表示好一点,5表示好很多。[13]在后期数据分析阶段,因五个选项中的“差一点”“差很多”和“不清楚”选项人数较少,数据集中在中上水平,故合并为“差和不清楚”选项作为后期数据分析内容。
社会阶层分为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两个指标: 1)主观阶层认同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认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等级上”来测量,采用10级评分制,10代表最顶层,1代表最底层,评分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即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越高。[14]数据分析时分为下层、中层和上层三个层次进行处理; 2)对客观社会地位的测量主要采用教育与收入两个指标来度量,通过询问“最高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月收入水平”来反映,并对教育和收入进行分类和分段处理,其中教育分为几个类别: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界定为教育下层,高中学历人群为教育中层,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为教育上层;对于收入而言,以个人月收入为主要参考指标。2020年福建省人均月收入在4 886元左右,[15]故根据月收入平均值的“0.5倍”“1倍”“1.5倍”“2倍”将客观社会阶层划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层次。结合调查问卷中的答案选项,将月收入2 000元以下界定为下层,2 001~4 000元界定为中下层,4 001~6 000元和6 001~8 000元合并为中层,8 001~10 000元为中上层,月收入1万元以上、大于收入均值2倍界定为上层。[13]样本中下层和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人数较少,故合并为收入阶层下层和收入阶层上层来处理。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居民社区感的总体情况分析
考察城乡居民社区感的整体状态,发现被调查者对所在社区持积极的情感或意识居于有点同意到同意之间(M=4.53,SD=0.91),其中得分最高的是自我维度(M=4.63,SD=0.97),其次是实体维度(M=4.59,SD=0.97),最后是社会关系维度(M=4.36,SD=1.06)。
调查显示,来自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在社区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422)=-0.37,p>0.05),而不同年龄群体的社区感差异显著(F(2,419)=8.41,p<0.01),事后比较发现,老年人和中年人的社区感显著高于青年人。另外,居住在不同类型社区的个体,其社区感差异显著(F(2,419)=3.36,p<0.05),其中自我和实体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F(2,419)=0.97,p>0.05;F(2,419)=1.74,p>0.05),社会关系维度差异显著(F(2,419)=7.27,p<0.01),事后比较结果发现,住在城市老旧社区和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区感及其社会关系维度显著高于农村社区。
(二)不同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的分析及其对社区感的差异比较
考察不同主客观社会阶层者的未来预期情况,结果发现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相符时,客观下层和客观中层者的未来预期水平最低(M= 2.00,SD=0.66;M=2.03,SD=0.81),客观上层者的未来预期水平最高(M=2.14;SD=0.83)。而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不符时,客观下层者感知为主观中层时(M=2.39;SD=0.79)和客观中层者感知为主观上层时的未来预期水平最高(M=2.50;SD=0.66)。
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社区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阶层中的教育阶层主效应显著(F(2,406)=3.68,p<0.05,η2=0.02),收入阶层主效应不显著(F(2,406)=0.89,p>0.05,η2=0.00),主观社会阶层主效应显著(F(2,419)=7.19,p<0.01,η2=0.04),教育阶层和收入阶层交互效应不显著(F(4,404)=0.74,p>0.05,η2=0.01),教育阶层和主观阶层交互效应不显著(F(4,404)=0.06,p>0.05,η2=0.00),收入阶层和主观阶层交互效应不显著(F(4,404)=0.22,p>0.05,η2=0.00),教育阶层、收入阶层和主观阶层三者交互效应不显著(F(7,401)=0.59,p>0.05,η2=0.01)。事后比较显示教育下层和教育中层人群的社区感显著高于教育上层的人,主观社会阶层处于中层和上层的人群,其社区感显著高于主观阶层下层的个体。
对不同未来预期人群的社区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两因素的方差分析,发现未来五年预期的主效应显著(F(2,419)=7.66,p<0.01,η2=0.04),下一代预期主效应显著(F(2,419)=8.64,p<0.001,η2=0.04),未来五年预期和对下一代预期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4,417)=1.11,p>0.05,η2=0.01),事后多重检验显示未来五年预期“好很多”的人群,其社区感显著高于“好一点”以及“差和说不清”的人群,而对下一代预期“好很多”的人群,其社区感显著高于“好一点”以及“差和说不清”的对象。具体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的社区感比较
(三)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对社区感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对社区感的单独作用,对其进行相关分析,排除相关不显著的收入阶层这一变量(r=-0.03,p>0.05),把教育阶层、主观阶层、未来五年预期和下一代预期这几个变量虚拟化作为预测变量,控制影响社区感水平的年龄和社区类型这两个人口学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变量的VIF值均小于 3,变量间相关性不明显,存在共线性可能较低。进而可见上层教育阶层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16,p值小于0.05,达到显著性水平,意味着上层教育阶层对社区感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上层主观阶层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12,p值小于0.05,意味着上层主观阶层对社区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未来五年预期认为“好一点”和“好很多”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18和0.30,p值都小于0.001,意味着对未来五年预期好的会对社区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下一代预期好一点和好很多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13和0.31,p值小于0.05和0.001,意味着下一代预期好的会对社区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和未来预期可以解释社区感29%的变异量,具体见表2。

表2 社区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四、讨论与总结
(一)城乡居民社区感的总体特征
调查发现城乡居民的社区感居于“有点同意”到“同意”之间,其中社区的身份及其对自我的重要性(自我维度)的得分最高,假设1得到验证。由此可见,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城镇化建设,大多数的城乡居民在以住房为中心、社区为主要场域的城乡结构再造下,[16]社区感的轮廓逐渐形成,产生了社区身份和群体意识的关联性内容。然而,由于城镇化不是城乡长期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在转型,这些压缩的时空、被切断的生活记忆和快速变化中意义系统的丧失造成了社区认同的弱化,[17]从调查中得到的城乡居民社区感未及“同意”甚至“非常同意”的程度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社会流动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下,研究发现户籍来自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在社区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老年人和中年人的社区感显著高于青年人,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应该说,户籍的产生是以限制社会流动和强化社会管理的二元体制为基石,它超越了对人的其他分类,把社会人群进行分割和简化,因此也掩盖了不同年龄世代背后的群际和群己差异。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社会分化和社区集群,以户籍主导的生活和生产局面被打破,其所带来的明显差异逐渐被取代,而户籍制度作用在集体记忆中带来的共享体验和社群界限在年长人群中的影响,相较出生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青年人则要强烈许多。当然,相比于制度意义明显的户籍,个体长期居住的社区则更具事实意义。研究发现老旧社区和商品房小区在社区感关系维度的得分要高于农村社区,这意味着城市小区里的人际互助和依赖明显好于农村社区。在城镇化的作用下,农村社区的社会交往由人情为上的道德秩序转向了效率至上的利益秩序,缺乏了城市社区里的服务供应和结构支撑,陌生的关系格局使得农村社区的社会交往显得有些无所适从。[18]
(二)不同社会阶层对城乡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分析
研究发现主客观社会阶层相符时,居于社会阶层上层者对未来预期的水平最高,而当两者不相符时,客观社会阶层下层者感知为主观中层时以及客观中层者感知为主观上层时的未来预期水平最高。亨廷顿在其社会变迁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会对人们的社会流动预期产生影响,它在给人们带来更高收入的同时,也激发人们向往登上更高阶层的欲望。[19]因此当主客观阶层相符时,流动到顶端的上层者获得了最高阶层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结构价值,对未来更有可控性和预知性。而当主客观不符时,个人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状况比较偏高时,体现的是对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信心和可能。
在客观社会阶层方面,研究发现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的社区感差异不明显,但教育阶层的主效应显著,其中上层教育阶层会显著负向预测社区感,也就是说,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会弱化对社区的情感或意识。当人们面对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重新分化带来的生活机遇变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时,出现了以收入、住房等为主要背景的次级群体,[20]形成了一种新的基于财产或住房权利的分层秩序,进而分离出不同的城乡社区类型,相似收入阶层的人群通过市场交易或世代传递等方式获取了入住同一社区的成员资格,因此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社区间而不是社区内。然而相对其他人群,高学历者对外在的标准、参照物等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知晓率,当他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些社区标准或者参照系进行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更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对自己所处的社区有更低的认同。[21]
相对于人们所处的客观社会阶层,对阶层认知的差异也会影响社区感的强弱。调查发现主观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主观阶层居于上层和中层的居民,其社区感显著高于主观阶层位于下层的人群,上层主观社会阶层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区感。应该说,主观社会阶层的形成脱离不了整个社会环境,它通过对社会环境的知觉和比较产生,与居民的价值取向及观念态度存在相关。[22]当下社区里的住房作为一种分层指标乃至分层机制,具有符号化区隔的特点,[23]因此,当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居于下层,人们就容易产生一种底层感或弱势感,面对社区这个最接近个体的“社会”,自然会降低对其的正面意识或积极情感。同时,我国的阶层认同与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趋中性”,即“中产认同偏好”,[24]中上层的主观阶层认同与当下社会整体阶层认同同步时,用来界定社会地位认同水平的整体参照系也会迁移或映射到作为具体参照点的社区身上,带动起对社区的认同。
(三)不同未来预期对城乡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分析
城乡居民对社区的感知不仅受到户籍、年龄、社区类型和主客观阶层认知的影响,关于未来时间点上的生活预期对居民社区感也具有前瞻价值。研究发现未来五年预期和对下一代预期的主效应显著,且两者对社区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无论对未来短期还是长期的生活预测,预期越好其社区感水平越高。作为衡量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未来生活预期,它是对未来超前的想象伴之以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理解或发生概率的判断,因为未来是未到达的现在,它带有不确定性,因而每一个人都依赖预期获得对未来的感知。[25]把时间从过去、现在延伸到未来,放置进社会结构中就有了社会性意义,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未来五年的生活预期是以“年”作为时间单位,它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时间,对其作出线性动态上升变化的整体判断,彰显了这一时间阶段的社会位置和角色期待,反应出所处的社会背景特征以及代表其地位属性的社区标签,进而投射在对社区的情感和意识之上是积极的、有希望的。
如果将视野放在下一代的生命时间中,排除日常生活中偶然的情况外,城乡居民对下一代未来生活的预期被当做是完整生命序列上可预见与可规划的时间轴,因为当下的生活而有了期待的框架去反映子代将要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预见未来将会经历的社会情境,以此联结我(当代)与他(子代)的生命时间和社会历程,嵌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之中。因此,这反映了城乡居民对当下所处社会的“静态”要求与期待,也表现出城乡居民面对变迁时“动态”的主体选择和表现能力。因此,对下一代未来生活的预期具有明显的动力特征,积极的预期会让人产生希望,催生对美好社区生活更加强烈的追求及发展的可能性。
五、对策与建议
(一)优化基础配套,助力社区治理
外部世界是与知觉、记忆、推理等过程相关的信息储存地,社区物理环境是居民直接接触的环境,认知、身体与其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是影响城乡居民社区感的重要因素。[6]便利的社区居住条件以及和谐的社区生态环境可以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和幸福感,进而维护社区的良好环境,爱护珍惜社区,推动社区的发展。[26]相对于城市,有些农村地区的基础配套相对较弱,社区的边界和范围不明确,容易影响社区感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应该加强社区环境的治理、改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交通状况、形成有边界的人文物理环境,从而有力增强社区感建设和社区治理的能动性。
(二)区分参与主体,强化社区引导
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关注,它是一种需求的表达,也是形成社区共识的基础。但相较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有着丰富生活半径的年轻人的社区感较低,因而让他们直接参与社区建设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社区共同体的建设需要结合不同生命周期的发展焦点来区分能动性主体,形成有关且有效的参与人群带动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时效性。因此,当不同利益诉求、文化习俗、信仰信念的群体愿意相互关注和接纳时,可以形成良好的对话机制和社区生态,这在社区引导上就有了有效的内部基础,可以针对不同人口背景的社区人群,制定相应的合作规则以及匹配的奖励。当然,这里的奖励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名誉或精神上的;不一定是当下的,也可以是未来和长远的,[25]进而为合作行为的方向或目的找到显著的靶点。
(三)丰富社区文化,发挥组织作用
文化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27]一直以来,基于地方的社区生活主要有两个基本文化面向:一是在地方有意义地生存,表现为“诗意的栖息”;二是形成有价值的集体,即“共同体”。[8]因而建立在社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是联通居民彼此之间的具身性底色,容易引发邻里之间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共享。因此,挖掘城乡社区的文化元素和历史资源,需要发挥组织作用,深入了解社区居民的普遍背景和生活经验,在共性的基础上找到不同社区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筑具有不同社区类型的文化识别特征和文化共同体,进而在多元社区类型的基础上体现有效且丰富的社区文化价值。
(四)开展社区教育,优化精神生活
开展社区教育是社区对居民思想和行为提供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指导,以加强在育儿技能、家庭关系、邻里相处、子女教育、心理健康、老年保健等领域的生活实践能力,其根本是让人以一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心态和思维来认知对待外周事物。相比于处于职业周期中的上班族,家庭主妇、老人和小孩是社区行为活动的主体,但他们对生活的感知、关系的理解更多的是出于学历教育和人生阅历,很多时候缺少了对不同生命周期事件的应对知识和必要准备,例如,如何与家人相处、心理要如何保健、该如何养护新生儿等。因此,作为基层组织单位的社区可就此作为着力点,组织和开展相应的社区教育,提供生活知识和技能的给养,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利于消解由个体生活挫败带来的社会戾气,把矛盾化解在社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