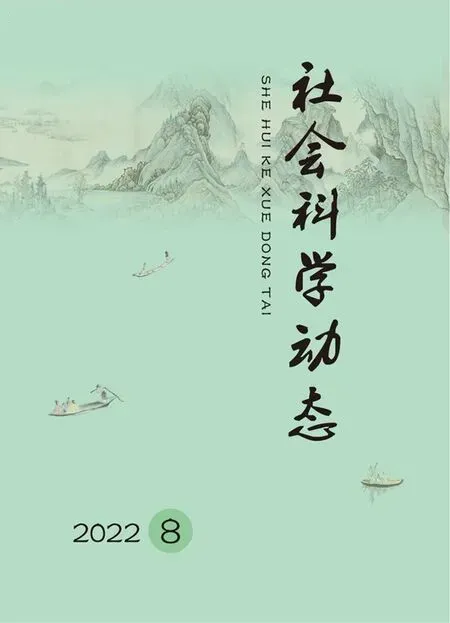印象记:吴永平的胡风、舒芜过从史考证
2022-02-03王应平
王应平
2013年9月的一天,我的导师金宏宇先生让我到湖北省社科院找吴永平先生拿一本书,当时吴先生的《胡风家书疏证》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先生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也得以顺利结题。我记得吴先生住在湖北省社科院家属区一栋极为普通的老楼里,家里陈设极为简朴,简直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在靠南边一间有阳光的小书房中,我请教了他几个有关“十七年”文学的问题。其时我的博士论文已完成开题,其中一个章节涉及“十七年”文学中的五次思想规训运动,而1955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对所谓“胡风集团”的批判自然算一次思想规训运动。吴先生侃侃而谈,寥寥数语就点破了“十七年”文学发生思想规训的原因和实质,接着如数家珍地罗列出胡风、舒芜的交往史料,指出学界对二人的所谓恩怨解读存在新的阐释空间。他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原则,爬罗剔抉,补苴罅漏,想努力还原历史,推动后学对“十七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我离开吴先生家时,心中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他对“十七年”思想史的梳理让我获得一个切入历史的直观感,知晓了论文中该章节写作的分寸和节奏。
予生也晚,我第一次知道舒芜先生是大二时在湖北大学老图书馆前的一次购书活动上。1990年代初,大学里的食堂、图书馆前常有出版社来卖书,时间多集中在周末。我记得自己买了一本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红楼梦》,书前有一篇舒芜先生写的很长的《前言》,讲《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该书第一次指出“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女子身上”。我思想深处像打了一个激闪一样,感觉舒芜先生真是目光如炬,道出了人人所想而未发之言。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堂上,老师粗略地介绍了胡风冤案始末,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同学们也难得其解,大家讨论时好像也是更同情胡风,有同学甚至指责舒芜不够朋友,出卖友人。大学快毕业时,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2万多字的小说《大学生日记》,因此毕业论文选题不知怎么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生兴趣,就拟了一个与“日记”相关的题目,指导老师是曾担任过湖北大学副校长的范际燕先生。后来在范先生家中,我亲聆謦欬,记得范先生总结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解决‘大众化’的问题,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解决‘化大众’的问题。”先生言犹在耳,而今却墓木拱矣。大学毕业后坎坷多年,我竟也走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道路。2014年,我申请到一个湖北省教育厅的研究项目《湖北籍现代文学作家全集编纂考察》,由此我细读了《胡风全集》,得以一窥胡风文艺思想的堂奥。我认为,整体上看,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多是从宏观政治角度出发,胡风文艺思想则多从文学局部自身角度出发。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强调作家思想的革命性,而胡风文艺思想则先验地强调作家对大众的启蒙作用,更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其次,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高度重视民间资源的积极作用。胡风文艺思想则认为民间形式≠民族形式,他认为民间、民众形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精神奴役的创伤”等封建糟粕的负面影响。
言归正传,尽管胡风也是左翼文学的重要一脉,但他似乎一直与所谓的“正宗左翼文学者”有抵牾之处。吴永平的研究,从1940年代中后期“正宗左翼文学者”在重庆、香港围绕“主观”等问题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切入,系统地考察了胡风、舒芜从相识相知到冷淡斗气的过从史。时过境迁,我们知道,1955年胡风冤案的导火索并不能简单认定为舒芜的“交信”事件,新中国诞生初期严峻的国内外情势决定了胡风事件的走向:当时国际上冷战阴霾密布,国内则国民党残余敌对势力活动猖獗,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批判与建构,其目的是“为了未来,是产生预防的效果,使意识形态权力深入日常生活中”①。大家只要琢磨一下加在胡风身上的“反革命”罪名就一目了然了。国共两党在现代史上有过两次深入合作,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现实,如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也曾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部长。故此,胡风在建国前与国民党友人有来往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曾是他能为党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筹码,但建国后这些历史事实竟简单地被视为“反革命”行为。学者姜德明曾指出,这些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信件也被编辑做了手脚,有意将胡风形塑为一个“阴险、恶毒”的“反人民”形象。故,舒芜“交信”并不是决定性的悲剧之源。事实上,吴永平通过考证发现,现代作家并不将信件作为私人隐私,他们常常在文章中加以引用,早在舒芜之前,胡风就将信件用于揭发批评舒芜的文章中,只不过文化界和官方不予采信罢了。他还指出,学界普遍看重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建设性意义,其实也是一种误读,因为胡风的文艺观同样有着很强的排他性,甚至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上比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某种意义上说,周扬的文艺实践还是相当宽容的,而胡风未必能有这样的胸怀。在搜集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吴永平认为,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其实与胡风自己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有很大关联。尽管“正宗左翼文学者”对胡风时有批评,但并非赶尽杀绝的态势,只不过是文化权力场域中司空见惯的一种争夺资源的常态化运作而已。如果当时胡风不采取进攻性姿态,能顺应“一体化”的时代语境,凭借他和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从事统战工作结下的友谊,或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吴永平进而大胆设想,如果胡风始终只是个文艺理论家,不在1943年之后跨入更加敏感的思想文化领域,想动摇所谓“机械论”的统治势力,或许他不会遭受厄运。尽管胡风的《七月》《希望》杂志在扶掖新人、开创抗战文学新局面上居功甚伟,当时就有人评价邱东平、阿垅、路翎、贾植芳、孔厥等人“代表了一种坚定的高扬的风格,企图突破日常庸俗的趣味”,“一种新英雄主义的理想使他们在坚韧乃至坚忍的特立风格下从事一种巨伟的塑像的建造”②。但胡风对这些新人的培养上也有“为我所用”的圈子化倾向,而这客观上显然不利于建国后文坛统一局面的形成。例如,胡风对姚雪垠的打压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为何要“亲者痛仇者快”呢?
2017年,吴永平的专著《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出版,该书共分三册,全面梳理了舒胡二人的关系。我当时就觉得颇为奇怪,因为其中有许多历史细节的考辨做得非常到位,这些资料作者从哪里获得的呢?现在谜底终于揭穿了,2021年这本《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也得以出版,该书分四册,以时间为序,完整记录了二人从2005年9月30日至2009年2月14日数千封电子邮件的通信内容,信息量很大,吴永平将专著撰写中的困惑之处随时向舒芜先生请教,然后根据回信来订正自己的表达,可谓事半功倍也。
整体上看,该著有三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厘清了很多常识性史料错讹。诸如1943年11月22日《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中提到的《××论民族形式》一文,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定为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其实并非如此。以往学者过多质疑舒芜《论主观》一文的逻辑理性,其实该文的要害却在文本之外,它“批评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机械论教条主义统治,说出了读者心中早就有的不满”③。惟其如此,“正宗左翼文学者”才大举伐之。
二是保存了很多第一手的史料实录。诸如舒芜的《论中庸》与《中国之命运》毫无关系、舒芜并未在《群众》上发表文章、舒芜笔名的来历——“有些是自己或别人名字的谐音或反切,如‘徐舞’‘许无’都是‘舒芜’的谐音,‘葛挽’‘郭畹’‘桂未晚’都是‘管’的反切,‘林慕沃、姚箕隐’是别人名字的反切”④。其他还有“竺夷之”“孙子野”“郑达夫”等取名或者因父母之故,或者并无来历,等等。
三是说出了很多真话,对历史的思考很有深度。如果说吴永平与舒芜的通信开始还是试探性的,那么后来双方敞开心扉,各自把对方看成知音,有时候给对方发一些有历史深度的网上文章,诸如王安忆的《执绋者哀》一文,两人关于“知识分子宿命”“政治话语霸权”“集团主义”的交流点评可谓鞭辟入里。
笔者认为,这些网聊记录有时也是颇为随意主观的,如果一定要将之作为证据使用,恐怕有失偏颇。一是这些网聊记录只是当事人一方的回忆解释,缺乏当事人另一方的辩解佐证。二是这些网聊记录有时候主观性很强烈,先入为主的色彩浓厚。诸如有关胡风性格过于孤傲、格局太小的评判,用语颇为尖锐。当然,聂绀弩对胡风也有类似的批评,但研究历史人物的视野应尽量开阔,不应以某个人的看法作为预设的结论,而应搜集同时代人更全面的评判材料。三是这些网聊记录过于相信一些“浮出历史地表”的所谓“白纸黑字”的证据,殊不知这些“白纸黑字”可能也是不可靠的。学者谢有顺曾谈到,真正的人心是无法用史料来考证的。学者张均也指出,学界对经典作品的版本研究热点不减,对初版(刊)本更是情有独钟,殊不知在初版(刊)本之前,作家心中可能还有一个“本事”的创作意图。这也说明人心难测,心事难寻。因此,我认为目前学界有关舒芜、胡风研究的时机并不成熟:太多的档案材料并未解密,即使部分文件已经解密,但我们也未必能过度相信它,因为人心难测,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氛围异化了人情关系。四是学界一方面普遍反感“十七年”政治对文学的过度束缚,另一方面却同样运用政治的评判标准来作为研究、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尺度,比如网聊记录中舒芜和吴永平多次看重周恩来对胡风“以观后效”的批示就是典型的例子。
注释:
①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3页。
②杨和:《〈七月〉与〈希望〉》,《春秋》1949年第6卷第2期。
③④吴永平编著:《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第1册,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