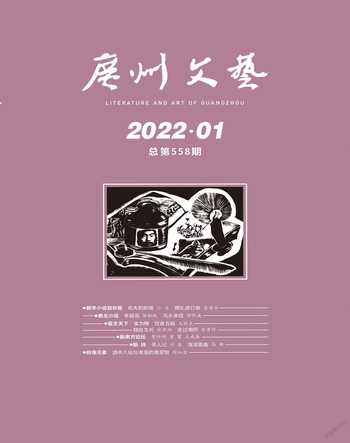酒中八仙与青岛的粤菜馆
2022-01-25周松芳
周松芳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进程。五口通商,开启粤商新时代——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迫远离故乡,走向“五口”以及更多新开口岸;特别是早期的买办阶级,成为各口岸贸易的中坚,也成为粤菜走出广东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之一。鲁海的《青岛老字号》正作如是观:
上世纪20~40年代,青岛的餐饮业有十家一等菜店(饭店),即顺兴楼、聚福楼、亚东饭店、春和楼、东华旅社、大华饭店、厚德福、三阳楼、公记楼和英记酒楼。其中唯一一家粤菜馆是英记酒楼。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占据香港,广东人开始与外国人进行经贸。1897年,德占青岛以后,急需一些懂国际贸易的人才,许多广东人来到青岛,有的在外国企业中干买办,有的自己开办外贸、金融企业。于是青岛“三大会馆”中的广东会馆在芝罘路上建成,有代表参与青岛政事。由于广东人来青岛生活,青岛也有了几家粤菜饭店,如广安楼(潍县路)、广聚楼(潍县路)、英记酒楼(中山路)等。(鲁海《青岛老字号》,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这十家一等菜馆之说,或出自1933年平原书店发行的《青岛指南》,第六编《生活纪要》提到的是十一家而非十家,漏掉的一家叫奇记。再则鲁海的记述一开始即出现重要差错——十家一等菜馆中,公记楼也是粤菜馆。留学日、美并获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的文理兼精的著名数学家黄际遇教授,1930年至1936年间历任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在青岛)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经常与友朋及广东同乡聚酒高会,对青岛的大酒楼可谓了如指掌,上得最多的正是公记楼,而且还在日记再三写明公记楼是粤菜馆:
1932年7月7日:晚赴里人袁伦铨之招,饮于公记楼,李家驹前辈适自旧都来,亦加入同席。
1932年7月28日:毅伯来,约明晚陪蒋祭酒饮粤菜馆,并代定菜单。
1932年7月29日:晚赴公记楼杜毅伯之招,乡厨甚美,同坐蒋梦麟(周按:夫妇)。
1932年8月7日:约太侔邀请济南诸友(何夫人、孙静庵、王子愚、李瑞轩夫妇)晚酌公记楼。并约实秋、毅伯、少侯、之椿陪,酒肆热甚,谈锋为之不锐。
1932年8月18日:晚随同人痛饮公记楼,蔡子韶来同席。
1932年9月10日:晚往公记楼小饮。
1932年10月29日:游泽丞招醉公记楼,实秋、怡荪、叔明同坐。
1932年11月17日:午为毅伯招往公记楼陪饮,甚恣饕腹,酒未及醺而仍不克制多言之病,言多必失。
1932年12月3日:晚偕泽丞、更生、保衡、少侯赴公记楼消寒会第二次雅集,怡荪、叔明、涤之、贻诚、智斋、咏声俱到,易令数番,酒风殊健。
1932年12月17日:七时余偕王竹邨赶消寒第三会于公记楼,少侯、咏声、涤之、保衡、实秋、贻诚、康甫在焉,转战大胜,然已不胜酒力矣。
1933年3月25日:晚王碩甫及门人智斋、保衡宴予于公记楼,饱餐后步归。
1933年4月28日:早课毕,招保衡看花,公园花事极盛。广东公记酒楼支店园中,薄饮啤酒,步归阅书。
1933年5月9日:晚少侯邀公记楼,酒不成欢,敛襟陪席。夜偕少侯、涤之步归。
1933年6月17日:晚涤之招饮公记粤馆,夜归有醉意。
1933年7月27日:晚以招生委员会名义宴诸君公记楼。
1933年9月20日:午涤之招咏声、肖鸿、任君小酌公记楼。
1933年10月28日:晚王哲庵招饮公记楼,健饮诸同人均在席。
1933年11月11日:夜曾省之招饮公记楼。(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黄小安、何荫坤编注《黄际遇日记类编:国立山东大学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8、31、36、44、67、76、84、92、106、113、119、138、155、157、170、174页)
然而,声名第一的英记酒楼,黄际遇却去得不多,仅录得二次,外加爽约的一次,也只得三次:
1932年7月8日:里人陈朋初柬饮粤馆英记楼,以疾辞。
1934年11月20日:晚宏成发开筵英记楼,趋往陪食,适功课最重之日,无心谈宴。
1935年1月6日:晡应采石酒约英记楼粤菜,乡人群集于此。(《万年山中日记》,第18、295、310页)
尽管如此,英记的威水史还是值得好好介绍一番。鲁海的《青岛老字号》说,英记酒楼为二层楼房,处于中山路、高密路黄金地带,旁为劈柴院东出口,楼下为散客,楼上为雅座单间,是青岛最早供应叉烧包、大鸡包、粤式粽子、鸡粥、鱼片粥等粤式早茶的饭店。厨师来自广东,能将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加以综合,制作精巧,花色繁多,美观新颖,有白斩鸡、油烹鳝鱼、蚝油牛肉、烤鱿鱼、油糟鱼、烤乳猪、脆皮鸡、咕噜肉、冬瓜盅、竹丝烩王蛇、龙虎斗等诸多特色名菜;还“美食配美器”,选用景德镇和广东佛山名瓷做餐具,房间布置也高雅。因此,在“十大名楼”中,英记酒楼虽然面积最小,但名气很大,名流云集,影响最大的则非康有为莫属。康有为自海外归来,于1923年购宅卜居青岛,时常到英记酒楼一尝家乡风味,却不料因此丧命。话说康有为在上海度过七十寿辰后,于1927年3月18日回到青岛,3月30日在英记酒楼参加宴会,因腹痛未终席回家,次日即告病逝,或因食物不洁所致。(鲁海《青岛老字号》,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212页)这应该多少影响到英记的声誉,故期年之后即告转手:
启者:本酒楼现改由鄙人接办,已将内部大加刷新,由粤沪聘到上等名厨,按日精制时鲜粤菜、各种点心,以供各界宴会。房间雅洁,招待周到,用具消毒,讲求卫生,务求尽惬人意。今定六月十八日开幕,敬希各界光临,不胜荣幸。本楼主人启,中山一路一百一十号。(《英记楼新号启事》,《青岛时报》1932年6月26日第7版)
鲁海的《青岛老字号》还提到过另两家粤菜馆,即广安楼(潍县路)和广聚楼(潍县路)。其实何止这两家呢?黄际遇先生就另有说到一家粤来馆:“1934年7月10日:承佑面饮夜饮粤来馆(芝罘路),入者半系酒徒,大学健饮之名几闻全国云。”(《万年山中日记》,第232页)而能聚齐一大帮闻名全国的高阳酒徒,即便这菜馆不大,也必定饶富特色。跻身这帮“酒徒”之列的梁实秋先生,后来详述过他们如何名闻全国之法:
(从杜甫《饮中八仙歌》说起)我现在所要写的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至二十三年(即1934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热,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
……
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即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
后面又具体介绍了除他本人和黄际遇之外“六仙”的情况,这里只就与酒有关的方面节录如下:
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为今甫,北大国文系毕业,算是蔡孑民先生的学生。青岛大学筹备期间,以蔡先生为筹备主任,实则今甫独任艰巨(后任青岛大学校长)。今甫身材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赵瓯北有句:“骚坛盟敢操牛耳,拇阵轰如战虎牢。”今甫差足以当之。
赵畸,字太侔,和今甫是同学。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莲池大师云:“世间酽醢醇醴,弥久而弥美者,皆封锢牢密不泄气故。”他有相当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
闻一多,本名多,以字行,湖北蕲水人,是我清华同学,高我两级。一多的生活苦闷,于是也就爱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他一日薄醉,冷风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陈命凡,字季超,山东人,任秘书长,精明强干,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关于拇战,虽小道亦有可观。我与季超拇战常为席间高潮,大致旗鼓相当,也许我略逊一筹。
刘本钊,字康甫,山东蓬莱人,任会计主任,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他不甚了了,只请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国文系执教兼任 女生管理。她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在青岛的期间,她参加我们轰饮的行列,但是从不纵酒,刚要“朱颜酡些”的时候就停杯了。老来多梦,梦里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发展,跑到砚台山中找好砚去了,因此梦中得句,写在第二天的默忆中:“诗思满江国,涛声夜色寒,何当沽美酒,共醉砚台山。”这几句话写得迷离倘恍,不知砚台山寻砚到底是真是幻。不过诗中有“何当沽美酒”之语,大概她还未忘情当年酒仙的往事吧?(梁实秋《酒中八仙——忆青岛旧游》,载《雅舍杂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除了上述粤菜馆之外,当年青岛粤菜馆还有不少;专门研究“青岛老字号”的人都搞不清了,我们也就很有必要特别考据。1935年有一篇广东人写的文章,先说中山路的英记楼固是粤菜馆最老的一间,“居然能跟着时代而踏上青市第一流酒馆之列,这不能不算是我们广东人的颜色”。紧接着说新开的一间也够威水:“二年前增加了一间福禄寿岭南酒家,地点在中山路上的一间影戏院的隔壁,兼营早市——饮茶,走堂伙计多有土人,生意颇发达,据当事人说,他们是从上海集股开来的,每月开销约四五百元。”更值得庆贺的是:“本年度四月间又增加一间陶然酒家,地点在德县路,从中山路上,可以望见它的招牌,其营业性质和岭南相符,唯早上之点心,则比岭南略佳,不只如此,比上海那一家的点心都要来得幽美,与十几年前香港之马玉山有异曲同工之概,座位亦较岭南清雅。”(志远《青岛粤侨一斑》,《粤风》1935年第1卷第4期,第29~30页)陶然酒家自己也曾大做广告以资招徕:“广州陶然酒家:包办酒席,随意小酌,茗茶美点,粥品面食,广州烧卤,叉烧包子。德县路二十九号。”(《青岛时报》1935年5月1日第7版)这新开的粤菜馆,多是后来记述者所不曾留意的。
这新开的两家,加上前面提到英记楼、公记楼、广安楼、广聚楼、粤来馆,粤菜馆至少已有七家之多了,其中两家还位列一等,这在当时不过二三十万人口的青岛,作为外地菜馆,占比实在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即便在今日近千万人口的青岛市面,你能找得出这么多粤菜馆以及一流的粤菜馆吗?想必不会。由此可以窥见当日粤菜业在寰中的辉煌。
黄际遇先生好客善饮,好美食,除了粤菜馆,他还“别有洞天”,另有去处。首先是他自己的寓所——他从家乡带来了上等的潮菜家厨,梁实秋几十年之后还赞不绝口:“任初先生也很讲究吃,从潮州带来厨役一名专理他的膳食。有一天他邀我和一多在他室内便餐,一道一道的海味都鲜美异常,其中有一碗白水汆蝦,十来只明虾去头去壳留尾,滚水中一烫,经适当的火候出锅上桌,肉是白的尾是红的,蘸酱油食之,脆嫩无比。这种简单而高明的吃法,我以后模仿待客,无不称善。他还有道特别的菜,清汤牛鞭,白汪汪的漂在面上,主人殷勤劝客,云有滋补之效,我始终未敢下箸。此时主人方从汕头归来,携带潮州蜜柑一篓,饭后飨客,柑中型大小,色泽特佳,灿若渥丹,皮肉松紧合度,于汁多而甜之外别有异香长留齿颊之间。”(梁实秋《记黄际遇先生》,载《雅舍杂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恃此佳厨,黄际遇先生便敢在寓所大宴宾客,大宴贵客,且十分自得:
1932年7月26日:约何仙槎(周按: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伉俪来校舍便餐,托金甫代约蒋梦麟夫妇。午回舍。晚吴之椿、赵太侔、杨金甫、仙槎夫妇来饮于此,粤厨乡味,颇恃时誉,鲁酒渗水,心脾羽化。
1933年6月18日:夜约杨金甫、吴之椿、赵太侔、梁实秋、赵涤之、杜毅伯、赵少侯、张怡荪、汤腾汉、曾省之、王咏声来寓便酌,尽欢,夜分始散,主人亦倦不可支。南方乡厨,甚合宾意。
1934年5月6日:李茂祥戏言与予决饮,以醉卧地上为限。晚特约太侔及其夫人任监军,实秋、文柏、少侯、康甫、仲纯相陪,壁垒森严。五雀六燕,瓶罄而扔,不分土厨,不辨鱼味,而宾主皆欢。
1934年7月10日:晨起已有暑意,厨人以干银鱼煮粥,厥味殊甘,招善基共食之。
1934年10月7日:日落诸友歱至,并约丁山申刻入席。乡厨土味,见赏群公,食谱烹经,开河洪子(洪浅哉大背食谱)。
甚而至于借出家厨,“越厨代庖”:“1935年1月1日:晚啸咸设席,假太侔精庐聚饮,虽曰越俎,云有代庖(席假余仆陈厨为之)。”(《万年山中日记》,第27、139、199、232、280、309页)
另一味胜菜馆的私厨就是潮州老乡蔡纫秋运销土产的店铺宏成发;他与宏成发关系亲密,适如梁实秋所记:
我们在青岛的朋友,有酒中八仙之称,先生实其中佼佼者。三十斤的花雕一坛,共同一夕罄尽,往往尚有余兴,随先生到其熟悉之潮州帮的贸易商号,排闼而入,直趋后厅,可以一榻横陈,吞烟吐雾,有佼童兮,伺候茶水,小壶小盏,真正的功夫茶。先生至此,顾而乐之。(《记黄际遇先生》,载梁实秋《雅舍杂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黄际遇先生日记当然更有记录:
1932年6月24日:日未中,校役急以群众环逼校长之小汛来报,至是知不可久居矣。匆匆披衣,徒步出门,携《北江文集》自随,间道而行,至热河路乃得车,驱往里人宏成发处。甫进食举箸,实秋太侔相继而至,共食之后,二君复先抵诣金甫于黄县路重围中。
1932年6月26日:采石送潮产鱼翅一副,命陈厨烹饪携至宏成发,招周廷尧、宋树三同饮。
1933年2月24日:晚偕涤之、少侯往宏成发便酌,肴馔极丰。
1934年12月17日:午赴宏成发,诸同乡多应海亨午宴,兼为予送行,予亦被请酒柬,则婉谢之。留饭柜上。
从上面几则日记看,不仅黄际遇跟宏成发老板及仆役熟得幾可不分彼此,梁实秋他们也跟着熟络得很,可以不打招呼去“蹭饭”。另一个乡党也熟到可“蹭饭”:“1934年8月9日:夜赴柳溪招饮于黄县路李庐,仅堪容膝,而陈书充壁,殊供清赏。先生故汉族而父以粤籍著,供馔尤有乡味,多先生手定者。”(《万年山中日记》,第12~13、14、98、303、251页)
未入日记的可“蹭饭”的乡党恐怕还有吧!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