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买卖契约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国家法的规制研究
——评《清代买卖契约研究——基于法制史角度的解读》
2022-01-24李伟,李晓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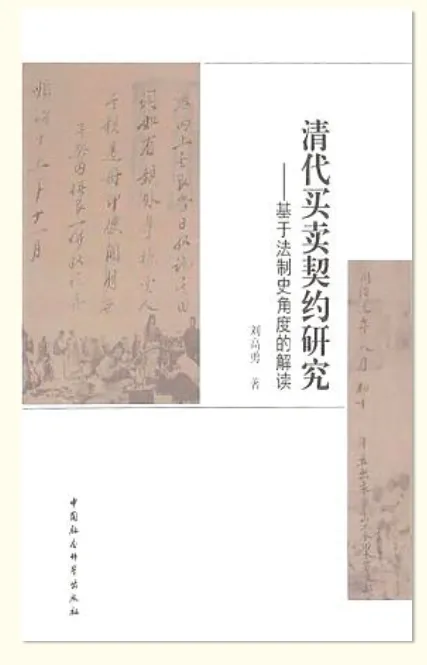
书名:《清代买卖契约研究—基于法制史角度的解读》
作者:刘高勇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6528-7
出版时间:2016 年8 月
定价:62 元
买卖行为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构建法律关系的高频次、普遍性渠道,对买卖行为的内容规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或社会对基本民生的关注水平与管理风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法律体系的先进程度与完善程度。对清代买卖契约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研究,能够为当代学者提供对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抽丝剥茧探索当时社会运行规则与经济文化发展趋势,进而获知封建国家同人民群众的交互关系。由刘高勇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买卖契约研究——基于法制史角度的解读》一书,立足法制史研究视角,对清代买卖契约进行全局探察,分别对该历史时期内的田宅、奴隶、畜产等各种财产买卖契约关系的订立与约束力进行阐述,为当代法制史研究人员及专业学生的学理掌握提供了诸多参照。
该书共分为十一章,全书依照总分结构对契约的规范作用进行分类介绍。第一章作者对我国买卖契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落脚于古代契约的发展巅峰——清代买卖契约特性、类别等诸多要素的详细介绍。第二章至第七章以国家法律为切入点,叙明清代田宅买卖的整体流程与各步骤的开启依据,说明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契约性质及其订立的影响因素与常见不动产纠纷解决方式。第八章对奴隶买卖契约的来源到其实现社会化认知的历程进行钻研剖析,指明其成立的关键要素,并对当时子女买卖契约的订立特征进行刻画,以彰显其本质属性。第九章以畜产买卖契约为主题,详细论述国家法律对该类交易的规范要求及其成立生效的形式要求。第十章陈述了清代法律对买卖契约订立的类别限制。第十一章引出清末修律背景下相关买卖契约订立的非实质性变革。
契约为我国学习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在此之前,“契”或“约”单独即能代表相同的含义,其二者均具有约束之延伸含义,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用以记载或承载人们交流交往信息的凭证。在中华法系的浩瀚苍穹中,质剂、傅别等法律术语曾作为不同时期“契约”的指代,清朝也使用“书”“据”等词汇称呼约定文书。结合清代对物资买卖的规范情况,除盐茶等专卖物项与禁止流通交易的物资外,人们可根据相互之间的供需关系与社会经济基础订立契约,从而完成对所有物的转移,而日常生活经常涉及到的即时交易则因太过普遍且重要性较低而多被省略。同时,清代依照财产的不同特性构筑了相应的划分标准,田宅、奴婢、畜产即为财物的主要类别,该种划分方式为当时买卖契约的类别化、层级化订立提供了诸多便利。因此,本文对契约的研究范围以书面契约为主体,主要针对各类买卖行为中作为凭证的文书进行探索论述。
一方面,清代法律体系为贵重财物与不动产制定了相应的契约订立标准,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须符合严苛的法律流程与交易规范,而其余财产的契约制定则限制较少,多依据交易双方的合意实现财物转换。笔者将依照清代财物交易类别对其买卖契约的订立标准进行阐述。
其一,清代法律对田宅买卖契约的规范已臻完善,构建起了体系化的契约主客体规范制度、契约书写规范标准、契税制度与税粮过割干预机制,从而促进田宅买卖顺利运行。清代田宅买卖契约订立主体受到地域、民族、阶级与宗教限制,官府估价供人买卖的田产依据旗人、民人身份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交易程序与价格抵扣标准。通常情况下,旗人相较民人具有更多的优势利益;而对于法律禁止私自交易的田产,也因其对边远地区统治力量的减弱而形成不同的标准,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限制汉民与少数民族间的单向买卖,另一部分则禁止不同民族人民间的双向买卖;同时,八旗子弟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被禁止在外省购买田产,“借名合同(契约)”也成为严格限制的内容,文武官员则不被允许在所任之地买卖田产。此类规范限制除旗人与民人的区别对待规则外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买卖纠纷的产生,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公平属性。买卖契约的书写也受到高度限制,不仅严格限制代写与涂抹,更要求交易双方使用官府的高价契纸进行书写记载,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契税制度与税粮过割作为保障买卖交易安全与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手段,虽然为人民提供了法律保护与指引,但司法实践过程中经办人员对钱财的克扣索要进一步加重了人民负担。
其二,清代法律体系对奴婢买卖契约及子女买卖契约的订立具有严格的规范程序。虽然在奴婢买卖关系中其已经成为法律客体参与法律关系,但其主观能动性与社会性的完全具备使得该项交易成为稳定性较低、易产生纠纷的契约类别。为规范奴婢买卖,保障买卖双方的交易关系,避免因不当买卖带来的经济与政治惩罚,担保人即凭人或凭媒在契约的订立过程中成为重要主体。而子女买卖契约的订立以其母作为主要责任人,盖因子女与母亲天然的深厚联系与密切感情,使得母亲的同意往往能够作为判定该交易稳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典卖儿女在父权制社会氛围中难免成为“不堪言辞之事”,家庭中男性出面交易的意愿较低。
其三,清代已经构建起对畜产买卖契约订立的明确要求。清朝政府将牛马等畜产作为重要军事物资与税收来源进行法律规制,因而政府要求买卖双方交易畜产必须订立契约,在契约形式要件并未严格限制的基础上,交易双方往往沿用发展较为成熟的田宅契约格式要件进行契约订立,通常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籍贯、交易缘由。
其四,清代法律体系对买卖契约的督促与规范还涉及对其他标的类别的限制。清代法律限制或禁止具有军事用途的物品交易,如箭矢弓弩、旌旗矛盾、枪叉剑戟等物的交易行为会令买卖双方遭受肉刑,而牛马、军需物品及丝帛绸缎与海外交易也不被允许。同时,涉及皇权威仪的物品也被列入禁止交易的范围,浑天仪等天文观测仪器与谶纬之书因其关系到“天子”与上天的玄秘而成为大众不能接触的事物。另外,淫秽小说、鸦片、赌具等对社会的巨大危害促使清代法律强力制裁其民间交易。
另一方面,清代买卖契约的发展也受到多种内外因素影响,其中法律规制下契约订立对人民财产的损益成为首要作用条件,而民间的习惯因素与宏观社会背景下的群众实践则为买卖契约发展提供了诸多合理创想与活跃动力。
一则,契税制度为人民带来的繁重负担阻碍了田宅买卖契约的规范发展。清代以契税缴纳后的官方钤印作为法律认可依据,然而,前述清朝政府对契纸、契文的严苛规定使人民获得法律承认的经济代价较高,交易双方除支付契纸的高昂费用外还需依照比例缴纳契税。因而民间田宅买卖交易往往放弃拥有经官方确定并缴税流程的“红契”,以未经缴税与加盖印章的“白契”为主,如此社会风气之下,民间对官方确认程序的由来与认可程度极低,白契与红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具有同等效力,人们在公堂讼诤开始之前补缴契税,仅仅为避免因未纳税而遭受惩罚。群众为减轻交易负担而绕过法定程序,使得国家法律对买卖市场的规制难以产生实际效用,难以实现买卖契约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磨合促进。
二则,税粮过割制度的不力实施影响了买卖契约的法定化、规范化发展。如前所述,税粮过割作为田产买卖法定程序的最后一步,需以契税缴纳为前提,因而民众对交易成本的切实考量促使该制度的实际实施成效偏低。而地方政府对田产的税收以年份为单位,依照下辖田地数目进行定量收取,税粮过割的不理世事并未对地方财政产生消极影响,因而朝廷对税粮过割的管理较为松散,加以经办人员对事主钱财的图索致使买卖双方尽可能避免与官府有所牵涉,从而导致买卖契约的法定规范发展遭到进一步阻碍。
三则,“一田两主”民间习惯的普遍使用提升了买卖契约的发展动力。“一田两主”惯例下,上层田皮与下层底地的分离管理与交易适应了明朝后期以来的地权分化制度,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化运行惯例,甚至影响公堂判定的认定因素。该习惯中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划分前瞻性地彰显了田产的经济学意义,为清代土地田产的交易带来新的认知与发展动力。
四则,奴婢买卖过程中对担保的重视为买卖契约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源泉。清代奴婢买卖涉及奴婢从属关系的移转,由于其自身同全体人类一致的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无法断绝,使得买方极易因不可控因素导致自身权利受损,因而除买卖契约中卖主本身的责任担保之外,保人(凭人)成为交易关系中的重要主体,以保障买主交易正当、所属权益不受侵害。买卖契约对于担保人重视程度的深化为奴婢的合法安全买卖提供了保障,使交易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升了买卖关系的稳定性与买卖市场的活跃性。
清代买卖契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不断革新发展,直到清朝晚期《大清民律草案》的颁布,将西方民法中的自由民主思想融入中华法系,但并未深切结合中国买卖市场的习俗惯例,而未产生实际效用。
民国时期对清末修律过程中显现的一系列缺陷进行优化改善,一方面深度考察民间契约并将其与法律规范全面融合,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依照地域差异与契约实践的复杂性实现国法同惯例的有机统一,除恶劣习惯之外,买卖双方甚至能够突破法律规范实现自主性契约订立,同时保留传统的契约形式,减轻群众对新型契约制度框架的陌生感与排斥感;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传承千年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使本土商业获得一定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了民间契约实践习惯的转变,带动了民国时期契约制度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实现国家法律规范同民间习惯的相互影响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