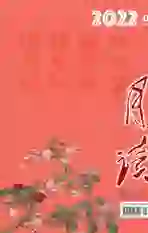人面桃花与红妆
2022-01-18曹喆
曹喆
唐代孟棨留有《本事诗》一卷,其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崔护是个帅哥,为人高洁自傲,进京考进士落榜。清明那天,一个人跑到京城城南去玩,看到一个一亩地大小的庄园,花木丛萃,寂静得似乎无人。他敲门讨水喝,好久才有个女孩子开门。女子让崔护坐床榻边,崔护自己则斜倚着桃树,看着她“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护搭话,女子只是注视着他却不接话。崔护离开时,女子一直送到门口。崔护眷盼而归。到了来年的清明,崔护忽然想起城南这位女子,情不可抑,跑去找她。门墙如故,但是关门落锁,家中无人。崔护就题诗在左门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又过了几天,崔护偶然到城南,又去找那位女子,听到庄里有哭声,就敲门问怎么回事。女子的父亲出来说:“你就是崔护吧?”崔护回答说:“是啊。”老人哭着说:“是你杀了我女儿啊。”崔护很吃惊,不知说什么好。老人说:“我女儿及笄之年就读了好多书,还没找婆家,自从你去年来了之后就一直恍然若失,前几天我和她外出回来,她看到门上的诗,就生病了,好几天没吃饭就去世了。我老了,女儿之所以没有嫁人,是希望能找到个好人家,也能为我养老,谁知女儿不幸去世,难道不是你害的吗?”崔护也陪着哭,求入内,抱着女子的头放在自己腿上,哭着说:“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不一会,女子的眼睛睁开,活了过来。女子父亲大喜,将女子许配给了崔护。
这个故事就是“人面桃花”的出处。诗中所说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是说粉红的脸和桃花一样美丽,另外,“桃花”也可代指妆容。《妆台记》有:“隋文宫中梳九真髻、红妆,谓之桃花面。”红色妆容被称为桃花面,也称桃花妆。唐至五代的很多绘画中都能看到桃花面。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三也记载:“周文王时,女人始傅铅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宋武宫女,效寿阳落梅之异,作梅花妆。隋文宫中,红妆,谓之桃花面。”
南朝梁江洪《咏歌姬》有关于红妆的精彩描写:“薄鬓约微黄,轻红淡铅脸。”辛弃疾《满江红·暮春》写道“红粉暗随流水去”,则用红粉比喻美人。成书于宋元之间的《事林广记》记录了“玉女桃花粉”,用玉女、桃花命名妆粉算是典故的灵活应用,这种粉的调制相当复杂,由益母草烧灰、石膏、滑石粉、蚌粉、胭脂等混合而成,据说能“滑肌肉、消斑点、驻姿容”。
唐代张泌《妆楼记》记载,魏文帝在水晶屏风后看书,一位魏文帝宠爱的叫薛夜来的宫女没留意撞在屏风上,伤到面颊,御医虽尽力医治,薛夜来的伤口痊愈后仍留下红色的痕迹,魏文帝反而更加宠爱她,于是宫中女子纷纷效仿在面颊画上红妆,这种妆容被称为晓霞妆,后又演变为斜红妆。《妆楼记》记:“斜红绕脸,盖古妆也。”
胭脂和粉从汉代开始使用,一直到近代,都是女性主要化妆品之一。元杂剧及元曲中有很多使用粉和胭脂的描写。如无名氏所作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第四折:“噤声!这里是经略府军政司,又不比风月所莺花市。错认做洛阳地面承天寺,花费了些金银饷钞,收买些腻粉胭脂。”张可久所作散曲《套数·牵挂》有:“麝脐薰五花瓣翠羽香钿,猫眼嵌双转轴乌金戒指,獭髓调百和香紫蜡胭脂。”亢文苑所作散曲《套数·为玉叶儿作》有:“(梁州)你为我堆宝髻羞盘凤翅,淡朱唇懒注胭脂。”
胭脂蜡是用胭脂、动物脂肪和蜂蜡调成的固态或半固态化妆品,用法如现在的口红。
按照元曲描绘,当时女性的完美外貌大致为:高高的云鬓,皮肤上傅着白粉,用黛色描绘过的柳眉,面颊上用胭脂粉染红,面上贴着翠靥,小脚穿着精致的绣鞋,细细手指,指甲上用胭脂染红。如吴昌龄《套数·美妓》描绘的美人:“藕丝裳翡翠裙,芭蕉扇竹叶樽。衬缃裙玉钩三寸,露春葱十指如银。秋波两点真,春山八字分。颤巍巍雾鬟云鬓,胭脂颈玉軟香温。轻拈翠靥花生晕,斜插犀梳月破云。误落风尘。”“常记得五言诗暗寄回文,千金夜占断青春。厮陪奉娇香腻粉,喜相逢柳营花阵。”乔吉所作散曲《小令·赠姑苏朱阿娇会玉真李氏楼》描绘的美人:“合欢髻子楚云松,斗巧眉儿翠黛浓,柔荑指怯金杯重。玉亭亭鞋半弓,听骊珠一串玲珑。歌触的心情动,酒潮的脸晕红,笑堆着满面春风。”
元代人还用胭脂涂红指甲,如现在的指甲油的用法。如张可久所作散曲《小令·红指甲》所述:“玉纤弹泪血痕封,丹髓调酥鹤顶浓。金炉拨火香云动,风流千万种,捻胭脂娇晕重重。拂海棠梢头露,按桃花扇底风,托香腮数点残红。”
按照目前考古资料,最早使用的红色化妆材料应该是铁矿石粉,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器物以及岩画上,红色物质都是赤铁矿石。据商代妇好墓出土有少量朱砂推测,商代开始可能使用朱砂作为红妆材料。朱砂呈大红色,又称辰砂、丹砂、赤丹,是硫化汞的天然矿石。商代用朱砂粉末涂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汉代《释名·释首饰》记载:“䞓粉。䞓,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颊上也。”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妆盒内有朱砂粉,说明汉代已经用红粉染面颊了,朱砂是红妆的主材。东汉之后,炼丹术兴起,开始用化学方法生产朱砂。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七有:“古者妇人妆饰,欲红则涂朱,欲白则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时未有烟脂,故但施朱为红也。烟脂出自虏地。”而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还没有胭脂。汉代时中原地区才陆续引入红花种植,将花汁榨出提取红色胭脂。
胭脂又称燕支、臙脂、焉支等。《妆楼记》记:“燕支染粉,为妇人色。故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阏氏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清人撰写的《胭脂纪事》中有一段关于胭脂的传奇记载。晋代汾阴少女秦子都,十三岁,面容姣好,有道人到其家,拍着她说,这个女孩子不像是凡人啊。传授给子都提炼红色丹药的方法,让子都去取汾水,注入古鼎中烧开。水沸腾时,道人从袖中取出少许东西,放到沸汤中,忽然鼎上升起袅袅紫烟。子都用手挥烟,烟越来越浓,满鼎都是紫金色。子都取绵絮盖到烟上。絮中饱蓄紫烟,被收起来用作涂抹嘴唇的化妆品。道人走了之后,子都经常收集紫烟,周围远近的女子,都来找子都求紫烟绵。子都性格比较懒散,到了二十还不嫁人,以卖胭脂来赡养母亲。自己不耐烦用水慢慢烹煎,凡来求胭脂的,子都用牙齿嚼绵汁少许让人家带走。不管绵多绵少,经过子都嚼绵汁后都是紫烟之色,于是千里内外的女子都来找子都讨要胭脂,称子都为胭脂师。后来子都慢慢老去,但是依旧面呈桃花色。一天晚上,大水冲走了她的房子,子都便消失无踪了。后人不得其制胭脂的方法,也汲汾水渍绵,浸泡不成,然后将水烤干又不成。有机灵女子出点子说:“胭脂男女之艳色也。”就择日与男子发生关系后制胭脂,还是不成。后来就在汾水上立庙,称子都为紫府胭脂之神。每岁三月八月,诸女郎着紫衣、紫裙、紫带、紫冠,发簪也是紫的,各种佩戴都是紫色,祭祀于庙,唱紫府之歌,以讨神的欢喜。神来就会有紫气出现在祭祀供品的上方,一会儿供奉的牺牲和花果等都变为紫色,祭祀者认为这就是灵验了,又各铸小神像在家中祭祀。如果要制胭脂,则先斫取桃枝煎水,遍洒屋两楹,又折桃枝寸许数千条,围插墙阴。禁鸡犬鸣吠,贡一杯紫琉璃于神前,礼拜一下。再用桃叶自然汁刮嘴唇,微微出血,然后将汾水置鼎内,住得远的没有汾水,则用井华水随便点紫色花,用开水温之,长跪等待,稍微等一会儿就有胭脂了。将胭脂入绵收藏,得到的颜色如天边朝霞。后世胭脂之法,始于此。这段记载虽然有趣,但不太靠得住。
南宋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七采录了多篇文献,有关于胭脂的记载:“清微子《服饰变古录》云:‘燕脂,纣制,以红蓝汁凝而为之。官赐宫人涂之,号为桃花粉。蓝地水清,合之色鲜。至唐颇进贡,惟后妃得赐,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亦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为红蓝耳。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为红蓝也。’《西河旧事》云:‘失我祁连岭,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红蓝,北人采其染绯,取其英鲜者作燕脂。《本草》:‘红蓝花堪作燕脂,生梁汉及西域,一名黄蓝。’《博物志》云:‘黄蓝,张骞所得,今沧魏亦种,近世人多种之,收其花,俟干,以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亦曰干红,目其草曰红花。以染帛之余为燕支。干草初渍则色黄,故又为黄蓝也。’《史记·货殖传》:‘若千畮卮茜。’徐广注云:‘卮,音支,鲜支也;茜,音倩,一名红蓝,其花染缯,赤黄也。’又知今之红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谓之乌红,系用苏方木、枣木染成,则非古之茜矣。”
据《齐民要术》记载:种红蓝花要在雨后赶快播种,可以漫散种、如种麻法耧种或者掩种。花开后,要在每日凉爽时摘取,不采摘就会干掉。摘的时候要摘干净,留着的花会合上。五月时,花的种子成熟,暴晒打子。五月可以种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可种。七月采摘花朵,色彩鲜艳,耐久不褪,比春天种的质量要好。种红蓝花的收入相当不错,如果种好田一顷,年收入可达绢三百匹。一顷花,每天需要百人来采摘,如果只是以一家劳力采摘的话,采摘量到不了十分之一。每天早上,将田地平分为两个区域,小儿僮女上百人在两个区分布均匀采摘。摘取到的红花用碓捣碎,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后,以清且发酸的粟饭浆再捣,再以布袋绞去汁,收取染红留用。放到容器里用布盖上,第二天天亮时捣匀,放到席上暴晒干。做胭脂时,烧藜蒿草调清水成灰汁,如果没有就用其他草灰代替。以汤淋取清汁,开始淘灰的水太厚,只能用于洗衣,第三遍淘的水用来揉花十多遍,直到颜色尽了。布袋绞取淳汁,放到瓷碗中。取醋石榴两三个,取子并捣破,倒入发酸的粟饭浆水搅拌,布包着绞汁用来和花汁。如果没有石榴,用好醋和饭浆代替。如果没醋,极酸清饭浆也可以。倒入适量白米粉,粉太多则太白。用干净竹筷使劲搅拌。盖上盖子过夜,泻去上层清汁,至沉淀物處停止,放到布帛的袋子中悬挂着。第二天,半干,捻作小瓣,如半麻子大小,阴干,就得到胭脂。制作过程中的碱性灰水用来溶解红色素,醋水将红色素沉淀。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杨贵妃的汗所谓“红腻而多香”,十之八九是因为胭脂、粉和香料的缘故。
胭脂是历代女性必用的化妆品,在各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成为与女性关联的符号。如唐代杜甫《曲江对雨》:“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宋代赵以夫《满江红·牡丹和梁质夫》:“满地胭脂春欲老,平池翡翠水新肥。”《敦煌曲子词·柳青娘》:“故著胭脂轻轻染,淡施檀色注歌唇。”金代元好问《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之一:“翠叶轻笼豆颗匀,烟脂浓抹蜡痕新。”明代张景《飞丸记·坚持雅操》:“我情愿甘劳役,思量忍命穷,拼得臙脂委落如云鬞。”清代孙枝蔚《后冶春次阮亭韵》:“梨花独自洗胭脂,虢国夫人别样姿。”
(选自《片花落无声:演变中的古代时尚》,中华书局)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女性妆容及审美的书,涉及古代女性审美文化及各时期的时尚。作者从妆容、服饰、发型、首饰、美容方、香方等十个专题探讨了与此相关的审美起源以及发展历程中的文化现象,其间穿插古代女性风雅的生活方式。引用了包括诗词、笔记小说、元曲等大量资料,讲述了很多典故的来源,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女性追求美的历程。书中有丰富的彩色插图作为文字的辅助,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各时期的女性形象。本书既是普通读者了解古代女性文化的一扇窗,也可以为专业读者提供相关的文献内容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