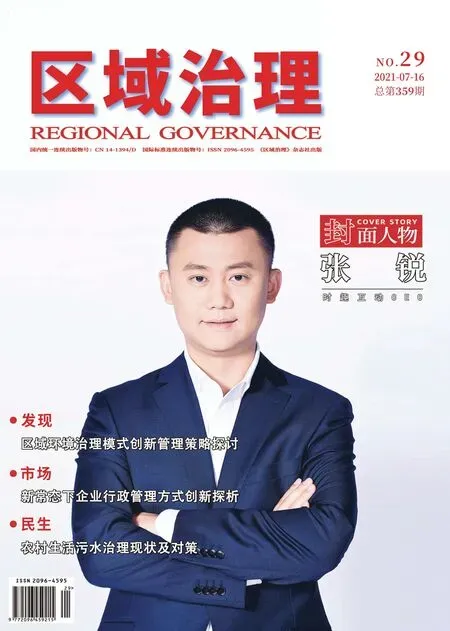论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在国际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2022-01-01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潇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谭潇
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一项法律概念,其提出与国家社会“共同关切”这一法律概念的提出相关,前者被认为是与后者相关的一个规范性概念,是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的一项责任。这项法律概念源于司法实践,自1970年以来,多次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中被提及,并被原告国和被告国作为起诉的依据及辩论中的援引,同时并被应用在多项国际法律文件中。这是一项广受争议的法律概念,国际法院在审判中对此概念的使用受到热切的关注和讨论,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在审判中对于这一概念的适用往往推动其理论的发展。因此,对于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探讨,应当对于其在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进行阶段性的梳理,从而实现对此概念的把握。
一、国际法院适用“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实践
国际法院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态度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概念源起并未直接适用阶段
早在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中称,关于通告的国际义务系基于“普遍的、广为承认的原则即人道主义的考虑,海上交通自由原则和国家不得故意允许其领土被用来从事违背其他国家的权利的行为”[1]。这里将一项国家义务建立于“人道主义考虑”而非具体的条约与法律文件,体现出“对国际社会整体义务”的价值内涵。其对象并非具体某一个国家因条约而建立的利益,而是所有国家共同具有的利益。这一阶段,其还并没有成为一个明确具体的法律概念,而是在国际法院的文书的论述中被阐述,即认为存在一种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考虑,而国家对于国际社会承担义务,对于其行为有所限制。
(二)概念正式提出并进一步发展阶段
1970年的“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是国际法院首次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进行了直接论述,在国际社会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本案中,比利时作为原告方要求西班牙政府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损失提供经济赔偿,主张其负有“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国际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判决中表明履行“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一种属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是产生于关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价值的原则,并且已经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被赋予受到保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权利。此后,关于这一概念作为依据进行起诉的案件增多。在1995年葡萄牙诉澳大利亚“东帝汶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自身的出庭权进行了论证与反驳的辩论,国际法院对于这一概念的适用回避,而未能进行进一步分析探讨。
国际法院虽然在1970年对此概念进行论述,但因顾虑敏感性和对于国际间国家关系的重大影响等原因,对此项概念的直接适用是非常谨慎的,表现出较为保守的态度。
(三)扩大适用阶段
2001年,“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被编写进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这体现出国际法中这一概念在立法领域的推进[3]。2019年,冈比亚在国际法院起诉缅甸,指控该政府的行为违反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请求法院裁判并宣告缅甸违反《灭种公约》的义务。该案成为国际法院历史上首次由一国在自身利益未受侵害或特别影响的情况下,确立自身诉权,通过诉诸“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概念援引他国国家责任的案件。这是国际法庭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概念具体适用的重大突破。
伴随国际责任法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矛盾持续增多,对这一概念的适用所涉及的范围,从最初的保护基本人权有关公约,进一步在物种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有所涉及,如2010年的“南极捕鲸案”是澳大利亚依据了《国际捕鲸管制条约》在国际法院向日本提起诉讼,日本最终被判败诉。2014年“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的谈判义务案”是基于《不扩撒核武器条约》。2019年原告诉权建立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成立,体现出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成熟与明确,同时也凸显了其适用规则和适用条件须明晰的问题。
二、国际法院适用"对国家社会整体的义务"存在的问题
在前文对于国际法院适用“对国家社会整体的义务”不同阶段的梳理,揭示出目前主要有如下问题。
(一)起诉权确立的法律依据不明确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否可以构成其诉权的法律基础,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方面,2012年的“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具有参考性。在该案中,塞内加尔质疑比利时的酷刑诉权资格制度是否成立,比利时指出依据《禁止酷刑公约》,所有的该公约缔约国都拥有要求其他缔约国履行公约条文规定之义务的权利。对此,国际法院在判决中,从公约中条款体现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一目的与宗旨层面进行适用。但其分析的是诉权问题这一程序性事项,并非《禁止酷刑公约》所使用的对象。在这里国家法院的论述体现出对于条约的实质内容与法律程序问题不加区分使用的问题,而其法律依据似乎只有《草案》第48条第1款中的内容,但并未被国际法院在判决中直接援引。
(二)诉讼程序规则不完善
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一方向来自他国的损失或者受到其他国家利益损害而提出赔偿请求,诉至国际上的司法部门,是任何一国在本国享有的主权和合法性体现。然而,对于未受到直接侵犯的第三国,是否有权利就任何一国对其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直接向其提起国际法上的诉讼,国际社会的争议比较大。依据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只有那些权益受到直接损害的当事国才有相应诉权进行起诉。
对此,国际法委员会主张,违反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并不仅仅损害了直接受害者的利益,还同时侵害了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成员的利益,因此每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法律主体主张要求行为国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负责仍然具有正义性,应当得到国际法的支持。然而,虽然这样的行为具有正义性,对于其实施性的解决方面,仍有较大的空白。
(三)具体适用的谨慎和相对滞后
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义务的概念,也与国际法其他邻域,如国家责任法、国际强行法等紧密关联,相关的配套规则并不健全,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响与不同态度以及可能对相关实践造成的影响,国际法院对此概念在审判中的具体适用往往采取审慎和回避态度[4],使得这一规则的发展呈现出迟滞的特点,使得其在司法中适用受限。
三、完善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在国际法院适用的建议
(一)防止对法律规则的滥用:明确法律后果
国家违反“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将会造成的法律后果,在目前国际法院的所有文书中,未得到具体规范和进一步明确,这样的缺失不但有可能造成解决争端中程序冗杂、诉讼成本增高,而且会增加争端解决的难度,在国际环境中加剧国家间的矛盾与怀疑,无助于国家间法律分歧的解决。
国际法院在适用这一概念对国家不法行为进行判决时,对于其后果应当依据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正确发挥国家法院作为适用法律机关的作用,对于目标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必须要进行严格的限制。
(二)逐渐构建具体的起诉规则
在协调国际法诉权资格理论的基础上,为更好地使“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能够被善用,其法益能够得到实现,避免规则被滥用,应当明确非直接受害国与直接受害国、利益受特别影响的国家这几个不同主体在援引他国国家责任时的顺序问题,在直接受害国由于管辖权等程序性原因无法直接就自身利益受损进行起诉时,非直接受害国能够依据相关条约确立起诉资格进行起诉。而当直接受害国能够进行起诉对于自身权益进行主张时,非直接受害国越过直接受害国先行援引“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在国际法院进行起诉的行为则应当受到限制。
四、结语
通过前文对国际法院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对于“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适用上,国际法院的相关法理以及回应的态度,都经历着一定的历史发展与变化。以“灭绝种族罪公约保留咨询意见案”和“巴塞罗那公司案”为基础起点,国际法院明确了国家对于国际社会承担一定义务,在2019年“冈比亚诉缅甸案”中,对于基于这一义务的诉请作出了积极回应,虽然其对于诉讼程序的探究仍然是不充分的,但这些司法实践将会对国家法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为实践《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第48条提供更多案例,推动并丰富国际法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国际社会中的干涉在司法领域铺开路径,不同国家对此更是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存在分歧,对这一规则的滥用将会为霸权主义提供工具,而对这一国际法理念的细化及规则完善,能够在更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调节上提供新思路,是国际法发展中重要的机遇,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注释
①该草案第48条规定了受害国以外的国家也有权在规定的情况下援引他国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其中包括:(1)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务或者(2)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