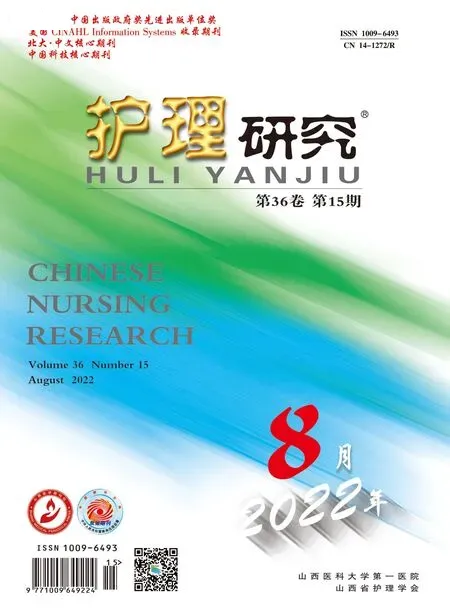癌性疼痛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研究进展
2022-01-01张晓霞喻小艳张翀旎
张晓霞,罗 倩,喻小艳,喻 鹏,张翀旎
1.南昌大学护理学院,江西 330006;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癌性疼痛是由肿瘤本身或因肿瘤治疗引起的疼痛[1],是癌症病人常见的症状之一。癌性疼痛可发生于肿瘤发展的各个阶段,初诊病人的发生率约为25%,晚期癌症病人为60%~80%,其中1/3 的病人为重度疼痛[2-3]。癌性疼痛不仅损害机体系统功能,导致病情进展、恶化,还会增加病人的心理痛苦,甚至出现自杀倾向[4-5]。本研究检索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对癌性疼痛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干预策略进行综述。
1 癌性疼痛影响因素
1.1 肿瘤部位 癌性疼痛是一种混合性疼痛,发生机制复杂。癌性疼痛包括由于原发肿瘤或转移瘤破坏或损伤头颈部、胸腔、腹腔或盆腔内脏器、骨骼、神经系统等引起的身体不同部位的疼痛[1]。肿瘤转移到骨骼所致的疼痛是导致癌性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转移至椎骨、骨盆、长骨和肋骨最为常见[6]。Fink 等[7]指出,肿瘤部位与疼痛有密切关系,其中头颈部癌症病人经历的疼痛最多,其次为妇科癌症、消化系统癌症、肺癌、乳腺癌和泌尿生殖系统癌症。研究发现,疼痛是头颈部癌症病人的常见症状之一,在接受治疗前最为突出,可达85%,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头部和颈部区域有丰富的神经支配[8-9]。宫颈癌靠近盆腔神经、软组织和骨性结构,且肿瘤容易扩散到腹膜后,疼痛发生率亦较高[10]。另有研究发现,胰腺癌病人常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并呈进行性加重,这可能与肿瘤生长侵犯胰腺周围神经导致神经损伤有关[11-12]。
1.2 治疗方式 癌性疼痛根据疼痛表现形式分为急性和慢性疼痛,急性疼痛主要与诊断性检查或治疗有关,慢性疼痛与肿瘤本身或相关治疗有关,包括化疗、放疗、手术等引起的疼痛[13],最常见的为口服或静脉化疗引起的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集中发生于手、足、面部等部位[1]。手术是早中期实体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术后常引起慢性疼痛、幻肢疼痛等,以乳腺癌和肺癌最为常见,约63%的乳腺癌女性病人在乳房切除术后9 个月出现持续性疼痛,33%的肺癌病人开胸术后3年内会发生疼痛[6,14]。放疗可致周围组织纤维化压迫神经、直接或间接损伤神经而出现慢性神经性疼痛[14-15]。Oberoi 等[16]指出,20%~40%接受化疗的病人以及几乎所有接受放疗的头颈部癌症病人会发生口腔黏膜炎,严重者可出现口腔剧烈疼痛。因此,治疗方式与病人的疼痛发生率及疼痛程度密切相关,如何减轻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仍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1.3 心理因素 疼痛是一种主观体验,病人的认知状态、正负性情绪通过大脑痛觉中枢及痛觉处理中枢的调节,改变下行痛觉信号传导通路,加之心理因素可激活大脑中的固有调节系统,从而影响病人对疼痛的感知[17-18]。Bingel 等[19]研究指出,个体情绪会影响病人对疼痛的感知,积极的情绪可使瑞芬太尼的镇痛效果翻倍,而消极情绪可干扰瑞芬太尼的镇痛效果,甚至使镇痛作用完全消失。此外,疼痛信念是个体对疼痛经历的感受及认识。杨文玉等[20]研究显示,疼痛信念与口腔癌病人癌痛水平呈正相关,不正确的疼痛信念会影响其疼痛水平。基于此,在临床工作中需要密切关注病人的心理状况,引导病人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和信念对待疼痛、疾病和治疗,减少消极情绪的疼痛放大效应。
1.4 其他因素 研究显示,文化背景、炎症等因素与癌性疼痛的发生有关[21-23]。研究显示,文化背景对癌性疼痛有一定的影响,亚洲癌症病人对癌性疼痛的感知障碍明显高于西方国家,而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通常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痛苦,加之对癌性疼痛、阿片类药物存在错误认知,往往经历更多癌性疼痛[21,24];炎症可能与癌性疼痛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22],白细胞介素6(IL-6)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参与炎症的起始和调节,其水平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术后疼痛等急慢性疼痛发作时均有明显变化,而其表达失调又会引起疼痛进展[25-26]。Reyes-Gibby 等[27]研究指出,IL-6水平影响肺癌病人的疼痛严重程度。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炎症与癌性疼痛的关系,以寻求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
2 癌性疼痛评估工具
医护人员对癌症病人及时有效的疼痛评估是护理和治疗的基础。目前,临床有单维度和多维度两种评估工具,单维度评估工具主要评价疼痛强度,包括数字分级法、视觉模拟评分法、主诉疼痛分级法等,多维度评估工具涵盖生理、心理等评估,包括简明疼痛调查量表、Mc Gill疼痛问卷法、整体疼痛评估量表等[5]。Stinson等[28]根据癌症人群特征,构建了Pain Squad 智能疼痛评估系统,后由我国王佳姝[29]研究团队引进并汉化,形成中文版复合式癌症儿童疼痛自我报告评估系统。Warden 等[30]研制了晚期老年痴呆疼痛评估量表(Pain Assessment in Advanced Dementia,PAINAD),可有效评估和监测无法自我报告疼痛病人的疼痛情况[31],由我国学者彭美慈等[32]翻译汉化形成中文版,但是目前尚未广泛应用于我国的癌性疼痛评估。该类评估工具受病人文化程度、理解能力等的影响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倚。因此,Jud 等[33]针对乳腺癌病人的疼痛特点,为该类病人开发了一个“疼痛地图”应用程序。病人使用平板电脑报告疼痛程度并且在人体结构图上标明疼痛区域后即可生成“疼痛地图”,其中白色部分为非疼痛区域,黑色部分为疼痛区域,颜色越深代表经历的疼痛越多。Bernier 等[34]将Color Me Healthy 应用程序用于接受化疗的学龄期癌症患儿,患儿通过游戏的方式在人物图像上描述自己的疼痛部位及其严重程度和困扰程度,有利于疼痛识别、表达和处理。“疼痛地图”和“Color Me Healthy”可以清晰、准确地反映病人疼痛的部位和严重程度,为临床医护人员实现精准化的干预提供实证。
3 癌性疼痛干预策略
3.1 药物干预 药物干预是目前缓解癌性疼痛最有效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三阶梯疗法已成为国内外药物治疗癌性疼痛的基本指南,三阶梯疗法是根据病人的疼痛程度将药物划分为阶梯式,一阶梯药物主要为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消炎药,二阶梯药物为可待因等弱阿片类药,三阶梯药物为吗啡等强阿片类药物,并辅以其他药物治疗癌性疼痛[4]。研究显示,三阶梯疗法镇痛效果明显,治疗后病人疼痛降低57%~81%[35]。有学者提岀“四阶梯疗法”即在三阶梯疗法的基础上增加第四阶梯,即区域阻滞技术、神经毁损阻滞术和植入式鞘内药物输注系统等,能达到更好的镇痛效果[4,36]。但目前对应用第二阶梯药物的必要性存在争议,有研究者认为早期使用低剂量吗啡止痛能达到更好的效果[37]。Nunes 等[38]研究指出,与三阶梯疗法相比,将吗啡作为首选药物并没有更好的镇痛效果,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高。因此,仍需要更多研究规范镇痛药物标准化使用流程,以达到最佳止痛效果。
3.2 非药物干预 三阶梯疗法的应用和推广使得癌性疼痛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仍有约20%病人承受癌性疼痛带来的痛苦[35],我国2018 版癌症疼痛诊疗规范指出适当地应用非药物干预可作为癌性疼痛的补充治疗方案[2]。近年来,非药物干预逐渐应用于癌性疼痛病人中,减轻了病人的疼痛感。
3.2.1 疼痛教育 疼痛教育是健康教育细化的一个分支,旨在通过开展以疼痛为核心的专项教育影响病人对待疼痛的态度和认知,从而帮助病人树立正确的应对方式[39-40]。《北京市癌症疼痛护理专家共识》[41]中强调疼痛教育应贯穿于疼痛治疗的全过程。沈艳[42]从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领域对癌性疼痛病人实施癌痛结构化教育,共3 次课程,1~2 d 1 次,每次持续30~40 min,与常规癌痛知识宣教相比,结构化教育更能提高病人癌痛的相关知识,提升自我效能水平,减轻疼痛强度。Yildirim 等[43]发现,在癌性疼痛病人中实施疼痛教育计划,能降低病人的疼痛强度,减少疼痛管理障碍。研究已证实疼痛教育对缓解疼痛的有效性[44],但目前缺乏科学、规范的教育模式和评价标准,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一个整体的教育体系,从而提高病人的认知。
3.2.2 心身疗法 心身疗法强调心理和身体的交互作用,通过心理来影响身体功能,进而促进个体身心健康[45],包括正念冥想、瑜伽、催眠疗法、放松疗法等。Carson 等[46]将48 例乳腺癌病人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予以瑜伽干预,共8 次,包含冥想练习、动作练习和呼吸训练,结果显示瑜伽干预尤其是冥想练习能改善癌症病人的疼痛,且病人的练习时间越长,疼痛改善效果越明显。研究显示催眠疗法能缓解癌性疼痛,其机制可能与催眠调节相应的感觉皮层有关[47-48]。国外早已将催眠疗法应用于癌性疼痛病人中,但是由于治疗的特殊性以及病人认识的局限性,加之正规心理治疗在我国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47],催眠疗法尚未广泛应用于我国癌性疼痛病人。因此,深入探究催眠疗法在我国癌性疼痛病人中的应用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3 虚拟现实(VR)技术干预 VR 技术通过计算机模拟产生的虚拟环境将参与者与现实世界隔离,参与者在视、听、触觉等多感官中享受沉浸式的体验,通过感知虚拟环境中的物体,并且与物体或者人物进行交互,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49]。研究表明,VR 技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缓解癌性疼痛的非药物干预方法,通过认知参与、分散注意力减轻病人的疼痛感[50]。国外已将VR 技术用于癌性疼痛病人中,且效果较为明显,Bani Mohammad 等[51]将乳腺癌伴有疼痛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仅使用吗啡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接受“深海潜水”或“坐在海滩上”的VR技术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Niki等[52]研究证实,VR 技术旅行可有效降低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感,改善其症状负担,且未发生相关不良事件。目前,VR 已广泛应用在我国的医学、教育等领域,但未见VR 技术应用于癌性疼痛的相关报道。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探讨VR 技术对我国癌性疼痛病人的有效性,促使VR 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3.2.4 中医干预 中医以辨证论治为理论基础,运用针刺、穴位贴敷、艾灸等技术,能降低爆发痛的发作频率,且无明显不良反应,能有效减轻癌性疼痛病人的身心压力[53]。Chiu 等[54]研究发现,针灸能缓解癌症相关疼痛,尤其是恶性肿瘤相关疼痛和手术引起的疼痛。魏有刚等[55]发现,与单纯口服奥施康定相比,联合穴位埋线具有更好的止痛效果,且爆发痛发生率和奥施康定使用量显著减少。顾亮亮等[56]将中医耳穴压籽法用于80 例癌性疼痛病人,结果显示中医耳穴压籽法联合常规三阶梯止痛法有更好的镇痛效果,同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病人的生命质量。目前无论是单一的或者联合多种中医干预方法均证实对癌性疼痛病人有一定的疗效[57],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医干预癌性疼痛的机制,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止痛效果。
3.2.5 神经调控技术 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是一种适用于急慢性疼痛的非侵入式镇痛疗法,其机制可能为脊髓背角内的胶质细胞存在一种类似闸门的神经机制,能减弱或增强外周上传到中枢的神经冲动,而TENS 产生的各种刺激通过激活阈限较低的大直径传入纤维关闭该闸门,从而达到镇痛效果[58-59]。Loh 等[60]对76 例接受TENS 的癌性疼痛病人进行随访,其中69.7%病人疼痛症状改善。何丽华等[61]首次将TENS用于胰腺癌疼痛治疗,证实该疗法可显著缓解疼痛,且无不良反应。但目前在国内尚未广泛应用,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进一步探究TENS 对癌性疼痛的影响,以及电刺激频率、时间、强度、治疗周期、选穴等与TENS治疗效果的相关性,以优化TENS 的镇痛效果。
3.2.6 综合干预 单一干预方法已被证实对癌性疼痛病人有不同程度的效果,研究者结合多种方法在癌性疼痛病人中开展综合干预。Dikmen 等[62]研究表明,反射疗法联合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能有效降低病人的疼痛严重程度和疲劳感。刘洁等[63]将96 例病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穴位按摩结合放松训练,干预持续2 周,不仅缓解了病人的疼痛,还能减少疼痛对其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综合干预多是非药物单一干预方法的组合,然而不同干预方法的协同效果仍不清楚,加之癌性疼痛的复杂性,综合干预在癌性疼痛病人中应用较局限,未来可鼓励多学科合作,组建多学科疼痛治疗小组,从而探索出最佳效果的干预组合。
4 小结与展望
肿瘤部位、治疗方式、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癌性疼痛的发生和发展,而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减轻病人的疼痛感,缓解身心的负担,可见探索针对癌性疼痛的干预措施是护理领域的重要课题。目前临床已开展药物和非药物干预,但是癌性疼痛是持续的过程,如何实现有效的居家延续干预与随访,关系到病人的生存质量及生命长度。由此,建议借助网络平台、智能手机等,为癌性疼痛病人提供远程评估、监测和指导。同时,通过对照顾者进行疼痛相关知识培训,提升其间接疼痛体验及照护能力,从而实现家庭与医院相融合的二位一体照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