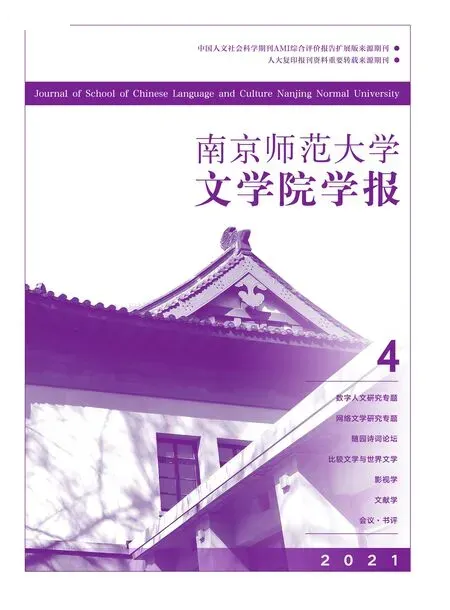贾谊《陈政事疏》经班固史笔的删节及考补
2021-12-31刘明
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班固在《汉书》贾谊本传里载其所撰《陈政事疏》(1)篇名据《汉书》本传“谊数上疏陈政事”拟定,又或题《治安策》,见《李卓吾先生批选晁贾奏疏》;或题《论时政疏》,见明张燮编本《贾长沙集》;或题《上疏陈政事》,见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夏炘题以《政事疏》。,并交待此疏的创作背景,云:“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1](P2230)此疏未见于《史记》有载,《文选》也未收录。因此篇属针砭时弊以提出政治见解的奏疏性质的政论文,不同于贾谊所创作的赋类作品及总结秦亡经验教训的名篇《过秦论》,故在文学史里的影响力有所不及(2)强调该篇的文学成就者,如刘勰《文心雕龙》评价贾谊奏议类的文篇创作,有“捷于议”(《议对篇》)、“议惬而赋清”(《才略篇》)诸称,“捷”和“惬”也可将此疏涵盖在内。另现代文学史家的评价,如林传甲称该疏“议论极伟”,“五千余言,痛切详尽,为古今敢言之士所宗”。参见《中国文学史》,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13页。鲁迅也称该篇:“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参见《汉文学史纲要》,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9页。。建国以来出版的几种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对此疏虽有所介绍,但并不侧重在它的文学成就,而是强调与《新书》的文本互见关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称:“贾谊有《陈政事疏》等一些奏议,还有一部《新书》。《新书》的一部分内容也见于《陈政事疏》等文里。”[2](P11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贾谊)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3](P135),且以小注的形式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称:“(《陈政事疏》)见《汉书》卷四十八。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3](P135)《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学术问题,但首先需要釐清班固所载《陈政事疏》的文本面貌。本文即以清人夏炘所撰《汉贾谊政事疏考补》(以下简称《考补》)为研读基础和出发点,针对该疏经班固史笔删节、改写及后人相继考补的诸多细节,尝试在细读疏文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何以删节”与“如何辑补”这样两个逻辑层面。同时也以《新书》、《大戴礼记》为参照对读了疏文中的各组成部分的内容,展现出它们之间存在的互见性文本关系及其复杂性,也藉此揭橥前人从事文献还原工作的学术方法。
一、班固对《陈政事疏》的删节与夏炘的考补见解
贾谊由任长沙王太傅而被文帝召回长安,旋即又拜为梁怀王太傅,本传云:“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1](P2230)颜师古注“数问以得失”云:“汉朝问以国家之事。”表明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的同时,又被文帝诏问政事,也必然有奏疏类文本呈进,班固也恰以载录该疏接续“数问得失”。据此推断《陈政事疏》的创作时间,最有可能是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奏进,时当在文帝七年(前173)。此疏也作为朝臣呈进的文书档案而藏于秘府,班固所依据者或即此秘府藏本(3)余建平认为:“班固所看到的贾谊奏议与《新书》中的贾谊奏议有不同的文献来源:一份为中央保留的文书档案,而另一份则是贾谊所留之草稿。”参见《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第32页。,不见得据自《新书》。班固又称:“(贾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1](P2265)“五十八篇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贾谊五十八篇”,班固所录《陈政事疏》即据自此秘府藏本“五十八篇”中的一篇,《四库全书总目》即认为:“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过秦论》《治安策》(即《陈政事疏》)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4](P771)而今传《新书》的文本肯定有来自此“五十八篇”者,但又并非“五十八篇”的原貌,而是文本经过了重新的组合,也不可避免地窜入非贾谊创作的文本。夏炘即认为:“《新书》虽非伪作,实隋唐间浅人掇拾改窜为之。”(参见《汉贾谊政事疏考补自叙》)而馆臣则明确称:“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4](P771)可以说比较客观地界定了《新书》的文本性质,也釐清了《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存在互见性文本的逻辑理据。故文学史家所称的班固截取拼接《新书》的相关文本而构成《陈政事疏》文本的观点,可能并不符合实际。
班固也并非照录疏文文本,而是对疏文进行了一番删节,根据是在本传中载录此疏时明确称以“其大略曰”(4)余嘉锡称:“夫曰大略,则原书固当更详于此矣。”参见《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1页。,另外本传末所称的“掇其切于世事者”亦可印证此点。按《陈政事疏》开篇云:“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删节前的全疏内容即围绕“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和“长太息者六”而展开,即它的组成内容是“一”“二”“六”,另加总撮篇旨的一部分,共计十个组成部分。针对作为疏文主体的九个组成部分,或称:“《治安策》的主要内容又分布在《新书·宗首》等各篇里,所以句中一、二、六不能一一指明。”[5](P27)或称:“这里所说的一、二、六等,和下文不相应,因为此文只是贾谊上疏陈政事的大略,有所删节。一说,六当作三。一、二、三是事情轻重缓急的次序。”[6](P215)理解全疏的文本组成,离不开与《新书》的对读;而对于班固的删节,自颜师古、真德秀到王应麟等有不同的看法,见解尤为卓荦者当推夏炘。夏炘不但一一指出疏文中的各部分起止,还概述各组成部分的旨意,同时明确指出班固的删节主要体现在“长太息者六”中,即删掉了“六”者中的其一即第四组成部分,而仅为“太息者五”。总体来看,班固的删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组成部分的删节,以及一些文句的删节,后者的目的是使载入本传里的疏文更简省,但并不影响组成部分的存在。至于班固删节的原因,夏炘《汉贾谊政事疏考补自叙》称:“作史者限于篇幅,不能不有删节,且所采既博,因以有误。”意思是说史传容量毕竟有限,不可能将疏文悉数录入。另外就是要平衡贾谊奏疏材料的使用,因为除本传外,《汉书》的《食货志》也录有贾谊的《论积贮疏》,只好做一些删节性的工作。由于此疏篇幅较长,班固在删节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或不应该删的组成部分的内容则删之(如“六太息”里的第四),或明确已删之的组成内容又通过改写的方式得以“还原”(如删掉“两流涕”其一,将所留存的一流涕改写为“两流涕”)。当然班固既称以“大略”,组成内容的删节似也属史笔的应有之义(5)余嘉锡认为:“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泛陈古义,不涉世事者,更无论也。”参见《四库提要辨证》,第541-542页。。但对于后人而言,界定清楚班固删节的具体内容和所做出的文本改写,并通过辑补的方式还原疏文的原貌,则需要加以考察。
自唐颜师古开始便注意到了此疏的删节问题,此后南宋的真德秀认为删节而致“长太息者六”阙一,并进行了辑补。王应麟则对“流涕者二”有所质疑,并补以《汉书·食货志》里的贾谊上疏(即《论积贮疏》)。清代姚鼐踵继此项工作,相较而言夏炘的辑补最为允当,被誉为“奄然如析符复合”[7](P1148),集中反映在他所撰的《考补》中(存世有清咸丰、同治间刻《景紫堂全书》本)。兹先对夏炘的生平仕履略作介绍,他出生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卒于同治十年(1871),字心伯,又字弢甫,安徽当涂人。道光五年(1825)中举,曾任武英殿校录,又任江苏吴江、安徽婺源教谕及颍州府学教授等职。为学专治经学,对义理、训诂、名物、小学和《说文》等均有精研,注重引申阐述程朱学说,并将书斋命名为“景紫堂”,以见对朱熹的尊崇,撰有《檀弓辨诬》《述朱质疑》等。生平事迹可参见《清史列传》卷六十七,以及《[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应该说,夏炘在前人的基础上围绕班固对贾谊《陈政事疏》的删节问题,又做了一番精深的研究,不仅明确指出疏文中存在的班固的删节之处,还对此删节进行了精准的考补,以复原疏文的原貌,更重要的是还归纳出班固删节致误的缘由,对如何开展作品文本的内部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夏炘的考补《陈政事疏》的见解,集中反映在所撰的《汉贾谊政事疏考补自叙》(以下凡“夏炘称”者均据此自叙)里,兹抄录全文如下:
汉贾长沙《政事疏》,《史记》不登一字,班《书》始著录于传,此孟坚之胜于子长者也。篇首提纲‘可为流涕者二’,今仅存其一。桐城姚姬传鼐谓后人因论匈奴有两流涕句,遂讹一为二,其说甚是。至‘可为长太息者六’,实阙其一。真西山《文章正宗》因《新书·等齐篇》有长太息句,遂取以补之。不知《新书》虽非伪作,实隋唐间浅人掇拾改窜为之。《铜布篇》亦有可为长太息句,何以置彼而取此?其不足据亦明矣。姚姬传又以为即《食货志》之《积贮疏》,不知《积贮疏》上于文帝之元二年。《志》前后文叙次甚明,非长沙召回时所上,较之真氏所补尤为臆断。案长沙此疏甚长,班《书》颇有删节,传中所谓‘其大略曰’可证也。今其全疏虽不可见,而《大戴记》《礼察》《保傅》两篇皆掇取此疏之文,《礼察》一篇即‘六太息’之第四段(实为‘六太息’中的第五者)。而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书》不载,今按其文义当有之。盖下文言‘定取舍,贵以礼’,故引孔子之言《礼》以发端,其为原疏无疑也。《保傅》一篇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以下凡一千八百九十二字,班《书》俱不载。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练也’以上皆论三太三少之职及王后胎教之法,与上文为一家眷属。自‘昔者禹以夏王’以下论任贤,则与不任贤则亡另为一意。班氏因教太子一段,文太烦冗,遂自‘此实务也’以下尽从删汰,而并误删任贤一段(小注:此段中有‘成王处襁褓之中’语,故班氏误认为论教太子而蝉联删之,大戴氏又误认为论保傅而蝉联取之),于是长沙此疏为不全矣。古人文字详简,各如其意而止,不似后人之必段落分明,长短如一也。故此疏六太息,短者才二三百字,长者乃两千字,正是汉人文法之妙。作史者限于篇幅,不能不有删节,且所采既博,因以有误,亦其势所必至。幸《大戴记》犹粗有梗概,得以考补其阙,使二千年来残破不全之巨制一旦复为故物,岂非快事?今合班《书》《大戴记》录之,字句多寡之间,择善而从,详注异同于下,并略疏栉其一二,难通之处以后世之治古文者取焉。道光甲午(1834)当涂夏炘。”
夏炘此序,针对《陈政事疏》主要列举了六个方面的意见:第一,疏文开篇中的“可为流涕者二”,就组成内容而言实则仅存其一。认可姚鼐“二”乃“一”之讹的判断,称“其说甚是”。第二,“为长太息者六”所阙之一,真德秀以《新书》里的《等齐篇》补之,不认可此见,并申述理由。第三,姚鼐以《汉书·食货志》里的《积贮疏》补之(王应麟则以此辑补“流涕者二”),亦不认可此见,并申述理由。第四,提出以《大戴礼记》里的《礼察》篇和《保傅》篇补之,并申述自己的理由,极具学术见地。第五,以此疏为例论汉人文法。第六,交待经“还原”之后的《陈政事疏》的文本面貌。该序很有学术含量,既涉及到学术史层面的《陈政事疏》考补工作,又“和盘托出”夏炘所从事的考补工作的方法论,还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还原”出新文本的《陈政事疏》,最后又谈及汉人创作的文法问题,体现了清人追求的义理、考据与辞章的近乎完美的学术融合。兹即以夏炘的考补为着眼点,既藉以充分认识班固史笔下的删节、改写和夏炘等人的文献辑补工作;同时也展开对《陈政事疏》全文的细读,特别是对读《新书》涉及到的相关篇章,以理解早期互见文本中存在的歧异性和复杂性。在对读的过程中,对于前人(如姚鼐等)有关疏文的考补所做出的诸种判断,也提出商榷性的意见。
二、 《陈政事疏》删节内容的考补及原貌拟定之上
《汉书》所录的《陈政事疏》(文字面貌依据中华书局整理本),对应到今本《新书》中则散见于各篇,呈现出被割裂的数篇形态。一种观点即四库馆臣认为疏文是原本《新书》五十八篇中的一篇。另一种观点是班固採摭《新书》相应各篇而隐括为疏文,意味着疏文属于班固刻意“制作”出来的文本,如王应麟即称:“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8](P1409)今学者余嘉锡也称:“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9](P542)也有观点称:“(《陈政事疏》)其实是贾谊的‘上奏集’,由班固删取归并而成的,因此与其文章原貌相去已远。”[10](P128)游国恩等编本《中国文学史》亦持此说。这些观点的共同取向,都是认为《陈政事疏》是班固从《新书》或贾谊的进呈材料中撷取相应文本组合而成。拙文依从馆臣之见,将此疏视为经班固删节而其原本为《新书》里的一篇,这里的《新书》指的是原本《新书》。也就是说,今传本《新书》反而将原为一篇的《陈政事疏》割裂为数篇,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按照馆臣“不全真”亦“不全伪”的界定,分散之后的诸篇可能保留着贾谊创作此疏的原貌。故在两者对读时采用了《新书》内相应各篇基本属原貌的假定,目的是揭橥班固对于《陈政事疏》文本删节及改写的细节。
今所见《陈政事疏》全疏共包括二十个自然段,分别用字母编序为“a”至“t”。据“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和“可为长太息者六”,及包括总撮篇旨的一部分在内,全疏应该原由共计十个组成部分。由于对班固删节理解的不同,今存疏文的组成部分之数存在差异。如颜师古云:“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汉书》注)依颜氏此说,则班固删节后存七个组成部分。王应麟则认为存“太息者四”[8](P1409),即班固删其二,如此则又为八个组成部分。而据夏炘的见解,则存九个组成部分,即“长太息者六”仅阙其一。如果再依据姚鼐“可为流涕者二”实为“一”的判断,夏炘也认可此说,则同样存八个组成部分,只是内容不同于王应麟之说。兹以全疏的各组成部分为基本单位,逐段细读全疏,将疏文的夏氏考补、前人诸说中存在的合理性及商榷之处,还有疏文与《新书》的互见性文本关系,一一详细揭橥如下。
第一组成部分即a和b两段,起“臣窃惟事势”句至“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句,夏炘称此部分的旨意是“论陈疏大指”。该组成部分与《新书》(依据《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长沙刊本)卷一《数宁》篇存在部分文句基本相同者,属文本互见。贾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概括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和“长太息者六”,他敏锐地看到汉初统治隐藏的政治危机,云:“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进而以“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对比,阐明治国之安危远逾“射猎之娱”的道理。同时提出三个“至”即“至孝”“至仁”和“至明”,劝谕文帝励精图治。《数宁》篇的文本在b段“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句下,有禹之下各五百岁而汤和武王分别“起”的叙述,反衬武王之后“圣王不起”,以此谏文帝要做“圣王”。又“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句下,有引晏子和髪子之语,述“万生遂茂”的道理。假定《数宁》篇保留着贾谊《新书》原著的内容,则班固或嫌其冗繁而删。但也有学者称:“文字上和《汉书·贾谊传》所载稍有不同,有些地方语言难解或不连贯,似多有讹误增窜处。”[5](P26-27)实际也不能够排除后人附益的可能性,显示出疏文与《新书》之间的文本复杂关系,王夫之即称:“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11](P159)
第二组成部分即第c至h段,即起“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句,至“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句,围绕“痛哭者一”而展开,夏炘称该部分“论诸侯强盛必反为痛哭之一”。其中c、d、e、g、h段分别与《新书》卷一《藩伤》篇、《宗首》篇、《藩强》篇、《大都》篇,f段与卷二《制不定》篇,存在部分文句基本相同者,似可视为《新书》的整理者据疏文割裂为上述诸篇,或又加以附益。该部分首先指出中央集权统治面临着诸侯国势力膨胀的威胁,但这些危机尚未显露出来,故表面上是“天下少安”。原因在于“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但等到“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而“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就是说诸侯势力危机一旦显露,汉廷便面临不可收拾的政治局面。接着指出同姓诸侯王与异姓诸侯王并无不同,都须加以防范,云:“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最后提出防范及化解同姓诸侯势力威胁的政治主张,称:“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要恩威并济,至于具体措施则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该措施实即后来武帝时所施行的“推恩令”,反映了贾谊超前的政治眼光和才干。该部分是全疏中字数较长者,充分体现贾谊的论辩艺术和汉人文法之妙。
第三、四组成部分即第i至j段,起“天下之势方倒悬”句,至“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句,围绕“两流涕”(即此两段各对应流涕者之一)而展开。大的背景是“匈奴强,侵边”,贾谊上疏建言如何处理汉廷与匈奴的关系,及化解匈奴对汉帝国政权的威胁。前人如颜师古对此为“流涕者二”无疑义,即视为两个组成部分。而王应麟则有不同意见,云:“至于流涕二,说其论足食劝农者是其一也,而固载之《食货志》,不以为流涕之说也。论制匈奴其实一事。凡有二篇,其一书以流涕,其一则否,是与前所谓足食劝农而为二也。固既去其一,则以为不足,故又分《解悬》《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8](P1409)至夏炘则引述姚鼐的意见称,“后人因论匈奴有两流涕句,遂讹一为二”,遂将此两段视为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两个以“流涕”为名目的组成部分,且称其旨意为“论匈奴嫚娒为流涕之一”。今检《古文辞类纂》,姚氏的确称:“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后论匈奴一事而叠出可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处增一为二。”[12](P141)按此两段中确实各存在一处“流涕者”,即“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德可远施……可为流涕者此也”。虽然是两处,但从所述内容而言确属一事,都是讲“天下之势方倒悬”。即汉天子与匈奴本为君臣关系,但实际情形却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且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也就是王应麟所说的“论制匈奴其实一事”,姚鼐同样据此作出“流涕者二”实为“一”的判断(6)曾国藩也称“实止匈奴一事”,参见《经史百家杂钞》上,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420页。。
姚鼐可能并不清楚王应麟之说,所以未提班固此处存在删节的问题。王应麟则不然,不但明确指出班固于此删其一,故离析“流涕者”之一的匈奴事而分为二,还尝试辑补所删之一以对应所谓的“两流涕”,以恢复原貌。王应麟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的《论积贮疏》补其一,当然也称班固不以此疏为“流涕之说”。检此疏,确未见到有“可为流涕者此也”的话,但所述隐然有与此“两流涕”相暗合之处。如疏云:“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背本而趋末”与“两流涕”里“天下之势方倒悬”叙述主旨相合。又疏云:“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此“边境有急”与“两流涕”论匈奴“嫚娒侵掠”相合。又疏云:“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怀敌附远”与“两流涕”里称“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亦相合。另外此疏与《新书》卷四里的《无蓄》篇存在文句基本相同者,而且该篇也是讲蓄积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属互见性文本。不妨将文句基本相同者举例如下(有差异者随文标出)。《无蓄》:“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饗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更为关键的是该疏末句为“陛下奈何不使吏计,所以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表明此《无蓄》篇与班固所删的“两流涕”之一存在着密切关系,而《无蓄》篇与《论积贮疏》所述内容又相同,由此判断王应麟补以《论积贮疏》是站得住脚的。当然王应麟如补以《无蓄》,似更贴切,因为此篇里同样有“流涕者”的表述。如此可理解班固删节的原因,正是缘于《食货志》也需要此部分内容,目的是避免两者的重出。这样针对“两流涕”之一的辑补,便存在着两个文本,即《论积贮疏》和《无蓄》篇,内容旨意相同,存在基本相同的文句,只是文句的表达序次不同。但何者属所删流涕者其一的原貌,很难做出判断。不过从《论积贮疏》未出现“流涕者”的话语,而是称以“窃为陛下惜之”,推测可能经过了班固之手的改写。当然还会有其它地方的改写,从它与《无蓄》篇的差异可窥一斑,从而弥合了文本剥离之后的矛盾。
经过上述推理,班固删掉了“两流涕”之一应可定谳。班固又将本为其一的“流涕者”易为二,其改写的手法是将本属一事的论匈奴嫚娒,离析为今所见的两段,并分别冠以“可为流涕者此也”。此两段的文句存在与《新书》卷三《威不信》篇相同者,不妨抄录此篇全文以与之对读: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且事势有甚逆者焉,其义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足下,是倒植之势也。天子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舟车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扪然数百里,而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威不信》篇所讲也是围绕天子与匈奴的尊卑关系而展开,内容旨意基本相同,可视为互见性文本。篇中划波浪线的句子,与“可为流涕者此也”第一里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以及“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足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人乎”,基本相同。划横线的句子,与“可为流涕者此也”第二里的“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基本相同。假定《威不信》篇反映贾谊奏疏的原貌,那么可以据此推定班固将本属一篇的“流涕者”离析为二。还可以看出班固改写的痕迹,如将“是倒植之势也。天子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直接简省为“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人乎”,的确更符合传体容量有限以简洁的要求。当然有些文句互不见于各自文本里,如该篇里的“古之正义”至“其义尤要”句,即不见于此“两流涕”里。而“两流涕”里的“今匈奴嫚娒侵掠”至“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句,也不见于此《威不信》篇。这又可印证,尽管整体而言属互见性文本,但文本的细节有差异,在缺乏更为原本面貌的文本可以验证的情况下,只能将之视为一种复杂性或歧异性的表现,或者视为有着不同的文献来源(7)余建平推测,“班固所见到的贾谊奏议是中央和秘府所保留的文书档案,而非《新书》”。参见《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第30页。。
三、 《陈政事疏》删节内容的考补及原貌拟定之下
《陈政事疏》里的“长太息者六”,对应的是经班固删节后的第k至第t段,起“今民卖僮者”,至“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句。其中出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字眼的仅有三处,分别出现在第k段、第m段和第t段。故颜师古认为“六太息”仅存其三,并以之与班固传赞所称的“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相印证。依此说则班固删其三,颜氏仅凭据“长太息者”诸字的有无,作为判断“六太息”的实际留存情况,是有待于商榷的。因为有可能班固只是删掉了“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所在的部分文句,而该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则还保留着。如第q段,起“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句,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句,虽不存在“长太息者”的字样,但所述旨意与此段前后均有别。此段是讲统治要施行仁政,用仁义礼乐治国,而不是法令刑罚。该段的前一段即p段讲的是谕教太子,后一段即r段讲的是朝廷大臣要“厉廉耻”,汉帝也要“行礼谊”,君臣和睦而不宜随欲逮系臣属。可见此段确实是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旨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即“六太息”之一(作为全疏的第九部分),只是经班固删节遂造成此文本面貌。
王应麟则认为“六太息”存其四,班固删其二,但并未明确指出此四者的各自起止。他称:“所谓太息之说也,固从而取之当矣。而其书又有《等齐》篇,论当时名分不正;《铜布》篇,论收铜铸钱,又皆其太息之说也。固乃略去《等齐》之篇不取,而以《铜布》之篇附于《食货志》。顾取《秦俗》《经制》二篇,其书不以为太息者则以为之。”[8](P1409)他的意思是说《新书》里的《等齐》《铜布》两篇皆有“太息”之语,而班固悉删而不取;而《秦俗》《经制》两篇无“太息”之语,却保留在了《陈政事疏》里。按《等齐》篇在《新书》卷一,该篇末句云“而此之不行,沐渎无界,可谓长太息者此也”。《铜布》篇在卷三,该篇末句云“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谓长太息,此其一也”。应该说王应麟注意到了《新书》与《陈政事疏》之间存在的互见性文本关系,并试图通过此种路径还原班固删节之前的疏文面貌,在他看来班固所删的两“太息”,即间接保存在《新书》的上述两篇文本里。但他同时也提到的《秦俗》《经制》两篇,则未见于《新书》,余嘉锡即云:“案今本《新书》及《玉海》所载之目录,皆无《秦俗》《经制》二篇之名。”[9](P543)检“秦俗”两字出现在《新书》卷三《时变》篇,该篇里的部分文句,恰与疏文里的第l至m段(起“商君遗仁义”句,至“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句),存在基本相同者,属互见性文本。如《时变》篇中自“商君违礼义,弃伦理”至“遂进取之业”句,即互见于疏文中第l段“商君遗礼义”至“遂进取之业”句,只是部分文字存在差异。“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句,则见于第m段中。假定该篇保留着贾谊创作的原貌,这些差异是班固在删节过程中加以改写的结果。如“弃伦理”改写为“弃仁恩”,“假父耰鉏杖篲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虑立讯语”改写为“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语”,更简省。同样又检“经制”两字出现在同卷《俗激》篇凡两处,而该篇与此两段同样属互见性文本,如“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壤败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句,即互见于第l段“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壤败,因恬而不知怪”句,经班固的删节或改写的确更为简练。由此推断,此两段的文本对应于《新书》里的《时变》和《俗激》两篇,而余嘉锡称“皆《俗激》一篇之文”(8)余嘉锡还认为疏文中的此两段,不过是“移易”该《俗激》篇的“前后”,只是在结尾“加长太息一句耳”。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543页。,稍显不妥。这两篇都未出现“太息”之语,与疏文里的两段以“可谓长太息者此也”结尾明显有别。王应麟可能是误混,以篇中的“秦俗”“经制”当作了篇题,也有可能所见《新书》之本即如此题篇名。
真德秀编《文章正宗》收录贾谊此疏,认为“六太息”阙其一,并在第k段前(即“今民卖僮者”句前)补以《等齐》篇,述其理由云:“按《新书》此下一节,天子之相号为丞相,诸侯之相号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千石……是臣主非有相临之分、尊卑之经也云云,此之不行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史削之。”(9)参见姚鼐《古文类纂》所引真德秀之语,载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夏炘不同意此说,理由是《铜布》篇亦有“长太息”句,何以不补此篇。按照夏炘的判断,“六太息”里的第一个“太息”对应第k段,起“今民卖僮者”,至“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句,旨意是“论奢侈无等为六太息之一”,即全疏第五组成部分。其中云:“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贵贱无等而致财力屈尽,故贾谊强调要有尊卑之差。而《等齐》篇强调的也是等级名分观念,云:“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乱且不息,滑曼无纪,天理则同,人事无别。然则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持面形而肤之耳。”推测删节前的此“太息”,也包含《等齐》篇的文本,可能是缘于其意叠加而删节。至于《铜布》篇讲的是朝廷要控制铜资源,而不可将此专营权下放民间,云:“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谓太长息,此其一也。”里面还特别提到“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矣。”这与“两流涕”里的论匈奴有相合之处,而且贾谊“退七福,而行博祸”的慨叹与“两流涕”开篇“天下之势方倒悬”亦相合。据文意推测《铜布》篇应属删节前“两流涕”里的文本,至于该篇出现的“太息”之语可能是经过《新书》编辑者改写的结果。依据是该篇作为互见性文本,也出现在了《汉书·食货志》,末句作“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可能这更为接近贾谊创作的原貌。由此分析来看,王应麟以此两篇来补“六太息”所阙之二,仅依据“太息”之语而并未深究文意是否契合,实则不宜据以来补班固的删节。
姚鼐也是认为“六太息”阙其一,而以《汉书·食货志》所载的贾谊《论积贮疏》补之,作为“六太息”里的最后一个“太息”,云:“长太息者六,文内阙一,西山先生引《新书》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补之。鼐谓《新书》者,未敢信以为真贾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坚必不删削之意。谓此一段为论积贮,即载于《食货志》者是已。”[12](P149)贾谊上此疏的背景,《食货志》云:“文帝即位,恭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1](P1127)结果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1](P1130)。按《汉书·文帝纪》云:“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1](P117)“其开藉田”之诏攽在文帝二年(前178),故一般认为贾谊上疏即在是年,如此便与贾谊的《陈政事疏》乃创作于召回长安之时相矛盾。姚鼐辨之,云:“《通鉴》因《食货志》有文帝感此开藉田躬耕语,而文帝二年有开藉田诏,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汉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几四十年’,必在长沙召回时也。”[12](P149)以此来弥合作年不合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将此《论积贮疏》作为班固删节的“六太息”之一,补入《陈政事疏》中。其实姚鼐并未明确交待该疏为“六太息”之一的理由,或许据自“窃为陛下惜之”句,以之等同于“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句。前文已指出《论积贮疏》与《新书》里的《无蓄》篇属互见性文本,就内容旨意而言更合于“两流涕”的文本,姚鼐所补恐非的当。故夏炘还是从作年不合的角度驳斥姚氏之补,称:“不知《积贮疏》上于文帝之元二年,《志》前后文叙次甚明,非长沙召回时所上,较之真氏所补尤为臆断。”
相较于上述诸家,夏炘的考补意见可描述为班固删掉“六太息”里的第四,同时在第三和第五有部分内容的删节,据《大戴礼记》里的《保傅》和《礼察》两篇予以辑补,应该说是最为恰切的。具体来说,他将第k段、第l至第m段分别视为“六太息”的第一和第二,即全疏的第五和第六组成部分,内容旨意是“论奢侈无等”和“论流俗败坏”。“六太息”的第三即第n至p段,起“夏为天子”至“此时务也”,即全疏第七组成部分。同时认为该部分班固有删节,应据《大戴礼记》卷三中的《保傅》篇而补之。按《保傅》篇(文字面貌依据清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里的起“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至“此时务也”句,恰与第n至p段属互见性文本,当然存在着异文。夏炘《考补》跋称:“大戴氏生于西汉孝宣之世,去贾子不远,故《保傅》篇自‘殷为天子’至‘此时务也’,与班《书》次第不紊。”按《汉书·昭帝纪》云:“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1](P223)颜注引文颖语云:“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故知《大戴礼记》里的《保傅》篇文本乃据自贾谊,而且保留了创作的原貌,以此来补“六太息”里的班固删节可谓若合符契(10)刘台拱《汉学拾遗》认为:“谊陈治安之策,与其《保傅传》本各为一书(余嘉锡称当作‘各自为篇’),班氏合之,而颇有所删削。”参见《四库提要辨证》,第543页。文颖为东汉建安时人,据其注知当时《贾子书》传本无题《保傅》篇者,而其文本则与今所见《陈政事疏》同载于该书的某一篇内,今《新书》所载该篇截取部分文句而非其原貌。班固据之有删节,戴德则据原篇抄录,且题以“保傅传”。据昭帝诏语,知由于戴德的“抄撰”行为,使得《保傅》篇独立单行,且具有与《孝经》《论语》和《尚书》相等同的地位。。该篇里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至“犹此观之,王左右不可不练也”句,夏炘跋称:“自‘天子不明先生王之德’以下,班《书》虽不载,其为当日次第无疑。”该部分文句紧接疏文第p段末句“此时务也”之后,两部分相合均是讲“论保傅之法”,夏炘称:“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练也’以上皆论三太三少之职及王后胎教之法,与上文为一家眷属。”正可构成完整的“六太息”里的第三,间接印证此部分正是班固所删节者。
夏炘又据《保傅》篇里的起“昔者禹以夏王”,至篇末“其不失可知也”句,作为“六太息”的第四,也就是全疏的第八组成部分,其旨意是“论任贤则兴,不任贤则亡”。该组成部分,经过了班固的全部删节,也就是夏炘所称的“六太息”阙第四。这意味着《大戴礼记》里的《保傅》篇,可以釐分为旨意不同的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对应“六太息”第三,另一部分则是“六太息”第四的全部。从篇题而言,《保傅》篇讲的是如何教育培养太子,很明显自“昔者禹以夏王”句至篇末,则偏离了该主旨,成为游离在主旨之外的文本。这表明戴德在据贾谊《保傅》编入《礼记》时,误读性地糅合了该篇相接连的文本,而没有做出区分。夏炘即称:“自‘昔者禹以夏王’以下论任贤则兴,不任贤则亡,另为一意。”更为精彩的是,夏炘又据此得出班固何以全部删去“六太息”第四,戴德何以会出现误取文本。他说:“班氏因教太子一段文太烦冗,遂自‘此时务也’以下尽从删汰,而并误删任贤一段(夏氏自注:此段中有‘成王处襁褓之中’语,故班氏误认为论教太子而蝉联删之。大戴氏又误以为论保傅而蝉联取之),于是长沙此疏为不全矣。”第q段起“凡人之智”,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句,夏炘又据《大戴礼记》卷二之《礼察》篇起“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至“而倍死忘生之徒众矣”句补在该段之前,两者相合作为“六太息”第五,即全疏的第九组成部分,旨意是“论人主当用仁义礼乐,不当用法令刑罚”。《礼察》篇起“凡人之知”,至篇末“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句,恰与此q段属互见性文本(同样存在着异文),只是多了所补的这一段,印证这也正是班固删节的一段。夏炘以此段作补的理由,云:“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书》不载,今按其文义当有之。盖下文言定取舍贵以礼,故引孔子之言礼以发端,其为原疏无疑也。”第r至第t段,起“人主之尊譬如堂”,至“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句,为“六太息”第六,亦即全疏的最后一部分第十组成部分,旨意是“论大臣不可逮系”。其中第t段里起“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句至篇末,与《新书》卷二《阶级》篇属互见性文本,班固做了部分的改写,如“刑不至君子”,“君子”改写为“大夫”等。附带说明的是,经夏炘考补之后的“六太息”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均未出现“太息”之语(11)《大戴礼记》里的《礼察》和《保傅》两篇,应该是最为接近贾谊创作原貌的文本,亦不存在“太息”之语,推测可能是戴德删去,目的是更适合作为《礼记》学习参考文献的功能。,是依据文意的各自独立性作出上述判断。另外以《礼察》《保傅》两篇文本与班固删节后的疏文对读,可以通过两者之间的差异看出改写的痕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陈政事疏》考补所体现的方法论意义
夏炘的考补工作,得到了当时学者的首肯,此可通过书中首末所载序跋窥见一斑。如程烈光《政事疏考补叙》称:“先生勤于治经,读书尤善觅间。一日论及贾长沙《政事疏》遗失不全,昔真西山曾以《新书·等齐篇》补之,近姚太史每以《食货志》之《积贮疏》补之,似均未当。惟以《大戴记》参之班史,斯能吻合……《保傅篇》后半文字考其辞义,于《保傅》颇不类,于此疏若相贯,断其为‘六太息’之缺,绝无所疑。余唯唯久之。”又道光二十四年(1844)韩菼跋称:“真西山、姚姬传非卤莽灭裂者,取《等齐篇》失之简陋,取《食货志》失之牵强。当是时,不自觉,人亦不之觉,得兹善本,立见妍媸矣。而其明眼细心,尤在自序中谓班氏读‘成王襁褓’句误以为教太子而删之,戴氏又误以为保傅而取之。能替古人设想,安见古今人不相及耶?”又道光十九年(1839)顾志熙跋称:“向读班史长沙《政事疏》,于六太息之说寻绎再三,不得其数。及见真西山《文章正宗》、近桐城姚姬传《古文辞类钞》,以《新书》之《等齐篇》、《食货志》之《积贮疏》即谓长太息之一,又觉附会牵强。今得于《大戴记》中掇拾缀补,不惟根据的确,文气亦殊相类,其为班氏删汰无疑。”
《陈政事疏》确实经过了班固的删节,就“六太息”部分而言,据删节后的内容所表达的旨意断定阙其一(即第四)。真德秀尝试以《新书》中的《等齐》篇作补,这就牵涉到《陈政事疏》与《新书》之间的文本关系。尽管韩菼跋称其“简陋”,但真德秀敏锐地注意到了疏文与《新书》所存在的文本互见现象。由于《等齐》篇也是以“可谓长太息者此也”句结束,使得真德秀认定此篇即为班固删节的“六太息”之一,文本互见的标志便是相同词汇“太息”的共享。通过互见性文本以辑补删节的疏文是可行的路径,但同时也要放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它是否具备恰当性,实际就是在文献考据与作品理解(辞章)两方面取得平衡。否则,照此而失彼,都不能算作是合格的文献考补,更遑论原貌之还原。事实证明,《等齐》篇的文意已经反映在“六太息”第一里,因此它只可能视为班固删节的部分文本,而不宜作为经班固删节的“六太息”之一。也就是在作品理解层面出现了“不合”,故姚鼐和夏炘都不接受真德秀的考补意见。姚鼐又以《汉书·食货志》中的《论积贮疏》作补,韩菼及顾志熙两人的跋都称之为“牵强”,其学理性还不及真德秀的考补。原因在于姚鼐没有在整体把握全疏所述旨意的前提下,便生硬地去进行考补。他更未注意到此《论积贮疏》与《新书》里的《无蓄》篇属互见性文本,都是讲积贮乃天下大本,而且在文意上更适合疏文中的“两流涕”部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应麟以《论积贮疏》补作班固删节的“两流涕”之一,便照顾到了文献考据与作品理解两者的统一。其实,从真德秀、王应麟到姚鼐的考补存在一个共同的文献取径,即都是从贾谊创作的文本中去寻找线索。不妨将《陈政事疏》视为“中心性”文本,而围绕在它周边的如载于《食货志》的《论积贮疏》以及《新书》相应各篇则属于“相邻性”文本,两种文本之间存在着互见性的关系,诸如共享标志性的词汇、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句以及大致相同的旨意表达等。但这些文本均系在著作者贾谊的“圈子”里,上述诸人的考补并未脱离这个“文本圈”,故也很难获得切实而有效的突破口。
夏炘的考补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究其根本就在于跳脱了贾谊创作的“文本圈”,而是从形式上与之完全不相邻的文本中去获得突破口。表现就是夏炘据《大戴礼记》作补,《大戴礼记》可以说与贾谊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只是他敏锐地注意到该书收录的《保傅》篇与疏文存在着高度的文本互见性。尽管该篇里的文本仍出自贾谊之手,但篇题毕竟未题以“贾谊”,而且《大戴礼记》属经部典籍,不同于子部属性的贾谊《新书》。这意味着读书宜摒弃四部的藩篱,而且还要具备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否则很难像夏炘那样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程烈光序称夏炘读书“善觅间”,可谓再贴切不过。不惟在文献考据层面,夏炘恰如其分地找到辑补“六太息”所阙之一,以及其它各“太息”里班固删节的部分文句来源;而且在作品理解层面,与既有疏文上下文的文意亦贯然相通,还分析出班固及戴德各自在文本操作中致误的原因,确实令人信服。此即顾跋所称的“不惟根据的确,文气亦殊相类”,“自非好学深思,覃精古籍,曷克于千载后确见如是”。
夏炘考补的方法论意义,首先是读书不应有部类之分,博涉群籍或许能够发现极有价值的隐秘学术关联;其次是读书要善于得间,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最后是从事文本内部的考据性工作,要与义理和辞章融合起来,也就是程烈光序所称的“始则羡其缀辑甚工,渐惊其笔状都有,终并喜其神理融合”。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相辅相承是读书治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夏炘围绕《陈政事疏》班固删节所进行的文献考补工作,为我们理解这种境界提供了典型的学术个案,也是笔者从揭示夏炘此作的层面而撰为该文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