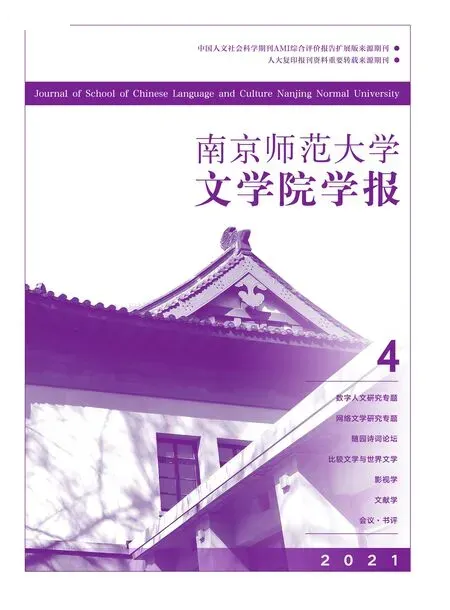唐人制诰文本编纂及编次观
——从制诰文本到制诰专集
2022-01-14王冰慧
王冰慧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0)
从文本生成到文本收录,再到文本编纂。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事物主要是两个:一是文本文字,一是文本载体。就制诰(1)本文所讨论的“制诰”采用广义上的制诰内涵。制诰,指称以君主名义发布的各类官文书,包括制书、册书、批答、敕文、手诏等。文本而言,变化背后逻辑与编次观念息息相关。具体表现有二:一是文本编纂的可能性与制诰性质、归属有关。唐初,发表权、署名权归属于君主,修改权分属于撰写者(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等)、门下省、中书省、君主等个体。而后权利变动间接影响了制诰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影响其编纂情况。二是编次具体情况与制诰功用有关。制诰原先属于史部,而后被允许编纂入文人集子。而由于制诰文本的功能性定位,其编次情况又不完全同于诗歌文本编次情况。这之间的制诰归属、具体编次等问题,都值得我们一探。
目前,关于唐代制诰文本编次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唐代文集(含制诰)的整理与介绍、后人对唐代制诰编纂情况的研究。(2)陈尚君《〈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超《唐代诏敕文献留存情况述论》(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期),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节“通代文集、诗文合集与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朱红霞《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09月)对唐代制诰编纂情况的问题有所涉及,如制诰专集的整理与研究。此类研究有所局限,或涉及到了唐人制诰编纂情况,却未能展现唐人制诰编纂全貌;或对于唐人制诰编纂背后动因未作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以唐代作为研究时限(3)文章以唐五代为时间限定范畴,这主要是基于《旧唐书》《新唐书》《崇文总目》《通志》等涉及到的总集、别集编纂的时间问题。第一类是有明确的著者、编者与作序者,可确定其于唐代编著的文集,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元稹《元氏长庆集》等;第二类在《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中有记载且在《唐书》传记中有相关记录,基本可确定为唐代编辑的文集,如《新唐书·艺文志》载“《来济集》三十卷”,《旧唐书》记有“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代”;《新唐书·艺文志》载“《李义府集》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载“《李义府集》三十九卷”,《旧唐书·李义府传》记有“文集三十卷,传于代”。第三类在《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中有记载且在《唐书》传记中有相关记录,但未言“行于代”,其成于唐代的可信度较前两类较低,如《旧唐书·经籍志》载“《李峤集》三十卷”、《新唐书·经籍志》载“《李峤集》五十卷”,《旧唐书·李峤传》记有“有文集五十卷”。第四类即仅有《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并无其他佐证记录,笔者则根据《唐书》的成书时间更为妥帖的将其时间范畴规定在唐五代之内。实际上,考虑到《唐书》成书的资料来源、唐人文集编次的习惯、五代的社会情况等,《唐书》中文集应多出于唐人之手。,探究唐人制诰文本编纂情况,以期窥视唐人制诰编次的背后逻辑。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并行展开研究:一方面以时间为线索,厘清制诰性质、归属问题,进而明晰制诰文本编纂的可能性、可行性;另一方面,以文本载体为切入点,厘清制诰文本具体编纂情况,进而了解其编次观。
一、唐初制诰存在模式与编纂基础:“君命文书”与文人属性
存在模式是指文本的存续状态,包括文本载体、文本归属等。然而文本载体、文本归属属于一个问题的两面,文本归属影响文本载体,文本载体又确认文本归属。故而,唐书制诰文本的归属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后,才能够进一步地探索编纂的情况。
(一)“君命文书”之渊源与继承
唐初制诰署名权多归属于君主。该模式的存在自有渊源。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制诰多系于君主名下(不排除个别特例)。据《文章辨体序说》载:“历代制册诏诰,盖皆王言。《文选》《文章正宗》止书世代而已;至《文鉴》《文类》始列代言名氏。今依前例,悉皆不书。若夫天朝诏诰,岂敢与臣庶文辞同录?今亦弗载。”[1](P10)也就是说,《文选》、(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皆未及撰写者姓名;(宋)吕祖谦《文鉴》、(元)苏天爵《文类》等总集中始言及代言者之名。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制诰归属并未完全掩盖实际撰写者之名,但至少至宋代,人们对于制诰归属判断更多是基于制诰的王言性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诰与其归属的情况,但部分细节仍需细辨。例如唐前制诰署名情况已多样化。
具言之,唐前制诰与署名情况存在三种情况。其一,以君主单独署名为主要存在方式。这种不具名实际制诰撰写者的制诰文本占比最大,且内容指涉甚广,涉及到礼仪、爵位、祥瑞、赦文等。例如始皇帝《除谥法制》(录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汉高祖《立吴芮为长沙王诏》(录于《汉书·高纪》),永光二年(BC42)六月汉元帝《赦诏》(录于《汉书·元纪》)等,元康元年(293)三月汉宣帝《凤皇集甘露降诏》(录于《汉书·宣纪》)都是以君主名义存在的制诰。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该类制诰的文本载体多为史部典籍。其二,唐前存在少数个人署名的制诰,如侯霸《立春下宽大诏》(录于《续汉·礼仪志上》)。又沈约《授蔡法度廷尉制》(录于《文苑英华》三百九十七)等。该类制诰的文本载体为史部典籍、宋之集部类书等。其三,君主与文人共同署名制诰文本也是存在方式之一。例如孝静帝、魏收《伐元种和诏》,梁武帝、沈约《立皇太子大赦诏》等。共同署名的文本载体为许敬宗《文馆词林》。而在“文馆词林”中,相较于前两类,第三种署名情况的占比介于前两者之间。
值得注意的的是,第二、三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类的,即署名权归属偏向于君主。例如“东晋安帝征刘毅诏一首”,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无署名,一般将其记于晋安帝名下,而《文馆词林》署名为傅亮。可见,当时及制诰编纂者即使知道真实作者,也未必将其归于撰写者名下。
结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几点:第一,君主亲笔、臣子代笔等两种情况间并非泾渭分明,多数制诰并非天然意义上即与实际撰写者相联系。即使不少制诰能考证(或说知晓)出真正撰写者,但其名义还是记于君主名下。第二,制诰的文人性已经产生。我们可以看到,《后汉·侯霸传》:“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结合《文馆词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发现,制诰撰写者之名不外乎以下几人,如张华(232-300)、傅亮(373-426)、沈约(441-513)、王俭(452-489)、徐孝嗣(453-499)、任昉(460-508)、温子昇(495-547)、魏收(506-572)、阳休之(509-582)、李德林(530-590)、江总(519-594)等。而这些人多为有文之士,自能为君而作制诰。换言之,尽管大多归名于君主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撰写者的不存在。第三,唐前制诰文本在唐前记录中多属于史部,而其在集子出现撰写者之名多为唐后的文本载体。简言之,此时制诰的文人性仍未达到可以使制诰文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故而只是酝酿了制诰文本编纂的可能性。
(二)制诰之文人属性的增加
不管是文本归属,还是文本载体,唐初制诰存在模式即承此而来。根据《全唐文》记录,唐代各君主名下皆有不少制诰文书,包括册文、赦文、德音、授官制等。例如武德元年(618)五月,唐高祖李渊即位。此时的《即位告天册文》[2](P30)记录于《大唐创业起居注》。《大唐创业起居注》属于史部范畴。这说明此时制诰文人性的认可度较低,而更多归属于官方历史文本。至于此时文本载体,“诏令奏议”多属于史部。除了上文提到实录,制诰文本载体还包括以下二类:一是在任时的宣底。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曰:“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3](P7458)苏颋制诰来源则是由此集结而成。二是个人留底的文本。唐前期,此类一般不作为流传的文本。根据《新唐书·陆元方》:“有一柙,生平所缄钥者,殁后,家人发之,乃前后诏敕。”各类群体对制诰文本的署名与传播都是采取相对谨恪的态度。故而,以上三类虽为后世制诰编纂提供了材料,但唐初制诰流通还是相对限制的。
最为不同的是帝王别集的出现。这为后世个人别集(含制诰)提供了前例。李世民有个人别集。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4](P2052)。又据《直斋书录解题》载:“《唐太宗集》三卷。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馆阁书目》但有诗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赋四篇、诗六十五首,后二卷为碑铭、书诏之属,而讹谬颇多。”[5](P466)此处文集编次已不可见,但至少可以看到“书诏”归于君主名下的这条信息。同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垂拱集》一百卷。虽该文集亦于五代之后亡佚,无可复见。然而,结合《全唐文》可见,实际上系于武后名下的制诰亦不在少数。又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其作多臣下代笔。此亦间接说明了武则天《垂拱集》极可能有臣下代笔之作(包括制诰)。
可见,实录、帝王别集、宣底、个人存稿等,在唐初皆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其存在更多是基于政治意义。此时制诰作为权力场重要产物,其与作为实际撰写者关系并未显性地呈现。
然而,帝王别集毕竟是制诰编纂可能性的一个重要信号。在唐代“文化天下”的氛围下,制诰与实际撰写者联系的显性化也指日可待。那么两者是如何逐渐产生联系的呢?答案就是制诰代笔情况逐渐增多、制诰文人属性的凸显。
从唐初至晚唐,制诰的归属问题有一个转变过程。若将《全唐文》记于君主名下制诰数量与此时有个人署名之制诰数量进行对比,发现唐前期两者差距巨大,唐后期则不然。而这之间,个人署名之制诰也从个别案例成为社会常态。唐代较早出现个人署名之公文本,主要是以下三大类:其一,册文。贞观四年(630),岑文本为中书舍人,有《册韩王元嘉文》《册彭王元则文》《册越王泰改封魏王文》《册郯王恽改封蒋王文》《册许王元祥改封江王文》《册赵王孝恭改封河间郡王文》等。其二,诏文。许敬宗于贞观九年(635)至贞观十年(636)为中书舍人,有《举贤良诏》。其三,制文。李峤于长寿元(692)年至约圣历二年(699)中书舍人在任,其现存制诰多为授官制。就《全唐文》记录而言,其数目已达四十四条。又李迥秀约神功元年(697)至大足元年(701)为中书舍人,作有《授何彦则侍御史制》。
可见此时已有不少个人署名之制诰。而这种情况得以出现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制诰的文学性特点逐渐凸显。但是这个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撰写者个人的水平,存在一定偶然性。二是制诰的文人作用力显性化。这与制度、撰写群体密不可分。我们可从册文入手,窥其端倪。册文虽属于《新唐书》所涉制诰种类之一,但是撰写册文活动并不是专属于某官(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等)的职能性创作。换言之,册文尽管属于王言之一类,但撰写册文并不属于此类官员专属(即排他性)职能。其他得到君主认可的官员们亦有资格撰写册文。例如严绶《文武孝德皇帝册文》,此时严绶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少保上柱国公食邑三千户。这使得册文可脱离于某官的固定职能而存在。于是乎,“文人——职能——文本”的关系链缩短为“文人——文本”,进一步强调了制诰与撰写者的联系。其他制诰虽属于职能创作,但其“文人——职能——文本”中的“职能”要素渐隐,而“文人”要素渐显。故而制诰归属随之改变。这是后来个人制诰集诞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综上,唐初制诰是唐前制诰情况(制诰系于君名)的一种延续,往往会有意识地忽略真正撰写者。此情况与制诰性质密切相关。第一,制诰地位高于普通文本,其属于政治属性的言论。正如上文提到的“若夫天朝诏诰,岂敢与臣庶文辞同录”。我们可以看到制诰作为文本超出一般文本的特殊地位。故而,制诰文本在编纂中,一度属史部。第二,制诰作为“君命文书”,制诰文本具有公共属性。在绝大多数初唐人认知中,制诰文本没有独立于君主存在的根基。因此,制诰文本多收录于实录、宣底、个人存稿、帝王别集之中。比较特别的是,帝王别集的出现,使得原本属于史部类制诰出现到了个人别集之中。
此时,制诰撰写者的文人性虽尚未成为主导因素,但也持续发挥着作用力。我们都知道,制诰撰写动机源于君主,制诰撰写者以君主立场去撰写,以君主思想组织文笔。故而制诰文本生成过程中,制诰执笔者(尤其文笔普通之人)是一直存在的。从唐初至唐末,个人署名制诰不断增多。这为之后个人制诰专集、个人别集(含制诰)的出现提供基础。
二、唐后期个人制诰集与编次逻辑:文学性与应用性
制诰文本之文人性是制诰文本得以独立的重要因子。之所以称文人性,而不称文学性,主要强调的是制诰文本生成中的文人作用力。这既不否认制诰文学性的增加,但不排斥制诰本身的应用性。这些性质将会影响具体编次情况。
自帝王别集之后,个人别集(含制诰)相继出现。完成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苏颋之事。据《新唐书·苏颋传》载:“帝(中宗)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此处“别录副本”,当指就“诏令”而编纂的制诰集合。而“帝(中宗)爱其文”则是对其制诰符合各方审美(文学性与应用性)的肯定。这种君主认可亦为后来制集编纂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此制诰文本集合指定读者为君主,不能等同于完整意义的文集。后来,苏颋有了个人文集。《苏颋文集》由韩休作序,其序文提到“诏公撰《朝觐坛颂》”,“则翰动若飞,思如泉涌,典谟作制於邦国,书奏便蕃於禁省,敏以应用”[2](P3323)。此处提到了颂、制、奏等不同文体,可见苏颋通行文集中包括制诰及其他文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别集(含制诰)。这也是后来个人别集的一种常态。
(一)个人别集编纂的限制与常规
自苏颋开个人制诰集编撰之先声。随后,其他个人别集(4)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是制诰的主要撰写主体,本文以此二者为主要分析对象。根据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宁:辽海出版社出版,2005年)、《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辽宁:辽海出版社出版,2007年)、刘万川《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提供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名录,笔者结合新出土墓志及其他典籍材料,统计到翰林学士226人,中书舍人410人,有别集70人。再结合《唐书》统计到:有制诰专集21人,别集明确含制诰文本的5人。另外,由于中书舍人基数较大,因此总体上来看著者身份多为中书舍人。但纵观全唐制诰集,唐后期著者为翰林学士的情况稍有增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之间的动态关系。亦逐渐出现将制诰纳入文集的情况。个人别集的出现,说明了制诰与实际撰写者的关系已更为紧密。具体如下:

表1:唐人别集(含制诰)名称及相关情况
就目前文集统计情况来看,个人别集(含制诰)数量并不多。据《全唐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他人名下虽有制诰文本,却无法确定这些文本状态,即于唐代已编入个人别集,或还是在处于散落状态。对此,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再除去《太宗集》《垂拱集》《玄宗集》等帝王别集的特殊情况,目前确定含有制诰的别集主要是上表六种。其中《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有版本可依、且收录有较多制诰文本,故可作为重要分析事例。
编纂是指按照一定的题目、体例和方法编辑文本的活动。它有相对常用的编纂体例、编次原则等。制诰文本作为官文书,有文本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个人文集(含制诰)编纂有同于普通文集编纂之处,亦有其独特之处。正如上文所说,制诰文本生成中,文人作用力存在使得制诰应用性与文学性是共存的。这在编纂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一方面,制诰文本编纂服从政治性安排,其具体体现为编纂活动中的诸多限制,如编纂者人选、编纂风格、可被编纂的文本、可以编纂的时间等。首先,撰写主体之局限导致制诰编纂者人选的局限,兼之制诰面向群体相对有限导致其接受群体有限。由编纂者至编纂对象,此奠定了编纂文本的基调。一般情况下,该编纂文本以合理公平、典雅博正为尚。其次,制诰文本要经过文书生成程序,才有被编纂的可能。这要经过多方审查。一是中书门下省、君主(包括储君)。众所周知,唐代制书和敕旨还保留宣奉行程序[6](P128),如中书“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门下“大事覆奏,小事则署而颁之”,皇太子“凡皇太子监国,于宫内下令书,太子亲画日”(《唐六典》)[7](P670)。这属于程序规定。二是受众期待。从韩愈《平淮西碑》被推倒、段文昌之重写便可看出端倪。碑文尚且要符合受众期待,何况制诰?这属于额外要求。只有确定公布的、修改至可行的制诰文本才是可被编纂的文本。再者,制诰公布时间须服从安排。那么,编纂时间也是有所限制。据《唐六典》载:“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7](P275)。可见,编纂时间必后于公布时间。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制诰编纂才得以实施。
另一方面,尽管制诰编纂相较其他文本编纂具有更多限制性。然而,这种限制在具体编次之中并未加以太多发挥,其往往参见普通文本的通用编纂情况、编次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在编纂过程中,尽管制诰文本应用性强、政治地位高,但其却未必占据中心地位。以体编次是中唐到北宋颇受欢迎的编集方式[8]。个人别集(含制诰)也不例外。例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9](P7738)根据白居易《长庆集后序》记载:“每秩十卷,讫长庆二年冬,号《白氏长庆集》。迩来复有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以类相附,合为卷轴,又从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10](P1396)结合现存《白氏长庆集》(5)判断别集是否有唐时面貌,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唐写本与传世本;目录学的卷数对比。参见项鸿强:《唐人诗体编次观与自编文集之关系》,《文学遗产》2020年03期。笔者以为尽管《白氏长庆集》在唐代的原貌难以窥见,但从各本目录相同之处亦可初探唐本之端倪。来看,不管是元稹先编纂的前五十卷,还是白居易自编的后若干卷,其都是遵循先诗歌而后制诰的顺序。无独有偶,其他文集也是如此。例如裴延翰《樊川文集后序》:“得诗、赋、传、录、论、辨、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11](P1)此处分列“格诗、律诗、碑、志、序、记、表、赞”等各类文体,可见,一般情况下,文集采用文本编次顺序是从文学性至应用性。
就制诰内部编次而言,《白氏长庆集》编纂较为规范,亦符合唐时编纂之风,可作为个人文集(含制诰)的重要参考。他人较之白居易,编次层次则相对简单,如元稹。白居易之制诰编次样貌大致呈现若干情况:(1)制诰与其他文体同属于一卷。具体编次卷目“试策问制诰”,然后采取“以类分类”方式又依次分为试策、试制等;(2)制诰单独列为一卷。具体编次卷目“翰林制诏”,然后采取“以类分类”方式又依次分为制(混有拟制)、批答、祭文、诏、批答、祭文、诏、批答、诏、批答、诏等;“卷目为“中书制诰(旧体)”然后采取“以类分类”方式又依次分为制、册文、制等;卷目“中书制诰(新体)”,然后采取“以类分类”方式又依次分为册文、制、祭文、制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卷目未必属于清一色的制诰,而同一卷目之下,制与制文本之间可能有其他文本的插入。此种情况多次出现,不可能仅仅是出于编纂者的疏忽,更可能是编纂者出于便利而未尝深究的心态。但总体上,白居易文集的编次还是极有规律的。该文集对制诰的一级分类是“以体编次”(将制诰与诗赋等分卷编次),二级分类是“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诏”。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于“中书制诰”部分区分了“新体”“旧体”,这在其他制诰集、个人别集(含制诰)中都未曾出现。三级分类是在“以体编次”的模式下,进一步采取了“以类编次”,即文章的册文、授官制等放在相近位置。
之所以文本会呈现出这样的编次面貌,主要是因为制诰编纂更多服从于文本本身的编次规则。至于制诰编排位置为何后于诗歌?原因有二。首先,《文选》“以体分类”影响深远,是后世重要的编次原则。《文选》所收七百余篇作品按赋、诗、文三大文类编排,每大文类之中再划分为若干次文类。《文选》共有七十六种次文类。《文选》有二十二种次文类每类仅收录一位作家的作品,因此,它们不存在次文类的编序问题。例如文类的“诏”“册”“令”“教”“启”“奏记”“难”“对问”“连珠”“箴”“墓志”与“行状”。《文选》有三十一种次文类,所收作家无论从生年考察,或者从卒年考察,均符合时代先后的顺序。其余为含有乱序的次文类。[12](P39-40)个人别集(含制诰)就是如此编次原则的继承。其次,文本本身性质导致编次顺序的原则。诗歌传播的可流动性、使用群体的广泛性、传播对象的多样性、使用范围的广域性等,导致了其诗歌类文体排列的优先性。我们此处可以类比唐人行卷编次的想法。唐朝是“诗”的国度,从以诗赋取士中可看出对诗的重视,故而文集往往将相应地将“诗”列于首位。又“制诰”入别集相对晚出,加之其文本性质偏于应用性,自然列在后面了。
然而,制诰终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文本。因此,在制诰内部编次过程中,文人还是做了不少新探索。比较特别的是《白氏长庆集》中“新体”“旧体”等名词的出现。这是极具时代性的特征,与长庆制诰改革密不可分。又二级分类按照职能所在分“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诏”。这从侧面说明翰林学士取得了部分草诏权。此时“内制”与“外制”之说虽不能将两者职能完全区分,但亦代表了两者的草诏内容上的一些区别。这种分类在宋《文苑英华》中得到继承与发展。而分类意识产生的本身则代表了编纂者对制诰文本的重视。
简言之,制诰文人性的加强促成了个人别集(含制诰)的产生。而在编纂过程中,制诰是王言,先强调是政治属性,其次才会提及文学属性。因此,编纂准备工作有所限制。但在具体编次过程中,制诰文本编次更多服从于文本本身的编次原则。比较特别的是,在编纂过程,文集有基于社会变革的“新体”“旧体”之分,基于职能的“翰林制诏”与“中书制诰”之分,前者很好地反映了制诰的文人性,后者凸显了制诰的应用性。
(二)制诰专集编纂的分类与专门化
制诰专集是以编纂制诰为主的文集。相较于个人别集(含制诰),制诰专集最大特征是其专门化。以情理度之,制诰专集类似于个人别集制诰部分的独立版,其出现应后于个人别集(含制诰)。实际上,八世纪开始,制诰专集出现的情况逐渐增多。根据《旧唐书》:“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之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4](P3977)高郢中书舍人在任时间为贞元八年(792)至贞元十六年(800),可推想除了在高郢之前任职的常衮、杨炎、陆贽等人(据《新唐书》已知存制集),其他人亦会留存制集。可见,个人别集(含制诰)与个人制诰专集的出现时间差距不大。两者都与苏颋之事脱不开关系。这可能与制诰文本在编纂过程中相对独立有关。故而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其与个人别集亦存在不少共同点。例如制诰编纂的限制性就与个人别集相类。故此不赘述。
然而,作为个人别集制诰部分延伸版的制诰专集,其在制诰文本有时反而不如个人别集。也就是说,制诰专集本以制诰为主,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玉海》《通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中,此处文集条目(6)制诰专集是制诰编纂的重要方式,以《新唐书》为中心,结合陈尚君《〈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卢燕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拾掇出21人的制诰集。以下,笔者按时间顺序展开罗列。具体如下:常衮《诏集》六十卷、杨炎《制集》十卷、陆贽《翰苑集》十卷、权德舆《制集》五十卷、元稹《元稹制集》二卷、段文昌《诏诰》二十卷、韩愈《西掖雅言》五卷、武儒衡《制集》二十卷、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王仲舒《制集》十卷、李虞仲《制集》四卷、封敖《翰稿》八卷、崔嘏《制诰集》十卷、刘邺《翰苑集》一卷与《凤池刀笔》五卷、独孤霖《玉堂集》二十卷、郑畋《玉堂集》五卷与《凤池稿草》三十卷与《续凤池稿草》三十卷、刘崇望《中和制集》十卷、李蹊《制集》四卷、钱珝《舟中录》二十卷、薛廷珪《凤阁书词》十卷、吴融《制诰》一卷。归于制诰类。实际上,此处文本虽以制诰为主体,但并非指所有文本都是制诰文本。例如郑亚《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凡两帙二十卷,辄署曰《会昌一品制集》。”[13](P4)此处“制集”包含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等各类应用文。又如《玉堂集》以地名命名,该文集应指任职翰林学士期间涉及到的各类文本,即除了制诰,还包括奏状以及其他奉敕撰写的文本。再例如《凤池稿草》《续凤池稿草》则可能包括拟制诰文本之类。又《翰苑集》所指称的内涵,亦有两个不同的义项。(7)《翰苑集》所指称的内涵,有两个不同的义项。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文曰:“则有《制诰集》一十卷……则有《奏草》七卷……则有《中书奏议》七卷……公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权德舆二十四卷本称《翰苑集》,包括奏议等内容。而韦处厚所编称《唐陆宣公集》包括“《论议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其中《翰苑集》十卷专指制诰。这种非完全意义上制诰专集之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源于某制诰的流行性,故而参与编纂者并非一人。二是制诰文本与奏议文本因为同属于公文书,因此在归类上的混同。引文参见:(唐)陆贽撰:《翰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宋)欧阳修:《新唐书》(卷6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 1616 页。
这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编纂过程中,制诰专集对文本的选择是扩大化。制诰文本与奏议文本因为同属于公文书,因此在归类上往往有相似性,导致编排位置的相近。二是在个人别集(含制诰)比较下,制诰专集确实已经达到了专门化的效果和目的。三是对于制诰文本的界限本身尚存在模糊边界。而在实际使用中,以功能分类,而不以“制诰”之说分类,故而“制诰”的定义并非那么重要。简之,制诰专集的专门化是有限的专门化,而该有限的专门化亦能完成制诰专集的编纂目的——应用性。
制诰应用性的影响在具体编次过程中无处不在。这主要体现在制诰专集对编次更符合制诰的功能性分类。在第一分级上,制诰专集注重以类分类,正如权德舆《答杨湖南书》提到“分列卷第”“相从以类”[2](P5804)。此与个人别集(含制诰)有相同之处。在此一级分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制诰专集的功能性分类。具言之,《翰苑集》(8)此处主要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制诰专集窥见一二,如《翰苑集》。考察诸版本,《翰苑集》二十四卷本与二十二卷本中的《制诰》十卷所收篇目完全一致,可见两位编纂者对制诰文本编纂很可能基于某个相同的文本,其很有可能反映的就是唐代陆贽制诰专集的原貌。的卷目下标有“赦宥”;“优恤宫城、名改州府”;“慰劳招抚处分事”;“册命、祝册、祭文、策问、答表”;“除授”;“铁券、慰问敕书”。再具体到文本,文本题目则依次包括大赦制、德音、诏、册文、告庙文、策问、批答、授官制、赐铁卷文、慰问敕书等。可见,其排列顺序是相当有规律。
正如《新唐书·百官志》言:“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王,临轩册命则用之;二曰制书,大赏罚、赦宥虑囚、大除授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勉赞劳则用之;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发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则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六曰论事敕书,戒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制,不易于旧则用之。”[14](P1210)此处“册书”可与《翰苑集》之“册命、祝册”,“制书”与《翰苑集》之“除授”,“慰劳制书”与《翰苑集》之“慰劳招抚处分事”等存在对应关系,诸如此类。可见,《新唐书》所言七种王言与制诰专集有一定的相似性。而《翰苑集》的分类之细,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天子策问”亦被《翰苑集》归属于制诰范畴,这说明此时“制诰”的内涵注重其来源,即王言性质。尽管制诰文本并未完全按照《新唐书》所言王言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但足见其编次顺序的功能性分类与应用性目的。这种方式在后世《文苑英华》中也有体现,如《文苑英华》卷四百十六“封爵、封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专集编次都如《翰苑集》一样整齐。正如《白氏长庆集》制诰部分较为规则,而元稹《元氏长庆集》则稍显平淡。这之中有个人习惯的区别。但他们在主要编次原则上,还是相对一致的,即同样考虑的功能性分类与应用性目的。例如《会昌一品集》(9)判断依据:宋蜀刻本与目录书籍著录一致。卷次依次包括册文、赞、铭、序、制(授官制、“赠xx制”)、诏(“赐xx书”、“赐xx诏意”)、敕旨、授官制(与外交有关的官职)、代xx书、敕、状等内容。这正是对以《翰苑集》为代表的制诰专集的呼应与证明。具体到文本层次,文本编次无定法,或以时间顺序为先后,如《上尊号玉册文》(会昌二年奉敕撰)、《上尊号玉册文》(会昌五年奉敕撰),或因内容相近而并列。
可见,制诰专集看出个人文集中“小制诰专集”的延伸版。相较于个人别集,制诰专集对制诰编次更符合功能性分类。那么,制诰专集背后编次逻辑是什么呢?一方面,制诰的专门化基于实用性需求。白居易《白朴》的流转可助我们窥视些许端倪。根据《野客丛书》记载:“仆读元微之诗,有曰:‘白朴流传用转新’。注云:乐天于翰林中,专取书诏批答词撰为矜式,禁中号为《白朴》。毎新入学,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检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无闻,每访此书不获。”[15](P297)可见,这种专门化用书的参考价值。这与部分制诰总集(10)例如温彦博(578~637)《古今诏集》三十卷,李义府((614-666)《古今诏集》一百卷,刘允济(武后时期)《金门待诏集》十卷,李麟(694-759)编《制集》五十卷,佚名(疑中、晚唐人)《唐德音录》三十卷、《太平內制》五卷、《明皇制诏录》十卷、《元和制集》十卷、《拟状注制》十卷,马文敏(待考)《王言会最》五卷,费氏(待考)《旧制编录》六卷等。参见卢燕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5-368页。存在意义是一致。
另一方面,制诰编纂的专门化基于制诰的非文学性。实际上,不少学士群体除了自己制诰专集,又另有文集,如《常衮集》十卷、《韩愈集》四十卷、《吴融诗集》四卷等。考虑到制诰的官文书属性,将其与其他文本分开保存、甚至不予保存,也是人之常情。同时,其他本文(尤其是诗歌、传奇等)可以作为文人交往、行卷宣传的重要文本,但制诰文本非是如此。由于与政治诸多关联性,其流传较普通文本受到了更多限制。因此不将其编入个人别集,而另编制诰专集,这确实是妥帖、谨恪的作法。
至于上文提到的,具体文本编次的些许混乱,这不仅仅是《会昌一品集》的个别问题,也是制诰专集、个人别集(含制诰)都存在的问题。毕竟文本收集的先后顺序,文本的类似性、个人的编纂习惯对此皆有影响。
三、余论
有唐一代,制诰文本的存在模式有个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从君主署名到个人署名制诰文本,再到各种文集并存的状态。
那么,制诰文本编纂为何会产生从制诰文本到制诰集出现的时间差?这是源于文本性质“公”与“私”的平衡。在文本性质上,制诰是官方文书。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出于职能所需而撰写文书。可见制诰的产生动机是王命所需,其撰写的内容代表君主意向。而作为撰写者按照相对固定化的形式体制,以自己话语表达君主意志。在这整个撰写文本过程中,撰写者拥有的是有限自主性。正如李德裕所说“近世诏诰,惟颋叙事外自为文章”云。这是造成前期制诰不能相对独立的重要原因,故而制诰文本多存在于相对不流动的文本载体上。具体为以下四类:(1)皇帝别集,如《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2)实录、起居注等涉及的文本,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3)在任时的宣底。(4)个人留底的文本。这四类都与国家制度密切联系,严格意义上,都谈不上个人意义上的文集编纂。
随着制诰撰写过程中,文人作用力得到肯定,制诰也获得相对独立的资本。在外在机缘、撰写者的文学精神两者作用下,制诰得以并被编纂成文集。外在机缘即指来自官方的认可,这在上文《苏颋文集》处已提及,此不赘述。至于撰写者的文学精神,这在苏颋等制诰“大手笔”中自有体现。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完成职能任务,还要完美完成职能任务,即写出符合“文质彬彬”的应用文。此其一。又权德舆《答杨湖南书》提到制集作用——“霈王泽,浊幽滞,振刑典,申肃杀,揄扬宏大,务极其言”[2](P5804)。此虽不乏虚美之词,却也符合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追求。因此,有信心于此的群体自会自主、自发地展开编集活动。这些是制诰文集从无到有、从单一文集到多类文集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其二。
具体文集可分为制诰总集、个人别集(含制诰)、制诰专集等。图示如下:

制诰总集的编纂源于传统。总集的发展不同于别集,它一直贯穿于唐代始终。《隋书·经籍志》便录有《诏集区分》《魏朝杂诏》《汉高祖手诏》《录魏吴二志诏》《晋咸康诏》《晋朝杂诏》等。但是,由于各类制诰总集已佚,无法窥探其编纂的面貌。考虑到《文选》“以类相从”的编纂特性,唐初的制诰总集很可能有此特征。这也为后世制诰编纂提供了参考。
至于个人别集(含制诰)与制诰专集出现时间相近,且有一定类似之处。一般情况下,该类集子一级分类是以体分类。若是个人文集的话,则将制诰与诗赋等分开编次。若是制诰专集,由于制诰的有限专门化,会将奏议、制诰等区分开来。二级分类往往以类编次。以类编次是比较方便的方法,也是自《文选》开始的一个重要传统。三级分类往往具体到文本,或以年编次,或以小类再分。这之间就体现出制诰文本编次的特殊性。例如《白氏长庆集》根据制诰文本的行文风格对制诰进行分类,如其中的“新体”“旧体”之分。又根据职能进行分类,如“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诏”。又例如《翰苑集》根据文本功能性进行分类,如“赦宥”“优恤宫城、名改州府”“慰劳招抚处分事”等。这三级分类各有其编次逻辑所在。一、二级分类是符合文本编纂的通用编次原则。三级分类则带有制诰文本的特征,即注重文本的职能性与功能性。这在后世《文苑英华》中得到继承,只不过两者之间存在些许不同。就《白氏长庆集》而言,更多是基于职能与在职情况进行划分;而就《文苑英华》而言,则更基于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之间的制诰涉及范畴的分类(尽管并不十分精准)。至于具体文本编次的些许混乱,这与文本的收集先后顺序、文本的类似性、个人的编纂习惯有关。
以上为唐人制诰编纂及编次观。由于文本有限,关于制诰编次其他情况、制诰文本载体、编次逻辑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