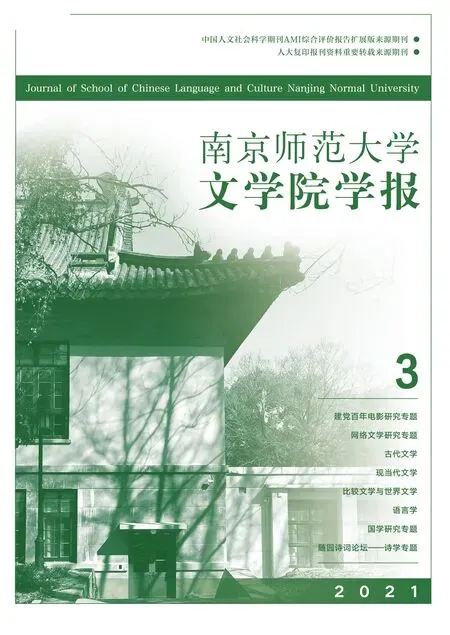论《金楼子》“兼备众体”的著述性质
2021-12-31伏煦
伏 煦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引 言
对于先秦诸子而言,无论采用格言、语录、对话还是专题论文的文体形式,“载之空言”,即说理都是最核心的著述方式;与之相对的则是“见于行事”,即记事,则是诸子百家说理的一种特殊方式。(1)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韩诗外传〉的研究》一文对“中国思想表达的另一方式”的讨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子书记事的传统可上溯至《韩非子》的《说林》与内外《储说》,降至西汉刘向所著《说苑》,依然有一定的思想系统,作者的理念先于所记载的古人行事本身。汉魏六朝子书逐渐改变记事以明理的做法,即刘咸炘所谓“诸子既衰,而子书变为杂记,其所以变者,记载淆之也”。“自扬雄《法言》始作史论,桓谭《新论》始记杂事,傅玄记载遂侵史职,《抱朴》词藻,几灭质体,至于梁元《金楼》,遂成类书矣。”(《旧书别录》卷四《金楼子》)[1](P457、458)从刘氏对中古子书的评述可以看出,“子书变为杂记”,对于子书衰变有着重要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金楼子》提要指出:“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逸。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搀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2](P1010)整体而言,除了《终制》与《自序》两篇延续了专题论文的体式之外,其余篇目均有“条目”,每篇连缀多个相对独立的事例,或作者萧绎的自述与议论;抄撮前代典籍的情况较多,(2)根据陈志平的统计,《金楼子》今存十四篇共549条,可以找到出处的有345条,剿袭他书的比例高达62.84%。氏著《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第五章《〈金楼子〉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9-264页。故而刘咸炘讥之“遂成类书”,但这种“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3](P1083)的著述方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类书,则是应当进一步讨论的,就辑本《金楼子》而言,现存较为完整的八篇之间,亦有必要分为不同的情况进行讨论,本节将以《兴王》《捷对》《立言》等篇为例,与类书、小说、读书笔记等不同性质的学术著作进行比较,以此更加深刻地认识《金楼子》“兼备众体”的综合特性。
一、子书与类书之别:以《兴王》与《艺文类聚》帝王部的比较为例
刘咸炘在评述汉魏六朝子书之时,以“遂成类书”描述《金楼子》,清代学者谭献亦批评萧绎:“自谓切齿于不韦、淮南之倩人,而杂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与《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相出入,未免于稗贩也。”[4](P107)谭献与刘咸炘二氏的意见,恐怕是阅读《金楼子》的普遍感受,只有厘清《金楼子》在著述方式上与类书的异同,才可能理解其“杂采子史”与记事因素较多的意义所在。
就《金楼子》的篇目而言,仅有《兴王》《后妃》《说蕃》三题与中古时代类书的部类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若以《艺文类聚》为例,三者分别对应帝王部、后妃部与职官部的诸王类。其中,《兴王》是《金楼子》的第一篇,萧绎汇集从上古到梁朝诸多立德建功的帝王事迹,与《箴戒》所列昏主暴君一并,颇有为当代及后世君王提供镜鉴之意。毋庸置疑的是,《兴王》的写作方式乃抄撮整合前代典籍而成,这一点与类书是相通的;然而萧绎在抄撮的基础上必须对资料加以整合,形成首尾完整而相对独立的段落,类书虽有对原始材料的剪裁与删削,但直接引录并在类目之下即可,无需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形成新的文本,试比较《金楼子》与《艺文类聚》“少昊金天氏”的有关文字:
少昊金天氏,一号穷桑,二曰白帝朱宣帝,黄帝之子,姬姓。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意感,生少昊于穷桑,是为玄嚣。姓姬氏,或云己氏。降居江水,以登帝位,以金承土,都曲阜。有凤鸟之瑞,以鸟纪官……天下大治焉。[5](P58-59)
《左传》曰: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焉。
《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即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6](P211)
《兴王》的“少昊金天氏”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其生平简述,后半部分则援引《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以鸟纪官”之事。引录《帝王世纪》的部分有一些关键信息与《金楼子》的记述重合,比如“穷桑”和“白帝朱宣帝”二号的来源,“登帝位,都曲阜”等。虽然在信息量方面,《金楼子》与《艺文类聚》几乎是等同的,但文本的形式有所不同;作为子书的篇章,即便以汇集前代典籍为成书的主要手段,却不能像类书一样,保持引录材料的原始状态,而必须整合成一个新的文本,对于《兴王》篇而言,每段有关帝王的条目近乎传记之体。
另外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子书的写作不可能是简单的材料堆砌,即便以记事为主,作者也不会抄撮所有的相关材料,而是选择某一个有兴趣的部分以表达出一定的主题与倾向。《兴王》与《艺文类聚》帝王部有关汉文帝的部分,亦多取自《史记·孝文本纪》,《兴王》的相关内容重点表现了汉文帝节俭与宽仁的品格,在“汉太宗恒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的综述之后,采录《孝文本纪》记载的罢露台、慎夫人衣不曳地等节俭之事,和以德行感化称帝的南粤王、化解政治危机,恐烦百姓而避免攻打匈奴,吴王刘濞诈病则赐以几杖等宽仁之事。[5](P172-173)而《艺文类聚》则共取三段,第一段为文帝的即位过程:吕后去世之后,群臣迎立时为代王的文帝,而代王臣属对此有不同意见;第二段为文帝节俭的品质,及对待匈奴进犯的保守态度;第三段则摘录司马迁“太史公曰”的部分,作为对汉文帝的整体评价。虽然第二段在信息量上,与《兴王》中的章节大致相当,亦体现了文帝的帝王形象和个人品行,但《艺文类聚》呈现给读者的是有关汉文帝的零散资料,无法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就文献的引录方式而言,子书或可依靠前代典籍而成书,但其写作方法和著述形态,皆与类书有本质上的差异。
学术史上曾有将类书溯源至子书的说法,如清代学者汪中《吕氏春秋序》指出:“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时,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7](P534)子书所关注的对象一般为与社会政治、道德修养有关的抽象概念,其范围与类书所具备的“天地万物”非常不同,以《艺文类聚》为例,大部分自然与社会的人、事、物皆具备一定的实体意义,如“岁时部”所列的春、夏、秋、冬四季,与元正、人日、正月十五日、月晦、寒食、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等节日;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等,则对应着现实的社会生活。从这些部类及其下属的类目中,我们可以看出类书所展示的“天地万物、古今之时”,对应的是客观而具体的现实世界,而子书的作者通常抱有较强的理论兴趣,子书所展示的亦是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热衷于抽象概念与义理的讨论。
这种本质的区别决定了子书与类书的交集非常有限,在类书的类目中,偏于人类社会活动的部分,才有可能在主题上与子书的篇章一致,如《艺文类聚》的人部(绝交、鉴诫)、治政部(论政)、刑法部(刑法)等,在汉魏六朝子书中皆有迹可循,甚至作为“文”的部分得以引录:如绝交包括交友是汉魏六朝子书颇为关注的问题,王符《潜夫论》有《交际》篇,徐幹《中论》有《谴交》篇,《艺文类聚》亦引录,葛洪《抱朴子外篇》亦有《交际》篇;《艺文类聚》人部“鉴诫”引录诸多诫子与家诫之作,亦是中古子书关注的话题,如曹丕《典论·内诫》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二篇,另外亦引录吴陆景《典语》之《诫盈》篇,类似主题亦见于《刘子》。
值得注意的是,类书的类目往往是名词性的,这与子书篇目常为某个动作或者倾向不同,亦与类书存录客观知识和子书表达作者主张的著述目的相配合,如《艺文类聚》人部有“贤”这一类目,汇集了有关贤者品德特质的表述,以及前代典籍对诸多具体的贤人的评价,然而子书中的相关话题,如《潜夫论·思贤》《傅子·举贤》《抱朴子外篇·贵贤》与《颜氏家训·慕贤》,皆表达了子书作者对贤人所采取的态度。同样的情况亦见于“言语”这一类目,《艺文类聚》所引录的材料,虽然明确了言语的定义,亦涉及诸多古人对言语的态度,但表达“贵言”、“慎言”等观念,还需要依靠子书或者论体文,如《中论》与《刘子》有《贵言》篇,《抱朴子外篇》有《重言》篇。由此可见,类书本身是材料的分类汇集,并不通过材料的整合表达思想;而子书即便大量利用前代典籍,甚至以记事改变了子书“立言”的性质,表达思想始终是这类著述的应有之义。
二、体近小说:《捷对》与《世说新语》的比较
辑本《金楼子》的《捷对》篇保存得相对完整,其序曰:“夫三端为贵,舌端在焉;四科取士,言语为一。虽谍谍利口,致戒啬夫;便便为嘲,且闻谑浪。聊复记言,以观捷对。”[5](P1102)虽然这段文字未必完整,但萧绎作《捷对》篇的宗旨已经非常明确:在承认言语对于社会政治的重要性这一前提下,劝诫与戏谑在言说在态度上虽有严肃与轻松之别,都是此篇所要汇集的内容。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成书早于《金楼子》约一个世纪的《世说新语》,“言语”作为“孔门四科”之一,亦是《世说新语》的篇目;而反映魏晋士人巧言机变的“记言”,亦根据主题分散在相关篇目中。尽管现存的篇序很可能不完整,条目的排列也较为散乱,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萧绎在编纂《捷对》之时,有特定的兴趣与倾向。
一、君臣奏对是作为藩王的萧绎非常重视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臣下随机应变,化解君上所面对的尴尬局面,如:
晋武帝受禅,探得“一”字,朝士失色。裴楷对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5](P1104)
宋文帝尝与群臣泛天渊池,帝垂纶而钓,回旋良久,竟不得鱼。王景文乃越席曰:“臣以为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此并风流闲胜,实为美矣。[5](P1105)
许逸民指出:“据‘此并’二字可知,此条与上‘晋武帝’条原当属同一条”[5](P1106),《世说新语·言语》亦记载晋武帝“探策得一”之事,正所谓“王者世数,系此多少。”[8](P88)而裴楷以《老子》第三十九章所述之“一”,消解了作为“王者世数”的“一”,同时以“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祝福了新生的晋朝政权及皇帝本人,堪称“捷对”。王景文“垂纶者清”一事见于《南史》本传记载,此回应固然没有裴楷之对具有政治意义,但也化解了宋文帝“竟不得鱼”的尴尬。类似的事例亦有: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咏古诗名句,亮诵王仲宣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5](P1115)
孤立地看这条记载,或许体会不到傅亮咏诗的意义。据许逸民《校笺》可知,在刘裕面前诵王粲《七哀诗》之人,一为郭澄之(见《晋书》本传),一为谢晦(见《南史》本传)。前者劝诫刘裕攻克长安后继续西进,乃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事;翌年长安陷落,谢晦劝止刘裕二次北伐,“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帝流涕不自胜。”[9](P522)在后一历史语境下,王粲《七哀诗》的名句更契合宋武帝得而复失的心情,似有助其悲哀之意。
二、六朝人所重视的“家讳”在《捷对》中有非常显著而集中的反映,萧绎汇集了众多汉魏以来士人为此针锋相对的故事,如“卢志问陆士衡:‘陆抗、陆逊,是卿何物?’答曰:‘如卿于卢珽、卢毓相似。’”[5](P1106)此事亦见于《世说新语·方正》,比《金楼子》多出论陆氏昆仲优劣的内容:“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8](P329)类似的故事亦有:
陈大、武该问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也。”[5](P1107)
安成公何勗,与殷元喜共食。元喜,即淳之子也。勗曰:“益殷蓴羹。”元喜徐举头曰:“何无忌讳。”勗乃无忌子。[5](P1110)
刘悛劝谢瀹酒,曰:“谢庄儿不得道不能饮。”对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悛乃沔之子。[5](P1112)
这三个故事较卢志与陆机之事而言,火药味减少许多,除了刘悛之外,前两例触犯“家讳”皆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如陈泰、武该之问以皋繇之名触犯钟毓父钟繇,而钟毓则以引《论语》“周而不比”、“群而不党”之说,在正面回应问题的同时,并巧妙地以此触犯武该父名周、陈泰父名群。何勗与殷元喜之事亦有类似之处,且殷氏的反驳更为直接有力,萧绎的记载更是直接指出其父名,以免读者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无法领悟“捷对”的意义。整体而言,三个故事的问答皆有表里两层不同意义,比之卢志与陆机而言,锋芒有所收敛。值得注意的是,《捷对》另有两则与姓氏相关的故事,亦可视作同一类型: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曰:“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正熊之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也。”[5](P1109)
杨氏子年七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有杨梅。孔指示儿曰:“此真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5](P1116)
两则故事亦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虽不直接涉及家讳,然而将崔正熊视作崔杼之后,杨姓之杨等同于杨梅之杨,依然是稍嫌过分的玩笑。崔、杨二氏的回应,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尤其是前者,虽然崔杼与陈恒皆为春秋时代齐国弑君之臣,但陈氏后篡齐,较之崔氏为更甚。
三、出使敌国、两国君臣之间的交锋,亦是萧绎在《捷对》中有意汇集的故事类型,如蜀汉费祎使吴,以“凤凰来朝,麒麟吐哺,钝驴无知,伏食如故”嘲笑东吴君臣,而诸葛瑾以“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反嘲之事;[5](P1121)东吴张温聘蜀,与蜀汉秦宓之间的问对,[5](P1124-1125)与东吴纪陟使魏,以“譬如八尺之身,其护风寒不过数处”,来回应“道里甚远,难以坚守”的质问。[5](P1127)
君臣、士人、敌国三方面之间的“捷对”,无论是化解君上的窘境,或是捍卫家族与国家的尊严,实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在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当然,在《捷对》全篇中,亦有“祖士言语钟雅相调”、“羊戎好为双声”等难以归入这三方面的故事,但这些例外并不影响我们理解萧绎选编之时的倾向性。或许,萧绎曾在篇序或者故事的排列中,明确表达这些倾向,不同类型的故事皆汇集在《捷对》中,实质上与《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志人小说集,按照一定主题或类别汇集魏晋士人轶事的做法是类似的;两者所使用的篇题,亦是形容士人德行、才能、性格与情感的概念,如《世说新语》以“孔门四科”为首,又有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至企羡、伤逝、任诞、简傲等名目,这与类书以自然万物、社会身份、人工器物等偏于实体的人、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同为抄撮前代典籍的编著之书,难以将其视作类书。
三、作为萧绎读书笔记的《立言》
辑本《金楼子·立言》篇幅较大,内容亦较为庞杂,某些抄撮前代典籍并加上作者萧绎个人意见的内容,亦与《杂记》相通;只是《立言》中保留了一些萧绎抒发个人情志的长篇文字,可以视作其“三不朽”之一“立言”志向的剖白,又切合篇题,使其与《杂记》有所区别。
综观《立言》全文,可以看出萧绎所采用的写作方式,最基本即直接摘录原文,(3)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梁元帝萧绎的生涯和〈金楼子〉》指出《立言》中的文字大多数并非萧绎原作,只不过是从过去的典籍里断章取义、排比而成;而这种做法在六朝是具有普遍性的。参见戴燕选译:《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62页。萧绎并未加以议论。如“与人善言,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戈戟。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5](P762)此段前半部分录自《荀子·荣辱》篇,后半部分则取自《非相》篇,体近格言,主题具有一致性,皆论述言论的重要性。
在直接抄录的基础上适当加以议论,或者有意识地汇集数条相关的材料,才是萧绎更常用的做法。如“俭约之德,其义大哉”条之下,即节录《左传·闵公二年》:“卫文公大布之服,大帛之冠,务材训农,敬教劝学。元年,有车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也。”并加上“岂不宏之在人”的议论;[5](P763)“明月之夜,可以远视,不可以近书。雾露之朝,可以近书,不通以远视”[5](P765)则取自《淮南子·说林》,此语引发了萧绎“人才性如是,各有不同也”的议论;类似的还有《列子·汤问》中“两小儿论日”故事,萧绎引发了“为政亦如是矣”的思考:须日用不知,如中天之小也。须赫赫然,此盖落日之治,不足称也[5](P829)。实际上,萧绎所思离故事本身的题旨已经很远,如果就此撰写专题论文,则很难将这个故事作为论据;而在读书笔记这种灵活自由的写作中,思想火花的迸发未必需要严密的论证,反而能留下作者宝贵的灵光乍现。
值得注意的是,《立言》亦保存了一些带有材料整理性质的段落:
夫言行在于美,不在于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之,可不慎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昔成汤教民去三面之网,而诸侯向之。齐宣王活衅钟之牛,而孟轲以王道求之。周文王掘地得死人骨,哀悯而收葬,而天下嘉之也。[5](P767)
此段先引桓谭《新论·言体》所论美言美行的重要性,再以成汤、齐宣王与周文王的例子证之。除了齐宣王活衅钟之牛事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其余两事皆见于《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所谓“异用”,乃“万物不同,而用之于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于用之。桀、纣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10](P234)成汤去三面之网,周文葬无名白骨,都是这种治国之术的体现。萧绎将此两例用以证明“言行在美”,对《吕氏春秋》所用的材料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亦是某种意义上的“异用”,这种做法证明《金楼子》抄撮前代典籍并非食古不化,与其说是读书过程中的随手记录,不如说是作者经过精心思考、为之后的写作而有意准备的素材。实际上,《立言》中亦保留了若干节有明确主题的议论,不同于杂钞加随感式的读书笔记,比如对九流百家之学的总结: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何者?夫儒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墨者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冬日以鹿裘为礼,盛暑以葛衣为贵。法家不殊贵贱,不别亲疏,严而少恩,所谓法也。名家苛察儌倖,检而失真,是谓名也。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务,中原丧乱,实为此风。何、邓诛于前,裴、王灭于后,盖为此也。[5](P805-806)
此节乃萧绎节抄《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引录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但对儒、墨、法、名、道四家的评价并没有继承原作的旨意,其中儒家仅录正面评价,墨、法二家录负面评价,而“虚无为本,因循为务”则是对道家思想的概况,以此引出萧绎对魏晋玄学空言义理的批评。表面上看,这一段节抄前代典籍的读书笔记,但绝对不是简单的省略,作者自身的观点和用意贯穿其中,使得节抄成为一种特殊的再创作方式。也正因为如此,《立言》作为读书笔记,才不仅仅停留在简单地抄撮史料,并以按语或随感的形式,记录下作者某些思想的火花。
尽管《金楼子》全书或者《立言》本身并未形成较为严密或者有系统的思想体系,现存的章节很难按照主题进行归类。但这些近乎碎片化的内容却涉及一个士人读书与修身的方方面面,《立言》中亦不乏萧绎自述情志之语,如“君子以晏安为鸩毒,富贵为不幸”一节,表达了对勤学的追求、对淫乐的厌恶;[5](P775-776)“立德”之外,萧绎在《立言》亦表达了建立现实功业的渴望:“吾尝欲稜威瀚海,绝幕居延,出万死而不顾,必令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尽忠尽力,以报国家。此吾之上愿焉。”[5](P810-811)而著述之事,则是退而求其次的:“次则清浊一壶,弹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著《鸿烈》者,盖为此也。”[5](811)由此可见,《立言》这一标题似有以“立言”赅“三不朽”之义,至少在纸面上抒发“立德”与“立功”之志。而读书勤学对于六朝士人而言则为“立言”之基石,故将《立言》视作萧绎的读书笔记并无不妥。
四、“记事”与魏晋南北朝子书的特质
对于《金楼子》而言,尽管抄撮前人成书的部分中含有记事因素,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记事中尝试总结萧绎著述的主题与感情倾向,某种意义上延续了《韩非子》至《说苑》记事以明理的传统。然而,作为杂家类子书的《金楼子》,明理或者“空言”的色彩比较淡薄,全书没有体系性,亦并无统一的思想主张,至少缺乏明确的意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记事还是抄撮前代典籍,皆非某种学术著述所独有的写作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记事”因素的加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子书“立言”的方式。
《金楼子》在《隋书·经籍志》中隶属子部杂家类,其类序指出:“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于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11](P1010)《隋志》从史官传统这一角度,为杂家类子书寻找依据,就《金楼子》而言,记事因素正是“记前言往行”以明“祸福存亡之道”,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语)然而,抄撮前代四部典籍的写作方式,又难免使之“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亦是记事因素加入之后带来的弊病。
尽管《金楼子》的写作十分依赖前代典籍,但其书又与南朝流行的诸多在旧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著述有所不同,胡宝国在《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一文中将这种著述分为集注、钞书与汇聚众书为一书等三种情况,[12](P59-63)其中钞书多指某书或某类书的摘抄,如葛洪《汉书钞》、张缅《晋书钞》,庾仲容《子抄》、谢灵运《诗集钞》,在没有“类书”类目的情况下,《皇览》等魏晋以后的类书亦归入《隋志》的子部杂家类,列于《杂事钞》《子抄》等著作之后。而汇聚众书为一书的情况,主要是谱牒书、地理书、杂传等。其他带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述,如钟嵘《诗品》与刘勰《文心雕龙》,在著述性质上亦与萧绎《金楼子》有着显著的区别,由此可见,无论是汇集前代典籍的材料,还是“兼备众体”上,《金楼子》在南朝的学术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将其视作书钞或类书显然忽视了它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子书“兼备众体”亦是先秦诸子以来的传统,如《荀子》和《韩非子》虽以论说文为主,但前者亦包括作为诗赋体的《成相》与《赋篇》,亦有论者指出《大略》为荀子的读书笔记(4)详见俞志慧《〈荀子·大略〉为荀子读书笔记说》(《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一文的论述,而《荀子》的注者唐代学者杨倞以之为“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后者则有《说林》与内外《储说》,汇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为韩非表达政治主张的写作素材。为何在一部著作之内,不同篇目的文体形式与写作方式会有不同,笔者认为,这是不同的思想表达需要不同的著述形式与之配合的必然结果,亦是子书“博明万事”的体现。若将《金楼子》与其《著书》篇中所序的其他著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诸如六经和诸子注疏(《周易义疏》《礼记私记》《老子义疏》)、史注(《注前汉书》)、杂传(《孝德传》《忠臣传》《研神记》)、类书(《语对》)等著述有着明确的性质,即便早已亡佚,我们很容易根据书名了解其属性,亦可依据现存的同类型著述推断其性质和体例。《金楼子》作为一部子书,其宗旨与写作方式与这些体制明确的著述不同,作者的选择与主观意愿可以更多地灌注其中,也可以在一部书中选择不同的著作体式。
记事因素的大量加入,无疑极大程度上解构了先秦诸子以来确立的“立言”传统,“空言”明理的写作方式被《金楼子》一类的子书边缘化,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暗示了子书在魏晋至南北朝后期面对的困境,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批评两汉之后的子书“明乎坦途”,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批评“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13](P1)在义理方面,汉魏以来的子书难以有所创见,学者也很难在六经与诸子之外建立新的学派及相应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又以注经和著论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并未涉足子书(5)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一书第三章《文体互动:经与子、注经与著论》对此有所阐发,指出了论体文的内容,往往就是清谈反复讨论的话题,如人物品评和玄学义理;而经注更好地体现了玄理在体用层面上的贯通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100页。。那么“理重”而“事不复”能否成为子书新的出路,在记事方面追求新意,一方面不妨记载近闻,萧绎在《金楼子·后妃》中为其母阮修容立传,《志怪》篇记载初婚之日所遇怪事,都是非常私人化的写作。另一方面则是评论与考辨史事,将前代典籍视作研究对象,比较重复六经和诸子的义理而言,这两种写作方式对应的是无穷无尽的题材,也使得子书从关注社会政治、天道人伦等方面,转向了作者的人生体悟与知识趣味,子书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走向笔记、文集等更加私人化的著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