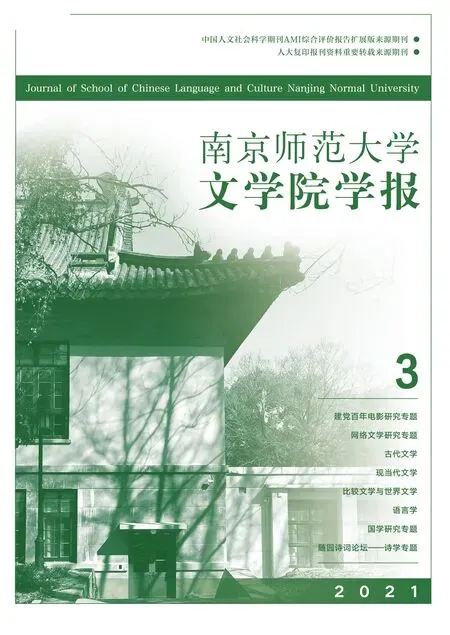论徐怀中小说的境界叙事
——以《牵风记》为考察中心
2021-12-31刘霞云
刘霞云
(南京财经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早在1980年,《西线轶事》在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以高票得分名列榜首,叶圣陶先生评价该作充分展现了徐怀中压抑多年的“创造境界”[1]的才华,而笔者认为多年后问世的《牵风记》则尽情展现了其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境界”一词最初在古代典籍中出现,诸多记载皆表明其本指一定的疆土范围。佛学东渐以后,在对佛经的翻译中,译者便开始借用“境界”表述个体心灵所能达到的觉悟状态。之后,“境界”便不再以一种实体的身份存在,而是以一种关系、一种抽象意义彰显。
在中国美学史上,王国维总结提出“境界说”,确立了美学意义上的“境界论”。此论不仅用于阐释诗学,在小说、戏曲研究等方面皆能获得全新视野。在王国维看来,艺术境界与人生境界相通,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成功再现了客观对象,而是在对象呈现中所能达到的精神层次。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的“真”决非客观实在之“真”,而是一种纯粹之“真”,即能体现理念的具有终极价值的“真”,将艺术家的认知与情感提高到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与体验层面,并以此确立诗学的精神内核。从诗学意义上说,境界不仅包括有形的审美评判,还包括无形的精神尺度,是审美主体通过体悟所达到的超然心境。对于小说而言,若想抵达此境,不仅要成功再现审美对象,更重要的则是诠释在呈现过程中达到的审美心境。而从“境界”的内核构成看,作家的审美状态是否自由本真、作品的价值形态是否超越现实、作家是否遵循内在审美机制等要素的具备,则是抵达理想之境的不二路径。以此观照《牵风记》,则可以发掘其在顺应天性的审美追求中彰显着境界叙事的超脱、和谐、至美的本真内涵。以此为基点,回溯作者六十余年的写作历程,则可以发现其在阶段性“保持沉默”背后,是文学执念的生长、回归自然的天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自觉认同,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促进境界叙事的形成。而徐怀中式写作因其所跨越的时间、所蕴含的特质而成为当代文坛的一种现象,此现象对于我们思考当代长篇写作与古典文学资源之间的关系,探究当代长篇写作的另维空间等皆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审美境界:超脱·和谐·至美
毋庸置疑,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心境会影响作家与作品的审美状态。“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2]。这是作者创作《牵风记》时的心境流露。打开文本,读者瞬间会被作者从容、超脱的心境所感染。开篇借古琴传心声,作者对气势磅礴的“七十二滚拂”不感兴趣,却喜好不做过多缓急变化的散音,领略其“不舍昼夜”的意味。此心境化到笔端,投射到创作中,显示出超脱的境界。如对生死的超脱。汪可逾知晓大限已至,从容去除身外之物,平静离世。此种生死观还借助意象“纸团儿”和碑文《银杏树》作进一步阐释。通讯兵曹水儿的死亡结局,亦体现此心境。曹水儿一身功夫,屡立战功,是战争年代的稀缺人才,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抓了典型,接受处决但不接受五花大绑,临刑前劝慰和保护陪刑的女人,如此快意跳脱,完全活出了自我。两个人物以各自的方式走完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相对于首长齐竞的苟活于世,启迪读者重新审视生死的意义。如对世俗伦理的超脱。按世俗观念,曹水儿沾花拈草乃恶习,与之交往的农家妇人也该被唾弃,但作者充满善意的述评明显有着对苦难生活中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几分赞许。如对时间的超越。在作者眼中,时间不仅是历时、动态、稍纵即逝的,也是共时、静态、相对永恒的。这种超越古今的时间观在文中多处体现,如初次会面论琴吟诗,齐竞表明其现代时间观,汪可逾则回应超越时间观。汪可逾对银杏树的迷恋,也主要缘于其作为“生物活化石”的绵长不绝与生机勃发,“人树合一”亦体现作者对这种超越性与永恒性的精神诉求。
除却畅意表达超脱观,作者在“如何表达”上也呈现出一定的自由自主状态。《牵风记》在故事讲述、人物塑造、视角安排等方面,回到人类艺术的起源,偏向于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超越现实主义手法。作者在尊重现实逻辑、强调细节真实的同时加入幻想成分,构建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的审美图像,与强调直觉的超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与超现实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牵风记》的故事讲述极其自由,尤其围绕溶洞的发现、汪可逾的“羽化”及人树合一、滩枣与汪可逾的心灵感应等描写,若从现实逻辑看着实令人费解,作者也承认这些细节的不可思议,但为了书写的自由及与主题的和谐,以人物自省的方式给了读者一个不算交代的交代。在这里,写实与写意、实然与或然、思辨与抒情高度融合,渲染出浓郁的神秘气息。尽管作者遵循现实与艺术同构的逻辑,但还是引起诸如“战争年代几乎不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女性”“或许过于理想化了”[2]等质疑;虽然行文中诸多评议与作品的气韵、品格相协调,但也有论者提出这些评议跳脱故事,阻断了情节链条[2],作者回应“时至今日,我已不再将小说创作中引入议论文字视为危途,而看作是人物性格发展以及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自然延伸”[2]。此番解释再次表明其自由超脱心态。
区分作品审美境界的有无,取决于作品审美品格的有无,而所谓“境界”与“品格”,则是一种尺度,其价值准则须是有限非功利的。曾有论者质疑《牵风记》“置残酷的战争进程于不顾的叙事策略显然是有意为之,因此小说中的战争状态或言氛围相对来说是淡漠甚至缺失的”[2]。此番质疑由对写作目的理解不同所引起。徐怀中认为“进一步强化战争进程,对于作者可说是驾轻就熟,顺手拈来。即或略加强如何克敌致胜,如何扭转战局,便不是你看到的这本《牵风记》”[2]。很显然,《牵风记》无意于正面演绎战争历史,让这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承担起“以史为鉴”的启迪功能,实际上以战地生活为背景,在战争的彩云流变之间,采撷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即“三人一马”,来表达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和对“美”的不遗余力的发现,超越了小说的教化、娱乐等直接功利性功能。
作品以“三人一马”为中心,通过人与社会、自然、人、物件等的对象化过程,畅意表达和谐观。一是人与社会的和谐。虽然汪可逾积极投身革命,但其参加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她眼中,战是为了不战。她支持革命,勇敢地冲在最前线,哪怕遭受赤身裸体的尴尬、遭遇强暴的切身之痛,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不退缩,但她厌恶战争中的死亡与暴力,尊重与爱惜每一个生命个体。为了不踩踏几具敌军的尸体,宁可接受通报批评;为了保全一船女人的性命,不惜赤身裸体带头作“人体展览”;突围过程中,自身性命难保却哀叹曹水儿身上沾染的杀人气味。这种超越国家、阶级、民族的仁爱之心,让“小我”与“大我”深度融合,有力回应了“人物不是生活在战争中”的质疑。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作者着墨最多的几株标本中,战马滩枣占据重要地位。曹水儿在突围过程中驾驭滩枣跨过黄泛区时人马合一,汪可逾虽不能驾驭战马,却与滩枣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尤其在弹奏《关山月》之后,人马互为无言的知音。在滩枣被作为野马处理消失后,一曲无弦《关山月》引来滩枣的悄然聆听。汪可逾“羽化”后,奄奄一息的滩枣再次出现,拼尽最后气力帮助汪可逾完成生前遗愿。如此描写,可谓人马合一,心心相通。三是人与人的和谐。文中人物关系多舒缓自然,即便存有冲突,也非狂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一切皆在无声中化解。如在汪可逾和齐竞之间,齐竞的身份决定其现实功利立场,和汪可逾之间注定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齐竞身上始终存有两个“自我”,“大我”时刻约束着他,迫其漠视美好;崇尚美好的本性又使他无限迷恋汪可逾的一切,二者博弈的结果在“美”被毁灭的瞬间揭晓,矛盾也随之化解。四是人与物件的和谐。作品中贯穿始终的物件是古琴。汪可逾怀抱古琴登场,一曲《高山流水》展示了与齐竞迥然不同的人生境界;一曲《关山月》暗示了人马殊途同归的人生归宿。历经战争的磨难,古琴被毁。“在人不在器,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弥留之际,汪可逾在无弦的琴面上弹奏出“洋洋乎!诚古调希声者乎”的曲子,正如“万物有盛衰,唯音声无变”,人琴合一,曲尽人散,唯音永恒。
《人间词话》云:“诗人就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人间词乙稿》序云:“原夫文学之所以有境界者,以其能观也。”可见,无论“入”还是“出”,基本前提都是“能观”即具有审美直观与领悟能力。有论者曾质疑《牵风记》:“大量讨论音乐、摄影、书法艺术以及时空、地质等科学问题不免有些突兀和虚妄,而人物在战场环境下的大量艺术化行为更会令人产生轻浮之感。”[2]此番质疑还是来自对作品写作目的之误解。承前所述,作者要本着审美直觉,尽力捕捉诸多超越于战争之上各种美的东西,在“战争小说”这块画布上,以结构、意象等为借镜,为读者绘制至美文本。
如在内容上竭力彰显各种“美”。文本标题是各种类型“美”的凝练呈现。一是艺术美。“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为整个作品定下诗意、唯美的基调,虽然这场晚会办于日军大扫荡的某个夜晚,但亲历者对曾经的杀戮与灾难记忆模糊,唯独对琴曲难以忘怀。“现代人的听觉依然处在休眠期”探讨音乐之魅力;“一道明丽灿烂的战地风景”由衷赞叹汪可逾爽快挺秀的书法艺术;“一名女八路 一只灰鸽 一簇蒲公英”展示战地人体与摄影艺术;“你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出生年代”则是对小春壶先天自然表演艺术的惋惜。二是人性美。汪可逾是人类美好自然天性的集大成者:“让春天随后赶来就好了”中的礼貌与天然微笑;“他发现了一颗未经命名的小行星”中的毫不设防与了无心机;“以晋冀鲁豫三千万人民的名义”“黄河七月桃花讯”“这种气味不是河水清洗得掉的”集中体现其仁慈与敬畏生命之心;“零体温握手”中与齐竞的诀别展示其高贵的灵魂。而在曹水儿、滩枣身上也负载着作者对美好人性的向往:“野有蔓草”中对原始生命力的欣赏;“活在二十世纪的古代野马群”中对回归天性、狂野无羁的战马群的礼赞;“瑟瑟战栗的紫薇老树”中对美好爱情的笃信。三是生活中一切直观的审美。文中无处不彰显着作者的美学倾向,如对女性的审美以优美为主,汪可逾则是优美的化身:健壮不乏娇弱的体态,匀称而又协调的巧手,近乎强迫症的爱清洁、整齐与对称等。总之,在对战地生活的记忆打捞中,能对作者产生惊艳的多是这些来自生活、自然以及人性深处的美。在文本建构过程中,直观美感与和谐观念相融,升华为澄明的理想审美境界。
如在形式上倾力构建各种“美”。一是结构的灵动诗意。从表层内容看,《牵风记》的故事始于1942年日军大扫荡,止于1948年初大别山敌军围剿的撤退,这是明线,但作者没有完全据此行文,而是在明线之下潜伏着一条暗线即“三人一马”的情感变化:如汪可逾与齐竞之间由初识、朦胧爱意,再到和谐相处、冰冷分手;如曹水儿与汪可逾之间由不了解、敬慕畏怯,再到誓死怜惜;汪可逾与滩枣之间由天然亲近,到互为知音、患难情深,同眠大别山。正是这明暗两线,构成小说形散神不散的灵动诗意结构。同时,作者还赋予结构一定寓意:将作品喻为一首曲子,首尾分别安排“尾声”与“序曲”,开始意味着结束,尾声又意味着新的开始,如此反复,体现着作者的开放循环观。二是意象的丰赡美好。作品善以丰赡的意象表达丰富的情感,诸多意象如琴、曲、春天、紫薇老树、蔓草、小行星、战地风景、灰鸽、蒲公英、野马群、银杏树等,寄寓着作者的美好心愿,如春天喻示美好的爱情;紫薇老树喻示对爱情的坚守;蔓草喻示民间风情;灰鸽寓意理性安静的思想者和爱情使者;蒲公英则代表永不止息的爱等。作者采用泼墨大写意与工笔式细描交融的方法,使微观意象与宏观世界、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呼应,传达悠远寓意,有机构建至美文本。
二、审美生成:沉默·执念·自觉
按自然时间分期,徐怀中的小说写作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1954年至1964年;1980年至1985年;1999年至2000年;2014年至2018年。如此看来,虽然作者关注写作六十余年,但真正写作时间也就二十余年。换言之,他在写作生涯中更多时候是“保持沉默”。为何保持沉默?沉默背后,其思想又呈什么状态?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层了解作者境界叙事的形成。
徐怀中第一个写作期的作品多关注时代重大题材,表达宏大主题。《我们播种爱情》《卖酒女》《无情的情人》关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地上的长虹》《十五棵向日葵》《雪松》《四月花泛》则盛赞集体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五十年代初,国家正在青春年少,构成了人民群众精神状态上一个令人难忘的黄金时期”[3]。部队文工团出身、同样青春年少的徐怀中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冀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以极快的速度写出起点高并迅速走向成熟的系列小说,其中《我们播种爱情》在国际、国内赢得相当声誉。《地上的长虹》得到“用极大的热情及时反映这一英雄业绩,歌颂了参加这一伟大工程的英雄”[4]的好评,但也有人指责作者“全凭主观臆造,歪曲了现实”[5],理由是作者任意描绘人物“落后”的一面,把革命部队的光荣传统完全从小说中抹掉了。其实,所谓的“落后”主要指战士在艰苦的工作中偶尔情绪会低落;团政治委员有谈恋爱的倾向;先进战士并不先进,在梦中梦见女学生等。与这种概念化的文学观相比,徐怀中的超越阶级、回归人性明显和时代保持了距离。
因褒贬不一,处女作所遭受的批评并没有对作者造成大的影响。1957年底,徐怀中在《松耳石》的基础上写出《无情的情人》,虽然很谨慎,但“不想正赶上下一次风浪,招来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批判”[6](P3)。在艺术上,《无情的情人》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概念化弊端,尽力探索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也正是其不同凡响之处,但因鼓吹阶级调和、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遭到批判。迫于政治压力,徐怀中作了自我检查。此后,除却《四月花泛》,徐怀中沉默二十余年。但凡对中国当代历史有些微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段沉默所昭示的意义,《四月花泛》也可看作其在沉默之中所作的挣扎。此文作为“四好五好战士”征文发表,作者回忆“我并没有想过如何配合‘四好五好’运动。写这篇东西,希望做到出自平凡,近乎天然。”[3]《四月花泛》是配合运动的产物,但从作品的写作理念看,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挣扎,这种挣扎是对文学追求的一种坚守,也标示着精神世界中高贵与平庸以及卑俗的界线。
正是出于这种执念,徐怀中以沉默的方式度过创作的黄金期。之后,徐怀中迎来人生第二个写作期。相比之前,少了激情,多了沉静,题材依然紧扣时代重大话题,关注的依然是人情与人性,变化的是思想,开始追求“要有主观热情的燃烧,要有哪怕是并不值得重视的,却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点思考和发现”[7](P4)。《西线轶事》取材于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主人公是几位女电话兵和一个有着女孩名的男步话机员。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行其道,同样作为伤痕人物,徐怀中有着自己的思考,他没有让人物声泪俱下地控诉,而是让其有怨恨有热爱,有反思有期待,有颓废也有忠诚。表现战争的惨烈也是军旅小说的应有之义,徐怀中无意于正面演绎战争,而是在战争的氛围中向读者展示其所蕴含的历史深刻性和生命丰富性。《没有翅膀的天使》关注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状态,但作者宕开一笔描写爱岗敬业的护士成长为科研人员的历程,尽管他们的实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不息的是一颗求真的心。《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探讨新时期年轻人崭新的恋爱观与择偶观。这些作品表明作者开始远离宏大主题,关注“小我”的内心体验。《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与同时期反思力作《八庙山上的女人》有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同为有功之人,后者的作者张弦力讽这位躺在功劳簿上接受人们爱戴实则薄情寡义的虚伪男人,而徐怀中笔下的这位老军人,同样有愧于女人: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始终不让出身农村的女人随军,让其在年壮时积劳成疾离世;离休后带着忏悔来到亡妻的故乡,在这里追忆过去,展开未来。老军人这种超越世俗的思想行为浸润着作者几十年经历所赋予的感慨与体验,也释放着作者进入升华的人生与艺术境界的信号。
徐怀中的第一次复出是成功的,代表作《西线轶事》惊艳了文坛,被誉为“开启了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新生命的先河”[6](P9)。这是对其坚守文学理念的一种肯定,但仅有的几部作品也折射出作者的心境及人物表现的转变。之后,除却新世纪之交的两个短篇,作者又沉默三十余年。对于第一次沉默,作者解释“多年来我写东西太少,客观原因不去讲它,主要是由于自己缺少许多有志于写作的同志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8]。对于第二次沉默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若回到忏悔的“老军人”那里,再续接上新世纪之交的两个短篇,或许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新世纪之交,作者开启了第二次短暂复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描写陌生女子的决绝赴死,作者毫不掩饰对纯净、自然、死亡的赞叹与欣赏。《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则表达对“标志性微笑”的推崇,那种无意识的、先天的、发自内心的赤子之笑,一旦沾染上社会习气就不再出现,作者对此怅然若失。至此,宏大主题一并消失,剩下的则是对“小我”幽微人性的品读与观照。这种对至纯人性美的追求与超然生死观的思考,若作单独阅读,或许令人不明就里,但若结合忏悔老军人的“境界”,再看《牵风记》与新世纪之交两个短篇的联系(扉页寄语、微笑、死亡),我们可推断作者对生死的哲思以及对“美”的追求已成为不二的审美标准与艺术追求。
虽然徐怀中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但阶段式创作依然体现其一贯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取向,正如作者所言:“一个写东西的人,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入和变化,会直接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7](P3)其实,自始至终,徐怀中都是一位有温度、善思考、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家。谈及“先锋”,傅逸尘曾向其发问:“假设把您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您能接受吗?”[2]对此,徐怀中态度明确:欣赏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但对乖张的形式实验以及对传统小说伦理的颠覆持保留态度。他的写作与先锋写作是背向进发的两列轨道车,但结果殊途同归。可见,徐怀中不是先锋作家,但特有的先锋气质使他位于先锋的行列。
先锋气质使得徐怀中的作品与时代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姿态的获得除了先天习性之外,更多得益于外在文化资源的浸染以及作者的文化自觉。十七年时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使其写作难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的影响,在题材选取、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与保持距离皆出于本能。进入新时期,各种文化资源的解禁与蜂拥而至令人无所适从,但从后期两个短篇可看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推崇,尤其是对老庄人生哲学的青睐。《你未曾见过日出》中那位军事博士几十年如一日地迷恋一个陌生女孩的天然微笑,并将其比作“日出”。《道德经·第十章》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指出成年人还能如婴儿那样纯粹而无欲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围绕生死的探讨展开。《庄子·至乐》记载庄子认为人死,生命元气消失,又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所以要顺乎自然,乐天安命,以超越生死的态度,达观冷静地对待死亡。小说中那位不知名但事业有成的年轻女人,奔赴小岛只求一死,作者对她的赴死描写正是对老庄超脱生死观的阐释。
从美学哲学角度看,徐怀中也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追根溯源,美学意义上的“境界说”早在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方术之士编写的《淮南子·修务训》中可觅得痕迹,其中有“见无外之境,以逍遥徜徉于尘埃之外, 超然独立,卓然离世,此圣人之所以游心 ”。此处的“境”指想象中的无限时空,所谓“见”不仅指眼见,还包括心灵的内视。“无外之境”源自老子,老子认为人的视野之外,另有一个包容天地的无限大的“物”在,此乃“道”。如此超越边界的时空观在《牵风记》中有着完美的阐释与体现。其实,老庄的哲学美学与儒家、佛家相通。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其中儒家的人道精神与道家的宇宙意识,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而自唐后佛家的“境界”说更成为诗词境界的本质内涵。徐怀中的境界叙事得益于中国儒释道哲学美学思想的吸取与内化,作者自己也坦承:“步入老年之后,个人的阅读兴致更多侧重于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只是建立了一个备忘录,抄写了老庄等古代哲人一段一段语录,我反复阅读品味,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9]
不仅沉迷于中国的古典哲学,作者也极力推崇在思想主张上与中国孔孟老庄之道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超验主义思想。新世纪之交的两个短篇与超验主义思想的联系尚不明确,但《牵风记》中的汪可逾几乎与超验主义的要义一一对应:自然、自我、自由,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个性解放,反对权威等,留给读者的是一个纯粹、真诚、唯美的女神形象,展现出战争年代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中国女性的别样风情。作者也承认《牵风记》与先验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无可辩驳,这种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2]。
三、意义反思:“现象”·现状·空间
早在80年代就有论者称徐怀中的写作为一种“现象”,认为“它所跨越的时间,它所蕴含的特质,它所出现与消失的某种规律性,都在向我们显露出这一命题的某种意味”[6](P1)。诚然,一个作家的写作之所以能被称为“现象”,并不仅仅因为作家个体的独特性,还因为其背后所昭示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与意味。徐怀中的写作,从代际角度看,作为二三十年代生人,其在文坛上的出现与消失,以及出现的方式和消失的原因,不可逃遁地显现出时代的印记。作者自己也坦承“虽然我凭着对于艺术兴趣的追求,极力抵御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演绎政治概念和单纯记述新人新事的简单化要求,但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实在没有能够从这张有形无形的网里挣脱出来。”[7](P3)从此角度看,徐怀中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时代共性。但与此同时,作为独立的写作个体,其与主流文学的发展又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在写作理念以及追求路向上呈现出一定的越位现象。若说在写作中与主流文学思潮保持对位是其心性使然,那么在写作中出现越位现象也是其心性使然。从此角度看,徐怀中的写作又具有一定个性。这种由共性与个性交织而成的写作能否称之为“现象”?《牵风记》的问世,则为这个早期断言的合理性做了注脚。李国平先生称《牵风记》“堪称‘现象级’的文本,蕴含着许多超越作品本身、超越军事文学的意义”[10]。确实,徐怀中1962年完成初稿,“文革”中迫于形势付之一炬,80年代几次动笔又辍笔,《牵风记》的写作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全程,使其既是一部个人文本,又是一部颇具启示意义的时代文本。
从徐怀中个人角度看,一部作品耗时半个世纪,在当下急功近利的年代,鲜有作家敢做如此尝试,而对于其审美倾向,发自内心,水到渠成,他人虽心向往之,却也很难全盘复制,这点可从《银杏树》碑文中对汪可逾的评价窥见一斑,我们姑且认为此乃作者自喻。但从文学角度看,徐怀中写作则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可缩影为中国作家向西方叙事传统学习与借鉴的过程,尽管其间夹杂有对中国叙事传统有限度的重审与再寻。如今中国作家有了向世界表达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自信,成熟的作家更倾向于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古典与通俗等传统与资源进行杂糅创化,而在诸多吸收与创化中,文坛已悄然形成一股向中国古典文化与叙事传统致敬的暗流,这点从近几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审美品格可窥一斑。作为茅奖获奖作品,有论者评价《牵风记》“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所匮乏的审美的高贵气质”[2]。不仅如此,作者将“牵风”化为动感的美学意象,为读者提供多元解读空间:“一是……牵引战略进攻之风;二是……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三是……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四是……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不可”[9]。于是有论者补充为“牵住了当代军旅文学的审美之风、探索之风、创新之风”[11]。其实,不管作何理解,都不可否认《牵风记》对当代文学在审美追求上所起的“牵引”之力,而其冲淡、纯净、雄浑、博大的文风,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构成独特文脉的继承与超越。从此角度看,《牵风记》具有延续中国现代文学流脉、牵引当代文风走向之价值。而从“境界论”的理论起源看,王国维借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在传统意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境界说”,作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其所体现的审美境界应是世界范围内长篇小说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由此又昭示着长篇写作的另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