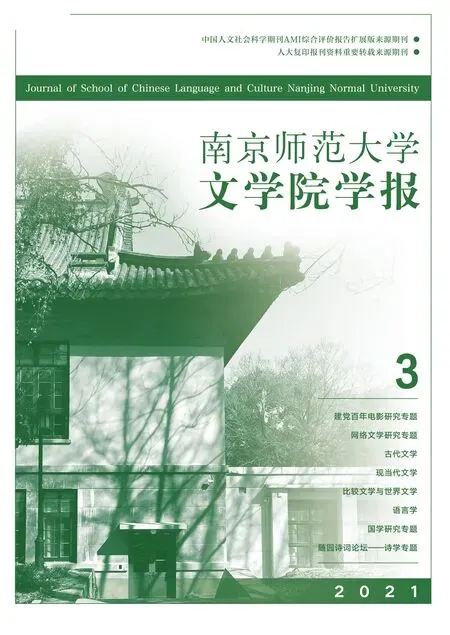福斯特与《印度之行》的“自治”书写
2021-12-31沈忠良
沈忠良
(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在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六部小说中,唯有《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 1924)的故事主线完全脱离了英国本土。作为一部根植于殖民时代的作品,《印度之行》对“助长了英帝国主义中产阶级的傲慢和冷漠予以了抨击”[1](P51)。众所周知,福斯特生前最喜欢的作家是以创作风尚小说闻名于世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对此,施瓦茨(Daniel R. Schwarz)曾敏锐地指出,“《印度之行》是风尚小说的现代版本”,福斯特意在借其表明,“在不牺牲艺术完整性的情况下,再也不可能写出一部奥斯丁式的小说了——当然也不可能写一个国家被英国征服的故事”[2](P245)。与奥斯丁描写男婚女嫁、凸显中产阶级社会风尚与乡绅礼仪的作品相比,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要复杂许多,这部历经十余年写成的小说,见证了作者在“一战”前后不同的政治立场。有鉴于此,施瓦茨进而指出:“在小说这个想象的世界里,奥斯丁的价值观是相对静止的,而福斯特的在逐步发展”。[2](P246)
在《印度之行》中,有三处现象最能体现福斯特价值观的演变,其一是来自英国的穆尔太太和阿黛拉的歇斯底里的爆发,其二是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穆斯林对伊斯兰怀旧情绪的摒弃,其三是英国人菲尔丁与印度人阿齐兹的分道扬镳。本文意在借小说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和怀旧这两种情绪,结合跨国友谊来引向“自治”(autonomy)这一题旨。《牛津英语词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对autonomy一词作有如下释义:“(国家、机构等)自我治理、制定自己法律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以及“追随自我意愿的自由;个人自由”。[3](P807)由是观之,从大的层面上讲,“自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治权;而往小处说,它是指个人的自主性。英国女性的歇斯底里源于缺乏自主权的社会现实,她们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被剥夺了认识殖民地印度的欲望,面临着与恪守深闺习俗的当地女性相似的命运。阿齐兹摒弃了伊斯兰王国的怀旧情绪,并在宗教立场上作出了妥协和让步,由此反映出印度穆斯林对民族独立和国家自治的清醒认识,反映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日益尖锐的种族矛盾以及20世纪初印度社会日渐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此外,小说作者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转变也在菲尔丁和阿齐兹的跨国友谊中得到了彰显。作为小说的两位主要人物,菲尔丁拥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阿齐兹渴望印度的独立与自由。两人友谊的破裂在暗示个人关系无法超越政治的同时,也折射出福斯特与帝国主义的分道扬镳。要而言之,对“自治”的探讨有管中窥豹之效,既有助于揭示殖民主义下英国女性和印度人的身份危机,也有助于阐释福斯特帝国主义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
一、自主性的缺失:英国女性与歇斯底里
小说《印度之行》有一处突转的情节,即阿黛拉认为自己在马拉巴洞穴内受到了阿齐兹的性骚扰。虽然福斯特对性骚扰的具体细节讳莫如深,但可以肯定的是,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人物穆尔太太和阿黛拉在参观完洞穴后都陷入了歇斯底里(hysteria)的情绪之中。从词源的角度上讲,hysteria源于希腊语词根hyster(子宫)。古希腊人认为这是一种原发于女性子宫的疾病,这种认知虽然带有不言而喻的歧视和偏见,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歇斯底里高发于女性群体。十九世纪一位名叫法布尔(Auguste Fabre)的医生直言:“每个女人都携带着歇斯底里的种子。歇斯底里在成为一种疾病之前是一种气质,而构成女性气质的就是最基本的歇斯底里。”[4](P287)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andCivilization)一书中也对女性与歇斯底里之间的关系做了一定的阐释,他指出,歇斯底里的出现与身体内的空间密度和渗透度有关,男女间的生理差异导致后者更易受此种疾病困扰;此外,当女性“过着轻松闲适、奢侈宽松的日子”,或者当“悲伤压垮了她们的决心”,她们就容易变得歇斯底里[5](P149)。
在剖析穆尔太太歇斯底里发作的原因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一人物先做一番简要分析。穆尔太太是印度治安官罗尼的母亲,属于英国中上阶层,生活相对富裕。她年事已高,但依然不远万里,从英国坐船数月来到印度看望自己的儿子,其慈母形象可见一斑。除了看望罗尼之外,另一个吸引穆尔太太踏上印度之旅的重要原因是印度的陌生与神秘。正如她本人所言:“我喜欢神秘”,[6](P63)正是这种出于探索的兴趣促使她前往马拉巴洞穴一窥究竟。从空间层面上讲,马拉巴洞穴的漆黑与小说中反复提及的“混沌”(muddle)一词遥相呼应,而混沌亦是小说对殖民地印度的总括性描述。可以说,马拉巴洞穴是印度社会的“模仿表征”[7](P156),穆尔太太和阿黛拉的洞穴之旅是认识印度的一个重要窗口。此外,它也是一个精神客体,是古德博这样的印度教徒“与上帝沟通”的宗教场域[8](P115)。穆尔太太信仰的是基督教,她在参观洞穴时出现了排异反应,如此看来便显得不足为奇。事后,她向基督教寻求慰藉:“但突然间,在她脑海的边缘,宗教出现了,可怜、矮小又健谈的基督教,她知道所有那些诸如‘要有光’和‘成了’的神谕,最后只是变成了一声‘嘣’”。[6](P139)光在西方世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英文中的“启蒙”一词就与光有关,代表的是知识和理性。“要有光”一句源出于《圣经》的开篇《创世纪》,暗示了以基督教为信仰的西方国家对理性的推崇。神谕化为了一声“嘣”,说明马拉巴洞穴的神秘超出了穆尔太太依靠宗教和理性所能理解的范畴。反观古德博,他在洞穴内安然无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印度教的参悟。从他所说的那句“然而不在场暗示了存在,不在场并非不存在”即可看出[6](P167),印度教具有“空”和形而上的特点。崇尚理性和实证主义的穆尔太太虽然对神秘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但与此同时她也直言:“我不喜欢混沌。”[6](P63)在没有光和理性的指引下,一片漆黑的洞穴使其陷入了一种与非理性抗衡的恐惧之中。
这种非理性便是福柯所指涉的歇斯底里在精神方面的重要表现,其特征是出现了“错误和幻象,即盲目”[5](P158)。马拉巴之行后,穆尔太太陷入了即将生病的幻觉之中,随后在与罗尼争论时歇斯底里开始发作,“变得异常急躁,显得相当不雅”;她抱怨道:“为什么就不能以我的方式做这做那,把它们做完之后,好让我安静一下?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做,我真的搞不明白。”[6](P189-190)从穆尔太太的上述话语和行为举止中不难看出,她缺乏自主权,以一种边缘化的身份被束缚于传统的家庭空间里。在印度旅行期间,她曾多次提到远在英国的拉尔夫和斯黛拉——罗尼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甚至还曾“梦到这两个鲜少被人提及、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6](P86)。穆尔太太一直将家庭作为她的生活重心,即便是身处印度这个能以外来者的身份探索未知的国度,她也依然受制于家庭这个封闭式的结构。作为慈母的她是十八世纪英国女性的“忧郁戏仿”,随后其歇斯底里的爆发反映了女性“在国家空间里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抵抗”[9](P219)。若从小说中找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形容穆尔太太的这种身份,那么最为妥帖的词语想必是martyr——用以描述她在男权社会下的受难者形象。事实上,martyr一词是福斯特用来指称罗尼的殉道者身份,讽喻罗尼承受了大英帝国的“所有罪恶”[6](P174),最后却沦为了政治牺牲品。从某种程度上讲,穆尔太太亦是一位殉道者,她是维系东西方的象征和纽带,与福斯特笔下诸多小说的共同主题——联结(connect)——相契合。穆尔太太不辞旅途困顿来到印度,在完成了行善的使命后,最终病逝于返回英国的轮船上。
如若说穆尔太太在洞穴之旅后歇斯底里的反应是对当下无力决定个人生活的愤然抵抗,那么阿黛拉在洞穴中的顿悟则是对未来家庭生活的忧虑与抗拒。中空和凹陷的马拉巴洞穴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性指征,在这个封闭和魆黑的空间里,阿黛拉通过阿齐兹这一东方男性认识到自己缺乏女性魅力。她攀登着一块看起来像“倒扣的茶碟”那样的岩石,突然意识到她与罗尼之间缺乏一个“立足点”[6](P142),而这一立足点便是爱情。形如倒扣之碟的岩石象征了爱情和婚姻的错位。当阿黛拉置身于洞穴内,她脑海中闪现的是一幅以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1)本文所引用的小说版本给出了关于Anglo-Indian一词的注释:“《牛津英语词典》引用了《纯正英语学会会刊》(S. P. E. Tract)1934年第41期的解释:‘英裔印度人’这一用语是指那些在英国出生但在印度生活了很久的人。1911年印度政府决定用‘英裔印度人’代替‘欧亚混血儿’(Eurasian),作为对英印混血儿的正式称呼”。参见E. M.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M]. ed. Oliver Stallybras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nkaj Mishr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p. 345.的身份在殖民地生活的前景,这与她此番印度之行的初衷遥相呼应。阿黛拉来印度的目的并非是想更好地了解未婚夫罗尼,而是出于她对未来婚姻的疑虑,即是否能适应英裔印度人的新身份。她想先体验一下殖民地的生活,再决定是否与罗尼结婚,而这种体验的方式无疑需要当地印度人的参与。与排他性的英国俱乐部里上演的戏剧《凯特表妹》不同,菲尔丁的茶会邀请了印度教徒古德博、穆斯林阿齐兹以及英国人穆尔太太和阿黛拉,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而非中产阶级的”私人聚会[10](P137)。罗尼的擅自闯入打破了这种友好的气氛,其粗鲁的举止和干涉阿黛拉社交自由的做法,既体现了他本人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缺乏自主性的社会现实。
罗尼的上述所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罗斯金(John Ruskin)的主张遥相呼应。罗斯金将男性定义为“践行者、创造者、发现者和防御者”,认为其职责是开拓外部世界,而女性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待在家中可使其“免受危险和诱惑”[11](P77)。家庭空间在保护女性的同时,也使其束缚于传统的家庭生活,与社会隔绝开来。身为白人的阿黛拉一直渴望认识一个真实的印度,但罗尼却反对她与印度人来往。从表面上看,罗尼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未婚妻安全的担忧,但实际上,他在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画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剥夺了阿黛拉想要认识印度社会的欲望,试图将她束缚在白人的社交圈内。此种行径“呼应了当地女性的深闺制度与白人女性的种族隔离这二者之间的对等关系”[12](P298)。在深闺制度下,女性除了不能随意抛头露面外,还需用面纱和衣服遮住脸和身体,以免被陌生男性窥视。如此一来,她们的社交圈和活动范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倘若阿黛拉嫁给罗尼,英裔印度人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使其面临与恪守深闺习俗的当地女性相似的命运,其区别在于,她要避免接触的对象不仅仅是男性,而是印度人这一更为广大的群体。她对婚姻的排斥,一方面说明她对自我情感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对种族主义下个人自主权被剥夺的强烈不满。
与穆尔太太一样,阿黛拉也在参观完马拉巴洞穴后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导致其情绪失控的既有精神创伤这一外因,更有自主性缺失这一内因。小说描述,躺在病床上的阿黛拉处于一种情绪崩溃的状态:“没有人理解她的困苦,也没有人知道为何她一会儿冷静得出奇,一会儿又变得歇斯底里”[6](P182)。然而,更多关于阿黛拉情绪无常、歇斯底里的描述其实见于她与穆尔太太和罗尼的争吵中:“阿黛拉喊道,伸手又去握[穆尔太太的]手”[6](P189);“这个可怜的姑娘又哭了起来”[6](P190);“当他[罗尼]回来时,她处于一种神经质的危机之中,不过换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她紧紧抓住他,啜泣道:‘帮我做我该做的吧。阿齐兹是个好人’”[6](P191)。在围绕阿齐兹一事的争吵中,穆尔太太和阿黛拉都觉得阿齐兹应该是无辜的,唯有罗尼固执地坚称阿齐兹是有罪之身。罗尼的此种做法看似是在给予阿黛拉鼓励,让她相信自己的直觉,但实则是把个人意志强加到阿黛拉身上,使这位弱女子代行他在印度惩恶扬善的使命。最终,在罗尼的厉声呵斥下——“我刚才是怎么警告你来着?你明明知道你是对的”——阿黛拉在大英帝国的代理人罗尼的说服下“开动了司法机器”[6](P193-194)。由此可见,阿黛拉实际上被剥夺了自我决定的权力,她将阿齐兹告上法庭的做法明面上是其个人行为,但其背后体现了像罗尼这种代表了国家意志的帝国代理人的蛮横与种族歧视。在与罗尼争论的过程中,阿黛拉的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前说明她在试图抵抗英裔印度人的新身份。此前,在谈到嫁给罗尼之后的身份转变时,阿黛拉说道:“我躲不开这个标签”,“有些女人对待印度人实在是太吝啬、太势利了,要是我变得跟她们一样,我定会措颜无地。”[6](P135)小说中诸如特顿太太和卡伦德这样的女性的确为人恶劣,且在随后的阿齐兹审判案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黛拉在起诉一事上犹犹豫豫,想必是不愿与其为伍。因此,归根结底,她并非种族主义者,真正发动这场种族主义攻势的实乃以罗尼为代表的白人男性群体。在论及印度社会的种族问题时,戴维迪斯(Maria M. Davidis)认为,白人男性对待印度人的态度颇为恶劣,“但大多数因残忍而受的指责却落在了女性头上,这些女性常常被看作是把两个种族的男性分开的推手”。[13](P264)
由此观之,穆尔太太和阿黛拉歇斯底里的爆发集中反映了个人自主权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也折射出福斯特对现代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其实,早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 1910)一书中,他就通过施莱格姐妹触及了由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所引发的生存危机。与姐姐玛格丽特相比,妹妹海伦更像是福斯特眼中的自由主义者,她跨越社会阶级的差异,与下层人物巴斯特恋爱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小说以巴斯特被杀收场,暗示海伦将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并将维持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相较之下,《印度之行》呈现的不仅是一种生存危机,更是一种由种族主义所引发的人道危机。对于阿黛拉这么一介弱女子而言,卷入种族主义争端的后果显然是其无法承受的。她选择离开印度这块政治是非之地,可能是一种逃避的消极表现,但却是其过上独立生活的前提。虽然我们无从知晓阿黛拉的最终去向,只知她将投身于自己的事业中去,但不难猜测,她很有可能会像海伦一样过着不婚的生活,选择做一位自由主义者以维持个人独立性。
二、失去主权的印度家园:清真寺与伊斯兰怀旧情绪
福斯特以“清真寺”开篇,一来是反映了主人公阿齐兹的穆斯林身份,二来是契合了殖民地印度的现实状况。纵观历史,伊斯兰教曾一度横扫印度次大陆,及至莫卧儿帝国时期(Mughal Empire),其势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然而,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曾经盛极一时的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穆斯林也从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沦为了殖民地的被统治阶级。赛义德(Edward Said)从西方视角回溯了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所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世界对伊斯兰教进行描述,将其限定在“东方舞台”,这种以欧洲为中心、以伊斯兰教为对象的表征方式是欧洲“控制令人畏惧的东方”的重要手段。[14](P60,P66)在小说《印度之行》中,福斯特一反伊斯兰教极富倾略性的形象,刻画了一个闯入清真寺的基督徒穆尔太太。这位英国女性脱鞋进入清真寺的举动,表明她希望“用一种被道德规范所禁止的方式建立友谊”。[15](P202)在清真寺的穹顶下,阿齐兹和穆尔太太这两位来自不同宗教和国度的信徒相遇和交谈,暗示了东西方在文化身份上的平等地位。因此,清真寺实际上代表了“福斯特所渴望的某种平等、半私人化和跨文化的空间”。[16](P49)
于阿齐兹而言,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是他政治抱负与精神理想的家园。在西方的殖民入侵下,曾经雄踞一方、维持了百余年统治的莫卧儿帝国不复存在,穆斯林的身份优越感也就此荡然无存。阿齐兹怀旧的对象正是昔日辉煌灿烂、能给他带来家园归属感的伊斯兰王国。英文中的“怀旧”一词nostalgia最早出现于十七世纪,由一位名叫约翰尼斯·霍夫(Johannes Hofer)的瑞士医生所创:“因为没有拉丁名,我就称这种病为nostalgia(源于nostos: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及algos:痛苦或悲伤)”[17](P341)。因此,nostalgia最初是用以描述一种思乡之情。然而,到了20世纪初,该词“表示的是一种短暂而非使人精神衰弱的‘遗憾或是伤感的回忆,或是对昔日的回想’”[18](P1)。阿齐兹喜欢吟诗,“他所偏爱的主题是伊斯兰教的衰微和爱情的短暂”,当他吟诵时,“印度似乎归于一体,成了他们自己的印度,他们重新获得了逝去的荣光”[6](P12-13)。此处,阿齐兹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既有对昔日伊斯兰王国的怀旧,也有对遭受侵略、被剥夺了自治权的印度家园的感伤。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沦为了没有独立主权的殖民地,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园。
《印度之行》中的清真寺与福斯特另一部小说中的霍华兹庄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霍华德庄园》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了“英国状况” (Condition of England)的小说,其故事背景发生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霍华德庄园在承受工业文明的冲击时,见证了“旧英国——乡村、封建社会组织和传统价值——与新英国——郊区、城镇化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1](P51)。福斯特称自己为“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的遗老”,高歌“仁义与乐善好施”[19](P54),这种固守传统价值的怀旧情结从他对朴实纯洁的施莱格姐妹继承霍华德庄园的刻画上可见一斑。与霍华德庄园类似,《印度之行》中的清真寺亦连接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昔日的莫卧儿帝国和殖民后期的大英帝国。清真寺既指向了阿齐兹所向往的伊斯兰王国,也见证了印度逐渐沦为殖民地、丧失独立主权的整个过程。它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文化符号,在排他性的英国俱乐部面前,它是印度穆斯林唯一可以不受阻碍、随便出入的场所。但正因如此,清真寺带有种族和阶级的烙印,受到罗尼等帝国代理人的歧视。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和英裔印度人,罗尼主张宗教要为大英帝国服务。他因自己的母亲擅自前往清真寺而心生愤怒,从中流露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帝国主义思想。与穆斯林阿齐兹对基督徒穆尔太太的接纳不同,罗尼排斥了清真寺的宗教属性,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西方人不得进入的政治禁区。他对穆尔太太的训斥,看似是出于对母亲安全的担忧,实则是一种政治关切,意在提醒她注意自己的白人身份。
阿齐兹经常造访清真寺的原因在于,他可以借助想象来重温昔日的伊斯兰王国,在精神上抵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清真寺这个半私人化的空间里,强烈的怀旧情绪油然而生,他渴望“北方的姊妹王国——阿拉伯半岛、波斯、费尔干纳和土耳其斯坦”[6](P96)。这种对伊斯兰王国的憧憬和想象使他的“内心被泛伊斯兰情绪和昔日伊斯兰文化的光辉所感动”[20](P10),也得以使其暂时摆脱身为英国臣民的劣等感。此时,阿齐兹尚未将重建伊斯兰王国编织进人生蓝图中,对政治所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一边对英国人的存在表示习以为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出了名的滑稽之人”[6](P49),另一边又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感不满。值得注意的是,阿齐兹对政治的不闻不问恰恰体现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在对窃听一事的看法上,他与罗尼不谋而合,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说明他对被殖民的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印度社会的现状来看,他这种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事实上,这种政治态度是20世纪初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其时,仅有少数穆斯林持民族独立的激进主张,大多数虽不满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
不难看出,阿齐兹这一人物有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他对泛伊斯兰文化的憧憬和对印度的民族未来仅仅建立在主观感受、而非实际行动之上,这与务实派的代表哈米杜拉大相径庭。与阿齐兹一样,哈米杜拉也是一位穆斯林,不同之处在于,他积极参加由不同宗教信徒所组成的委员会,对印度的未来有着更为理性和现实的认识。关于这个委员会,小说如是描述道:“印度教徒、穆斯林、两位锡克教徒、两位祅教徒、一位耆那教徒和一位本地的基督徒努力超越门户之见,对彼此多一些好感”[6](P97)。这说明,在民族独立面前,宗教分歧让位于政治矛盾,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教徒实现了暂时的和解。这一卓有成效的宗教联合影射了20世纪20年代由印度穆斯林所发起的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 Movement)。在当时的印度社会,它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 Movement)一起将民族独立的情绪推向高潮,并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架起了合作的桥梁。小说在第三十章的开头写道:“这场审判在当地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达成了谅解”[6](P251),这一情节指涉了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基拉法特运动。
经历过不公的司法审判案后,阿齐兹不再怀有空想伊斯兰王国的怀旧情绪,意识到只有当印度“成为一个国家,她的子民才会受到尊重”。[6](P253)他将国家自治与个人自尊直接挂钩,指出民族独立对社会公正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阿齐兹意识到,他的受害者身份直接源于英国的殖民统治。正如哈米杜拉所言:“像你这样的灾难迟早会发生。”[6](P253)对英国统治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阿齐兹转变为了一个试图解放印度、愿意在宗教立场上做出妥协的民族主义者:“我们需要一个国王,哈米杜拉,这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实际上,我们必须努力欣赏这些奇怪的印度教徒”。[6](P253)从“奇怪”二字可以看出,阿齐兹对印度教徒是持一种讽刺和轻蔑的态度。然而,“努力欣赏”则表明他试图达成和解、转变宗教立场的决心。在印度社会,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仅在宗教上相互对立,在统治权上也有根本性的矛盾。回溯印度历史,可以说宗教政权即王朝本身。比如曾经盛极一时的莫卧儿帝国,它系伊斯兰政权,而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自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此前,身为穆斯林的阿齐兹坚持伊斯兰王国的正统性,对其他宗教嗤之以鼻。然而,在司法审判之后,他抛弃了仅靠怀旧来重建伊斯兰王国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在宗教立场上也做出了妥协:“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所有人都会结成一体”。[6](P306)
阿齐兹从伊斯兰王国的空想者转变为行胜于言的民族解放者,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转变是民族独立运动中的积极姿态,反映了整个印度社会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变化。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随着一战和基拉法特运动的相继爆发,种族主义的情绪在印度社会弥漫开来,印度人对国家自治的诉求已然非常激烈,与英国政府的关系也已经走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
三、印度的自治前景:跨国友谊与福斯特价值观的演变
小说《印度之行》见证了福斯特帝国主义价值观的演变。他最初创作该小说的目的是表达对印度人民的同情,弥合东西方之间的隔阂。然而,在第二次印度之行中,他看到了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当地印度人对英国人的冷漠姿态。福斯特的两次印度之行前后相隔将近十年,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时间可谓恍如隔世,中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姆利则惨案(Amritsar Massacre)和基拉法特运动。战争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下的种族暴力使福斯特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他所寄予厚望的仁慈(goodness)与善意(kindness)终究难以维系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两个民族间自发性的交往”已经越来越不可能。[21](P243)
梅德里(David Medalie)指出,从时间跨度上讲,“洞穴”的后半部分内容呼应了福斯特的第二次印度之行。[22](P161)在第一部分“清真寺”中,小说的总体基调积极而明快。但到了第二部分“洞穴”,分水岭开始显现,小说所营造的整体气氛从神秘主义开始过渡到犬儒主义,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穆斯林对大英帝国的愤怒与敌意。这种笔调上的突转,与20世纪初印度不断高涨的独立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9年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随后又爆发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此,小说有诸多含沙射影的描述,如第二十章,税务官特顿先生“想要鞭打每一位他所看到的印度人”[6](P172),影射了阿姆利则惨案中雷金纳德·戴尔将军(Reginald Dyer)对印度人施以鞭刑、为一位名叫玛塞拉·舍伍德(Marcella Sherwood)的英国女传教士复仇的事件。又如第二十四章,特顿太太说“只要看到英国女人,他们应该跪在地上,用手和膝盖从这里爬到山洞”[6](P204),此处涉及的历史事件是戴尔将军要求印度人像跪拜神一样向传教士舍伍德进行跪拜。福斯特于1921年重访印度,在那里他看到了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同时也注意到了印度人对待英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曾一度受苦,在羞愧和怨恨中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我们的俱乐部之外。他敏感而亲切,一向尊重权威……如今,他已不再受苦。他学会了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要么以他自己的方式,要么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他在痛苦中编织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当他继续编织时,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质地就不那么好奇了。[21](P243-244)
福斯特第一次访问印度时,“仍然支持那些试图将自由的美德带到印度的[英国]人,可以体现这点的是,他当时在火车上对亲眼目睹的种族和谐予以了热情的回应”。[22](P29)与“自由的美德”相呼应的改革措施的确在印度有所推行,例如1909年通过的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s)和1919年实行的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前者允许一部分印度精英进入政府和立法机构参与决策,后者则是赋予印度人有限的自治权,让他们自行管理地方事务。福斯特最初对大英帝国的改革是持支持的态度,他希望英国能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这一点从他对罗尼的刻画中可见一斑:“要知道,我来这儿是工作的,是用暴力来控制这个令人厌恶的国家。”[6](P45)在这一阶段,福斯特更多的是“谴责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做法,而非英帝国主义这一思想”。[22](P26)然而,在第二次印度之行中,他看到了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此背景下,福斯特意识到,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英属印度政府所推动的有限自治的改革。小说中的阿齐兹说道:只要“英国人还嘲笑我们的皮肤”,“这些改革又有何用呢”[6](P107)。此处所说的改革影射了上述莫莱—明托改革和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在说到改革前,他反复提及“善意”(kindness)二字。这即是说,改革应该建立在英国人善待印度人的基础之上,在一个充斥着种族主义和流血冲突的殖民社会,改革只是杯水车薪,无助于实现印度的自治。
福斯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粗暴行为,一度希望借仁慈来改善英国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福斯特对帝国主义仍存有幻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于我而言,人际关系意味着一切。”[21](P318)他对英国治下暴力横行深感失望的同时,塑造了一位心怀善念、维系东西方联结的女性人物穆尔太太,以缓和小说阴郁的色调。阿齐兹初见穆尔太太,就称她是东方人:“你理解我,你知道我的感受。要是别人也像你一样该多好啊”[6](P20)。不难看出,阿齐兹欣赏穆尔太太的同理心,他希望别人在给予印度人善意的同时,也能理解他们对殖民现状的不满。反观菲尔丁,这位英国人虽然心地善良,重情重义,但内心却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他坦言自己来印度的目的是“需要一份[教育]工作”,认为“英国占领印度是为了她[印度]好”[6](P106)。在司法审判案一事发生后,菲尔丁“后悔了选边站”,因为他“今后将被人称为‘反英分子’和‘煽动叛国’——这样的用词让他感到厌烦”[6](P164)。实际上,抛开帝国主义的立场不谈,菲尔丁称得上是完美的化身,他的重情重义甚至连穆尔太太都望尘莫及。他与阿齐兹一度是莫逆之交,此前甚至还看过阿齐兹妻子(一位恪守深闺习俗的穆斯林女子)的照片。福斯特在突显菲尔丁善良公正的美德时,特意渲染了这一人物秘而不宣的帝国主义立场,为小说最后跨国友谊的破裂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与持保守见解、主张维持英国殖民统治的菲尔丁相比,阿齐兹的政治立场颇为激进,他希望菲尔丁“屈服于东方”[6](P246),承认印度有朝一日将会实现国家自治。菲尔丁对阿齐兹怀有民族独立的想法嗤之以鼻,讥讽地问道:“你要用谁代替英国人?日本人吗?”阿齐兹激动地回答说:“不,是阿富汗人。我自己的祖先”。[6](P305-306)由此可见,两人其实都是种族主义者,区别在于,阿齐兹排斥了跨国友谊的可能性,他认识到民族独立和国家自治是跨国友谊的基础,当前两人尚做不了朋友。在菲尔丁这方,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想未能使其认识到,他与阿齐兹之间的隔阂已经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在印度实现独立之前,两人的友谊无法得以维系。
小说通过菲尔丁与阿齐兹的跨国友谊揭示了隐藏在民族主义的幕帘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这段友谊的破裂归根结底是由种族矛盾引起的,它表明仁慈和善意尚不足以在殖民时代维系一段跨国友谊。福斯特虽然肯定善意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但他进一步指出:“善意是不够的。我很痛心地认识到了这点。实际上,善意在当下毫无用处可言。人们立即对它表示嘲讽。能起到一点影响的唯有关爱,或者说有一丝关爱的可能性。”[21](P322-323)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殖民地印度,像阿齐兹这样的有色人士并不受人待见,他在法庭上所受的指控便是言之凿凿的证据。即使阿齐兹不要求阿黛拉支付赔偿金,他也依然无法摆脱英国人的种族偏见。福斯特让阿齐兹原谅阿黛拉,一方面体现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践行了他对人际关系的主张。毋庸置疑,善良并不等同于友谊,阿齐兹与阿黛拉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来自殖民地,渴望民族独立,后者来自宗主国,对印度的兴趣是对殖民地本身,而不是对印度人。正如菲尔丁对阿黛拉的那番话所示:“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就想着要去看看印度,而不是印度人,我那时就意识到:啊,我们是没法融入这里的”[6](P245)。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身份差异导致阿齐兹与阿黛拉无法成为朋友。
《印度之行》乍看之下是一部缺乏英国性(Englishness)的作品,描述的无外乎是殖民地印度的人情风貌。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其英国性与印度的民族性相互交织,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在福斯特对跨国友谊的刻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最后,阿齐兹与菲尔丁各奔东西的结局暗示了印度的自治前景,与此同时也折射出福斯特对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菲尔丁前后两次用了“流沙”一词表达了他内心的忧虑:“公正永远无法满足他们[印度人]——这就是为何大英帝国建立在流沙之上”[6](P245);“我们的一切都建立在流沙之上;这个国家越现代,崩塌得就越惨烈”[7](P260)。菲尔丁担心的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根基像沙子一样不够稳固,因此其出发点始终是在英国这边,脑海中从未闪现过印度将会实现独立的念头,他坚持认为“大英帝国不能因为统治残暴就被废除”[6](P305)。福斯特让阿齐兹和菲尔丁就此别过,表明改良式的自由主义在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以破产告终。实际上,在战前的手稿中,福斯特仍然相信“自由的共识和妥协”这一治世良方,但在最终付梓的版本中,他借菲尔丁之口“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无能为力”[22](P27)。与穆尔太太一样,重情重义的菲尔丁也体现了善的美德,是福斯特希望弥合东西方隔阂的一个重要纽带。但即便如此,他最终仍然与阿齐兹分道扬镳。二者孰是孰非,小说的基调并不明朗,但结尾那段拟人化的描述可谓是意味深长,苍穹用“不,还做不了朋友”来回应万物齐声发出的“不,还不是时候”[6](P306)。这句话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是阿齐兹内心的真实写照,表明这段跨国友谊的根基在于国家而非个人,其发展历程——从升温到降温再到最终的破裂——从很大程度上已经昭示了个人关系尚不足以构建民族主体性。“还不”二字在指明阿齐兹与菲尔丁眼下无法成为朋友的同时,也暗示了福斯特对英印两国的未来给予了深切的思考。
实际上,在第二次印度之行中,福斯特从印度人对民族独立的追求中预见了大英帝国的衰落,他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首先,相比于十年前,负责任的英国人对印度人已经友善很多了,但这为时已晚,因为印度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社会支持;其次,在历史上,粗鲁的行为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帝国的解体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21](P246)。经历了英属印度政府长期的压迫以及阿姆利则惨案的暴力镇压后,印度社会要求改变殖民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时过境迁的变化中,福斯特在价值观上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彻底决裂,他意识到了帝国统治下自由和改良的无用,仁慈和善意终究无法解决根本性的种族矛盾,印度人真正想要的是印度的独立与自治。
四、结语
从“自治”的角度考察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从中不难窥见他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这种关怀既指向个人,也指向国家这一主体。福斯特首次将英国女性置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细致刻画了她们在殖民地的生存现状,放大了男权统治下女性缺乏自主权的受害者身份。除了英国女性之外,更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深受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正如小说中的菲尔丁所言:“当印度不再是任何人的印度时,你们就无法写‘印度,我的印度啊’这样的爱国诗了”[6](P261)。为了让印度重新成为印度人的印度,福斯特对印度自治的前景做了深刻的思考,将矛头对准了大英帝国和英裔印度人。从艺术层面上讲,他在小说中牺牲了那段弥足珍贵的跨国友谊,此外在人物塑造上对印度人有明显偏袒。正因如此,有印度读者在采访中对福斯特说:“你对其中一方(英国人)是不公平的。”[20](P15)
让我们重新回到施瓦茨对福斯特那句中肯的评价上:“福斯特的(价值观)在逐步发展。”在《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一文中,福斯特坦言其“并不相信信仰”,但他认为在一个穷兵黩武的战乱年代,“人必须要订立自己的信条”[19](P65)。20世纪前半叶,历史风起云涌,整个世界处于战乱之中。经历过一战后,福斯特显然认识到了单纯以善来拯救世界的苍白无力。他在《印度之行》中试图借穆尔太太和重情重义的菲尔丁在英印两国之间嫁接一座友善的桥梁。然而,这座桥梁终究未能横亘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小说以跨国友谊的破裂收场,意味着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必须与以菲尔丁为代表的英国分道扬镳。菲尔丁一厢情愿的自问自答“为何我们现在做不了朋友”,“这是我想要的。这也是你想要的”[6](P306),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福斯特在战前关于英国统治与印度的殖民现状可以共存的看法,而阿齐兹的断然拒绝则反映了福斯特对此前这一想法的摒弃,暗示印度将会实现国家独立和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尔丁和阿齐兹两人就此别过的结局折射出福斯特与帝国主义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