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贸易与“中国根”
——菝葜类中草药在欧洲的传播和重定义*
2021-12-29颜宜葳
颜宜葳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16世纪对于欧洲人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通过海上的长途贸易线路,物品、知识与人口开始了全球流动,原来局限一隅的流行病跨越洲际传播。[1]欧洲探险者带到美洲的天花和结核灭绝了美洲大陆上整族整族的人口,非洲的疟疾和黄热病也让欧洲军队损失惨重。[2]此时距离黑死病首次横扫欧洲大陆已经一百多年,但鼠疫的威胁并未消退,法国和西班牙为争夺那不勒斯统治权进行的战争又把一种当时称为“高卢病”、现在看来可能是性病性梅毒的传染病在欧洲散播开来。[1,3]面对新病的威胁,来自海外的新奇药物成为欧洲医生和药剂师积极求索的对象。
随着这一波输入殊方异药的热潮,一种名为“中国根”(China root)的新药从16世纪中期开始贩运到欧洲。这种药的名字此时也开始出现在波斯和印度的医学文献中。[注]菝葜类药材在16世纪开始以“Chopachini”等若干名称出现在阿输吠陀医学文献中,见文末参考文献[4- 5];开始输入波斯的时间仍有争议,但至少1540年已有波斯作者在文中对此进行讨论,见文献[4]。称雄海上的葡萄牙王国把它的贸易网络延伸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奔波于两地间的欧洲商人们对于寻找亚洲的药物和验方很是热心,这既是为了因应欧洲疾病的新形势,也是牟利的一条通途。“中国根”(或泛称为菝葜类药材,理由详见本文第3节)在16—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一直是欧洲进口香药类货物的一个大宗,为商人们带去了可观的利润,至18世纪中期才基本从欧洲几家东印度公司的货物清单中消失。[6,7]
2018年笔者在上海大学参加“全球视野下的医疗与社会:历史中的食、药与健康知识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提交本文的第一稿[8],当时从下文将介绍的同样4种16世纪欧洲文献出发,重点讨论了“中国根”的来源植物及其介绍到欧洲的过程。当写作该篇会议论文时,感觉到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以国外和港台学者居多[4,6,7,9,10]。不意此后不久,中国根的问题开始吸引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学者的兴趣,2019年有李庆博士的长文发表[11],其中关于中国根流传到海外的过程以及当时著名医生对此药的记述方面,恰巧也参照了笔者用过的欧洲古籍和一些当代的英文研究文献,文章后半部分又梳理了中国根输入到欧洲以外国家的线索,对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覆盖地区的交易情况记述尤详,时间段也下延直到17世纪。至此,笔者在2018年的文章中有关中国根初次外传过程的描述有一些已属冗言,故本文尽量删减了第一稿中的相关内容。
不过,中国根远销海外的缘由,毕竟是因为它最初被人当作对抗新疾病的有效药物,它在中国和欧洲医学体系里的定位是它的重要属性;作为一味中草药,它的来源植物及鉴别标准在当时和今天都是医家时时关心的问题。成为中国根来源的几种药用植物,今天的中医仍然在使用,人们已经利用现代医学科学的手段对它们的药效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那么,当年广受推崇的这一大类草药治疗梅毒的实际效用究竟如何?当时的欧洲医生和中国医生基于实际诊疗经验,会不会对它们做出与贸易商不同的评价?本文仍然准备从第一稿使用过的几份16世纪欧洲记载出发,在医学史和疾病史的大背景下回顾中国根传播到欧洲的缘由,结合中医学和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其来源植物的种属,认识它在中国本土原初的使用方式,同时,借助国外的医学史研究提供的背景知识,进一步讨论它初次传出域外时,欧洲医学界如何及为何赋予它新的定位。
1 知识流动渠道中的“中国根”
16世纪的欧洲人已经掌握了印刷术,它成了传播新知识最方便的手段。在欧洲的出版业中心城市刊行的不仅有大部头的著作和游记,也有以实用为务的单行本,其中医学小册子为数尤多,而且它们常常抛开了作为学术通用语的拉丁文,而用各国的民族语言写成。[12,13]有几种作品因率先介绍了欧洲人在海外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新事物和获取的新知识,而成为世人所重的经典,它们均译成过数种欧洲语言,又叠经再版和重印。迄于今日,历史研究者围绕其文本进行的开掘仍未停止,有的书在本世纪又有新译本面世。
在这一类16世纪医学单行本里,有4种以较大篇幅谈到过“中国根”的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管窥问题的起点。一是比利时医生、现代解剖学之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的《中国根书简》(EpistolarationemmodumquepropinandiradicesChynaededocti,1546年拉丁文初版,本文使用2015年英译本);二是葡萄牙医生奥尔塔(Garcia da Orta,1501/1502—1568)的《印度香药谈》(Colóquiosdossimplesedrogashecousasmedicinaisdandia,1563年葡萄牙文初版,本文使用1913年英译本);第三本是西班牙医生兼商人莫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c. 1493—1588)的《新世界佳音》(PrimeraysegundaytercerapartesdelahistoriamedicinaldelascosasquesetraendenuestrasIndiasoccidentales,quesirvenenmedicina,1565—1571年西班牙文初版,本文使用1577年英译本);最后一本是荷兰商人、探险家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2/1563—1611)的《东印度水路志》(Itinerario:VoyageofteSchipvaert,vanIanHughenvanLinschotennaerOostoftePortugaelsIndien,1596年荷兰文初版,本文使用1598年英译本)。
1546年时,维萨里驻留在威尼斯。他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宫廷医生之一。此前,他已经从意大利的帕多瓦(Padua)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又曾在帕多瓦大学、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比萨(Pisa)大学任教,始终身处欧洲正统医学的主流与核心。1543年维萨里划时代的著作《人体之构造》(DeHumaniCorporisFabrica)出版后,招致许多人尤其解剖学泰斗西尔维厄斯(Jacobus Sylvius, 1478—1555)的激烈抨击。维萨里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并进一步阐发他的解剖学新理论,利用约12周的空闲时间匆忙撰成《中国根书简》一书。此书表面上采用当时最风行的草药验方集的形式,选择了彼时在欧洲被誉为万应灵药的中国根作为主题,但全书仅前面一小部分涉及中国根,绝大部分是维萨里阐发自己解剖学理论的内容。维萨里对此书的包装非常成功,它在出版当年再版两次,而其中的中国根部分还在1548年单独印行了一个德文本。2015年的英译者尽量把维萨里晦涩的拉丁文改写成了比较通畅的英文,并对原书所涉故实进行了大量的考订。([14],xvii-xxvii页)
奥尔塔虽然也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但一直生活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拜葡萄牙的航海贸易之赐,才找到避难的栖身处所。他生于葡萄牙一个改宗基督教的犹太家庭,曾在葡萄牙行医,并在里斯本(Lisboa)大学教授医学。为躲避宗教裁判所对改宗犹太人的残酷迫害,1543年移居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Goa),担任殖民当局前后几任总督以及当地古吉拉特苏丹国国王的私人医生。期间也曾随军出征,到过印度西南沿海的几个城镇,还有斯里兰卡,最后在果阿居住至1568年终老。奥尔塔在果阿不仅勉力研究当地医药,还开辟了草药园种植他搜求到的新植物。1563年,他将汇集自己东方医药知识的著作《印度香药谈》[15]在果阿印行,据说这是在亚洲以欧洲文字印刷出版的第2部书籍。[注]据英译者Clements R. Markham所撰导言。见:[15],vii- xvi页(Introduction)。《印度香药谈》初版标题为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he cousas medicinais da ndia e assi frutas achadas nella onde se tratam cousas tocantes a medicina, pratica, e outras cousas boas pera saber. (Goa: João de Endem,1563)。《印度香药谈》原书以对话体写成,共分59章,记述了80多种印度及远东药物。第47章介绍“中国根”(RaizdaChina)(图1)。奥尔塔对这味药物有第一手的经验,是他最早把这种药介绍给在果阿的欧洲人的,他本人还用这味药给人治过病。中国根的介绍在书中占据了对开本好几页的篇幅。原书为葡萄牙文,流传不广,比利时学者克鲁修斯(Clusius 或Charles de L’Ecluse,1526—1609)节录其主要内容改写成叙事体的拉丁文,1567年在安特卫普出版。该拉丁文编译本风行欧洲,据此译出的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本接踵而至。[16- 18]葡萄牙文原书初版时排印错误很多,各家译本又多删节,直至1891及1895两年,葡萄牙学者菲卡略(Count de Ficalho)经过仔细校勘和考订,重新出版了《印度香药谈》的葡萄牙文足本两卷。本文使用的英文本即根据这个菲卡略版本译出。[19- 21]1578年,继奥尔塔之后担任果阿总督私人医生的犹太裔葡萄牙医生阿科斯塔(Cristóbal Acosta,或写作Cristóvão da Costa,约1525—约1594)在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以西班牙文出版了一本同样有关远东药物和植物的著作《东印度药物志》(TractadodelasdrogasymedicinasdelasIndiasorientales,或TreatiseofthedrugsandmedicinesoftheEastIndies)[22]。后人大率以为此书除个别原创之处外,大部分抄录自《印度香药谈》。[17]但是阿科斯塔的书也自有其贡献在,它帮助把《印度香药谈》中汇集的知识传播到了大得多的读者圈子,另外便是为书中的植物增添了46幅绘刻精美的插图,包括中国根的图像。本文所据的《印度香药谈》1913年英译本便将阿科斯塔的插图全数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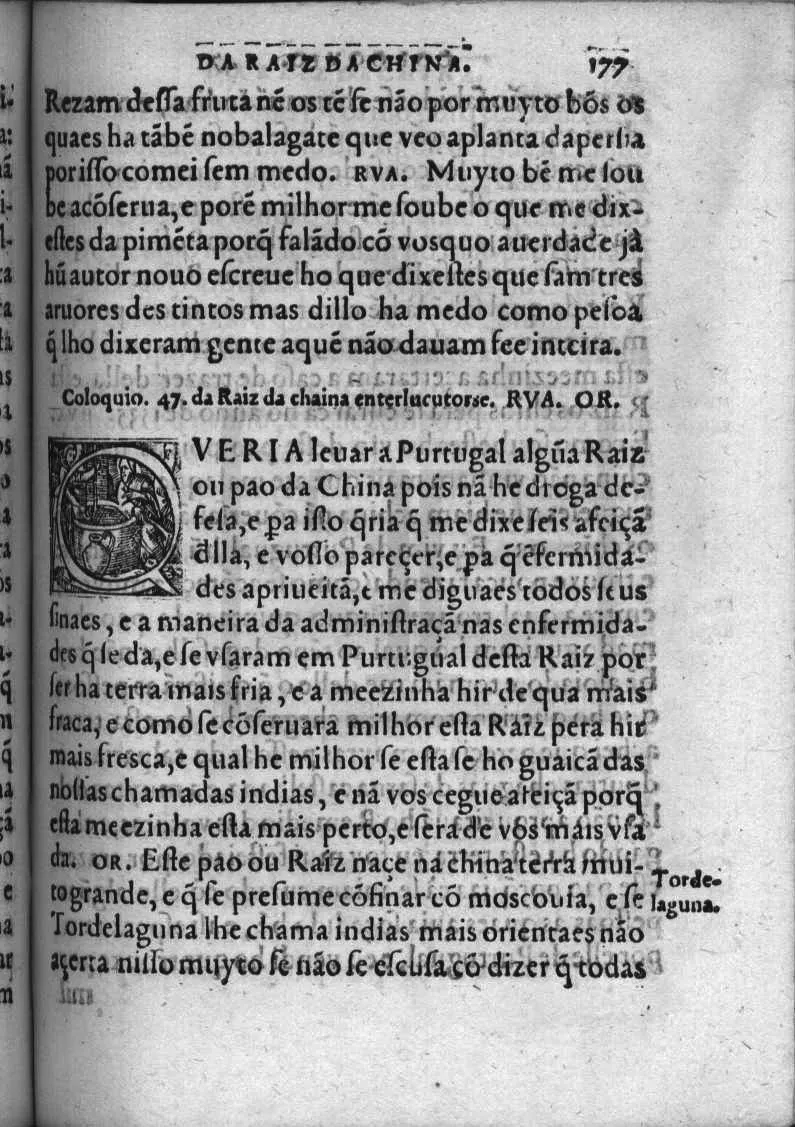
图1 《印度香药谈》1563年葡萄牙文初版中国根的章节([15],177页)
16世纪欧洲的航海贸易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分天下,《新世界佳音》的作者莫纳德斯是西班牙西印度贸易的获利者之一。他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在大学取得过医学博士学位,开业行医后行走于西班牙上流社会,后来又转行经商,通过贩卖美洲药材等货物及贩卖奴隶成为巨富,交游广泛,著述众多。他的《新世界佳音》是欧洲第一本专事介绍美洲药物的本草书,书中讨论了100种左右的美洲药物。西班牙文的书名原意为“来自西印度的诸药物之医学史三卷”,或可译为“西印度药物志”。1577年的英译者给它改成了《新世界佳音》(JoyfullNewesoutoftheNew-FoundWorlde)这个更加耸动闻听的名字,一方面是想向读者宣传书中的药物如何效验,另一方面也是预料到销售这些药材的利润必将十分丰厚。[23]该书分为两部分于1565、1571年出版,1574年将已出部分合为一集刊行。它出版后很快被译成拉丁、意、英、德、法等文字,广为传播,据说前后出现过50多个版本。这本书帮助把莫纳德斯塑造成了16世纪最著名的西班牙医生,尽管他本人从未到过美洲,却成为介绍新大陆药物的权威。《西印度药物志》的拉丁文译者是翻译过《印度香药谈》的同一人克鲁修斯。借着克鲁修斯1574年的拉丁文译本,《西印度药物志》进入了欧洲上层医生的阅读范围。[24]虽是介绍美洲药物,书中也有一大段关于中国根(DelaChina)的介绍,放在愈创木和美洲菝葜的部分之间。([25],26- 29页) 作者说他所谈的中国根确实是产于“东印度的中国”(the China, which is the Orientall Indias),唯因当时已有人准备在“新西班牙”(指美洲)大量种植这种植物并运回西班牙本土出售,故此他把中国根收入这本西印度的药物志。他这样做不足为奇,因《西印度药物志》本来就包含着莫纳德斯为自己经销的药材做广告宣传的用意。
16世纪末,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开始动摇,荷兰和英国挤入竞逐行列。当时的荷兰人刚刚脱离西班牙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新教国家,急于开展远东贸易,因而迫切需要了解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航路与市场,但这些情报被葡萄牙当局严密垄断,旁人无从染指。林索登的《东印度水路志》首次向荷兰人披露了远东航路的地理、经济、文化情况,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开东方财富之门的钥匙。此书一经杀青便大受重视,第二卷因是描述航海路线的部分,甚至被提早到第一卷之前出版,以便荷兰首次远航东方的船队能够携带参考。《东印度水路志》1596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1598年便有德文本和英文本出版,1599年有了拉丁文译本,其后的40年间出现了3个法文译本。[26]林索登的情报得自他本人的东方旅程,他是荷兰港口城市恩克赫伊曾(Enkhuizen)一个旅店店主之子,16岁时离开家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随人经商,几年后靠兄长帮助在新赴任的果阿大主教身边谋得一个秘书职位,1583到1588年在果阿居住了5年。他在果阿的职位使得他有机会接触机密的文件和书信,包括途经果阿的葡萄牙船只带来的航行记录。大主教死后,林索登启程回国,途中遇英国军舰拦截,被迫在原属葡萄牙但其时新被西班牙攫取的亚速尔群岛滞留两年,最终在1592年返回荷兰。林索登的传记作者认为《东印度水路志》第二卷的内容即编辑自林氏滞留亚速尔群岛期间从葡萄牙军官那里获得的航海指南。([27],xv-vii页) 《东印度水路志》全书99章,第49至第87章讲述了亚洲的草木花果及少数动物药和矿物药。现代研究者经过对勘比较,认为林索登书中的植物学知识完全来自对奥尔塔《印度香药谈》的裁剪编排。[28]然而,对比两部书中有关中国根的部分,可以见到内容仍有不少差别。奥尔塔从一个医生的角度,重点介绍用药时应如何根据季节和病情的不同以增减剂量,另外还需施用哪些辅助的治疗手段例如清肠等等。林索登的复述省略了这些方面,多半篇幅放在煎药服药的具体方法以及应如何忌口和禁欲,不过叙述得相当生动,像是曾有亲历亲闻。《东印度水路志》记录的信息多数攸关国家经济命脉,“中国根”出现在这样一本书中,是这一药物当时受重视程度的佐证。而且,林索登的书为不谙拉丁文的荷兰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根的途径,所以也是一份很值得参看的资料。
中国根相关知识的传播迅速而有效。如果我们把研究者描述过的中国中古时期医药知识的流动方式拿来作为对照,就可以看到,写本时代除了少数医学精英掌握的珍贵手抄本外,一般人要到刻有药方的佛教石窟或类似的处所才能接触到正规的医药知识([29],269- 297页)。彼时的药方与石壁一样是静止的,观看者的长途跋涉帮助它向外扩散。而在中国根传入欧洲之时,印刷术带来的便利、大众识字率的提高、学者把学术著作翻译为民族语言的热情,完全改变了药物知识传布的方式、速度和范围。
2 物品流动渠道中的“中国根”:市场需求的作用
中国根最早在欧洲露面是在16世纪的上半叶。目前能够确切知道的年代为1535年,但这并不是它开始输入欧洲的时间,只是那一年奥尔塔在印度初次接触到了这种药材。奥尔塔明确知道这种药生长在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所有地方都有这种那不勒斯病,仁慈的上帝给了他们这种树根作为药方”([15],379页)。说到这里,《印度香药谈》中奥尔塔假设的那个对话者问了他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既然中国船从不越过马六甲,而去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又跟他们言语不通,你是怎么知道这种根的用处的?”奥尔塔对此给出了一段冗长的回答,大致是说,他离开葡萄牙时原本携带了一些愈创木弥补川资,由于果阿有“许多人死于西班牙疥疮(sarnacastellana)的肿痛和各种溃疡”,他的药材到达果阿之后的确售出了高价。但该地的愈创木完全依靠来自欧洲的葡萄牙货船补给,供不应求,恰好这时他的庇护人、果阿总督索萨(Martim Affonso de Sousa)在印度第乌(Diu)认识的一位“非常可敬且富有的人”患“西班牙疥疮”用中国根治愈了,这个富人把中国根的效用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了索萨。中国根售价既廉,服用时忌口的食物又比较少,所以立刻在果阿流行起来,以致后来的葡萄牙货船运来的愈创木没有销路。([15],380页)
林索登也断言中国根进入印度是凭借价格优势,“因为在那[注]指1535年。之前他们不知道它,当时他们治疗大水痘(在印度是常见的病)使用一种愈创木,那是从西班牙的印度运来的,可以说价比黄金。”而自从中国根介绍到印度,“他们再也不用其他的药方了,因为它在该地取之不尽,且是全世界最好的”。([30],107页)
在莫纳德斯的《新世界佳音》中,中国根的部分紧接在另一段篇幅明显更长的文字之后,前面这段介绍的是治疗梅毒的另一种外来药物:愈创木。愈创木是一种生长在南美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木质极为坚硬的常绿乔木,因在建筑业和造船业的特殊用途,其售价本来就居高不下。愈创木一属包括6个种,其中2个种能提取有药效的树脂,今天的制药业仍用愈创木脂作为原料制成检验试剂和消炎止咳的药物。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时期,美洲当地人使用愈创木的树脂治疗类似梅毒的疾病。这个秘方在1508年到1514年间流传到西班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一世(Maximilian I)为了这个药方专门派遣手下人在1517年前往西班牙探听,队伍中的御医波尔(Nicolaus Pol)返回后写出了关于愈创木用法的报告。从此,愈创木的消息在医生和上层人物中间不胫而走。据后来的研究者估计,16世纪前半叶有几十位作者写过介绍文字。当时初显身手的印刷业借着这个商机,刊行翻印与愈创木有关的医学小册子,有的畅销作品两三年内就被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出版业的几个中心城市印行多次。16世纪的百年里,宣传愈创木的医学册子和未刊抄本在欧洲至少出现过两百种,引发的热潮是后来露面的中国根难以望其项背的。影响最著的作品之一,当然是意大利医生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约1478—1553)创作的文辞优美的医学诗《梅毒,或曰高卢病》(SyphilissivemorbusGallicus,1530),现代医学词汇中的“梅毒(syphilis)”一词即来源于这首诗。弗拉卡斯托罗在诗的后半部分极口称赞了愈创木的治疗价值,还介绍了煎制和服用的方法。愈创木成为众人眼中治疗梅毒的神药,被冠以“圣木”(lignumsanctum)的美称。随着时间推移,它还渐渐被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举凡疑难顽症都要用上一用。[31]
愈创木本来就是贵重的木料,成为梅毒特效药以后价格愈发飞涨。由于贩售的利润惊人,西班牙皇室甚至规定每艘归国的商船必须装载此项货物。运回的愈创木垄断在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一个商人家族手中,这个家族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专门开设了一家使用愈创木疗法的医院。医院利润可观,从中分拨出的金钱把很多医生笼络到愈创木疗法的鼓吹者之列。这进一步推高了市场价格,有能力负担医药费的患者百无其一。[31]
愈创木不仅价昂,制药过程也耗时费力。由于木材极度致密坚韧,煎制前先要把它慢慢锯成木屑或用斧子砍碎,在水中浸泡一天一夜,然后再慢火熬制很长时间。[31]愈创木的这些特点自然使得人们希望找到更加量大价廉、易得易用的药物。愈创木的产地美洲受到西班牙掌控,葡萄牙人若想打破垄断,只能在自己势力范围所及的东半球寻找货源,中国根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进入了欧洲。奥尔塔的消息来源曾经告诉他,中国根在婆罗洲的市场上以几百磅为一个单位出售。([15],19页) 这种药与愈创木一样有发汗的作用,在亚洲又出产丰富、售价便宜,它显然是理想的替代品。
维萨里谈到中国根的来源时说过:
我们为自己的目的而把中国根挑选出来,如同我们把大黄从其他根类中挑选出来一样,那是因为它的分量特别沉,而且药根在非常干燥的时候含有更多肉质,更少遭受虫蛀和腐坏,它那松软湿润的基质在干燥过程中能免于腐烂,所以它也更能抵抗腐烂带来的其他损害。([14],23- 24页)
这样看来,最初葡萄牙商人意图收购的药材或许还不止中国根一种,最后选定中国根,只是因为它质地沉重、保存相对容易,适合当作远洋运输的货品。
其实,奥尔塔自己认为中国根的药效不如愈创木,但他辩解说“若将病人的性质和特点、病的属性、季节、国度、燥热、风寒、服药者的性别和年龄考虑周详”,则中国根“肯定也十分有效。我称赞它你们不必讶怪,因为我未听到过任何别人对它的称赞,可是这许多的作者每天都在称赞愈创木”([15],381页)。中国根能够取代愈创木成为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价格低廉是主要原因,奥尔塔尽力称许中国根的好处,作为当地名医,他的意见大概也影响了不少人。
维萨里在《中国根书简》中回忆,中国根风靡欧洲的原因是1519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在身边贵族们的鼓动下主动尝试过它一次。国王使用中国根治病这件事激起了达官显贵们巨大的兴趣,中国根在德意志诸邦成为御医们热议的话题。当维萨里1537年作为一名低年资医生在威尼斯谋生时,这种药已经“被人寄予至厚期望,并受绝高之赞誉”。([14],15页) 因此,奥尔塔介绍这一味其实由他自己发现的药物时,也拿皇帝御用这件事来加强说服力,因为不管别人怎样说,“皇帝查理五世服用过它且获得益处,就是这种药有价值的充分证据。”([15],381页) 实际上,查理五世试用中国根原是为了治疗痛风,服药的期间很短,用量也不规律,不仅如此,他在服用中国根的同时还一直在服用愈创木。([14],18页) 这件事后来大约也传扬出去,因此林索登在自己的书中稍微改换了措辞,说“这种根不仅对水痘和脓疮很有益,而且还对……痛风有益:因为皇帝查理五世的确使用过它,而且发现它对他有好处。”([29],110页) 无论如何,查理五世用药的例子大概已经是中国根的宣传者们能够找到的最显赫的证据了。
不论皇帝后来是否继续青睐中国根,它的销路迅速扩大。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情况为例,据前人的研究[6],该公司从17世纪开始成为欧亚贸易的主力,进口的药材从16世纪下半叶每年一二千英镑的价值增加到18世纪下半叶每年100 000英镑,种类从17世纪初年的10种上下增加到一个世纪后的百余种。这些药物通过转口贸易销往欧洲各地。中国根在1566到1754年间一直位居英国香药贸易的前10名之内。
即使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欧洲药材市场的供货商之一。另一种用于梅毒治疗的草药、生长在西班牙势力范围内的美洲菝葜(或称洋菝葜,SmilaxsarsaparillaL.)正从另一个方向成批成批地贩运到欧洲。[23]美洲菝葜引入欧洲比中国根略晚,但在莫纳德斯的书中也已有详细介绍,治病的效力照他说起来比中国根有过之无不及。([25],16页) 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又开始在新夺得的美洲殖民地大量种植这种药材,它进口到欧洲,逐渐占据了中国根的市场份额。[4]尽管两者都在风光几十年之后便被欧洲医学界认定对梅毒并无确定效果,这两种外来药物还是在洲际贸易的大宗货品中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中国根甚至在逐渐退出欧洲市场之际东山再起,作为治疗梅毒的神药向日本贩售。[9]研究者在深入考察了各方证据后,认为这个时期欧洲市场进口药物种类变化的原因,既非医学理论也非医疗实践的改变,而是新商路不断开辟的结果。[6]
3 中国根究为何物?来源植物及原初的使用方法
16世纪时,书籍仍是贵重之物。中国根在几种不同的本草书中都占有一席地位,显然受到时人的推崇。然而这一味药究竟来源于什么植物?
中国根在欧洲有过五花八门的名字,大多源自最初传入者使用的不同语言,究其含义,则多为“中国”与“根”、“木”、“树皮”这几个词汇的组合。[7][注]详见参考文献[7]。文章开始部分讨论了菝葜类药物在欧洲曾有过的各种名称。“中国根”或“中国木”,仅指称植物的原产地和药用部位,与植物的种类无关。
1879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比较权威的生药学里仍可见到TuberChinae(中国根)的词条[32][注]参考文献[32]。据《印度香药谈》英译者Clements R. Markham的看法,这本生药学在20世纪初被视为“最新最好的本草书之一”。见参考文献[15],vii- xvi 页(Introduction)。, 它的拉丁文名字也叫做RadixChinae,当时英文里一般称它为China root或直接简称为China,法文称为Squine,德文称为Chinawurzel,但可以确定欧洲医学界提到“中国根”时,指的始终是百合科菝葜族(Smilaceae)[注]1973年以来的主要植物分类系统已将菝葜族的地位从百合科(Liliaceae)中提升出来,独立成为菝葜科(Smilacaceae)([33],1- 2页);但1959—2004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仍将菝葜族归入百合科[34]。本文以《中国植物志》的分类为准。某一种植物的根。菝葜族植物有3个属约320种,广布于全球热带地区,也有少数种类产于东亚及北美的温暖地带和地中海地区,其中2属即菝葜属(SmilaxL.)和肖菝葜属(HeterosmilaxKunth.)产于中国。菝葜族包含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在中国的蕴藏量大,药用历史悠久,本族中可用为中药材的植物将近20种,在祛风利湿、解毒散瘀等功效上具有相似作用,其中最常用者是菝葜属的菝葜(SmilaxchinaL.)及土茯苓(即光叶菝葜,SmilaxglabraRoxb.)两种,药用部分皆为其根状茎。[33,34]菝葜功效袪风利湿,解毒散瘀;土茯苓解毒去湿,通利关节,两种植物今天均收录于《中国药典》[注]菝葜族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及在中国和世界的分布,参见文献[34- 38]。,书中推测“中国根”最可能是菝葜、土茯苓和马甲菝葜(S.lanceifoliaRoxb.,亦名台湾土茯苓)这三者之一。
仅从16世纪的文献无法确定“中国根”的来源植物,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见到的都是炮制过的饮片,且它们到达欧洲之前一般都已在海船上颠簸了一两年。比如,维萨里见到的中国根是一些干燥破碎的块茎。他试图向商人打听它的来源,只得到含糊其辞的回答:
那些人说它是在海岸附近采来的,沿海的沼泽地带最多,正如我们常常见到各种蒲苇一类的植物都在那里生长。([14],22页)[注]本文所有英文引文由笔者自行汉译。
因此维萨里推断中国根来自蒲苇之类普通的水生植物:
事实上,假如我们正确地想想,若那些芦根不知何故被水手和渔人从土中拔出,又因各种缘故被分成大小不等的断块,然后在海水中长时间翻滚,最后落在沙滩上,那么它们的形状也就和这中国根相去无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我所说的这些落在海滩和河岸上偶然被人看见的芦根更像中国根的东西。无非芦根的颜色较暗,而中国根略泛红色,像是泻根(bitter root)或我们所谓的高良姜(galanga)而已。的确,假如撇开前者的大小和硬度不论,还有什么比腐朽后带上了沉闷滋味的菖蒲根更像中国根的东西呢?中国根的特点是大而粗糙、各片大小不均,更偏于木质,但呈现明显的海绵状,同时正如前面提到的各种块根一样,它生长时肯定像刚运来时那样是富含汁液的,很快它便变得非常干燥了,而且经常遭受虫噬。([14],22- 23页)
不仅如此,销售商又对这些朽坏虫蛀的药材做过手脚:
……那些商人,为假装这些腐坏处和蛀虫都不存在,便用一般药店出售的亚美尼亚红土把中国根包裹起来,就像我们见过的把姜块裹在红粘土里又在商店出售的方法,尤其是在安特卫普。……([14],22页)
莫纳德斯可能由于本人经销药材的缘故,有机会见到新鲜的中国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
这种中国根像藤条的根,内中有些疤结,白颜色,有些的白色是象牙白:外皮是红色的,最新鲜者最佳,新鲜者无孔洞,分量沉,未受虫噬,滑腻如凝脂,尝之颇乏滋味。([25],25页)
这虽然比维萨里的描述详细很多,但仍不足以让人判断植物的来源。
奥尔塔是唯一对中国根来源植物拥有第一手知识的人。他曾设法弄到一棵活的中国根种在他的药草园里:
它是一种矮灌木,长在地上有3到4拃(palmo[注]1 palmo=0.22米。)高,根部长约1拃。它有一条粗根和一条细根,如你所见,根从那里发出来。这种根刚挖出来的时候很柔软,无论生熟都可以大口地吃。咬它的时候冒出甘蔗一样的汁液。从根部发出几条细小的须,大小和形状如同鹅毛笔,根生长的时候这些须也抽芽,芽又发出像橘树新叶那样形状的叶子。中国人把这种灌木叫做“冷饭团”(Lampatam)。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此灌木及其根的知识。我曾于果阿见到一株幼小的植株,但它未及长大便枯萎了。([15],387- 388页)
由于奥尔塔见到过“中国根”的活植株,又明确指出这药材的原名叫做冷饭团,“中国根”原物即土茯苓,遂成各家采用最多的解释。
《印度香药谈》1913年的英译者在为书中植物编制索引时将中国根的学名误写成美洲植物愈创木(Guaiacumofficianale),但在正文注释中又将其重新记作菝葜[注]参考文献[15],xix页,拉丁名注为愈创木之名;同书378页脚注1,拉丁名注为菝葜之名。。现代的研究者均将中国根认定为菝葜或土茯苓,或二者之一。例如温特博特姆(Winterbottom)认为中国根主要是菝葜和土茯苓,可能包括其他菝葜属植物,但文中对药物来源的讨论基本围绕李时珍《本草纲目》土茯苓一条进行[4];博尔施贝格(Borschberg)则认为中国根即今日中药市场上的土茯苓,但它在贸易中可能经常与姜、高良姜、人参相混淆[7];郑维中在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香药贸易的文章中使用菝葜的学名SmilaxchinaL.,但标注的中文名是“土茯苓”亦即光叶菝葜[10];佩雷拉(Perera)则从印度古代医学文献及现代药物学研究结果归纳出结论,认为16世纪输入印度的中国根应为菝葜和土茯苓两种植物[5]。
但当时运往欧洲的中国根是否仅限于奥尔塔所见的“冷饭团”,而“冷饭团”又是否一定就是土茯苓呢?
阿科斯塔为中国根配上的插图PalodelaChina(图2)经常被后人引用,作为奥尔塔记述的中国根即是土茯苓的证据。实际上,阿科斯塔的插图并未澄清问题,毋宁说更添纷乱,因为这幅相当程式化的插图还是细心地绘出了植株蔓生茎上的许多小刺,而茎上疏生刺是菝葜属其他几个种的特征,土茯苓的茎应该是光滑无刺的。([34],193- 194页,213- 214页)

图2 阿科斯塔书中描绘的中国根([22],78页)
既然“中国根”产于中国,且曾经大宗出口欧洲,它在中国亦应属于广泛使用的药物。考察菝葜、土茯苓及其类似药物在中国本土的使用情况,或许有助于我们推测“中国根”最可能是哪一种植物。
菝葜是中国民间常用的传统药物,陶弘景辑注的《名医别录》已经收录了菝葜,说它“味甘、平、温和,无毒。主腰背寒痛,风痹,益血气,止小便利。”[39]后来它也屡见于本草记载。[39,40]土茯苓见载于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称“禹余粮”、“白余粮”,书中还说它“叶如菝葜,根作块有节,似菝葜而色赤,根形似薯蓣,谓为禹余粮。言昔禹行山乏食,采此以充粮,而弃其余。”[41][注]关于古本草中名为“土茯苓”或“菝葜”的药物的考证,参见参考文献[39- 40]。然而,这些在古本草中出现的药物,实际鉴定起来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虽然现代的中医认为菝葜、土茯苓和萆薢是在功效主治方面具有相同点的不同药物,疗效各有侧重,并不能完全替代[42],但直至今日,菝葜和土茯苓在中国各地仍有不同的地方名称和商品名,由于同物异名及成药外观相似,中药市场上普遍存在彼此混用及与其他同属植物混用的情况。不仅如此,与它们混用的还有另一种药物萆薢。至20世纪60年代,中医药界虽已很少使用菝葜这一药名,可是这种药材仍然作为土茯苓和萆薢的代用品行销市上,土茯苓和萆薢混用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据统计,当今在中国国内中药市场上出现的菝葜属植物包括二十几个不同的种,肖菝葜属至少有4种。[37]菝葜属的不少种及肖菝葜属的短柱肖菝葜等在市场上常与土茯苓混用。再者,粉萆薢(DioscoreahypoglaucaPalibin)和绵萆薢(DioscoreasaptemlobThumb.)也常被混同于土茯苓或菝葜,它们在分类学上不属于菝葜和土茯苓所在的百合科,而是薯蓣科的植物。中国古本草中所称的菝葜,则可能是这几种植物中的任何一种。中药界人士认为,除了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用药习惯不同以外,本草记载的混淆以及原植物近似、生药外形及饮片类似,也是混用的主要客观因素。[39,41,43- 45]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576)中对菝葜、萆薢和土茯苓3种药材植株的形态区别描述得相当明确。在萆薢条下他说:“萆薢蔓生,叶似菝葜,而大如碗,其根长硬,大者如商陆而坚”,菝葜“山野中甚多,其茎似蔓而坚强,植生有刺,其叶团大,状如马蹄,光泽似柿叶,不类冬青,秋开黄花,结红子,其根甚硬,有硬须如刺,……”,而土茯苓是“楚蜀山箐中甚多,蔓生如莼,茎生细点,其叶不对,状颇类大竹叶而质厚滑,如瑞香叶而长五六寸,其根如菝葜而圆,其大如鸡鸭子,连缀而生,远者离尺许,近或数寸,……”。[46]《本草纲目》描绘这3种药草的插图,虽然是粗线条的木刻,但也足以看出它们根、茎、叶形态的不同。(图3)据此回看阿科斯塔书中所绘的植物(图2),蔓生的茎像是萆薢或土茯苓,不似菝葜,而且藤蔓画得纡曲柔弱,愈发符合李时珍所说土茯苓“蔓生如莼”的特点;粗大长硬的根状茎却又像是菝葜或萆薢,与李时珍见到的仅“大如鸡鸭子”且连缀而生,相隔尺余寸许的土茯苓根状茎似乎有别;尤其3条纵脉清晰可见的椭圆形叶片和茎上的硬刺一望便令人联想到菝葜,不符合李时珍所说土茯苓“茎生细点”的特征。这幅插图简直可以说是几种不同植物的复合体,因此,很难把它当做判定种属的依据。唯一可以推测出的是,确有一些人见过中国根的活植株,而其所见并非同一种植物,为阿科斯塔作插图的画匠最终综合了他们提供的信息。
在中医历史上,菝葜、土茯苓和萆薢一直存在混用的情况。隋唐以前,主要是狗脊、萆薢、菝葜三者相互混乱;唐宋时期延续旧说,而且萆薢出现2 个主要品种;在明代,主要是萆薢、菝葜相互混乱,且二者混作土茯苓使用。[41]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这几种药物的使用明确地涉及到了梅毒治疗。如文人俞弁医话类著作《续医说》(1522),被认为是最早记述杨梅疮病状的医著之一[47,48],书中有关于萆薢治疗杨梅疮的记载:

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愈。近医家以萆薢鲜肥者四五两为君,佐以风药,随上下加减,服者多效。按《本草元命苞》云:萆薢,味甘平,无毒,主腰背骨节疼痛,治风湿痹不仁,疗瘫痪软风,治恶疮久不愈。生真定山谷,今荆蜀有之,凡有二种,无刺虚软为胜,有刺白实次之,一名仙遗粮,一名土茯苓,俗谓之冷饭团是也。([49],510页)
俞弁把“萆薢”、“仙遗粮”、“土茯苓”、“冷饭团”作为同义词对待。此外,陈嘉谟《本草蒙荃》(1565)中对有关药物的记载是“按近道所产,呼为冷饭团,即萆薢也。俗之淫夫淫妇,多病杨梅疮。剂用轻粉,愈而复发,久则肢体拘挛,挛为痈漏”[50];杨宗魁《本草真诠》(1602)“萆薢”项下则言“又与菝葜相类,但菝葜根作块,赤黄;萆薢根细长,浅白。按近道所产,呼为冷饭团,即萆薢也。俗之淫夫淫妇多病杨梅疮,用轻粉愈而复发,久则肢体拘挛,变为痈漏。用萆薢三两或加皂刺、牵牛各一钱,水六碗,煎耗一半,温三服,不数剂多差”[41];李时珍《本草纲目》“土茯苓”项下则曰“近时弘治、正德年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取效,毒留筋骨,溃烂全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诸医无从考证,往往指为萆薢及菝葜,然其根苗迥然不同,宜参考之,……”,上文已述,李时珍对这几种植物的形态区别了解十分清楚,但他又说“萆薢、菝葜、土茯苓,三物形虽不同,而主治之功不相远,岂亦一类数种乎”。([46],39b页) 这些记载说明,在16世纪,中医常用于治疗梅毒的草药,既有土茯苓,又有菝葜和萆薢,它们被用来替代疗效显著但毒副作用比较严重的矿物药——轻粉(主要成分为氯化亚汞),或在病人服用轻粉后作为解毒剂使用。医家通常都认识到这是数种“根苗迥然不同”的植物,但他们认为这几种植物药“主治之功不相远”,所以在实践中经常将它们混用。无论如何,“冷饭团”之名未必专指土茯苓。至清代,这些名称愈发淆乱,尤其当时的药商为了牟利,经常在市场上用萆薢代替土茯苓,因前者比较易得,而土茯苓“不易得巨者,而近时饮用甚伙”。[45]这使得原来的混乱状况进一步加剧,以至清人陈士铎在《本草秘录》中说“萆薢,即土茯苓也,岂特一物而两名之,一曰菝葜,一曰冷饭团,一曰岐良,是一物而五名……。”[41]
欧洲记载不能够确指,中国本草中的名目多且游移。鉴于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16—18世纪出口欧洲的“中国根”不仅不是单一一种植物,而且未必如一些现代学者所认为的,主要限于菝葜和土茯苓两种。可能性较大的情况是,名为“中国根”的贸易品中包括了大同小异的几种或多种植物的根茎,但其中的主体成分仍是菝葜族的植物。因此,在提到“中国根”及类似名称的药物时,比较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将它们统称为菝葜类药材,而将“中国根”的药物基原统称为菝葜类植物。
综合考察了各方的证据,我们最后发现所谓的中国根是一大类根茎形态及药用效果相类似的中草药的总称。定义模糊不清,在医生和药剂师眼中是有待匡正的问题;作为商品属性,却可能是中国根的一项巨大的优势。来源广泛的替代品保证了这宗货物在市场上始终能有稳定的供应。
4 西方医生手中的“中国根”:新病、新药、旧理论
梅毒到来是对欧洲因循守旧的医学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它的传播方式、剧烈程度、症状表现都不同于以前的黑死病和其他一些传染病,而且其皮肤表现既可怖又令人作呕。医学界一开始完全处于震惊和迷茫之中,不久后便对其来源、性质、传播方式展开了激烈辩论,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有效的疗法。([51],26- 30页;[52],128- 130页)
如前所述,中国根只是梅毒来袭之时欧洲医生仓皇引入的诸种草药之一,愈创木比它更早输入,也出名得多。实际上,除了放血、发汗这些盖仑医学的传统手段之外,药物治疗中最早投入使用的是水银。伊斯兰医生们至少从10世纪开始就用含水银的油膏外搽治疗各种皮肤病,这个方法大约14世纪起在欧洲得到推广,此时被移用到梅毒的治疗。水银疗法在当时被公推有效,但汞有明显的毒副作用,过量使用会引起精神异常、震颤、偏瘫、流涎不止、牙齿脱落等症状,严重者会危及生命。[53,54]当时的医生们治疗梅毒并无经验,既然水银是唯一的特效药,他们便在处方里开出惊人的大剂量,偏偏汞剂的治疗有效量与中毒量相当接近,结果很多病人因为用药而丧生,即使侥幸未死,因过量使用汞剂导致的后遗症往往比梅毒的后果还要严重。医生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使得寻找温和的替代药物变成了当时的迫切需要。1517年,他们得到了愈创木的方剂,稍后又听说了中国根和产于美洲的洋菝葜。[31]
这些草药一开始被选中,都是因为它们具备发汗作用。当时的欧洲医生并不认为中国根在中国本土是专门治疗梅毒的药物。维萨里在书中说:
……当地人用它治疗疥疮,就像我们使用酸模。不过,有一种人也多得是,他们为了让中国根更易贩卖,就一本正经地断言中国根的煎剂让当地人远离了所有各种病痛。([14],23- 24页)
莫纳德斯虽然断言中国根能“治疗各种大病”,具体到药效也只是说“它能神奇地引发汗水”。([25],27页)
盖仑学说主宰下的欧洲医学体系用四体液的理论来解释健康与疾病,认为组成人体的成分除固形物之外,有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4种体液,它们各自禀有冷、热、燥、湿4种性质之中的2种,这4种体液的比例平衡与否决定了人体的健康状态。因此,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疾病,同样的体液失衡到了不同病人身上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症状。疾病的原因是某种体液过多或过少,也有可能是体液变得“腐朽”或“败坏”。治疗的思路,一是运用节食、放血等手段矫正体液的平衡,一是通过发汗、利尿、泻下等途径设法驱除腐坏的成分。[54]到梅毒袭来的时候,医生们开始特别强调后一种患病机制,即体液在外界的不良影响下变得“腐坏”。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给患者设计了各种疗法,包括放血、清肠、全身浸泡在药酒或橄榄油里,还有一个重要手段是把患者安置在生了火炉的密闭房间里,让他们终日大汗淋漓。所有这些办法都是为了逐出体液内的败坏成分。[53]愈创木引入后,保暖发汗的同时增加了饮用药汤这一项,具体流程首先记载在波尔的报告里,后来的医书又各自给出据说是自己的效验配方。医学史研究者考察了这些流程[31,56,57],发现它们除了煎药时加水的比例以及每次服用量有些区别外,其他方面大同小异,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病人安置在无风的小房间内,冬天室内生火炉取暖。疗程开始前先清肠、放血,以后每日早晚饮用药汤。煎药的方法是先把愈创木用斧头劈成很小的碎片,然后每磅木片加12磅水,浸泡一天,再用小火煎到水只剩一半或三分之一。煎药时浮起的泡沫捞出晾干,用作敷疮的药粉。每日早晚服药,服药后在床上躺3—4小时,多盖衣被发汗,如不能发汗还要给全身做热敷。饮食严格控制,不可食肉,严禁饮酒,只能吃饼干面包,外加少量葡萄干或梅子,而且要限制在足够维持生命的最少量。饮水用二煎或三煎的淡薄药汤代替。病人要戒绝性交,保持心情愉快,日常服泻药使大便畅通。一个完整疗程约需30天。若有复发,则全部手续重来一遍。有些反复使用过汞剂的病人治愈过程长达一年。
对照这些记载,则很容易理解中国根在欧洲医生手中的使用方法。以煎药为例,维萨里在《中国根书简》中描述了与煎制愈创木几乎相同的手续([14],27页),并且断定:
我们使用中国根制剂的手续越接近我们使用含有愈创木的药剂时候的手续,就是说从中国根的第一次用药开始就用那种方式而基本不加改变,那么,各种结果就会越好。([14],22页)
实际上,维萨里本人对当时人宣扬的中国根的种种效用十分怀疑,觉得“我不能理解长久以来很多人归功于中国根的一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归结到它那里的,也不明白什么新的推动力让它现在声名增长,又被冠以更多的新效力。”他认为中国根的作用远逊愈创木:“(对于骨的赘生物、肿瘤,或恶性的疮疡而言)我十分肯定中国根的制剂远比愈创木的制剂低劣。”([14],25页)
在受过大学教育、服务于上流社会的医生手里,病人服药绝非简单地一吞了事,而是要遵循一整套的繁琐手续。体液论把能够影响体液平衡的外界因素归结为6类,或称6种“非自然”原因:一空气、二起居、三饮食、四劳逸、五通与滞(即汗水与二便是否通畅)、六心思情志。用药之前、之中、之后都要考虑到这6个方面的影响,并对治疗过程做出相应的调整。[52]维萨里身为御医和大学的讲师,对这套规矩奉行维谨,虽然在《中国根书简》的字里行间多处流露出对这种舶来药物功效的怀疑,他还是从6种“非自然”因素的角度,对用药过程可能受到的影响逐条做出了详尽说明,多半系转述他人说法,有时也增加自己的观察所得。在“中国根的配制方法”之后,维萨里依次谈到“中国根初煎药汤的给药量以及给药时间”、“如何发汗”、“何种饮料有用”、“睡眠与觉醒”、“动与静”、“关于排出体内废物”、“对头脑的哪些影响是适合的”、“性事”、“初煎药汤应使用多久”、“二煎药汤的配制和服用方法”,最后落实在自己的结论——“应使用本土和熟悉的药物而非域外新奇之物”。([14],27- 41页) 《中国根书简》与中国根真正有关的部分便终结于此。
维萨里讨论中国根用法的文字过于冗长,其中实际的操作手续,另一位医生莫纳德斯在《新世界佳音》中给出了比较简洁的概括:
……病人在最适时机完成清肠以后,应取一份药根,将它们切成大小薄厚如同3便士硬币的小片。如此切好后,称出1盎司,倾入新的罐子里,再注入3波特尔(pottel,合2夸脱)水,浸泡24小时,盖好罐子,放在燃着微火的木炭上,直至一半吸收掉了,剩余一波特尔有半,此量通过所做的记号得知,如同前文在愈创木煎法中讲过的一样。这之后,俟其变凉,将其过滤,保存在上釉的容器中。必须注意,药汤要存放在靠近火的暖热处所,盖此方法能保存更多精华,并令其存放更久而不腐坏。
栖身在方便的密闭小室里的病人,每天早上应空腹饮用上述方法制成的药汤10盎司,在能忍受的限度内越烫越好。然后他应设法发汗,至少保持2小时。发汗后,他应清洁身体,换上干净的衬衫和床单,把它们烘热,出汗以后再回到床上静卧2到3小时。之后让他穿上衣服,充分保暖,待在没有冷风和外界空气的房间里,享受良友陪伴和交谈的各种乐趣。他应在11点钟吃饭,吃半只煮软的子鸡或四分之一只母鸡,加上少许的盐。…… ([25],27- 29页)
然后是一大段关于晚餐的详细指示,可食之物包括肉汤、鸡肉、腌菜、面包干、饼干,而且要遵循一定的次序,先吃去籽的葡萄干或去核的梅子干垫底,最后吃果酱结束。饮料没有别的,只有浓淡不等的中国根药汤。这些饮食起居的琐事,当年都是治疗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个菜单也告诉我们,即使中国根价格远较愈创木低廉,它同样不是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晚餐之后再次发汗,手续与早上相同。临睡前再吃些腌菜、葡萄干、杏仁和饼干作为夜宵,饮中国根的药汤解渴。“病人应如此不间断地进行30天,期间不须再像第一次那样清肠,他也可以坐起来,穿得严严实实,尽力使自己安心欢畅,远离任何可能激怒他的事物。”([25],29页) 30天后,第一个疗程就完成了。后面还有40天的巩固阶段,期间仍然禁酒,用二煎的药汤作为日常饮料。
奥尔塔所用的煎药方法与维萨里类似,小火慢煎,撇出浮沫留作疮疡的敷药。但他强调他的用法根据当地情况做了修改:
倘若病情很重,他们就将一盎司这种根煮在4canadas[注]中世纪计量单位。量度容积时,1 canada合1400毫升。的水里,使用一半的水。余下的他们保存在玻璃罐或者上釉的罐子里。他们取出煎药时的浮沫,因为它敷在疮疡上很好;有时我们趁水沸腾的时候把浮沫敷在肿胀处,它对减轻疼痛非常好。其他时候我们用这种热水给肿胀处作热敷。另有些时候我们在疮疡上放上湿布,它是非常好的清洁剂。中国人在他们国家里惯于给予病人大剂量的这种根,此地有些人也想模仿中国人,煮上2盎司或1盎司的根,但最后发现这只有害处,因为它是非常热性的。([15],381页)
奥尔塔在自己身上也试用过这种新药,并根据切身经验修改了中国根的用量:
我因髋部痛风(sciatica),与发汗药同时服用此根,并不疑及高卢病。但因我依疗程起始的一般做法,服发汗药并饮热水,待此根起效时我全身遍布丹毒,处处疼痛,这起自于我肝中所生的大热。人们不得不给我放血,给予我大麦水和甜的玫瑰水,如此我方得恢复健康。后来许多人效仿我的做法,不再饮热水,也不再使用如中国用量那么多的药根。因为彼地寒凉,而此处天热。只是在此地服中国根时,假如还需要发汗,就在早上用热的方法,并用一些办法在早晚二时发汗。如果天气太热,我们便不再用中国根,而用更多发汗药。我们现在习惯使用的最大剂量是1盎司药根用4canadas水煎,煎至水消失一半。其他人用的药根更少,煎药时间更短。([15],382页)
维萨里和莫纳德斯都提到过,但未详言其操作的一个步骤,是服药之前或同时要给病人施行的清肠手续。在16世纪的欧洲医生眼中,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发汗和节食。奥尔塔非常重视清肠,可能因为住在气候炎热的印度,他给病人清肠的次数也更多一些:
常规是在施用它[注]指中国根。之前先给病人糖浆,然后给予泻剂,假如病情严重,将糖浆稀释。因为多数情况都会有炎症并发,故我们加入印度牵牛和伞菌,并在配药时用中国根所煎之水稀释糖浆。泻下清肠之后,按常规开始施用这种根,15日后如有必要再行一次轻微的泻下,有时在30日终了时再泻下一次。如果此时仍不见缓解,则每天用药根所煎之水及蜂蜜玫瑰水、油、番泻叶等加以巩固,视病情的需要而定。我们时或给予病人的这些轻泻剂,不外乎木蜜和番泻叶、中国根汤、融化在菊苣汤里的大黄,还有梅子汤、甘草汤、大麦汤等等。之后我们便给予分量较少的中国根水煎剂,如有必要,将煎剂混以菊苣汤和烟堇,或混以蓝蓟。([15],383页)
印度牵牛、伞菌、番泻叶、木蜜、菊苣、大黄、都是当时常用的缓泻剂。其他几种,蜂蜜玫瑰水据信可以养胃并遏制“热性的溢流”,梅子清凉润肠,菊苣也有清凉作用,甘草止咳化痰,烟堇内服用于舒肝利尿。服用中国根时不仅需要佐以这许多泻下和滋补的草药,冷饮还是热饮,搭配什么食物,水煎剂中是否加盐,都在处方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本文第一节介绍的4位作者中,林索登是唯一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他似乎也未学过拉丁文,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推测他书中的医药内容摘抄自奥尔塔和阿科斯塔的葡萄牙文及西班牙文原著。[26]不过,对比前后二书,可以看到林索登的记述其实超出了奥尔塔书中的内容,而且相当富于色彩:
他们拿到这种根,把它切成小块或薄片,取一盎司,用4罐或4夸脱的水熬煮,熬煮到水消耗一半。他们每天这样煮一次新药:这种水他们必须单喝,并且吃饼,除烤小鸡外不搭配其他任何东西,既不放黄油,也不放糖、盐或酱料,只是干巴巴地就着烤饼吃,这必须是晚餐——因某种缘故而在夜里,还吃只加蜂蜜的烤面包。每天两次他们必须躺(在床上)盖得严严实实,尽量发汗,每次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这事情他们要持续做30天,始终不让自己暴露在空气中,也不被风吹到,头和耳朵紧紧包起来,一直呆在屋子里,尤其还要戒绝女人的肉体陪伴。([30],28页)
严格履行上述手续之后,据林索登说,虽然前15到20天里全身四肢和关节会疼得越来越厉害,但不要对药物丧失信心,因为最多25天后疼痛就会好转,到了30天时“疼痛便会全部消失,全身和它的各部分将会像从未生过病那样又新鲜又有活力”。他声称这事已经“被印度的千千万万人所证实”。([30],28页) 林索登之书晚于《印度香药谈》约30年出版,他的这番话从侧面说明30年来中国根在印度也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
林索登自称他的信息得自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见闻,但从其中的生活细节看来好像并不完全如此。这套疗法与50年前维萨里所言者如出一辙,与愈创木的使用方法也无甚大异,可见既非创新,也不是随着中国根的输入而学到的中医的方法,恐怕只是当年同样把植物药当作主要武器的西方医生们煎药和发汗的常用路数而已。
从维萨里到林索登,4个人一致把中国根的疗程记为25—30天,却无人说明理由。其实此乃当时医生确定疗程的惯例。16世纪的欧洲医学仍将占星术作为解释工具之一,天人相应,日月星辰的一切运动无不折射到尘世间的事物。梅毒入侵欧洲的初期,不少名医把疫病流行的一个原因归结于火星和木星之间不吉利的交会。([58],136- 139页) 治病的时间节点也根据天象确定:月亮30天一圆缺,体液的扰动犹如潮涨潮落,理应在30天(精确说是26天又22小时)走过一个完整的周期。([51],第5章)
按照体液论的思路,药物的分类并不是按照它主治的疾病,而是按照它所具备的冷热干湿的特性。奥尔塔认为中国根是热性和干性的。他遵循这些原则,将中国根用到多种疾病的治疗当中,尝试的结果是它可用在:
那不勒斯病(morbonapolitano)导致的任何疾患或(过多的)体液。它对瘫痪、对阵发的寒战都有益处,我用它在短时间内治好了尼扎王[注]即古吉拉特苏丹Bahram Nizam Shah。据参考文献[15],viii页。(Nizamoxa)的病,它也有益于关节炎、湿疹(exema)、髋部痛风、普通痛风、瘰疬、还有因忧郁症(melancholy)或白肿瘤(white tumours)引发的肿胀、陈旧的创伤,有时它对膀胱的结石和溃疡也有效,因为使用了这种根,以前无论如何无法清除的结石便可排出。([15],386- 387页)
奥尔塔下结论十分谨慎,他所介绍的中国根的用法全都来自他实地治疗过的病例。他的做法并非个例,与愈创木的情况一样,中国根在投入使用不久后便被当作万应灵丹,用在各种各样的病状上面。维萨里在他的书中罗列了同时代人对中国根药效的看法:
据推测说它是热性的,具备疏通功能;它尤其能够利尿和发汗;人们发现对于冗余和有害的物质以及不论何种体液,它是消耗者和干燥剂,因此它是血液的净化剂;它具备缓解与净化的功效,它让腹部松弛,催尿和发汗时又使之紧张。胃部为粘液所困时,可用它治疗;它驱走肝和脾的疾病,其效非浅;它有效保护受到结石折磨的人,化解结石。它驱走痛风,特别有益于象皮肿患者(elephantiacs)[注]依16世纪的字典(Thomas Elyot,The Dictionary of Sir Thomas Elyot,London,1538)解释,象皮肿(elephantiasis)一词所指的疾病当时类属于麻风项下。,治愈皮肤病,对瘘以及恶性的或其他无法治疗的溃疡有不一般的助益。它神奇地治愈新发和旧染的高卢病(the Gallic disease),治愈该病导致的溃疡,修复疮疤。它驱散肢体的痛苦,消解肿瘤,帮助将要化脓的肿块发热、开口、净化、结疤。它使骨头的腐坏和脓肿康复,松弛抽搐和挛缩的筋肉,排干受阻和软化的部位,烘热因高卢病而僵化的筋肉;它使罹患消耗病(wasting)的筋肉重新变得丰腴。它给溃烂坏死的躯体带来好闻的气味,去除口臭,为呼吸困难的人提供保护。它令长期的喉咙肿痛(angina)消散,驱走高卢病给脑造成的损伤,凡体液溢流(fluxion)它均能遏制,且功效非同小可。总之,人们认为中国根与愈创木的功效相同。事实上,它因许多其他的性质而比愈创木更受欢迎,即使这些性质是互相抵触的,因为上文已言,它那沉闷的滋味丝毫也不像是有收敛能力。([14],25页)
莫纳德斯对中国根则毫无保留地加以肯定。比如,奥尔塔虽然说过中国根“对瘫痪、对阵发的寒战都有益处”,莫纳德斯却断言中国根能够治愈瘫痪、疟疾和瘟疫:
许多病都可用这种药汤治愈,如大水痘(the Poxe)的所有恶果、各种陈旧的疮疡。它消解各种肿胀和结节,它带走人称关节痛风(Arthetica Goute)的病症所造成的疼痛,也带走其他位于特定器官或位置的痛风尤其是髋部痛风的疼痛。它带走头部和胃部的旧痛。它治愈诸般头疼流涕(Rewmes),纾解肝肠积滞(Opilations),治愈水肿(the Dropsie)。它使面部出现好气色,带走黄疸及肝病造成的各种坏脸色。它的用量应时时调整,此事上面它是众药之王。藉此方法便可治愈诸病。它治愈瘫痪(the palsey)及各种神经疾病(the Sinewes),它治愈尿的疾病,它带走来自忧郁症以及冷性疾病的各种不适。它确能调理胃部,并有疏风的奇效,又能消解长期的或急性的疟疾,比如日发疟:在合宜之时服用这种药汤,便可将它们连根拔起并移走。它做到这一点,是凭借发汗,在发汗方面它超越所有其他的药物,有人更说,遇着瘟疫性疟疾(Pestilent Agues)到来时,它亦能借助发汗治愈之。它的干燥性是第二级的,带有极微的热性,这点可从此木的各种汤剂看出。美洲菝葜(Sarcaparilia)确是热性和干性的,此木则不然,它亦不留下热力的痕迹。([25],15页)
现代研究者认为,考虑到《新世界佳音》原是为推销药物而作,莫纳德斯过分夸大了中国根的效力。[24]维萨里和莫纳德斯都是转述他人之见,唯有奥尔塔具备给药的切身经验,鉴于菝葜类药材多数确实有发汗利尿、镇痛消炎的作用,3人中大概奥尔塔的谨慎结论最为接近实际。
梅毒是慢性的传染病,病程很长。临床上表现为3个较典型的时期,各期之间都存在暂时的潜伏阶段。虽然不经治疗或治疗不彻底的情况下会逐渐发展到有致命危险的第三期,但是在二期和三期之间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伏期,期间患者并无临床症状。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终生停留在潜伏状态,小部分甚至可以自行痊愈。所以,单纯从服用中国根之类的草药之后出现的一时好转,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药物的效果。从维萨里、奥尔塔和林索登都描述过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表现看来,更像是梅毒正在走完它的自然进程,而据信是治疗收效的患者也许正好是落在了梅毒的潜伏期或开始自愈。林索登报告的情况也符合这个猜测,他说:
……水痘越陈旧,患病时间越久,药根治愈它们就越快,病人年纪越老治得也越快,因为体液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成熟。([30],109页)
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医生普遍认为复方比单方有效,所以在给药的时候习惯开出复杂的处方,有的大处方包含多达几十种成分。这种给药习惯,再加上像奥尔塔描述过的那些与中国根配套应用的形形色色的清肠、凉血、养胃草药,也使得单独评估某一味药物的效用几乎变成无意义的事情。
中国根在欧洲只是医学界为了在梅毒治疗中摆脱对汞剂的依赖而尝试使用过的多种植物药之一。愈创木首先受到质疑,1546年,最初深信愈创木功效的弗拉卡斯托罗承认他发现有许多接受过这种疗法的病人梅毒复发。渐渐地,更多的人表示他们其实没有见过单纯由愈创木治愈的病例,从他们的行医实践看来,汞剂是唯一有确实效果的药物。[31]18世纪末一本英国性病学专著总结二百多年来用草药治疗梅毒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前代的作者们谈到过很多植物界提供的治疗性病的药方。它们中有愈创木、洋菝葜、中国根……,等等。然而无数次的试用只是让人们对它们作为梅毒特效药的声名嗤之以鼻,尽管它们在化脓性梅毒和有合并症的病例中,作为汞剂的辅助药物还是值得推荐的。”([59],216页)
在愈创木、中国根和洋菝葜这三者间,中国根扮演治疗梅毒主角的时间最为短暂。它1535年正式出场,不到30年便在欧洲大陆失掉了主流医学界的信赖([58],225页;[59]),18世纪晚期基本退出了欧洲主要的药典。它并未立刻从市场消失,而是被秘方药的贩卖者与愈创木和其他多种曾经在梅毒治疗中试用过的药物混合在一起配成营养糖浆推销,号称可以医治包括性病在内的各色病痛。[60- 62]但中国根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数量逐年下跌,1752—1754年间它还保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香药贸易的第10位,1754年后便退出了前10名,而美洲菝葜同期的贸易额在该公司的账单上位居第3,1772—1774年间更升至第2位。[6]
中国根传进欧洲时,完全从原有的医药体系剥离,它既没能像中古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药物[29]那样,随着成套的药方一起出现,也没能像5世纪便开始了巡游世界之旅的阿魏[63]那样,经受漫长的审视与试验,最后还获得引种,变成中医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6世纪到达欧洲的中国根是一种单纯的原材料,最开始仅因发汗利尿的效能而得到采用,被置入盖仑体液论医学的体系中,直接继承了愈创木原来的角色。欧洲医生按照自己的理论,将它分类为热性和干性的药物,又从这个假定出发,将它用于包括梅毒在内的形形色色疾病的治疗。几十年的诊疗实践最终改变了医生们的看法,主流的欧洲医学界到16世纪末便不再把中国根视为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虽然秘方药的药贩们还继续利用了它很长时间。
5 中国根与本土的梅毒治疗
梅毒16世纪初传入中国,从1513年的《岭南卫生方》开始,大部分中医外科名著中,几乎都记载了梅毒,其中薛己的《外科心法》(1525)和《外科发挥》(1528)、汪机的《石山医案》和《外科理例》(1541)、王肯堂的《疡医准绳》(1606)、陈实功的《外科正宗》(1617)、张景岳的《外科钤》(1624)和陈司成的《霉疮秘录》(1632)等著作中还分别载录了若干病例。诸家一致认为梅毒是传染病,汪机、李时珍、陈司成等人认识到梅毒有性交和非性交的传染途径,薛己记录了小儿先天性梅毒。[48,64- 68]
土茯苓治疗杨梅疮,据今人考证是薛己首先提倡。[68]薛氏《外科心法》认为汞剂“收毒于内,以致迭发”,于是主张使用萆薢汤,由川萆薢二两加水煎服,今人认为这里的川萆薢就是土茯苓。后来李梃《医学入门》(1575)的仙遗粮汤、龚信《古今医鉴》(1577)的神仙汤等,都以萆薢(土茯苓)为主要成分。[64]汪机积累收集了不少民间治疗杨梅疮的简便方法,其一即愈后服萆薢汤。[65]陈实功《外科正宗》也有“虚弱溃烂疼痛不敛者,十全大补汤同土茯苓煎服”,及“土茯苓汤调人中黄末,每日数次,共饮四五分”治胎传梅毒的记载。[69]医话著作《续医说》和本草著作《本草蒙荃》、《本草真诠》、《本草纲目》亦记载菝葜类药物治疗杨梅疮的方剂,前文已经述及。
中国医家与同时代欧洲医生对于梅毒病源的解释不乏相通之处,两方都认为祸根是一种外来的邪毒,且都把毒气能够肆虐的原因归结到季节和风土。不止一位16世纪欧洲医生在诗文中说过,梅毒猖獗是因那一年欧洲各地的夏季都湿热多雨,这种湿性和热性产生出“腐坏的种子”和沼泽瘴气,而且洪水泛滥使得空气和土壤普遍地败坏,这才造成疫病横行。([58],140- 141页) 薛己认为杨梅疮是天行时毒,或通过传染而患,或因禀赋不足所得,认为湿邪是致病因素。[68]李时珍和陈司成认为杨梅疮发病与地理环境有关,如李时珍所说:“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温热之邪积蓄即久,发为疮者,逐致相互传染。”[70]
然而,中西医生在治疗时应用的理论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例如,汪机解释梅毒发病是相火妄动,煎熬津液,遂致浊痰流注,发为疮肿溃烂。他治疗上强调固本补元,主张“湿胜者宜先导湿,表实者宜先解表,表里俱实者解表攻里,表虚者补气,里虚者补血,表里俱虚者补气血。”[65]陈司成则在中国现存第一部中医梅毒学专著《霉疮秘录》中,将梅毒的不同症状归结为毒气进入不同经络的表现:“毒之相感者一气也,脏之见证者各异也。”而毒气进入人体后,“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中于阴,或中于阳;或伏于内,或见于外;或攻脏腑,或巡空窍;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有越经而传者;有间经而传者;有毒伏本经者,形证多端。”因此他倡导分经辩证论治,根据毒气之有无、轻重,分别采取发表、攻里、疏利、温补、凉解等治则。[66,67]
明代中医在菝葜类药材的使用上已经积有数百年以上的观察与经验,对药物作用机理的解释框架是气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无毒性。“萆薢,足阳明厥阴经药也。厥阴主筋,属风,阳明主肉,属湿,萆薢之功长于去风湿,所以能治缓弱痹遗浊恶疮诸病之属风湿者”;“菝葜,足厥阴少阴药,气温味酸,性啬而收,与萆薢彷佛”;“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药,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46],38b- 42a页) 实际应用方面,若以《本草纲目》收录的药方为例,除了治疗杨梅疮,它们主治的病症还包括:萆薢治腰脚痹软、小便频数、白浊频数、肠风痔、头痛发汗,菝葜治小便滑数、沙石淋疾、消渴不止、下痢赤白、风毒脚弱,土茯苓治骨挛痈漏、瘰疬溃烂。([46],38b- 42a页)
维萨里、莫纳德斯和奥尔塔书中给中国根找到的多种用途,例如发汗利尿、消肿镇痛、愈疮通痹等等,也与中医的用法相当接近。不过,这几本欧洲古籍里没有证据显示西医和中医在这方面有任何直接的知识交流,相似的用药思路恐怕只是整体论的医学思维导致的殊途同归的结果。
中国传统医学的梁柱是阴阳五行、虚实表里、脏腑经络,欧洲盖仑医学的框架是四体液、四禀性、六非自然,就理论构造而言,双方的体系难以对接;然而,中西医生给菝葜类药材找到的用途却并无什么本质区别。这或许再次说明,无论古今中外,医学里占据首要地位的永远是务实的精神。
在现代中国,通过政府的不懈努力,梅毒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度基本被消灭。[71]检索医学文献,目前有关中草药治疗梅毒的研究文章数量很少,主要集中在土茯苓的药理作用。通过本文第3节对于中医本草著作的回顾,我们知道明代医家将根茎形态及药用效果相类似的多种菝葜类药材基本上作为同种药物对待,因此我们也不妨将土茯苓和菝葜视为中国根的代表。
1990年,曾有中医根据20世纪50年代保留下来的记录对土茯苓方剂治疗梅毒的效果做出非常乐观的估计,认为疗效与青霉素相当。[72]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未注意到,早在1962年,中国皮肤性病学科的西医便以土茯苓治疗梅毒为题组织过学术讨论会,总结之前3年来关于土茯苓治疗梅毒的实验及临床治疗的研究。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未发现土茯苓对梅毒螺旋体有杀灭或抑制作用,不能控制梅毒感染,不宜用于孕妇梅毒或早期梅毒的治疗。[73]2010年的一篇综述文章总结了当今国内外对菝葜和土茯苓的植物学、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临床应用的研究概况和进展,发现不同实验肯定了菝葜的抗炎抑菌、抗凝血、抗肿瘤和降血糖的作用,也肯定了土茯苓的抗血栓、抗肿瘤、抗炎抑菌、镇痛、利尿作用。但是,用来测试抑菌活性的微生物中并不包括梅毒螺旋体。[36]另一位作者指出,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土茯苓可能通过增加尿量来促进体内汞的排泄,并通过保护肝肾功能达到解汞毒作用,但具体作用通道和机制尚未明确。尽管古籍中有较多关于土茯苓解汞毒的记载,土茯苓解汞毒的现代临床研究甚少,更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74]其他文章在肯定土茯苓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血栓、镇痛、抗炎、抗肿瘤等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为对于这种药材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够,一些经临床证实的疗效尚待理论支持。[75]整体看来,现代医学研究虽然确认了菝葜和土茯苓的一些药理作用,但它们对梅毒病原体没有直接的杀灭或抑制作用,对于汞中毒的解毒作用在目前也只是一种推测。
6 结 语
中国根是为应对梅毒的突然来袭而在16世纪前半叶引入到欧洲的中草药。随着欧洲印刷术的兴起,中国根的消息散布到比抄本时代广泛得多的受众手中。本文选取的记载了中国根的4种16世纪欧洲古籍都是深受当时人推重的作品,它们经由多次的翻译、再版、重印、改写、补订,将包括中国根信息在内的大量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传递给欧洲学术界和各个语言圈的大众读者。
新发传染病梅毒在欧洲激发出对新药物的空前需求。中国根具备发汗作用,相对廉宜易得,原产地又处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因而得到居住在印度的葡萄牙医生的关注和介绍,其后作为愈创木的替代药物大量贩运到欧洲。在欧洲甫一落地,它便被置入盖仑医学的理论框架中,直接袭用了愈创木的全套用法。并且同愈创木一样,在医药资源匮乏的时代,充当了类似于万灵药的角色。欧洲医生使用它的方式只是当时他们使用植物药的常规手续,治疗的时间节点是根据星占学推算而选择的。梅毒本身的特点,加上体液论医学的治疗惯例,使得后人无法根据当时的记载单纯评估中国根的药效。不过,欧洲医生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在16世纪晚期便已经认定中国根对治疗梅毒没有明确效果,但它仍作为秘方药的成分之一在欧洲医药市场继续存在。
本文中使用的几种欧洲古籍对中国根来源植物的记载比较简略含混。笔者结合中国学者对古本草的考证和对现代中医药市场的调查,推断中国根并非来自一种单一的植物,而是百合科菝葜族和薯蓣科多种植物根茎的制成品,是一大类药物的总称。今天把它们统称为菝葜类药材比较适宜。从商品属性的角度看,定义宽泛反而是中国根的一项优势。
产于中国的菝葜类药材在欧亚贸易的香药类货物中占据显要位置计约二百年,17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被更加廉价的美洲菝葜在市场上取代。它们最初的热销和最终遭到冷落,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商业的力量,医学界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是次要的。
在中国,明代医家面对新病梅毒,也曾重用菝葜类药物组成方剂,有的是为了治疗梅毒,有的是作为服用汞剂之后的解毒药使用。现代中医继承了这两方面的很多用法,但是,这些药治疗梅毒和解汞毒的效能与机制仍有待科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尽管16世纪中西医的理论框架完全不同,当年的西医为中国根找到的用法却与中医殊途同归,这充分体现了医学的务实本质。
中国根进入欧洲药物市场并在欧洲医生手中得到重新定义的过程,代表了药物及其知识的流通在航海贸易时代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方式。
致 谢2018年10月12—15日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办“全球视野下的医疗与社会:历史中的食、药与健康知识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组委会将本文初稿的电子文本上传网络,助其进入了广阔的传播空间。本次的匿名审稿人提供了诚挚而宝贵的修改意见,谨申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