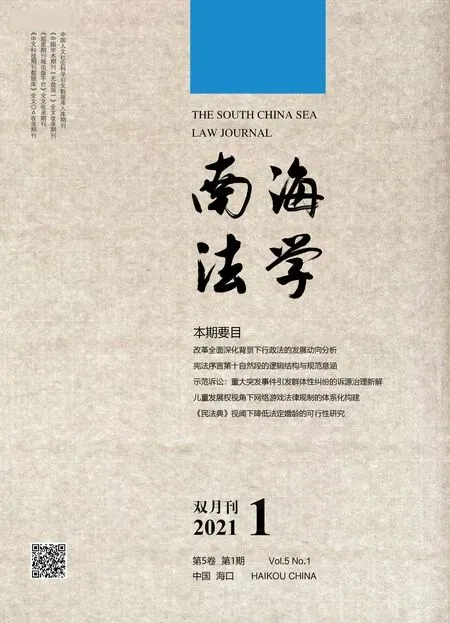美国堕胎案中司法审查标准的嬗变与前瞻——以“最严反堕胎法案”切入
2021-12-29薛天涵
薛天涵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6)
引言
2019年5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旨在限制堕胎的法案《阿拉巴马州人之生命保护法》(The Alabama 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①该法案编号为House Bill 314(HB314),分别由阿拉巴马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关于该法案基本情况及其中文文本,可参见薛天涵:《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美国最严反堕胎法案中译文》,“法学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Nqn-iGUGIp36ONUMnvaK0Q,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5月28日。,该法案承认尚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支持其具有合法的权利,并认为1901年的《阿拉巴马州宪法》不包括堕胎的基本权利,亦禁止使用公共财政资金为堕胎提供条件。其中最直接且重要的是该法案规定:除孕妇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禁止医生为任何阶段的妊娠妇女实施堕胎,并将堕胎和堕胎未遂(attempt⁃ed abortion)②attempted在刑法上特指“未遂”的犯罪形态,例如attempted murder(杀人未遂),在本法案中,指医生准备实施堕胎的具有可归责性的行为。分别定为A级和C级重罪③根据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刑法规定,触犯A级重罪,将面临终身监禁或10—99年监禁;触犯C级重罪,将面临1—10年监禁。See Alabama Code Title 13A.Criminal Code§13A-5-6.。这一法案对妇女堕胎施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被称为“全美最严反堕胎法案”,引发美国社会各界热议。美国妇女堕胎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和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冲突与博弈,更触及美国人最根本的价值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以下简称罗伊案)中以7:2的投票结果判决了一部得克萨斯州将堕胎犯罪化的法令违宪,这一判决为州的堕胎立法搭建了框架。罗伊案与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息息相关,虽然该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判决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该案并没有结束美国堕胎问题的纷争,反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对罗伊案的拥护和批判同时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常见话题,以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在后续的堕胎案中不断重申自己的立场。如学者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人的心灵被罗伊案撕扯得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对生命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是对自由的世俗崇拜”①任东来:《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其立宪者们大有“为生民立命”的抱负。从宪法的视角看,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的这部法案已然直接挑战了罗伊案以及后续一系列判例中所确立的妇女享有的作为基本权利的堕胎选择权等奠基性权利或者制度。那么,如果这部法案最终走进司法程序,②目前,已有就该法案提起的违宪审查案件,地区法官以本法案违反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先例而认定其违宪,法案被暂时中止生效。See Robinson v.Marshall,415 F.Supp.3d 1053,2019 U.S.Dist.就会将美国妇女堕胎的命运再一次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阿拉巴马州的挑战愿望能否实现呢?本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考虑到堕胎案在美国宪法理论和司法理论中所牵涉的深度和广度,③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可参见江国华、李鹰:《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河北法学》2021年第1期;方流芳:《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堕胎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司法解释》,《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封丽霞:《政党与司法:关联与距离——对美国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解读》,《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清华法学》2009年第6期。堕胎问题背后反映了胎儿的生命权、妇女终止妊娠选择权(right to choose/right to abortion)、妇女健康权等权利的激烈冲突④宪法学者认为,基本权利的冲突是指数个基本权利主体的基本权利相互对立,一个基本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会侵害另一个主体的基本权利。在堕胎问题中主要是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选择权间的冲突。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17,第294页。,本文的重心不在于宗教、伦理派别和势力等其他对法案前途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仅聚焦在司法审查标准这一问题上。这是因为罗伊案以及后续一系列案件中所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构成支持妇女堕胎权背后的方法论支撑,不但在微观上基于宪法文本解释的基本立场而实质地决定了堕胎案本身的裁判逻辑,也在宏观上基于释法说理的司法场域妥善地处理好了司法与政治立宪原则、司法与社会价值观等一系列美国宪制中的敏感问题,构成观察美国堕胎案的核心法治立场。
在具体的展开思路上,文章将首先基于历时性的逻辑对罗伊案以及后续案件所确立起来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梳理和介绍;其次,文章将对阿拉巴马州这一法案如何构成对前述审查标准的挑战展开分析,即描述挑战将在哪里发生,又是如何形成的;再次,文章将基于司法审查标准的历史及其可能遭遇的挑战,并结合美国司法运作的一般逻辑和运作惯例,试图回答前述挑战能否成功的问题;最后,文章将得出一个预测性的结论,并结合平衡基本权利冲突的美国经验这一主题,作出一个简短的评价。
一、堕胎案司法审查标准之嬗变
自罗伊案这一标志性案件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受理过多起有关妇女堕胎、生育自由、胎儿生命权等有关的案件。笔者通过分析美国历史上堕胎案的经典判决,试图爬梳并总结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以及利益平衡的相关逻辑。总体而言,以1973年罗伊案为开端,堕胎案的司法审查标准经历了从“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向“过度负担”(undue burden)标准的嬗变,在个案发展中赋予了法官更多的主观裁量权。
(一)严格审查标准的确立
罗伊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有关妇女堕胎问题的开创性、标志性案例,该法案推翻了大多数限制堕胎的州法律,从而使许多州选择将堕胎合法化。该案使得美国大部分地区被划分为“支持堕胎权”①“United States abortion-rights movement”为“美国争取堕胎权运动”,其中“rights”用复数,代表堕胎权是一项权利束。该运动主要主张妇女应享有终止妊娠的合法权利。See Schultz et al,The Ame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1ed.),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9,p.195.和“反堕胎权”②“Anti-abortion movement(also called the pro-life movement or right-to-life movement)”指“反堕胎运动”,该运动旨在通过取缔或限制堕胎来保护胎儿。在这个群体中,许多人认为人类的生命始于受孕。See Schultz et al,The Ame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1ed.),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9,p.195.两派。此案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堕胎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罗伊案中,法院按照严格审查标准来审查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案,指明了限制妇女选择权的条件。法院指出:“一国可在维护健康,维持医疗水平和保护潜在生命方面适当主张重要利益。在怀孕的某个时刻,只有当这些各自的利益变得足够有说服力,才能实现对限制堕胎因素的调节。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个人隐私权包括堕胎决定。但这项权利并非无条件,必须在法规中与重要的国家利益一起考虑。”③Roe v.Wade,410 U.S.113,93 S.Ct.705,35 L.Ed.2d 147(1973).④Ibid.当涉及基本权利时,只有重大的州利益才能够成为限制该权利的正当理由,而且只有当重大的州利益处于危险时,限制性立法才能被制定。
法院审查得克萨斯州堕胎法合宪性,主要基于对以下权利或者权益保护的冲突和平衡:妇女堕胎选择权、胎儿潜在的生命权、妇女的健康权与州的各项利益。
第一,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属于宪法正当程序条款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在论证过程中,法院试图用“隐私权”来解释妇女的堕胎选择权。法院认为,隐私权足够广泛并包含孕妇选择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但法院同时承认州有权规制某些隐私领域以保护州的利益,例如州可以主张保障健康、维持医疗标准、保护潜在生命等重要的利益,这也说明隐私权并非绝对权。持少数意见的大法官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在一部为自由人民制定的宪法中,毫无疑问,‘自由’的含义必须是广泛的。宪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提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个人选择权,但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自由’(liberty)所涵盖的范围比权利法案中明确规定的那些自由还要多。”④因此他主张妇女堕胎选择权能够被“个人自由”所包含。
第二,关于未出生的婴儿是否具有潜在的需法律保护的生命权。法院认为:除刑事堕胎领域外,法律并不承认生命始于活体出生之前,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未出生者任何法律权利。因此,法院反对得克萨斯州“生命始于受孕”的理论。在孕期某个阶段,州保护健康和潜在生命的利益居于主导地位。孕早期之后,胎儿才可能具备在母亲的子宫外独立生存的能力,此时州的立法保护才“具有逻辑的和生物学的正当性”①判决原文为“logical and biological justifications”,See Roe v.Wade,410 U.S.113,93 S.Ct.705,35 L.Ed.2d 147(1973).。
第三,妇女妊娠时期的健康权保护。法院提出,根据当前的医学知识,在孕早期结束之前堕胎死亡率比正常生产的死亡率还要低,因此,孕早期结束之时是州保护孕妇健康的时间节点。自此之后,只要与保护母亲的健康合理相关,州即可规制堕胎。举例而言,州可在如下领域进行规制:堕胎实施者的资格许可、堕胎是否必须在医院中进行、医疗设备许可等。尽管美国联邦宪法中不存在健康权规范,但在该案中,健康权通过正当程序条款获得了美国宪法的间接保护。②参见李广德:《健康权如何救济?——基于司法介入程度的制度类型化》,《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
最终,法院将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以平衡各利益之间的冲突:一是妇女妊娠前三个月结束前,堕胎的决定和实施由孕妇的主治医生作出医学判断,妇女可自行决定是否堕胎;二是前三个月结束后,国家为了保护妊娠妇女的健康,在妇女愿意的情况下,可以以与产妇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规范堕胎程序;三是在胎儿具有独立生存能力(viability)的阶段,国家为了促进其对潜在生命③See Roe v.Wade,410 U.S.113,93 S.Ct.705,35 L.Ed.2d 147(1973).的保护,可以管制甚至禁止堕胎,但根据适当的医学判断,为维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必须堕胎的除外。
在美国宪法中,当法院发现一项法案侵犯了个人享有的基本宪法权利时,经常运用严格审查标准来判定该项法案是否违宪。为了满足严格审查标准,法律或政策的规定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第一,政府能够证明该法案对于实现“不可抗拒的州利益”(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是必要的,虽然法院从未明确界定一项州利益是否不可抗拒,但这一利益通常指的是必要的或关键的东西,例如国家安全,保护群体的生命等。
第二,法案的规定“密切契合”(narrowly tailored)此种不可抗拒的目的,如果法案涉及的范围太广,则不能认为法案符合“密切契合”的规定。
第三,运用“最小的限制手段”(least restrictive means)去实现此目的,否则法院将判定此法案违宪。严格审查是美国司法审查最严格的标准,也被法院用于判定一项宪法权利或宪法原则是否应当让位于限制该权利或违反该原则的政府利益。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对于严格审查标准性质与目的的解读一直存在矛盾,这也影响着该审查标准的实施。对此,法院存在着三种解释,也形成了严格审查的三重标准:
第一,不论政府的动机如何,严格审查都体现了对侵犯基本权利行为几乎绝对的禁止,但是在政府可以证明侵权是避免高度严重甚至灾难性损害所必需的情况除外。
第二,严格审查标准在本质上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的比例原则审查(proportionality inquiries),都是平衡各方权利的方式,在两种情况下,法院都应当审查对受法律保护自由的侵犯是否能因其所带来的好处而被证明为正当。
第三,严格审查并不能决定侵害基本权利何时能被相应的政府利益证明为正当,该种解释将宪法权利定义为不被以违禁目的支配的政府行为所损害的权利,例如以牺牲少数族裔为代价促进白人特权,发现违禁目的需要立即予以谴责。④See Fallon,Jr.,Richard(2007).“Strict Judicial Scrutiny”.UCLA Law Review,54:1267.罗伊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采用的严格审查标准一定程度上符合上述的第二种解释,法院通过妊娠三阶段的框架平衡相冲突的权利与利益,这种依据时间的客观划分方式为合宪性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导致绝大多数反堕胎法案因违宪而无效。
(二)过度负担标准
自罗伊案判决后,在后续美国堕胎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基本贯彻了罗伊案的判决理由与基本精神。但随着几十年来美国国情的风云变幻与大法官的迭代,法院对堕胎案判决较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许多新的理由与观点,司法审查的标准也在具体个案中演变与发展,并在以凯西(Casey)案和海勒施泰特(Hellerstedt)案为代表的案件中形成了新的过度负担标准。
过度负担标准规定立法机关不能制定过于繁重地限制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该审查标准起源于19世纪末,后被运用于堕胎案中。1989年的韦伯斯特诉生育健康服务中心案(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简称韦伯斯特案)中,奥康纳(O'Connor)法官提到了“高昂的费用给妇女的堕胎决定带来了‘严重和不必要的负担’”①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492 U.S.490.。1992年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简称凯西案)将罗伊案严格审查标准替换成过度负担标准。本案肯定了宪法优先保护妇女堕胎选择权的原则,但法院推翻了罗伊案的三阶段论。多数法官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胎儿被证明可以在第23或24周具有生命而不是在罗伊案中理解的第28周。”②Ibid.在该案中,上诉人凯西要求法院审查1982年《宾夕法尼亚堕胎控制法》(Pennsylvania Abortion Control Act)对人工流产施加的负担以及法案保护的利益。本案法官认为,造成过度负担的法律限制是“在妇女选择将一个不能存活的胎儿堕胎的过程中有目的地设置实质障碍(substantial obstacle)”③Ibid.。即使一项法规的目的是保护潜在生命利益或另一有效的国家利益,如果它在妇女选择权的道路上造成实质障碍,也会成为“过度负担”。因此,该案中联邦法院判定法案中妇女堕胎需要通知配偶的要求违宪,因为这一规定“使丈夫能够对妻子的堕胎选择行使有效的否决权,不利于阻止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情况的发生”④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505 U.S.833(1992).。最终法庭认为《宾夕法尼亚堕胎控制法》没有对妇女选择权构成过度负担的几项限制是合宪的,而构成过度负担的限制是违宪的。⑤See June Medical Services,LLC v.Russo,591 U.S.(2020).在全妇女健康联盟诉海勒施泰特案(Whole Woman's Health v.Hellerstedt,简称海勒施泰特案)中,法院裁定:得克萨斯州不能对提供人工流产服务施加限制,以防给寻求人工流产的妇女带来了过度负担。⑥See Crockett &Emily,Pro-choice advocates just won the biggest Supreme Court abortion case in decades,Vox,June 27,2016.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法官发表意见,认为:“那些要求堕胎的医生在当地医院获得‘优先许可’,并且要求诊所拥有昂贵的医院设施的规定侵犯了妇女的堕胎权。”⑦See Adam Liptak,Justices Overturn Texas Abortion Limits:“Burden”Is Found-10 Clinics to Stay Open,The New York Times,July 3,2016.多数法官得出结论:“(得克萨斯州的规定)对妇女寻求堕胎的道路上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每一个给堕胎带来过度负担的规定都违宪。”⑧Hurley&Lawrence,Supreme Court firmly backs abortion rights,tosses Texas law,Reuters,June 29,2016.金斯伯格(Ginsburg)法官写道:“许多医疗程序,包括分娩,对患者的危害更大,却不受医院特权的要求。因此不能认为该法案可以真正保护妇女的健康,但可以肯定此法案只会使妊娠妇女更难堕胎。当一个国家严格限制获得安全和法律程序的机会时,处于绝境的妇女只能求助于非正规从业者。”①Wray&Dianna,The Supreme Court Strikes Down the Texas Abortion Law HB2,Houston Press,June 27,2016.该案的裁判结果对判断后续类似法案的合宪性产生了广泛影响。如路易斯安那州在2014年通过的第620号法案,要求实施堕胎的医生需要在30英里内的医院获得许可,最高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裁定:“路易斯安那州的法案同样违反宪法。”②June Medical Services,LLC v.Russo,591 U.S.(2020).
可以看到,法院判断一部堕胎法案是否造成“过度负担”的主要依据是法案的目的和效果。
第一,就目的而言,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案(City of Akron v.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中,奥康纳法官指出:“如果特定的法规没有规定‘过度负担’基本权利,那么我们对该法规的评估仅限于我们判断该法规是否合理、合法,以及是否与州目的相关。”③City of Akron v.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462 U.S.416,453.州不能试图阻碍妇女的选择,也不能颁布旨在打击堕胎选择权的规定,但是允许州表现出支持对妇女足月分娩的倾向性态度。
第二,就效果而言,必须依据事实,从被限权的妊娠妇女的角度来分析在个案中审查一部法案引发的所有直接的和附带的后果。这意味着,一项规定可能会被废除,即使它只对它所影响的百分之一的女性施加了实质性的障碍。④See 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505 U.S.833(1992).
但是相关经典判例的判决意见并没有为适用该标准提供一个系统且统一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这一缺陷可能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扩大以及妇女堕胎机会的地区差异,从而剥夺一些妇女的宪法权利。凯西案中法院的意见未能指出“旨在告知妇女自由选择”的法规应该如何区别于那些旨在“阻碍妇女自由选择”的法规。⑤See Metzger,Gillian E.“Unburdening the Undue Burden Standard:Orienting‘Casey’i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Columbia Law Review,vol.94,no.6,1994,pp.2025–2090.在实践中,对限制堕胎法规的司法审查力度实际取决于法院为“不当负担”设定的阈值有多高。在凯西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宾夕法尼亚州反堕胎法案中的大多数规定,这表明最高法院实际上将对妇女堕胎行为设置一个较高的门槛,也许只有当一项规定接近禁止妇女堕胎时,才会被界定为妇女堕胎道路上的实质障碍。
美国学者通常将过度负担标准中的目的性与效果性与理性基础审查(rational basis review)及中度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类比。理性基础审查是美国司法审查的最低标准,指审查政府的行为是否与合法的政府利益“合理相关”⑥在琼医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诉鲁索案中,法院认为,堕胎法规只要不构成实质障碍并满足与“合法目的”(“legit⁃imate purpose”)“合理相关”(“reasonably related”)的最低要求,即有效。See June Medical Services,LLC v.Russo,591 U.S.(2020).,其禁止政府对自由施加非理性或武断的限制。而中度审查介于理性基础审查与严格审查之间,为了通过中间审查的测验,必须证明法律或政策实质上运用相关的手段来促进重要的政府利益。结合对判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对不当负担设定的门槛可结合上述两种标准来判定。
二、现有堕胎案司法审查标准面临的挑战
目前,联邦最高法院在堕胎案中一般采用过度负担标准对州反堕胎立法进行司法审查。在美国分权制衡的体制下,一方面,在司法与立法存在明显分歧时,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来影响和修正立法;另一方面,部分州的反堕胎立法也在向联邦最高法院不断施压,以期推翻现有的司法审查标准。
美国哲学所吹捧的司法独立是相对的,实质上往往无法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通过联邦司法选任与州法官的选举制度给司法系统打下深刻烙印,各种冲突最终往往转化为没有一个司法问题、社会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才得以解决的。①[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9页。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代表着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最高法院面对阿拉巴马州如此严格的反堕胎法案的冲击,现有的过度负担标准主要面临以下两种挑战。
(一)过度负担标准的解释性挑战
从罗伊案的严格审查标准到过度负担标准,是由一个明确客观的“三阶段”标准到一个更主观的判断标准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法官们必须在个案中审查一项规定所施加的负担,并确定该负担是否过重。有学者指出,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合理的国家目的和审查的程度发生了变化。②Field M A.Abortion law today.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1993,14(1):3-24.对胎儿具有生存能力之前堕胎的限制不再需要“密切契合”“不可抗拒的州利益”,如果这样的限制合理地与保护胎儿生命的合法州利益相关,那么其不构成不当负担。
从凯西案等判例中可以发现,目前过度负担标准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且统一的判定方法,“它是一个公认的抽象原则”③Morgan v.Commonwealth of Virginia,328 U.S.373,377.,州立法对妇女选择权的侵犯在何种情况下能被定义为“过度”(undue),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在限制堕胎立法的目的是否与州利益合理相关的问题上,立法目的的射程、州利益的涵盖范围、限制妇女选择权的方式与州利益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的合理性等问题都存在大量的解释空间;另一方面,法案是否对妇女选择权构成重大障碍的问题的判定不仅取决于个案情况、具体州情,更涉及反堕胎法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效果,且法案对堕胎的限制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实质障碍,是完全剥夺了妇女的选择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为妇女堕胎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以《阿拉巴马州人之生命法》第3条“判断妊娠妇女是否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需要两位在该州获得执业许可证的医生联合决定”的规定为例,其是否构成实质障碍需要法官结合阿拉巴马州具体州情及个案中妇女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未来对“最严反堕胎法案”的合宪性审查中有可能为过度负担标准设定更高的阈值,意即限制措施要极其严格才会被认定为不适当。
(二)平衡权利冲突的挑战
近年来,美国部分州不断通过限制堕胎立法制约司法,以期推翻罗伊案的判决。目前,有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俄亥俄州等19个州通过了“心跳法案”④目前,有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俄亥俄州通过了“心跳法案”并生效。怀孕大约六到七周时,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但是使用多普勒胎儿监护仪(Doppler fetal monitor)时胎儿心跳在妊娠12周时才可能被检测到。许多孕妇在怀孕后六周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怀孕情况。因此大多数想堕胎的妇女在怀孕六周后才会流产。因此支持堕胎权的人士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胎儿心跳法案实际上是禁止流产的。See Belluck&Pam,What Do New State Abortion Laws Really Mean for Women?,The New York Times,May 18,2019.,这些法案规定,一旦检测到胚胎或胎儿心跳,堕胎便成为非法行为。⑤Lithwick&Dahlia,A Regrettable Decision,Slate,August 11,2015.面对此种情况,最高法院极有可能推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案系列判决,美国国内对此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上。
司法审查标准中对“适度”(due)的界定往往伴随着对权利冲突的平衡。在堕胎案中,一方面,胎儿生命权、妇女健康权以及堕胎选择权等基本权利存在冲突。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行为的防御,①参见韩大元:《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及其平衡》,《人权》2020年第3期。然而胎儿生命权是否受保护以及从何时开始受保护需要结合宪法的具体规定。健康权的防御权功能包含了非歧视原则下其所具有的健康平等权、隐私权、与健康有关的程序参与权,②参见李广德:《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基于健康权的论点使堕胎权支持者能够更好地解释堕胎选择权如何帮助妇女获得平等公民权。③See Ziegler M.Abortion and the Law in America:Roe v.Wade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8(2020).虽然这种选择权不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但联邦法院将其归纳在隐私权这一基本权利的范畴。因此,上述权利冲突是宪法层面的。然而联邦法院享有宪法最终解释权,妇女生育自主选择权是否受宪法保护历来存在争议,如果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那么它所属的权利位阶将低于其他宪法规定的权利,在面临权利冲突时将无法得到优先保护。妇女的健康权亦是如此,由于美国联邦宪法不存在健康权规范,健康权受宪法保护的程度也取决于司法审查的标准,具有较大变数。
另一方面,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州公共利益存在冲突。例如妇女选择权与国家公共健康的冲突。从目前的实践来看,针对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调和与解决,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中的个案衡量与各州的立法衡量存在矛盾,亦需要未来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可行的判定标准。
三、司法审查标准下美国最严反堕胎法案的合宪性前途
公权干涉的行为要想被法院认为合法正当,必须满足一定条件,虽然判例中没有明确概括,但可以结合基本权利裁判的普遍经验,④有学者在对欧洲人权法院基本权利裁判的司法审查标准上,进行了审查步骤的提炼和框架总结,从而为堕胎案中的基本权利审查学理分析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将目前联邦法院采用的过度负担标准的审查步骤拆分为三个方面或者阶段:(1)合法性(狭义层面上的合宪性);(2)目的合理性;(3)效果适度性。因此,站在过度负担标准的立场上,这里尝试对阿拉巴马州“最严反堕胎法案”的合宪性展开一个预判论述,以此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这部法案能否成功挑战罗伊案以来的相关宪法判例。
(一)合法性审视
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制度保障。1973年的罗伊案对各州立法权构成了严重挑战——联邦司法侵入各州立法领地,它确立的妊娠“三阶段”划分实际上是给各州政府提供了一个立法纲领。韦伯斯特案进一步明确:在怀孕中期限制堕胎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美国的政体,最高法院有权审查联邦和州法律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宪性)。
在现行的州法律中,《1975年阿拉巴马州法典》(Code of Alabama 1975)第13A-6-1节定义故意杀人的对象包括子宫内任何阶段的胎儿而不论其是否有独立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因此法案对胎儿的生命权采取绝对保护的原则,任何妊娠阶段的堕胎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在讨论胎儿生命权的问题上,HB314法案采用“心跳说”——“在第6周左右,胎儿的心脏开始跳动。在大约第8周时,可以通过超声波测听到胎儿心跳。第10周时,多普勒仪(A fetal Doppler)可以探测到胎儿的心跳。”该法案也被称为“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其承认妇女可以堕胎的唯一情况是:“如果在阿拉巴马州获得执业许可的主治医生认为必须进行堕胎以防止对妊娠妇女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则应允许进行堕胎。除此法案中定义的紧急医疗情况①根据《阿拉巴马州人之生命保护法》的定义条款(第3条),医疗紧急情况(Medical emergency),指根据合理的医学判断,这种情况下孕妇的身体状况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必须终止妊娠,以避免本法所界定的严重健康风险。外,还应由在阿拉巴马州获得执业许可的第二位医生书面确认(第一位)医生的决定。该确认应在堕胎完成后的180天内进行,并作为允许堕胎的证据。”
《阿拉巴马州人之生命保护法》的立法逻辑是坚决保护胎儿的生命权,但它并不合法。前述罗伊案的裁判理由已经表明:美国联邦宪法并不承认生命始于活体出生之前,除特定情况外,法律没有赋予未出生者任何法律权利,即不承认胎儿具有一定人格,只赋予胎儿一定的继承资格——未出生的孩子能通过继承或者其他类型的财产转移获得利益,并由诉讼监护人代表之。上述所涉利益需视活体能否出生而定。总之,在法律上,未出生者从未被视作完整意义上的人。
(二)目的合理性审查
观察判例可以发现,目的合理性至少包括两部分:第一,干涉的目的必须正当。例如为了保护妇女的健康权。第二,干涉的措施必须适合该目标。例如凯西案中法官认为对选择权的限制需要满足与合法目的“合理相关”(reasonably related)的最低要求。
上文已经提到,法案目的是保护胎儿的生命权。就胎儿是否有生命权暂且不论,在胎儿生命权和妇女的选择权之间,笔者认为,从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在妊娠的特定阶段优先保护选择权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首先,从权利产生的根源上看,女性是孕育生命的母体,只有母体的自主权得到尊重,胚胎的生命权才能得到保证;其次,从道德准则困境上看,母子关系是最亲密的亲子关系,从胚胎的生命权出发,母体的利益更应该关注;最后,只有当母体已经做好准备愿意接受孩子的到来,孕育胚胎才有意义。
而实际上,选择堕胎的女性大多是意外怀孕的,包括未婚、婚外怀孕的女性,从长远来看,“母亲的身份或多余的孩子会将悲惨的生活和未来强加在妇女身上。心理上的伤害可能迫在眉睫。照顾孩子可能影响她的身心健康。另外还会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与这个多余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痛苦,以及把一个孩子带进一个在心理上和其他方面无法照顾他的家庭所产生的旋涡。”②[美]斯坦利·I.库特勒:《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朱曾文、林铮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600—601页。将来孩子诞生后的健康权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一个女人不得不孕育一个不受欢迎的生命,这对那个即将诞生的生命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③有学者认为,生命权和选择权的博弈,从中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即法律是否应介入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或宗教学说,这也是罗伊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参见陈忠林、周芸野:《道德困境与法律中立——再论“罗伊诉韦德案”及实践检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1期。而“最严反堕胎法案”并未将强奸或堕胎作为禁止妇女堕胎的例外情况,有可能将损害的利益范围进一步扩大,这种过分严苛的干涉措施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胎儿的生命权的目的。
除此之外,从法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最严反堕胎法案”的社会效果有限。虽然合法正规的堕胎被限制或禁止,但地下的堕胎并不会结束,这将会严重阻碍妇女及胎儿的生命健康保护,亦不利于维护州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合法利益。怀孕的妇女不仅要自担生产风险以及日后的养育风险,她们的医疗健康也不能得到保障,妇女的权利负担会增大。因此,综上所述,“最严反堕胎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目的合理性。
(三)效果适度性考量
在堕胎案的司法审查中,效果适度性主要指限制堕胎的立法在特定阶段和背景下不能给妇女堕胎施加直接的和附带的实质障碍。事实上,“适度”(due)这一术语暗含了比例性与平衡性。比例性是指限制手段要与限制的目的相符,平衡性是指为了保护免受不适度的负担,法院必须在立法目标的重要性和负担的利益的重要性之间取得平衡。①See Metzger,Gillian E.“Unburdening the Undue Burden Standard:Orienting‘Casey’i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Columbia Law Review,vol.94,no.6,1994,pp.2034.
以宪法的视角审视,在特定情况下,同为基本权利的生命权与选择权处于博弈状态,属于不同主体基本权利的冲突。为限制妇女滥用堕胎权,国家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措施,以期实现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的双重保护,并实现与其他利益的妥当配适。当竞争性的宪法权利发生冲突之后,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语境来确定哪一种价值处于更重要或优先被保护的地位,以确保特定主体基本权利总量的最大化。通过对比其他反堕胎法案,②与其他类似法案做比较也是判断适度性的重要依据之一。See Metzger,Gillian E.“Unburdening the Undue Burden Standard:Orienting‘Casey’i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Columbia Law Review,vol.94,no.6,1994,pp.2033-2035.阿拉巴马州最严堕胎禁令“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对所涉权利及州利益进行对比研判,该法限制堕胎的唯一例外——“严重健康风险”属于极端小概率情况,相当于禁止绝大多数的堕胎行为,并对未遂的堕胎行为苛加重刑,这对妇女堕胎选择权施加了不合比例的障碍,造成了权利保护的失衡,明显违反了适度性的原则。
四、结语:平衡基本权利冲突的美国经验
基本权利具有相对性,它的存在和实现是有条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受到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被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其中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可以被此处的“私生活”涵盖。《欧洲人权公约》的一些条款也明确:为了公共利益、保护他人合法权利等合法目的,部分基本权利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③参见邱静:《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与人权保护的相对性》,《国际论坛》2019年第5期。但在面临冲突时,基本权利并非总能胜出,基本权利的保护亦受制于多种因素。
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的问题。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维的,阿列克西假定了四种可想象的概念结合方式:第一,个人权利意味着公共财产;第二,公共财产意味着个人权利;第三,公共利益以个人权利的存在和满足为基础;第四,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独立地存在于任何“手段—目的”关系或身份关系中。④See Aileen McHarg,Reconcil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Conceptual Problems and Doctrinal Uncer⁃tainty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he Modern Law Review,Vol.62:5,p.672(1999).拉兹认为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理解权利的核心,而这一冲突与我们所处的文化、道德信念和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⑤See J.Raz,“Rights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44-50.但对于权利(尤其是受司法保护的人权)的理解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保护个人的利益或选择不受公共利益的不当侵犯。①Aileen McHarg,Reconcil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Conceptual Problems and Doctrinal Uncertainty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he Modern Law Review,Vol.62:5,p.672(1999).一部理应保护个人不受公权力侵害的法律有时可能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它本身可能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批准对权利的限制,这需要法官找到平衡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的方法,也需要对产生冲突的基本权利进行平衡。“平”是在各种权利及利益之间进行不断权衡,是在规范和事实间不断“往返流盼”,也是人权司法保护中的价值目标,联邦法院在堕胎案中的司法审查标准虽然还存在诸多瑕疵,但为平衡权利冲突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当前,联邦最高法院对堕胎案件的态度及司法审查标准牵涉着许多因素,终身任职的大法官能为总统提供历史机遇,影响超越总统在任期中的国策方向。②参见[美]戴维·M.奥布赖恩:《暴风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胡晓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0页。可以看到,从罗伊案到韦伯斯特案③在该案中,多数法官提出,要求法院“修改和缩小罗伊及其后继案件对妇女选择权的保护范围”。See 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492 U.S.490(1989).再到凯西案和海勒施泰特案,从严格审查标准到过度负担标准,最高法院对妇女堕胎选择权的保护力度减弱,给予了州立法更宽泛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对阿拉巴马州“最严反堕胎法案”的合宪性前途进行了基于规范逻辑的分析预测,但这部法案的前途命脉仍然取决于美国人民,尤其是阿拉巴马州人民。因为按照美国宪制的基本惯例,只有通过个案司法的裁判方可最终提请美国联邦法院作出是否违宪的结论。但尽管如此,通过对阿拉巴马州法案的研究,可以一窥美国宪制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多重因素对立法和司法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