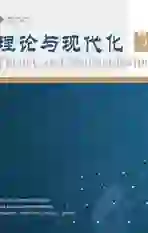“真理”考辨
2021-12-28周可真
周可真
摘要:“真理”一词在古汉语、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中各有不同含义,且其语义多重。在现代汉语中“真理”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或正确认识;二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其中第一种含义是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概念,其思想源头是古希腊“符合论真理观”,更直接和更主要的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但又不尽同于后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理概念,是在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概念,把真理本质地理解为知与行的历史统一以及在这个历史统一关系中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自由从抽象到具体、从观念到实在的历史性转化关系。
关键词:真理;知与行;精神力量和意志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3-0088-11
尽管人们经常使用“真理”一词,尤其在一些宏大叙事上,所谓“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为真理而奋斗”之类,更是十分庄严与郑重的说辞,但这些说辞中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这些说辞倒是表明了“真理”與“知识”并不等值。如果说“追求真理”还可以被替换成“追求知识”,那么“忠于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就很难被替换成“忠于知识”“为知识而奋斗”了。至于“知识创新”,就更不能被替换成“真理创新”了,这尤其凸显了“知识”与“真理”之间的语义差别。
一、“真理”的语义考查
(一)古汉语中“(真)理”的四种含义
在汉语系统中,“真理”是由“真”和“理”两个词素所构成的一个偏正式的合成词,其中“理”为该词的中心要素,“真”则是其修饰因素。因此,无论有没有这个“真”字,都不会影响该词的核心意义。单单一个“理”字,也可独立成词,且足以概括“真理”一词的核心意义。通观中国古代学者、哲学家所论之“理”,不外乎是下述四种含义。
1.客观事物之理——北宋理学家张载论之曰:“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1]
2.文辞义理之理——如晋葛洪《抱朴子·钧世》:“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方之于士,并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艺文,不可谓一例也。”[2]清代朴学家凌廷堪于此类理,评论甚精:“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3]
3.宇宙本体之理——如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谓“理一分殊”[4]的“理”之类。
4.“本心”之理——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于此类理,言之最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添一分”[5]。“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5]45。“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5]239-240
与“理”相比较,“真理”一词在古汉语典籍中出现较晚。先秦典籍中有“真宰”“天理”“道理”等名词①,但无有“真理”之名。直到魏晋,佛教中观学派兴起,才有“二谛”(“真谛”与“俗谛”)之说。此派学者据有关佛教经论(如《摩诃般若经》《中论》),将“二谛”理解为诸佛教化众生而假设的言教②,并以“真谛”为其第一义谛,视之为佛法真义,故又称其为“真理”。萧统所著《令旨解二谛义》有云:“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6]此“真理”乃“真谛”之同义词(案:后来它们都被英译为“truth”),是指为心有所惑者所不解的诸佛言教之实义。以此,东晋佛学家慧远乃有“理蕴于辞”[7]之说,意指佛法实义隐含于佛教经论。要之,作为一个佛学术语,“真理”所指是属于上述第2类理——文辞义理之理。
中唐以后,儒家学者反佛风气渐行,至宋而益盛。宋明理学家虽多有出入于佛、老者,且暗取其义,然表面上常为伸张孔孟之道而辟佛斥老,故“真谛”“真理”“真如”一类的佛家术语亦颇为一般理学家所忌而不取。像顾炎武这样不但辟佛斥老而且批评“今之理学,禅学也”而力倡“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8]的学者,甚至反对使用“真知”一词,他说:“‘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原注:《荀子》‘真积力久’亦是此意。《黄庭经》曰‘积精累气以为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9]顾炎武认为,庄子“真知”说的实质是在于否定“学而知之”,主张以“无知”为“真知”,所反映的是“以生为寄,以死为归”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只有“以生为寄,以死为归”的“真人”才推崇“真知”。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居然觉得,光讲“真知”还不够,须讲“真理”才得劲,这或许是明清以后中国又更进一步佛教化的缘故吧。
(二)古希腊语中“aletheia”(真理)的四种含义
在西语中,与汉语“真理”一词相当的一个古希腊语词是“aletheia(aλ?浊θεια)”。吴国盛根据海德格尔对该词的解读(即从现象学角度将它视为由前后两个词根“a-”[非]和“letheia”[遮蔽]组成的一个否定性的词,意味着“去掉遮蔽的状态”或“揭开遮盖而显示出来的状态”),认为“在其原本的意义上,aletheia作为‘真理’是‘去蔽’和‘敞开’”③。但问题是这个“去蔽”和“敞开”究竟是对自然的过程还是指人为的过程而言呢?若对自然的过程而言,则“aletheia”应该是“体(本体、实体)显于用(现象、功用)”之意。德谟克利特所谓“真理和现象是同一的,真理和显现于感觉中的东西毫无区别”[10],显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aletheia”一词——该词在这里是指客观事物本身(与显现于感觉中的现象相对);若对人为的过程而言,则“aletheia”应该是“解蔽以得周道”④之意,赫拉克利特所谓“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10]29,显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aletheia”一词——该词在这里是指对自然运动法则毫无偏曲的陈述。
与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都不同,苏格拉底则认为:“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是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10]175照此观点,真理既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周全陈述,而是存在于心灵世界并依靠心灵本身去把握的东西。继承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更认为,要获得这样的真理,须靠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并且“如果我们要对任何事物有真正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灵魂若是和肉体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有纯粹的知识;知识如果真能获得的话,也必须是在死后才能获得”[11]。
曾师事柏拉图20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尊敬他的老师,但思想上却不敢苟同他的老师,遂讲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千古名言。在真理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不同于柏拉图的真理观,而是认为“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12] 这是最早的“符合论真理观”,其与晚期希腊斯多葛派关于“真理是对象和意识的一致”[13]的真理概念形成对照: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概念是强调了与对象(“事物之实是”)相符合,而斯多葛派的真理概念是强调了与意识(“宇宙理性”⑤)相符合。但二者也有共同点,即它们都把真理归结为与本体(亚里士多德的“实是”、斯多葛派的“理性”)相一致的现象,故均可被归入“符合论真理观”。
要之,古希腊语“aletheia”(真理)一词有四种含义:1.客观事物本身;2.对客观事物的如实陈述;3.存在于心灵世界并依靠心灵本身去把握的理念;4.现象与本体的一致。
(三)英语中“truth”(真理)的两种含义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宣称:“一切真理都来自上帝”;“上帝本身不仅是真理,而且还是最高和第一真理。”[14]这个“真理”和苏格拉底所说的那个“真理”恰好形成鲜明对照:它们的关系犹如朱熹的“天理”和王阳明的“本心”,一个在“天”,一个在“人”,似有“天”“人”之别。然究其实,它们都不过是外于客观事物的“形上之理”——这“形上之理”到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终于被归结为“绝对理念”。对于这类“形上之理”,弗兰西斯·培根将其归入宗教神学信仰范畴,认为它是依靠神的启示得来的真理,这完全不同于从感觉经验得来的真理。不过,在培根看来,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真理互不相干,但不是不共戴天,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培根的这种“双重真理”觀与英语中同汉语“真理”相当的一个单词“truth”的含义颇有一致性。《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truth”词条之第三目是这样解释的:“fact,belief , etc accepted as true:真理;真义”[15]。这里的英文解释可具体化为“被承认是确实发生了或完成了的事(fact)或被承认是确实的或合于事实的所信之事或教义(belief)等”。要之,“truth”的基本含义有二:“fact accepted as true”和“belief accepted as true”。前者大抵相当于培根所谓从感觉经验得来的真理——或可称为“事实真理”⑥;后者大抵相当于培根所谓依靠神的启示得来的真理——或可称为“信仰真理”。
(四)德语中“Wahrheit”(真理)的本义
叶秀山曾指出:“中文译成‘真理’的德文为‘真(东西)’(Wahre)的抽象名词化——‘Wahrheit’,即‘真(东西)’之所以为‘真(东西)’的那种特性。‘真’与‘假’(Falsche)相对,一切‘有对’(相对)的东西都有‘(虚)假性’,而只有‘无对’(绝对)的东西才真的是‘真(实)’的。”[16]
如果说“Wahrheit”就是意味着“绝对”,或只有“绝对”才是“Wahrheit”,那么“Wahrheit”未尝不可以被汉译为“道”——中国先秦道家老子哲学之“道”:这个“道”不仅意味着“一”“独立”(“无对”),还意味着“朴”“全有”(无所亏遗的全体;all-inclusive totality)⑦。当然,它还意味着“无形”(无感性特征)、“无名”(无可称谓)。在老子哲学中,这个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不是“知”(感知和理智)的对象,而是在自我“涤除玄览(鉴)”后所达到的“无疵”“虚静”的“心”之“观”(直觉)的对象。这样一种只有依靠神秘直觉才能与之“玄同”的东西,如果也可以把它称为“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应该是与上述所谓“信仰真理”(“belief accepted as true”)大致相当的。
(五)现代汉语中“真理”的两种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1996)将“真理”释义为“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17]。这个解释近似《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94)“(真理)即主体的认识同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相符合或相接近”[18]之说,其共同点是都把真理理解为与客观事物本身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意识或认识,在这种联系中意识或认识与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有一致性。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使用的“真理”概念则有别于上述两本书所阐释的“真理”概念,他写道:“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19]“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9]296
其中,前一段所讲的“真理”是指某种认识或理论——据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中所提出的“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20]的论断,这种被称为“真理”的认识或理论,也就是反映客观实际并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
后一段所讲的“真理”是指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的对象——从下面所引《实践论》的另一段论述来看,这个被称作“真理”而其实是人们所要认识的对象的东西是客观过程的规律:“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19]292-294
这里“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和“理性之认识……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这两个提法分明是表示“客观真理性”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是同一概念,“客观真理”与“客观过程的规律”也是同一概念。
要之,在现代汉语中,“真理”一词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或正确认识;一是指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律。
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理概念
“真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或正确认识”,这是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真理概念,这个意义的“真理”之名在古汉语系统中未曾出现过,应该是一个外来概念。
这个外来概念首先跟古希腊的“符合论真理观”有关。古希腊的“符合论真理观”属于一元论哲学的真理观,其肯定现象和本体有同一性,实质是将世界统一的基础归结为某种绝对的东西,并视之为世界的本体。它所推崇的真理,本质上是作为世界统一基础的宇宙本体;其崇尚真理,不过是追求世界的统一性,要求以绝对、唯一的本体来统摄相对、多样的事物。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符合论真理观”亦是属于一元论哲学,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的真理观,其思想特征在于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其所推崇的真理本质上是属于物质范畴,其崇尚真理不过是主张意识统一于物质,要求意识同物质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真理概念乃是一个物质本体论概念,与古希腊“符合论”的真理概念固然有原则性区别,但在一元论哲学思维方式上是彼此相通、互相一致的。由此可以说,古希腊“符合论真理观”是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真理观之思想源头。
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真理观更为直接和更主要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以德语为母语的德国哲学家,他们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其真理概念既与德语中“Wahrheit”(真理)一词的本义有语言文化联系,更与德国古典哲学真理观有思想传承关系。
上文提到,“Wahrheit”的本义是“无对”(“绝对”)。因此,如果是在一元论哲学意义上,则“Wahrheit”照理是既可用来指称具有“无对”(“绝对”)性的世界本体,亦可用来指称与世界本体相符合的现象。但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的哲学却是二元论哲学,这种哲学将世界分成本体和现象两截,而称世界本体为“物自体”,认为“物自体”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它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只是起到刺激人的感官而引起人对现象的感知的作用,但人并不能认识它,人所感知到的现象与它之间并不存在同一关系。因此,“Wahrheit”这个词不能被用来指称世界本体或与世界本体相符合的现象了,于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Wahrheit”做了这样的解释:“什么是真理?对真理这个名词的解释是: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21]。由于这个“对象”不是“物自体”的真现象,只是显现在人的经验中的东西,故从本质上说,所谓“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不过是人的精神现象之间的一种联系,所以在《逻辑学反思录》中,康德又说:“真理是知性与理性的一致”[22]——“知识”的精神本质是“知性”,“(知识的)对象”的精神本质是“理性”,它们之间的一致是人类理性诸要素(“理性”“知性”“感性”)[23]之间的一种统一关系。康德的真理观强调“真理是知性与理性的一致”,其实质是要求“知性”服从“理性”。而康德的“理性”概念有三层意义,分别被邓晓芒称为“理性1”“理性2”“理性3”,其中理性3是最狭义的理性,理性3的实质是实践理性、自由意志,是一个实践本体论概念[24]。故服从“理性”即意味着是服从“自由意志”——这便是康德二元论哲学的真理概念之意蕴所在。德语“Wahrheit”所固有的“无对”(绝对)意义到康德这里,实是指人类道德实践所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普遍道德规律)——“自由意志”了。
如果说二元论哲学家康德是从“Wahrheit”之本义引申出了实践本体论的本体概念——作为支配道德实践主体的“绝对命令”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话,那么一元论哲学家黑格尔则是从“Wahrheit”的本义引申出了“绝对理念”(Die absolute Idee,又译“绝对观念”)。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25]。这就是说,黑格尔把人类认识的对象世界理解为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的“绝对理念”,而“绝对理念”有一个逐渐实现自身的过程,人类所认识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真理概念正是指一切与“绝对理念”相符合的東西——包括与这个理念相符合的认识和其他一切真实的事物,但又不是指表现这个理念的个别具有真实性的认识或事物,而是指所有这些彼此互相联系和结合的个别实在所组成的总体。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这个总体中,“绝对理念”才能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当作真理本身,而把一切个别真实的存在只是当作真理的一个方面来看待:“理念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客观性跟概念的符合……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换言之,一切真实事物之所以为真的,即仅由于理念的力量。一个个体的存在只表示理念的某一方面,因此,它尚需要别的实在,而这些别的实在同样好象有它们的独立存在似的。唯有在这些个别的实在之结合和关系里,概念方实现其自身。那孤立的个别事物,是不能符合它的概念的。”[26]
1886年,恩格斯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篇长文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关于真理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25]212-213
从恩格斯针对黑格尔哲学所发表的这番肯定性评论可以看出,恩格斯所使用的“真理”概念是指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为该过程某个阶段上所获得的某种认识,但这不是那种再也不能前进一步的所谓“绝对真理”,而是可以继续向前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的认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恩格斯把这种认识称作“相对真理”,并且主张“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5]215-216。这里所谓“相对真理”的“相对”是相对于“绝对真理”(或“最终的绝对真理”)的“绝对”而言的:其“绝对”的意思是“认识已然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反之,其“相对”的意思就是“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永远都不能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强调“真理”的“相对”而不是“绝对”,是因为“绝对”是意味着认识过程的结束和真理的终结。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25]213-214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被他视为“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永恒真理”终究还是属于“绝对真理”。然而,恩格斯强调,假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25]215。所以恩格斯主张,应当顺乎历史永恒发展的趋势,沿着为黑格尔本人(虽然不是自觉地)所指出的认识道路,走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的迷宫,切实地去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即放弃对不可求致的最终的“绝对真理”的幻想,去追求那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5]215-216。
但是,德语中“Wahrheit”(真理)一词原本是包含“无对”(“绝对”)意义的,故即便是“相对真理”也还是包含“绝对真理”之意的,不过在恩格斯的真理概念中,这种“相对”包含“绝对”的意思是指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是由该发展过程之每一阶段所达到的认识所构成的。然则,恩格斯真理观之特点乃在于强调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无限性与其发展过程每一阶段的有限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其真理概念即是标志认识的无限性与有限性之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概念。
与恩格斯的真理概念有所不同,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则是强调了思维对物质实践的依赖性。马克思在1845年春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真理问题有这样一段论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⑧这段评论是针对费尔巴哈的相关论点⑨而发,表达了马克思真理观及其与费尔巴哈真理观的分歧。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真理观有某种共同之处——都承认“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这也表明了他们的真理概念都是表示“思维”对“客观”的关系概念。由于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故在他们的语汇里,“思维”与“客观”是指意识与物质,抑或精神与自然界;其真理概念即是指意识对物质、精神对自然界的一致关系,他们对此都肯定这种关系,亦即承认物质可以为意识所反映。但是,物质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为意识所反映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思想产生了根本分歧:费尔巴哈是把作为意识对象的物质理解为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自然界,人的意识就是对自然界的直观反映;马克思则认为,与人的实践无关的自然界并不能作为意识的对象而存在,意识的对象是由人的实践所造成⑩,因此,只有在实践中,物质才能为意识所反映;若是离开了实践,意识与物质之间有没有同一性,就会成为“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从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将永无休止,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对马克思来说,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本质上是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力量的问题,即思维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转变为现实,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转变为现实,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才能证明自己的思维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在这里,“真理”不过是用来表示要求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者的思维对促使它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实践的依赖关系的一个概念。正是借助于这个概念,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承认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遂具体化为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所强调的思维对实践的依赖性。
据以上考察与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的真理概念和马克思的真理概念的差异性在于:马克思的真理概念是着眼于思维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强调了思维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故真理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思维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力量借助于实践由精神力量到物质力量的转变过程;恩格斯的真理概念则是着眼于人的实践的历史过程性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是强调了认识必将随着实践的无限发展而无限发展,故真理是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认识作为人脑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上升的历史过程。
要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理概念,并不是在一般世界观意义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主张意识统一于物质,要求保持意识与物质的一致的物质本体论概念,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概念,其所推崇的真理本质上是作为人的历史存在之本体的物质实践,其崇尚真理不过是追求人的历史存在的两个方面——认识(人的精神性历史存在)与实践(人的物质性历史存在)的一致。这种一致关系,不仅是作为无限发展着的认识过程的一个历史环节或历史阶段而存在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人的认识达到了与自己的实践相一致的程度,以至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由观念的东西转变为现实的东西,由精神力量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且是作为无限发展着的实践过程的一个历史环节或历史阶段而存在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人的实践达到了与自己的认识相一致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在自己认识的指导下,由不自觉的或自觉度较低的行动转变为自觉的或自觉度较高的行动,由不自由的或自由度较低的行动转变为自由的或自由度较高的行动。在后一种意义上,其崇尚真理的实质在于崇尚自由,因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現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27]。
由是观之,我国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真理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坚持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有较密切关系,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之前提下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尚存差距,它仅仅是从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出发,看到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但未能透过其现象而进一步看到这种关系的本质在于认识(人的精神性历史存在)对实践(人的物质性历史存在)的依赖关系,因而不能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理解为就是对人的物质实践的本质和规律(即人的物质性历史存在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从而也就不能把真理本质地理解为知与行的历史统一,以及在这个历史统一关系中人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自由从抽象到具体、从观念到实在的历史性转化关系。
注釋:
①《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46.)《庄子·养生主》:“依乎天理”(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韩非子·解老》:“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188.)。
②也就是根据受众不同的理解力等具体情况,对某些受众采取某种言教形式,对另一些受众采取另一种言教形式,如:为著“空”者依“俗谛”说“有”,为著“有”者依“真谛”明“空”。
③参见吴国盛.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D].北京:北京大学,1998.另可参阅彭公亮.论“无蔽”(Aletheia)——兼论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J].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6).
④《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孔子仁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梁启雄注:“此语盖谓:不见全体而但见一偏之谓;略如佛家‘盲人摸象’之喻。……孔子总结大理而且全面地用大理;同时又不犯‘私其所积’的错误,——即不被狭隘的经验论所偏蔽。”(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6.292.)
⑤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所引述的斯多葛派的真理定义(“真理是对象和意识的一致”)中,“对象”应是指宇宙万物,“意识”应是指宇宙理性。斯多葛派认为,宇宙理性(或译“世界理性”“宇宙理智本性”)是决定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主宰力量,它普遍存在于自然事物中,也存在于人心中,故而被黑格尔当作“意识”来看待;又因为宇宙万物由“意识”所主宰,故而被黑格尔当作 “(意识的)对象”来看待。在斯多葛派的代表性著作《沉思录》(Meditations)中,作者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写下这样一段话:“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你按照你自己的理智本性生活;没有任何违反宇宙理智本性的事情对你发生”(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93.)。由此可以看出,在斯多葛派看来,宇宙理性是人皆有之的,人们应当按照自己固有的宇宙理性行事。
⑥如此译法不免有点儿“言不尽义”,因汉语中“真”“实”常含“非人为”之义,而英语“accepted”却并不含“非人为”之意,相反,它是意味着被人接受、同意,这里包含着人的意愿、意志、观念等主观因素。这也就是说,“fact accepted as true”并非指那种与人的意识毫不相干的客观实在,而是指与人的意识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事物,只是这个与人的意识有联系的事物又不是人的意识本身,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并与人的意识有某种联系(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故译之为“事实真理”也不过是强为之译。
⑦《老子·二十八章》有云:“朴散则为器”(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75.)。“朴”喻“道”,“器”喻“万物”。老子将“道……生万物”比作“朴散为器”,认为这是世界从原始的整体、全体逐渐分化为众多部分的过程。魏晋玄学家王弼解《老子》所谓“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110.按:“无”指“道”而言)的思想即来源于此。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按:这段话在马恩选集新版中的译文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覿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⑨费尔巴哈有“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178.]之说。
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按:意识的对象是由人的实践所造成,这个观点也可以用马克思所说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来加以概括。
参考文献:
[1]张载.张子语录(上)[A].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13.
[2]葛洪.抱朴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55.
[3]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A].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M].道光六年宣城张氏刊本.
[4]黎靖德.朱子语类(六)·卷九十四[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409.
[5]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
[6]萧统.令旨解二谛义[A].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一[M].四部丛刊.
[7]释慧远.大智论钞序[A].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75b.
[8]顾炎武.与施愚山书[A].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58.
[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A].日知录集释(外七种)[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04.
[11]〔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A].转引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82.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3.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
[14]〔意〕托马斯·阿奎那.真理论[J].傅乐安,摘译.哲学译丛,1978,(5).
[15]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1243-1244.
[16]叶秀山.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重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J].读书,1991,(4).
[17]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98.
[18]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43.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0.
[21]〔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A58/B82.
[22]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康德著作集(第29卷)[M].柏林,1902-1983.16.S250.转引自王建军.论康德对真理概念的判断力奠基[J].哲学研究,2016,(4).
[23]参见刘凤娟.康德的“知性存在”与“理性存在”概念之区分[J].江淮论坛,2010,(1).
[24]易晓波,编著.邓晓芒点评:论康德的知性与理性·中文摘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1.
[26]〔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399.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3-154.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