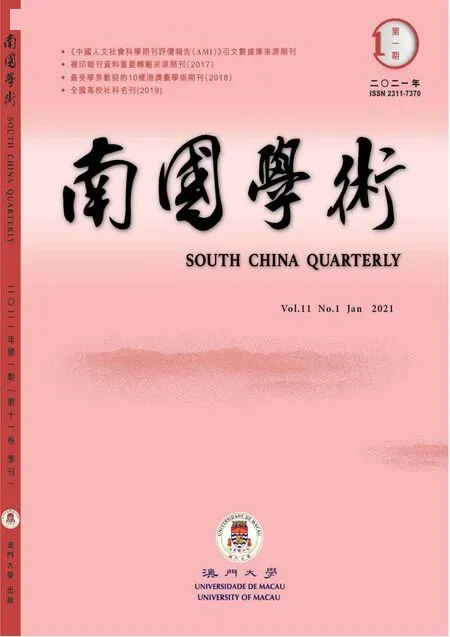“想象地理學”的發軔
——賽義德《東方主義》開闢的空間批評
2021-12-28陸揚
陸揚
[關鍵詞] 賽義德 東方主義批判 想象地理學 空間批評
引言
愛德華• 賽義德(E.W.Said,1935—2003,一譯“薩義德”)藉他提出的“東方主義”理論一舉成名之際,正值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轉移,各類新進理論此起彼伏,開始稱霸文學理論領域的時代。從空間批評的角度來看,列斐伏爾(H.Lefebvre,1901—1991)的名著《空間的生産》雖然早在1974年已經面世,但直到1991年英譯本刊佈之前,英語世界對它並不熟悉。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幾乎在同時提出過“空間修整”(spatial fix)概念,儘管他後來成了“空間轉向”當仁不讓的一代宗師,但在賽義德寫作《東方主義》之時,同樣沒有注意到這位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家。就文學批評來看,在20世紀70年代,羅蘭• 巴特(R.Barthes,1915—1980)、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是領軍人物,特別是德里達頻頻到耶魯大學講學,所謂的“耶魯學派”已見雛形;但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除了順帶提到羅蘭• 巴特外,對德里達和是時風頭正勁的解構主義卻隻字未提。在《東方主義》書中,作者推崇備至的是福柯(M.Foucault,1926—1984),提到和徵引的福柯著作計有《知識考古學》《監禁與懲罰》《詞與物》等多種。但是,福柯1976年那篇專題講演,即後來儼然成爲空間批評一大靈感來源的《異質空間》(Des Especes Autres)卻未有片語議及。這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因爲這篇講演的刊佈,已是八年之後的福柯去世之年了。要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不失爲空間批評的一部發軔之作。美國人文地理學家愛德華• 索亞(E.W.Soja,1940—2015)就承認,他本人的“第三空間”概念建構來源之一,便是“賽義德著作中影響深遠的‘東方主義’批判”①[美]愛德華• 索亞:《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陸揚 等譯,第176頁。。
在迄今已被譯爲近四十種外國語言的《東方主義》譯本中,有兩個阿拉伯語譯本即賽義德母語的譯本引人注目。其一是敍利亞詩人和批評家迪布(Kamal Abu Dib)的譯本,1981年由設在貝魯特的阿巴拉研究所出版。其二是時隔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開羅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艾那尼(Muhanmmad Enany)再度將《東方主義》用阿拉伯語譯出,由魯雅(Al-Ru’ya)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比較兩部譯作,其不同個性甚至在書名的副標題上也可見一斑。迪布譯作的副標題是《知識、權力和建構》,艾那尼譯本的副標題則爲《西方的東方概念》。迪布譯本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本土化,避免使用西方流行術語,諸如“話語”“擬像”“範式”“代碼”等等,即便這些術語在阿拉伯語中早已屢見不鮮。爲此,賽義德在《東方主義》1994年的再版後記中,給予了高度評價。艾那尼的譯本則是反其道而行之,有意識走通俗路綫,用現代阿拉伯語對接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思想。在篇幅長達二十頁的“譯序”中,譯者說道:“我翻譯《東方主義》的使命,是基於兩個考慮。其一是清晰接力愛德華• 賽義德的相關概念,即便用阿拉伯語境來重建有些英語結構,殊屬不易。其二是在現代阿拉伯語境中,保留愛德華• 賽義德風格中的特殊品質。”②Quoted in Lina Alttalah, “Translating Orientalism”,Egypt Independent,2010-09-26.這個宗旨比較在先一心求“雅”的迪布的譯本,可謂更看重“信”“達”。該譯本初版很快售罄,一度躋身埃及暢銷書榜首之列。
一 東方主義與霸權
《東方主義》初版於1978年。作者在書的“致謝”部分說,他雖然關心東方主義由來已久,但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在1975—1976年間寫成的,那時候他在斯坦福大學的行爲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研究員。在1994年的“再版後記”中,他又說道,像他這樣一種將權力、學術和想象糅合於一體,來回顧過去兩百年來歐美視域中的中東、阿拉伯和穆斯林敍述,能不能吸引廣大讀者,心裏是沒底的。2003年,該書又出版了二十五周年紀念版,作者增添了新的序言。今天,在該書面世四十多年之後,回過頭來重讀賽義德所寫的著名“導論”,依然可以感覺到一種貌似感傷主義的情懷作態撲面而來:
在1975至1976年可怖的內戰期間,一個法國記者造訪黎巴嫩,傷心地記下了市區地帶的滿目瘡痍景象:“它曾經似乎是屬於……夏多布里昂和奈瓦爾的東方啊。”當然,他沒有認錯地方,特別是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說。“東方”幾乎總是一種歐洲的發明,從古代起,它就始終是一塊充滿了羅曼蒂克、異國情趣、神思夢牽、美妙回憶和美麗風景的土地,那裏的經歷精彩絕倫。如今,它在漸行漸遠。一定意義上說,它已經消逝,那個時代結束了。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antage Books, 1978), 1, 2.
之所以說那是一種情懷作態,照賽義德的意思,那是活該。他接着指出,在這幅圖景中,東方人,自打夏多布里昂(F-R.d.Chateaubriand,1768—1848)、奈瓦爾(G.d.Nerval,1808—1855)時代就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東方人,其生生死死是無足輕重的;對於歐洲旅人來說,舉足輕重的是表徵:如何來表徵東方人和他們的當代生活?這就事關緊要了。所以,誠如是書兩條題記中所引的馬克思(K.H.Marx,1818—1883)的《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話:“他們不能表徵自己,他們衹能被別人表徵。”這句話對於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批判,可謂畫龍點睛。
賽義德發現,法國人、英國人,再下來是德國人、俄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等等,都有一種他愿意叫做“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傳統。美國人則有所不同,他們的東方觀要現實得多。美國人言東方,更多的是指遠東,主要是中國、日本,還包括韓國、印尼和中東,政治和經濟的考量居於首位。而在歐洲的“東方主義”傳統裏,東方不僅緊鄰着歐洲大陸,也是歐洲最爲廣大富饒、最爲古老的殖民地,是歐洲文明和語言的來源,還是它文化上的對手,是它最深邃、最常見的“他者”形象之一。不僅如此,“東方”作爲與歐洲或者說西方處處相反的意象、觀念和人格經驗,也幫助歐洲界定了自身。東方的這一切,無疑是出自想象,但它也是“物質”文明與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鑒於此,東方主義不是別的,它是在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上來表達和表徵這個傳統的話語模式。這個模式不是隨性而來,其背後的支撐基礎是制度、語彙、學術、想象、教義,甚至殖民官僚政治和殖民風格文體。
賽義德坦言,他談東方主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指義。第一個指義,它是一個學院派概念。即是說,大凡教學、寫作、研究以東方爲主題的,不論他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還是文獻學家,它就是一個東方主義者或者說東方學家。雖然與東方研究、區域研究、國別研究這類學科相比,“東方主義”這個概念太含糊,而且帶有早期殖民主義的強烈政治色彩,不過它終究還是堅持到了今天。這如該書的另一條題記所言,那是19世紀殖民主義高峰時期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Disraeli,1804—1881)的一句話:“東方是一種職業生涯。”
東方主義第二個指義也是它最普遍層面上的意義。對此,賽義德指出:
東方主義是一種思想風格,它的基礎是“東方”和“西方”(大多數時候寫作“Occident”)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區別。是以多不勝數的作家,包括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以及帝國管理人員,都接受了這個區別,由此出發來構築有關東方、東方人,以及其習俗、“心靈”、命運等等的理論、史詩、小說、社會描述和政治綱領。②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antage Books, 1978), 1, 2.
這一最普遍意義上的想象中的東方主義,賽義德指出,可以將諸如埃斯庫羅斯( Orientalism),前525—前456)、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雨果(V.Hugo,1802—1885)和馬克思這一類名字包括在內。它與前面的學院派指義,其實從來就是互通的。
東方主義的第三個指義是霸權。用賽義德本人的話說,這是比較前面兩個指義更側重歷史和物質的釋義。他認爲,大體從18世紀後期起,東方主義便嶄露頭角,成爲應對東方的特定機制。它發佈關於東方的陳述,確立關於東方的權威觀點,以及描述東方、教授東方、殖民東方、統治東方。總而言之,東方主義是主導、重構、掌控東方的一種西方文體。在這一方面,賽義德自謂福柯《知識考古學》《監禁與懲罰》這兩本書中的話語觀念,給了他很大啓發。所以,他的看法是,假如不是將東方主義作爲一種話語來考察,我們就無從理解東方主義這個龐大的系統性學科,無從理解歐洲文化如何能夠在後啓蒙時代,通過它在政治方面、社會學方面、軍事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科學方面,以及想象方面,來應對甚至創造東方。不僅如此,“東方主義佔據着這樣高的權威地位,以至於我相信不論是誰來書寫、思考東方,以及與東方交往,可以不顧及東方主義對他思想和行動的鉗制”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3, 7, 7-8.。
由是觀之,東方主義就是一張巨大無比的網絡,凡西方人言說東方,無一能夠擺脫它的糾纏。這裏的空間分界,顯然遠超過了單純地理即物理空間的界限。故而賽義德強調,他談東方主義的前提,就是東方並不是地理事實,並不是就在“那裏”,就好像西方也並不是就在“這裏”。他認爲,維柯(G.Vico,1668—1744)所說的“人類創造自己歷史,其知識空間就是他們造就的世界”這條至理名言,同樣可以推廣到地理學上來。它意味着,像“西方”“東方”這樣的地理和文化的實體——更不用說它們還是歷史的實體,都是人爲建構起來的地方和區域。所以,就像西方自身一樣,“東方”這個概念也有着自己的歷史,有着自己的思想、意象和語彙傳統。而正是這一歷史與傳統,使它成爲真實的存在,並且與西方互相呼應。所以,東方、西方這兩個地理實體是互相支撐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映照着對方。
爲了說明“東方理論”的霸權性質,賽義德除了列舉福柯外,還大量徵引了葛蘭西(A.Gramsci,1891—1937)的相關論述。他指出,葛蘭西就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作過區分,前者是自願構成的社會,或者至少是理性地、非強制性地聯合了學校、家庭、工會這些社團;後者是國家機構,包括軍隊、警察、中央官僚集團,其政治角色是直接控制。這裏就涉及了文化霸權的問題。秉承葛蘭西的傳統,賽義德這樣重申了“霸權”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文化當然是見於市民社會內部的運作之中。在市民社會裏,觀念、制度和其他人物的影響,不是通過主導控制,而是通過葛蘭西所言的讚同來實施的。因此,在任何一個非極權社會中,總有某種文化形式支配着其他文化形式,一如某種觀念比較其他觀念影響更大。這一文化的領導權形式,就是葛蘭西予以命名的“霸權”(hegemony)。對於西方工業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切理解中,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概念。②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3, 7, 7-8.
賽義德指出,就是這個霸權,或者說施行文化霸權的結果,使得東方主義續命直至今天,而且照樣是無比強大。它使歐洲成爲“我們”,使一切非歐洲的地區成爲“它們”。它意味着,歐洲人的身份比一切非歐洲的化外之民與文化都要高人一等。歐洲的東方觀念亦然,它是“先進”與“落後”的鮮明對照。
關於東方主義的策略,賽義德強調說,它始終是建立在這一形態各異的優越性上面的。以至於但凡西方人與東方人交往,無不佔據上風。這在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直抵今天的歐洲上升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科學家,學者,傳教士,商人,以及士兵等等,都在出沒東方、思念東方,因爲他們想去就去、愛想就想,東方本土對他們幾無阻攔。故而:
在“東方知識”這個總標題下,頂着西方對東方的霸權保護傘,從18世紀末葉開始,一個錯綜複雜的東方拔地而起,它相當適宜在學院中學習,在博物館中展出,在殖民機關中重構,在事關宇宙的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種族和歷史主題中作理論闡發,在發展、革命、文化個性、民族或宗教性格的經濟與社會性理論中來作例證。③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3, 7, 7-8.
賽義德這一大串叫人眼花繚亂的排比足以顯示,東方主義在當代西方學術、文化乃至革命和宗教領域中的無所不在。不僅如此,賽義德指出,對於東方的這一切想象性考察,多多少少總是建立在至高無上的西方意識之上。這個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識從未受到過挑戰,東方世界就浮現在這一意識的核心部分。由於立足西方意識的西方人來考察誰是東方人、什麽是東方,這些總體性概念的邏輯不僅來自經驗世界,同樣來自一系列慾望、壓抑、投資、投射的組合。概言之,東方主義界定出的東方世界,其物理空間是無關緊要的;憑藉“話語”“權力”“霸權”這些受惠於福柯和葛蘭西等人的後結構主義流行觀念,讓賽義德毫不猶豫地將東方主義打造成爲了社會空間批判的一個樣板。
二 從文學批評到東方主義
作爲一個文學批評家,賽義德是如何走上東方主義這條獨特研究道路,成爲了日後如火如荼的東方主義第一推手的呢?這要從他的一個標題“純粹與政治知識的區別”談起。
賽義德指出,人們都會說,關於莎士比亞(W.Shakespeare,1564—1616)、華茲華斯(W.Wordsworth,1770—1850)的知識無關政治,反之關於當代中國和蘇聯的知識則是有關政治的。而他本人的正式職業屬於人文學科,算起來與政治並不相干。這其實是籠統而言的。因爲,一個人文學者寫華茲華斯,一個編輯編濟慈(J.Keats,1795—1821)的詩集,說他們無關政治,是說他們的工作對現實並不具有平常意義上的政治效果;但英國、法國以及近來的美國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事情但凡牽涉到帝國的海外利益,這些國家的政治社會就會給其市民社會施加一種緊迫感,這就是一種直接的政治壓力了。這意味着,人文科學中的知識生産,永遠不可能忽略或否認作者與自己生活環境之間的聯繫。故而對一個研究東方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言,同樣不可能否認他寫作行爲的政治環境:
他首先是作爲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來談論東方,其次纔是作爲個人。在這種境遇下,你是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並非無足輕重的一個事實。它過去意味着,現在也意味着,你會意識到,即便是模模糊糊,你也是屬於一個在東方有着實實在在利益的大國;更重要的是,你屬於地球上的這樣一個區域,它有着一段幾乎直溯荷馬時代的捲入東方事務的明確歷史。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11.
賽義德作如是言說,是不想把帝國主義控制這種“昭然若揭”的事實,機械地用來作爲文化與觀念領域的决定性因素,他需要另闢蹊徑。但是,即便另闢蹊徑,從他書中述及的歷史事實來看,也足以證明,歐洲和美國對東方的興趣是政治性的。而産生這一政治興趣的,是文化。正是文化與殘暴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因狼狽爲奸,使東方成爲一個變來變去、撲朔迷離的地方。它的真實空間在哪裏,已經無足輕重;它顯而易見矗立在現在叫做東方主義的這個領域中,這就夠了。
由是觀之,東方主義不妨說是預演了一個真實與想象兩相結合的“第三空間”。正如賽義德所言,它決不單單是一個政治題材或領域被動地反映在文化、學術、學院之中,也不是一個關於東方文本的大雜燴,不是在表徵或表達某個窮凶極惡、旨在控制“東方”世界的“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恰恰相反,它是地理政治意識向美學、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哲學文本的一種分佈。對此,賽義德強調說,它不僅是處心積慮將世界在地理上平分兩半,一半東方,一半西方,而且通過學術發現、文獻重構、心理分析,以及景觀和社會學描述,精心策劃並維護了一系列“利益”。所以,說到底,東方主義是與政治權力密切聯繫的一種話語,雖然這聯繫似乎並不是一目瞭然、直截了當的。既然東方主義是一個文化與帝國主義政治的事實,那麽,它就不可能存在於檔案材料的真空裏面,而是有着清晰的知識綫索。誠然,讓文化去攪和政治被認爲有傷大雅,而且在賽義德看來,文學研究特別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沒有認真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
爲解决這個帝國主義與文化或者說東方主義研究的困頓,賽義德從兩個方面尋找答案。首先,差不多19世紀,以及在先時期的每一位作家,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帝國意識。比如,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專家很快就會承認,像約翰• 穆勒(J.S.Mill,1806—1873)、馬修• 阿諾德(M.Arnold,1822—1888)、卡萊爾(T.Carlyle,1795—1881)、約翰• 亨利• 紐曼(J.H.Newman,1801-1890)、羅斯金(J.Ruskin,1819—1900)、喬治• 艾略特(G.Eliot,1819—1880),甚至狄更斯(C.J.H.Dickens,1812—1870),這些彼時的自由派文化英雄,都對種族和帝國主義抱有明確立場。以穆勒的《論自由》《代議制政府》這兩本書爲例,公開表明,他書裏的觀點不適用於印度,因爲印度不說在種族上,至少在文明上也低下一等。其次,更爲重要的似乎是:
相信政治是以帝國主義的形式影響了文學、學術、社會理論與歷史撰寫,並不意味着文化有失顔面,成了貶值的東西。恰恰相反,我的全部觀點是,衹有當我們意識到像文化這樣無所不知的霸權系統,其對作家和思想家的內在制約是“生産性”的,而不是單方面的抑制,我們纔能更好地理解這些系統何以能夠一以貫之,長盛不衰。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14.
正是秉承這一理念,葛蘭西、福柯、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的著作雖然風格各異,卻在殊途同歸地展開闡述。即以威廉斯1962年出版的《漫長的革命》中談論“帝國的作用”的那一兩頁篇幅而言,在向人們揭示19世紀文化的豐富性方面,已勝過許多整本整本的封閉式文本分析了。
賽義德因此宣稱,他所研究的東方主義,是專注於個別作家與英、法、美這三大帝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因爲他們的文字都是在這三個國家的學術和想象國土裏生産出來的。而他本人作爲一名學者,最感興趣的不是總體的政治真相,而是細節。由此來看東方主義引出的政治問題,他認爲可以歸結爲以下類型:其一,哪些其他類別的知識、美學、學術與文化力量參與建構了東方主義這樣的帝國主義傳統?其二,文獻學、詞彙學、歷史學、生物學、政治與經濟理論、小說以及詩歌寫作,如何服務於東方主義廣義上的帝國主義世界觀?其三,東方主義內部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修正、升華甚至革命?其四,在這一語境中,原創性的意義是什麽,延續性的意義是什麽,個性的意義又是什麽?其五,東方主義怎樣從一個時代過渡或者說再生産到另一個時代?其六,如何將東方主義這個文化與歷史現象看作是一個有意志的人類作品,而不僅僅是無條件的推理?面對這些問題,賽義德表明的態度是,任何一種人文主義探討,必須能夠闡明上述特定語境中知識與政治之間的聯繫性質、相關主題,以及歷史情境。
《東方主義》面世之後,在一路風靡的同時,也招致不少反對意見。賽義德說,他寫作此書並不是要將一個完整的世界分成“西方”“東方”兩個部分。然而,反對意見之一,恰恰就是質疑賽義德用想象性話語,將全球空間割裂成了兩個世界。例如,塔夫茨大學的莉莎• 羅威(Lisa Lowe)教授在《批評地帶》一書中,除了從女性主義角度質疑賽義德東方主義學說外,還明確反對以東方爲西方他者鏡像的立場。作者開篇就指出,《東方主義》這本書固然讓她受益匪淺,但是,“我的研究最終是要挑戰該書的這一假設,那就是《東方主義》一厢情願、一股腦兒將東方建構成了西方的‘他者’”。②Lisa Lowe,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她也“重讀”了同樣受到賽義德關注的一些英法作家,包括孟德斯鳩(C-L.d.Secondat,1689—1755)、福樓拜(G.Flaubert,1821—1880)、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等,同時引入新的視野,諸如後結構主義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羅蘭• 巴特筆下的“中國烏托邦”等,以表明賽義德東方主義的批判范式其實是疑雲密佈的。
三 方法論問題
關於人文學科中的方法論,就是找出一個起點,一個啓動原則。而賽義德研究東方主義的方法論有兩個:一是“策略方位”(strategic location)。即如何來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尤其是他與他所敍寫的東方物質世界的關係。二是“策略形成”(strategic formation)。這是分析不同文本之間關係的一個方法,即探討不同的文本系列和文本類別甚至類型,如何在它們之間、進而在整個文化之中脫穎而出,得以廣爲傳佈。這裏同樣涉及地理空間問題。固然,英國、法國早在17世紀末葉,就主導着地中海東岸地區。可是,假若東方主義研究衹看到這一點,那就是忽略了其他國家的重要影響,諸如德國、意大利、俄國、西班牙、葡萄牙的貢獻。
在這些國家裏,賽義德特別關注的是德國。他指出,19世紀中葉,德國學術已達到很高水平,英法學者卻視而不見,導致喬治• 艾略特《米德爾馬契》中的卡索邦(Casaubon)先生沒法完成他的《神話大全指要》,原因就是不擅長德國學術。而德國學術在盎格魯-法蘭西,還有後來美國人的心中,此時已毋庸置疑地代表着歐洲的領先水平。這是一切東方主義的研究所無法迴避的。不僅如此,德國的“東方”幾乎無一例外是學術的東方,至少是古典的東方。它是詩歌、傳奇,甚至小說的題材,但它從來就不是真實的東方,與夏多布里昂、拉馬丁(A.M.L.d.Lamartine,1790—1869)、奈瓦爾等人筆下的真實埃及和敍利亞判然不同。賽義德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認爲它意味深長,那就是德國最有名的兩部寫東方的作品:歌德的抒情詩《西東合集》和弗里德里希• 施萊格爾(F.Schlegel,1772—1829)的《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前者的靈感來源於萊茵河上的一次旅行,後者是埋首巴黎的幾家圖書館所得。所以,“德國東方學術所做的,便是用技能來美化和深化英法帝國主義從東方幾乎是原初面貌收集過來的文本、神話、觀念以及語言”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19.。要言之,這裏的方法分工,便是英法提供素材,德國再做深加工。
至於“策略”,賽義德強調他使用這個術語作爲方法論的核心,純粹是爲了挑明每一個寫東方題材的人必然面臨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把握東方、接近東方,而不爲它的高深、寬廣以及可怕的多重維度壓倒而不知所措。這意味着,凡敍寫東方,必須將自己定位在東方的坐標之中,將這坐標轉譯入他的文本。這一空間方位包括,他採用何種敍述聲音,搭建何種結構,以及他作品中的意象、主題和母題類型。所有這一切匯聚起來,可組合成各種方法來對話讀者、涵蓋東方;最後,表徵東方或爲之代言。而這一切策略都不是抽象論道,任何一位敍寫東方的作家,甚至荷馬( Lamartin,約前9世紀—前8世紀),都會認定某個東方先驅、某種在先的東方知識,他會提及它們,那也是它寫作的基石。不僅如此,每一部論述東方的著作,都親密聯繫着其他著作,聯繫着作者、機構,以及東方本身。這些作品、讀者和東方某些特定方面的關係總體,便形成了一個可供分析的形式,如文獻學研究、東方文學中的人類學研究、旅行札記、東方傳奇等。這個形式在不同時間、不同話語、不同公共機構如學校、圖書館、外事部門等等中的反復出現,就使它有了一種權威意味。
賽義德強調,上述東方文本形式的權威性,不在於文本內部的特徵,而在於外在文本的特徵,即東方主義是如何被表達出來的。這不但適用於想象性文本如文學和藝術作品,同樣適用於所謂的真實性文本如歷史、語言學和政治著作。讀者關注的是風格、修辭、場景、敍述技巧,以及社會和歷史背景,而不是表述的正確性。因爲,表達的外在性總是有點似是而非:倘若東方能夠表述自身,它一定會表達自己;既然它無能爲力,那麽就必須由別人當此重任。爲了西方,也爲了可憐的東方。這又呼應了前面他引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東方“不能表徵自己,衹能被別人來表徵”那句格言以爲題記。賽義德指出,歐洲早在17與18世紀之交,就開始關注東方語言的悠久歷史,它比《舊約》中的希伯來語系更爲悠久。拜倫(G.G.Byron,1788—1824)、歌德、雨果們在其作品中用浪漫主義手法再造了東方,令東方和東方人大放異彩,這其實與真實的東方是大相徑庭的。是以西方有語言學的東方、達爾文(C.R.Darwin,1809—1882)的東方、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東方、斯賓格勒(O.A.G.Spengler,1880—1936)的東方、種族主義的東方,然而從來不存在一個純而又純的無條件的東方。同樣,凡言東方主義,必有其物質形式,從來就不存在諸如東方的“觀念”這樣的天真東西。
有鑒於此,賽義德坦言,就方法論而言,他不同於那些研究觀念史的學者。他不僅考察學術著作,同樣也考察文學作品、政治論文、新聞文本、旅行札記,以及宗教和文獻研究。換言之,他的混血視角具有廣泛的歷史性與“文類學”性質,因爲他相信,所有的文本都是世俗的,流轉在不同的文類與不同的歷史階段之間。但在這一點上,賽義德表示,他與他的偶像福柯有所不同。對於福柯來說,大體相信個別文本和個別作家無關重要,但賽義德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福柯所言固然有理,卻不適用於東方主義。故而對東方主義這個特定的領域,賽義德的分析採用了文本細讀的方法,其目的是揭示個別文本或作家與其所屬之複雜綜合形式之間的辯證關係。
賽義德對他的《東方主義》方法論的最後說明是,寫作此書,他心裏面裝着好幾類觀衆:
對於文學與批評的學生來說,東方主義提供了一個奇妙的例子,顯示出社會、歷史和文本性之間的交互關係;不僅如此,我以爲東方在西方扮演的文化角色,也對文學共同體呈現了東方主義與意識形態、政治、權力邏輯等相關問題的聯繫。對於東方專業的當代學者,從高校學者到决策者,我寫此書有兩個目的,一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他們的學術譜系呈現出來;二是批判他們的著作大多數時候認爲是天經地義的立論依據,希望由此引發討論。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本研究應對的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它們全都不但聯繫着西方關於“他者”的概念以及對“他者”的應對,而且事關西方文化在維柯所謂民族世界中扮演的獨一無二重要角色。最後,對於所謂第三世界的讀者而言,本研究不但是走向理解西方政治與這些政治中非西方世界的一個步驟,更是理解西方文化話語“力量”的一個步驟。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24-25, 55.
賽義德稱,這個被置入引號之內的力量一語,過去多被人誤解爲“上層建築”,但這裏他明確闡明,它不是別的,就是令人生畏的文化主導結構。
賽義德上述以形形色色想象空間涵蓋現實空間來歸納東方主義研究、以文化替代上層建築來作爲研究主導脉絡的方法論,同樣並非沒有疑問。任教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印度裔比較文學教授阿赫邁德(Aijaz Ahmad),在他收入書評文集《理論之中:階級、國家、文學》中的《東方主義及其後續》一文裏,便是在相繼而來的後殖民主義語境中,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視野。阿赫邁德雖然與賽義德在許多政治觀點上意見相同,而且支持賽義德在巴勒斯坦知識分子中的領軍地位,但質疑《東方主義》聯手福柯後結構主義和奧爾巴赫(E.Auerbach,1892—1957)等人的人文主義爲理論基礎,指出,“在用什麽理論來理解世界,以及對世界歷史的看法上面,我與他有着根本性的分歧”。②Aijaz Ahmad, “Orientalism and After: Ambival enc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in the Work of Edward Said”,In Theory: Classes,Nations, Literatures (New York: Verso, 1992), 159.阿赫邁德的尖銳批評在東方主義後殖民研究中同樣後續不斷,讚成的、反對的各執其辭,被認爲是馬克思主義介入帝國主義空間文化批判的典範之說。
四 兩部希臘悲劇
本着東方主義的批判視野,賽義德對西方文學進行了縱橫捭闔的大量評述。他認同法國哲學家巴什拉(G.Bachelard,1884—1962)在1957年出版的《空間的詩學》中的一個著名觀點:因爲相關的經驗和記憶,走進一棟房子,會有一種親密、秘密和安全的感覺,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想象的。他引巴什拉一段經常被人引用的話說:
房子裏的客觀空間——它的角落、走廊、地下室、房間,遠遠沒有人們賦予它的詩意來得重要。那通常是一種特質,具有我們可以命名、可以感覺到的想象和比喻價值:如是,一棟房子可以是鬼屋,可以充滿家庭溫馨,可以像牢獄,也可以是奇境。所以,房舍通過一種詩意的過程,獲得了情感的甚至理性的感覺。這樣空洞的或無名的空間,這裏就被我們轉化成了意義。③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24-25, 55.
不僅空間,賽義德認爲時間也是如此。諸如“很久以前”“起初”“最後”,同樣是可以具有詩情畫意的。因爲,想象地理學和歷史,幫助我們的心智壓縮了距離和差異,什麽近在咫尺,什麽遠在天邊,它會有自己的感受。同樣的道理,比如我們的感覺對於16世紀和塔希提島,就會更有一種“家園感”。
賽義德進而分析了現存最早和最晚的兩部希臘悲劇,一部是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一部是歐里庇得斯(Eυριπίδης,前480—前406)的《酒神的女祭師們》。埃斯庫羅斯參加過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他的兄弟就陣亡於馬拉松。《波斯人》首演是在公元前472年,這部劇作以波斯王宮爲背景,由報信人報告波斯艦隊全軍覆沒薩拉米斯海戰的消息。它雖然是以波斯人的視角敍述戰爭,但顯而易見帶有作者本人當年目睹的血戰經歷。所以,誠如《東方主義》的題記所言,它毋寧說是西方人代言東方的一個古代樣本。賽義德指出,埃斯庫羅斯描述了信使報知國王薛西斯一世率領的波斯大軍魂歸薩拉米斯之後,籠罩在波斯人頭上的愁雲慘霧。他引了歌隊的一段歌詞:
到如今整個亞洲大地
都在虛空中絕望悲泣。
薛西斯一往無前,噢噢!
薛西斯一敗塗地,哇哇!
薛西斯的計謀悉盡流産
在大海的戰艦之中。
可爲何大流士
也曾帶領他們衝鋒陷陣
卻未讓他百姓遭禍殃
這位帝都蘇薩人,敬愛的先王?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56.
賽義德對此的評價是,這裏的關鍵是,亞洲人通過歐洲人的想象在說話,而歐洲被描寫爲戰勝亞洲的勝利方面,後者是大海彼岸敵對的“他者”世界。是以留給亞洲人的衹有虛空、失敗和大禍臨頭感,那就是他們挑戰西方的回報。大流士一世戰勝歐洲的輝煌歲月,畢竟是一去不返,衹能迴光返照在哀歌之中了。
《酒神的女祭師們》是現存歐里庇得斯悲劇作品的最後一部,寫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帶了一幫亞洲信衆,回到忒拜(Thebes),要報當年的殺母之仇。當初狄俄尼索斯母親塞默勒(Semele)是死在自己的親姐妹手裏,蓋因她們出於妒忌,不承認她是宙斯的新娘。塞默勒跟宙斯懷下的孩子,凶手以爲也是胎死腹中。這孩子就是狄俄尼索斯,他其實沒死,而是長大成神,去了亞洲,向人類傳播他的狄俄尼索斯新信仰。既抵忒拜,一國女人無不走火入魔,蜂擁而至曠野間歡歌狂舞,變身成爲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師。這當中有一個女人,就是塞默勒的一個妹妹,忒拜當今年幼國王彭透斯(Pentheus)的母親阿加芙(Agave)。彭透斯該是太爲年輕,不解神一旦記恨意味着什麽,一意驅逐瘋瘋癲癲的狄俄尼索斯宗教。狄俄尼索斯化身凡人傳佈新教,被彭透斯拘捕打入地牢後,發動地震摧毀忒拜宮殿。爬出廢墟的彭透斯賭神發誓,要發兵與酒神的迷狂女祭師們開戰,卻又架不住好奇心,被依然是凡人身的酒神誑騙易裝,加入女祭師隊伍,一樣如痴如醉迷狂起來。然後,狄俄尼索斯曝出彭透斯真實身份,被瘋狂的女祭師們撕成碎片。第一個動手的,就是彭透斯的母親阿加芙。此劇中有阿加芙手提彭透斯腦袋登場亮相的血腥場面,腦袋插在酒神手杖上面,她向父親卡德摩斯誇耀徒手殺死了一頭獅子。父親讓阿加芙看一眼手杖上是誰的首級,道明真相後,父女抱頭痛哭,連女祭師們也爲之動容。最後,狄俄尼索斯輝煌真身亮相宮殿上空,下令分頭放逐阿加芙和卡德摩斯。父女哀悼死去的彭透斯,也哀悼彼此的命運。這個結局使人想起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ς,前496—前405)的《俄狄浦斯王》中的結尾,一切真相大白後,俄狄浦斯刺瞎自己雙眼,自我放逐荒野。可以想見,三個人一樣是前路漫漫,凶險莫測。
賽義德認爲,《酒神的女祭師們》是雅典地區所有悲劇中最具有亞洲特色的。狄俄尼索斯這個西方的酒神,顯然與東方神話中無奇不有的恐怖行爲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彭透斯這位年輕的忒拜國王,慘死在他母親和那一群酒神女祭師手裏,是因爲他挑戰狄俄尼索斯,否定他的權威,不承認他的神性,由此受到恐怖的懲罰,最終也如悲劇結尾所示,反襯出這位乖戾大神的恐怖法力。他並且指出,現代學者在讚美這部巨作非凡的知識譜系和審美效果之餘,也不會忽略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歐里庇得斯顯然感覺到了狄俄尼索斯信仰的一個新側面——它肯定受惠於異域狂歡宗教,如本迪斯(Bendis)、塞伯萊(Cybele)、阿多尼斯(Adonis)、伊西斯(Isis)信仰。這些信仰都是從小亞細亞和黎凡特地區(Levant)傳入歐洲的。對此,他總結說:
上面兩部劇作中,把東方與西方分別開來的兩個方面,將持續成爲歐洲想象地理學的基礎母題。一條分界橫亘在兩塊大陸之間——歐洲孔武有力、表達明晰,亞洲一敗塗地、地處遙遠。埃斯庫羅斯“表徵”亞洲,讓年邁的波斯王后、薛西斯的母親來代表她說話。那是歐洲在言說亞洲。這一言說的特權不屬那個傀儡主人,而屬真正創造者,他生死予奪的大權表徵、激活並且構造了熟悉邊界之外的那個否則將沉默無聲、險象環生的空間。①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57.
這又是東方無言,非得西方代言的主題。賽義德認爲,東方有別於西方見之於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埃斯庫羅斯的合唱隊包含了一個劇作家構思出來的亞洲世界,它與東方主義學術的博學門面之間有一種類似關係,因爲後者把握那個浩瀚無邊、變幻無定的亞洲世界,雖然時有同情,卻總是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由此過渡到第二個方面,即東方的主題暗示着凶險。賽義德對此的說明是,東方的恣意妄爲損害了西方的理性,東方神神鬼鬼的各類花招,與西方的自以爲是的價值規範背道而馳。是以東西方的差異,首先就體現在彭透斯對那幫歇斯底里酒神女祭師的嚴厲拒斥中。後來,當他自己變身爲女祭師時,其死於非命與其說是屈服於狄俄尼索斯,不如說是一開頭就錯估了狄俄尼索斯的恐嚇。所以,歐里庇得斯後來請出卡德摩斯和盲先知提瑞西阿斯(Lamartine),讓這兩位見多識廣的老人來提示教訓:要統治民衆,“君權”是獨力難當的,還需要有判斷。而判斷意味着正確把握外來強權,以作專業應對。如此東方的神神鬼鬼瘋狂行徑就不可小覷,因爲它們挑戰了理性的西方心靈,讓它曠日持久的野心和權力有了一個新的對手。
結語
賽義德將東方主義定義爲西方強權文化殖民的近代史,就像他一以貫之的文學批評視角和立場一樣,並非沒有爭議,但是它開闢了一個學派的奠基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個學派的宣言,即是該書的“導論”部分。批評意見指責它突破了學科之間的界限、將本質上屬於政治和經濟的殖民主義作文化至上的解釋,以及人爲地從文化上將完整的世界星球分爲“西方”“東方”兩個想象空間等等。這些反對意見,在多年以後的學術規範中,有幸也罷,不幸也罷,反而發展成了常識。
美國學者亞當斯(Hazard Adams)、塞爾(Leroy Searle)在他們主編的著名文選《柏拉圖以降的批評理論》中,在賽義德名下全文收入了《東方主義》的“導論”部分。兩位編者認爲,在《東方主義》之前,還沒有哪部著作像它那樣構造出一個整合了哲學、人類學、文學、政治學的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批評和研究框架。而相關的早期著作,如法儂(F.O.Fanon,1925—1961)的《全世界的受苦人》、葛蘭西的《獄中札記》,談的要麽是迫在眉睫的事關民族解放戰爭的實踐問題,要麽是底層民衆的主導權問題。但是,賽義德不同:
賽義德的整合模式無論是在學院派內,還是在其他領域,都影響到一個利益同盟。不用說,他這本書也引來了批評和反對意見,因爲正是這個把它樹立爲樣板、讓年輕學者和批評家來加效仿的同盟,提醒我們注意,學院研究與其他人衆(這裏叫做“東方主義者”)之间錯
綜複雜的深層同謀關係,以及職業知識分子對於剝削要麽譴責、要麽讚揚的政治態度。①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Boston: Thomson Wadsworth, 1992), 1369.所謂學院派與東方主義學者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也是從文學批評推進到文化批評必然會遭遇的問題。由是觀之,《東方主義》正是演繹了從文學向文化批評的擴展進路——以東方爲背景,討論了從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到雨果、夏多布里昂、喬治• 艾略特等大量19世紀作家的作品。特別是殫精竭慮,將威廉斯、葛蘭西、福柯等人的批判理論運用到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之中,從而造就政治文化與文學文本聯姻的一個經典。而從空間批評的角度來看,與其耿耿於懷它是變相鼓吹的文化决定論,由此界出“西方”“東方”兩個壁壘森嚴的空間,不如說是賽義德的這本大著對想象空間鍾情太多,而多多少少忽略了跟它對應的真實空間,即意識形態批評背後的物質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愛德華• 索亞在他影響了空間批評一代學人的《第三空間》一書中,給予了賽義德高度評價。他認爲,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是演繹了一種“想象地理學”,代表了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打破學院裏學科壁壘的努力。它顯示,針對殖民主義文化控制的反抗和民族解放鬥爭,不僅是表達了一種時間序次,同樣也是批判地再思考了地理政治的空間安排,即便它依然帶着歐洲中心主義的遺風。所以:
賽義德解構形形色色的東方主義二元對立,其基礎在於強行推廣種種“想象地理學”。它們主導了傳統的空間表徵,也主導了物質的空間實踐。在這些真實和想象的東方主義地理學中,中心的建構強大無比,井井有條,監測四方;反之,邊緣則連連敗陣,默默無言,位居附庸,衹有服從,沒有自己的歷史。通過批判殖民主義的空間實踐以及它對空間、知識和權力的令人生畏的表徵,賽義德也打開了表徵的後殖民主義空間和權力,而導向一種嶄新的地理詩學修正。②[美]愛德華• 索亞:《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第177頁。按照索亞的說法,賽義德寫作《東方主義》,是走邊門進入了第三空間。什麽是“第三空間”?它既是現代的,又是後現代的;既是想象的,又是真實的。這樣來看,“東方主義”作爲一種想象地理學,與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産》所悄悄開啓的“空間轉向”經典性方位,距離不過是一步之遙。至此,我們或者同樣可以說,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批判,是在歷史性與空間性之間迄今迷霧密佈的互動遊戲中,走邊門開闢了一個方興未艾的空間批評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