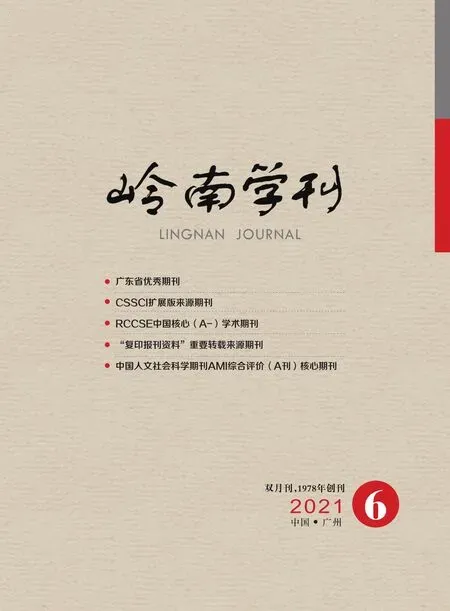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
——基于消费扶贫的理论视角
2021-12-28伍小乐
伍小乐
(湖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一、问题的缘起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整体实力和形象的缩影,其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区位概念,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对外的“窗口”,担负着边疆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双重任务,“不管是在何种国家形态,抑或何种历史时期,边疆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都是不可言喻的。”[1]费孝通先生指出,“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2]在中国,农村连片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的边疆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3],边疆民族地区受多重致贫因素相互叠加的影响,导致其贫困面积大且连片化、贫困人口多且分散化、贫困程度深且多维化。近年来,在国家精准扶贫和政府兴边富民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尽管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大幅缩减,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滞后、交通网络较差等特征,导致政府行政成本、社会物流成本、居民生活成本偏高,并且边民“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依然存在,传统精准扶贫措施效果并不明显。[4]概言之,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边民肩负着守土固边的政治任务和兴边富民的社会责任,易地搬迁、转移就业等国内其他地区行之有效的扶贫方略却不宜在边疆地区大范围使用。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十四五”期间边疆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便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这是实现国家2035远景目标的关键。
作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消费扶贫是一种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造血式”扶贫模式,它不仅能够使边民守土固边,还能够兴边富民,弥补了精准扶贫时期的某些方略不适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缺漏。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提出,要“设计推出网络公益扶贫百家谈等解读传播项目,充分挖掘网络公益扶贫的理念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全体网民积极参与,开展各具特色的消费扶贫活动。”[5]同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等16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贫困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休闲农业的宣传推介,鼓励支持电商平台常年开展富有特色的网购活动,共同营造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6]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多渠道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推动批发市场、电商企业、大型超市等市场主体与贫困村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贫困村,推广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场活动。”[7]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则明确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以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8]2020年2月,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指出,要“发挥中国社会扶贫网消费扶贫平台的作用,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以藏区青稞、牦牛和南疆大枣、核桃等为重点,以东西部扶贫协作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馆、地方特色扶贫馆等为载体,专门销售扶贫产品。”[9]同年3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行动方案》提出,“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打通贫困地区产品流通和销售‘瓶颈’,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旅游等服务供给质量,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宣传考核。”[10]显然,消费扶贫一方面连接着相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另一方面连接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广大的消费者,因而需要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和消费市场之间持续性互动的深度以及贫困户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性互动的“温度”,从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和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情况,通过宏观层面阐述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主要效应,旨在更深入地剖析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现实困境,为“十四五”期间党和政府进一步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二、消费扶贫赋予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四重效应
不同于以往“输血式”的扶贫方式,消费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方式,它能有效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并产生如下四重扶贫效应。
(一)政治效应: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
扶贫旨在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贫富差距的拉大,加上国外反华势力的渗透、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11],势必会破坏边疆的政治稳定和政治认同。消费扶贫政策的实施在助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同时,能对边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的生成产生重大影响,其政治效应不容小觑。本质上,消费扶贫有助于转变边疆社会中“行政化”的扶贫方式,扩充边疆社会中的社会资本,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12]诸如通过“县长代言”“镇长代言”“第一书记代言”的“官方”宣传形式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和旅游服务做推广,一方面可以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畅通销路,吸引游客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消费,促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进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缓解某些贫困户“仇富”的心理和对政府“不公平公正”的政治认知,避免外界打着“人权”“民主”等极度虚伪的幌子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舆论煽动,引发不必要的民族矛盾,真正让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人人都享有消费扶贫带来的“政策红利”,从而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二)经济效应:带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消费扶贫的核心是实现消费者需求和贫困户供给的充分对接。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国家的边远地带和交通网络的末梢,如果按照传统线下消费的方式,消费者必须在实体店进行线下购买,这无疑对于交通本身并不发达的边疆民族地区实施消费扶贫是“雪上加霜”。但是,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们网购的热情,电商平台也凭借其强大的信息传递和交易功能使得消费者和贫困户之间跨越空间的供需对接成为了可能。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较2018年底增长了1.00亿,占网民整体的78.6%,网络购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下沉市场、跨境电商、模式创新为网络购物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动能。[13]显然,消费扶贫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之后,不但扭转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劣势,推动了边疆特色农产品、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集群发展,形成了集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个环节的产业链,而且促进了边疆贫困地区产业的更新换代和产品质量的转型升级,加速了边疆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某些“小众产品、小众需求”也可通过平台的聚合功能实现供需匹配,使“长尾理论”变成现实,更加符合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特色民族产品与服务供给现状,从而使贫困户供给和消费者需求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14],进而带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文化效应: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边疆扶贫事业的基础。消费扶贫需要对边疆本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让边疆特有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艺术形式融入到边疆特色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当中,不但能集聚形成一种消费扶贫的文化效应,还能凸显边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例如,“壮族三月三”是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等广西世居民族的重要节日,其中气氛最隆重、特点最鲜明的当属壮族地区的赶圩对歌,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壮族歌圩文化成为广西一个重要的民族特色文化品牌[15];西藏则推出了“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发现中国”“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系列对外文化交流品牌,进一步提升了其品牌文化项目的国际影响力[16];云南文山州着力打造砚山县稼依镇大稼依社区、富宁县里达镇里达村委会、麻栗坡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等一批具有少数民族和边疆特色的廉政文化品牌[17];内蒙古通过美术、摄影、舞蹈、民间文艺、文学创作等形式倾力打造“草原文化”品牌[18];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精心打造的集胡杨手工艺品展示、胡杨根雕创作观摩、胡杨文化体验和餐饮为一体的胡杨文化品牌。[19]毋庸置疑,文化品牌代表着一个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标杆,意义深远。一方面,通过精心创造和深度传播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品牌,能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品牌的文化效应,以旅游消费助力扶贫的形式,吸引广大消费者积极消费边疆“文化品牌”、助力边疆脱贫攻坚;另一方面,边疆民族文化品牌的创建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边疆多样化民族文化更高的敬畏和认同,能彰显边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
(四)社会效应: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消费扶贫主要是通过以购代捐和以买代帮的方式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从而让扶贫更有温度和价值。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消费扶贫也是通过消费者购买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产品,诸如藏区青稞、牦牛和南疆大枣、核桃,以线上线下消费的方式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以及通过吸引消费者来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消费,带动周边特色餐饮、民宿、民族特色产品、民族文创产品等产业链的发展。随着消费扶贫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效应的不断凸显,相对贫困人口的腰包鼓起来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感增强了,则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自信心,坚定其脱贫致富、积极就业的决心,有助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消费扶贫整体成效来看,它开辟了社会力量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领域,解决了某些相对贫困人口的农特产品难以优质优价售出、提高附加值等问题,某些知名企业发起的农产品众筹或“扶持产业发展”众筹项目[20]带动了更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消费扶贫行列中,其扶贫成效更高、社会效应更加凸显。概而论之,消费扶贫的不断深入开展,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则会逐步提高,驱使着相对贫困人口主动学习产品改进的新技术和服务改善的新理念,扩大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规模,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标准,从而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化、标准化,形成了消费者满意、可信度高的良好社会效应,有助于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治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梗阻性难题的多维透视
满足边疆民众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消除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既是消费扶贫的应然之意,又是边疆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起点。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多处于偏远的山区、交通的末梢,贫困程度远深于其他地区,再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开放程度受限以及多元化民族文化和多样化宗教信仰的错综复杂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导致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不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1]48从边疆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原因来看,除了由于伤病、债务、灾害和懒惰等因素致贫外,绝大多数边疆地区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是由于自身生产能力的不足,要么是没有富余的农产品可在市场售卖,要么是没有足够优质的农产品可在市场竞争。从主观方面来说,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不足,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独立生产和经营,生产的初级产品较多,产量小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虽已不再“为生存而生产”,但也很难转向“为市场而生产”[22],这是导致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不高的根本原因。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3.4%,西部地区①则为53.4%,从统计数据来看,即使是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文化程度也并不乐观,全国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4.2%,西部地区则为40.9%。从客观方面来说,由于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偏远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再加上软硬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工具相对缺乏,成为导致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不高的重要因素。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5公里以上的全国比例是9.2%,西部地区则是19.3%;生产工具方面,西部地区每百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仅拥有拖拉机5.4台、耕整机1.4台、旋耕机4.0台、播种机1.2台、排灌动力机械3.6套、机动脱粒机5.6台、饲草料加工机械2.8套。可见,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自身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理念和生产技能不足,再加上地理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条件不便、基础设施落后,造成了边疆贫困人口生产能力不足,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最大障碍。
(二)社会参与的可持续性不足
消费扶贫的本质是充分运用市场规则,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在增加贫困人口收益的同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会参与程度的强弱关系着消费扶贫成效的高低。不可否认,消费扶贫在短期内能够收获较好的扶贫成效,拓展边疆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和少数民族文化衍生品的销售网络,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然而,扶贫虽然讲求差别对待,却也内含对平等、公正等价值的追求[23],而这种基于道德的“慈善式”消费扶贫难以维持长久。其一,如果社会力量是受政府政策“驱动”而参与消费扶贫的,则其可能是基于一种“助人为乐”的扶贫心理预设而选择消费边疆民族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有效需求存在“泡沫”现象,再加上少部分企业、公益组织、NGO等社会力量的公益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社会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动力不足。其二,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现状以及发育不太成熟的专业市场,在产品分级、储藏保鲜、物流运输、包装设计等环节相对落后,时常出现“有产无量”“有量无质”的现象,造成消费者的体验感较差且社会参与成本太高,进而可能削弱社会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热情。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西部地区仅有36.2%的乡镇拥有粮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市场,只有34.0%的村落建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其三,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市场消费结构不匹配,单一式传统农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水稻、小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和生猪、鸡、鸭等畜牧业为主的产品与市场对接程度并不高,市场需求的优质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瓜果蔬菜、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却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打击了社会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其四,某些社会企业和网络平台发起的消费扶贫活动往往是一次性的“买卖”,缺乏后续的持续运作和长效对接方式,甚至还存在少部分企业或平台打着“公益”的幌子利用消费扶贫“浑水摸鱼”,对边疆民族地区滞销产品进行炒作和虚假的消费扶贫众筹、感恩回馈等,对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严重影响了社会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可持续性。
(三)政府角色的功能定位不准
政府作为架在消费扶贫中贫困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对于引导和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具有关键作用。可是,从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在推动消费扶贫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角色的功能定位不准,导致“行政性”帮扶、“账本式”脱贫、“指标化”扶贫等问题广泛存在。一方面,政府在消费扶贫过程中“重业绩轻实绩”。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出现片面的“指标化”倾向,通过“巧立名目”将一些消费扶贫的政策措施变成新的“政府包干”制度,把实施消费扶贫的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了“包干花钱”上。对内硬定“硬指标”、暗设“考核”,甚至将消费扶贫任务“政治化”,明确规定单位部门每年必须去对应帮扶点开展多少次活动、花多少钱,单位职工必须消费多少钱的“扶贫产品”,完不成指标任务则在年终考核中对单位部门和个人实施“一票否决”;对外则将其作为单位扶贫业绩,夸大消费扶贫的成效,以此应对上级政府部门的考核。一方面,政府在消费扶贫过程中“重激励轻管控”。消费扶贫中“以购代捐”“以买代帮”“订单帮扶”等形式极大地刺激了市场对贫困地区的产品需求,而政府的角色却是最大限度地激励农产品企业和贫困户扩大产品的生产规模,实施“政府包干、销路保障、利润保底”的策略,对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标准则并没有加以严格的管控和监督。尽管这种策略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但从长期来看,其并不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持续性发展,一旦政府由于某种原因减弱了这方面的政策支持,由于这些农产品企业或农户在“政府包干”的政策下并不实时了解市场动态,势必会造成产品销路不畅、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不足等困境,消费扶贫成效得不到有效保障。总之,政府角色的职能定位不准,容易造成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策略偏差与监管缺位,且这种单纯的“喂奶”“输血”“包干”的消费扶贫策略并不能起到长效作用。
四、迈向可持续的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基于消费扶贫的理念
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并且石漠化、荒漠化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农牧业发展的先天性条件不足,产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可见,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不但要考虑贫困户脱贫的问题,还要考虑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客观环境因素。消费扶贫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实践中的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贫困户、社会和政府这“三驾马车”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实现边疆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愿景。
(一)集聚能人效应:带动消费扶贫“全民皆能”
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持续开展的关键在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有效实现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根本动力的来源又归结于贫困户是否有生产高质量产品和提供高质量服务的能力。当前贫困户“等”“靠”“要”的懒惰思想依然存在,导致贫困户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不高、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首先,要转变贫困户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的落后是贫困户的“穷根”,要想拔掉“穷根”,需要转变贫困户的思维观念,让其摒弃以往“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由政府自上而下“政策灌输”的效果往往并不如村落族长、乡约等乡贤的“政策说教”管用,因而,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要充分调动乡贤的积极性,以乡贤的行为示范带动贫困户的参与积极性,进而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其次,当贫困户的参与热情被充分激发以后,则需要增强贫困户供给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重视“土专家”“村干部”“田秀才”等“乡土人才”的挖掘和培养。[24]在贫困户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方面,不仅应包括非农就业技能和手艺,也应加强养殖、种植、设施农业、林下经济、花卉苗木培育等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培训。[25]譬如,通过鼓励“致富能人”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田间学校”“民间智库”“实训基地”的建设,支持边疆民族地区非遗传人、民间手艺人等“能人”参与融合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创作空间”“创意工坊”“DIY之家”的创建,让贫困户主动“回炉再造”,以提升其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最后,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技术型精英”和“技能型能人”的“虹吸效应”,吸引在外青壮年劳动力和大学生群体返乡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充实消费扶贫的人才队伍。总之,消费扶贫为每一个人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机会,并通过“乡土能人”的示范作用和集聚效应,带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全民皆愿为”与“全民皆能为”。
(二)营造社会氛围:避免消费扶贫“昙花一现”
在消费扶贫中,消费者能否持续参与直接关系到消费扶贫能否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创造出鼓励消费者参与扶贫的社会氛围,消费扶贫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6]。这要求我们:其一,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公益精神的培育,并努力将之转化为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中的公益行动,将“被动消费”转化为“主动消费”,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公益氛围。其二,要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公益部门、NGO等社会组织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中的正向宣传作用。据社会组织数据网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累计登记社会组织211789个,其中,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有72909个(内蒙古9323个、新疆411个、西藏52个、云南2119个、广西4319个),仅占全国的7.7%,这说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需要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其三,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偏远山区、交通不发达、信息流动相对闭塞,在宣传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时,要树立消费者和贫困户“双赢”的理念,切不可为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而夸大宣传甚至虚假宣传,防止市场出现“劣币逐良币”的现象。通过探索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合作社+企业”模式,实现贫困户和消费者的信息和利益共享、风险和责任共担,从而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畅通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增强农产品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其四,建立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农产品和少数民族特色产品线上线下宣传平台,不仅要建立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固定的专业市场,用于展销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农产品和少数民族特色产品,还要以“互联网+”为载体,并借助知名电商平台开展线上宣传和展销。譬如,线上推出“山货上山头”扶贫项目,打造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将农产品信息和品牌故事结合起来,帮助提炼总结特色农产品差异化卖点,并通过创意策划提出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定位,赋予其更好的品牌价值。[27]另外,通过与电商平台建立定制型采购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产品的社会影响力,进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产品的品牌化,营造良好的消费扶贫社会氛围。其五,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调整和升级边疆民族地区产品生产结构,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标准的基础上,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的转型升级,促进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譬如,开展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产品消费扶贫和自然风光旅游消费扶贫,让消费者在餐厅可以品尝到西藏的青稞、云南的火腿、内蒙古的烤全羊、广西的巴马香猪肉等;在超市能买到新疆阿克苏的薄皮核桃、鄯善的哈密瓜、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库尔勒的香梨、叶城的大籽石榴,云南的普洱茶、过桥米线,西藏的藏红花、冬虫夏草、尼木藏香、藏毯等;去领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风光、雪域高原雄壮美丽的西藏风景和民族文化、海天一色“醉美山水”的广西山水文化、城市与沙漠“共舞”的新疆大漠戈壁风光、云南自然生态和少数民族风情等。概言之,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社会氛围的营造既要让产品有“可销售的渠道”,还要让产品有“可保证的质量”。一方面,通过线下专业市场的搭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拓展,大力开展“本土化”消费扶贫社会氛围的营造;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线上的信息流推送技术对品质有保证的产品进行曝光,扩大产品“客土化”的影响力,从而吸引平台潜在消费者购买产品,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框定政府角色:扮演消费扶贫“安全卫士”
虽然消费扶贫是一种买卖双方的市场交易行为,理应遵循市场的规则,但作为一项国家策略性的扶贫政策,却始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其一,政府要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中扮演好“推销员”的角色,在解决边疆民族相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销售问题的时候,要避免“政府包干”下的行政性“消费摊派”,在注重扶贫业绩的同时也要关注扶贫的实绩,通过国务院扶贫办指导的中国社会扶贫网、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网站和消费扶贫传播媒介进一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进而拓宽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渠道。其二,政府要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中扮演好“监督员”的角色。对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从产品分级、储藏保鲜、快递物流、包装文创等各方面提升产品科技含量、管理水平和文化底蕴,用制度为特色产品的安全和品质保驾护航。[28]同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为消费扶贫建立一条公开透明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并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使农产品销售的上下游都明确知晓价格,从根本上解决“中间商挣大钱”的问题,并直接将有供货需求的贫困户与寻找商品的消费者连接,实现消费者跟贫困户精准对接,全程监控保证销售数据真实。[29]其三,政府要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中扮演好“引导员”角色。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具有其特殊性,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导向性政策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通过整合消费扶贫政策,引导和鼓励政策性商业银行、保险机构、担保机构等金融单位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譬如,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结对子”帮扶的方式,推出适合小农资本和贫困户需求的小额贷款、助农信用卡等金融产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增加农村转移支付,提高政府对普通农民的福利支持,通过对普通农民增加福利支持,间接减轻农民负担,进而激发普通农民的消费行为。[30]一言以蔽之,在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实践中,政府要找准自身的职能角色,全面保障边疆民族地区消费扶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 本文选择西部地区数据是由于国家统计局划分的西部地区覆盖了本文所指的边疆民族地区省(自治区),具有一定的说明力和解释力。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