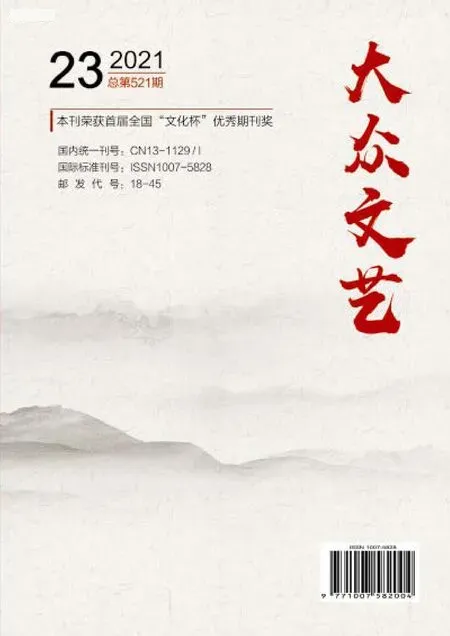摇滚乐中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均势妥协”
2021-12-25胡奕彤
胡奕彤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市 100031)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出现,其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之。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与此同时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各种思想文化繁荣呈现。后现代主义具有反对中心性的特性,消解对于本质和真理的追求。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先在艺术中产生了影响,音乐艺术领域也不例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后现代主义不仅影响了专业音乐领域,大众音乐文化领域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蓬勃发展,摇滚乐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之一。
一、后工业时代音乐产业化中的摇滚乐
后工业社会时代音乐的传播和欣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摇滚乐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并蔓延至全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音乐的传播方式变得更为多样,传播力也更强。音乐不再局限于音乐现场,经过录制的音乐可以随时随地呈现,摇滚乐也不例外。热烈的摇滚现场被灌制成唱片,不仅满足了乐迷多次再现的需求,摇滚乐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因此大大增加。这种复制技术产生的音乐,与传统音乐会现场相比在美学意义上存在差别。德国犹太学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认为,经过复制的艺术,失去了传统艺术中独一无二的特性。音乐作品的每一次现场表演皆存在即时即地性,听众和演奏者的状态以及环境状况都是影响因素。音乐艺术是感性的传达,音乐的每一次表演都具有创造性是有生命力的,这也是音乐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独特之处。经过录制而复制的音乐显然不具备传统艺术的独一无二性。这种独一无二性是本雅明所谓“韵味”的因素之一,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复制艺术的美学价值持否定态度“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韵味”。不过本雅明对复制艺术带来的价值是积极肯定的,他指出,“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
音乐的精英性质和贵族性被后现代主义消解,以媒体和唱片作为载体大量传播。一方面由于后工业时代文化产业兴起,音乐突破了原有的特定范围,音乐厅不再是音乐唯一的消费场所。同时音乐随着录音录像以及电子技术的发展大量被复制,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欣赏到音乐,大量生产使音乐具有了大众化的性质,它失去了传统艺术的神圣性,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同样由于电子技术在音乐领域的应用,“并无艺术天赋和音乐艺术修养的人,也可能依靠他的计算机知识在计算机上设计、生产出‘精美’的摇滚乐‘艺术品’来”。带有贵族色彩的西方专业音乐创作在其中消解。大众文化领域的摇滚乐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音乐形式,它走出传统古典音乐的旋律情感化的方式,选择了节奏这种人类最原始和基本的感受力,以节奏情感化的音乐方式走向大众,人们不需要拥有良好音乐修养的“音乐耳朵”,便可沉浸在摇滚乐丰富激荡的节奏当中。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主义时期音乐的过分精英化,也促使了大众化音乐的发展。现代主义音乐语言远离了普通人耳所能接受的乐音审美范围,成为少部分人的音乐。以勋伯格的十二音作品为例,虽然音乐在安排好的包含12个音的音列中展开,但人耳几乎无法区分出同类作品,更无美感可言。于是一部分作曲家加入大众化音乐的创作行列。
在20世纪不同时期摇滚乐CD中可以听到录音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数字录音技术改变了摇滚乐最初的模拟录音时集体同时录音的方式。在听早年模拟录音的摇滚乐CD,杂音偏多,但多是乐队成员同时演奏录制的,音乐还是自然和完整性的产出。而采用了数字录音技术录制的唱片音响效果非常出色,每一轨都清晰可辨,各音轨之间也有完美的配合,但录音师可能只需要采录片段的实际演奏录音,并且可以对所采录的音逐个修改。以此方式产生的音乐的自然性和完整性缺失,音乐丢掉了在传统音乐中极为重要的感性表达的完整性,散落的音乐碎片经过录音师本人的“录音美学”拼凑成了与作曲者同名同形的音乐。这其中音乐感性完整性的缺失也体现了后现代的反中心特征。这种“拼凑”的音乐作品与后工业社会人们“快餐式”的音乐欣赏相适应。从早年的随身听到现在的手机、电脑都是大众最为普遍获取音乐的方式,但是音质不说与音乐厅现场相比,同早年黑胶唱片的还原度都无法相提并论。高频随着噪音一起被遗弃,音乐的表现力当然也难逃被丢弃的命运。
二、摇滚乐现场的广场音乐性质
摇滚乐的后现代性不仅仅体现在后工业音乐产业的消费方式,摇滚现场也体现了丰富的后现代特征。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的狂欢化理论认为,广场是狂欢的必要场所,摇滚乐的广场音乐形式是必然的走势,广场音乐的形式可以使摇滚乐中酒神崇拜的狂欢状态更进一步。在摇滚现场可以发现,乐手的舞台通常高于观众所在的地面,舞台有灯光布置由专业的灯光师操作,巨大的声浪由音响设备传出,摇滚现场是没有座位的,所有观众站在舞台前自由地随着音乐摆动或吼唱。乐手的表演和台下的参与者融为一个整体,乐手带动参与者一起沉浸在当下的“狂欢”中,同时观众的热情反馈给予乐手动力,形成一个能量传递的循环,这与传统音乐厅听众作为被动接受的一方不同,摇滚现场消解了传统音乐厅文化中潜藏的等级观念,广场音乐活动中人们的等级和身份区别消失。此外,灯光的通力配合是摇滚现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摇滚现场通常是在夜晚举办,因为黑夜比白天更具超现实性,灯光在照亮夜晚的同时,给现场披上迷幻的色彩,具有酒神性质。音响更是摇滚音乐现场的核心力量,电控音响的巨大声场加之激荡奔涌的电声乐器,参与者轻易地达到了如酒神祭祀般的陶醉状态。在传统音乐中,只需要听众的听觉参与,摇滚乐参与主体的感觉不仅仅集中在听觉一点,而是分散给各个感官,比如现场“pogo”中观众彼此发生的肢体接触,听众气氛热烈与否会影响到在场所有人的体验,台上摇滚乐手激情的表演带来迷幻丰富的视觉冲击等,参与者的多种感官被充分调动。广场音乐也将传统音乐厅的隔墙消解,使现场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这种特质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属性。
巴赫金认为摇滚乐现场不完全是酒神精神,还有一丝理智的存在,这一丝理智是可以认识到自己主体的存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以及战争造成人们自我认同障碍而导致了自我的零散化,摇滚乐现场酒神精神的笼罩给现场参与者提供了自我整合的平台。摇滚现场的参与者在“民众整体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一致性”,在现场的狂欢中“异化暂时消失,人回归到了自身,人在人们之中感觉到了自己是人,这种真正的人性的关系,不只是想象或抽象的思考的对象,而是现实实在的,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接触中体验到的,乌托邦的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了”,这个特殊的环境修补了后现代主体的零散化,使人得以回归人的自然本性。摇滚现场的广场狂欢状态体现了主体的消解,美国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认为后现代人的狂欢是一种“欣喜若狂与自我毁灭”的状态。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能量都在自由独立的拼搏中耗尽”,从而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既是后现代主义中的“主体的灭亡”特征。个人的一切特征消解,情感也随之消失,这种状况需要摇滚现场的狂欢文化。摇滚现场的参与者与现场融为一体,个性化的情感消解在现场的整体氛围中。舞台上的摇滚明星可以看作是参与者理想中的形象,由参与者们共同造就,是他们心中投射出的另一个自我,而非真实的明星本人,摇滚明星被异化成为一种形象。
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所谓的“焚化”,摇滚乐现场是焚化的过程,人们和摇滚明星一起营造了一场狂欢,而就算现场被录制成影像,但现场已经不在,影像只是焚化后的灰烬。后现代主义具有反美学的无序的特点,美国评论学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1925-2015)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不确定性内在性”。“不确定性”中反叛文化的姿态以及多元性,在摇滚乐中有着丰富的体现。摇滚乐的歌词及摇滚明星的着装充斥着反对贵族精英文雅高贵姿态的理念。口语化歌词添加的十分随意,内容上也无文学的艺术性可言,比如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并无意义的文字重复等等。摇滚明星在穿着打扮上混淆男女着装的特点,并且行为举止也完全反叛以往人们所追捧的高贵优雅。多元性体现为摇滚乐现场相比传统音乐的参与方式。如前文所述,参与者不仅调动听觉,还有视觉、触觉、多种感觉的共同支持,才能完成摇滚现场的完全体验,仅靠传统的听觉感受是远远不够的。
三、摇滚乐与主流文化的“均势妥协”
摇滚现场这种大众广场的文化形式,具有非官方的性质,它往往不受主流文化的约束,自然会给主流文化带来冲击。正如巴赫金提道,“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以自己的广场语言,建立自己世界以反对官方的教会,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反对官方的国家”,摇滚现场这种广场狂欢形式带有强烈的自由和反叛精神,人们常常以这种非主流文化的地下活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及反叛情绪,这也是摇滚乐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在我国被誉为摇滚教父的崔健,20世纪八十年代与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匈牙利贝斯手巴拉什和马达加斯加的吉他手艾迪等人组成ADO乐队,乐队中的外籍成员使他受到了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摇滚乐作为极具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音乐形式的代表,其自由与反叛的品质与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相背离。原本作为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手的他,后来走上了摇滚乐的道路。摇滚乐在中国初期的发展从崔健的经历可见一斑,1986年崔健创作了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在八十年代崔健的音乐风格开始融合了西方摇滚乐、雷鬼和中国当时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崔健摇滚现场的热烈场面,音乐中的反叛精神遭遇了主流文化的对抗,致使他在北京被封禁了近二十年之久。直到2005年才得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自己的大型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崔健和他摇滚乐的经历,可以尝试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的“均势妥协”来理解。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他是用霸权这个概念来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为何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内无法产生社会主义的更替。所谓霸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他描述了统治文化通过操纵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社会中的一切冲突都消弭了,也不是一成不变自上而下强加的文化,而是统治文化与被统治文化之间“协商”的结果,其中包含了“抵抗”也包含了“收编”,多种力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构成了葛兰西所言之“均势妥协”。
以崔健摇滚乐在我国的发展为例。在当时的环境下,崔健的摇滚乐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一方,在主流文化的环境中,摇滚乐的反叛精神是不被需要的,崔健摇滚乐代表的激进反叛文化遇到了限制。在经济和工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摇滚乐这种富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音乐形式是被人们所需要的,由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决定,虽然不被允许公演,崔健在一些小酒吧和迪厅活动,继续创作,其间不乏支持者,主流文化遭到了冲击。但是摇滚乐在最初兴起时的激进和反叛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被主流文化所收编的趋势。
崔健2010年和2011年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交响音乐会,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这位“中国摇滚乐之父”站到了主流文化的中央,这次合作被称为“一场史无前例的跨界盛典”。摇滚乐的形式被收编到主流文化当中,为主流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其中的反叛精神被拦截在外。摇滚交响音乐会的录像简介中提道“到底是摇滚被交响了,还是交响被摇滚了,越是亲临现场,越是无法说清”,演出中摇滚乐的反叛精神被收编,几句平淡唱出的脏话也并不显得突兀。
崔健摇滚乐此后走上了主流文化的台面,随之而来的是被送入主流文化的文化工业进程。文化工业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录像、录音等机械复制手段,使音乐从音乐现场走向个人,相比于之前的摇滚音乐现场音乐与大众生活的距离更近了一步。被收编的摇滚乐成为文化工业中积极服务的一分子。文化工业对大众娱乐审美具有引导的作用,它抓住了人们对欢乐的追求,并尽可能地降低快乐中的个体精神因素寻求。主流文化的文化工业带有经济和政治属性以及文化霸权的独断作风,对摇滚乐的叛逆成分做了剪裁,具有文化霸权的统治文化与富于反叛精神的被统治文化之间“协商”,被统治文化的“抵抗”的结果是留下了摇滚乐的形式。
后现代思潮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下,具有反叛精神的摇滚乐,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种,是当下文化产业的“当红明星”,近年“乐队的夏天”等娱乐节目开始流行,在具有些许反叛精神的地下摇滚人成了全民偶像时,也就是他们的“均势妥协”之时。他们的摇滚乐场地从小酒吧和广场变成了商业公共舞台,拥有更多附庸风雅的粉丝伸出手来学会了“金属礼”。在文化工业的趋势下,摇滚乐可能会被主流文化精神所同化,其中代表后现代反叛和自由的精神也逐渐退场,这样看来,后现代主义在与主流文化的遭遇中,似乎也经历了一场“均势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