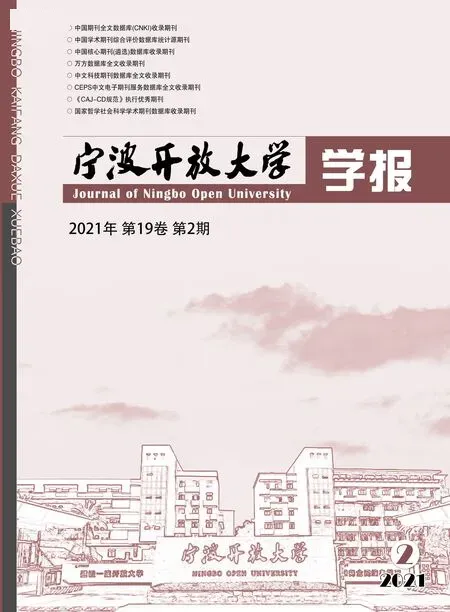公共事件的文本世界
——媒介建构公共事件的符号学分析
2021-12-24王立慧
王立慧
(成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人类社会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基本都要借助媒介来完成建构,记录历史的演变,塑造集体记忆。“9·11事件解释了所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建构的世界(a world ofmedia)而非媒介世界(mediaworld)的含义”[1]6。媒介在社会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被媒介人物(群体和个人)、媒介组织、媒介产业、媒介机构以及媒介文化等共同建构起来的。媒介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是利用各种符号和象征建构起来的“符号性的现实”,从而使人们接受媒介提供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现实图景”,是以完成对社会真实的建构。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即环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正在并且已经创造出属于它的独特符号环境,就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在塑造工具,工具也随之塑造我们。自1994年中国获准加入国际互联网算起,互联网络在中国地区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具规模,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记载历史事件的媒介。它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最重要的平台。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在网络时代产生哥白尼式革命,人类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呈现出不同形态。
一、关键概念与理论依据
(一)“后真相”与公共事件文本
“后真相”最初是指“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2],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后真相”有所不同。其首次出现是源于一篇名为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the Nation的文章,刊登在1992年的美国《国家》杂志上。随后,美国作家凯伊斯(Ralph Keyes)在2004年出版的《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一书中明确指出“后真相”是一种模糊的陈述,它既不是准确的真相,也不是谎言,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形[3]。
2010年,大卫 罗伯茨提出,事实真相被政客们所左右,媒体报道环节、公众舆论和相关政策讨论环节三者完全脱钩,他将这种情况称为“后真相政治”。尽管不断有学者提出“后真相”的相关论断,但是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直到2016年,“后真相”才广泛引起关注,英国脱离欧盟和美国总统大选是“后真相”突然受到瞩目的源头。其实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尤其笛卡尔以降,哲学家们对于“是否存在真相”或“能够到达真理”这个问题上一退再退,他们开始承认真相或许不可能到达。到了当代,福柯干脆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相不过是权利的代名词,而知识只是一种社会控制术[4]。
2016年8月,威廉 戴维斯(William Davis)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时评指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2]。“后真相”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阐释。第一,情绪建构与情绪解读大于事实。客观事实在强烈的情感呼吁下被放置一边,观点的表达比事实本身更有影响力,裹挟着情绪色彩的言论的传播往往能够“一招取胜”,吸引受众的关注。第二,对事实的消解成为“后真相”时期网络公共事件传播的常态。抢占关注度、轻视真相、无限放大碎片信息、无底线的戏谑等,让受众自以为对事件做出了正确的解读。在公共事件的演进过程中,相比于现实的风平浪静,网络空间中各种风起云涌。
公共性问题由来已久,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汤普森(J.Thompson)继哈贝马斯之后发展了关于公共性的一种新的概念,认为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理解过于片面与消极。汤普森认为大众媒介改变了公共性的属性并提出了媒介化公共性(mediated publicness)的三个特点:空间上的去在地化(non-localized space)、非对话性(non-dialogical)、一个对各种符号形式表达的开放空间(open-ended space)[5]。
现如今,公共领域脱离了和一个特定地点的结合;公共领域假定单一的特征被转换成不同公共空间的拼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今天用现有的媒介发展重新审视,公共性的概念又具有了新的表征:其一,参与空间的公开性与参与者身份的广泛性,参与空间不再局限于哈贝马斯说提到的咖啡馆、报纸、杂志等,网络的普及与智能化新媒介都降低了参与者的门槛,讨论公共事务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特权;其二,公共性更多含有批判性色彩,关于公共权力的行使把讨论变成行为;其三,公共性多伴随情感冲突,关于公共性的讨论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任何物一旦被人类使用,就会符号化[6]35。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中认为,意义是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的再现①产生的,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霍尔自己也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并无固定的、最终的意义。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使事物具有意义。但是人类社会从一个文化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文化时期,事物的意义通常会发生变化[7]。据此推断,公共事件就可以被理解为携带意义的文本。没有孤立的文本以供阐释,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文本”(intertext)。
(二)从符号学进入网络文本社会分析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探讨的公共事件的文本专指借助网络媒介展开大规模传播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从时间上划分以1994年4月20日,中国获准正式连入国际互联网为起点。笔者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所选取的中国国内公共事件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包括了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这些信息的生成、扩散和演化,都依赖互联网这个基础性传播渠道。
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20公里竞走比赛中,一直默默无闻的选手王丽萍出人意料夺得冠军,而比赛结束后电视台在报道中对冠军没有任何镜头和采访,只是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那些先于王丽萍的选手都因犯规被罚下,夺冠后的王丽萍如同接受道德审判一般,丝毫不敢提及比赛相关事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电视屏幕上的这一幕画面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热议,约有六千多人参加了搜狐网发起的讨论[8]。2001年第二期《青年研究》杂志就该事件发表了一篇文章《网络讨论的社会学思考——“王丽萍事件”侧记》,这是国内比较早的研究公共事件网络讨论的文章。
2003年以后,伴随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稳定发展,以“公共事件”为主题的论文逐渐增多。“瓮安事件”“俯卧撑事件”“PX事件”“于欢案”“雷洋事件”“魏则西事件”“哈尔滨天价鱼”“王娜娜事件”“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等,无不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由此可见,公共事件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已然成为考察社会文化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此外,若以符号学方法透视媒介化的公共事件,需要从研究的预先假设与目标诉求、方法论基础来说明该问题。本课题的研究前设是:任何公共事件的问题冲突都是因为“刺点”(punctum)打破了正常文本话语的统一性而导致的交流冲突。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路径从最初的对话语结构的静态描述转向对话语意义生产过程的动态分析[9]57。它与符号学无论是在理论渊源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着诸多的相似性,赵星植认为,当代符号学不仅适用于社会分析,更是社会文化分析的重要工具[9]60。这也为笔者对公共事件的媒介建构分析提供了思路。
在符号诸要素中,符号的解释项起着决定性作用。符号的“意义”不等于“客体”,它是“符号所引发的思想”[10],必须要有一个“解释项”来完成符号意义的最终解释。因此,符号不断被“衍义”[11]。在符号的无限“衍义”中产生新符号,那么无限“衍义”的符号就会受到整个文化社群中阐释规则的影响,并制约其意义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与话语分析、媒介建构能够互相包容,并为符号学理论注入新的资源。
二、互联网背景:媒介建构的符号环境
建构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实践的世界[1]6。媒介语境是不稳定的,它始终存在于流变之中,任何关于媒介影响力的讨论都无法回避历史因素,这其中既有媒介自身的历史变化,又含有社会系统中媒介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并非中立,不同的传播媒介有不同的价值偏倚,通过编码、传输、解码的系列符号操作,最终实现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总有其相应的传播科技、媒介制度、传播组织及信息生产能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整体格局和面貌,这种传播状况反过来又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并成为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2]。
工具、技术及原基数推动了文化和社会发现传播与培育传播的新方式,并进而将其制度化[13]90。1994年,中国获准正式连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一家名为“瀛海威”的网站的创立标志着互联网开始介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迈入千禧年,继中国三大门户网站网易、搜狐、新浪宣布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后,2002第二季度,率先宣布盈利的搜狐,宣告了互联网春天的来临。
互联网络在中国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具规模,其公信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互联网为中国网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重要平台,网络交往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去中心化和交互性、平等性的交往方式使得各种观点在网络平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互联网络开放的姿态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也让更多的人有了发声的意愿。于是人们更乐意在这个虚拟的公开场合去发表意见,表达观点。
信息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受到物质工具和思维判断标准的影响[13]7。不同于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速度方面相对滞后的劣势,互联网以其即时传播和易复制等绝对优势,占领了现代媒介传播信息的高地,跟进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视觉冲击。网络将分散的观点和力量融合在一起,这种“化学聚变”式的能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
三、伴随文本语境:媒介建构的阐释框架
符号文本的解释,依靠的是接受者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意义契约”,它不仅是一个符号组合,更是一个裹挟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结构,在解释过程中,不仅文本本身产生意义之外,其携带的附加因素也会影响解释。赵毅衡称这些附加因素为“伴随文本”,明白了伴随文本所起的作用,也就理解了符号表意的机制。
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公共事件想要引起社会关注,除了事件本身因素之外,“型文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型文本”是对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做出明确的归类。在所有的公共事件中,“强弱对抗”和“官民对抗”最能吸引全社会的关注,比如“于欢事件”“雷洋事件”“杭州七十码事件”和各类“PX事件”等都属此类型文本。其次,与民生问题相关的型文本最能引起全社会共鸣,比如“魏则西事件”“山东问题疫苗”涉及到了医疗问题。第三,与“反腐”相关的话题往往会在热度上居高不下,比如“四川严春风事件”等。网络时代,人们要面对的信息浩若烟海,从某种程度上说,型文本是公众判断信息重要程度的依据之一。
文本在生成过程因各种因素而留下的痕迹就是生成性伴随文本[6]147。前文本和同时文本都属于生成性伴随文本。关于前文本,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前文本就是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6]147。在公共事件中,广义的前文本是影响事件的“隐形因素”,狭义的前文本更能在网络公共事件的解读中起到更大的解释压力。就以“武汉再现‘70码’事件”来说,作为前文本的杭州的“70码”事件令网民印象十分深刻,对于这起事件大家的态度也是心照不宣的,杭州的“70码”事件带给武汉“70码”事件的解释压力这个就不言而喻了。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剽窃、暗示等都属于狭义的前文本[6]147,比如这样一则公共事件“武汉再现‘70码’事件”,在这起“富二代飙车,一车两命”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前文本,就是2009年发生于杭州的“70码”事件,同样都影射一个特殊群体,同样都具有争议性。
文本在生产的时候会出现影响文本产生的因素,这就是同时文本。同时文本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出现有时候会刺激和加剧这个事件的戏剧化过程,而且笔者认为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同时文本都是“见微知著”的。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了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元文本是文本生成后在被接收之前形成的,它是关于文本的一种评价。网络公共事件中有时候往往评论比事件本身还具有吸引力,评论也往往会左右对事件解释的压力。在近几年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笔者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元文本带来的影响力超越了事件本身。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争论除了事件本身的争议性外,更多的是关于事件评论的争议,在前网络时代我们会说“沉默的螺旋”,然而在如今身处于“麦克风”时代的社会公众,敢于也愿意就网络公共事件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与其说他们在争辩事件中的是非曲直,不如说他们是对自己思想的表达与捍卫。元文本能够控制解释方向,此外,元文本本身具有强有力的造势功能,除了能够起到宣传作用外,也可以直接传达文本意义。
链文本是一个形象的指称,它原指文本被解释时,文本接收者出于主动的要求抑或是被动的无奈,将其他相关文本“链接”一同接收的文本[6]149。在这个言必称“大数据”的时代,链文本真的就是“大数据”的产物。网站用户只要在该网站搜索过某一内容,之后网站会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给用户。网民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链文本的选择一般倾向于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或相仿的信息和评论,其他的伴随文本都可以被链文本纳入其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语境空间。
看似分散的公共事件实际上是社会文化中的“标出项”,以非常规方式设置公共议程,同时凭借互联网的“加持”,产生并制造舆论。研究发现,当公共事件以媒介文本的形式传播后,所有的意图意义“始终处在协商和改变的状态,以对新的境遇做出反应”[14]。
四、元语言:媒介建构的深层机制
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发现,“严格地说,并没有所谓的个人思想,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在前人思考框架内的进一步思考”[1]6。以网络为主的传播环境下,大多数公共事件的舆论生成不再依靠单一的平台或中心,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转换与新、旧媒体的联手构成了媒体的融合化传播。这种全新的传播模式越来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模式,它拓宽了信息传播范围,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公共舆论。公共事件的跨媒体、跨平台的融合化传播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但是隐藏在“喧哗”背后的元语言却被掩盖了起来。
元语言原本是哲学用语,其观念的出现早于概念。伴随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逐渐进入到语言学领域,尤其在符号学已然成为“显学”的今日,面对当代多元的文化语境,元语言的作用愈加重要,合理运用元语言才能应对当下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
罗素的分支类型论可以被看作是语言分层的雏形,对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按照罗素的理论我们可以推知,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的层级,语义悖论的产生就是因为混淆了这些层级。由此可见,罗素是最早提出语言分层的思想的。明确提出“元语言”概念的,是20世纪波兰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塔尔斯基,从解决“说谎者悖论”入手,以形式语义学的方式讨论了真理的定义问题。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则将元语言推进到言语行为的层面,即言语交流的语境。
符号学层面元语言思想最早见于皮尔斯的“解释项”,他认为必须要有一个“解释项”来完成符号意义的解释。相对于某一具体符号这个“常量”而言,解释项则是一个“变量”[11]。雅克布森认为,对于意义的解释,符号从来都不是被动地接受,符号本身所带有的某种特性推动着解释的朝向。
中国当代符号学学者赵毅衡在符号学诸家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元语言”观念:第一,元语言不等于符码。因为符码是单个的存在,而元语言则是符码的集合。赵毅衡认为符码就是“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的规则,控制解释时意义重建的规则”[6]223。那也就意味着,符码问题更应当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因为只有在构成形式和表意的相互关联之后,符码的功能才可能得到社会或群体中成员的一致确认。第二,人们在每次解释符号文本时,可以调动不同的元语言,从而组成一个“元语言集合”。符码提供了一整套解释符号的规则,使用者只有在相同文化语境下达成的“共识”中完成对符号文本的意义转换,这个文化语境就是“元语言”。只要意义能够被传播,势必就会有相应的元语言来提供与其相对应的解释符码。第三,元语言并非统一完整,而是呈现碎片化,并且首次提出了同层次元语言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可能构成的冲突,即“解释旋涡”。
总的来说,元语言是一个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文本只有在解释中才有意义,元语言的目的,就是从文本中推压出一个意义解释[6]228,但这个意义解释绝不是唯一正确的意义解释。
符号表意有三条悖论:
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
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符号;
任何理解都是理解[6]46。
一个文本在该文本发出和传播的过程中,解释意义必然不在场,只有意义不在场,文本才会滑向解释,才会产生解释的必要。在解释之前,符号已经含有既定意义,元语言的集合在符号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此时的解释,只不过就是临时选择合适当前解释活动的元语言集合来完成一次意义解释活动。同时,临时元语言集合由文本接受者的知识水平、认知状况、经验和情感等多方面构成,从而得出文本接收者所能解释出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则公共事件会引发公众截然不同的反应。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是赵毅衡划分出的元语言的三种类型[6]231。其中,语境元语言表示的是文本与社会之间的诸种关系,它影响着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6]232。语境问题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论及,但直到20世纪才逐渐受到关注。之后,无论皮尔斯还是海德格尔,学者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问语境问题,其根本在于人类对其生存论境遇和诠释的本质性诉求[15]。能力元语言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主要体现为,文本接收者解读事件文本的能力,即接收者站在何种角度、以何种立场看待网络公共事件。文本自携元语言指导此文本该如何解释[6]233。其解释指向具有明显的暗示性,这种暗示会对信息接收者在解读时产生误导。一些网络公共事件本身在元语言层面已经先入为主地带上了解释压力,例如关于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一篇报道为“中国摄影金像奖再爆作假丑闻¬——又现‘周老虎’?”“南京宝马肇事案又现‘70码’”“娱乐圈另一个‘王宝强’!王自健遭前妻‘骗财’,因抑郁暴瘦!”,这些事件本身就已经携带了能指导解释的自携元语言。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2009年“杭州70码事件”和2017年“王宝强事件”均在当年处于评论热点峰值,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众多反思。这些事件本身已经被贴上了某一种标签,被符号化为一种“元符号”,当其他类似事件产生,冠以同样的原因,产生的解释压力不言而喻。
五、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符号文本成为媒介建构现实的常规操作。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对文本解读起决定作用的是元语言。公共事件传播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播现象,信息技术与手段都决定着它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媒介的技术变迁、社会的转型、个体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化的转向,网络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阐释媒介信息的意义[1]147。信息的复杂性导致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技术的异化表现为物的异化,而在虚拟的网络互动中符号成为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16]。媒介(既包括传统的广播、电视、杂志、报刊等,也涵盖以网络为技术支撑的新媒介)建构的公共事件是巴尔特所谓的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现实是基于图像、文字和声音符号构建而来的,这也是米尔斯(Mills)笔下的“二手世界”。
公共事件为我们考量媒介建构现实提供了一个契机,经过逻辑推断得知,媒介建构的现实并非现实本身,它是由媒介创造出的空间纬度上的“在场感”。“在场感”是指一种以精神过程为中介的对周围环境的感觉与意识。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17]。从该层面而言,“在场”并非是客观实在,而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在媒介建构的世界中,媒介使用者与网络行为个体、网络环境融为一体,具有了在场感。故而我们可以判断,只要行为主体能够在媒介活动中获得一种在场意识,那么这就是媒介所建构的“公共事件”。互联网时代,媒介对公共事件的建构携带着或者裹挟着某种特定的意义,谈论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注释】
①中文译本一般都用做“表征”,本论文中笔者将representation都释作“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