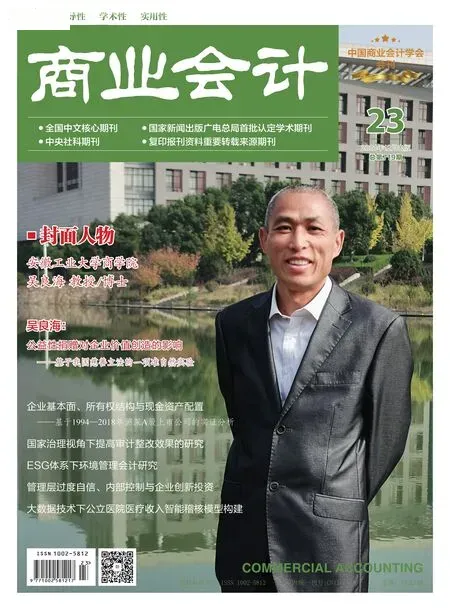上市公司商誉现状及后续计量探究
——以北京某文化公司为例
2021-12-24袁加睿重庆工商大学重庆400067
袁加睿(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一、引言
当前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商誉规模增长迅速,不少上市公司也因此计提了大量的商誉减值,造成了资产虚高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商誉的现状、后续计量进行分析,并探讨解决的方法。
对此,许多学者对现行准则下商誉存在的问题研究后发现,企业商誉资产确认计量不完整,也未确认并购协同效应所带来的合创商誉,商誉披露的信息未反映出人力资本对企业超额获利能力的作用(冯卫东、郑海英,2013);商誉估值方法使用不当(郅彦、石美琪,2020);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初始计量虚高、商誉后续计量随意、减值测试不规范、商誉减值计提“两极化”等问题(刘芳,2020),应采用系统摊销与减值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不摊销,只减值”的做法相当于变相鼓励上市公司确认巨额商誉,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商誉泡沫的形成。基于此,本文对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商誉及减值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并以北京某文化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商誉巨额减值的原因进行剖析,探究缓解商誉巨额减值负面影响的方法,采用结合法模拟北京某文化公司的商誉减值数据并与减值法进行对比予以说明。
二、A股市场上市公司整体商誉情况分析
2005年我国推进的股权分置改革掀起了企业合并的大潮,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合并商誉。2006年我国建立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准则规定,对商誉后续计量采取减值测试而非系统摊销的方式。本文以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采用WIND数据库对2014—2020年的商誉及其减值数据进行统计,并与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信息结合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014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商誉净额仅为3 344亿元,2016年则达到了10 533亿元,而2020年商誉净额更是高达11 797亿元;同时,商誉占净资产的份额在2014—2016年持续大幅增长,2017年、2018年增速放缓。2014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仅为26.33亿元,2015年为87.85亿元,2016年商誉减值为156.76亿元,2017年为368.2亿元,2020年商誉减值更是大幅增长到了1 209.06亿元。商誉减值占净利润的比例同样逐年提高,在2018年提高至4.3%。商誉和商誉减值大幅增长,使得大量企业经营业绩不稳定,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更是难以获取真实、可靠的财务情况信息,也为部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留下了空间。
亏损对上市公司影响重大,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将会被ST,持续亏损下去还有停牌、退市的可能。因此,很多上市公司在连续两年亏损后,会以某种方式将亏损转化为盈利,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将本年度的盈利隐藏起来以便未来平稳过渡。商誉减值对利润有显著影响,当企业处于盈亏临界点时,企业就有可能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当企业已经处于亏损状态时,可大幅计提减值,以为下年“盈利”做准备。2014—2018年A股市场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从165增长到897家,2020降至793家。各年发生商誉减值损失的企业中盈利的占比较大,平均占比76.89%,而在亏损的企业中,虽然剔除商誉减值损失扭亏为盈的企业数量与占比逐年升高,数量仍然较少,79.76%亏损企业剔除商誉减值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这些企业可能是在当年无法实现盈利的情况下大幅计提减值,以为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减轻负担。
三、北京某文化公司商誉情况
北京某文化公司1998年在深交所上市,前身为旅游公司,具有优质的旅游文化资源;2013年,公司开始了转型之路,从旅游逐渐转向影视娱乐业,涉猎电影、电视剧网剧、艺人经纪、新媒体等业务板块。2020年4月29日,公司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该文化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 533.5万元,较2018年上涨15.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0 583.48万元,资产减值损失204 612.87万元,较上年增长94倍,其中商誉减值损失147 578.43万元,将亏损原因归结为全资子公司S公司和X公司因经营业绩下滑而计提商誉等资产减值损失影响了公司业绩。
(一)北京某文化公司商誉数据分析。2013—2019年北京某文化公司的商誉经历了两次大幅度的提高:2014年,公司收购文化传媒企业M公司,形成商誉11 185.14万元,商誉总额提升至12 663.99万元,较上年提升了756%,商誉占净资产的比值升至1.35%;2016年,北京某文化公司的商誉总额为158 763.58万元,较上年提升1133%,商誉占净资产的比值更是提升至35.97%。该公司并购文化传媒行业S公司,形成商誉83 438.36万元,并购文化传媒行业X公司形成商誉64 140.07万元,处置子公司北京L公司、重庆G公司,分别冲销商誉1 478.85万元、210.07万元。2019年S公司、X公司业绩均下滑严重,对两家公司所有商誉计提减值,公司2019年巨额亏损231 924.79万元,剔除商誉减值后仍亏损84 346.36万元,亏损难以扭转,此时大规模计提商誉减值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极可能是为未来实现“盈利”做准备。
(二)合并商誉的形成及减值情况。
1.收购M公司产生的商誉。2013年,该公司从旅游公司更名为文化公司,决定在原有的旅游业务基础上,涉足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影视文化行业,以满足公司增强盈利能力和扩大公司规模的需求,以15 016.49万元人民币价格,从西藏某投资公司购买文化传媒行业M公司100%股权,并就补偿事宜于收购协议签署日同时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作为收购协议附件,协议中,西藏的投资公司做出了业绩承诺。
表1显示了M公司2014—2017年度的预测业绩和实际业绩,2014及2016年度M公司超额完成承诺的业绩,尤其是2014年,实际业绩为预测业绩的2.73倍。2015年、2017年M公司均未完成业绩承诺,特别是2015年净利润较2014年下降了77.98%,在这样的情况下,2015年、2017年北京某文化公司均未对商誉计提减值,根据各年财务报告,M公司虽然有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但是累计总净利超额完成业绩承诺。

表1 M公司、S公司、X公司2014—2017年度的预测业绩和实际业绩 单位:万元
2.收购S公司、X公司产生的商誉。根据北京某文化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2014年5月12日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两家影视文化公司。2016年4月5日新发行股票上市,北京某文化公司完成了对S公司和X公司两家影视文化公司100%股权收购,分别形成商誉83 438.36万元、64 140.07万元,目的是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S公司、X公司做出了净利润业绩承诺。S公司各年均完成了承诺业绩,而X公司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期的2014年、收购后的2017年均未完成承诺业绩,但各年度累计净利润加上累计收到的税收优惠1 591.35万元才达到了累计承诺业绩,基于上述情况北京某文化公司未对相应的商誉计提减值。2017年为对赌期的最后一年,北京某文化公司实现净利润32 030.01万元,较上一年大幅下降,M公司、S公司、X公司共实现净利润26 773.21万元,占该文化公司合并净利润的83.59%。对赌完成后,北京某文化公司业绩立即发生巨大转变,2018年净利润仅12 140.36万元,2019年巨额亏损231 924.79万元,剔除资产减值损失后仍为亏损。2019年北京某文化公司财务报告显示,由于影视行业监管政策调整、演员限薪令、规范税收秩序等影响,对S公司、X公司全部商誉进行计提减值。
四、北京某文化公司商誉巨额减值原因分析
(一)初始计量确认阶段高估商誉。在溢价并购时,商誉为收购价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差价,差价的一部分为被合并方做出的业绩承诺,不切实际的高估业绩承诺是初始确认阶段高估商誉的原因之一,用存在虚高可能的业绩承诺对被收购企业进行盈利预测高估了商誉在未来的潜在价值。北京某文化公司的三起并购被并购方都做出了业绩承诺,M公司、S公司、X公司的累计业绩承诺分别为11 751.8万元、48 000万元、29 970万元,M公司和S公司刚好完成业绩承诺,而X公司净利润未达到预测业绩,各年度累计净利润加上累计收到的税收优惠才达成。北京某文化公司收购M公司形成商誉11 185.14万元接近业绩承诺,而收购S公司、X公司形成的商誉远高于其业绩承诺,在虚高的业绩承诺基础上进一步高估了商誉,对未来对赌合约完成后的企业业绩埋下了巨雷。此外,溢价并购形成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并不完全符合商誉的定义,应当划分为无形资产。并购时,许多高价值资源以无实体的形式存在的,但并没有在账面中体现,如内部研发的非专利技术、影视品牌、经营能力等。这些无形的核心资源会通过高溢价的方式被并购方买入,这一特质在轻资产行业中尤为突出。北京某文化公司并购产生的巨额溢价,一部分是为明星资源、IP价值、流量和品牌效应等买单。北京某文化公司收购S公司,同时吸纳了包括影视投资人、知名编剧及导演等在内的核心团队;收购X公司也绑定了影视圈王牌经纪人,以及旗下知名艺人的明星效应。但由于目前会计计量的局限性以及评估标准缺失,很难将其可靠计量为无形资产,只能在并购中确认为商誉,使得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低于公司实际价值,商誉账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
(二)商誉减值测试可操纵空间大。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需要管理层进行大量的专业判断。商誉企业应当至少每年年底进行一次减值测试,以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为单位。在这个过程中,资产组、折现率、收益增长率都取决于管理层的专业判断,这就给予了管理层很大的自主权,往往相关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也并不详细。这种的自主权给调节利润和盈余管理增大了空间。
(三)减值测试的难度及成本较高。减值测试的方法要求较高,使用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会计素质,对市场环境的发展程度要求也较高,使得此种方法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实际操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公司规模越大,商誉减值测试形成的成本越高,出现纰漏或者畏难怠工的可能性也越大。高昂的成本和复杂困难的商誉减值测试,增加了管理层敷衍塞责、浑水摸鱼的可能性,形成恶性循环。
五、商誉后续计量探究
(一)计量方法选择。目前,依照会计准则,对于商誉的后续计量仍然采用减值测试,即“不摊销、只减值”的做法,变相鼓励了上市公司确认巨额商誉,这种做法很容易虚增商誉,商誉频频暴雷也证明了此点,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商誉的后续计量进行重新思考。对商誉后续计量目前国内外主要采取系统摊销、减值测试以及系统摊销与减值测试相结合三种选择。
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进行系统摊销有合理的成分。首先,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中有一部分性质与无形资产相近,但由于无法可靠计量而并入商誉中,造成商誉计量的虚高。其次,商誉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耗性资产,虽然商誉体现了未来超额收益能力,存在协同效应,但随着对赌时限临近、协同效应相应减弱、未来收益减少、风险增大,因此,可采用系统摊销法。但仅仅采用系统摊销法不够,商誉与未来流入的经济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所以系统摊销无法满足配比原则,况且现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需要减值测试,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依然具有必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系统摊销和减值测试结合的方法(以下简称结合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来缓解存在的问题。
(二)两种计量方法经济后果对比。以下对北京某文化公司的商誉采取结合法进行后续计量,并与减值法进行对比。北京某文化公司在2014—2016年间通过收购四家公司形成商誉,收购北京L公司的时间未知,仅在2007年开始列示商誉。公司收购五家公司形成的商誉均未发生减值,仅在2016年处置北京L公司和重庆G公司,相应的商誉冲销。假定北京某文化公司各年的减值测试均客观合理。
根据北京某文化公司年报,2016—2019年结合法下,各年的资产总值和净利润均有下降,除了2019年的净利润亏损有减轻,结合法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突然计提大额商誉减值而对公司业绩带来的影响,净利润更能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提前发出危险信号,促使管理层关注风险,改变经营策略,避免亏损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减轻对资本市场的损害,减小投资者的风险。结合法下,北京某文化公司在2018年就出现了轻微亏损,此时公司应考虑减值测试中的所采用的标准是否合适、下一年的经营活动是否需要调整等。
从上述分析可得,目前商誉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初始计量虚高、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的难以规避的主观性强、高成本、预估未来收益的难度大等现实问题,但由于会计计量的局限,以上问题难以直接采用特定的方式解决,但可以在后续计量环节,采用结合法减轻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频繁出现的商誉混乱。
六、总结
首先,北京某文化公司在商誉初始确认阶段存在合并商誉虚高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将溢价中部分性质更接近无形资产的确认为商誉、收益计算方式不合理以及高估业绩承诺。其次,北京某文化公司在商誉后续计量阶段采用减值测试的方法,但减值测试过程中存在主观性强、盈余管理操作空间大等缺陷。最后,减值测试成本高、难度大,忽视了协同效应随时间减弱等问题导致资产、利润大幅虚高后又大幅下降,进而导致投资价值失真。企业巨额的商誉泡沫,一旦被戳破,商誉的减值将导致企业巨额亏损,错失补救时机,损害资本市场及投资者利益。在对北京某文化公司的商誉数据采取结合法分析商誉后续计量的变化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后,本文认为,对商誉的后续计量采用结合法,可有效使溢价中不完全属于商誉部分资产价值更加可靠,解决商誉消耗带来的协同效应的下降、未来收益的实现减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