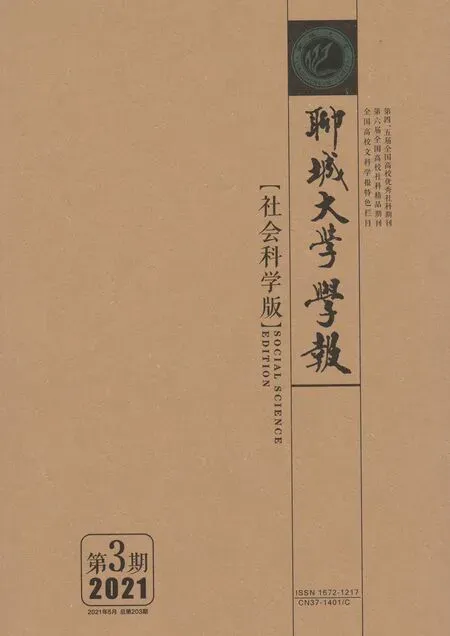从心像到心画:苏轼“清新”风格的生成
2021-12-23关鹏飞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士人首先追求的是士大夫人格,苏轼《李氏园》“何当办一身,永与清景逐”之“办一身”,“即不徇身外之物,惟修身养性是务”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第3170页,第4177页。,在此基础上才能长逐清新之景。清新是苏轼审美风格中的重要概念,他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第3170页,第4177页。一般理解,是把“天工与清新”的“与”理解为并列连词,如有的学者在解释“天工与清新”时就说:“其真谛是否即指此一技巧之‘天工’与作品之‘清新’?”③戴丽珠:《苏东坡诗画合一之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41页。明显是把“与”前后的词视作并列关系。但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苏轼明明说诗画是“一律”,后面却用“天工”和“清新”两个维度来阐释,前后颇有矛盾。如果把“天工”和“清新”视作内在关系密切的两个单位,把“与”理解为“吾与点也”之类的动词,就跟“一律”更为贴切了。如此一来,天工就成为“清新”风格的赞同者,则清新更多地指向一种被外部天工所许可的内在美学,即苏轼所谓的“胸中丘壑”。笔者以前研究苏轼的“清新”美学,是从老庄和佛学切入④详情可见关鹏飞:《万象自往还:苏诗与苏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一章第一节。,但两者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从绘画的角度来看,又有再现与表现的区分。苏轼云:“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⑤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第3170页,第4177页。此指表现。又《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云:“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⑥蔡国黄编著:《东坡谈艺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此指再现。表现与再现的统一,使画之求真从求外形之真转向内求神韵,从逼真再现物象转到写意表现心像。概括来说,先见于心,再见于画,故画是心画之再现。但心画并非真实存在,故画又是心画之表现。这种统一是如何实现的?它又是如何反映苏轼融合三教思想而萌生出来的清新风格的呢?本文略作探讨。
一、身世两忘:心像的诞生
要想穿透真实的迷雾,就不得不放弃对主体或客体的单一向度的再现或表现,而要在融合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心像,再把心像变成纸上的心画才能达到。苏轼正是从这个路径入手的,他往往强调“意行”,如元祐七年(1092)《九日次定国韵》就说:“意行无车马,倏忽略九州。”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059页,第3170页,第3003页,第4177页。这其实也包含诗人深刻的观察与强烈的想象能力。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指出:“借助于语言的力量,用比较强烈的色彩刻画和描绘出来的一种想象中的景色,要比亲临此地进行实地考察更给人以逼真生动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似乎能更好地认识自然。”②保罗•史密斯等:《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第22页。经过诗人观察、想象加工之后的景象,用苏轼的语言来讲,就是“清景”,或叫“心像”:“模仿艺术从一种消极意义上来说是对心像的接受,但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被视作源自实物的产品,这些实物旨在使感知者的心灵深处产生心像。”③保罗•史密斯等:《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第22页。这就说明,当心像通过艺术途径展现出来,也会在接受者心中产生新的心像。由于强调心像,苏轼早年对技巧颇为忽视,认为“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后来明白只有道艺结合才能在纸上画出心像。总之,从心像表现的角度来看,它并非为了表现外物,故不讲究与外物之形似,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059页,第3170页,第3003页,第4177页。;而从心像再现的角度来看,纸上心画不是再现外物,而是表现心像,故常不同于外物,尤其是在形体上,即“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⑤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059页,第3170页,第3003页,第4177页。。
心像究竟从何而来?最为苏轼强调的是此人之德,要有此德才能有此心像:“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其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⑥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42页。便将德与文诗书画合而为一。值得注意的是,诗乃文之毫末,书乃诗之溢出,惟画乃诗之变,变者,与诗不同者也,可见苏轼自然知道诗画之异,但这是同中不同所在:“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059页,第3170页,第3003页,第4177页。妙想是诗画一律的基础,但妙想不一定形成心像,而心像一定离不开妙想。故由于诗画中有妙想,其成品自然亦有相似之处:“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芬,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⑧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12页,第12页。又如苏辙《王诜都尉画山水横卷》:“行吟坐咏皆目见,飘然不知世俗词。高情不尽落缣素,连峰绝涧开重帷。”⑨蔡国黄编著:《东坡谈艺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指出诗画在“高情”上的相似。由于心像非万物所有,故能画心像者评价更高:“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⑩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12页,第12页。而欲得心像,必从万物之理处寻得,黄庭坚《刘仲明墨竹赋》云:“妙万物以成象,必其洞然好学者。”[11]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一旦心像形成,人己皆忘,“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故竹子并非指画上之竹形,而是指心竹。晁无咎对此过程论述最细,其《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说:“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经营似春雨,滋长地中绿。兴来雷出土,万箨起崖谷。”[12]转引自陈衍编:《宋诗精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页。只有胸有成竹,触之以兴,才能画出竹之神韵。当然,此时如不凝神,则破坏心竹,画亦不成。在这过程中,身世两忘是最重要的方法。
首先,从万物生成来看,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不受主观意志所左右。苏轼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二乐榭》中就说:“此间真趣岂容谈,二乐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文与可原诗云:“暖山孰云静,汉水亦非动。二见因妄生,仁智何常用。”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二诗对读可知,在文与可和苏轼看来,自然是真,人为是伪,故苏轼在《赠陈守道》中又强调说:“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又如绍圣四年(1097)《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其二说:“渊明岂知道,醉语忽谈天。偶见此物真,遂超天地先。”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指出醉饮对于回归自然的作用,且将“真”之追寻过程也自然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涉及到天与人之关系,在苏轼看来是趋向于同的,他说:“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同,而可以涉川也。”⑤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141页,第213页,第149页。在苏轼看来,人性本来也就是自然之一分子,没有什么独特,甚至在造物之生、要以“我”为阶的时候,不仅不能过分强调自身,还要积极配合:“阶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为阶,故人升之。我不为阶,而人何自升哉?木之生也,克土而后能升;而土以生木为功,未有木生而土不愿者也。”⑥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141页,第213页,第149页。以我为阶,让别人提升,也就是甘愿自己做垫脚石,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苏轼却通过自然中的相辅相生之事来加以论证,可见人性与自然,苏轼是在人性是自然的一份子的角度来加以肯定的,而不是强调与自然对立的人性。因为极度强调自然和自然中的人性,就要求画家在作画时不随画家而随造物,苏轼说:“大、时不齐,故《随》之世,容有不随者也。责天下以人人随己而咎其贞者,此天下所以不说也,是故大亨而利贞者。贞者无咎,而天下随时。时者,上之所制也,不从己而从时,其为《随》也大矣。”⑦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141页,第213页,第149页。那些强人所难,使之随己的做法,在苏轼看来,会引发世人的不悦,这当然含有讽刺王安石新法之意,但从绘画角度来说,也是突出造物之重要,而要跟随造物,就要首先能把自身遗忘,尤其是遗忘进造物之中。
其次,追随造物不仅要遗忘画家自身,还要遗忘由人为所创造出来的人间世。一方面要遗忘自身,苏轼在元祐二年(1087)《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中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⑧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前面所谓“不见人”,即画竹之时不受与竹不同之人尤其是他人(包括世人对竹之画法、看法、观念等)的影响和污染,甚至在画竹的时候连自身也遗忘,即“嗒然遗其身”,也就是在画竹的那一刻,要抛弃自身以前画竹所形成的惯例、观念、心情等,而要“其身与竹化”,即整个人像庄周凝神那样,跟眼前所画的竹子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像大自然中每棵竹子自然生长却又没有两竹是一样的那样生生不息,即“无穷出清新”。正因为此刻的作者自身与笔下所画的竹合一,所以才能诞生真正有生命力的竹子,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其二感慨“若人今已无,此竹宁复有”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可是文与可毕竟已过世,苏轼不能让他复活,如果想要世间的人学习,也当给出方法,所以后面继续写道:“君看断崖上,瘦节蛟蛇走。何时此霜竿,复入江湖手。”⑩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所谓断崖,非人所易至之地,自然也不会受人世之污染,而蛟蛇奔腾是形容竹竿之态没有一定之形,即竿竿不一样,这样的自然中的竹竿,怎么能够画出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江湖手”,即江湖隐逸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状态中的变化万千的竹子,如果连这个过程都没有,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这种看法,在元祐二年(1087)《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二中说得更清楚:“人间斤斧日创夷,谁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11]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人间之竹树,受人砍伐修剪,已无“龙蛇”自然奔腾之势,正对应“君看断崖上,瘦节蛟蛇走”,而画家独自前往溪山之间去探访此类不受人世污染的竹树,才能画出这样自然生趣的枝条来,又与江湖手相映成趣。其一“家在江南黄叶村”[12]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1356页,第1357页,第4793页,第4860页,第3160页,第3162页,第3162页,第3169页,第3167页。,诗中的“江南”指的是黄州,正说明黄州之行对苏轼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给他提供了江湖生活的经验。
另一方面要遗忘人为世界。无论是厩马还是其他逼真之画,主要以人间物像为模拟对象,而缺乏创造力,真正有创造力的绘画则在其不似人间上,如元祐二年(1087)《郭熙画秋山平远》:“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巘。”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3144页,第3379页,第3383页,第3287页。前四句所写,据《蔡宽夫诗话》乃是“春江晓景”,而后四句所写则是“秋山平远”。前云“非人间”,后云“恰似江南”,似乎有矛盾,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恰似”是指就像在江南送客之时,在江中舟上回望所见的云山,这“云山”才是“恰似”所要强调的地点,而这样的云山,既然需要“回望”,当然不是普通的人所能攀援而上的人间山水,而是较少受人世污染的地方。此种思路,在元祐三年(1088)《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中更为明显,该诗先写画中景象,不类人间,后写自己住在黄州之经历,前半云:“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3144页,第3379页,第3383页,第3287页。既然不知道人间何处有这样的幽境,便只好回忆自己在黄冈之岁月,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岁月不一定就能写好,尤其是与画中看似非人间的景象相比更难写好,汪师韩认为苏轼后半写得“与前相称”,原因是“以自然为祖,以元气为根”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3144页,第3379页,第3383页,第3287页。,所言甚是,苏轼之诗歌创作与王晋卿之绘画创作,皆由此途而进,所以能相得益彰。当然,并非幽人隐士就完全不受污染,有时候他们反而会被他们心中的幽期观念所束缚,从而弄巧成拙,如元祐三年(1088)《书艾宣画四首•黄精鹿》:“太华西南第几峰,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鹿养茸。”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3144页,第3379页,第3383页,第3287页。黄精本是道家认可的轻身延年之药,诗中的“幽人”隐士便以为画中仙境的功劳在黄精,所以想要采走,殊不知黄精之所以有功效,在于其所生长之地,远在人迹罕至的太华山,而今采之入俗,倒还不如留在山中的鹿悄然长角而强气益体呢。
最后,通过身世两忘将主观意志降到尽可能低之后,心像就可以较为真确地获得,苏轼认为,不留于物,观之入心,心有此物,观纸绢上亦有此物,然后奋笔追之,自然无画之痕迹,而得绘画之真谛,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走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⑤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147-148页,第600页。故所画必其所见,而不一定要是大家所见,其《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就说:“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⑥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147-148页,第600页。此佛指卧佛,乃李公麟所创,也就是他所“意造”出来的,却因为他自己已经达到华严相之境界,所以哪怕是自己创造的,也已经集合了“万物”“百工”的智慧,此时如果不把自我放低,而一味强调自身的创造力,会适得其反,李公麟融合人我,在苏轼的文笔中表现为两种形象,即标题中的“李伯时”和文中的“居士”,实际上不过是主客体之分而已,都还是李公麟,这类手法在苏轼的名作《后赤壁赋》中运用得最出神入化,背后的道理都是通过身世两忘而使心像圆融。
二、庐山真面目:心像的客体化
学界对“庐山真面目”之说探索已久,这里从心像客体化的角度略作探究。所谓真面目或本来面目,就是心像的客体呈现,在苏轼看来,心像与真面目是一体两面的。苏轼在《题西林壁》中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578页,第2579页,第5333页,第2596页。乍看之下,此诗与“旁观者清”同理,然陈衍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578页,第2579页,第5333页,第2596页。若仅是旁观者清之理,何谈新思想?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引用柏拉图《理想国》的文字说:“一张床,你可以从侧面看,可以从前面看,也可以从其他任何方面看,是不是观察点不同,它就有相应的变化,不同于它自身呢?还是尽管它显得有所不同,事实上却毫无变化呢?”用这段话来说明“画家不能按实际的样子再现床,只能按照从一个侧面看上去的样子再现它”③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翻译,邵宏校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已经跟苏轼比较接近了,可惜还是困在西方绘画强大的再现传统中,而苏轼诗却巧妙地通过心像来全方位表现庐山。实际上,苏轼诗意,前两句意谓庐山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样子,这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后两句才是阐发道理,之所以在这么多样子中迷失庐山本来面目,原因就在于“身在此山”,它的意思不是说要身在山外,像“旁观者清”那样,何况身在山外就能看见真面目吗?也未必,我们在航拍的飞机上看群山,群山真的是那个样子吗?那些样子都是因为有观者在“横看竖看”,他们自然就迷失在自己通过各种不同角度看到的庐山面目之中了,所以才会疑惑究竟哪个面目是真的。也就是说,起初,观者因为所看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心中看到的庐山面目呈现出多种样态,接着他们又把自身的标准、观念、审美等思想带入,要在这多样心像中确立一个所谓的真面目,那就必然要排斥其他的跟真面目不同的心像。最终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真面目不过是他们所理解的真面目而已。更要命的是,同一个人所理解的真面目,也会因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角度的观看而发生变化,这样大家就开始困扰了:究竟我所理解的真面目中,哪个才是真正的真面目呢?如此循环往复,到头来陷入更深的迷惑。而苏轼指出,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观看者们都“身在此山”,而没有在欣赏山的时候泯灭自身,他们总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殊不知,庐山所具有的那所有的样子,都是它的真面目啊。为什么观看者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一定要追寻那个唯一确定的答案呢?这是因为观者之身的存在,也就是说观者总是把自身视作唯一,这当然没问题,然而一旦以此为起点,用这种唯一之身带来的唯一的观看之道来看待庐山群像,就会自然地迷失在唯一之身与庐山群像共同营造的繁多心像之中,在真幻的徒劳思考中不仅没有战胜幻相,反而连真相也难以把握。
那究竟应该如何观看真面目呢?其实答案就在“横看竖看”之中,只要在看的时候忘掉自身,如苏轼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说的“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578页,第2579页,第5333页,第2596页。那样,观看者忘掉自己的唯一之身,使自己与庐山融为一体,则庐山的美,那无限丰富的美才是真。苏轼最擅长与万物合一,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一种拟人手法,如《龙尾砚歌》云:“我生天地一闲物,苏子亦是支离人……愿从苏子老东坡,仁者不用生分别。”⑤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578页,第2579页,第5333页,第2596页。诗中把龙尾砚拟人化地表达为写诗的“我”,把写诗的“我”又陌生化地称作“苏子”,但实际上无论是诗中的“我”还是“苏子”,都是写诗的“我”,也都是诗中的“苏子”,它们不过是苏轼营造的心像而已,需要统合起来才能真正读懂诗意,因此苏轼在诗中提示说“仁者不用生分别”,不要把这些心像视作有别。这种思想与“身在此山”导致的分别之心如出一辙,其思想来源或与《维摩诘经•观众生品》有关:“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尔时,天问舍利弗:‘何故去华?’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不著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便也。已离畏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著也。’”⑥李英武注:《禅宗三经•维摩诘所说经》,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395页。文中指出花是否黏在身上,跟花无关,而跟人之是否断尽一切分别心有关,只要无所畏惧,尽弃五欲,则花自然落下,否则,光在抖花上努力是没有用的。这些“花”,岂不就是各种幻相吗?苏轼在绍圣四年(1097)《和陶东方有一士》中说得更为清楚:“忽然返自照,识我本来颜。”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这里的“本来颜”就是本来面目的意思,苏轼自注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即主张去尽分别之心,则自得本来面目。实际上苏轼亦曾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的写法写过诗,如绍圣四年(1097)《和陶拟古九首》其一:“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诗中的“客”“友”“我”看似各别,亦如“东方有一士”,不过都是诗人故作狡狯,笔下幻化出来的多重幻相而已,归根究底,这些“客”“友”都是苏轼自身之一,只不过苏轼在陶渊明一分为二的基础上一分为三,又增加了入梦和睡醒的障眼法,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大步地推进了陶渊明的诗法。
此种求真,也与佛法密切相关。苏轼在元祐元年(1086)《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中回忆武昌西山菩萨泉说:“饮泉鉴面得真意,坐视万物皆浮埃。”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苏轼饮用菩萨泉并以之照自己身影,即通过如镜子的泉水水面来看见自己,从而获得自我的水上幻影,与此时他眼前所看见的尘埃般浮动的万物一样,都是虚而不实的。等到真幻已分,真意便自在其中,即该诗后面所云“石中无声水亦静,云何解转空山雷”⑤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之意,苏轼此诗句化自韦应物“水性本云静,石中固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⑥转引自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80页。。此物我之情,即诗人与万物、诗人与庐山等之间的关系,苏轼由此悟出所谓的雷声,就是水石各别、无法合一造成的,如果我们无法与万物泯尽差异,也会同样激起“雷声”,因此,一旦说出“物我情”,就已经有差别之念,因此韦应物要在“物我情”前面加个“了”(了却之意)字,而苏轼要在末句加上“愿求南宗一勺水”,用禅宗之法来消解物我之情。校注引《释氏通览》云:“又问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溪一滴水。’”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法眼禅师的回答即A=A,不生分别,看似没有回答,实际上才是最准确的回答。苏轼对禅宗的借鉴,在绍圣元年(1094)《南华寺》中体现得比较全面:“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⑧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苏轼诗中引道明禅师从慧能求法之事,慧能南下传法被追,道明禅师最先追上,慧能就把传法的衣钵给他,让他拿回去,结果道明禅师拿不动,这个衣钵,跟前文所说的附身之“花”有异曲同工之妙。慧能因此开示道明禅师去追寻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不要道听途说地成为别人利用的手段,泯然善恶,忘怀人我,即苏轼诗中说的“万法了一电”后,自然就能获得“自己面目”。苏轼诗意便从慧能与道明禅师之事而来,他先说自己此次来拜访南华寺,是为了“要识本来面”,中间详述道明禅师之得法过程,并由此反思自身,最后是恍然大悟,“抠衣礼真相”。由此可见,所谓的本来面目与真相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必强生分别。然而,禅师尚且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何况尘世中人呢?在苏轼看来,杂念太多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辅助手段,最多的就是饮酒,如元祐七年(1092)《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韵》:“醉时真境发天藏。”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喝醉的时候自然能抵达真实不虚之境。而酒对于作者之自然的激发作用,也是苏轼比较看重的,其《试笔》诗就说:“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霓。”⑩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900页,第4900页,第4884页,第3054页,第3054-3055页,第3057页,第4401页,第4039页,第4446页。
总而言之,想要获得真面目,同时就会产生假面目,应当泯灭自知,不再执著于真假面目,此时看似没有真假之念,实际上却是真知者,只不过不必这么说出来而已。一旦泯灭自知之后,不仅不会“自以心为形役”,甚至连江山也能为我所役使,从而获得大自在,如苏轼绍圣二年(1095)《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六:“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520页,第4345页,第4311页,第4442-4443页,第2593页。江山在世人看来,常常引发“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疑虑,何况是不断隐见出没的动态江山呢?岂不要把世人眩晕?但在获得自己面目的苏轼看来,不仅不能引发他的迷幻之感,反而成为他所役使的对象,预示着苏轼的生活、创作都由此进入自由境界。
三、清新风格:从心像到心画
前文所说的自由境界,反映在创作风格上就是清新。“清新”原指自然之景,如《赠清凉寺和长老》:“老去山林徒梦想,雨馀钟鼓更清新。”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520页,第4345页,第4311页,第4442-4443页,第2593页。这种自然之景,乃是“天质自清华”而非人为“剪刻”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520页,第4345页,第4311页,第4442-4443页,第2593页。所成,也可以引申为人之自然状态,如绍圣元年(1094)《寓居合江楼》:“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520页,第4345页,第4311页,第4442-4443页,第2593页。被苏轼引入绘画之中后,则与心像有关,而从心像到心画还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这一生产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心像的创造阶段和用诸如绘画或雕塑这样的物质形式来赋予心像以可视形式的技艺阶段。”⑤保罗•史密斯等:《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第48页。具体来说就是“四种能力沟通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间的间隔:判断力、完全脱离实际的幻想、想象力和记忆。观察事物就是通过判断力去接受感官印象,将它们保留在幻想中,凭借想象力和理性精神把它们加工成清晰易懂的精神意象,并出于未来重新得到这些印象的目的而将它们储存在记忆中”⑥保罗•史密斯等:《艺术理论指南》,常宁生、邢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第48页。。这种精神意象就是心像,画在纸上便称之为“心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说:“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夫画犹书也,扬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⑦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把富有气韵的作品称作心画。卜寿珊《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中也引用“心画”的概念,但没有直接下定义,我们只能从全书的论述中发现其所指包括士人画(scholar’s painting)和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⑧卜寿珊著:《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皮佳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其实也带有特定的画种指向。这都是心画发展之后的结果,后人在研究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种历史发展所限制,我们希望从心画的最初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就是指书写(或描绘)在纸绢等载体上的线条,即心画是心像在载体上呈现出来的结果。心像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胸中丘壑,如苏轼元丰七年(1084)《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中说:“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520页,第4345页,第4311页,第4442-4443页,第2593页。又如苏轼弟子黄庭坚评价苏轼诸诗如“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⑩蒋方编选:《黄庭坚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11陆会琼、王朋、谭杰丹著:《黄庭坚题画诗赋注评》,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和“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12黄宝华选注:《黄庭坚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等。此类肝肺中所生之竹石,就是心像的具象化表述。如何从心像出发,画出能够打动观者、哪怕是毫无修养之“痴儿”的清新心画呢?
首先要从心像上入手,也就是说,绘画之清新与心像的营造者画家有关,只要画家像君子那样保持内心纯洁,自然心像清新,苏轼说:“其心至静而清明,故不善触之未尝不知,知之,故未尝复行。知之而复行者,非真知也。”[13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74页。]内心清明,并付诸行动,自然会像“楼中老人日清新”,但事实上心却是不断变化的,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不断被尘蒙的同时不断去洗心,从而达成心之纯洁如初:“以神行智,则心不为事物之所尘垢,使物自运而已。不与,斯所以为洗心退藏于密也。”①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66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75页,第217页。在苏轼看来,不与外物竞逐就是最好的洗心,但这已是很高的境界,而从普通人的角度上来说,不断洗心的过程就是不断养心,以把灰尘去掉,让心之清新日日如此,这刚好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两条路子,苏轼说:“君子所受于天者无几,养之则日新,不养则日亡,择居所以养也。《彖》曰:‘井养而不穷。’所以养井者,岂有他哉?得其所居则洁,洁则食,食则日新,日新故不穷。”②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66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75页,第217页。井里的水如何保持清洁?只有不断食用,日新也是如此,不能靠天,而应该靠自己所养。只要我心在养护之中保持不变,那不断变化的万物,于我便总是全新:“富有者未尝有,日新者未尝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③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66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75页,第217页。每天都全新的不是我们那不变的心,而是不断变化的全新万物。因为心是清明的,才能使物无所遁形,苏轼说:“至静而明,故物之往来屈信者,无遁形也。”④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66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75页,第217页。但有时时机不对,养心似乎无用,此时千万不要因此而自恻,不要怀疑自己养心或洗心的无用,而应该看到“受福者”哪怕不是自己而是他人亦可:“井洁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会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为戚者也,凡为我恻者,皆行道之人尔,故曰行恻。行恻者,明人之恻我,而非我之自恻也,是井则非敝漏之瓮所能容矣,故择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洁者乎?器之洁,则王之明者也。器洁王明,则受福者非独在我而已。”⑤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东坡易传》,第266页,第217页,第259页,第275页,第217页。如此,清新之心便可由己及人,化用无穷。
其次,要使画者的妙想与天工自然契合起来,才能使“剪刻”之类的创造行为达到“天质自清华”⑥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310-4311页,第4329页,第3170页,第3206页。的境界,而那些临摹的画手,则不过是“狂花客慧”而已,因此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中说:“每摹市井作公卿,画手悬知是徒隶。吴生已与不传死,那复典刑留近岁。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310-4311页,第4329页,第3170页,第3206页。妙算要不差毫厘才能得“天契”,即与大自然契合,而真的放笔作画实际上是在精妙入微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的,但如果只知精微刻画,而不知真放也不行,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⑧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310-4311页,第4329页,第3170页,第3206页。苏轼批评那些过分追求形似、拘泥此诗的画家和诗人,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画家和诗人,因为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都遵循同样的规律,就是通过“天工”即大自然工巧的创造力来获得像大自然般“无穷出清新”的绘画或诗歌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作品,它们都跟大自然的万物一样独一无二,所以它们之间唯一的规律就是像大自然那样让每一件绘画或诗歌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清新存在,换句话说,诗画都没有必然要遵守的清规戒律,就是它们所共同遵循的自然规律。苏轼虽然举出诗画为例,其实在他看来,恐怕艺术规律皆是如此。当达到此种境界后,则如《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一所云:“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4310-4311页,第4329页,第3170页,第3206页。将画中景与诗句合二为一,泯灭主客。因此,达到“天巧”以后,创作就会跟大自然一样丰富多彩,而达到“天巧”之后所形成的不同风格的诗画,也会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喜爱。
最后,清新的心画要通过水墨才能较好地呈现出来。墨具五色说就是典型的以作品特征唤醒观者记忆,从而产生五色错觉的艺术手法,看似五色,实际上还是水墨,这与心像、心画等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思维极其相似,因此水墨天然地与心画可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契合。《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篇》云:“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⑩张彦远撰,周晓薇校点:《历代名画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页。就指出水墨与五色之间的转化关系,一旦用墨到这种程度,就是得意之作了,与诗中之自得相通,但如果刻意去追求五色,则反而与物象乖离,适得其反。这些观点对苏轼倡导水墨画或有启发,他在元祐八年(1093)《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中说:“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尽将书画散朋友,独与长铗归来乎。”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诗意谓天公自有水墨,即月光和松竹之间光影交叠所形成的东窗竹疏影和松霜枝,但是由于月光不断在移动,昼夜交替,所以松竹之影所形成的“水墨”也在转瞬之间生成变坏,不断转化,就像无中生有的“造物初无物”一样。而画师对于水墨画的这种动态的把握,需要有诗人那样的妙想才能不断跟上手中千变万化的光影,这不是一个沉迷于教条的俗人所能办到的。画家李伯时(枯木图盖是李伯时所画)本身就是一个诗人,能够画出飞动的骏马,吴传正虽不是画家,但他的诗人眼光背后的妙想使他能够领略画中妙义,而李伯时也是因为胸中有无数骏马的妙想才能在画面中呈现出骏马的姿态与神韵,只要吴传正为这画写出杜甫那样的妙诗,李伯时或许自然就能按照他的诗意作画,由此指出诗画之间相互转化(由李伯时的画到吴传正的诗,又由吴传正的诗到李伯时的画,由此不断切磋,提高彼此的诗画技艺,起到士人之间的交流作用)的关键在于“妙想”,这是诗与画、诗人和画师理解、交流的基础,也是诗与画、诗人和画师转化、提高的关键。此论早在顾恺之时就已提出来,其《论画》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②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王世襄以为迁想妙得者,是“用人之感官灵觉,将对象之微妙部分,所谓神也者,领会在心,更以纸笔一一表现之”③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页。,这种“迁想妙得”,被苏轼概括为妙想,并从绘画延伸到诗歌领域。正是因为诗画皆与妙想有根本关系,所以有大自然召唤苏轼过去,苏轼就能获得自然万象,而把那些模拟自然万象的书画作品散给朋友即可——由此使妙想本身成为诗人和画家最重要的作品,而非诗歌或绘画作品。如《书晁说之考牧图后》:“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寻山跨坑谷,腾趠筋骨强。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④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此诗题写之妙,跟考牧图关系不大,纯由苏轼之妙想,而以文笔出之,如王文诰所云“文笔则得之于天也”⑤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甚是。此类作品虽云题画,实则独抒妙想者甚多,如《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真。生年不知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⑥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汪师韩云:“笔歌墨舞,实有手弄白日、顶摩青穹之气概,足为太白写照矣。”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所云甚是,这类题画作品,与其说是为画面而感发,不如说是苏轼本身因画而触动心中妙想,称其为题画诗,不如径称“声画”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妙想在释惠洪看来就是“妙观逸想”,他曾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⑧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页。惠洪虽然承认妙想,但颇有与自然脱离的嫌疑,与苏轼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有所区别。
花果之类的画通过水墨的处理,也能有显著成效,尹白就在做这类大胆尝试,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墨花》叙中说:“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为赋一首。”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7-4178页,第4189-4190页,第4192页,第4233页,第4237页,第2847页。诗中说:“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缥缈形才具,扶疏态自完。莲风尽倾倒,杏雨半披残。独有狂居士,求为黑牡丹。兼书平子赋,归向雪堂看。”①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847页,第2848页,第3175页。诗中前六句表达尹白之墨花,已不完全求其形似,更注重其神态,所以哪怕用墨也能画出花心、春色,这当然是脱离赵昌、雍秀才之类的写生逼真的水平,因为大自然没有黑色的花,如果用墨来画花,天然地摒弃了求逼真的可能,正是如此,就更需要尹白将个体的心像注入画中,校注解释“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时说得好:“二句言尹白已达作画之道,迅速画成,画并非难事。”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847页,第2848页,第3175页。这与苏轼快速作画一致。因此,作为尹白心像描绘出来的心画,哪怕是黑色的莲花、杏花,也都能富有意蕴,苏轼对其也很赞赏,希望他能再接再厉,画出黑牡丹,这样自己就可以带回雪堂,让黑牡丹与雪墙壁相映成趣,黑白分明,一如士人之心胸。当然,水墨只是比较便于展现心画之清新风格,并不意味着彩色画就不可以,不能过于拘泥,比如苏轼就认为彩色折枝也可以画好,元祐二年(1087)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二中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第2847页,第2848页,第3175页。虽然瘦竹不像竹而像隐士,幽花不像花而像贞女,可是花枝上的雀儿仿佛能把花瓣摇荡成雨,两只翎鸟从竹枝上飞起,它们往前助飞所产生的后坐力仿佛让竹叶因此自然地举起来,而那可爱的采花蜜蜂,正将它采来的清蜜藏在两股上——这一切的画面形成自然生动的场景,就好像画它们的王主簿不是在画它们,而是有着“天巧”即大自然巧妙的创造力,不是他在用笔描绘这样的春色,而是春色这样的场景自然来到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总之,通过心像形成心画,清新风格便由此得以表现出来,而心画由于在心像、妙想等方面与诗歌共享生机,长存不灭,于是心画就成为不受载体、时地尤其是描绘对象等因素的限制,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画,解决了苏轼等人对真的困惑。正如张鎡《南湖集》卷二《马贲以画花竹名政宣间,其孙远得贲用笔意,人物山水皆极其能,余尝令图写林下景,有感,因赋以示远》所说:“世间有真画,诗人干其初。世间有真诗,画工掇其余。飞潜与动植,模写极太虚。造物恶泄机,艺成不可居。争如俗子通身俗,到处堆钱助痴福。断无神鬼泣篇章,岂识山川藏卷轴。我因耽诗鬓如丝,尔缘耽画病欲羸。投笔急须将绢裂,真画真诗未尝灭。”④张鎡:《南湖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不仅心画的代表画类士人画如此,士人所创作的诗歌亦然,正是诗画的交融,使苏轼的清新风格具备广阔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