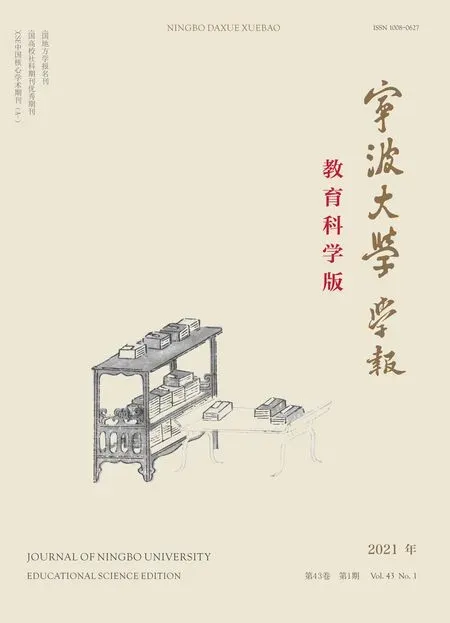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悖论与化解
2021-12-23马小芳
王 乐,马小芳
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悖论与化解
王 乐,马小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文化传承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原初根脉。乡村文化的现实挣扎揭示出两者之间的逻辑悖论,包括整体思维与一元思维的系统差异,开放性与保守性的特性殊途,文化改造与自然承续的方法分歧,以及制度建设与观念建设的建设思路不同。因为矛盾始于整体性差异,所以只能采用教育现代化文化自觉的共生理念,搁置差异与冲突,引导两者在不同的逻辑路向上寻求价值共识。共生策略是化解逻辑悖论的操作性设计,包括利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重塑乡民的文化观,构建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区隔—合作”机制,以及探索乡村教育文化自觉阶段化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城乡教育一体化;乡村文化;教育现代化;文化自觉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重大、深刻和必然的社会改革。其中,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均依托于教育的支持。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和核心动力。它是我国统筹城乡教育改革、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等政策实施以来,中央为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动城乡教育公平与和谐发展而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提出,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3]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4],乡土根脉孕于文化。霍尔和尼兹(Hall & Neitz)认为,文化提供了塑造社会角色行动的价值与规范。[5]也就是说,乡村文化形塑了乡民人格,建立了乡村秩序,培育了民族精神。所以,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发展的灵魂。《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明确了“繁荣发展农村文化”[6]的战略任务。在此背景下,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能否完成乡村文化传承的使命,两者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协同性,这应当成为乡村教育振兴的前提性问题。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文化功能与乡村文化传承的教育责任
教育与文化是一种彼此敞开的关系,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关系也是基于属性与价值的相互支持,一者承担文化功能,一者履行教育责任。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文化功能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命题,次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城乡一体化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资源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它是在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取向下,打破城乡二元僵局,建设城乡教育共同体,在保持与发挥城乡教育区域性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城乡互动联结、相互帮扶、相互作用、消解差距,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7]
此外,“一体化”具有内在的文化关联性。一方面,“一体化”是“属文化的”。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其中“一体化”既是一种文化视角,也是一种文化概念。另一方面,“一体化”又是“含文化的”。它是一种全纳结构的发展动向,而文化必定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逻辑,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文化建设,它也将成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有学者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基于文化、通过文化、为了文化的教育体系。[8]由此可见,文化功能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内在价值演绎。它又可以从系统功能的角度分为系统外的“一体化文化功能”和系统内的“文化一体化功能”,前者是“城乡一体化”范畴内教育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一体化互构,后者则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范畴内文化因素在教育系统内的一体化表征。
从外部的系统功能看,城乡一体化中的教育与文化是两种相互区隔且彼此支持的独立系统,两者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系统共同构成城乡发展的“一体”。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质是城乡的统筹发展,教育与文化在整体性原则指导下,围绕“城乡共同体”的目标各司其职、兼收并蓄、协同发展。此外,由于属性、特点、功能、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教育与文化又具有不同的系统结构和发展路向。从内部的系统功能看,教育系统中文化因素的“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城乡教育一体化要求其在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目标等方面符合“城乡融合”的一体化标准。因为乡村文化具有继承性和保守性,所以城乡教育一体化需要进行教育系统内的“文化改造”,使文化因素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表达性”,能够同时向农村和城市“开放”,建立城乡统一协调发展的教育模式。
总而言之,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文化功能服务于城乡统筹发展,宏观上形塑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微观上培养城乡间自由流动的“文化人”。
(二)乡村文化传承的教育责任
文化是一种体现于符号中的意义的历史性传承模式,是一种以符号形式表达的概念的传承体系,能够交流、保存和发展他们的生活知识与生活态度。[5]传承性既定义了文化的内涵,也规约了文化的属性。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自我传承的需要厘定了延续文化薪火的必要条件——稳定性、保守性和一元性。文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意义之网”,意义由某一群落的公众编织和所有。[9]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被文化自身及其承载的主体所承续并维持稳定,以文化的纯粹性为矢夯实积极意义的保守状态。所以,文化和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定义着教育的内涵,教育建构着文化的“生命机制”。[10]
乡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肇始,是孕育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摇篮。梁漱溟说:“中国的国命寄托在农业,寄托在农村。”[11]然而,在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随着一座座消逝的村落而日渐凋蔽。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12]如此一来,乡风、家风和民风失去了文化上的物质依托和精神依归,进而导致珍贵的习惯风俗无以为继,智慧的乡规民约无以为守,实用的耕植经验无以为用,朴实的乡民性格无以为傲。村庄的破败与文化的落寞互为因果,它们与孤独的农人共同描绘了一幅萧瑟的乡村图景。在不可逆的时代趋势下,教育成为传承乡村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堡垒。
乡村教育的文化责任在于激活教育自身的“生命机制”,担承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乡村教育应当扎根乡村文化深处汲取养分,建立教育与文化的深度对话,将土地里生长出的文化编译成教育的语言和符号。一方面,乡村教育成为“文化化”过程中的重要路径,教育获具文化属性;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承担着筛选、保存和改造文化的责任,使珍贵的乡村文化通过乡民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乡村文化的教育责任是培养对乡村文化知识上认识、价值上认可和心理上认同的“乡民”。所以,乡村教育要使乡民成为理解乡村文化的“文化获得者”,喜欢乡村文化的“文化欣赏者”以及宣传乡村文化的“文化自豪者”。乡村教育不是鼓励乡民“走出乡土”,而是让其怀有愿意“走回乡土”的情怀和自信,同时能够吸引新质乡民的归入。
文化是传承性的,乡村的区位(偏远)、样态(聚落)和生产劳动(四季轮回)特征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文化的稳定性、保守性和一元性。如果教育志在推动乡村文化兴盛,它必然不能违背文化传承规律,应当尊重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避免基于他者逻辑建构教育理解。这也意味着,乡村教育的文化立场是本土的,文化思维是动态的,文化价值是服务于其内在发展的。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逻辑悖论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构建理念预设着其与乡村文化传承的逻辑一致和价值适切,后者能够在政策的推动下自然融入一体化建设体系。然而,乡村文化的现实挣扎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很可能不是操作层面的失误,而是根植于一体化与文化传承意涵深处的逻辑悖论。
(一)整体思维与一元思维的系统差异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整合城乡教育资源,将处于分隔状态的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融合统整为一个教育共同体,将城乡教育视为整体进行统筹发展的目标模式。[7]城乡教育一体化既非农村教育城镇化/城市化,也非乡村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以整体思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速度、规模和质量,构建统合的稳定系统。这种整体思维选择宏大视角,将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放入同一范畴,采用“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模式,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乡村文化是基于历史、地理、资源、生产方式等特色而生长出的区域文化。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个地区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刺绣、蜡染、编织、山歌、舞蹈等民间艺术都是某一地区或村落所独有的文化遗产。“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范式反映了乡村文化的一元思维,它只会依据本土文化的逻辑和视角保持生命力,文化资源仅在自成体系的文化圈内流动。所以,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特征,以特定场域为边界,面向已获文化资质的特定人群的有限文化继替模式。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整体思维属于技术逻辑,乡村文化传承的一元思维则属于观念逻辑。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都可以进行“整体化”的技术处理,唯独文化难以如是。乡村文化是在长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经验文化,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可说性”。所以,乡村文化的意蕴是无法进行技术化处理的,反之,强行的技术设计势必消弭最本真的乡土韵味。而且,乡村文化传承的区域生成逻辑也不适应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整体思维,两者的价值理念和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当乡村文化传承同意被一体化系统所接纳,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历代坚守的身份。
(二)开放性与保守性的特性殊途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教育双向沟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区域开放系统。它打破了城乡相互区隔的教育结构,在开放的动态系统中探索城乡教育融合的机制。所以,城乡教育一体化是资源整合型的结构式开放,包括城乡教育之间的内部开放和城乡教育共同体的外部开放。前者指城乡教育面向彼此的全景式敞开,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教育质量获得全面均衡的发展。后者指城乡教育作为统一的教育系统,以主动、多元、创新的姿态参与外部世界互动,保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对话,建立不同教育共同体之间跨区域和跨国别合作。
从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功能分析,文化为了保持自身的原生样态和核心价值,需要在积极意义上维持自我的保守性。保守性在本体论上是文化的核心属性,在价值论上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必要条件。乡村文化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劳动关系中形成的独特价值观及其表征方式。“熟人社会”中的交往关系和“靠天吃饭,赖地穿衣”的劳动关系孕育了追求“安稳”的生存哲学,“差序格局”和敬畏土地都说明了乡村文化深层次的保守性。乡村区域圈定的文化传承边界使乡村文化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稳定性,因为文化往往只在特定的区域形成、流转和认可。可见,乡村文化并非不愿走出乡土,而是不能离开根脉,“离根”预示着文化失去了原初的精魂。
在此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开放性与乡村文化传承的保守性在“变与不变”中就产生了冲突。变是开放的逻辑,不变是保守的态度,时代的变化已经使乡村文化无从选择自己的立场。当乡村文化向外部世界敞开,它的核心价值和传承方式会受观念、制度、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改变。城乡教育一体化解构了乡村文化自我保护的机制以及文化传承的既定规则,而且它使乡村文化沿着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承续下去,这种生长又会同时作用于相同的群体,继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身份的困惑(我要去哪)或自卑(我要离开)。
(三)文化改造与自然承续的方法分歧
城乡教育一体化文化建设是依循从分散到整合、从“落后”到“先进”的价值路向的文化改造。理论上,文化改造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向调适,两者共同向一体化聚合,达成文化在教育上的融合。然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立场却非交互的,而是基于城市文化改造乡村文化的单向立场,其蕴含着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的价值预设。当然,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的改造是必然的。文化的价值良莠不齐,呈现形式异彩纷呈,运行方式也与教育截然不同,所以乡村文化无法直接进入教育场域。它需要在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尊重教育规律,通过筛选和修整的方式,进行科学化、系统化和可操作性的改造。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文化传承是在生命成长的整全环境中经验的自然承续。融于生活的自然承续是文化传承的原初方式,也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核心途径。它具有两类特征:生活生成和“因信称义”。生活生成是自然承续的方法论解释,乡村文化是在春耕秋收、迎来送往的乡土生活中自然生成的。“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的教育方式说明了乡村文化传承的耗散性和碎片化。“因信称义”是自然承续的价值论规范,“信”是乡村文化的认同,“义”是文化传承的行为正义。只有乡民对文化身份自信,才能导出文化传承行为的自然发生。
文化改造和自然承续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一者是基于城市立场的外部改造,一者是基于乡村立场的内部承续。如果用文化改造的逻辑代替自然承续,势必会破坏乡村文化传承的原有生态。他者改造是程序化的技术处理,往往会忽略文化内在的历史、规律和细节,丢失乡村最珍贵的“精气神”。梁漱溟认为,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浸入,一种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殖民。这样的教育塑造可谓对乡村内在活力的侵蚀。[11]反之,如果乡村文化继续坚持自然承续,固步自封的观念会剥夺乡民“看世界”的机会,也会消弱文化的生命力。在“改”与“不改”的张力中产生的纠节最终只会作用于乡村,城市一直都是处于既得利益位置的“旁观者”。
(四)制度建设与观念建设的建设思路不同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制度建设,[12]是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1]城乡教育二元分化的结构主要是由制度差异和制度壁垒造成的,只有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可见,制度建设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制度建设是一种政府行为,具有计划性、强制性、稳定性和指标化的特点,政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意味着,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政策的酝酿、颁布和实施的过程。此外,制度建设是城乡教育一体化框架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之后的具体行为则遵循政策指导下的自我运行逻辑,受政策下行方式、执行主体、操作规程等因素的影响。
乡村文化的传承即文化建设,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思想及其外化,所以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观念建设。它是一种态度的培养和认知的塑造,通常基于两种特性(长期性和偶然性)和两类中介(教育和环境)展开。文化观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观念建设也是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渐渐完成的。而且,形塑文化观的不是系统的知识,而是散布于乡村生活中的种种偶然因素,例如历史、故事、述说、体验等等。这一意义上,观念建设又具有间接性和生成性,它是通过教育和环境的中介,以及乡土世界的真实栖居,影响乡民对待文化的态度以及文化知识的获得。
制度建设与观念建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建设材料和建设视角两个方面。从前者分析,城乡教育一体化依据政府制定的政策,乡村文化传承则赖于乡民的态度。但是,乡民的态度无法撼动政策的推行,政策的制订往往又无视乡民的态度。双方的对峙又非“势均力敌”,乡村文化一定会在“经济利益”的裹挟和多方“合谋”下成为牺牲品,这也是“乡村荒漠化”产生的原因。从后者分析,制度建设从宏观层面专注城乡教育的结构调整,观念建设则从微观层面关心乡民在乡土生活中的文化态度。制度建设难以深入具体的文化生活,观念建设也无法影响顶层的政策调整。这也导致了宏观视角下乡土文化被视为阻碍发展的顽疾,微观视角下制度规划忽视民声和民生。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共生理念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文化传承是民族精神延续的原初根脉,两者的逻辑冲突势必会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弘扬乡村文明,遏制乡村教育衰败;[13]乡村文化传承的意义是保持文化活力,培养能够面向未来的乡民。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存在某种价值契合,基于这一共识的阐释、生发和建构将成为化解两者逻辑悖论的可能。此外,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逻辑悖论始于系统结构、本质属性、运行方式和建设思路的整体性差异,所以两者的冲突无法从本质上彻底解除,浮于形式的功能调和既无持续的远见,也无深层的功效。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搁置差异与冲突,引导两者在不同的逻辑路向上寻求价值共识,立足长期可持续的教育发展,使阶段性冲突走向整体性融合。这一共生理念即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自觉。
教育现代化是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14]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5]文化环境影响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进程,教育现代化则致力培养具有“文化自知之明”的“现代人”,所以教育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即文化现代化。甚至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也是没有意义的。”[15]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自觉是从教育与文化内部自然生长出的时代精神,鼓励教育扎根本土和服务本土,利用区域文化特色和发展规律,培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现代公民。它主要表现在乡村文化自觉和乡村群体现代化两个方面。
(一)乡村文化自觉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关键是“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以及在社会大变动和大发展中,基于文化转型寻求生路。[16]我们也可以改变下陈寅恪的表述“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一方面不忘本来乡土之地位”。因为文化是流动和扩大的、变化和创新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同时强调维持和创新。所以,“文化自觉”既非“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是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17]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都是文化自觉的“自知之明”。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正确处理文化交流、文化融通、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和问题的意识状态、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18]它要求教育传承乡村文化,守住乡土根脉;尊重乡村文化的主体性,树立乡土自信;赋予乡村文化新的内涵,保持乡土竞争力。这是一个在不断对话中寻求认同的过程,是在维持与创新的张力中探索出路的努力。教育形塑的乡村文化自觉是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既能扎根具有历史意蕴的土地,又能通达具有时代精神的世界。“土地”与“世界”正是两种意识、价值和精神的表征。所以,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积极学习的共生关系。教育也不再竭力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而是为双方提供可以对话的平台,引导其构建协和的文化生态。乡村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面向传统的乡土文化传承与面向未来的乡风文明改造是基于自觉与发展的现代化思维,超越“变与不变”“改造与承续”的二元冲突,同步制度建设与观念建设,尊重乡村文化自由权而获具自适应性的时代使命。
此外,文化自觉的主体是拥有这种文化的人,而不是文化本体。[18]乡村文化自觉的落脚点是人的自觉,这也是实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它致力于使乡民在了解本土文化脉络与认同区域文化身份的基础上,形成以“真善美”为标准的文化理解力、判断力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生命力。因为自觉本身即人们的自我意识高度成熟,能够对自己的存在、各种责任担当、处置各种关系的问题的能力状况,以及对自己精神成熟度的高度认同的状况。[18]所以,乡民的文化自觉是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心理状态,包括对乡村文化历史的自觉识认和对乡村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乡村教育是培养乡民文化自觉最重要的途径,一方面建立乡民与乡村文化的历史关系,引导其熟悉文化成长的完整脉络,另一方面建立乡民与乡村文化的情感关系,唤醒其对滋养祖祖辈辈乡土的“深沉热爱”。由此可见,文化自觉又非停留于认识论上的文化感知,而是嵌入价值论的情感认同,即文化自觉之上的文化自信。一种基于理性认识之上的精神成熟度表现,既非自卑,也非自大,而是一种文化上知己知彼的高度自觉。[18]简而言之,乡民能够呐喊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
(二)乡村群体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们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9]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现代性发生、发展的现实活动,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知识结构、行为方式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14]在此意义上,乡村群体现代化是指向未来美丽乡村的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改造。谢岳和曹开雄指出:“人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问题。”[20]人是由文化形塑而成,人的现代化即文化现代化的表征。人又是文化的承续者,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依靠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教育的宏大目的本质上是在探索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培养何种意义上的现代人,塑造何种意义上的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乡村群体的现代化就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建立起了同一性,而后者又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之一,如此一来,共生理念的两类内涵也形成了互为推证的逻辑关系。
因此,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文化人”的培养。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转变人的意向性结构,即在深层次上重构人的价值秩序。[21]乡民的现代性价值内核即立足本土立场,具有开放视野,成为自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顶天立地”的人。“顶天”是未来指向的后喻思维,能够与外部世界自由对话,适应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向世界和未来不断敞开的过程中保持自信和学习力。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创新”能力,持续赋予乡村文化和文化主体新的生命,提升其在时间(未来)和空间(世界)向度的竞争力。“立地”是历史指向的前喻思维,在扎根与发展的逻辑下成长为有文化修养的现代人,“维持”“我曾经是谁”和“我现在是谁”的价值统一,建立主体与文化之间的“知情”关系。所以,了解乡土根脉成为乡民最核心的竞争资本,这也是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遗失的珍贵品质,例如历史、人情、生态、沉思等等。
乡村群体的现代化是面向整个乡村世界的现代化改造,乡民能意识到身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张力之间的责任,并且能在其中张弛有度、游刃有余。乡村群体的现代化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态度,并最终表现为主体的文化观念。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正是走向乡村群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知情意行等方面将乡民培养成具有现代化素养的“文化人”。脚下土地的历史、经验、情感、智慧等需要教育去传承,参与外部世界和未来社会决策和改造的话语、能力、责任等需要教育去培养。乡村文化和群体现代化的逻辑前提是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的乡村现代化生态,而后者又以民主性和公平性、终身性和全时空性、生产性和社会性、个性性和创造性等为特征。[22]
由此可见,“文化自觉”和“现代化”最终都作用和指向于人,并在教育中形成内在统一,即“顶天立地的文化人”的形塑。前者偏向心理维度的身份构建和内省,后者强调发展维度的能力获得与敞开。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在此建立了共同作为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指归。需要补充的是,义务教育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重心,但“一体化”绝非局限于此,它是以义务教育为基,统合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生态。因此,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自觉是一种系统思维,而且具有较强的未来指向性。
四、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共生策略
如何创造一种既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又根基于中国文化特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之真正问题所在。[15]教育现代化文化自觉的共生理念是价值层面的应然预设,其仍然需要在乡村教育的实然土壤落地生根。从共生理念到共生策略实质上是乡村教育文化自觉的现代化设计,是化解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困境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论证。
(一)利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重塑乡民的文化观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的是人的培养,乡村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人的责任,所以共生策略的关键在于乡民赋予文化的态度、理解和判断,即乡民的文化观。在乡村振兴的转型阶段,乡民文化观的形塑将经历极大的挑战,它需要克服外部文化、生产方式变革、人口流动、数字化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干扰,而教育是突破这一困境的最佳路径。
转变落后文化观,重塑新型文化观,必须利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首先,突显教学区域特色,引导乡民了解本土文化。乡村教育应积极创建具有本土优势的教学环境,充分利用地方性教学资源,增加乡土知识的教学融入,创新教学方式的地域风格,帮助乡民系统地走近、理解和体悟乡村文化。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和难以言说性,教育应重视对生活常识和故事的挖掘,引导乡民与乡土文化的“相遇”(encounters),在日常“叙事”(narratives)中达成文化形塑。当前,乡村学校已经开始了相关探索和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教学成果奖”中频繁出现的乡村学校身影可见一斑。其次,利用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理念,培养乡民文化认同。将乡村文化放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视野,引导乡民感受不同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尊重区域间文化差异,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指引下培养乡土文化主体意识。多元文化对乡土世界的长期旁观,一方面说明乡村文化身份未获觉识,另一方面也揭示一元逻辑对乡村改造的“统筹”支配。所以,多元文化教育不仅是对乡村文化地位和发展逻辑的修正或补偿,更提供一种重构教育价值的全新思路。最后,推动乡村教育对外开放,鼓励乡民进行文化改造。乡村教育应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关系,保证乡民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服务,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拓展乡民的文化视野,培养文化创新精神与能力。落后、保守、封建、贫瘠等标签被贴在乡村文化身上的很大原因在于乡村的封闭性,而只有努力通过教育以及让教育走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重塑文化形象,四川、江西、江苏等地乡村小学的声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
(二)构建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区隔—合作”机制
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关系是横亘在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之间最核心的问题。城乡教育一体化致力建立相互融合的关系,乡村文化传承则坚持彼此的区隔发展。化解冲突的关键是找到更为合理的关系运行机制,消除两者在城乡教育关系上的分歧。“区隔—合作”机制是建立在双方对“关系需求”共同满足基础上的最优方案,要求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保持独立的运行逻辑,在相互区隔的系统结构中,建立平等互惠共享的合作关系。
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是两种相互区别的教育系统,而且这种差异性会持续存在。任何盲目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机械逻辑都是对现实与教育规律的违背。在即定环境下,乡村教育不需要“你送我一所学校”,更希望“我有自己的学校”。它能结合本土文化,发挥教育智慧,利用乡村资源,建立区域教育特色,培养学生在未来可以自由迁移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乡民成为在不同文化间自由流动的人。诚然,我们希望破除二元结构,但要建立二元思维,在尊重差异和利用差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乡村教育要探索出能够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区隔道路。尽管国家教育方针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规格不变,但是乡村教育在“殊途同归”的逻辑下依然能够寻找结构化的区隔点,核心在于其构建思路是“自我的”,而非“他者的”。从教学目标(阶段性)、内容、方法、手段、模式等方面祛除“看齐”或“模仿”思维,在不断的回身中寻找“差异”和“特色”。简而言之,城市有引以为傲的“城市学校”,乡村也要有为之自豪的“乡村学校”。
此外,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合作的难点又非采用何种视角与立场,而是教育公平的实现。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教育资源明显优于乡村,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鼓励城乡教育合作,通过教学理念、教学资源、师资等方面的优势共享,共同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例如远程教学、教师轮岗等。这里的抓手主要在于利用政策推动和现实驱动,促进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面对城乡资源配置不均无法短期解决的局面,乡村学校在深挖本土资源的同时,还应积极寻求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等基金或项目,而非被动地等待资助。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对特色教育的宣传,合理利用“晕轮效应”,扩大社会影响,寻求资源补偿。
(三)探索乡村教育文化自觉阶段化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阶段化发展模式,包括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五个步骤。[23]它遵循在体制框架内稳步发展的规律。乡村文化传承是代际间文化继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旨在保证本土根脉一代代源远流长。它遵行在观念层面上长远发展的规律。乡村教育文化自觉在两者的共生过程中自然要恪守共同的发展规律。
一方面,遵循稳步发展的规律,探索乡村教育文化自觉的阶段化发展模式。乡村教育文化自觉应当立足社会和教育现实,结合文化特征和属性,走科学稳健的渐进式发展道路。根据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和文化传承的要求,乡村教育文化自觉可以划分为政策推动的文化写入阶段、环境催动的文化合作阶段和需求驱动的文化自觉阶段。第一阶段,完善乡村教育政策,要求将乡村文化融入教学活动。文化写入是政策的强制推动,通常包括目标设计、内容编排、任务执行等方面。然而,政策的落地效果主要取决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实施效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受操作影响较大,很容易产生价值偏差。我们当前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二阶段,加强乡村教育与其他(非)教育系统的合作,积极满足环境变化的需求。合作的初衷是资源互补和互惠,所以它是乡村教育向外部系统寻求对话或者被问寻的过程,其本质上是二元或多元思维的表征。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逻辑起点即着眼于此。第三阶段,激活乡村教育的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乡村社会文化传承的自动化。在乡村、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真正实现现代化之时,整全意义的文化自觉才真正可以实现,它是在理解、内化和继替过程中的完全自动化。尽管如此,文化自觉的理念依然可以在前两个阶段发挥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遵行长远发展的规律,探索乡村教育文化自觉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乡村教育文化自觉是在长期的教育生活中生成,并服务于教育与文化长远发展的使命。教育和文化传承都具有长期性,乡村教育文化自觉的培养也不能一蹴而就,应保持与教育和社会现代化同步,在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逐步转身中耐心调整与适应。文化自觉是一种能力、意识、价值和境界,它是在乡土的栖居中伴随着主体性的增强而显现的。所以,它要求人在教育世界与乡土文明持续对话,在一次次的“相遇”、述说和沉思中,渐渐形塑主体的能力、意识、价值和境界。此外,当前社会习惯以改革的逻辑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然而,冷静之于改革的意义要远远高于热情,因为理性才是发展的洞见,教育尤其需要这份冷静。乡村教育的文化自觉不能追求断崖式的功利改革,应着眼于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未来,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城乡教育一体化与乡村文化传承的共生、共融和共荣。
[1] 褚宏启. 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J]. 教育研究, 2009(11): 3-10, 26.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 10-27)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2018-02-05) http://www.moa.gov.cn/ztzl/ yhwj2018/zxgz/201802/t20180205_6136444.htm.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
[5] 霍尔,尼兹,周晓虹. 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 徐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5, 20.
[6]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18 -09-26)http://www.gov.cn/xinwen/2018- 09/ 26/ content_5325534.htm.
[7] 李玲,宋乃庆,龚春燕,等. 城乡教育一体化: 理论、指标与测算[J]. 教育研究, 2012(2): 41-48.
[8] 魏峰. 城乡教育一体化: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 2010(5): 20-24.
[9]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5.
[10]王乐. 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学校的使命[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6(6): 26-32.
[1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672.
[12]杨卫安,邬志辉. 城乡教育一体化: 范围、实质与研究路径[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4): 5-9.
[13]邬志辉. 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探讨[J]. 教育发展研究,2012(17): 8-13.
[14]褚宏启. 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与评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现代化[J]. 教育研究, 2013(11): 4- 10.
[15]高伟. 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基于文化现代化的视角[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 33-140.
[16]费孝通. 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 文史哲, 2003(3): 15-16.
[17]费孝通.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 思想战线, 2004, 30(2): 1-6.
[18]邱柏生. 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需要对待的若干问题[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1): 14-19.
[19]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86.
[20]谢岳,曹开雄. 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改革开放 30 年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15-22.
[21]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16.
[22]顾明远. 试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J]. 教育研究, 2012(9): 4-10.
[23]周加来. 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概念辨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1(5): 40-44.
Dilemma and Resol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WANG Le, MA Xiao-fang
(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approach towar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serves 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realistic struggle of rural culture reveals the logical dilemma arising from the systematic difference between overall thinking and unitary view, openness and conservatism,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al inherit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resolve these dilemmas,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steps can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symbiotic concept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seek value consensus on different logical paths. The symbiotic strategy is an operational design to resolve the logical paradox through using modernized educational concepts to reshape the cultural views of rural residents, constructing the “jurisdiction-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phase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education .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ural cultur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auto-psyche
G40-02
A
1008-0627(2021)01-0019-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西部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的生存压力与教育支持研究”(17SZYB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振兴乡村战略中的农村教育现代化研究”(VHA180004);2019年留基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王乐(1984-),男,安徽宿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多元文化教育和教育基本理论。E-mail:leowang@snnu.edu.cn
(责任编辑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