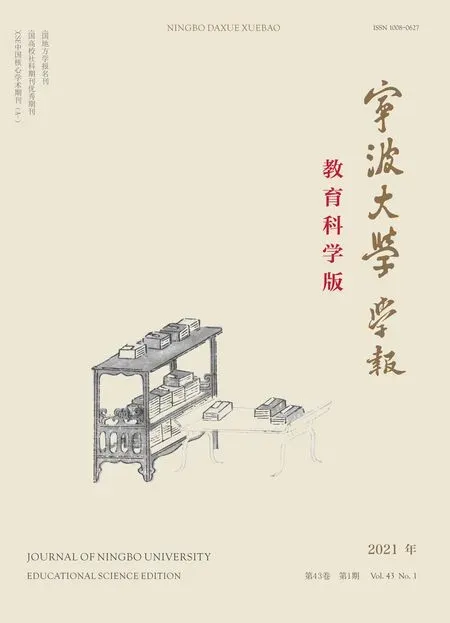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
2021-12-23赵国权周洪宇
赵国权,周洪宇
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
赵国权1,周洪宇2
(1.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在古代,“庙”为主祀孔子的重阵,“学”为育才重地,“庙”与“学”结合后形成中国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现象,二者的结合体被称之为“庙学”,亦即各级各类官学的代称。用历史、文献和比较法,从概念、学科、史学三个维度来研究庙学,旨在阐释庙学作为践行儒学的特殊物质载体,既是一种历史、政治、文化符号,更具有普遍的教化价值,一部庙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学校史。基于庙学的史料积累以及庙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社会支持和现实需求,需要建构一门新的学问“庙学学”和专门研究领域“庙学史”,通过从历史、教育、政治、经济、哲学、建筑、文物、民俗、伦理、艺术、宗教、图书等多学科角度,对其学科属性及学科理论进行深度挖掘,以此来传承和弘扬中国的庙学文化。
孔子;庙学;庙学学;庙学史
在人类轴心时代,中国的“庙”作为礼制性建筑已有定制,或称“名堂”,或称“太庙”,设庙目的主要在于祭祀先祖先贤,以缅怀他们的恩德、遵循他们的教诲、传承他们的基业,甚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依据礼制,从天子到士皆可建庙,故孔子卒后,“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1]1945,此便是历史上第一座主祀孔子的庙宇,称之为“孔庙”,明清以后多以“文庙”称之。自两汉以后,伴随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主祀孔子的庙宇与官学及宋元以后的部分书院渐渐融为一体,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也形成颇具特色的“庙学合一”景观,我们称此类礼制性建筑为“庙学”,也有称之为“学庙”的。且自有庙学以来,如同书院、贡院、祠堂一样,成为各个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文化及教育的“活化石”,以致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学问”即“庙学学”,有必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庙学史”,以此来推动庙学研究,让中国的庙学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庙学文化。
一、庙学:政教一体的物化形式
在史书及后世研究文献中,庙学多与文庙、学庙等混用。通常每一概念的出现都有一定的背景和语境,概念又恰恰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2]4。“庙学”作为“庙学学”的核心学术用语,必须有一个明确而又准确的界定,且有别于文庙、学庙等与“学”有关的概念时,才能合理地进行“庙学学”及“庙学史”体系的建构。
有说“庙学”一语最早出自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其中所谓“惟此庙学,邺侯所作”[3]491-492。事实上,唐之前已有“庙学”的说法。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二十二中,考证河南淮阳郡一方《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时,曾写道“时人不复寻其碑证,云孔子庙学,非也”[4]535。北魏司空、清河王元怿上表要“修明堂辟雍”,召臣僚商议,国子博士封轨议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国之阳……至如庙学之嫌……。”[5]766卫尉卿贾思伯则依据蔡邕所言“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而称之为“蔡子庙学之议”[6]1615。虽然唐之前学者笔下的“庙”即“明堂”,但有“庙学合一”的涵义。而韩愈所谓的“庙学”,实际上也是“庙”与“学”的结合体,他撰文时没有以“处州庙学碑”为题,而是直书《处州孔子庙碑》,在叙述修建过程“既新作孔子庙……又为置讲堂”后,才有“惟此庙学”一语。从表述上看应该是对前人之见的借鉴,所不同的是,韩愈笔下的“庙”确为主祀孔子的庙宇,在唐朝“庙学合一”是普遍认同的客观存在。
“庙学”在表述上之所以“庙”先“学”后,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庙设学、庙中有学问题,而是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孰轻孰重的问题。在佛教本土化及道教勃兴后,佛寺、道观遍布天下,致使儒学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于是,在兴学重教、弘扬儒学的同时,儒学的物质载体、士人的精神家园孔子庙也被统治者纳入到学校建设的议事日程,因此唐宋以后要求有庙必有学、有学必设庙,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和治国之策。或者说“庙学”中的“庙”,就是“儒”的代称,而儒学又是历代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哲学,教育历来又是从属于政治的,因而“庙学”的话语表达更具有政治学意义,同时也是“政教一体”的存在形式,或是对“庙”与“学”合一现象的真切描述。
除外,就字义上来说,“庙”是来限定“学”的,既有别于佛教的“寺学”和道教的“道学”,更有别于那些没有庙宇性建筑的书院、私学、族学、义学、家学等教育机构,但落脚点在“学”而不在“庙”。这样,“庙学”就是对各级官学及部分书院的通称,研究庙学既要研究“庙”更要研究“学”。如果说绝大部分孔庙属于“学庙”的话,那么古代的官学及部分书院和私学都可称之为“庙学”,这样,一部“庙学史”就近乎一部“中国学校史”。
正是基于对“庙学合一”的政治及教育文化的认同,元之后的史书多使用“庙学”这一术语来描述“庙”与“学”的结合体即地方官学。如《元史》载:“成宗即位,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7]1901《元史•忽辛传》亦载,忽辛就任云南行省右丞后,“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8]3069。
后世学者同样因袭前说,从教育史角度上积极从事“庙学”研究,普遍将中央国子学、太学及地方府州县学称之为庙学。如《中国教育通史》在谈到金元之际的庙学时,认为广义的庙学“是指各级各类的儒学”[9]296。日本学者牧野修二等在探讨元朝庙学时,认为“庙学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10]。而在台湾学者高明士看来,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由“学”到“庙学”发展的历史[11]46。他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共有五章内容,其中四章都是在讨论“庙学”问题,内容分别是:第一章“从‘学’到‘庙学’的教育”,第二章“‘庙学’教育制度的普遍化”,第三章“书院的‘庙学’化”,第五章“庙学制的崩溃与近代学制的建立”,之外的第四章讲的是“师生关系”,可以说是庙学研究的代表之作。
二、庙学学与庙学史:教育史领域的专门学问
目前学术界对与孔子庙有关的学理性探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提出要建立“孔庙学”,将“孔庙学”界定为是“以祭祀孔子的庙宇及相关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并视之为一门新的学科,而非“专学”。[12]二是提出要建立“文庙学”,即“以文庙及与文庙相关的教育文化设施、制度、理论和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13]。而对于“庙学”,台湾学者高明士只是大致梳理了庙学发展的历史,至今学界尚未提出要建构“庙学学”问题。对此,我们从教育史的角度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专学”即“庙学学”。那么何谓“庙学学”,其与庙学史、教育史有何内在联系等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新兴的专学“庙学学”
所谓“庙学学”,是指以庙学及与庙学相关教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者说“庙学学”如同书院学、科举学一样是一门新兴的“专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学术界对“学科”的界定是非常严格和明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范围与边界,有自己的代表性人物与成果”[14]。对于尚不具备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基本条件的“庙学学”来说,自然不能称之为一门完全意义上的“学科”,也许若干年后,当“庙学学”具备一门新兴学科的条件时,则可以从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角度进行“庙学学”学科再建构。
就目前来说,将“庙学学”称之为一门专学或“学问”则是合理的。因为“学”有学问和学科双重含义,“学问是完全开放的,它是一种研究领域,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进入研究领域,开展研究,取得成果。而学科则带有一定的专有性与封闭性,有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独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独有的研究范围与边界”[14]。方泽强等提出,凡是称之为“专学”的,需要具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等四个条件,相对于“学科”而言,“专学更侧重于知识维度的探究,它为研究兴趣而追求学术,而并不刻意追求社会建制”[15]。鉴于“专学”也是目前学术界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诸如相继兴起的四书学、朱子学、阳明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一系列“专学”,那么也完全可以将“庙学学”定位在一门“专学”或“学问”,既符合教育史研究的价值导向与追求,又能避开“学科”这一极易引起歧义的字眼。
(二)庙学学与庙学史
“庙学学”与“庙学史”都以庙学为研究对象,都是教育史的专门研究领域,与庙学文化能在新的时代得以“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所不同的是,“庙学学”所研究的是庙学自身所承载的教育文化及其功能,需要以知识为轴,从历史、教育、政治、经济、哲学、建筑、文物、民俗、伦理、艺术、宗教、图书、生态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借以探明庙学的价值取向及运行机制,为现存庙学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理论指导。而“庙学史”则是以时间为轴,来探讨庙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专门学问,以便“古为今用”。
“庙学学”与“庙学史”之间,无疑是一种既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庙学史”是“庙学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庙学学”成为一门专学的主要标志,或者说没有系统深入的庙学史研究,“庙学学”很难成长或成熟为一门专学。而“庙学学”既是以庙学史研究为基础的一种理论再生,反过来又能拓展庙学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并为庙学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引领。
(三)庙学史与教育史
按照学科分类,“教育史”是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庙学史”则只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或专门研究领域,因此二者不是同位概念,“教育史”居上位,“庙学史”居下位,教育史研究包括“庙学史”研究,“庙学史”归属于“教育史”。
就研究内容来说,“教育史”是研究自古及今教育活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过程,借以探寻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中学校制度及教学活动是教育史研究的重点,包括学校政策、各级学校设置、行政管理、教学活动、课程与教材、教师任用、招生考核及就业等,设庙祭祀只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一个“点”,在学术研究上重“学”而不重“庙”。而“庙学史”则是研究学与祭、学与庙相融合的历史,包括庙学之建筑布局、祭祀礼仪、诗词碑刻,以及学校如何利用孔子庙这一祭祀空间来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庙又如何借助学校来充分彰显自身的教化功能等。
目前,“庙学史”研究不为内地学术界所关注,在多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中也只是在讨论辽金元时期的官学教育制度时才提到“金元之际的庙学”,多卷本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没有专列条目来讨论庙学问题,在诸多版本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中“庙学”还多是一个盲点。台湾学者高明士对“庙学史”研究多有建树,虽然在其《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中主要探讨“庙学”问题,但“官学”或“书院”因素比较突出,书名亦冠之以“教育制度史论”而非“庙学史论”。这也为“庙学史”研究创造一个难得的机会和空间。
三、庙学学与庙学史建构的多元基础
依据“专学”资质,“庙学学”“庙学史”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成为一门专学的多元基础,包括史料积累、学术成果、社会支持及现实需求等。
(一)史料基础:丰厚的庙学史料积累
“庙学学”及“庙学史”研究属于教育史学范畴,必须有足够的庙学史料才能支撑起这一门“专学”。事实上,自两汉“独尊儒术”后,庙学便在全国各地得以建置和开展一系列的祭拜及教育教学活动,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庙学资料的原始积累,见于正史所载的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之后问世的《汉书》《晋书》《魏书》《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的帝王传记、礼制、学校、选举、祠祀部分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大唐开元礼》《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清通礼》等仪制类史书,以及《通典》《唐会要》《宋会要》《明会典》《大清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等通制类史书,都含有丰富的庙学祀典、释奠资料。宋以后纂修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等地方志中,对庙学设置、修葺、迁建等,包括各种碑文、诗词、舆图等,几乎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历代学者的文集中,同样保存有大量的与庙学相关的记文、碑文、祭文、诗词等。如:唐朝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中载有《处州孔子庙碑》;宋朝黄裳的《演山集》中载有《安肃军建学记》《重修澶州学记》,朱熹的《晦庵集》中载有《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白鹿洞成告先圣文》;《全辽金文》中载有赵秉文的《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党怀英的《棣州重修庙学碑》、王去非的《博州重修庙学碑》等。这些庙学史料虽然散在于各种史书之中,但以其原始和不可替代性,以及融入诸多文人学者的思考,都是支撑“庙学学”“庙学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二)研究基础:明清以降丰硕的学术成果
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开始对庙学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汇编。如:《明史•艺文志》中载有潘峦的《文庙乐编》、瞿九思的《孔庙礼乐考》、黄居中的《文庙礼乐志》、何栋如的《文庙雅乐考》;《清史稿•艺文志》中载有阎若璩的《孔庙从祀末议》、蓝锡瑞的《醴陵县文庙丁祭谱》、庞锺璐的《文庙祀典考》、郎廷极的《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等学术成果。其他史料还载有清朝陈锦的《文庙从祀位次考》、金之植的《文庙礼乐考》、张偀的《文庙贤儒功德录》、牛树梅的《文庙通考》,民国孙树义的《文庙续通考》等。这些早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庙学沿革、建筑、祭祀、从祀、礼乐制度等作了系统考辨,为后世“庙学学”“庙学史”研究积累了详实的史料。
在新中国初期的“破四旧”及后来的“批孔”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庙学遗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对庙学的研究和保护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也为庙学研究带来新的春天。自1987年版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列出一目专门探讨“金元之际的庙学”后,学术界开始关注庙学研究,截至1999年发表不少相关的学术论文,如牧野修二的《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1988年)、高明士的《庙学教育制度在朝鲜地区的发展——中国文化圈存在的历史见证》(1995年)、范小平的《中国孔庙在儒学传播中的历史地位》(1998年)等。期间的代表作,当推台湾学者高明士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论》(1999年)。他在“自序”中指出,民国以来因受日本和西方教育史研究取向的影响,学术界只重视“学”的研究,而忽略“庙”的研究,事实上“一部中国教育史,本来是‘学祭’合一的教育史,也就是‘学庙’合一的历史”,因此他在书中专以探讨“庙学”问题。
2000年以后,庙学研究成果倍增,除发表诸多相关学术论文外,还呈现出四大亮点:
一是出版多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如:范小平的《中国孔庙》(2004年),陈传平主编的《世界孔庙》(2004年),刘亚伟的《远去的历史场景:祀孔大典与孔庙》(2009年),孔祥林的《世界孔子庙研究》(2011年),彭蓉的《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2011年),董喜宁的《孔庙祭祀研究》(2014年)、朱鸿林的《孔庙从祀与乡约》(2015年)、刘绪兵与房伟的《文庙释典礼仪研究》(2017年)等等,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美学等多角度多维度地对孔庙及庙学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
二是重视庙学史料及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如:耿素丽、陈其泰编撰的《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2012年),收录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庙研究资料21种,编为14册。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成一农编著的《古今图书集成庙学资料汇编》和《地方志庙学资料汇编》(2016年),这是他在整理《古今图书集成》中“中国古代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积累起来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古今图书集成庙学资料汇编》收录当时京畿、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个总部179个府(州)下属各级官学或儒学、庙学设置的基本沿革情况,既是庙学资料汇编,也是地方官学资料汇编。《地方志庙学资料汇编》是对489种地方志所载的庙学史料加以汇编而成。
三是有一批硕博生开始围绕文庙或庙学来做学位论文,如:柳雯博士的《中国文庙文化遗产价值及利用研究》(2008年),田增志博士的《文化传承中的教育空间与教育仪式—中国庙学教育之文化阐释与概念拓展》(2010年),董喜宁博士的《孔庙祭祀研究》(2011年),田志馥博士的《宋代福建庙学的历史地理学分析》(2013年)等。
四是开始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探究文庙问题,如:刘振佳的《孔庙学刍议》(2010年),周洪宇、赵国权的《文庙学: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2016年)等,分别提出要建立“孔庙学”和“文庙学”。虽然有关文庙或庙学研究成果丰厚,但至今尚未有学者提出“庙学学”这一学术性概念,更没有《庙学学导论》《庙学史》之类的学术性著作出现,因而建构“庙学学”、探究“庙学史”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诉求。
(三)社会基础:文保、社团及媒体各界的普遍关注
社会支持也是衡量“庙学学”能否成为一门专学的重要因素,来自社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重视对庙学遗存的保护,现存的近300所庙学遗址基本上都是国家、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二是1995年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多次举办学术会议,聚集一支规模较大的研究队伍。除外,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及多个省市县所成立的孔子学会或孔子研究会,对庙学的研究也给与较多的关注。三是各地得以恢复的文庙或庙学,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不断开展“祭孔”“孔庙学术研讨会”“孔子文化节”以及“开笔礼”“入学礼”“拜师礼”“成人礼”等活动。四是出版媒体的关注,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签约出版文庙研究、文庙专题研究丛书;河南大学、宁波大学等部分大学学报以专栏、笔谈的形式发表文庙、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等。
(四)现实基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庙学学”“庙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庙学研究与复兴中诸多难题的必然诉求。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愈加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更基于对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而提出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五四”青年节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将《大学》中的八个条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由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6]。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弘扬儒家文化便成为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并进行长远规划和战略部署。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那么,庙学作为儒学传播的主阵地及重要的教育文化遗产,对其研究、保护和利用也自然被推向学术前沿,我们提出要“以祭祀活动打造民众的精神守望地”“以传承国学来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地”“以所奉祀人物来打造人生坐标地”“以人生节点打造生命体验地”[17],旨在使庙学资源在新时代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利用。
但在现实中,庙学遗存的保护和利用还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有的庙学或文庙遗存没有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及有关规定加以修复和保护,任其自毁自灭;部分得到修复的文庙,未能发挥其公众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存在过于功利化倾向;部分文庙设施及祭祀活动不合礼制;还有一些文庙打着国学的名义而出现办班乱象等。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诸如祭祀时间应在生日还是卒日?公祭孔子时其他配享者如何受祀?在尊重已往配享制度的前提下是否可以续增一些新儒学代表人物以及在文庙内如何举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及儒学传播方面的活动等。
总之,无论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还是解决庙学遗存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需要从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以庙学理论来引领庙学的保护和利用,以充分发挥庙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助推作用。
四、庙学学与庙学史体系建构的初步设想
“庙学学”与“庙学史”作为一门“专学”既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需,那么其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庙学学与庙学史体系建构
“庙学学”与“庙学史”在体系建构上,要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8]532因而,在庙学“专学”建构上,既要客观再现庙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又要科学揭示庙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既要施与真实的历史叙述,又要坚持深度的逻辑分析;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庙学作为儒学的物质载体和特殊的教育现象,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还波及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因此既要以全球视野做宏观把握和研究,将庙学置于世界文化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才能对庙学文化予以准确定位与合理解读,还要坚守中国立场,避免用西方文化中心论来决断中国的庙学文化,以此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同时,又要对不同地区庙学之间的个别差异做具体的分析与比较,以再现各地的庙学文化特色;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庙学不单是学科发展的诉求,也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考虑,因此既要有“问题引领”,不断地从文本、实物及图像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将庙学研究推向深入,又要坚持“实践导向”,紧紧围绕着国家政策及社会需求,针对庙学遗存保护和资源利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同时借鉴兰克、斯宾格勒、汤因比、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勒高夫和勒韦尔等学者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采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献法、历史法和比较法等一般研究方法,以及图像、计量、叙事、考察、个案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从历史、教育、政治、经济、哲学、建筑、文物、民俗、伦理、艺术、宗教、图书、生态等多个角度或维度,全面系统而又立体地探讨和展现庙学的历史与文化。
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并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庙学研究才会充满活力和生命力,也才能构建起科学系统的“庙学学”“庙学史”理论。
(二)庙学学的体系建构重在“学”
“庙学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涉及到它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问题。
1.“庙学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属性决定着一门“专学”研究的学科倾向或着力点,“庙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专学”,虽然需要多个学科介入研究,但就庙学所承载的基本功能而言,可以将“庙学学”界定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专学”。
2.“庙学学”的研究对象。庙学既是儒学的物质载体,又是“庙学学”的核心概念,自然也是“庙学学”的研究对象。换句话来说,“庙学学”就是研究庙学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专学”,在实际研究中既重“学”又重“庙”。
3.“庙学学”的研究内容。庙学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所承载的文化及功能也是非常丰富的,因而所要研究的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庙学的沿革及现状。研究“庙学学”,首先要对庙学有一个清晰、合理的认识,故需要对庙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和系统梳理,对庙学的现状进行准确把握和描述。
二是庙学与政治。高明士认为,“在中国,因为教育一直依附在皇权之下发展,所以教育虽然力求自主性,终究不脱其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11]53。因而庙学承载着传播儒学的政治使命,两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不重学修庙,各级地方官员也无不以兴修庙学为己任,竭力使之成为“弘扬王道的政治场所”[19],因此要探讨庙学与政治认同、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
三是庙学与经济。庙学一般都有稳定的田产及政府拨款为常年办理经费,需要大修时还会面向社会多方筹措经费,因此需要探讨庙学田产来源、经营方式、费用走向以及经费对庙学发展的影响或制约等。
四是庙学与建筑。庙学是一种屋化的礼制性建筑,其选址迁址、建筑布局、建筑空间、建筑礼制以及建筑物自身的石雕、砖雕、木雕、漆雕、绘画等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生态文化、美学尤其是教化等元素,故有学者称,从建筑学和建筑现象学角度解读庙学建筑空间,解构庙学建筑的教化旨趣和教育意蕴,乃是庙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20]
五是庙学与祭祀。儒教非宗教却人人都要接受洗礼,庙学非宗教活动场所却具备宗教活动的形式,孔子非神却像神一样被祭拜,学子非教徒却有着教徒般的虔诚,最终促成士人及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信仰,因此需要探讨庙学的配享制度、祭祀礼仪与学人文化信仰、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
六是庙学与教化。庙学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如清代学者庞锺璐在《文庙祀典考》中所言:“夫欲敦教化、厚人伦、美风俗,必自学校始。学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贤先儒,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21]9可见,在“学”是文本化的儒教,在“庙”是具象化的儒教,需要研究“学”与“庙”是如何“合一”又是如何相互促进的,对学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如何发生影响的,以及如何对民众实施伦理、风俗教化等问题。
七是庙学与科举。庙学是培养人材的,科举是选拔人材的,在“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观念影响下,庙学与科举之间便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庙学都建有“棂星门”“泮池”或“状元桥”,有的庙学会被当做“考棚”,有的庙学傍边还有魁星阁、文昌阁等设施,考生考前考后总会到庙学内拜谒先圣先师或魁星,中榜后还会在庙学内“金榜题名”,并刻碑以名垂青史等。因此需要研究庙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以及庙学与科举文化传承、庙学与区域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规律。
八是庙学与书院。自宋朝书院演变为授徒讲学的教育机构,从而与官学、私学一起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学校的三大支柱,且有部分书院仿照官学庙制,建有主祀孔子的庙宇或殿堂,这部分书院也具备庙学的意蕴,因此需要探讨书院祭祀与儒学、书院文化传承问题。
九是庙学与藏书。大凡庙学都有“藏书阁”或“藏经楼”等设施,以珍藏儒家先贤先儒的书籍,对藏书的来源、书籍的利用以及藏书、刻书活动对学校教学和古籍保存的促动等问题需要做系统研究。
十是庙学与艺术。庙学内处处充斥着美的元素,如建筑风格与院落布局艺术,木雕、砖雕等各种雕塑艺术,碑刻、匾额、楹联中的书法艺术,彩绘、壁画以及祭祀活动中的音乐、舞蹈、服饰艺术等,每一种艺术又都充满着政治色彩和伦理说教,因此要研究这些艺术作品的伦理教化内涵,对学子审美及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等。
十一是庙学与寺观。儒教下的庙学与佛教下的寺学、道教下的道学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质的不同,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以分析归纳,探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借以凸显庙学的文化特质。
十二是庙学与儒学文化圈。自两汉以后,儒学开始影响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即儒学文化圈。伴随中国庙学制度的定型和发展,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开始复制庙学制,如现存韩国的成均馆、越南河内文庙及日本汤岛圣堂等,都是典型的“庙学合一”建筑。因此需要研究庙学如何被复制、对当地华裔民族心理的维系以及海外儒学文化传承带来怎样的影响等。
十三是庙学与现时代。庙学既是一种历史符号,其文化遗存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在举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针对庙学遗存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深挖并充分利用庙学遗存所隐藏的文化资源,使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国学教育与普及中继续发挥其强大的教育和文化传承作用。诚然,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更新,“庙学学”体系还会进一步拓展完善。
(三)庙学史的体系建构重在“史”
“庙学史”如同“庙学学”一样,都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是,“庙学学”侧重于“学”的建构,“庙学史”则侧重于“史”的建构。
1.“庙学史”的学科属性。根据上述对“庙学”“庙学史”的界定,那么“庙学史”的学科属性便一目了然,毫无疑问它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即要用教育学的知识对“庙学”这一特殊的教育文化载体进行史学分析和研究的一门“学问”。
2.“庙学史”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庙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庙学发生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庙学沿革、演变的历史轨迹来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旨在丰富和充实教育史学科内容,展现多彩多姿的教育历史文化,并为庙学文化的延续和功能发挥提供史学依据。
3.“庙学史”的研究内容。教育史研究几乎都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划分历史阶段的,虽然通过大历史可以窥测到小历史,但小历史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鉴于“庙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具体而又有针对性,因此有必要按照庙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梳理庙学史的研究架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庙学前史。从夏商周三代“学”中出现祭祀行为到汉初“庙学合一”之前。据《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这里的“先圣先师”绝非孔子,但所制已为后世“庙学合一”提供了制度依据。在高明士看来,“若不拘泥于‘庙’的硬体建筑的出现,而以其祭祀礼仪活动作考量的时候,亦即学祭教育的施行,则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11]53。故“前史”需要研究庙学问世之前的学祭制度及演变、第一座庙祀孔子建筑的创建与发展、汉初文庙设置及日常管理等,这一切都成为庙学问世的历史铺垫与实践。
第二,庙学合一史。自汉初文翁在蜀郡兴学设置“礼殿”主祀周公、孔子等先圣先贤,学与庙“合一”初现端倪,至清末新学制建立时庙学分离为止。这一阶段时间跨度大,王朝更替多次,统治者的庙学政策也多有变化,且也是庙学真正合一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繁荣期,因此按朝代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一是两汉为庙学制初创期,汉初统治者的尊孔崇儒政策,引起各阶层对“立学祀孔”问题的普遍关注。蜀郡太守文翁兴学时,在郡学所建“礼殿”内既有周公等圣贤画像,也供奉有孔子及其弟子等儒家人物,且岁时祭祀,可认为是“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最早范本”“左庙右学”的雏型。[22]到东汉永平二年(95年)“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23]3108,表明庙学初步建制。
二是魏晋南北朝为庙学制形成期。期间虽政局动荡不安,但在继续推崇儒学的情况下开始“依庙立学”和“因学设庙”的尝试。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曹丕曾“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24]78,此举开依庙立学的先河。宋太元九年(384年),宋武帝刘骏建国子学,“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25]365。另据《建康实录》载,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26]277,足见为“左学右庙”建制,此举可谓国学立庙主祀孔子之始。至北齐文宣帝时,“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以祀,[27]181是为地方上明确因学设庙祀孔之始。
三是唐朝为庙学制度化期。为“重振儒术”,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玄宗接连推出立学设庙的重要举措。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自此周公、孔子单独立庙奉祀。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令“天下学皆立周公、孔子庙”。贞观二年(628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28]470自此天下庙学主祀孔子,遂成定制。贞观四年(630年)又诏州县“皆特立孔子庙,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唐玄宗时,加封孔子为“文宣王”,享受最高祭祀礼遇,其弟子也被封为公、侯、伯等,庙学也开始被称之为“文庙”。
四是宋元时庙学制被普遍认同。两宋的“重文”之举及宋初的三次兴学,使得各级官学以及书院获得快速发展,也就意味着庙学的大发展。辽金元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国家治理上“尊用汉法”,因而辽、金朝建庙设学成为常态。元朝更是如此,“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29]。
五是明清之际庙学“遍天于下”。明清之际虽然政治上走向专制,孔子不再称“王”而改称“先师”,但儒学依然是官方哲学,统治者对立学设庙仍不遗余力,以致“庙学遍于天下,百余年来,文教大兴”[30]。清朝入关后,建国子监文庙,升孔子之祭为大祭,与祭天地、太庙、社稷同礼,至清末各地庙学多达1560多处,且多以“文庙”相称。
第三,庙学后史。自清末学庙分离到改革开放后庙学遗存普遍被保护前,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为一个时期,期间因发展新式学校,导致庙学分离、学退庙存,庙学虽然完成了它的学校教化使命,但其遗存在学子及民众心目中的位置依然不可替代,继续发挥其大众教化的功能。且国民政府提倡“四维八德”,定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庙学遗存继续得到保护和利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一个时期,期间因多次发生政治运动,庙学遗存被毁严重,得以幸存的庙学多因其建筑移作它用之故。
第四,庙学新史。自改革开放至今,庙学遗存迎来新的时代,其保护和利用被普遍关注,多被列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对庙学遗存的规模、维修、保护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对新时代庙学如何发展及其资源如何利用进行思考和展望。与此同时,对周边国家庙学遗存情况予以充分关注,为中外庙学之间的互通互动和交流架起一座桥梁。
总之,庙学作为儒学及教育文化的物质载体,如同书院、贡院一样,不仅在中国文化及教育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发生过重要影响,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研究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一门新兴学问“庙学学”恰逢其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庙学史”势在必行。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庙学学”一定会成为21世纪儒学研究中的一门“专学”或“显学”,“庙学史”也会成为教育史研究中的一门特色“学问”。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945.
[2] 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M]. 吴勇,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4.
[3]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91-492.
[4] 郦道元. 水经注校证[M]. 陈桥驿,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35.
[5] 魏收. 魏书: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66.
[6] 魏收. 魏书: 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15.
[7] 宋濂等. 元史: 第6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901.
[8] 宋濂等. 元史: 第10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069.
[9] 毛礼锐, 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 第3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296.
[10]牧野修二, 赵刚.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J].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88 (4):74-79.
[11]高明士. 中国教育制度史论[M]. 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9.
[12]刘振佳. 孔庙学刍议[J]. 济宁学院学报, 2010(4): 11-15.
[13]周洪宇, 赵国权. 文庙学: 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J]. 江汉论坛, 2016 (5): 94-103.
[14]周洪宇. 建立陶行知学[J]. 生活教育, 2013(9): 10-13.
[15]方泽强, 张继明. 科举学的学科与专学辨析[J]. 江苏高教, 2012 (4): 29-31.
[16]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 人民日报, 2014-05-05(02).
[17]赵国权, 周洪宇. 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对文庙再定位的几点思考[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5): 119-125.
[18]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532.
[19]广少奎. 斯文在兹, 教化之要——论文庙的历史沿革、功能梳辨及复兴之思[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5) : 126-131.
[20]邓凌雁. 空间与教化: 文庙空间现象及其教育意蕴的生成[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5) :132-139.
[21]耿素丽, 陈其泰. 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 第8册[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9.
[22]舒大刚, 任利荣. 庙学合一: 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5): 21-29.
[23]范晔. 后汉书: 第1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108.
[24]陈寿. 三国志: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78.
[25]沈约. 宋书: 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65.
[26]许嵩. 建康实录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77.
[27]魏征. 隋书: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81.
[28]吴兢. 贞观政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70.
[29]虞集. 道园学古录 卷36•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M]. 浙江巡抚采进本.
[30]王樵. 方麓集卷6•镇江府重修学记[M]. 两淮马裕家藏本.
The Subject Attribute and Construction of Studies, Schooling and History of Confucian Temples
ZHAO Guo-quan1, ZHOU Hong-yu2
(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In ancient times, a multitude of temples were built a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to worship Confucius and academies were set up for learning to educate tal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emples and academies developed a unique unity of temples and academ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t was called temple academies, a sign of official learning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Us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omparison,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nfucian templ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ncept, discipline and history to explain the special material carriers of Confucianism teachings of Confucian temples as academies, a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 as well as a universal educational value. A history of Confucian temples-based academies is almost a history of Chinese schools.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uitful literature, soci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new branch of Confucian Temple Studies and a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Temple-based Academie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and theories of Confucian temple studies is nee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education, politics, economy, philosophy, architecture, cultural relics, folk custom, ethics, art, religion, books and other disciplines, so as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temple culture.
Confucius; Confucian temple academies; disciplines of Confucius temple studies; history of Confucian temple academies
G529
A
1008-0627(2021)01-0001-11
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南历代文庙史料整理与研究”(2018BLS005)
赵国权(1961-),男,河南荥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E-mail: 553069451@qq.com
(责任编辑 赵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