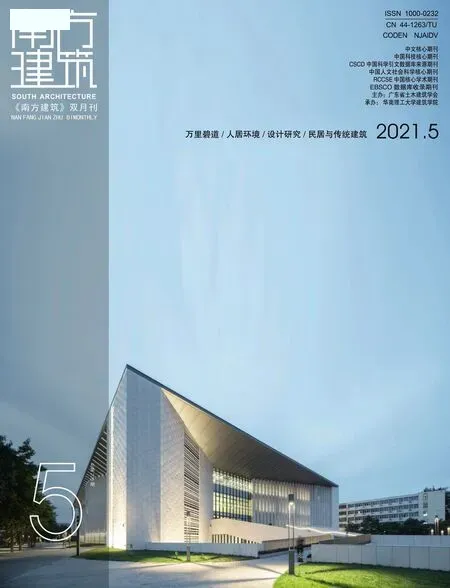岭南大学校园轴线空间的演变及文化建构研究*
2021-12-17黄雯雯林广思
黄雯雯,林广思,任 静
19世纪末20 世纪初,近代大学的兴起将西方高等教育和校园建设模式传入我国,校园空间多以轴线控制其内部结构秩序和生长方向,具体形式包括单轴、并列轴,以及“十”字、“中”字和“井”字型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轴[1]。其中,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是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运用美国布扎式规划设计手法,以宽阔宏伟的纪念性轴线和对称规整式布局手法组织各建筑群[2]。校园发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十”字轴线空间格局。
2015年12 月,中山大学广州校区规划修改方案正式公示并征询意见,是否迁建南校区的岭南堂等问题成为争议焦点[3]。岭南堂是由莫伯治院士设计,在1994 年6 月建成于校园南北轴线中央[4]。提出迁建的一方认为其选址破坏了中轴的历史风貌[3]。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近代大学校园在改建和扩建中常面临新旧建筑、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冲突等问题。
我国近现代大学因文化渊源上的异质性总是处于政治改造、文化冲突和教育理念融合的中心[5],其校园形态演变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关于大学校园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多将轴线作为整体中的关键元素纳入系统研究,而针对校园轴线的案例研究较少。例如,陈晓恬总结不同时期“轴”的演变特征包括象征性、礼仪性、双向延展性等,指出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是校园形态表征的恒定元素[1]。魏皓严和郑曦等认为中轴计是源于国家/权力意志的古老计策,造成我国大学校园中轴线泛滥的思想来源是美国、前苏联和本土传统的国家意志[6]。前者侧重不同历史阶段中复杂的社会进程对大学校园空间形态的影响,后者侧重社会关系中不同利益群体在大学校园空间博弈中的作用,并都以岭南大学校园为例浅析其空间形制,但如何诠释和展示校园轴线空间的多元价值仍未可知。
因此,笔者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审视岭南大学轴线空间的文化建构,以轴线空间格局的演变为主线,通过档案研究、情境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在《岭南大学校园规划溯源(1904—1938)》基础上,分2 个阶段研究岭南大学校园轴线空间的形成、保护与发展,分析轴线空间的形式、功能及其文化建构的特征和动因,探讨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人文内涵和社会价值取向变迁。以期加深对校园轴线与整体空间关系的理解,完善对校园轴线空间的多元价值认知,并为今后我国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提供历史借鉴。
1 校园轴线的形成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于1888 年成立的格致书院,自成立后名称多次更改1),于1904 年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村建立永久校址,亦称“康乐园”。岭南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教派或教会联合组织[7]。岭南大学曾有过两次校园规划方案,分别来自1904 年前斯道顿事务所(Stoughton & Stoughton Architects)和1918 年詹姆斯·埃德蒙斯(Jas. R. Edmunds Jr.)。1938 年前,校园建筑布局和南北轴线基本按照詹姆斯·埃德蒙斯的规划方案实施完成,东西轴线尚未完成[2]。
1.1 单轴线空间格局
至1938 年前,校园南北轴线以开阔的草坪作为空间基底,以直线和对角线道路分割草坪,两侧建筑均衡布置。轴线中央设有一系列建筑和构筑物,从南到北依次为怀士堂、圆形广场(惺亭)、气象站、喷水池、水塔、游泳池等(图1),颇具法国古典园林构图之美。
轴线上的构筑物兼具美化校园和实用功能,以满足师生观赏游憩、教学科研等需求。例如,轴线最北端的游泳池类似法国古典园林中水景的设置,在1918 年前就已建成供全校师生使用。菲文气象观测站(Freeman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的造型更像是雕塑,用于获取相关气象资料进行农业研究试验[8],1930 年代迁建于惺亭和喷水池之间,既有科学实用的功能,也起到点缀作用(图1)。
由于种种原因,校园实际建设并未完全按照规划方案进行。轴线中央的喷水池、水塔和水泵房,以及轴线南部的蚕丝学院都是规划之外的。1932 年,学校建设了一系列供全校师生生活用水的设施,喷水池、水塔和水泵房点缀在开阔的草坪中央,成为校园中一大亮点(图1)。轴线南部是蚕丝学系(图1),周边是农场和竹园。农场及相关设施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南北轴线格局,是因为规划之初未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农业教育的迫切需求。

图11938年岭南大学校园南北轴线景观分析图
中轴开阔的草坪绿地是岭南大学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图2),其建植来源于西方的造园传统,并在近代广泛应用于我国城市公园和大学校园中[9]。在学校领域,草坪建植观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大学校园中[10],比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内的草坪庭院。至今,西方大学校园内的部分庭院仍采用以四边建筑围合中心草坪的布局形式。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则开创了以大草坪为中心,两侧建筑沿纵长轴线对称布置的新模式,并影响此后美国、欧洲、苏联等地区的校园规划及景观营造。其中,在我国最为出名的是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于1915 年所做的清华校园规划方案,在大礼堂前设计开敞的草坪绿地[11]。

图2 岭南学校校园内草坪绿地(1915年)
1.2 从基督教到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
岭南大学校园是典型的布扎式规划在校园中的运用,遵循纪念性组织原则,利用尺度巨大的南北轴线将不同风格的建筑统一起来[2]。轴线上的建筑和构筑物作为意识形态和校园文化的载体,被用于物化时任决策者对纪念性的设想,并通过环境育人的功能达到某种教化目的。以1927 年学校收归主权为分界点,岭南大学校园轴线的文化建构在基督教和民族主义两种势力之间抗衡。
怀士堂是于1916 年建成的基督教青年会会馆,用于举办各类基督教传教活动,位于中轴的核心位置,承载着传播文化宗教的重要作用(图1)。这种建设模式在同时期的教会大学中颇为常见,将行政楼、礼拜堂置于校园主轴线上。例如1903 年东吴大学校园中心的行政楼“林堂”,1913年金陵大学规划总平面图中主轴终端的行政楼,金陵女子大学校园中心也是行政楼[1]。可见,西方高等教育和校园建设模式传入中国后,在时任政权控制下,位于校园中心的建筑自然以反应决策者意识形态为主。
从20 世纪20 年代起,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大冲击下,岭南大学于1927 年收归国人自办[7]。1928 年,学校在轴线中央的圆形广场上建设惺亭(又称钟亭、烈士钟亭)以纪念史坚如、区励周和许耀章三位烈士(图1)。这种措施既符合校园师生乃至广大人民的心意,也是教会顺应当时政治局势的妥协。这与当时使用人像雕塑纪念英雄和伟人的方式不同,选择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式亭子,是突破教会控制下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之举。
自此,风格迥异的两座建筑分别作为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园林文化的载体,首次在校园中轴汇集。至抗日战争前,在国内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10 年间,中国本土营建的大学校园进入黄金时期。以弘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为目的,取法自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型制成为当时校园建设的主流[1]。
2 校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
1938 年抗日战争爆发,校园建设停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的文、理等院系并入新中山大学,校园也改为新中山大学校址。新中山大学将校园的扩张与轴线的生长相结合,在原空间基础上延伸南北轴线、形成东西轴线,并在轴线两侧均衡建设新建筑,最终形成校园“十”字轴线空间格局。
2.1“十”字轴线空间格局
南北轴线上,学校保留了怀士堂、大草坪、惺亭和水景,拆除了南部的蚕丝学院及其周边农场,新建了国旗、孙中山铜像、岭南堂和北门的牌坊(图3)。新增的构筑更加注重纪念性和象征意义,在美化校园的同时也丰富了使用者游憩体验。
在轴线南部延伸段,道路两侧种植着高耸挺拔的白千层(Melaleuca leucadendron),不仅增强了轴线空间的围合感和纵深感,还与开阔的草坪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图4)。北门外,码头、校门牌坊和成排的鲜花,形成了气派的校园入口景观(图3)。

图3 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校园十字轴线景观分析图

图4 中山大学校园南北景观轴线(南部延伸段)
东西轴线在1938 年前并未实施完成,仅有南侧的格兰堂、马丁堂、科学馆和十友堂、东侧的八角亭以及中央的惺亭。学校在扩建中完善了东西轴线,在其西侧新建图书馆,北侧新建3 座建筑,并将乙丑进士牌坊迁移至在惺亭与八角亭之间(图3)。
如今校园的“十”字轴线空间格局,不仅成为校园景观之精华,也因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背景,成为校园历史和多元文化的展示空间。
2.2 延续历史文脉的文化建构
1952 年之后,学校通过轴线整合校园各时期文脉,尤其注重保护和延续校园的历史文化。在新增的构筑中,乙丑进士牌坊和孙中山像都与学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分别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近代民族民主主义的载体。
乙丑进士牌坊始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用于纪念明代进士为官清正廉明,曾位于广州四牌楼地区(今解放中路一段)。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曾在1898 年于四牌楼福音堂内重启运作。1947年,岭南大学考虑到该牌坊见证了创校历史,将牌坊置于校园内格兰堂西侧,也可用于激励学生努力上进[13]。文革时期牌坊遭到毁坏,后经校友捐资修复,最终于1999 年被移至校园东西轴线的惺亭和八角亭之间。
孙中山铜像是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经历多次搬迁,最终在孙中山诞辰90 周年时(1956年11月12 日)迎置于校园南北轴线中央,以示瞻仰纪念[12]。如今的孙中山铜像已成为校园文化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寄托。
此外,北门外的码头是岭南大学时期校园与外界联系的重要入口。随着与外界交通联系越来越便捷,码头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如今,学校保留并改造码头,不仅为珠江游览观光之便,也为再现岭南大学时期的码头景观。
2.3 历史校园整体保护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和社会思潮传入我国,人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和高扬,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14]。新兴的建筑设计思潮成为校园建设的新动力,但也引起历史建筑保护和校园更新之间的冲突。岭南大学通过轴线空间拼贴融合不同时期的文化符号,在弘扬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以及变革创新等方面都有所建设。
1994 年6 月,岭南堂建成于校园南北轴线中央,其选址和建筑设计都是一次革新之举,在协调新旧建筑风貌、组织空间秩序和延续历史文脉上面临巨大的挑战。
岭南堂作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兼具展览、学术交流、瞻仰先贤功烈等实用和纪念功能。该建筑采用良诸文化玉器体型,造型外方内圆,是莫伯治院士运用古典秩序强化建筑涵义表达的又一尝试。其风格、体量与周边建筑迥异,却巧妙运用绿色玻璃外墙的通透感弱化了大体量的压迫感[4]。对于校园整体空间而言,岭南堂的存在改变了以怀士堂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和线性视觉通廊,形成了“南校门—逸仙路—怀士堂—草坪—中山像—惺亭—岭南堂—水景—北校门—牌坊”的中轴新景观,营造出富有纪念性和历史文化气息的空间序列。
21 世纪初,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引起公众对历史校园和历史建筑保护的广泛关注。“康乐园早期建筑群”在2002 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岭南大学舍建筑群(马丁堂、格兰堂)、岭南大学附中建筑群、马岗顶洋教授建筑、模范村中国教授住宅群、孙中山铜像、七进士牌坊。
但在2015年12月,迁建岭南堂事件引起诸多争议[3]。鉴于这个已经成为事实的大师级作品,本身体量也不是很大很张扬。最终在2016 年4 月,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公布实施《中山大学南校区、北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规定保留岭南堂,保护中山大学南校区“十”字轴线的空间格局,新建建筑不得影响中轴线视廊以及视廊背景的通透性[15]。是否迁建岭南堂的争议最终平息。公众参与的形式将管理者、使用者和校园组织联系起来,历史校园保护也由历史建筑单体转向校园整体环境和历史风貌。
结语
历经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岭南大学校园最终形成“十”字轴线空间格局,以轴线有效统筹校园的空间结构、功能分区和空间秩序。轴线空间兼具观赏游憩、科研教育等实用价值,亦是校园文化建构的主要载体。轴线上的象征性构筑物被用于物化决策者对纪念性的设想,标志着时代变迁的印记。师生们在使用中感知轴线空间的物质建设和文化氛围,促使校园空间成为历史记忆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大学的轴线空间在规划之初就被赋予纪念性,如何言说纪念取决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学校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的异质性是价值观冲突的客观前提,在校园物质建设中体现为代表不同文化的建筑与景观营造。同时,受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社会思潮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校园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从岭大校园轴线空间的演变中可管窥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社会价值取向变迁。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社会价值取向可分为2 个阶段。1949年前,因社会政治动荡和中央政权疲软,西方大学校园建设模式和教会文化传入我国。随着中华民族民主主义的觉醒,大学校园建设取法自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以对抗西方教会文化的入侵。建国后,以改革开放为重要节点,校园建设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新兴的建筑设计思潮,并以延续校园历史文脉、保护校园历史风貌作为大学校园建设的新价值取向。
笔者通过分析岭南大学校园轴线空间的演变及其文化建构的特征和动因,以管窥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社会价值取向变迁。一方面可以加深对校园轴线与整体空间关系的理解,完善对校园轴线空间的多元价值认知,大学校园规划常用轴线统筹空间结构、功能分区和空间秩序,并通过景观节点的营造赋予轴线使用、体验和象征意义。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公众参与、整体设计、延续历史文脉是我国校园建设和管理的新趋势。营造功能复合、文化多元的校园环境以及注重校园整体风貌是新建大学和历史校园保护的重要内容。
图片来源
图1、图3:作者绘制。
图2:耶鲁大学电子图书馆。
图4:作者拍摄。
注释
1)该校的中文名称沿革是:1888—1900 年,格致书院;1900—1912 年,岭南学堂;1912—1918 年,岭南学校;1918—1927 年,岭南大学;1927—1952 年,私立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