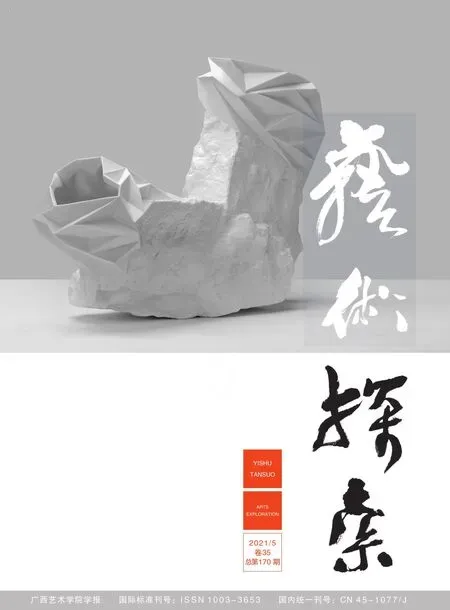连续与变迁:12 至16 世纪的英格兰皇家礼拜堂及其音乐
2021-12-16葛佳嘉
葛佳嘉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西方艺术音乐发展初期,宗教音乐理论及其实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世纪以来,宗教音乐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教堂、隐修院以及学院中的相关培训、教士和唱诗班团体。文艺复兴时期,礼拜堂(chapel)与圣乐学校(maitrise)成为促进音乐发展的重要机构。①chapel,英语,原意为小教堂、小礼拜堂;maitrise,法语,原意技巧、师傅、唱经班。在《基督宗教音乐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中,作者陈小鲁将以上二词分别译为“圣乐队”与“圣乐学校”。本文中的chapel 取“圣乐队”之义,但仍用“礼拜堂”的译法。礼拜堂不同于一般的唱诗班(choir/chorister),在早期具有多重含义;而在15 世纪往后的相关语境中,其指由教士—音乐家组成,作为无伴奏合唱团服务于权贵或教皇的音乐机构,其中的人员有时被统称为歌手,有时根据他们履行的神职或在唱诗班中演唱的声部来称呼。②详见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词条“Chapel”。历史上罗马天主教教皇的礼拜堂就是这类机构的典范,其吸引了来自法国与尼德兰地区的众多优秀音乐家。英格兰的皇家礼拜堂(the Chapel Royal)便是一个与此类似的独特机构。其产生于中世纪盛期,至都铎王朝晚期达到鼎盛,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音乐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且极具历史特色的作用。英国早期音乐史上最知名的一系列音乐家更是于其中诞生,如约翰·邓斯泰布尔(John Dunstable,1385—1453 年)、罗伯特·费尔法克斯(Robert Fayrfax,1464—1521 年)、托马斯·塔里斯(Thomas Tallis,1505—1585 年)、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540/43—1623 年)以及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1557/1558—1602 年)等,对英国早期音乐影响甚大。
关于英格兰皇家礼拜堂的研究,国外成果丰硕,早期有斯坦利·罗珀的综述性研究《1135 年至今的英格兰皇家礼拜堂音乐》,世纪之交有菲欧娜·凯斯比的专题研究《皇家礼拜堂研究:1485—1547 年》,以及乔治·鲍尔斯的论文《皇家礼拜堂、爱德华第一公祷书以及伊丽莎白一世的1559 年宗教和解政策》等。③E.Stanley Roper,"Music at the English Chapels Royal c.1135,Present Day",Proceedings of the Musical Association,54th Sess.(1927 -1928),pp.19-33;Fiona Kisby,"Officers and Office-Holding at the English Court:A Study of the Chapel Royal,1485-1547",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Research Chronicle,No.32 (1999),pp.1-61;Roger Bowers,"The Chapel Royal,the First Edwardian Prayer Book,and Elizabeth's Settlement of Religion,1559",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3,No.2 (Jun.,2000),pp.317-344.而国内相关成果甚少,鲜有专题研究。本文主要通过12 至16 世纪英格兰皇家礼拜堂的史料记载,来论述特定音乐机构的功能、作用及其音乐风格在历史发展中的连续与变迁,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抛砖引玉。
一、皇家礼拜堂的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据《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格兰皇家礼拜堂最初是指存在于英格兰皇室内的一个特殊机构,它的职责主要是为君主策划各种祭祀、宗教礼拜以及仪式庆典,并进行表演。此外,礼拜堂也可用其本意,指供放礼拜仪式所需的祷告书、礼服、圣物、容器等用具的处所。它独立于中世纪以来的各种教堂与学院合唱团,但偶尔也会根据需要短暂加入。④详见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词条“The Chapel Royal”。作为一个皇室附属机构,它没有固定处所,随君王四处走动,可以去到各个行宫、庄园、城堡甚至战场,如15 世纪初随亨利五世到法国,16 世纪中期随伊丽莎白一世到温莎城堡等。因此,“皇家礼拜堂”一词在此更多指英格兰皇室的一个下属机构,由成人与男童组成,而非通常意义中的宗教建筑。
作为专门的仪式音乐机构,英格兰皇家礼拜堂的历史记载多来自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记事簿》(Check Book),为当时的礼拜堂书记人员用以记录礼拜堂人员、器皿、事件以及酬劳等之用。⑤E.F.Rimbault ed.The old Cheque Book,or Book of Remembrance of the Chapel Royal,CamdenSociety,n.s.,iii,1872.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A.Wienandt,New York,1966.伊丽莎白一世之前的信息,则大多散见于皇室事务记录(household recorder)中。据目前皇家礼拜堂官方介绍,其成立于爱德华一世(1272—1307 年在位)与爱德华二世(1307—1327 年在位)期间,兴于都铎王朝,光荣革命(1688 年)后日衰,迄今仍作为一个辉煌的传统保留在英国的汉普顿宫、伦敦塔以及圣詹姆斯宫中。⑥http://www.chapelroyal.org.但音乐学家罗珀认为,礼拜堂早在亨利一世(1100—1135 年在位)与约翰王(1199—1216 年在位)时期便已现雏形并进行了演出。如相关国家财政红皮书(Red Book of the Exchequer)提到,在1135—1200 年间,教职人员在特定场合演唱了圣歌《基督得胜》(Christus Vincit)并接受了一定报酬;而在1227—1240 年间的日历卷轴(the calendar of the liberate roll)中,则有数条有关“国王礼拜堂”(the king's chapel)在约克、坎特伯雷等处进行表演的记录。[1]19-33由此可推断,在爱德华一世之前,对皇家礼拜堂一词的使用可能并不多见,但专门供职于皇室的音乐群体已实际存在,且有相关文献记录。它与其他唱诗班、合唱团分开建制,费用单独支出。
在礼拜堂成形之前,人们会挑选部分神职人员专门服务于皇室,其中一部分人会因文化修养提高而成为更高级的神职人员,主要在政治方面向统治者提供咨询建议并成为管理者。但同时作为司祭,他们仍需在君主需要的时候,挑选其中3—4人参与仪式庆典。久而久之,其中有歌唱天赋的人员被划入礼拜堂,作为在特定场合演出的人员。1318 年,礼拜堂初步成形,主要包括1 名首席神甫、5 名神甫、6 名世俗人员、3—4 名唱诗班成员,以及一些附属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机构规模的壮大,音乐技巧逐渐成为其人员招募的重要标准,礼拜堂也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世俗宗教唱诗团体。据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时期宫廷大臣的记录:在1547 年,礼拜堂共有49 名成员,除其他人员外,常规教职与唱诗班成人共计31 名,唱诗班男童12 名。[2]1-61因此,从人员构成及其变化可知,礼拜堂不属于纯粹的宗教机构,带有较强的世俗性;礼拜堂的职能由早期的以宗教礼仪服务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仪式庆典表演为主。
这种盛况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得到持续与发展,该时期也成为皇家礼拜堂规模最大、气势最盛的时期。查理一世(1625—1649 年在位)之后,皇家礼拜堂被短暂废除,但很快又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60—1668 年)重建。然自此以后,其规模逐年下降,至今维持在常年6 名成人、10 名孩童左右。
二、皇家礼拜堂的功能及历史作用
与一般教堂、隐修院以及学院唱诗班所具有的浓重宗教特性不同,皇家礼拜堂自成立之初起,服务于君主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功用上的双重性。
一方面,皇家礼拜堂是君主进行礼拜仪式及庆典的常规音乐机构,具有宗教服务功能。尤其是在其成立早期,无论日常还是节日或者某些重要事件中,礼拜堂的唱诗与祈祷行为都具有着明显的宗教性质。根据早期礼拜堂的唱诗班记录显示,在1226 年圣诞节期间,国王的唱诗班在约克演唱了圣歌《基督得胜》;而1200—1226 年间,随亨利五世去到法国的唱诗班在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期间,多次演唱了《基督得胜》以及其他赞美诗。[1]19-33同时,由于礼拜堂的皇室机构性质,其仪式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起着表率作用。16 世纪40 年代末,英格兰宗教改革在仪式音乐方面曾一度模糊不清,当时的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便于1548 年9 月分别致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副校长,让他们“不论礼拜堂还是教堂,在弥撒、庆典、早晚祷以及圣礼中的所说所唱,都需统一为皇家礼拜堂的现用模式,而无其他”[3]10-11。由此可见,皇家礼拜堂不仅以宗教仪式功能为基础,而且在某些特殊时期,它在宗教礼仪上的权威性甚至要高于各主教与学院教堂,成为一种示范机构。
另一方面,尽管通常情况下礼拜堂的表演以宗教作品为主,但同时它又体现出极强的世俗性。首先,它会采用一些世俗的方式博取君主欢心。例如在1490 年的圣诞节,当时的唱诗班教师劳伦斯·斯夸尔(Laurence Squire)将唱诗班孩童打扮成美人鱼的样子以取悦亨利七世,颇受欢迎;1501 年,在亨利八世与皇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礼上,皇家礼拜堂的孩童再次被打扮成美人鱼,并唱起“甜美和谐的歌”。[1]19-33其次,由于深受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君主为了展示他们的虔诚和财富,往往会大力扶持皇家礼拜堂,并在适当的时机对外炫耀,因此礼拜堂又是一种君主建立良好公共形象的优良媒介。1509 年9 月,当时的礼拜堂唱诗班教师威廉·科尼什(William Cornish)带领唱诗班孩童随亨利八世前往比利时的图尔纳,时人观其表演,不禁盛赞:“唱诗班吟唱的弥撒,其声神圣空灵,那低沉缭绕的乐音闻所未闻”[1]19-33。凭此,亨利八世不仅展现了其作为虔诚基督教徒以及优雅伟岸世俗君主的形象,还展示了英格兰雄厚的国力。在学者凯斯比看来,皇家礼拜堂的音乐与宗教庆典不仅以公共的方式将皇室生活的核心内容呈现给来访者,而且由于君主参与了游行与礼拜仪式,其也成为公众一睹君王风采的首选。[2]2如1536 年6 月,亨利八世和王后出席一个盛大庆典时,在奏乐中随列队一起走向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大弥撒。[4]249-250在这一过程中,皇室、礼拜堂与民众不仅共建了一种公共观礼体验,还共塑了君主形象。
此外,礼拜堂在一些特殊时期,还可以利用其特殊性,达到一定的政治外交目的。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初期,为了缓和前二十余年以来由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危机,信奉新教的女王将许多天主教的视觉与音乐元素保留在皇家礼拜堂内,并适时向来访者展示。例如,天主教国家西班牙的大使在1559 年参观完女王的皇家礼拜堂之后,写信给另一名主教说:“事实上,一个月前被公然焚毁的耶稣受难像以及法衣,现在就被供放在皇家礼拜堂中,不久之后,整个王国都遵循此例”[3]33-34。在这一情景中,礼拜堂具有文化外交的作用,暂时消解了当时某些在宗教立场上与英格兰对立的国家的敌意。
由此可见,虽然在成立之初,服务于宗教仪式是皇家礼拜堂成立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随着时间不断推进,人文与政治效用成为其主要功能。尤其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礼拜堂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一方面,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式君主,有着较高的人文修养,并对艺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君主们意识到文化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皇家礼拜堂,恰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远不像一个附属的边缘机构,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门”[2]2。也正因为服务于君主,在具有宗教礼仪属性的同时,皇家礼拜堂也产出了许多非宗教作品。尤其是在近代早期,世俗声乐与键盘乐成为英格兰皇家礼拜堂作曲家创作的主要对象,并促进了英格兰早期音乐的发展与繁荣。
三、皇家礼拜堂中的键盘学派
不同于通常意义下以宗教礼仪为主的教会唱诗班或学院礼拜堂,近代早期英格兰皇家礼拜堂在产出大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孕育出一个以世俗维吉娜琴演奏与创作为主的键盘学派,这一群体对当时欧洲大陆键盘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音乐学家艾兰·布朗曾说:“即便是最简明的西方音乐史,也逃不开对维吉娜琴音乐家的叙述,他们是兴盛于伊丽莎白一世晚期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一个英国键盘学派。”[5]22学派以皇家礼拜堂的音乐家威廉·伯德(William Byrd)为中心,同时还包括许多同时代的年轻音乐家,如约翰·布尔(John Bull)、奥兰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等。学派体现出明显以礼拜堂为中心的师徒传承关系,如伯德的老师是历经四代都铎君主,同为皇家礼拜堂成员的著名音乐家托马斯·塔里斯(Thomas Tallis),而伯德又是后生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约翰·芒迪(John Munday)、托马斯·汤普金斯(Thomas Tomkins)等人的老师或所追随的对象;除此之外,学派的其他重要作曲家如布尔、吉本斯、费迪南德·理查德森(Ferdinando Richardson)等人,都曾受训或供职于此。礼拜堂成为师徒之间、同事之间的纽带,加强了作曲家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这使得学派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人群,还体现在极具英格兰特色的作品风格与材料运用之上。
首先,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对小教堂、修道院的解散,以及激进改革派对教堂中管风琴的敌视与禁用,导致教会管风琴学派传承的断裂。这种颓势曾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有所改善,以维吉娜为主的键盘学派便是重要体现。⑦除此之外还有两次键盘乐的短期发展,分别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詹姆斯二世时期。详见Alexander Silbiger ed.Keyboard Music before 1700,Routledge,2004,pp.22-85.为新教教堂所禁止的管风琴音乐、赞美诗等体裁形式被许多音乐家,尤其是具有强烈天主教信仰的音乐家,改编至键盘乐作品中,并成为当时键盘乐作品的重要类别之一。例如英国所特有的《圣号经》(In nomine)便是由此而来。
器乐《圣号经》来自都铎王朝早期著名作曲家约翰·塔弗纳(John Taverner,约1495—1545 年)的弥撒代表作《圣三一荣耀经》(Gloria Tibi Trinitas)中的《降幅经》,取其歌词“以主之名”(In nomine)处出现的定旋律(谱例1)作为器乐作品的定旋律。塔弗纳是在英格兰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最后几年中,写作拉丁圣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将《降幅经》定旋律用于器乐创作的方法开创了英国作曲家写作《圣号经》的历史,直到现在,都有作曲家沿用这一方法进行创作。在16—17 世纪著名的手抄本《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中,《圣号经》(包括《圣三一荣耀经》)多次出现,如约翰·布尔的《圣号经》(谱例2)。

谱例2 约翰·布尔《圣号经》(《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第37 首)主题定旋律
其次,尽管从15 世纪末开始,老一辈的都铎王朝音乐家如休·阿斯顿(Hugn Hston)、托马斯·塔利斯等人都写有键盘乐作品,但直至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前,作曲家们仍以声乐作品为主。16 世纪中期以后,一个以皇家礼拜堂音乐家威廉·伯德为中心的键盘学派发展并短暂繁荣起来,约翰·布尔是他们之中维吉娜琴作品最多的一位。从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对音乐材料的运用上,可以看出几条明显的承继线索。
1.在帕凡舞曲(pavan)与加亚尔德舞曲(galiarda)的套曲创作上,作曲家们大多偏离了莫利所倡导的双人舞曲模式,而希望获得更丰满的表达。莫利在《音乐实践简明介绍》(1597 年)中写道:“帕凡舞曲是一种庄重而古板的音乐,一般有三段,每段都要演奏/演唱两次;一般每段为8、12 或16 小节,本人没见过比8 小节更短的帕凡舞曲段落……它一般后面接更加明亮与富有动力的加亚尔德舞曲,加亚尔德舞曲比帕凡舞曲更加活泼明亮。”[5]38然而只需稍微比较一下《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下册中托马斯·莫利(谱例3)的帕凡舞曲与威廉·伯德的同名作品(谱例4),不难发现,后者的音乐语言与表情要更加繁复。尤其是对重复段的大量装饰,成为伯德写作帕凡舞曲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与莫利认为的无需装饰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在段落与小节的处理上,伯德的方式要比莫利的更加灵活。

谱例3 莫利《帕凡舞曲》(《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第153 首)选段

谱例4 伯德《帕凡舞曲》(《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第254 首)选段
谱例4 并不算伯德键盘作品中复杂的段落,但仍可见他与莫利之间的差异,无论声部进行还是装饰音的使用方面,前者都要更加精致一些。伯德的这种创作方法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年轻人。纵观当时的键盘作品,帕凡与加亚尔德舞曲的套曲形式成为作曲家最常创作的体裁之一,而无论“大胆华丽的布尔、庄重沉静的吉本斯还是浪漫迷人的法纳比,都无一不受到威廉·伯德的影响”[5]47。
2.对同一种或相似音乐材料的使用,并进行不一样的处理和发展,是当时许多作曲家爱用的方法。如莫利与芒迪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变奏曲《从我的窗前走过》(Go from my window),唯一不同的是后者的作品共有八段变奏,比前者的多了一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年轻作曲家都倾向于对伯德的作品进行改编,在其基础上或模仿或创新,以期达到学习的目的。例如,《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中的作品《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分别有两个版本,其一为伯德所作(第68 首,谱例5),有22 段变奏。另一则为约翰·布尔所作(第1 首,谱例6),有30 段变奏。在对布尔版本的说明当中,富勒·梅特兰(J.A.Fuller Maitland)这样写道:“布尔的这一首变奏曲明显是伯德变奏的续篇。主题由伯德所创并用于22 个变奏当中,之后布尔在伯德的主题基础之上又创作了30 个变奏”。⑧J.A.Fuller Maitland and W.Barclay Squire,ed.,The Fitzwilliam Virginal Book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Dover Publications,1963.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主题的形态之中。

谱例5 伯德《沃尔辛厄姆》主题

谱例6 布尔《沃尔辛厄姆》主题
以《菲兹威廉维吉娜琴曲集》为例,类似的同名作品还有伯德与汤姆金斯的《好运》(Fortune),吉本斯与伯德的《荒凉的森林》(The Woods So Wild),伯德与布尔、汤姆金斯的《六音阶》(Ut re mi fa sol la)等。同时,伯德的后辈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特点。例如布尔与汤姆金斯创作了大量以素歌为基础的高修饰性作品,而吉本斯则发展出一种自由幻想曲,其节奏特征比伯德的作品更为统一。
与他们的老师不同,年轻一辈中有许多人常年或多次游历欧陆各国,并将他们的键盘乐作品与创作风格带到各地传播开来。如约翰·布尔于1582 年任职于赫尔福德大教堂;1585—1586 年任职于皇家礼拜堂;1591 年接任他的老师约翰·布里斯曼(John Blitheman)成为皇家礼拜堂的管风琴师;1601—1602年旅居欧洲大陆达18 个月,期间遇到了尼德兰的斯威克林(Sweelinck);1613 年再次离英;1617 年在安特卫普任教堂管风琴师,直至1628 年逝世。而彼得·菲利普斯(Peter Philips)则是位天主教徒,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跟随当时的贵族托马斯·佩吉特爵士(Lord Thomas Paget)游历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尼德兰等国家和地区,并将大多数作品(拉丁语经文歌与意大利牧歌)在安特卫普出版。这些年轻的音乐家成为当时连接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桥梁,极大促进了双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促进键盘学派与世俗音乐作品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近代早期器乐制作技术的进步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在贵族阶层的传播,而英格兰独特的新教氛围,又使得许多具有传统宗教情感的音乐家们努力将被圣乐限制的音乐情感和题材方式,移植到世俗声乐与器乐作品当中。在这一过程中,皇家礼拜堂的作曲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集中的音乐家与作品,新教形态与旧教思想并存,宗教作品与世俗作品共生,成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皇家礼拜堂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礼拜堂最明显的特征。
综上所述,皇家礼拜堂自成立之初起直至都铎王朝结束,逐渐成为英格兰统治阶层借音乐手段展示其宗教与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它产生于宗教礼仪,伴王权成长,因世俗目的而强盛,其中的音乐家与音乐活动勾勒出英格兰辉煌的近代早期音乐史。而皇家礼拜堂本身笼罩着一种强烈的悖论色彩:宗教目的与世俗目的的相对性与相容性。这种特性既保障了皇家礼拜堂在英格兰宗教动荡时期的正常发展,又使其推动了世俗音乐的发展。这一时期键盘学派的脱颖而出,不仅是皇家礼拜堂发展史,更是英国音乐发展史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