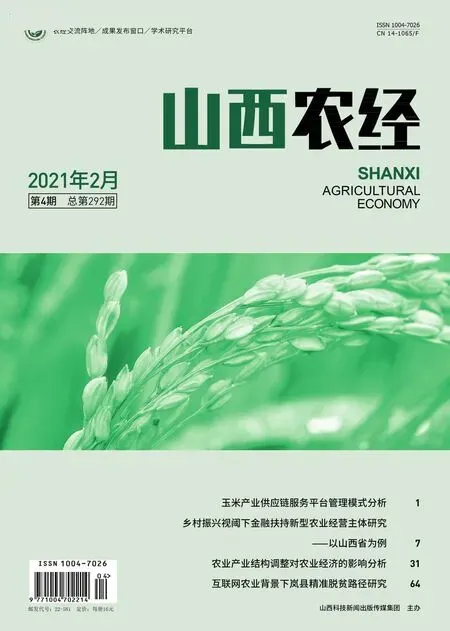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湘南地区文明乡风的构建
2021-12-15□于皓
□于 皓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00)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五位一体”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体系中,乡风文明的主要指标包括以下4 项。2020 年村综合性质文化服务中心的覆盖率要达到95%;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及乡镇的占比要达到50%;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中,专职任教教师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要达到65%;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及娱乐支出的占比要达到12.6%。相比较而言,村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村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提升、村民文化娱乐支出通过资源配置易于实现,但文明乡村的打造、良好乡序家风及民风的建设非一时之功。
乡风即乡土风俗,是人们在乡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形成的风尚、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等[1]。乡风是一个村庄精神风貌的核心,涵盖村民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在处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当前乡村普遍存在邻里关系冷漠、休闲生活低俗化、婚丧嫁娶奢侈化、家庭伦理道德弱化等问题,乡规民约对村民的约束力明显淡化。社会上往往从弘扬传统孝道构建文明乡风,对于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社会和乡村社会而言,孝道固然重要,但塑造文明乡风应从乡村的传统文化、先贤人物中挖掘乡风的“根”,以乡规民约形塑乡村道德,并通过文化下乡,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新思想、改变旧观念,让适应时代的新理念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力量。
1 保护特色村庄,挖掘乡风底蕴
村庄处于不同的区位、具有不同的发展现状及资源禀赋,便有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村庄特色。特色保护类村庄在湘南比较集中,例如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他们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建筑是一部史书、古村落是一所博物馆”,特色村庄作为凝聚传统建筑风格、浸润传统礼俗文化的象征,应努力保持其建筑的完整性、生态的真实性和文化的延续性。在村庄传统选址、建筑布局、村容风貌和自然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上加强保护意识和保护行动,保护传统建筑,例如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及传统民居等,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位于湖南永州的何仙观涧岩头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相传周敦颐六世孙周佐父子公元1450 年左右迁徙至此,始建周家大院(老院子)。周家大院走出了周希圣(明朝户部尚书)和周崇傅(晚清重臣)等杰出人物,周崇傅曾描述其地理布局:“左边有青石挂板,右边有双凤朝阳;门前是二龙相汇,屋后是锯子朝天”。负阳抱阴,星座式布局,“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是息息相通的整体。从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上看,周氏家族注重生态,敬畏自然,爱护环境,与自然和谐共处,继而衍生出生态意识和公德意识,促成民风淳朴。
建筑本身区分出内外空间,隔离出远近秩序,并赋予内部某些秩序等级,体现人伦。周氏家规威严,对家族成员的行为起到规范和训诫作用。现代留守家庭权威缺位、家庭教育缺失,长幼关系失序、夫妻关系异化,如遵祖训守家法,发扬宗族成员责任意识,将改变村民行为和家庭状态。
子岩府门匾上书对联“翰林门弟,濂溪家风”,宗祠祖位上书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归功于周氏家族的家训,做人要做一等人,做忠臣、做孝子;做事要做好两件事,读书和耕田,即出人投地和安居乐业这两大人生选择。翰林门弟,书香百世,正是周氏家族重视教育的结果。
家规、家训的长期践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具体体现在为人、处事的观念与行为,造就了独特风格的家风。村由宗族繁衍生息而来,家风即族风,即村风。濂溪家风、尊重自然、重视教育、爱国敬业、修身养德,这是周家大院文化的精神内核,奠定了涧岩头村乡风的基调,也是村民文化自信的源头。在此基础上涵养乡风,则一蹴而就。
2 依托乡规民约,建设道德框架
乡风文明建设就是村民思想道德建设。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规范性公约,由村民共同约定并自愿履行。但由于其是民间公约,不具有强制力,只能靠村民的自觉性。村规中虽有一定的经济处罚条款,但缺少奖励和激励措施,在规范村民行为上发挥的作用有限。
乡规民约的内容涉及到环境保护、经济生产、团结邻里、和谐家庭等方面,还包括禁止赌毒等非法活动及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乡规民约实质上是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抓手和依据。落实乡规民约,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德行教育真正做到深入民心、震撼心灵。
以先进模范人物引领乡村主流价值,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及个人品德。在乡村内部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挂牌授证“模范父母”“模范子女”“模范邻居”“模范村干部”等,同时匿名评选“最不称职父母”“最冷漠邻居”“最懒村民”等反面典型,反向教育引导村民向上、向善[2]。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家风影响着家庭成员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家庭作为乡村的基本构成元素,家风凝聚成乡风。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诚信守礼的个人作风、勤劳致富的价值操守、守望互助的处事原则、尊老爱幼的伦理观念、夫妻恩爱的家庭氛围,都从家庭熏陶而来,对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行具有塑造性。开展和征集创立家规活动,从规范自身、规范自家做起,争做文明村民、文明家庭,进而建设文明乡村[3]。
涂鸦墙是乡村旅游环境建设的一道风景线,不仅美化村容村貌,还能传播社会文明。文化涂鸦可以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规民约,图画先贤人物、时代楷模活动事迹,图文并茂,增加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要创造村落标识文化,例如永州“千家峒”“漕渡村”等瑶族村,不但有村名村牌,村口还立有石头底座与牛角、长鼓舞造型组成的“村标”,“勾蓝瑶寨”“上甘棠村”有门楼或牌坊,诸如此类的村落视觉识别起到了提示和标识作用,也体现了民风民俗的特别,时刻提醒村民作为瑶族的一份子,有责任和义务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利用媒介平台,落实移风易俗
创建文明乡风的同时,要抛弃愚风陋俗。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并流行的观念、仪礼、习惯、禁忌,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缘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因素、传统文化、政治及经济因素,同时具有一定的象征性,难于一时改变。需要借助内外媒介平台,利用传统节日,传播新思想,改变旧观念,进而去除传统不良惯习而脱胎换骨,推进风俗文化的变迁。
真正将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并利用好,用文化装饰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设置文字宣传栏、电子宣传屏,宣传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本土文化人才,对接地方学校,培养乡村文化能人组建文艺活动队。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利用瑶族赶鸟节、洗泥节、盘王节、端午节等节俗举办契机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加强村民凝聚力和乡村文化自信。
文化下乡,送图书、送报刊、送戏曲、送电影、送节目,通过公共文化供给,丰富乡村精神文化活动,加强村民道德建设。实现戏曲下乡村,为农民提供戏曲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使戏曲送文化进村庄成为常态化。例如湘南地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祁剧”“祁阳小调”“瑶族长鼓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零陵花鼓戏”“零陵渔鼓”“道州调子戏”等传统优秀地方文化,融合方言乡音、民族舞蹈、民族器乐,吹拉弹唱、唱念做打,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戏曲目)剧本剧情,遏制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同时,要挖掘民间传统技艺,例如“永州木(石)雕”“江永剪纸”“瑶族织锦”以及传统饮食、瑶医药技艺,开展基层培训活动,增强村民谋生能力,填充空闲时间,改善村民精神风貌。
另外,文明乡风的另一面则是野蛮乡风,“高速路上货车侧翻,货物被村民一抢而空”“设置村路路障,收取过路过桥费”“村匪村霸”等丑恶现象,则是野蛮民风、野蛮乡风的表现,要从立法上规范乡民行为,打破地方保护网,杜绝不文明行为,做文明村民、展文明乡风。
4 结束语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