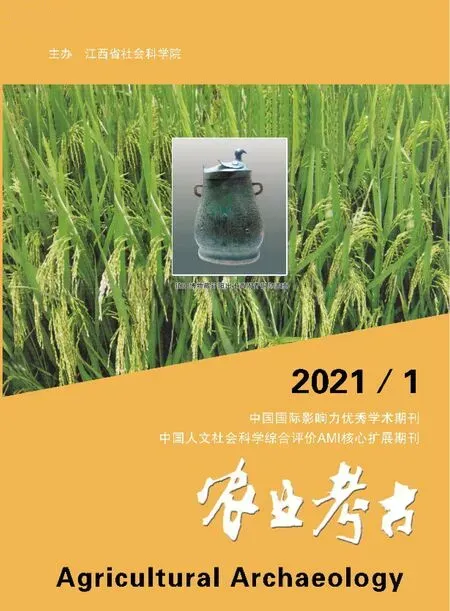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隐地初探
2021-12-14刘超建
刘超建
刘超建,男,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移民社会史与边疆问题。
一、引言
2016年3月18日,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到一份《1945年第一行政区(即迪化区)新疆省各宗族人口性别统计表》,根据该表计算,当时乌鲁木齐地区总人口为410754人①,而同时期耕地数为1556345亩,此耕地亩数基本上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②。根据这组数据计算,1945年乌鲁木齐地区的人均耕地约为3.79亩。这一人均地亩数不仅低于18世纪60年代乌鲁木齐地区人均5.07亩耕地的最低值[1](P255),也低于同时期中国人均4亩耕地的饥饿线。最为重要的是,乌鲁木齐地区的农业与内地相比,农耕技术较为粗放,即多采用撂荒与轮耕、休耕制,且耕地贫瘠,亩产量相对较低。这即说明当时乌鲁木齐地区的耕地并不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即是说,1945年乌鲁木齐地区的人口与耕地数据是否符合实际呢?人口数来源于档案,是当时人口调查的数据,无疑是可信的。即使有所出入,也应是基本接近。而耕地数据,多是学者根据当时政府所收赋税进行推算的,亦得到了学界多数人的认可。基于这种情况,那就说明当时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里所推算出的应该是当时升科耕地亩数。即是说,实际上乌鲁木齐地区还应该存在着大量的隐地。那么该时期实际耕地应该是多少呢?我们不妨根据劳动力的数量做一大致推算。“一般来说,一定的人口规模同劳动力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比率,如一个五口之家在经过折合后一般有三人左右的劳动力”[2]。如此计算,乌鲁木齐地区当时应该有246000多个劳动力。这还没有考虑到移民大多数是年轻力壮者,所以劳动力人数应超过我们所估算的数量。就当时生产力与分配额定地亩数而言,一个劳动力为20亩,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其耕地应该在490万亩左右。齐清顺亦认为:“对于入籍移民,政府给予每户60亩的额定耕地,但在家庭劳动力许可的条件下,尽力开垦私地,其数量虽然不多,大概是额定耕地的三分之一左右。”[3]这与清代乌鲁木齐地区耕地的峰值155万余亩相比,其耕地已经得到了很大拓展。而在劳动力富裕的家庭,开垦私地应该会更多一些。通过上面的计算,说明当时乌鲁木齐地区实际地亩数与升科地亩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亦即是说当时乌鲁木齐地区应有大量的隐地的存在。
二、产生隐地的原因
隐地在人多地少的内地省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农户通过隐地以达到减少缴纳赋税的目的,有些地区将其称之为“黑地”,即指未经升科或在官府册籍上失去记录的土地。近代以来,随着清廷财政开支不断增加,为此在直隶地区开展了清查“黑地”,以增加财政收入③。但在地广人稀的乌鲁木齐地区,隐地亦是普遍存在的,这在一些档案等资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综合这些档案及田野调查等资料来看,其隐地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除为少交赋税的有意隐瞒耕地数量外,同时还在着一些其他隐地情况。
(一)有意隐地
通过对所收集史料的梳理,根据隐地的主体与目的,就其有意隐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首先,耕地拥有者的有意隐瞒,以逃避赋税为目的。这种状况与人多地少地区的“黑地”很相似。如三道坝村户民周涛,在村中仅稻田就拥有4000余亩。可是周涛自报的田赋粮只有一斛半地(合300多亩)[4]。可见,周涛通过隐地就可以少缴纳很多的赋税。其次,地方官员的有意隐地。地方官员虽知道辖区内的实际耕地亩数,但上报时以多报少,这样可以截留一部分赋税为他们所享用或贪污,而对与农户来说,并没有达到少交赋税的目的,甚至他们对此并不知情。这在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中亦有详细的记载:
其百姓凭垦官地不报升科,实属违法。究竟历任地方官有无私收隐粮、讳匿不报情事,亦应查究。惟据称“报垦升科,每亩须缴纳银三钱六,以作纸笔之费”等语。如此重索无怪乎百姓隐垦不报也,姑从宽免究。现在该县所收原、被告交银九十六两,应即当堂退给该原、被告等……概行免缴,以后不准再收,免滋扰累。所有县属隐垦,宜出示,晓谕户民,悉数呈报,毋得再行隐瞒。倘有不知宽典,故为隐匿,一经查觉,定当从重惩办不贷。[5]
地方官出身的杨增新是十分熟悉基层官吏的做法的,所记载的应该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盛世才及国民党主新期间,鉴于地方官吏隐地已相当普遍,严重影响了各级地方的财政收入。为此,政府制定了《查整地亩通则十六条》,对耕地进行整顿,统一耕地面积标准,以达到耕地亩数与额粮相符,杜绝由此而发生的各种纠纷。并对具有隐地现象的地方官吏进行严厉处罚。如阜康县(今阜康市)、昌吉县、孚远县、玛纳斯县等多数县长因此而受到相应的处罚。
最后,通过改换粮名、少报耕地以达到少交赋税和侵占别人耕地的目的。这种状况在耕地纠纷中多有出现,如马忠状诉安俊杰霸地不还,就是明显的一个案例:
状诉安俊杰霸地不还、私换粮名,仰祈鉴核,依法索归事。
窃民祖父马禄、马祥很久已(以)前在河州工各承拉地半解。因为后来乏力耕种,就在民国十三年由小民祖父经手,将之共一解的田地,推借给该安俊杰耕种,自行缴纳田赋,我们不吃租子。并且言明,在我们家有力耕耘的时候,仍当要交还,并无异说。岂知在小民祖父们去世以后,该安俊杰起哄小民年幼无知,竟把马禄、马祥的粮名更换为安俊杰的名业了,并减半解地,以便应纳半解地的粮赋。于是对已半解地隐于无形了,这是以多报少。但是在渠上浇水或是借领公款的时候,该安俊杰便拿一解地的名义行事。这他的以少报多,自欺欺人,这些弊端是本渠众户都知道的。到二十九年的时候,公家以解改亩了,他始行更加半解,才按照一解地完纳额粮。如今小民向该安俊杰追索祖田的时候,他便空口狡赖,霸不肯还,诚心讹占。虽然屡次催索,无奈他何。因而恳请钧府依法索还,以便管业,状呈。
具状人:马忠。④
很明显,这是一份关于耕地纠纷的案件,但在诉状中,涉及到了隐地的问题。我们且不说耕地的归属问题,从诉状中可知,安俊杰故意隐地,其目的有二:一就是达到少缴额粮。后来,官府对耕地统一丈量,以“解”改亩,才将其隐地统计在粮册中。二是因为耕地本身并不属于安俊杰所有,他是私自改换粮名占有马氏之耕地,以便可以讹诈马氏之半解耕地。当然,隐地的主要目的还是逃避赋税,从而造成了地方财政上的流失。
通过档案与田野调查资料的梳理,发现乌鲁木齐地区的有意隐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被隐瞒之耕地不但是已开垦成熟的耕地,而且多数属于肥沃、有较为充足的水源能够保障灌溉之地。如上述所列周涛之隐地,位于米泉县三道坝村,不仅有丰富的水源,而且还是乌鲁木齐地区稻米的重要产区。头道坝、二道坝、三道坝及湖南村都是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安置裁汰湘军的主要聚落,属于耕地条件较好的区域。其次,隐地者多属于村官或恶霸、地痞之类。因为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权势,即使隐地,其他农户亦不知其所为。第三,地方官吏的上行下效助长了隐地的发生。正如杨增新所记载,地方官吏为了截留更多的赋税,他们往往参与了隐地活动,遂成为隐地发生的主要诱因。
(二)无意隐地
与有意隐地相对应的是无意隐地,这种隐地大多发生于地广人稀的边疆省份,而对于人稠地少的内地来说则不可能发生。自乾隆勘定新疆至清朝末年,乌鲁木齐地区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⑤。与乾隆时期的移民相比,清末移民不仅来源区域广,“其汉人十八行省之游手皆有,而北五省人为较多”[6],而且还具有民族多元化的特征,“汉户、回户、缠户”[7]皆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蒙古、满、哈萨克等,这就造成了各村屯对耕地面积的计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如陕甘地区的移民多以“晌”为单位,维吾尔族多以所播种的种子数量“石、斗、升”为单位,此外还有以“户”“角”“解”“斛”“对牛”等为耕地单位,繁杂的耕地面积计量单位大量存在于各乡村中。“户”虽是常用的耕地单位,但即使“户”数相同,而上地、中地、下地所包括的地亩数亦有不同。如绥来县长胜乡(乐土驿)之户民,耕地在“习惯上以‘户’作为计量单位。为计算方便起见,根据当地一般就说法,中地一户100亩,下地一户120亩。但实际上每户地面积大小颇不一致”;周金茂自报有“两户三角”耕地,实际测量则达到了330亩。此外,还有以下种的数量作为耕地计算单位,如一石地、一升地、一斗地等。甚至在同一聚落中,多种耕地计量单位同时并存。如东乡大“水利”王宝山就出租八石地,以当“水利”掠夺来的水供给租户浇地[8](P4-6);除此之外,本村还存在另外一种计量单位就是一对耕牛一天所能犁耕的地亩数,如“一对牛的庄稼,一般可耕四石到六石地,多也超不过八石地”[8](P10)。
即是说,由于官府对耕地没有统一丈量,农户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大多只是估算,再加上民间计量单位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他们自己亦并不清楚所拥有耕地的确切数量。即使后来政府查出隐地,也不是他们有意隐瞒。耕地单位混乱,没有统一换算标准,官府又无力进行统一丈量等,这就使得耕地统计较为困难,给赋税征收带来了诸多问题。笔者在玛纳斯县凉州户镇李家油坊村做调查时,李家大户当时自报耕地50户,但实际上有多少耕地,他自己也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统一丈量,耕地却高达1万余亩,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因当时耕地单位混乱而造成的隐地,则多属于无意隐瞒之行为。
三、隐地的治理
从杨增新在《补过斋文牍》中的记载来看,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隐地应是普遍存在的。隐地的大量存在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隐地成为地方官员攫取民间财富的一种手段。如三道坝村因地理位置优越,且拥有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耕地,早已成为军阀杨增新觊觎的目标。杨氏曾想以低价购买周涛的4000余亩的水稻田,但却遭到周涛的拒绝。后杨氏查到周涛自报的田赋粮只有一斛半地,其隐地的事实被杨氏所掌握后,为得到周涛之耕地,杨氏就故意放出话来,说“即将丈量土地,对于隐地者严惩”等语。周涛听说后,很害怕露出马脚,被官方抓住辫子,而被迫将耕地全部以较低价格卖给杨增新[4],周涛之田产亦成为杨氏在乌鲁木齐精心经营的重要产业之一。杨氏如此,各级地方各级官员亦上行下效,他们通过隐地来截留赋税,据为己有者更是屡见不鲜。通过隐地截留的赋税以应付官府开支与中饱私囊,这在各级官府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即是说,隐地亦成为地方官员贪腐的一种常用途径。二是造成地方财政流失,使得本来就左支右绌的各级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基层官僚出身的杨增新,对于隐地问题亦有深刻的认识。当时杨氏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对隐地的查处往往采取较为宽容的处理办法。但至盛世才及国民党主新期间,随着各项社会事业的逐渐开展,财政开支日益浩繁。为增加财政收入,新疆省政府通过统一丈量耕地,以杜绝隐地,特制定了《查整地亩通则十六条》。通过对耕地的整顿,统一耕地面积标准而达到堵塞地方财政流失的漏洞。一方面使耕地数与额粮相符,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亦可杜绝因赋税缴纳不均而产生的各种纠纷。
查本省地亩混乱,纠纷层出不穷,人民缴纳不均,政府征赋亦感困难。为解决地亩纠纷,使地粮户相符,人民公允起见,特订定《查整地亩通则壹拾陆条》。经本府委员会议通过,公布实施。⑥
为了彻底实施耕地通则十六条,进行耕地查整,各县区成立了查整组,到各乡、镇、村、保等对耕地进行彻底丈量,核实面积,以期达到彻底整顿,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如孚远县政府及征收局,即要求各查整组迅速共赴各保甲,严格按照通则要求,认真查整耕地状况,以彻底根除隐地现象,实现赋税的全额征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省政府电令“赶速进行,限期完成”等因。当即召开会议,详细讨论分组下乡,全县当地参议员及各乡前饬介绍之工作人二名,共同赴各保,认真办理,迅速完成。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员等,即速前往各保进行工作,勿误此令。
县长孔庆文,副县长吉令义。⑦
孚远县政府征收局。本省三十七年度田赋,奉行政院及粮食处电示“应按全额,不再减少”等因。仰照省政府颁布《查整地亩通则》,认真清查,以期上不亏公,下不累民。本年田赋即照查整后赋额,全数征收,并限于年底前据查整完缴。北疆各县未曾开征,南疆各县电示开征。于开征后,三个月扫数,不得因征延误或损田粮!否则即以损失赋程议处。特电遵照。并将查整后赋粮及地亩数字,先行报核为要。⑧
尽管政府对查整地亩做了大量的工作,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已腐败透顶的民国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已有心无力,所以并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乌鲁木齐地区的隐地仍较为严重。直至新疆解放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对全区耕地进行了统一的丈量,才彻底根除了隐地的恶疾。
四、余论
综上所述,乌鲁木齐地区关于隐地的史料虽然不多,但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梳理,足以说明民国时期隐地现象大量存在。由于乌鲁木齐地区具有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隐地产生的原因、类型及地方政府的治理态度与措施等方面而言,与其他区域相比,则明显存在着空间差异性。隐地作为农业社会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不同区域多有存在。但由于各地环境不同,隐地情况自然应有所区别。综合目前研究成果来看,隐地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还极为缺乏,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1945年第一行政区(即迪化区)新疆省各宗族人口性别统计表》,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12-6-1997。
②参见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齐清顺《1759-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等等。
③参见(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5—277页。
④参见《马忠向安俊杰索还祖田的诉讼(1941年)》,收藏于昌吉市档案馆,档案号:J1-1-26-27。
⑤参见刘超建《移植与模拟:清至民国乌鲁木齐地区宗族与大户的实践——以个案分析为例》,载《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异地互动:自然灾害驱动下的移民——以1761-1781年天山北路东部与河西地区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
⑥参见《为电请各区县议会及当地公正士绅整饬地亩(1948年)》,收藏于呼图壁县档案,档案号:J05-1-19-18。
⑦参见《关于省政府整治各县地亩的训令(1948年)》,收藏于吉木萨尔县档案馆,档案号:J2-1-62-51。
⑧参见《孚远县政府及征收局训令(1948年)》,收藏于吉木萨尔县档案馆,档案号:J2-1-6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