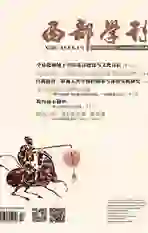论无效取证行为的转换理论
2021-12-11陈高鸣



摘要:安徽省高院对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主张被告人的供述发生了转化,成为了独立的、新的供述,并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案从证据法学以及更深层次的法理角度,探讨被告人审判前和庭审中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提出取证行为作为程序行为的一种,属于法律行为的概念范畴,亦存在有效、无效等效力形态。事实上,采用行为—证据的二阶层模式的无效取证行为转换理论,与传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比,更加侧重发现实体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平衡。
关键词:重复性供述;无效取证行为转换理论;非法证据排除;行为—证据二阶层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075-03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某日,被告人李继轩与吕某约定,由吕某提供海洛因用于贩卖。在交易过程中,李继轩和吕某派来的彭某某被民警当场抓获,查获海洛因共计703.4克。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李继轩对其贩卖毒品行为以及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其侦查阶段有罪供述没有异议。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继轩构成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继轩不服判决,以2016年11月27日被抓获后,遭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及原判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安徽省高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李继轩及其辩护人两审期间均没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由于诉讼参与人是否申请不影响法院依职权审查证据,故二审法院仍应当依法履職,审查一审法院所采用的证据的合法性。安徽高院认为本案中,不管李继轩侦查阶段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由于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明确告知、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且其本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也能够正确认识,故李继轩所作的供述应当属于任意性供述。相应的,其对供述真实性的确认也属于自愿确认。综上,李继轩的有罪供述,虽系侦查阶段供述的重复性供述,但显然不会再受到侦查阶段可能发生的非法取证行为所带来的有罪供述的影响,故对于这一份供述的界定,不应是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而是由其转化而来的独立的当庭有罪供述。在此基础上,安徽省高院认为,对于一审判决采信的李继轩有罪供述不需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二审期间提出的受到侦查人员殴打逼供的情况与本案二审证据审查无关,应当视为对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控告,交由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①。
二、问题之所在
贝林曾言:“证据禁止乃为刑事诉讼真实发现之界限”[1]。基于对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反思[2],以及对发现实体真实与保障人权之平衡,2017年6月27日“两高三部”②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非规定》),对重复性供述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原则上排除犯罪嫌疑人的重复性供述,除非更换讯问主体或诉讼阶段,且释明诉讼权利。
安徽省高院对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主张虽然被告可能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但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的供述发生了转变,成为了独立的、新的供述,该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另案审查。本案的宣判早于新规定的出台,在裁判过程中却已蕴含了《严格排非规定》的规范意旨,但从证据法学以及更深层次的法理角度,可以窥见其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把握被告人审判前和庭审中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背后是否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则案例为上述问题的思考抛砖引玉。关于重复性供述,相关研究如过江之鲫。本文尝试以新的视角探讨重复性供述的排除及归纳背后与既存法理的相似之处。
三、无效程序行为转换理论
证据法是一个规则和标准系统,用以调整诉讼审判中的证据的可采性[3]。其中取证行为与证据之间无疑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厘清取证行为的概念并非易事。此时或许可以采用“类型(Typen)”的思维方式:尤其当借助抽象——普遍的概念及其逻辑体系都不足以清晰明白地把握某生活现象或者某种意义脉络时[4]。
(一)程序行为是广义的法律行为
本文主张程序行为可以被纳入广义上的法律行为这一类型。事实上,法律行为可一般性定义为当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5]。自萨维尼以降,法律行为通常被置于法律事实(Rechtstatsachen)范畴。法律事实可分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Handlungen im Rechtssinne)、状态(Zustnde)和事件(Ereignisse)[6]。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可作进一步分类(见图1)[7]。德国刑法学家与法哲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N)的这个分类舍略了公法上的合法行为与程序法上的行为,因此并不完整。取证行为(程序行为之一)作为刑事司法行为的一种,与行政行为具有高度相似性③。由于在能够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方面,诸如警察命令等行政行为与法律行为相类似[8],故根据传递原理(∵A≈B,B≈C,∴A≈C),取证行为亦与法律行为相类似。但程序法上的行为确实与其他的法律行为有诸多不同,因此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分支(见图1)。
法律行为成立之后,是否能够如当事人意愿那样发生法律效力,本质上要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的意志,符合的才能获得法律的积极性评价[9]。民事法律行为存在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四种样态。由于民法是私法,当事人充分享有意思自治,故程序行为的样态并不如民事法律行为那样丰富:是否存在效力待定和可撤销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肯定存在有效和无效两种最基本的形态。
以取证行为为例,有效的行为需要满足:(1)取证人员是适格主体,即法律规定的符合条件的侦查人员或法官④;(2)主体具有“取证”这一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⑤;(3)不违反宪法、批准加入的国际条约⑥、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重复性供述等。
本案中,根据传统非法证据排除理论:李继轩在侦查阶段由于受到刑讯逼供,所作的供述显然是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根据本文理论,上述表述应当置换为: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所进行的取得李继轩口供的行为因违反《刑诉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从表面上看,似乎两种理论的表述差距甚微,但事实上,新理论的证据排除时间提前了。更进一步讲,如果抛开传统的线性结构,而采用行为—证据的阶层模式,可以认为新理论没有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因为取证行为的无效,而导致没有获取到证据,自然不必讨论证据的“三性”(见图3)。
(二)无效取证行为的转换:对重复性供述证据规则的再理解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源自民法理论,是为了缓和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严苛性而产生的。事实上,由于刑事诉讼是对人权的限制,因而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法定原则[10],必须有严苛的无效制度。因此,无效取证行为的转换,是发现实体真实的关键所在,是“度量实体真实和保障人权的水平仪”。
若某一无效法律行为符合另一替代行为的要件,而且当事人在知晓其所缔结的法律行为无效时也愿意缔结该替代行为,则该替代行为有效,无效行为由此被转换为有效行为[11]。所谓重复性供述的取得,前后必然包含至少两个取证行为,但是由于两个取证行为的客体是一致的——都是犯罪嫌疑人相同的供述。因此,前后行为在天然上就有同一行为的相同基因片段,而又由于其他要件的不同,使得前行为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后行为的无效。换言之,如果后一行为符合了有效取证行为的要件,则可以理解为前后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重叠,从而由无效的取证行为转换为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行为,而控方为获得对被告人供述的意思表示正是这一转换的中心轴。
本案中,如根据我国《严格排非规定》,李继轩案的主审法官已在一审庭审时告知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且诉讼阶段发生了改变,因此一审的当庭供述虽然属于侦查阶段供述的重复性供述,但显然已不受先前获取有罪供述的侦查行为影响,因此不予排除。但是,如此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不是一定能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尽管本案的裁定书对被告人自愿性作了判断并亦有说理,但实务中还有很多法院不是将自愿性作为构成“例外情形”的一个要素,而是依据个案情形确认了重复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后,才予以采信[12]。这种个案正义(Einzelfallgereechtigkeit),因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因此将牺牲法律原则的一般性[2],以至于这种正义如同蜃景般飘渺。
重新梳理一些重复性供述的排除例外,如在美国证据理论中重复性供述作为衍生证据,具有以下排除之例外:独立来源管道(the Independent Source),必然发现(the Inevitable Discovery),污点涤除(the Purged Taint),出于善意(the Good Faith)[13]。这种规则可能是对的,但是与其承认排除之例外,不如直接认为这些重复性供述是符合某种要件,因此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如果根据本文主张的无效取证行为转换理论,则更为抽象的无需先检讨这些证据的是否符合“三性”,而是考察这些重复供述的取证行为是否符合有效的取证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以本案为例,在一审庭审中,取证的主体变成了法官,且法官具有取得李继轩贩卖毒品之自白的意思表示,在庭审中法官对基本权利的释明符合宪法、人权公约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成立一次有效的取证法律行为。
此时,究竟是根据取证行为证据的二阶层理论,应当直接进入下一阶层以检讨被告人供述的“三性”?还是说,一审的取证行为实质上就是侦查阶段无效取证行为的转换?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前后是两个行为还是一个行为。本文主张后者。也许批评者会指出,前后行为的主体不同,怎么能是一个行为呢?事实上,这种观点混淆了主体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和成立的要件。所谓的“前后行为”实际上都追求相同的效果意思——获取被告人李继轩的供述,而这一供述又恰巧是相同的,从法律行为的成立意义而言,前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应属同一法律行为。此时,由于一审对李继轩供述的获取满足了有效的取证法律行为的要件,因此可以说无效的法律行为发生了转换,成立了有效的法律行为。事实上,所有的重要规则下面都有一些理由,它们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它们的目标在于通过冷静而精细的推理来获得真相[14]。在这种理论模式下,或许可以言之,发现实体真实和保障人权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
至于被告人在作出第一次供述之后,是否有受到先前被迫作出的供述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这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可于第二阶层由证据“三性”⑦检讨。
注释:
①为便于分析,对案件中涉及刑事实体部分以及与本文无关的内容和事实作了简化处理,仅保留判决书中的刑事程序部分以及必要的实体部分。参见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刑终278号刑事裁定书。
②“两高三部”: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
③例如,警察可以讯问/询问行政相对人,以取得行政处罚的证据。而与作为刑事司法的侦查手段,侦查人员亦得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取证。
④根据取证行为的效力理论,一些原本困难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德國法规定,抽取嫌犯之血液,只得由医师为之(§81a StPO)。甲因涉嫌醉酒开车肇事,被警察乙带到医院强制抽血。实际上抽血者并非医生而是护士。若警察乙明知抽血者并非医师,问上述血液检验报告可否作为证据使用?参见林钰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中国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61页。本例中,可以视抽血者与警察乙之间是委托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认为是代理关系。那么由于乙明知抽血者的主体不适格,自然可以视为整个取证行为不存在适格主体,因此取证行为无效。
⑤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案例:甲涉嫌贩卖海洛因,于依法实施监听中,意外得知某甲另犯重利罪。检察官乃依违反毒品防制条例及重利罪起诉甲。试问监听贩毒中取得另案重利之证据,得否作为认定重利有罪之证据?参见朱朝亮:《另案监听之证据排除》,载《月旦法学教室》2011年总第110期,第39页。本案中,显然侦查人员只有侦查与贩毒相关证据的意思表示,并没有侦查其他犯罪的意思表示,因而侦查其他犯罪证据的行为因欠缺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
⑥刑事诉讼法的趋势正在从“应用的宪法”到“应用的公约”。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5-27页。
⑦证据“三性”:是指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三大特性。参考文献:
[1] BELING.Die Beweisverbote als Grenzen der Wahrheitserforschung im Strafprozess[M]//林钰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304.
[2] 戴长林,罗国良,刘静坤.中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原理·案例·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81.
[3] 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第五版[M].汤维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
[4]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全本·第六版[M].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577.
[5] 朱庆育.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0.
[6] FV KLAUS,HC RHL.Allgemeine Rechtslehre[M].Berlin: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1969.
[7] 亞图·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02-103.
[8] 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M].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6.
[9] 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2.
[10] 黄朝义.刑事诉讼法:五版[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1-10.
[11] 殷秋实.无效行为转换与法律行为解释——兼论转换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J].法学,2018(2).
[12] 牟绿叶.论重复供述排除规则[J].法学家,2019(6).
[13] 林辉煌.论证据排除:美国法之理论与实务[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118-159.
[14] 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M].吴洪淇,杜国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7.
作者简介:陈高鸣(1997—),男,汉族,浙江温州人,单位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