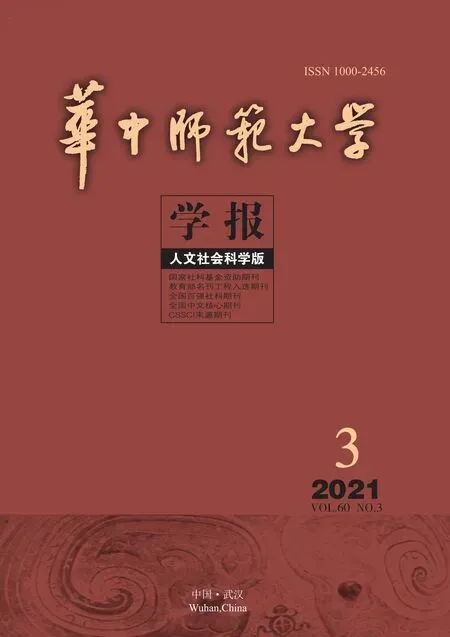论理论心理学的科学使命与历史命运
2021-12-09高申春邢雷雷
高申春 邢雷雷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在我国心理学事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论心理学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方向,至少就其表面特征而言,经历过两次“辉煌”或繁荣的时期。其一是“文革”后心理学重建至改革开放初期,以潘菽为代表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就心理学的对象、方法、学科性质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和论证。其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心理学被大量引入我国,其时,针对几乎每一个西方心理学流派,以引介和评述为主要特色的批判性研究工作全方位展开,既为我们整体地了解西方心理学及其历史线索做出了重要贡献,又造就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理论心理学(及心理学史)的研究队伍。然而,进入21世纪后的二十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理论心理学研究普遍陷入迷茫、困惑甚至是渐近萧条的局面,由此首先在理论心理学界内部引发了大量不同方向的思考,其中包括自我检讨。无论如何,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事业中,关于理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是有普遍共识的。因此,既为了理论心理学本身,也为了心理学作为整体的未来发展,以对当前局面的反思和思考为契机,澄清理论心理学究竟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的科学使命、理解它的历史命运,便成为理论心理学自身在当下面临的一项基本的理论任务。
一、理论心理学究竟是什么?
这里以严肃提问的形式作标题,或许会刺痛一些人的神经,似乎作者要将到目前为止有关理论心理学的讨论成果置之不理;又或许会引起读者方面的疑惑,甚至是质疑作者讨论理论心理学主题的资格。这两个方面都不是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关于理论心理学是什么,我们大概停留在一个笼统地模糊的和感性地直观的把握水平,而不能给出一个系统地明确的界说,乃至于当我们面对某一研究成果时,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它属于理论心理学性质的工作,但却难以细说它在理论心理学中的系统的意义,由此造成很多概念的混淆、甚至是匪夷所思的论证。所以,这个提问毋宁说是一个邀请或呼吁:摆脱一切外在考虑的束缚,就理论心理学本身的可能含义进行系统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性的反思和澄清。
无疑,理论心理学这个名称不是新近才产生的,也不是我国心理学独有的特色。同样,对这个名称如何兴起以及在这个名称下展开的研究工作进行历史的考察,当然是有益的,但出于上述原因,本文不采取这样的论证策略,而只是把它当作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才发现,理论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概念含义未曾得到明确、系统而统一的规定;不同作者以理论心理学的名义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其结论,就其“理论的”性质而言,有时甚至违背了理论心理学的潜在本质;也因此,如果我们以这种工作为基础尝试说明理论心理学是什么,怕是难以达到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例如,二十年前,有美国学者明确地倡议“理论心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来建设,并赋予理论心理学家以心理学科学研究之“顾问(consultants)”的角色①,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厢情愿的一己之声而已。
但另一方面,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有更多不是以理论心理学的名义完成的工作,却恰恰能够更加完满地充实我们关于理论心理学之本质含义的直观意向,因而应该成为我们尝试澄清这个直观意向的有效线索,进而阐明理论心理学的本质含义。例如,在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学家西格蒙·科克曾受命于美国心理学会,组织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对心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的全面评估与清查,既在否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心理学理论困境的历史根源,又在肯定的意义上指出了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希望。虽然由于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的背景和过程,他所指出的希望未能在学科的水平上实现,却无论如何也在他作为心理学家个人的生命中富有意义地得到实现②。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里所包含的全部事实,都是很耐人寻味的:正是在类似这些事实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隐藏着理论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的答案。
科克的研究工作和结论,同时包含了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其中,否定的方面是明确的,即对行为主义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否定,包括它的内容和它的理论基础;肯定的方面虽然就内容而言不如否定的方面那么明确,但就其态度的方向而言同样是明确的,即在摆脱行为主义并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解放”之后,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走上为心理学真正走向科学而积累知识的预备道路。无须说,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构成辩证的统一体:否定以自我肯定为前提而排斥自我的幻象和异己者。具体说来,科克通过系统的历史批判,终于认识到,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的科学思维,原来是“失去意义的思想活动(ameaningful thinking)”,由此形成的心理学知识只能是“伪知识(pseudo-knowledge)”;正是这种否定的认识同时为他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和空间,得以肯定地认识心理学必然是什么,即心理学作为“人类自我理解事业”,就其整体性质或特征而言更接近于人文科学(the humanities)而不是自然科学(the sciences)③。这个关系反过来说是同样有效的。换言之,否定的方面或力量和肯定的方面或力量,是同时兴起而相辅相成的。当然,在由此形成的思想的辩证地对立统一的张力空间内,否定是相互的:这就是上文指出的那个事实的根本原因,即科克在肯定的意义上指出的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希望终于未能在学科水平上得到实现。概而言之,科克的全部研究工作及其结论和意义,取决于他对心理学就其内在本性而言必然是什么获得的真理性洞察,他的结论同时包含的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只有以这个洞察为基础才是可理解的;如果我们无论如何认识到并承认,他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典范,那么,经过系统的分析,这一切便意味着,所谓理论心理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心理学必然是什么的系统追问。
因此,并反过来说,一切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讨论或追问,都属于理论心理学范畴。例如,我们一般将奈塞于1967年出版的那本同名著作当作认知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之一。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奈塞著这本书的动机确乎是理论的或论辩的:在行为主义盛行的时代,论证并确认感知觉、注意、记忆等认知过程作为心理事实的实在性,由此阐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至于他采用信息加工的语言来描述这些认知过程,无非是在类比作为思维方法论的基础上,利用信息论等科学发展动向作为外部影响,便利地表达他的理论思考结果的工具而已④。由此扩展开来,任何一个思想流派的创始人或始作俑者,都必然提出一种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新的理想或观念,而学派的后续发展,无非是以具体的技术和理论展现创始人新的理想或观念潜在地包含的内容而已。在这个关系中,创始人的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当然都是理论心理学的。
当然,这里还必须强调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任何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讨论或追问,在占有心理学真理的意义上是等价的。例如,华生据以提出行为主义纲领的那篇文章⑤,虽然确实蕴涵着一个关于心理学的理想,但如果深入其中细究其每一个论证步骤,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想不是逐步逼近于、而恰恰是在远离心理学的真理,也正因此,结合历史来说,此后心理学普遍走向行为主义,与其说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不如说是情绪的和动机的⑥。又比如说,“潜意识”无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的本体论基础,但由于其特殊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个概念是不可能得到系统论证的⑦,乃至于弗洛伊德竟如此蛮横无理地说,虽然“潜意识的概念是我们无法觉察到的。但是,考虑到其他的证据和迹象,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准备承认它的存在”⑧。如果我们理想地将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形态当作心理学真理的准绳,那么,我们便获得了一个稳定而系统的思想坐标,据以把握或判定每一个心理学体系所蕴含的或以之为前提的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特殊理解的真理性或谬误性。在这样一个极端错综复杂的思想空间内,从任何角度、在任何水平上、对任何一个心理学主题的研究,只要在逻辑上系统地贯彻追根究底的彻底精神,都必将上升为理论心理学,并最终共同地指向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系统的追问和阐释。
二、理论心理学的科学使命
因此,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作为整体是水乳交融地统一的,是心理学作为整体之科学思维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维度,并在其中承担着它必然要承担的、其他任何分支或维度不能替代的特殊使命,它的存在也正因此才是合理的。事实上,上文关于理论心理学概念含义的分析,主要就是依据它在心理学作为整体中的科学使命或理论职责展开的。然而,由于心理学及其历史的特殊性,上文揭示的理论心理学的本质含义,似乎又与我们关于理论心理学的直观印象相去甚远。所以,还必须结合心理学的历史,进一步地具体阐明它的科学使命或理论职责。
毫无疑问,心理学一定是什么,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尚不能明确地说出它所是的那“什么”的具体内容。至19世纪中叶,作为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塑造我们现代人世界观的产物,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普遍兴起,即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或起源。经过系统的分析,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关于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信念作为一个命题是富有欺骗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作为命题,其形式的完成性限制了我们的思维、特别是我们思维的批判性的发挥,似乎我们由此完满地获得了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理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心理学实现为科学,而不进一步地从实质或质料方面追问心理学是什么;另一方面,在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信念中,“科学”观念的历史原型当然是自然科学,这种原型关系同样制约了我们的思维,并特别易于使我们对“科学”观念之概念含义的理解沉降到自然科学作为它的历史原型之中⑨。这两个方面的限制或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将我们直接引导到自然主义的道路而不自觉,从而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盲目信念,由此反过来将自然科学关于它(们)的质料作为它(们)的研究对象的理解方式强加给心理学,从而使心理学误解了它自己的质料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并由此走向自我异化。这就是在心理学作为整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实质:正是对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地位的追求,构成了它统领一切的、最内在、最强烈、最为始终一贯的历史动机,乃至于由此实现的结果,可以不是“心理学”的,但一定要成为“(自然)科学”的。因此,对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来说,只要它不放弃对“(自然)科学”存在地位的历史追求,那么,无论它采取怎样的理论形态,都必将注定走向困境和危机⑩。
以此为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狭义地理解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范围内,理论心理学最直接的、并因而也是最基础的使命或任务,就是对各种危机表象进行根源的诊断。事实上,综观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理论心理学作为主题及其重要性的突显,与特定时期对心理学危机局面的普遍感知,是同步的和对应的,如前面提到的西格蒙·科克的工作,就是由赫尔体系的崩溃带来的普遍危机促成的。这个水平上的理论心理学研究,其特征必然是挑剔地分析的。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绝大多数的理论心理学研究方案,都处在这个水平上。由此进一步,如果挑剔地分析的工作足够深入和系统化,则必将指向对作为一切“科学心理学”共同目标或前提的它的“(自然)科学”的存在性质和历史动机的消解和否定,这就是理论心理学第二个层次的科学使命。这个水平上的理论心理学研究,其特征必然是批判地否定的;特别是对于出身于“科学心理学”传统的理论心理学家而言,其结论带来的压力往往是难以承担的,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他作为心理学家的存在。也因此,在这个水平上坚持理论心理学的人,实不多见。
消解、甚至是否定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实际上是引导我们反向追踪到现代心理学诞生的起点,重新探问心理学及其作为科学的观念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游离于人类思想及其历史之外、而是以之为背景,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个观念兴起之前的思想史背景中、亦即在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中,这个观念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违背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但如前所述,这个观念无论如何在19世纪中叶普遍兴起,甚至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史趋势中最具引导性的思想史力量之一,从而将人类思想引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的连续工作,他们的努力的结果,不仅真正阐明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而且还由此引导了人类思想的整体转换进入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之中,从而拯救了人类思想:现代哲学的兴起,原来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追求自我实现的产物;它所确立的,乃是这个观念能够在系统地合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所必然要求的那个思想逻辑。概而言之,与前述自然主义传统不同,他们坚持不懈地通过对作为心理学实质内容的“意向性”的系统分析,得以超越“自然科学”作为我们现代人“科学”观念的历史原型,达到对“科学”含义的普遍理解,在这种理解中,“自然科学”成了普遍“科学”的一个特例。胡塞尔具体地将这种普遍科学称为“现象学”或“现象学科学”。按胡塞尔的解释,“科学”意指意识在本质上可能的全部各种活动形式及其具体的内在环节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必然性的整体,而对这些活动及其关系的本质的描述和揭示,就是心理学或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和“科学”必然是内在地相统一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可以合乎逻辑地加以设想,并追求实现它自身而成为现象学心理学。
在这个背景中,理论心理学最直接、最基础的使命或任务,就是阐明心理学及其作为科学的观念按照它自身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并具体呈现为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同时,如上文关于这个历史背景的概述所已暗示,正是通过对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的本质含义的阐释,现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才得以确立,并由此塑造了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由此,并反过来说,在现代世界,现象学心理学作为理论心理学,还承担着为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科学事业提供基础的逻辑职能。在这里,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本身达到了统一,并与人类思想作为整体也是水乳交融地统一的。而且,在这个背景中,亦即在宏观地以人类思想及其历史作为整体的背景中,而不是狭隘地在因为其特殊历史而塑造的自然主义“科学心理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背景中,只有现象学的科学心理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才构成人类思想的主流。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并构成理论心理学需要加以研究的主题之一。
上文分析似乎要将心理学的历史划分为其自然主义传统和现象学传统,并在两个传统中分别讨论理论心理学的科学使命,似乎理论心理学本身亦分裂为两种形态。这是理性分析的有限性带来的幻象。事实上,实际发生的心理学的历史,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而且,就心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来说,其自然主义传统毕竟是主流,理论心理学亦生根于此。因此,我们可以将上文揭示的理论心理学在现象学传统中内在统一的两个层次的使命或职能,即一方面是肯定地阐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另一方面为全部人类科学事业奠基,理解为它在自然主义传统中所承担的科学使命的逐步递进的两个层次的进一步延伸,因为如前所述,消解甚至否定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毕竟是批判地否定性的,类似胡塞尔所说的清理地基的作用,并因而需要在这里建设性地肯定地说明心理学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理论心理学及其科学使命的全域。这也是前面以定义的形式说理论心理学究其根本乃是关于心理学必然是什么的系统追问的背景。
三、理论心理学的历史命运
若要认真地讨论并由此真正理解理论心理学的历史命运,必将是一件颇令人尴尬的事情。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系统地批判的,这不仅意味着,它要将一切相关的要素同时置于理性的阳光之下进行全面的审视,而且也意味着对理论心理学及其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本文引言所指出的我国理论心理学在当前遭遇的渐近萧条的局面,与其说是理论心理学自身的必然命运,不如说是由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作为宏观社会管理制度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贯彻执行的实践形式促成的。就是在心理学内部,如上文分析所已暗示,其中包含的不同思想力量之间的差异,甚至在逻辑上是直接地相互对立的,而对这些力量及其关系的揭示,恰恰是理论心理学的职责。深入分析还将揭示出理论心理学及其研究者在理论和思想的积累和创新方面捉襟见肘的窘迫,如此等等。
但另一方面,亦如前面交代的本文写作动机所暗示的那样,系统地理解理论心理学的历史命运,却又是我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并得以坚持理论心理学的必要补充。这里依然要排除外在考虑的干扰。而且,为了避免这样的印象,即似乎作者要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读者,这里以上文阐明的理论心理学科学使命逐步递进的层次序列为参照,结合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理论心理学研究方案及其人格体现为例,展示理论心理学在不同情况下的历史命运,具体表现为这些方案各自在执行理论心理学科学使命的过程中能走多远、达到哪一个层次。当然,这里的分析工作毕竟也是以心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为背景的,所以以上文指出的在狭义地理解的自然主义心理学范围内理论心理学最基础的使命或任务为基线加以展开。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的理论心理学研究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其动机往往是肯定地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服务,并因为受这个动机的制约而失去理论心理学最本质的批判精神,从而在科学心理学范围内成为多余的和无用的。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学者斯莱夫和威廉姆斯的倡议以及例如斯塔次倡导“统一的实证主义”作为“统一心理学”的基础等,就其一般特征而言,都是试图对科学心理学取得的经验资料进行“理论的”综合,以描述科学心理学的一般特征、揭示其发展规律,或论证这种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本质规定等,所有这些工作作为理论心理学,实属“科学心理学”题中应有之意,却不能像实证研究那样为之做出实质的贡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理论心理学”,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普遍遭到来自“科学心理学”的质疑、甚至否定,是合乎“科学心理学”的“情理”的。又比如说,20世纪下半叶,受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鼓舞,很多人尝试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分析并论证心理学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但却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即心理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然而,这一结论不是引导他们进一步反思心理学的科学性,反倒是促使他们篡改库恩的理论,将心理学规定为“多范式”科学,从而使这一研究传统作为理论心理学退化为一种“无所事事的闲谈”。
如果一个理论心理学研究方案无论如何得以摆脱或不受上述动机的支配或制约,并因而能够在自身保持着甚至是培育了日益增长且系统化的批判精神,那么,如前所述,它的结论必然是指向对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存在性质的怀疑和否定。无疑,无论对心理学作为整体的事业还是对心理学家个人而言,这个结论都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并在这里产生了分化。对绝大多数的研究方案和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受其批判能力的制约,他(它)们由此回归到自然主义心理学而重新陷入它作为“(自然)科学”的盲目信念并与之合流,如前述利用库恩“范式”理论的那个研究传统所做的那样。又比如说,黎黑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史》第二版“序言”中竟然庆幸自己终于由第一版时的一只“刺猬”变成了一只“狐狸”,所以不难理解,比较该书不同版本,就是作者批判精神不断衰退、写作风格日趋叙事化的过程。对于少数愤世嫉俗、其眼界又不足以涵盖全部心理学及其历史的人而言,他们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这里、否定自然主义心理学,几乎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如英国学者乔因森,他的最后结论是,“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部历史,它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人类理智的退化”。对同样属于少数的另一些人如西格蒙·科克而言,他当然清楚地看透了自然主义心理学的盲目性和虚妄性,并也在方向上看到了心理学真正走向科学的希望,但却无力以理论的形式将这个希望展示出来而实现为真正科学的心理学,于是退回到常识,在拒绝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同时占有心理学的原初真理。在以自然主义心理学为出发点的背景中,只有詹姆斯在通过系统批判而达到否定之后,进一步获得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必然是什么的洞察,所以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头也不回地走上了现象学道路,虽然在他自己的思想中实现为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体系。
经由批判的道路达到否定的结论之后,若能进一步肯定地阐明心理学及其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便进入理论心理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能力,还要有追求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毅力。概而言之,这个水平上的理论心理学研究,其成就主要是由胡塞尔在布伦塔诺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可以参照胡塞尔的术语体系统一地称之为现象学心理学,又在如詹姆斯及下文要提到的卡西尔等人的思想中得到回响。从据以理解理论心理学历史命运的角度看,这里的情况显得异常复杂。一方面,在人们的印象中,与前面提到的各种研究方案及其累积效应相比,似乎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批判工作没有那么系统化。事实上,他们同样是经历了极艰难的批判工作后才达到他们肯定的成就的,只是他们批判的对象,不是自然主义“科学心理学”的具体内容,而是塑造了这种心理学的思想逻辑,即陷于“自然科学”作为“科学”观念历史原型之中而兴起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思想态度。因此,他们的批判工作,就其否定自然主义心理学的逻辑力量而言是断然的,就其潜在的范围而言是真正系统化的;又因此,他们的终生努力所呈现出来的,主要是在肯定的方面阐明心理学及其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是经历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塑造成型的。一言以蔽之,并如上文所暗示的,这种心理学作为历史的追求,不是逐步逼近于、而恰恰是日益远离了心理学的真理,从而表现为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对于系统地接受过这种心理学训练的人而言,若要像詹姆斯那样在批判之后达到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理解,实非易事。然而,亦如前所述,在心理学作为专业学科的背景中,总而言之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自然主义的“科学心理学”终究占有“主流”的地位,由此造成的效果是,它狭隘地以其作为“主流”的特权,拒绝现象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存在,几乎阻绝了通向现象学的道路。对此,美国学者吉尔吉以触动人心的情结感慨地说,“心理学的那些敏锐的观察家们看得很清楚:关于心理学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以及它在科学群体中的地位如何,依然得以一种由占主流地位的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所认可并接受的方式来加以判定”。所以,虽然“在关于心理学最终实现它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上”,吉尔吉“坚持他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在心理学立即实现它所急迫需要的”向人文科学的“转换”方面,他又觉得“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最后还应该结合上文暗示的第四个层次来补充理解理论心理学的命运。如前所述,在这个层次上,理论心理学的科学使命主要表现为对全部人类科学事业、甚至是人类世界观的奠基作用,并因而与人类思想及其历史融为一体。熟悉布伦塔诺著作和思想的人知道,这正是他经由心理学的道路重构形而上学的理想或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一理想最终由胡塞尔的现象学得到实现,如后者对20世纪思想史进程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证明的那样。总体而言,在这个水平上,理论心理学已无暇顾及对狭义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批判,而是积极论证真正科学的心理学必然是什么,或是利用这种心理学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基础。就后一个方面举例来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以其符号形式哲学或称文化哲学的体系在当代思想世界独树一帜。系统的分析证明,在他的思想中,潜在地蕴含着一种系统化的关于心理学的思考;这种心理学,究其实质,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是同质的、一致的;正是这种心理学才肯定地赋予了他的思想以特色和基础,但也正是这种心理学作为主题的缺位,决定了他的思想的不彻底性或未完成性。所以,通过对类似卡西尔的思想体系展开理论心理学研究,不仅将有助于阐明心理学本身必然是什么,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论证并凸显心理学对全部人类文化事业的奠基职能。
概而言之,我们不能抽象而狭隘地讨论和理解理论心理学及其科学使命和历史命运。只有以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思想作为整体在其历史进程中展现的各种可能路径为背景,洞察其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既拥有心理学的真理,又获得一个完全敞开的理论视域。也只有在由此构成的极端错综复杂的思想空间和由此获得的完全敞开的理论视域内,才能透视理论心理学及其科学使命的全域,进而以各自在其中适得其所的位置为参照,客观、全面而又冷静地理解每一种理论心理学研究方案及其人格体现的历史命运。由此,我们既得以从否定地批判的消极情绪中走出来,又得以在肯定地建构的努力中获得力量、信心、勇气和希望,坚持并繁荣理论心理学的事业。
注释
②③高申春:《心理学的困境与心理学家的出路——论西格蒙·科克及其心理学道路的典范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④参见U. Neisser,Cognitive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1967.
⑤参见J. B. Watson,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in W. Dennis,ed.,ReadingsintheHistoryof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8.
⑥高申春、祁晓杰:《科学的含义与心理学的未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⑦孟秋丽、高申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无意识观念的理论性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⑧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长春: 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