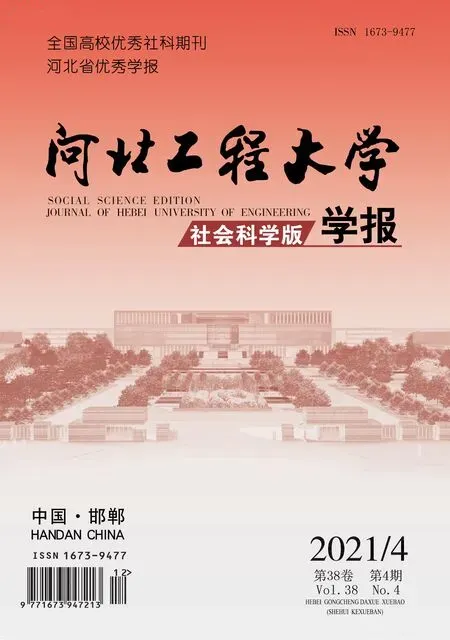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2021-12-09周娜梅涵
周娜, 梅涵
(1.河北经贸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62;2.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北宋时期的诸多学者想通过融通道家、佛家思想实现儒学的复兴与重构,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与主导角色。而在吸纳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仅此还不足以彻底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必须要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对儒学形上系统的不足加以补充。由此,更多学者企图从经典中找到儒学超越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关怀,而《周易》“玄之又玄”的精妙特性及其形上的价值旨归吸引了众多儒者进行研究,特别是儒家理学思想鼻祖周敦颐通过对《周易》的思考和阐发,从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系统化地建立了一个上通天命、下立人极的哲学体系,更好地回答了“天”在儒学系统中的问题。其“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义理的发微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易学与儒学融合的范式框架,填补了儒学天人问题展开不充分这个漏洞,使“诚”这一哲学概念更具超越性,也对儒学形上的理论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诚”的动、静性质——“寂然不动”与“至诚则动”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1]37。运动时未见静止,静止时未见运动,这是“物”的动静。运动时并未见动,静止时并不是真正的静止,这是“神”的动静。而濂溪“诚”的观念贯彻了这一动静观,针对《周易》的不同角度来立论,“诚”亦是即动即静,动静不离的,可从“寂然不动”与“至诚则动”两方面论述。
(一)人之本性——寂然不动
濂溪云:“寂然不动者,诚也。”[1]33陈来认为:“诚指人之本性,本性是诚,是至善的,又是寂然不动的,就是说本性没有活动,没有思维。”[2]42人的本然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没有发念的,故人之本性本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四个字充分涵盖了诚的本性。此外,“寂然不动”出自《周易·系辞传上》,是周敦颐对《周易》的高度提炼,“寂然不动”可为“静止”义,又可分为“寂然”与“不动”两部分,“寂然”有主静之义,而“不动”则指事物停止状态即止之义。
1.“ 寂然”之主静
李翱说:“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是故,诚者圣人之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3]李翱认为“诚”在寂然不动时与“性”同一,感而遂通时才发为有所感动的“情”。故“诚”具有“去伪”之意,“诚”的性质亦可追溯至静止义。“寂然不动”原义出自《周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4]284“而这种“无思”与“无为”就落在了“诚”之性上,“易所谓‘无思者’,以谓无所事乎思云尔”[5]。“诚”指的是思虑、意念之未发,这是“诚”的本性,心的作用还没有发用,这时候的“诚”没有思虑,没有杂念,是至真至纯的“一”,即喜怒哀乐发作之前要先反求己心,做到孔子所言的“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诚之性本无善恶意念发动,保持中正清和。“寂然之中,天机常动,应感之际,本原常静”[4]288。在这种寂然的状态下,虽有精微动处,但诚之本性始终是保持不动的静,此“动”意为不被杂乱意念所扰动,是无动的静。濂溪云:“无妄则至诚矣。”[1]41此“无妄”出自濂溪对《周易》中无妄卦的解读,不善之动为无妄,即放下私心杂念,才能达到思想纯粹的“至诚”之境。
《蒙艮》是周敦颐受《周易》蒙卦与艮卦中的含静之义启发而作:“‘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则乱,乱不决也。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1]42其中“静”与“清”所述是澄静光明的心性本身。山下涌出的泉水,本来是静而清,如未启蒙的童子,至纯之心。而启蒙就要如治水而因势利导,一旦欲望杂念扰乱心性就会“汩则乱”,以至于心性不清不静。“艮其背”意指艮卦所象征的背部,背是自己见不到,也是常静的部分。周敦颐认为若能常把意念止于背部,即使有杂念引诱,亦是看不见的,如此心就不会杂乱,故能静。能安静就可没有纵情的出格行为,做到“止非为也”。“诚”本身落实在人道性命上就是人心,而此心本身是清而静的,只有做到静心清欲,“诚”的本然光辉才能复显。“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1]38。此“静”意为“诚”,指人性本心之清静祥和、干净无杂,没有欲念就能自然获得虚静之心,通达至心境澄明。
2.“不动”之主止
周敦颐在《通书》中以“慎动”作为单独的一节内容展开论述:“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故君子慎动。”[1]33动机纯正,符合“道”,施用时不偏倚自然合道德规范。这是从力行上强调君子做事必须审慎三思,强调“动而无动”的道德境界。“慎动”即是主静,即动而无动,而周敦颐所言“寂然不动”的“诚”与《周易》中的艮卦义理相通,即“诚”从本性存有上来看是主止义。其一,艮卦的主卦与客卦都是山,两山相对意为暂时停止、不变动之意。“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安止之义,止其所也”[4]210。事物是不可能永远恒动不变的,有需要停止的时候,因此需保持不动,并且要“安”于止,以“止”为旨归,而“诚”的本然就是寂然不动,久居于静止状态之中的,艮卦的义理还原了“诚”的本然面目。在周敦颐哲学思想中,“诚”象征着万事万物的究极本元,无形不动却能化变万形之物。其二,《艮卦·初六》爻:“艮其趾,无咎,利永贞。”[4]211人体最开始的发力点是趾,趾代表着细微动作的最小单位,此意在止于动之初,在事物发展刚开始时就停下来可“未至失正”,免于事物整体偏离正道,因此就没有咎害,濂溪以此来比会“诚”之邪念发起初就立即停止的状态,以避免“诚”脱离正道。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1]33。“诚”指人之本性,“神”指人的思维能力。人的本性是至善的诚,又是寂然不动、无为的,可以说本性没有活动,只有当人的“几”与“神”发挥作用才会变动,在此以“几”和“神”的动与用衬托出“诚”的止与体。《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6]621船山注:“几者变之微也,极而至之、研而察之者,神也。”[2]456濂溪援引易学中的“几”与“神”,取二者微妙变动义理,与变化的“几”和“神”相对而言“诚”之本体是静止。周敦颐对“诚”的本性进行规定:“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此,诚动于彼。[1]35“诚无为,几善恶。”[1]32而在《周易·系辞上》中,早已有对“几”和“神”的论述:“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6]621濂溪对“几”和“神”的阐发源于《周易》,并做了新的建构,以“几”与“神”的动之微所产生的善恶念引向对人的内在心性的涵养的思考,此涵养本体即本诚心虚静不动。“无思”是本,强调了诚道德本性无意念流动,有不动之义,而其发而为动的原因是“几”的交感,这是从“诚”的本心和人性上来谈。
(二)“诚”之发用——至诚则动
除了“寂然不动”的一面,从发用上来看,“诚”则能动。其一,“诚体”的存在具有发动之用,通过内部受到感发从而向外投射呈现变动。“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1]33。发而为精神知觉是动,精神活动刚刚萌发而尚未明显时叫作“几”,当外发投射到相对物之前,人作为主体内部也自然而然发动。当人与外部客体事物开始接触,本来处于不动的本性就当即决定思维活动,做出反应,这是“诚”与“神”之间的感通。“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1]41此节濂溪援引自《周易·系辞传》以显诚的发用。朱熹认为达到“至诚”就可以将一切行为落实,存在着“至动”的性质:“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7]40“至诚”即精诚,外物能够感动人,人心受到感动就会改过。但只靠至诚属于主观范畴,因此说话之前应该把要说的东西先进行思考即“拟”,才能发表意见,经过讨论即议,再付诸行动。如此经过“拟”与“议”,然后施行,才能让事物正向地发展变化。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心理状态无一不是由“诚”的牵引所起的。似于《周易》咸卦中的“感而遂通”之“内感”,唯有内在的感应才能使之外通,那么可以说一定是有内在的存在而运作,“诚”就是一种既超越外、感通外又内化于其中的存在。“百家谨案:‘吾儒之学,以言动为枢机,惟恐有失。必兢兢业业,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1]41这种“兢兢业业”即是本心之至诚,是有所活动的,达到这种至诚方能通过“诚”的发用得到其中精微的道理,以至于上达道体。其二,致力于“诚”的过程与状态是能动的。“君子乾乾,不息于诚”[1]40援引《周易·乾卦》中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惿若厉,无咎”[4]2。此爻辞意在警示真正的君子应白天勤勉夜晚谨慎省思,做到“日夕不懈而兢惿”,是对达到“至诚”的内在追求。周敦颐对此进行发微,认为君子应勤奋不息于立诚,这种求诚状态是不息不止,恒转而随化的,修业立诚的过程亦是能动的。
濂溪从《周易》意念不动、保持本心清静的内在意蕴来论述“诚”本性之静止义,又引自《周易》中“拟”“议”的思想进而对“至诚则动”的“诚”进行阐释,实现对“诚”的动静观的塑造,而正因其内在即动即静的性质才可完成“诚”对天命的贯通与对人极的确立。
二、“诚”的体系建构——“通天命”与“立人极”
周敦颐通过对《周易》的阐发延伸以“诚”建构起了沟通天道与人道性命的桥梁,将人性道德的生发与宇宙的创生结合起来。濂溪于《通书》中实现天与人的纵贯,“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1]31。在这里“诚”既是圣人修身立命的道德标准即圣人之本,亦是资始万物具有生命意识的宇宙本体。如从形上与形下之层次划分,既是形而上的天道落实的表现又可落实到形而下的人道层面,其将本体论与人性论紧密相结合,形成圆融并包的整体体系。
(一)天道之“诚”
其一,“诚”之创生义。早在《中庸》中,就将诚与天之实体相连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32。“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中“乾元”作为“诚”的源起,是从宇宙论的生发来看。“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则是从“诚”生成五常与百行的生成论角度来谈,“诚”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更是所有行为准则的发用之基,“诚”作为本体衍生出万物。“本”字和“源”字突出了诚的起始义、创生义,这是本体论才具有的意义,“诚”不仅为万物生成的起源,还是人情感道德的来源,这点周敦颐受《周易》生生之创生论影响颇大,无论是太极本体还是卦象的变化,都渗透着“生生”之理。此外,既然“诚之源也”的“乾元”是万有本体,那么源于其的“诚体”也具有存有意义。牟宗三先生将“诚”作为一个名词,他认为:“‘诚’本具实无妄意,为形容名词,其所指目之实体即天道。天道以‘生物不测’为内容,即以创生为内容。此作为实体之天道,即以诚代之亦无不可。……诚即是体,此即是本然、自然,而当然之天道。”[8]周敦颐赋予“诚”创生意味,使其承贯天道,而不流于空疏。可见,“诚”是一个可以下落又可以上达的实体存在,“诚”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不测之实体,因其可创生万物,故其本就与自然流存而不可测的天道混为一体。
其二,“诚”所禀元气义。“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1]31。可以肯定乾元为诚之源。“物皆有本,事皆有始,所谓“元”也。《易》之言多矣,唯纯乾之为元,以太和清刚之气,动而不息,……发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兴起有为而见乎德”[2]16。王夫之认为纯乾的太和清刚元气资生万物,有肇化万有之功用,故从繁育、生长、教化万物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元气,也正因为有元气人才得以有德性。“木、火、水、金、川融、山结,灵、蠢、动、植,皆天至健之气以为资而肇始。乃至人所成能,信、义、智、勇,礼、乐、刑、政,以成典物者,皆纯乾之德;命人为性,……亦莫非此元为之资”[2]16。从除却人的万物本性来看,虽元气本身无形体,但正因为禀天所授乾元之气才使世间的一切生灵乃至山川都具有生的可能。从道德伦理所建构的空间上来说,元气创生信、义、智、勇等德性,而“诚”本身作为五常之本就具有道德本体意义,如此,“诚”与太极、乾元所承乃同一元气,气本能动,为一体而流行,故“诚”亦为天道所禀受。
综上可见,乾为实体之天,元为无形质之气。万物于广大而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存在着,而在这有空隙的空间中无不充斥着气,万物便禀受这些元气所凝结、化合而成。“无论是立象之形,成物之性,为人之德,无不由纯乾的‘太和清刚之气而来’”[9]。故既然“诚”同样源于乾元,“诚”可与天道同一,“诚”与乾元、太极一体不分。从质料而言,“诚”不仅源于乾元而且与太极一样同贯一气,是对《周易》中元气的一脉相承,由具有相同的质料元素所构成,故内在含有本体的天道意义。
(二)人道之“诚”
“诚”既是万物生生不已的化生之源,也是内在于人心的普遍道德价值之本。“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1]48。“人极”是道德标准与修养方法,即为圣之道。而“诚”作为道德实体,还可下落至立人极之人道。
其一,“诚”是人德性本源。“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1]31。此句提到的“元亨利贞”是《周易》乾卦的卦辞。程颐注:“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4]1元亨利贞象征着乾卦中四种美好的德性,元亨是诚的贯彻,而利贞则是结果,如此通过乾卦就将“诚”与“人德”衔接在了一处。朱熹论《太极图》时还将“中正仁义”与《周易》中“元、亨、利、贞”提到一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如《乾》之元亨利贞,元即仁,享即中,利即义,贞即正,皆是此理。”[1]70仁、义、中、正乃儒家一直所推崇的“圣人之道”,是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原初,其他德性都可看作是这四种德的延伸与发展,而这四德又与“诚通”“诚复”相连,故“诚”亦秉承德性之精神,为道德源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1]32。周敦颐认为拥有大德的圣人,就是仅仅做到“诚”而已。“诚”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根本,追溯至源头,乃德性之始。内在的“诚”即德性之本,在没有行为发显时看不出来,一旦有所行动就发而为光明的德性。
其二,“诚”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规范。“诚”不仅表现为道德精神的本源,还是具体的礼仪规范,体现着向内约束、收摄的作用。“中正仁义”通往“诚道”,是“诚”的具体表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故曰:‘一曰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1]32“五常”与“百行”如果不以“诚”为基础,则是昏暗污塞之邪道,故只要有“诚”就不会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这样,“诚”就直接被提到了伦理道德标准范畴,诚则有德,不诚则无德。“诚”的存在亦是一种道德规范,每个人只有克服自身欲望,使自己言行都符合礼的规范、“诚”的要求,才能达到“诚”,进而使天下充满仁心。“诚”即利物贞固之德,“诚”不仅生就天地万物之德,且追求这种德行就代表着进行严格的自我规范。《中孚·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巽风和缓,以俟议之平允。巽命以施泽于下,宽道也。”[6]550君子有灾要以诚待人,“施泽”有施恩泽之意,“宽道”即指宽厚至善的待人之道,以真心诚意来要求自己,就终会得到好的结果。《中孚·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6]548中,内也。孚,信也。“中孚”象征君子内有柔顺之德而又刚健中正,使人民心悦诚服,用诚信教化天下。而诚信可理解为诚信之心外化,故诚信可推至诚心义,诚信广施于豚鱼等世间万物,故“诚”即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周行于万物的最高道德标准。
综上所述,正如“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1]31,元是始,亨是亨通,有万物初始生命亨通之义,元亨上至天理;利主义,贞主正,有事物发展祥和之义,利贞下至人伦。故“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既具天道境界又具人道价值,并从中起到中和的作用,使天道与人道得以沟通交感。
三、“诚”之修养——“惩忿窒欲”与“省思改过”
(一)惩忿窒欲
“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1]40。濂溪从中涉及了乾、损、益三卦义理。“然必惩忿窒欲”出自《损卦·象》:“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6]370惩,克制;忿,怒;窒为阻塞。虽然要做到乾卦这种“君子终日乾乾,夕惿若厉”的勤奋以立诚的状态,但还必须要自觉平息心中的愤恨怒意,抑制欲望的出现,才能够实现“诚”。周易中的“惩忿窒欲”就是抑制欲念之意,濂溪援引此句来明确立诚之法。
在这种人与外物交感的过程中“诚”的作用非常精妙,“诚”对外在的动机与行为、思维进行交感,在这里“诚”是自然内化于心的存在,而“几”则是善恶之动机,“诚”作为内在力量可支配外在动机,二者实现感而遂通的情感双向交流。诚而至善的本性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外物之来对于本性是一种“感动”,本性通过思维的活动做出反应,即是感而后通。“几”则是从“五性感动”到“神发知矣”的中间环节。诚之性本来没有恶,但到了“几”的状态就可能有善恶即“几善恶”,因此要去掉不善的妄念,周敦颐认为人必须在欲念萌动时慎重地加以检查,即去欲,这是保养“诚”澄明之性的方法。
(二)省思改过
《中庸》中的“诚明”就已有“自省”“自觉”之义,《象》中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1]40其中的“迁善改过而后至”即见善则迁,闻过则改,强调主观能动的反省。周敦颐在《周子通书·家人睽复无妄》中专门援引《周易》中的无妄卦与复卦来说明诚的修养过程:“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1]41治家、治国、身正最终都要归于诚心,而修养诚心之法就是切己自反。“诚”在心中,如果察觉到有任何不好的动机,马上能被善返过来。不好的行动就是“妄”,由“妄”恢复“善”则无“妄”,无“妄”便是“诚”。濂溪认为这是“无妄”卦排在“复”卦后面的原因,濂溪强调的是将不符合“诚”的发念动机和行为改正的过程。《四书章句集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7]32复卦包含事物否定之否定含义,即在否定中获得最后肯定,强调复归的过程。从人性的修养观之,实强调人觉察细小过失,及时省思改过的过程。卦象显示主卦是震卦为雷,客卦是坤卦为地,意为阳刚从亢极回复至于地中,重新培育积蓄力量的过程。《复卦·彖》:“复其见天地之心乎。”[6]230“诚”既养长于天地,亦与天地乾坤一体流行,又生人之仁心,故其可为天地之心,“诚”与天地之心、人心皆为同质,那么复其诚心更需修养自己。《复卦·象》曰:“复,不远之复,以修身也。”[6]231“复者,复于礼也,复礼则为仁,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4]97。程颐将“复”解作对礼的归复,对道德本性的回归,君子得诚之道在于知有过失不合礼之处就及时改过从善,即使自己行为规范合乎礼,最后复善本性,回归诚体。“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4]99。通过复卦的改变,进行反方向的迁善改过的过程,使刚健诚心重新回复至正道,即达到无妄卦的天地大德流行之境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诚”动与静的性质可谓源自于对《周易》的分别解读,“诚”之通天命与立人极的架构与惩忿窒欲、省思改过的修养方法皆存在周敦颐对《周易》内涵的发微,可见濂溪“诚”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周易》息息相关、脉脉相通,其对《周易》新的诠释运用于“诚”亦对当下“诚”内在意蕴的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