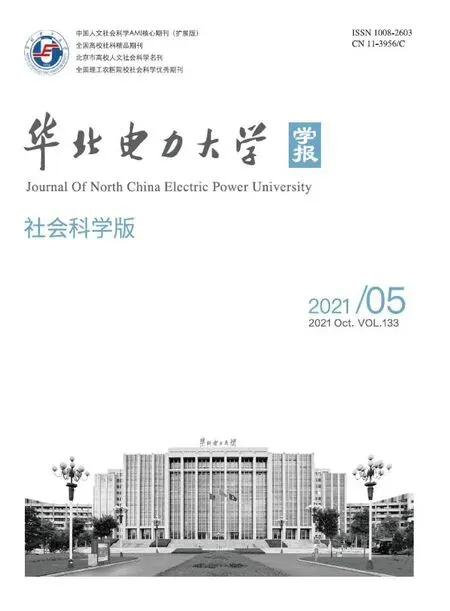族群与政治:唐代对外交往中的文化互动举隅
2021-12-07韩婷
韩 婷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唐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唐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同时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往来。李渊起兵时正值隋末各地豪强拥兵割据,鉴于实力薄弱等多方原因,李渊父子以太原和关中为根据地,北向少数民族区域霸权政权突厥称臣,对内废除隋末苛政,不断向关东进兵,铲除地方割据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增强自己的实力,最终实现中原一统,开始经略边疆,一统中国的宏业。李世民更是凭借骑兵劲旅和壮大的实力相继平定了边疆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的割据统治。其后,历经高宗、武后、玄宗等进一步经略边疆,使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以中原为核心,周边少数民族为辐射,疆域空前扩大的唐帝国,其治边政策相对开明,对周边民族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民族关系上既有武力征讨,又以和亲、赐姓名、会盟、朝聘、质子宿卫、封授、互市、招抚、设置羁縻府州等和平方式为主。在诸多政策背后携带与附着的文化交流在更为广博与深刻的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宏伟大厦,同时对唐代中原与边疆之间关系的处理与应对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成为唐代边疆文化政策的闪光点。在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唐王朝秉持与边疆民族往来基础上更广泛的开放与交流,是唐王朝对外关系的进一步拓展,文化因子在外交往来中的广泛参与,为唐朝的发展构建了一个相对和谐的外交往来关系网络。
一、意趣相投:儒家文化的动态互动
唐代在文化上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唐长安城里以各种身份居住着不同族群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包含使节、质子、留学生、学问僧、宾贡进士,甚至是昆仑奴、僧祇奴、胡姬以及各色商人等,长安一时间更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整个唐代的对外交往中,广泛的文化参与和文化互动,促进了族群间的政治往来,同时也刺激了文化表现形式的进一步丰富多彩,常常为族群间的交往注入生机和活力。儒家文化作为核心文化基因,在与周边族群的动态互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与吐蕃、新罗、高丽、百济、日本等周边地区的交往过程中。史载,贞观十四年(640):“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两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1]6153学舍规模之大,学员人数之多达到相当规模。
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2]667至开成二年(837),渤海国随王子大俊明入朝的留学生十六人请为生徒,文宗准其留六人留唐习学。[2]668无论是书籍的流通,抑或是人员流动,在唐前期与后期渤海地区都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多有慕学。
三韩地区,史书常言高丽之俗,尤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3]5320新罗女王真德,曾于贞观二十二年(648)遣其弟与子入朝,其弟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之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3]5335-5336永徽元年(650),真德又遣其弟入朝报大破百济,并织锦作五言诗《太平颂》以献。[3]5336至垂拱二年(686),新罗王政明亦遣使入朝,并“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3]5336据《唐会要》,至唐代后期,新罗仍保持与唐在儒学上的交流,开成元年(836),新罗请留住学生,准员两人;开成二年(837),准还本国的在唐新罗留学生达216人之多。[2]668可见长期以来,新罗皆保持向唐派遣留学生的交往惯例。
日本国亦好经史,解属文,遣使来朝多请儒士授经。其使在唐所得锡资多市文籍而归。同时多遣入唐使和留学生至唐交流学习,甚至自愿留而不还。
南诏与唐朝基本保持着和好的关系,但同时也表现为依附与分离的动态变幻。南诏亦颇慕儒典,唐王朝许其“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4]6289韦皋领剑南时,南诏自请以大臣子弟为质,韦皋“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4]6276甚至有以战中所虏儒士为师,格外爱重与信任,乃至任其为清平官者。《旧唐书》载南诏王阁罗凤命战败被俘的巂州西泸县令郑回教授其子习儒学。至异牟寻即位,又令郑回教授其子寻梦湊,待郑回以师礼,且以郑回为清平官。[3]5281
唐与吐蕃之间的儒学往来,往往是建立在和亲的基础之上,由和蕃公主充当文化传播的纽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交往惯例中的一个面向。贞观十五年(641),吐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3]5222高宗即位,吐蕃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3]5222此皆建立在文成公主入藏的基础上。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强化与周边族群的文化纽带,“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2]667至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2]667亦是建立在和蕃公主的和亲基础之上,并且此次围绕是否应赐经籍于夷狄,引起朝堂上的一场讨论。秘书正字于修烈上书极谏恐资其智,认为不可。[3]5232侍中裴光庭反对此说,赞成赐书,以其“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修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2]667玄宗最终采纳了裴光庭的建议,可见唐王朝从心态上是认可文化互动在族群交往中“混一戎华”的教化之用。
儒家文化的动态互动在整个唐代的治边与外交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唐与吐蕃、新罗、高丽、百济、日本等周边地区的交往过程中多有体现,学界历来关注较多,亦有丰硕成果,此不赘述。
除儒学典籍赐予往来,派遣留学生等与儒学紧密相关文化往来外,唐王朝在对外往来中,也十分关注族群兴趣爱好,志趣相投的互动更利于打开良好的对外交往局面。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兴光卒,玄宗“诏赠太子太保。仍遣左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璹等金宝及药物等。”[3]5337此次使臣的选派以善讲儒家经论的刑璹为吊唁、册封主使,以善于弈棋的杨季辅为副使,即是投以新罗人的兴趣爱好,从结果来看,达到甚至超出了预期效果。可见文化外交的成功。大中二年(848)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3]620因其善棋,便在外交活动中安排对弈博棋的活动,是对双方意趣爱好的重视。
每个族群有自己独特的族群特性,即地区的社群实践以及社群这个实体所造成的地区文化中人情交往的仪式,共同遵从的习惯,地理环境造成的生活方式,以及本土化的文化习惯等等,造成地区的“共同生活”所诞生的地区文化,成为决定族群的主要元素。在处理与边疆地区民族群体关系时,因俗理边,构建比政治实践更广的文化实践区域,抓住族群政治文化习俗,建立超政治的文化族群,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二、“爱之如一”:尊重族群的特定政治文化习俗与心理
唐王朝与周边族群交往中时常借助其他边缘文化的媒介与桥梁作用,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
隋末唐初,中原丧乱,突厥一时成为雄踞东亚的强大军事霸权力量,中国之人多有奔逃突厥之地,史称“突厥强盛,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2]1687“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3]5153,各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以求与其保持相对和平,并借其势力争夺天下。“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越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5]突厥亦乐于收纳各地方割据败逃势力,借此平衡和控制对中原的相对优势。一时之间,突厥政治态度的向背,直接影响中原地区的政治局势。唐初,局于实力亦采取对突厥称臣的策略,李渊“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3]3突厥始毕可汗“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3]5153据陈寅恪考证,唐初高祖称臣突厥当为太宗李世民主导。而实际上,唐初几次突厥进犯事件,唐王朝或小有胜利,多无力制衡而以金帛优容之,武德年间的多次突厥进犯危机最终也以太宗为主导得以解决。太宗个人的国际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核心策略是与突厥首领结为“香火兄弟”,刑马歃血会盟,受授鼓纛,故而得以有固有之中国人身份和随突厥法为突厥人的双重身份认可。[6]此时,唐王朝在与突厥的关系上处于守势。太宗从突厥族群的政治文化习俗与心理出发,用其习俗约为兄弟,在此基础上,示以恪守誓约的诚信话语体系,以安边。如“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被约深入吾地?’”[3]5156“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同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3]5156太宗对突厥使臣说“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虽尔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3]5157实际行为上也敢于以一国之君的身份身驱前阵,甚至是单骑直入,“驰六骑幸渭水上,与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3]30“太宗独与吉利临水交言”“又幸城西,刑白马,与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纵突厥部落尽叛,六畜皆死,朕终示之以信”[3]5157-5158随着唐政权的巩固以及“贞观之治”的发展成效,对突厥的防御随之转变为进攻。太宗抓住突厥部落离叛,吉利与突利不睦,遭逢大雪之战机,一举征服东突厥,将其纳入版图,设置羁縻府州及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治理。
军事政策和政权实力虽发生了变迁,但处理族群关系时,太宗仍尊重边疆民族的政治风俗习惯,保持其一贯的超政治的文化族群信任话语体系,“爱之如一”“示以诚信”的心态。“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自渭水曾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3]5159平定突厥后,围绕实施怎样的安边之术,太宗与其大臣进行了一次探讨。[3]5126分歧有三,其一,完全分其种落,散居各州县,化为百姓使其耕织。加户之利,塞北常空。其二,以温彦博为代表,建议准汉武故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全其部落,保其习俗,加以抚慰,置都督以统之。实北境之地,示无猜之心。其三,以魏征为代表,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强其卑服,我弱其寇盗,居于肘腋之地,必为祸患,强烈反对安置突厥之人于河南之地,但并未明确提出安边的具体策略。最终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其中既有太宗对国家发展的自信和自己独特的政治眼光与见识,也不可或缺的存在有强烈的示之以信、爱之如一的情感因素。魏徵所言是过去历史展现的边疆与中原关系的事实总结,其不但是中原与边疆关系的内核实态,实际上也是所有政治军事实体之间的较量实况。太宗清晰的明确这一事实,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太宗个人积累了丰富的与边疆民族交往的经验,对边疆民族的政治文化心态有自己的认知,从太宗处理与突厥关系中的几次辞令可以看出,太宗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中十分注重结以盟约,其中包括政治层面的盟约,也包含私人情感方面的盟约,强调示以恩信,构建中原与边疆族群交往实际中不同仪式的同等诚信话语体系和行为姿态。
史载“入居长安者数千家”,[3]5163贞观三年(629),户部奏称“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3]37中原与边疆民族的之间的超政治与地域族群融合卓见成效。之后整个唐代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延续了前代及唐初贞观故事,继续保有和平的联姻和亲、册授、互市、朝贡等往来模式,同时也不乏一定的边疆冲突与侵扰,始终坚持赓续太宗理边过程中的诚信话语传统。边疆民族与中原的关系继续在此消彼长的整体趋势与格局下相互往来。
此外,太宗于赐薛延陀的玺书中也道“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无异。”[3]5164唐德宗时期,为抵御吐蕃,调整了对南诏的政策,由西川节度使韦皋具体实施。韦皋经过一系列运作,最终恢复了南诏对唐的归附,会盟并连兵抗击吐蕃。贞元十一年(795),唐朝派册南诏使,颁“贞元册南诏印”。在印章材质的选择上,中央朝廷听从韦皋的建议,从蛮夷所重,以传示无穷,故赐印铸用黄金,以银为窠。[3]5283这是唐后期延续和继承充分尊重族群政治文化习俗的对外交往惯例的自觉选择。
在理边过程中也常将诚信理边的话语体系赋予宗教色彩。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以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乞力徐相约两国和好,朝廷发使者与乞力徐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孙诲欲邀功,奏吐蕃不备,朝廷使赵惠琮往诏崔希逸发兵击吐蕃。战获胜,孙诲与赵惠琮皆得厚赏。然崔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尹,行至京师,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3]5233可见对于歃血刑牲献祭的盟约守信是带有宗教约束成分的,不守约可能遭神灵惩罚。
三、神祇共享:族群宗教信仰在理边中的广泛显现
唐代对各类宗教兼容并蓄,允许其传播,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得以传播发展。唐代佛教已完成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各种佛教宗派,因而与道教、儒学并称“三教”。武则天时还组织学者二十多人,编纂《三教珠英》。在浓厚的宗教社会背景下,宗教因素的参与在唐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往来中屡见不鲜。
(一)道教和景教在族群交往中的参与
武德七年(624),高祖遣沈叔安往高丽册封高丽王高建武,并“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3]5321天竺国属国伽没路国遣使随唐出使天竺使臣王玄策入唐贡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3]5308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和好,西川节度使韦皋命巡官崔佐时到达羊苴咩城,异牟寻使其子阁勤及清平官等共盟于点苍山神祠。南诏与唐形成对吐蕃的犄角之势,常连兵抵御吐蕃,[3]5282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对唐而言,实现了“断吐蕃之右臂”。[1]7505代表唐王朝的崔佐时与南诏此次会盟选于苍山神祠,是充分认识到会盟在有宗教意蕴的神圣空间举行可加持会盟的神圣性和稳固性。
5、6世纪左右,景教已传入中国北方。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永明寺》条载,“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奏”,[7]235又称,“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7]235-236所谓大秦国沙门,指的就是经景教徒。有纪年可考景教来华在太宗贞观九年(635)。根据唐代景教徒《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8],635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携带真经到长安“译经传道”,当时称作波斯经教。唐太宗派人将阿罗本迎到宫中。638年,允许阿罗本传教,并批准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2]864因阿罗本从波斯来中国,故将景教寺庙称为波斯寺。高宗时又允许在各州立寺,碑称“高宗纂祖,更筑精舍,和宫敞朗,遍满中土”。开元七年(719),拂菻国主就曾遣其国大德僧作为使者,至唐朝贡。[3]5375745年,唐玄宗以景教经典出自大秦国,下令改波斯寺。[2]864
(二)摩尼教在唐与回纥交往中的使者身份
在唐与回纥交往中,摩尼教以使者身份介入在史籍记载中俯拾皆是。波斯宗教祆教在北朝传入内地,摩尼教则于延载元年(694)传入。隋唐时期不仅允许其传播,并给予礼遇,设置萨宝管理祆教事务。而摩尼信徒人数更多。史载,元和元年(806)“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湩酪。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1]7638宪宗元和二年(807)春,“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3]420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9]后来、荆、扬、洪、越等州也有摩尼寺。元和八年(813)十二月,“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3]5210-5211宪宗时,回鹘屡请尚公主,宪宗因资费过多,未得核准,回纥借此为口实对边州多加侵扰,宪宗于是欲借摩尼的宗教力量以得缓期。“回鹘屡请尚公主,有司计其费近五百万缗,时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许。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命宗正少卿李诚使回鹘谕意,以缓其期。”[1]7730借用宗教力量,摩尼之口影响回鹘决策,当是中原王朝深思熟虑认为可行之策。至元和末年,宪宗才以回鹘有功王室,西戎边患,求之弥切等因许以妻之,但终宪宗一朝未行册定和亲公主。从元和八年(813)请和亲至宪宗崩,先后近八年未行和亲,可知,此次借族群宗教信仰理边的策略是成功的。至穆宗即位,长庆元年(821)回鹘遣“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3]5211
“会昌三年(843),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3]5214-5215其亲信包含摩尼在此次往来中扮演什么角色,史书并未细说,但该年中原对回鹘的军事斗争获得胜利,迎回太和公主。武宗下制曰“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3]594这既反映了宪宗和武宗个人的宗教态度与政策,同时也展现了族群政治权力和实力对本族群抑或是跨族群的宗教之兴废产生直接影响。实际上武宗下敕制大规模灭佛尚在会昌五年(845),可见武宗于会昌三年(843)整饬摩尼与唐回的政治军事往来变化密切相关。
仆固怀恩叛后,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军进兵唐边州郡县,郭子仪率军数次击败之,仆固亡,诸军退散,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部请降,郭子仪亲入其阵,执其手责以负约,回纥请共追杀吐蕃,于是郭子仪与回纥盟约咒誓,回纥云发兵之时有巫师两人言“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3]5206以显见郭子仪并盟誓合巫师所占,颇有应验。郭子仪此次与回纥之盟誓亦颇有几分宗教蕴涵。可以想见族群宗教文化深刻影响族群控权者的决策。此次合军追击吐蕃获得大胜,唐朝也付出了大量的金帛财物以犒赏安抚回纥。对回纥的纵容与优赏,大大增加了唐王朝的府库压力和回纥轻视中原与贪婪之心,此是他话。
(三)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动态互动
佛教在唐王朝与边疆和海外民族的交往中,也常常扮演者媒介的角色,且在诸多宗教因素中明显更具有世界影响力。这得益于佛教传入中国后获得的极大发展。
唐与吐蕃的往来中佛教的参与呈现出反复的特点,这与藏传佛教自身在吐蕃地区发展的历史阶段状况有关,同时也受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状况的影响。肃宗元年(761),“吐蕃遣使来朝请和,敕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宇寺为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须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从之。”[3]5236-5237实际上,在唐与吐蕃的八次会盟中,[10]187围绕会盟的具体地点与仪式过程的选定问题,唐蕃有过多次较量与交锋,此次不选佛寺并非其长期既定原则。如永泰元年(765)三月,吐蕃请和,唐代宗“遣宰臣元载、杜鸿渐与蕃使同盟于于兴唐寺。”[3]279大历二年(767),代宗遣“宰臣内侍鱼朝恩与吐蕃同盟于兴唐寺。”[3]286-287建中四年(783)的清水会盟,唐以陇右节度使张镒为会盟使,吐蕃以尚结赞为会盟使,升坛为盟,祭以三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3]5248先后几次会盟对是否于佛寺或向佛盟誓,吐蕃的态度不尽相同。这其中可能存在会盟史臣个人的抉择与观念,同时选择盟誓之地也是政权实体之间实力的较量,背后也包含诸多宗教与文化习俗的潜在力量与因素。
佛教是唐蕃交往中重要的交往面向。建中二年(781)三月,“以万年县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持节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2]1734既作为出使吐蕃使团成员,又成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互濡染的路径。贞元十三年(797),“吐蕃使臧河难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等五十四人来朝。”[3]5261体现了佛僧作为使团成员之一的交往史实。元和十五年(820)秋七月壬戌,穆宗令“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3]480长庆四年(824)九月,吐蕃遣使向唐求《五台山图》。[3]512(“长庆四年遣使求《五台山图》。”[2]1739)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一次高潮。寺庙林立,僧侣若云,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有僧侣三千余人。唐德宗时,合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寺院的兴旺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唐武宗遂于会昌五年(854)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即“会昌毁佛”。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即位,又再兴佛教,规定五台山的僧数可达“五千僧”。实际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僧,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五台山的突出特色是既有青庙,也有黄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并重,青庙和黄庙相互比邻,共同发展,这在佛教名山中是独有的现象。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时敦煌归义军第四代节度使曹元忠营造的功德窟,内有巨幅壁画《五台山图》,全图长13.45米,高3.42米,面积达45.999平方米,[11]寺院林立,香客云集即反映了唐、五代五台山的地理位置、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风貌。由此推测,吐蕃所求《五台山图》极有可能与敦煌壁画之《五台山图》反应同一主旨,即佛教的兴盛,这其中当是既包含藏传佛教,也包含汉传佛教。唐与吐蕃之间的这一交往恰体现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唐代的传播与交融,也反映了宗教在族群往来中的参与。①参见[美]罗伯特·M·詹密罗著,冀培然编译:《晚唐至金国初期五台山地区的佛教状况》,《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第152-157页。
另外,贞元十八年(802),骠国遣悉利移跟随南诏使者重译来唐朝贡,献其国乐十曲和乐工三十五人。[3]396其国尚佛,所献乐曲皆演绎佛教经论之意。[3]5286也是对外交往中音乐艺术与宗教文化的结合产物。新罗(朝鲜)、北印度罽宾国、南天竺(南印度)、中印度、日本等都曾有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僧侣,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从唐代中外佛事交流中足以看出五台山在海外各国民众中的地位,俨然成为国际宗教文化基地。佛教文化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和纽带,不但有入唐僧众,亦有中国僧人出唐求法或传法,对中国与亚洲各国间的沟通和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一些虽为个人行为,但其在本国与他国所受到的礼遇与重视,包括政权统治者抑或参与其中,都充分展现了唐王朝与周边和海外民族交往中的佛教参与。
由此可见,在处理对外交往关系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唐王朝的角度还是从边疆或海外民族的角度,都十分注重宗教因素的参与和影响。无论是族群原始宗教信仰,还是道教、摩尼教、佛教,虽信奉之神不同,但同样相信神灵的护佑作用和超越性特征,同时借用诸神之力实现和服务于其现实目的。这一神祇共享、兼收并蓄的思想在促进族群性宗教地域化,地域性宗教全球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族群间的政治往来。
总体来看,唐代的对外交往是一个复杂多样、因时而变的动态系统。儒家文化交流互动在整个唐代的对外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族群政治文化习俗、族群宗教信仰、族群生活业余爱好,相较于儒家文化的广泛和深入而言属于边缘文化,在理边与对外交往中,这些文化元素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使不同族群之间的往来以一种自然濡染式文化交往方式存在,其发挥的不够显现实则深刻的影响以及其给文化带来的交融与丰富是族群交往的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总体而言,无论是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儒家文化,抑或是边缘文化,在不同地域族群和政权族群的往来中,总有文化因素贯穿始终,使得族群间的交往超越政治与地域而营造出文化认同与互动,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形成全新的文化族群认知。唐代是中国文化辉煌的重要时期,这毫无疑问与唐代开明的边疆和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分不开,为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的打造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而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经过历史时期的不断交流、融会发展积累起来的,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包容性、开放性、独特性和与时俱进性。同时文化互动为国家对外交往中和平、和谐的周边关系贡献力量。在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海外诸国的往来中,通过彼此之间的文化互动,有形无形中共同构筑了七世纪至九世纪浓墨重彩的民族交往史,这也正是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