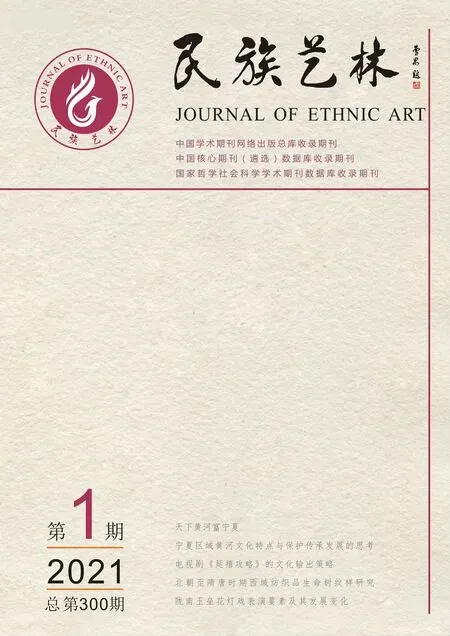电子游戏中的“身体技术”:观看、互动与控制
2021-12-07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电子游戏”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的迅速发展,得益于技术的迅速迭代和各个阶段成功的商业化策略。在今天,谈起“电子游戏”,甚至仅仅是提及“游戏”二字,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火爆的画面、震撼的音效或者玩家的呼喊带向了虚拟的世界,仿佛那里就是现世生活的彼岸。但若要进一步反思“电子游戏”的社会文化意涵,就要从这种幻觉中下线,重新审视电子游戏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类学通过比较世界各地的游戏传统,考察了游戏的文化性与历史性,在其作为人类行为的普遍意义上,提供一种基于“玩”的经验洞察。[1]当代流行的“电子游戏”①,特指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游戏形式或游戏方式,是本文的讨论对象。考察电子游戏的社会文化性,需要以反思常识的眼光发现/恢复电子游戏表层叙事下的情境化体验,以免深陷技术话语和商业逻辑钩织的专业图谱,提出更切身的问题。
我们发现,电子游戏的体验是高度具身/身体化(embodiment)的,玩游戏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一种身体交互的实现过程,这意味着游戏对玩家的作用可能比人们想象得更为深远。当代的游戏开发深谙这一点,一款制作精良的游戏并非仅仅提供“玩”的场景,而是在玩的操作/行动过程中使玩家获得一种身体经验,或许是“瘾”与“快乐”的重要来源。由莫斯(Marcel Mauss)开启的关于“身体技术”的讨论,[2]提醒我们关注不同社会中,人们如何从对文化传统的习得中学会使用身体。身体技术是“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合成”[3],是处于不同文化或社会之中的“身体”(复数)对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表征。虽然莫斯之后的研究对身体表征社会规范的被动角色提出异议,为身体与训练的复杂关系扩容出更大的讨论空间,不是“身体被训练”,而是“通过身体训练”(如身体如何能动地塑造经验而不是相反),但“身体技术”作为讨论的基石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莫斯的洞见为线索,本文基于对游戏设计与玩家体验的分析,从电子游戏的视觉中心性出发,探讨身体在游戏中如何学习观看、动作反应以达成人-机交互,从而给玩家带来“玩”的体验与“控制”之感。
一、电子游戏简史:图像设备的重要性
电子游戏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研机构逐渐走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也是电子游戏的历史。
1962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史蒂夫·罗素(Steve Russell)等七名学生在PDP-1 型计算机上制作的《太空大战》(Space War),被认为是史上第一款电子游戏。运行这款游戏的PDP-1 型计算机是史上第一款商用小型计算机,配备阴极射线显示器。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两名玩家分别操作键盘上的几个按键,各自控制屏幕上的一艘飞船,互相发射火箭,胜负即以规避攻击、摧毁对手为判[4]。《太空大战》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是昂贵的计算机设备却使得这一阶段的电子游戏仅在科研机构中流传,大众层面的普及度不高。
直到1972 年,早期电子游戏业的翘楚雅达利公司(Atari)发布了一款名为“电脑空间”(Computer Space)的街机(Arcade,中译或为“拱廊游戏机”),运行于其上的《Pong》,最终让电子游戏逐渐升温,这也标志着电子游戏产业的兴起[5]。“电脑空间”以黑白电视机作为显示器,配备一个控制柄用于操作,而整个游戏机被制作成立式,常被置于人流众多的娱乐中心,故俗称“街机”。玩家通过投币获得玩的权限,单人或双人通过操作摇杆来控制画面。
此后近十年间,大量商业资本涌入电子游戏行业,疯狂逐利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了一场被称为“雅达利震荡”(Atari Shock)的市场大萧条,欧美游戏业进入了低谷。同时,80 年代初期的美国媒体界开始质疑电子游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了“电子海洛因”的说法,使这一行业因而背上了道德压力。但在大洋彼岸,任天堂(Nintendo)这家靠制作花札纸牌发家的日本老店开始在电子游戏业界崭露头角,该公司于1985 年发售的FC 游戏主机(Family Computer,在欧美市场称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简称NES,在中国俗称“红白机”)成为一时期内家用游戏机的代表,而发布于其上的许多游戏至今仍是玩家群体公认的经典②。家用游戏机不再配备专门的显示设备,而需要将游戏机通过视频线缆连接到家用电视机上,从此电子游戏成了普通人家客厅的新宠。到了90 年代初期,经过重新洗牌的欧美游戏业界重新崛起,以至于今。这期间又有着更多游戏公司的生死存亡、全球范围内的潮涨潮落,以及政府监管和资本运作的诸多变迁。如今随着计算设备的小型化及大众普及度的提高,电子游戏的运行设备变得更加多样。
实际上,在关于电子游戏的诸多争议中,以“家用游戏机”或“街机”为代表的游戏方式并不为所有玩家接受,甚至这类游戏方式在中国内地一度是小众的。部分原因正在于电子计算机普及的背后其形态的演变,这衍生出了目前多样的游戏平台,并且形成了彼此有别的游戏体验和“游戏文化”。这些平台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手机、专用游戏掌机等,它们所提供的游戏体验迥异于传统家用游戏机或街机。这些差异一方面造成了游戏业界和玩家群体内部的争吵,也提醒我们关注造成这些差异背后的技术、市场和政策等方面的因素。但是,虽然游戏机形态及与其相关的游戏体验区分出了不同的电子游戏类型,但根本上的游戏方式仍是如一。以家用游戏主机为例,其基本的使用方法是:通过线缆将游戏主机连接到电视或专门的显示设备上,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使用控制器(即游戏手柄)操控。更晚近的手机或掌上电脑则削减了更多物理层面的安装或设置,仅需使用手指在显示器上触摸。
以上关于电子游戏发展史及其基本游戏方式的梳理,并未涵盖全部的细节与分支,如此叙述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既有文献不乏电子游戏史资料,再次重复千篇一律的观点和材料意义不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上特别提到的事件和细节意在指出看似复杂、颇显神秘的电子游戏史当中一个值得深思的要素,那就是显示器/屏幕的重要性。从最早的射线显示器,到后来的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再到当下最为流行的手机屏幕,甚至方兴未艾的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电子游戏的一切游戏体验,都无法绕开图像设备。这是本文问题意识的出发点。
图像设备是电子游戏发展史当中的一个常量,因此“看到”成了电子游戏的一个基本特征。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讨论“电子游戏”并非是分析某一特定类型③,也不是在“游戏”研究的意义上探索“游戏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6],而是强调电子游戏普遍具有的一种人-机关系,即,电子游戏的身体性。
二、视觉与观看:物我关系的建立
当我们玩一款电子游戏时,不论是在哪种平台上,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必然要动用身体的视觉系统,也就是要看到。近年来电子游戏在国内受到了更多资本和玩家的青睐,一些媒体和玩家群体也重提其“第九艺术”的说法④。在论证电子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合理性时,研究者通常的论点是“综合性”,即电子游戏是综合了过去八大艺术的新的艺术门类,即包括文学、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电影和电视。在当今时代的电子游戏中,玩家也很容易就能指出所谓“八大艺术的综合”。
以2015 年由波兰游戏工作室CDPR⑤发布的《巫师3:狂猎》为例。游戏改编自波兰当代的流行小说《巫师》系列,游戏忠实于原著的情节、人物和台词设计,玩家不仅能够重新感受小说的故事,还能从画面上感受到文字隐含或无法描述的情境;宏大且丰富的配乐使得猎魔之旅充满战斗的激情和漫游的闲适;主角杰洛特优雅的剑舞,使即便不善动作游戏的玩家也能随意舞出一套赏心悦目的连招;作为一款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就是游戏主角,不管是控制、代入还是成为主角,玩家就是提木偶线的人;而雕塑与建筑则直接呈现出中世纪城堡、村庄和城市的风貌;至于游戏当中不断穿插的CG 播片,单独拎出来也都是制作上乘的影片。当这些要素同时呈现在一场战斗、一段骑马漫游或一番与NPC 的互动当中时,玩家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综合”感,历史的、幻想的、遥远的……艺术的事物同时出现。
但是,且不论是否将某些艺术的要素组合起来就能够生成新的艺术,至少我们看到电子游戏所谓对“八大艺术”的综合仍然是通过看到来实现的。文本或以字幕的方式出现,或通过画面直接表达;音乐的目的是烘托特定场景的氛围,画面上进入某个场景也伴随着背景音乐的自动跳转;人物动作的判定要通过画面的显示才能为玩家所感知;为角色换装不仅是提升角色属性的需要,也同时表达了玩家的审美倾向;画面中的建筑物与雕塑,可以只是充当背景板的贴图,也可以是需要发生互动的部分;强制或可以跳过的播片,调节游戏节奏也推进游戏剧情,或者只是掩盖游戏加载的缓慢。总之,重要的仍然是看到。
视觉使电子游戏的“互动性”成为可能。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款电子游戏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的,即便是近几年许多实验性质的独立游戏尝试仅利用手机的陀螺仪来操作游戏内容,也至少需要玩家把手机握在手里左右晃动。电子游戏的互动性,是基于计算机语言产生的,也就是指令-运算-反馈的基本逻辑⑥。比如在经典的格斗类游戏中,玩家利用控制器上的摇杆和按键操控游戏角色,不同的按键和按键组合代表不同的“招式”,两个或多个角色就是通过过招进行较量,最终决出胜负。在这个过程中,玩家通过控制器给出指令,经过内部计算机运算后,反馈通过画面上人物的动作表达出来,而玩家何时出招(何时给出指令)、出什么招(给出什么指令)、如何判断战斗形势等都要通过画面所呈现的情况来判断。再一次,重要的仍是看到。
如果格斗游戏的战斗过程无非就是数值的计算,用1 把算盘、1 张白纸和1 支铅笔就可以玩,何必要做成电子游戏?的确如此,电子游戏实际上就是用电子计算机和显示器替代了算盘、白纸和铅笔,电子游戏早期阶段的角色扮演游戏对桌面“跑团”游戏的电子化是极好的一例。而视觉体验让计算变得可感,大大提升了思维与情绪情感的关联性以及主体之间“感同身受”的互动可能。后来的电子游戏的发展,计算机所负担的不只是替代大量的数值运算,还让游戏过程本身加入了更多可操控性,玩家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丰富,并且能够直观地通过图像实时呈现出来。电子游戏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此。
约翰·伯格对“观看”[7]的分析有别于艺术鉴赏的“无功利”传统,在他看来,观看是先于语言的人类本能,我们首先是在观看中确立物我关系,进而构建起对个体周遭的认识,因此不同的观看方式就体现出不同的物我关系。从这样的思路出发,他指出,欧洲中世纪油画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一般的人物画或风景画往往表露出阶级心态和财富占有关系。当照相术取消了透视法绘画中的上帝视角,其复制能力又彻底改变了此前画作的意义,现代广告就能够按照市场经济逻辑构建起消费与财富的关系,用“消费”许诺美好生活的幻梦。以约翰·伯格对“观看”关系的文化批评考察游戏的观看,可以得出与一般电子游戏史叙述全然不同的理解。
在梳理电子游戏的视觉发展时,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沿着技术演进的脉络展开,如单色到多彩、单像素到高分辨率、低刷新率到高刷新率、平面俯视角到3D 第一人称,等等。随着画面技术的提升(背后是硬件能力和设计观念等一整套的不断革新),电子游戏的视觉呈现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早的玩家只能控制几个像素点的位移,而如今电子游戏的虚拟或增强现实技术甚至可以反哺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其他领域。但从观看的角度思考,实际上玩家的视觉体验已经从识别图像在人为控制下的变化,即人的行为改变图像,发展到图像反过来主导玩家行为,如在许多第一人称视角的电子游戏中,玩家通过画面内容决定操作行为。后者正类似约翰·伯格关于广告观看中物我关系的看法,并且其边界已然模糊。
类似广告许诺一种美好的未来生活一样,电子游戏同样提供了某种遁世隐逸的期待或现世欢愉的可能。似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的或在不远未来的人类将有能力从肉体的躯壳和自然的枷锁中逃逸,人为地创设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是自身与世界的主宰者,这正是赛博世界/控制论(cybernetics)的永生梦想。此处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理解所谓“虚拟-现实”的亚文化实践时,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式的“霸权-抵抗”批评结构,玩家并非是在一种“被蛊惑”的意识形态欺诈下“逃避现实”,而是在物我关系的不断重建中有意识地行动。图像营造出的感官阵营让玩家体验到的并非“不会存在”的虚无,而恰恰是“可能存在”的行动空间。换言之,游戏(中)的观看体验强化了玩家对图像的认同。
然而,电子游戏塑造观看经验的第一步是消费。电子游戏厂商、游戏制作者以及游戏行业的各生产与流通部门,为电子游戏市场持续供应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游戏产品,用户/玩家则需要通过消费,搭建起由游戏机、游戏软件、显示器、控制器以及电力、互联网等要素组成的物理框架,为开启游戏的具身体验创造必要条件。
三、互动:身体动作与运算指令
玩家“进入”电子游戏,包含着两个连续又一体的过程。一是电子游戏本体的数据进入游戏机的处理器,即电子游戏本身被启动了。这个过程会通过图像设备呈现出来,在较早的时代就是显像管电视机满屏的雪花点变成了每个游戏不同的启动画面,上面罗列着开启游戏世界的诸多指令选项,比如“新游戏”(New Game)、“载入游戏”(Load Game)、“游戏选项”(Options)等,以及游戏的标题、插画,主题音乐此时一般已经响起。二是玩家的身体成为整个游戏过程中指令系统的一部分,开始通过控制器向“游戏”发出指令。玩家通过操作控制器上的按钮、摇杆、内置的运动感应器、图像感应器、速度感应器等,向运算系统输入本质上都由0 和1 组成的电信号。在这个意义上,玩电子游戏实际上是运算指令与玩家身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互动关系。
游戏机在做判断时与人类的逻辑不同,它的判断系统是电子游戏程序/软件。当玩家发出指令后,处理器根据指令迅速在游戏程序中“跑”出结果,再将结果输出至图像处理器,最终图像设备将图像处理器的结果以像素点的排布、明暗等呈现给玩家。因而在整个“进入”的过程中,玩家所感知到的,大多是视觉上的信息,并且往往是表示语义的普通文字、形象直观的图标或画面的变化。玩家对这些图像化了的指令进行选择,也以画面发生的变化来判断下次的指令选择和发出指令的动机。如果对于首次进入某款或某类电子游戏的新手来说,阅读文字信息和观察图像还是进入游戏的第一步,那么对于老手而言,迅速判断并准确选择则是习以为常的操作。新手与老手在“发出指令”这个行为上的差别,就具体涉及玩家的技术、经验、反应能力等要素。电子游戏设计中预设的“学习成本”,就是玩家在初期游戏中需要建立起判断系统的成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时间成本。
2018 年有一款精致的独立游戏风靡全球,名为《空洞骑士》(Hollow Knight),该游戏以“银河恶魔城”玩法为核心,类型上属于2D 平台战斗类。玩家要控制一只眼神空洞的虫子骑士,在一个失落的虫子王国中探索旧日的秘密以及自己的故事。故事的剧情被拆解、分散到整个游戏世界的各个角落,而游戏世界的地图则需要玩家在探索中逐渐解锁,并且在庞大的世界中各个区域的特色不同,不同区域会遇到不同的敌人和任务。玩家的探索没有直接的指示,整个故事剧情的推进因玩家探索路径的不同而不同。这是“银河恶魔城”一类电子游戏的特色。但是让这款游戏饱受好评的并不只是其“探索”的玩法,还有战斗的“乐趣”。《空洞骑士》的战斗十分“硬核”:玩家需要灵活地左右移动、跳跃和冲刺等,以控制进行攻击与防御的位置和时机,需要适时积累能量并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技能,需要迅速对敌人的移动或攻击做出反应,需要研究敌人的攻击模式、范围和阶段,等等。由于游戏世界是在探索中展开的,(对于新手而言)进入某一战斗区域或遭遇不同等级的敌人是很难预知的,加之“硬核”的战斗要求,玩家们常感叹能在这款游戏中如鱼得水的人“熟练得让人心疼”。
“熟练”就是关键。要达到熟练的程度,玩家只能不断试错,也就是不断在“游戏结束”(Game Over)以后再次进入战斗,在一次次耗光生命值的过程中慢慢摸索敌人的“套路”,最终有针对性地控制移动、释放技能,以保全自身,消灭敌人。玩家在如此玩游戏时,试错就是不断重复发出移动、攻击等指令,并且逐渐学习发出指令的时机。而摸索、学习的方法就是:仔细看,并反映到手指的操作上。试错的目的是摸索规律,通过仔细观看和尝试,寻找敌人的运动和攻击规律,然后把这些“知识”作为最终战斗的基础之一。最后,“熟练”形成一套身体反应。虽然一场战斗的打法可能并不唯一,但每一个通关的玩家都是基于一套身体反应来完成的。可以说,玩家的身体被异化为指令系统的一部分。虽然所有的游戏指令本质上都是“开”和“关”组合排列的电信号,但是不同电信号的发出却是由身体不同的动作来施动的。轻点、重按、双击、持续点按、触摸滑动、倾斜……以及不同动作的组合。身体的动作及动作组合构成了一套指令集,而电子游戏中设计的指令系统则是对这些身体动作的编码。
换言之,游戏身体动作的形成也可谓游戏-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身体化。电子游戏的诞生以及后来电子游戏的设计开发,其基础是“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提出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是“输入设备—CPU—输出设备”。比照这一框架,玩电子游戏的基本逻辑便是:
控制器——指令——操作/控制/输入
处理器——运算——计算/判断
显示器——反馈——移动/变换……
这只是单一操作的基本框架,在实际的游戏过程中,如此进行的“指令—运算—反馈”数量巨大,而且每一次操作的耗时不一,有时也许多个操作同时进行,乃至程序内置自主运行的AI 也数量巨大、耗时不一、多线同时,更不必说多人同时在线游戏。这对游戏机的运算处理能力、图像设备的显示能力以及玩家的控制能力均提出了要求。
在最初的教学关卡中,游戏设计者往往或巧或拙地使玩家接受并熟悉某款游戏的指令系统,即教会玩家该游戏的操作方法。这一阶段的游戏难度一般较低,着重使玩家能够迅速掌握基本的操作。这些操作方法也会在游戏当中不时出现以提醒玩家,进一步提高操作的熟练度。这是电子游戏对玩家身体的一种训练,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些指令的操作,玩家在整个游戏周期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关于《怪物猎人》系列游戏的网络讨论中,“老猎人”们在向新玩家传授经验时会说:“真正成长的不是角色,而是你自己。”意思就是,优秀的玩家是靠着自身游戏技术的提高来获得游戏角色在数值系统上的提升的,比如角色等级、装备属性、社群声望等。
而自定义按键的功能,除了本质上是调整指令与玩家动作之间的匹配关系,也同时与玩家以往游戏经验或个人习惯相适应;所谓的“偏好设置”就是玩家既有的身体技术反过来影响游戏体验的例证。三大主机游戏平台⑦在手柄按键的设计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PlayStation 平台的手柄右侧按键为“上△、下╳、左□、右○”,Xbox 平台的为“上Y、下A、左X、右B”,而任天堂平台的为“上X、下B、左Y、右A”。从商业层面考虑,三家不同的按键设计可能与培养用户习惯以提高留存度有关,在此不表。对于具体的玩家,尤其是同时拥有多个平台或计划更换平台的玩家来说,重新习惯一套按键布局与其游戏体验密切相关,一些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操作可能在更换平台后制造麻烦。调整按键映射的功能——比如将Xbox 手柄上A 和B 键、X 和Y 键所对应的指令对调,便与任天堂平台的手柄按键布局一致了——为这类情况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功能看似是为迎合玩家需要或出于一定的商业考虑,但也提醒我们注意玩家习惯的韧性。玩家长时间在某一平台训练而来的身体技术,也会持续影响他们在其他平台的游戏体验。
回到视觉的问题上来,玩家之所以能够学习、接受并成为一套指令系统的一部分,视觉能力及其运用最后实现了人-机互构的闭环。玩家需要具备特定的视觉能力。观看电子游戏画面的某些技能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学会观察画面,什么要素值得关注,以及何时以何种方式注视某些要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子竞技上),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玩家的体验。玩家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比如要能够判断怎样的游戏画面是好的,怎样的风格是具有表现力的,这与游戏设计以及商业化有关。玩家还要学会观看其他玩家玩游戏,比如某位玩家的操作是否高级,某种战斗策略是否充满智慧,在此,电子游戏已经超出了它自身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媒介对象。
玩家需要具备视觉主导的一系列身体反应能力,游戏的愉悦感建基于身体训练之上,“玩”亦需要技术,比如脑手协调、肌肉记忆的形成、应激反应的灵敏度、空间识别能力等。玩家与电子游戏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工具之间的支配关系。身体本身在游戏中也被编码,在电子游戏的物理框架之中,玩游戏的人与提供电子游戏体验的机器之间实现了混合,整个游戏过程被“文本化”(textualization)了,成了一种并不新鲜的赛博格(cyborg)[8]。
四、控制:身体作为技术总体
赫伊津哈在100 年前的论述中强调“玩”(play)与日常社会生活的隔离[10]。按照他的观点,“玩”是纯本性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不受任何来自社会的文化的约束和要求,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按照“玩”本身的规则和秩序进行活动。游戏(game)相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纯然的快乐。“玩”似乎使人类在对“社会性”的严肃背负中,找到了一丝放松的间歇,并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之感。然而,这种哲学意义上“玩”可以通过游戏实现,游戏却不只有“玩”(因而不等同于玩),“快乐”的来源甚至更加复杂。在莫斯的意义上,电子游戏仍然表征着我们当下社会和文化的某些特定观念。电子游戏与身体的关系,持续再生产着我们当下对信息技术的信仰,而它的外表被资本、政策、观念等包装成“娱乐”“艺术”等不同的面目,实践着“社会权威”[9]对个体的训练。
如《空洞骑士》这类“硬核”游戏会挑选玩家。当下的电子游戏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娱乐产品,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社会生活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闲暇和耐心玩这类电子游戏,短平快的手机游戏占据整个电子游戏业界最大市场份额⑧,这一现象就从侧面说明了“核心”玩家的相对小众。努力完成这类游戏,不仅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接受训练并达到通关游戏所要求的身体控制能力则对玩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法做到的玩家被“拒”之门外。玩家群体在这一意义上的区分,与其说是个人游戏偏好使然,不如说是电子游戏本身就在挑选玩家。在游戏设计上,即是目标群体的设定。
而目标群体的设定,与游戏制作者对市场、资本和政策的把控有关,其背后则是对不同人群在性格、能力、兴趣、消费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判断,这些“设定”利用了我们社会对于不同人群特质的预设,先在地区分了受众。《空洞骑士》只是一个极小并且较为极端的分析案例,电子游戏类目纷繁,这也意味着身体控制方式的多样。在大型商业游戏公司的生产模式下,针对不同的玩家群体,比如女性玩家、儿童玩家等,游戏制作的目的和具体玩法设计迥异,它们分别“迎合”并强化着不同人群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在欧美电子游戏业界,分级制“保护”青少年玩家远离色情、犯罪等因素,而成年人则可以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不受约束。中国实行游戏版号制度,许多在国际上饱受好评但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游戏无法过审,而国内市场上一大批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赌博游戏却疯狂敛财,政策通过限制玩家的选择培育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玩家。
那么,玩家的乐趣何在?我们将“玩游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当玩家投身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时,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侠盗猎车手5》(Grand Theft Auto V,简称GTA 5)是美国Rockstar 公司于2013 年推出的一款角色扮演游戏。游戏场景设置在原型为洛杉矶城的Los Santos,故事主体是3 个黑帮分子于资本和政府之间从事犯罪活动。这款游戏在本世代的玩家眼中是一款“神作”,发售至今销量仍在持续增长,这相对于一般的电子游戏来说的确难以想象。使得该游戏受到如此热捧的原因很多,GTA 系列的长期口碑积累、高度自由的开放世界玩法、“犯罪”主题的吸引力、持续的更新与线上运营等等,特别是该游戏“真实”的体验感。GTA 5 的“真实性”同样包括了很多方面,如果要按照游戏研究者提出的“综合性”指标来看待它,它真实到“令人发指”。在一个网络论坛的游戏板块里,有一位玩家分享了一张从自己家窗户往外拍摄的照片,那正是洛杉矶海滩的景象。并列在这张照片旁边的游戏截图,是这名玩家在游戏中发现的,两张图像惊人的一致。其实熟悉这款游戏的玩家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GTA 5 的场景本身就是以洛杉矶和加州南部为原型,经过实地测绘以后建模创作的。因此,游戏中的高楼、街道、路牌、海滩、游乐场……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甚至几可乱真。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Ubisoft 公司出品的《刺客信条》(Assassin’s Creed)系列游戏中。当地时间2019 年4 月15 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栋建筑严重损毁。当世人哀号一幢人类文明结晶被毁于一场大火时,Ubisoft 公司宣布在其自家游戏平台Uplay 上限时免费向所有玩家赠送《Assassin’s Creed Unity》(中译“刺客信条:大革命”)。这款游戏的背景即设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其场景建模以真实的巴黎圣母院为基础,通过实地测绘完成,而在游戏中,玩家可以操作主角在这幢建筑的外墙上攀爬跳跃,也可以潜入其中。在现实中被大火吞噬的巴黎圣母院,永久地存在于计算机代码编制的世界之中。这几乎是电子游戏业界的高光时刻。
不过,如果游戏只是停留在对“拟真”的震撼,玩游戏与我们直接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又有何区别?除了由拟真技术所引发的崇拜,电子游戏还有何等的魅力让人沉迷?实际上,在人类微妙的情绪情感中,快乐亦可能来自控制。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如果我们想要聆听一段音乐、看一场话剧、参观某栋历史建筑或阅读一本文学名著,即便能做到同时进行这些“艺术”活动,完成这一目标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更不太可能让每个人都能轻易地做到;但电子游戏可以。如果再考虑到电子游戏对“幻想”的表现能力,日常生活就进一步失去了它的魅力。更何况,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每一个人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控制当中,任何行为的限度都被事先规定好了。但在电子游戏构建的世界中,不仅同时进行多种艺术活动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超现实地体验想象力,甚至成为“主宰”。最后这一点,正是置身电子游戏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最大的不同。
在电子游戏提供的虚拟世界中,玩家似乎是一切的最终控制者。玩家的指令控制着角色的行动,玩家的选择决定了剧情的走向,即便不满游戏当中的规则也可以选择拒绝游戏来体现主宰者的意志。而日常生活可能正好与此相反。于是,电子游戏似乎成了玩家逃离日常生活,追求纯粹自由与快乐的净土。“逃离”的期待,是许多电子游戏厂商进行营销的要点,也是许多玩家借由电子游戏安抚情绪的手段。然而,所谓的“逃离”是由控制来得到补偿的,是游戏世界里获得的“另一段生命”。
电子游戏的想象力终究受到当世时代和思想的限制。电子游戏尽力模拟现实的一方面就说明了这种倾向,犯罪、暴力、色情、赌博等无非只是让玩家在一个不必受到法律和道德惩罚的地方做一些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事情;即便是幻想作品,其精神内核也很难逃出旧有的思想范式,如果考虑一下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观念和信息技术逻辑,这样的质疑就更坚定了。不过本文试图说明的并不在此,这样的质疑在文化研究对亚文化的讨论中已经体现得相当充分了,而是意在阐释,电子游戏使我们无法真正逃离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控制进入对游戏世界的控制时,正好掉进了更深层次的受控状态,那就是电子游戏对身体的驯化。
最终,玩家对游戏世界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实现对个体外部世界的控制,不管这个外部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还是被想象为“彼岸”的电子游戏的世界。并且,由于电子游戏提供给玩家以“成长”的机会,在玩家的体验中,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是可以提高的。但是,这种控制的另一面是身体习得的游戏训练。当身体被异化为指令系统的一部分,它就成了一种控制技术或工具,而真正的玩家藏在屏幕背后。不过,身体并未结束。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技术亦是身体的一部分/延伸。[12]这再次重申了身体技术的重要性:身体作为人类的技术本身与总体。
“玩”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在玩的过程中习得社会规范、掌握某些生存技能,甚至按照赫伊津哈的看法,它奠定了人类文化的基石。[11]电子游戏是当代人类的新玩法,它在游戏的规则、工具以及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上发生了变化。视觉的主导性和身体的根本性是电子游戏有别于传统游戏的要点,而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当今人类观念的新窗口,从这里看出去,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或许就在我们的身体上。
注释
①“电子游戏”一词译自英文video game,后者也被称为digital game,因二者本质上都是指依托计算机技术实现的游戏方式,本文不作具体区分。除特别说明外,文中“电子游戏”均指video game。
②例如“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s),中译或为“超级玛丽”。
③关于“电子游戏”的分类,可参考《游戏概论》一书。
④严格来说,“第九艺术”这一复合词汇的所指充满争议。在不同的领域,这一概念或指“漫画/连环画”(comics)[13],或被当作本文所提的“电子游戏”(video game)[14],甚或专指“网络游戏”(online game)[15]。
⑤全称CD Project Red,是CD Project 公司旗下部门。
⑥即冯·诺伊曼提出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其基本结构为“输入设备-CPU-输出设备”。
⑦即Sony 公司的Play Station 平台、Microsoft公司的Xbox 平台和Nintendo 公司的掌机平台。
⑧据报道,我国2019 年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330.2 亿元,其中移动游戏市场占比6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