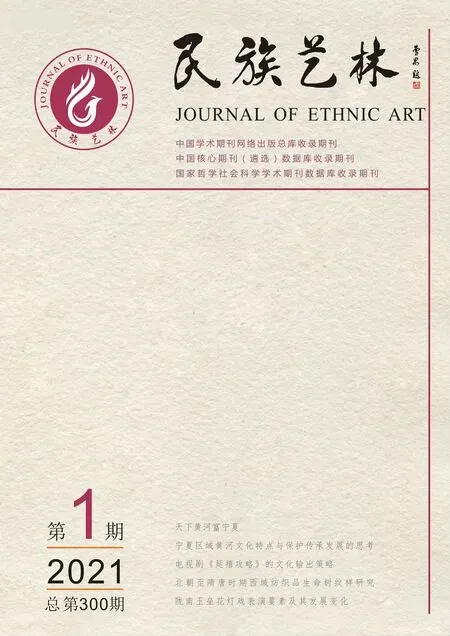诗意审美与乡土喻说
——李睿电影中的意象建构与文化阐释
2021-12-07刘晓东
刘晓东
(山东技师学院 数字创意系,山东 济南 250000)
旅美电影学人李幼蒸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一书中针对电影语言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西方传统的电影研究中,‘电影语言’并不专门指电影中的天然语言,而更多的是指电影作品中天然语言的以外的其他表达方式(主要是画面形象)的‘语言’之间的关联,因此大多数是用在譬喻意义上的。”[1]作为观众感知电影世界的本体存在,电影语言也在深刻影响着作品美学被感知的方式的构建。在李睿的作品中,大量兼具东方文化与地域属性的意象的使用将艺术的抽象处理成了生活具象的“景深”,进而使影像拥有了更宽广、更超脱却又更真实的视域,这种独具魅力的视觉标签在建立了其影像诗意的同时,更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作品意义的召唤。
一、马与鹤:卑微的当下生存与浪漫的死亡想象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言:“心灵的思索离不开形象。”作为在传统中国家庭成长起来的电影导演,借助马与鹤这两种极富东方哲思的意象的视觉化表达,李睿连通起了现实语境的反思与文化精神的自觉。
《周易》以“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方式来“假物”阐明我国生民累积生成的生存智慧。而马则因在生民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周易》时代的“假象”之物,马因之成为意象。[2]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为被寄予了无数内涵意蕴的马,因其俊朗的外表、朴实的性格以及与生俱来的高度忠诚自古便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具体到李睿的作品中,马也曾多次出现,与影片人物形成了潜在的映射关系,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透露出导演对人物生存境况的观照与思考。《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马似乎更容易被解读为老马“老骥伏枥”的象征,尽管面临晚年物质生活的清贫、精神的无处归依等诸多困境,但是在对于自己死后将以何种方式继续留存于世,老马却有着自己清晰且执拗的判断。然而,当故事被安放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志在千里”的雄心却令人倍感唏嘘,老马卑微的生存境遇亦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早已突破90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64644 元的繁荣景象中以“极少数”的名义被遮蔽。《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伴随爷爷的离世,其生前在马背上反复吟唱的“父亲般的草原正在消失,母亲般的河流早已干枯”悲歌成为兄弟二人寻父归家途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遗留下来的白马成为迥异于任劳任怨的骆驼的意象符号,其顽劣的性格一度让年幼的阿迪克尔和巴特尔束手无策,直至在爷爷的坟前奔向未知的远方。然而其看似桀骜不驯的背后却是代替爷爷展现出的不愿面对家园不再的恐惧与失望,这种面对快速消退的草原与早已干枯的河流时的无力感从爷爷生命的戛然而止延续到了白马的不辞而别。事实上,以爷爷为代表的裕固族人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从未曾因生命的结束而消逝,在兄弟二人夜宿古城之时,作为爷爷化身的白马奇迹般地闪现,在亲吻了梦中的阿迪克尔之后再次离开,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再出现,这种双重逃避使得影片的象征性得到充分的表现。依据影片给定的信息,大部分时间爷爷都在远离城镇的荒漠中独居,定期回来的孙子与不定期出现的儿子成为其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孤独与穷困是爷爷生活的常态,但在这种常态中其歌声里依然清晰地展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哀思,而丢失了草原与河流的白马选择出走又何尝不是源起这无尽的失落与孤绝呢?影片借助爷爷与白马深陷孤独与穷困情境的设置,有力展示了政策变迁与发展失衡对个体生存权利的褫夺,同时也更加彰显出反抗的无力与悲壮。《路过未来》中的白马既是耀婷的属相,又是其走向命运终点的承运者,某种意义上来说,白马伴随了耀婷短暂的一生,从起点到终点。作为新一代民工,耀婷背负了整个家庭的希冀,以汗马功劳试图扮演好识途老马的角色,为家族扎下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正如影片中出现在街头茫然无措、只能与盲人歌手为伴的骆驼那样,现代化的深圳,马注定只能在被猎奇心理消费殆尽之后,在沙漠中奔向未知的远方,群体的无望被个体的荒诞推向台前,并且迅速放大。这是一群人的生存困境,更是一代人无解的生命常态。
艺术电影中惯常使用的意象往往对应着社会现实与人文历史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攸关作品文化主题的构筑。“在巴特看来,影像的魅惑是跨媒介的。影像、图像、文学等一切基于符号阐释的艺术,都可以成为‘魅惑力’的作用场。”[3]
二、荒漠与废墟:被迫迷失与主动抛弃的母亲意象
“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就是说,艺术的意境,要和吾人具相当距离,迷离惝恍,构成独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4]作为一种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的产物,荒漠与废墟大量地出现在了艺术家的创作之中,二者天然具备的荒凉和丧失气质,往往使作品借助其“含蓄意指”生发出一种悲剧美的特质。李睿在影片中通过大量荒漠与废墟的描画,将冷峻的现实情境与人物内心的繁杂情绪内化其中,随着主人公依托这种典型环境所经历的迷失、找寻直至绝望的情节,完成了作品中被迫迷失与主动抛弃的母亲意象的建构。
《老驴头》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两部影片的故事即发生在西北荒漠景观之中。老驴头面对即将吞噬掉祖坟以及家园的浩瀚沙漠,选择以杯水车薪的方式执拗地对抗,在影片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与其相伴的只有无尽的风沙,治沙的艰难通过大量固定镜头展现,人物在画面中缓慢地移动、变小,直至以消失的方式与沙漠融为一体,这种个体的渺小与未知的命运对抗的苍凉,十分生动地放大了影片的迷失况味。而阿迪克尔与巴特尔寻父归家途中穿过的那一片巨大的荒漠与影片中借助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呈现的水草丰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态的迅速恶化正在无情地改变裕固族人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存方式。无疑,借助电影符号学提供的模型与思路,在思想层面对以上两部电影的文本进行细读,可以深切地体察到蕴藏其中的情感意味和象征意义。《周易》中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承载着西北乡民社会生活烙印的土地,在经济转型、政策更迭的时代背景下,其状况正迅速恶化,存在空间亦被无情挤压,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充满变数,无法预知,这种借用土地与荒漠界线的日趋模糊而呈现出的被迫迷失的窘境映射的正是以地母为意象的乡民的精神危机。
废墟并非近年来才开始作为表意符号出现在电影中,电影史上,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东德曾经闪现过因探寻国家重建而将镜头对准战争废墟的“废墟电影”(Rubble Film),影片《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沃尔夫冈·施陶特导演,1946年)便是这一类型影片的典型代表。毋庸置疑,作为场景空间的废墟被编织进电影文本之中,必然承担起对人物的生存处境和对现实景况的隐喻、象征的重要使命,甚至成为电影创作者一种特别的表达意愿。影片《路过未来》中,耀婷一家重回的农村老屋,是继《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之后对于废墟的又一次呈现。年久失修的院落早已成为羊群的居所,久居深圳却始终无法获得接纳的尴尬最终还是要依靠当年抛弃的土房化解,电影中的土房正是母亲的象征,目送耀婷一家远去,而后,在孤独中选择守望,在守望中走向破败,当远行的人归家,却再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庇护,这种对于母体的主动抛弃因社会变动而始,却以个人命运的颠沛流离而终。相较而言,《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废墟所承载的创作者的意旨阐释要更具分量,剥落的墙皮、干枯的胡杨、残存的断壁以及洞穴中粉蚀的壁画都指向裕固族严峻的生存处境。如果说生态的恶化是老驴头坚守无以为继的祸首,那么奥道吉尔(影片中的父亲)选择淘金的生存之路无疑带有某种逃避色彩,其悲哀的短视加剧了环境恶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文明的消亡,进而借由废墟转喻的被抛弃的母亲意象在银幕中得以浮现。由此可见,影片中废墟这一意象符号更多地被李睿指涉为遭受乡民主动抛弃的母亲,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乡民始终难以面对却终究无法逃避的精神上的无根困境。
三、道路与梦境:去魅洞见与附魅诗意
在影视作品中,运用道路象征取譬极为常见。追本溯源,1969 年由美国人丹尼斯·霍普执导的《逍遥骑士》的上映,首开公路片的先河,道路开始作为场景空间和电影意象受到关注。其后,新德国电影运动的主将维姆·文德斯更是先后奉献了《爱丽丝城市漫游记》《错误的举动》《公路之王》等名垂影史的“道路三部曲”,从而巩固了自己在公路电影类型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电影史上,道路兼具叙事空间与主题意象的影视作品,首推孙瑜导演的《大路》,影片中金哥母亲在临死前嘱咐丈夫的那句“找路,只有向前”,近乎明喻的暗合了导演寄寓的探寻中国道路的宏大母题。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公路片中,流浪与疏离往往成为其借助道路意象惯于表达的主题。而早期中国电影中,大量道路的出现常常伴随着某种诗情画意,在这种以具象聚焦现实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更具风格魅力的“中国图景”。
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在《周穆王篇》中对于“梦”曾有过这样的描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形神所遇。”[6]讲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道理。作为现实主义电影导演,毫无疑问,李睿借助梦境的描绘力图完成的是对于现实图景与底层人物的深切观照,这种忠于生活与审美追求的创作态度,展现出新时代电影人在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处散发出的弥足珍贵的人文情怀与道德理想,何尝不是李睿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言“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的写照?[7]
四、结语
众所周知,在久远的20 世纪30 年代,持续而严重的经济危机让法国陷入空前的困境,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电影工作者不得不关注现实和日常生活,努力在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亮色和生存的一点点诗意”[8]。然而,如何将忠诚记录社会真实、揭示生活本真的现实主义电影呈现出美学上的诗意,从让·维果在其《操行零分》中的超现实主义探索到让·雷诺阿《游戏规则》中景深镜头的创造性使用,不同导演对于诗意的理解和呈现亦显现出卓诡不伦的个人特质。而李睿电影中的诗意则是通过影片中大量意象符号的使用氤氲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