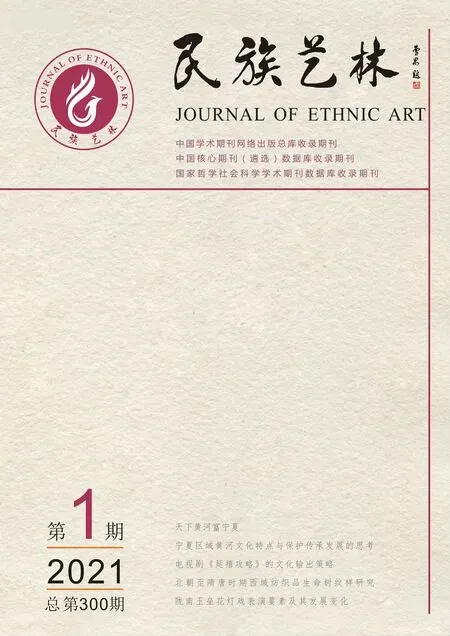历史缝隙中的现代精神光芒
——评新编秦腔历史剧《关中晓月》
2021-12-07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关中晓月》是以历史剧创作而闻名的剧作家郑怀兴近年来首次为古老剧种秦腔而创作的一部新编历史剧,颇具现代精神光芒,引人注目,成为21 世纪以来秦腔剧目建设的重要创获。作为当下县级剧团的佼佼者,周至县秦腔剧团在长年累月扎根基层埋头演出的同时,积极拓展自身的艺术格局,自觉介入当下的戏曲创作实践,以与戏剧界艺术名家携手合作的方式,经过艺术指导王晓鹰、导演何红星以及秦腔“梅花奖”齐爱云、侯红琴的通力合作,完成了该剧的二度创作,使其呈现出了卓尔不群的品相,实现了“古老秦腔在当代创作中的现代提升”[1]。
一、宏大悠远的文化意蕴
秦腔《关中晓月》以清末庚子国难之际,陕西泾阳安吴女商人周莹因向逃难西安的清廷捐献巨资而被封“护国夫人”的史实为原型。在这一史实大框架下,郑怀兴以独特的眼光来激活题材,将人物置于“晚清国运已颓萎,岁逢庚子局势危”的中国近代历史新旧更替变化的情境中,聚焦于秦商女杰商英以一己之力“愿寸忱化晓月驱除黑暗”[2],逐步开启解救关学大儒刘古愚的核心行动。剧作家以深邃的透视对人物行为动机深入开掘,凸现了人物行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将现代思想赋予剧作之中,使其主旨归结于文脉的存续与保全。
如果说全剧的主旨在于文脉的存续与保全,那么剧中的刘古愚不仅是动荡国事中问题与矛盾的焦点,更是国家文脉的象征。历史上的刘古愚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是被誉为“南康北刘”的陕西维新派领袖,倡导实学救国,既非“康党”,也与“双寡”几无瓜葛。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郑怀兴依照艺术真实的原则,以点睛之笔将颇具忧国忧民情怀的关学大儒刘古愚的命运,拼接融入商英的生活之中,架构起了商英、慈禧与刘古愚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对“晚清国运已颓萎”的大历史的多维度关照。商英营救刘古愚是为其“身系关学之兴与废”,而慈禧缉拿刘古愚乃是为“根除康梁之辈”,于是便生成了一场文脉的存毁之争。
剧中主人公商英办粥厂、以工代赈、设同绩社乃至购机器办工厂,是一位叱咤商场、勇于创新的商人,但剧作家并未着意凸现其商人特质的一面,而是瞩目于其文化担当的一面。作为新旧时代交替的新兴民族资本家,商英并非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而是从常人的直觉与本能出发,来营救陷入困境的时代思想引领者刘古愚、于右任。然而,在看似出于本能的义举背后,却凸显了其深层的内在动机——家国情怀。商英是生活成长于关中的商人,其必然受到绵延数百年的关学的滋养与濡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文化基因,早已浸透商英的血液中而化为潜意识,因此,处于近代历史更替变化背景之下的商英,之所以义无反顾勇于解救刘古愚,深层原因在于受关学深厚影响下的家国情怀。由此,让我们感受到了关学文化横亘古今的永恒魅力,实现了借陕商文化写关学精神与文脉传承的创作主旨。
剧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慈禧,是一个特定情境下的“落魄者”。剧作家在呈现其政治意识面向的同时,以理性的认知历史精神的方式,对处于国运颓危情境之下的慈禧的文化反思意识进行了深入开掘。作为一位政治家,慈禧对作为“康党”的刘古愚急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在商英的觐见谏言下,她对当时处于危局的国运也进行了一定反思,对刘古愚的认识从“图谋不轨”转变为不可多得的“国士”,最后将这位关学掌门人聘为兰州大学堂总教习,而将商英诰封为“护国夫人”。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经历庚子之乱后,作为政治家的慈禧在大变局之中的反思以及对文脉的重视,也意味着对商英存护赓续文脉的“护国”之举的肯定。
傅谨先生曾言:“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戏剧似乎正在进入‘地方题材’时代。”[3]若以21 世纪以来的戏曲创作实践而言,此断言可为定论。伴随“地方题材时代”而来的问题是,剧作家的创作视野如何超脱地域的捆绑与束缚,进而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开掘出独特的文化意蕴,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剧作家们的创造力。秦腔《关中晓月》其实也是一部地方题材“命题之作”,但郑怀兴凭借自己多年的思考与积累,以高妙的史识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游走于历史与想象之间,用思想的灵光去激活历史题材,赋予其现代思想光芒,让古人穿越历史风尘与今人隔空共鸣,跳脱了宣传地方文化的窠臼,使剧作洋溢着宏大悠远的文化意蕴,呈现出了独树一帜的精神亮度。
众所周知,赋予剧作现代思想光芒,一直是作为艺术命题的戏曲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全剧虽以女商人商英营救关学大儒刘古愚为核心情节,但剧作家“在商英的身上,已注入了今情——即我的思考、我的理想、我的情感了”[4],将今情注入古事,将眼光投射到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物背后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因此,故事的内核是表现一个商人的文化担当,从而凸现国运颓萎、时代转型大背景下绵延不绝的关学文化所具有的现实力量与价值,从而使该剧散发出耀眼的现代思想光芒,颇具文化品格与浩然之气。同时,剧中浓郁的文化意蕴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不经意中润物无声地给人以深思,使古今对话,启发今人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与赓续。
二、洞烛幽微的心灵透视
作为历史剧创作的斫轮老手,郑怀兴善于开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认为历史剧艺术虚构的天地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史学家记录历史人物的外在行动,剧作家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一心一宇宙,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供我们剧作家想象力驰骋的无限广阔的天地。”[5]“在大厦将倾、国运颓危的规定情境中,剧作家剖析历史载录的缝隙”[6],通过艺术化的虚构与再造,完成了大历史背景下洞烛幽微的心灵透视,凸现了商英在风雨如晦中保护文化命脉的曲折心路历程,呈现了冰冷历史中人性的温柔光泽。
商英的身份虽是富甲一方、赫赫有名的商人,但剧作家未以其商业谋略与智慧作为心理开掘重点,而是择其“凡人”一面,对其不同情势下的心理境况进行洞烛幽微的心灵透视。在劝刘古愚逃难时,商英以朴素的“堂堂正正活世上,干干净净赴泉台”道理来劝慰;揣摩慈禧捕杀刘古愚的原因,认为是“莫非他谈国事有人告密,为此事教太后心里发毛?”认为进献牛奶可使慈禧消怒,对发牢骚的读书人应包涵;面对淳朴的饥民送还散失奶牛时,她期望统治者“请莫把民当作猛兽看待,施仁政多爱民否极泰来”。
在将商英视为平凡“小人物”的同时,作者并未将其心灵扁平化,而是以细腻笔触凸现商英心灵的复杂性。当得知曾仗义救助自己的恩人刘古愚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时,商英建议“快到我安秦堡密室藏一阵”,不仅是出于报恩心理,也有“哲人一去华山颓”的隐忧心理,较复杂地书写出了商英在特定历史境遇下解救刘古愚的心理动因,体现了剧作家对笔下人物的理解与同情。当得知捐献之资由十万陡增至五十万两时,商英不免心里动摇而退却,“(旁唱)叹太后漫天要价,感抚台体恤商家。觐见不如且作罢,捐五十万力竭乏”,显示了困境中商英脆弱的一面。尤其在得知族议不许入葬秦家祖坟时,“此一生为秦家心血费尽,死难道反落个野鬼孤魂”,其内心之苦以长达40 句的核心唱段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将嫁入秦家以来遭族人欺凌之痛与作为寡妇的孤独之苦和盘托出,使人更加体会到商英作为普通人不易的一面,也更能凸现商英“愿寸忱化晓月驱除黑暗”的难能可贵。
在以“小女子”视角开掘商英心灵平凡而复杂面向的同时,剧作家并未忽略人物心理的变化。当岑春煊索要十万两银子时,商英先是担忧“他请求捐款狮子大开口,若不允恐右任一命将休”,然后是“逢灾年我也是捉襟见肘,你开口我应当仔细运筹”,凸现了其内心两难的复杂性,既要顾虑经济方面的问题,又担忧于右任的命运。在踌躇之际,岑春煊说因刘古愚与于右任是师生关系,若不以银换信,后果将不堪设想,商英的心理又是“捐十万可取信能解我忧,又听这挂上号陡添我愁!救古愚这句话怎好出口,顷刻间心如遭万马践蹂”,为如何解救刘古愚而心忧如焚。恰值李莲英来问奶牛来源,于是商英“(旁唱)悉慈禧对牛奶赞不绝口,顿让我又一计涌上心头”,凭借商人特有的机敏,称“自小多崇拜慈禧太后”而提出觐见慈禧以图面谏。通过一连串的心理活动,揭示了商英心理变化过程,使人物内心获得了动感与质感。
除了凸现商英心灵复杂性与变化性外,另一位构成戏剧张力的主角慈禧的心灵开掘也与以往不同。作为近代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慈禧形象难免脸谱化窠臼,而剧中的慈禧既有政治人物的气势,又平添了些许人情味。在“联军进犯风雷沸,两宫西逃秋风催”的形势下,慈禧作为统治者要根除危及社稷的祸害“康梁之辈”,因而下令立即缉拿刘古愚,不失杀伐决断的王朝女主气势。在历经生死劫难后,对“鞠躬尽瘁”的李莲英、护驾功高的岑春煊感激不已,充满了人情味。在惊魂甫定之余,权势倾天的慈禧的愿望不过是“入关中但愿我能得安睡,还思量鲜牛奶日饮几杯”。当慈禧得知商英请求觐见时,“(旁唱)我仓皇逃入秦惊魂未定,对民妇求觐见不免疑心”,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敏感;当得知商英与康党并无瓜葛时,她充满了人情味地说:“喝了人家送来的牛奶,不恩准人家请求,也说不过去呀。”剧中的慈禧不再是冰冷的政治面孔,而是具有人性的温度与丰富性。
在“双寡夜谈”中,其被商英守寡创业的艰辛所触动,“你与我命运都一样,年轻轻守寡苦难当。你有苦不敢对人讲,我有苦唯你能猜详”,生发出了“治家治国理同样”的同病相怜之感,甚而认为“儿你艰难胜过娘”,俨然一位心地善良、面目可亲的慈母形象。特别是最后听完商英诉说后,务要缉拿刘古愚的慈禧的反应是“哦,原来刘古愚是这么一个人……”政治家杀伐决断的冰冷面孔终于卸了下来,艺术真实地体现了政治剧变情势下,慈禧痛定思痛后的内心反思。
剧中的岑春煊是当时识时务的朝廷官员的典型代表,他曾因追随康梁险被治罪,在西狩中又立功被擢拔,也并未脸谱化、简单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慈禧下令缉拿刘古愚时,岑春煊犹豫迟疑,“杀大儒将冒天下大不韪,太后她大权在握难抗违”,处于两难之境,只能在幕僚岑炽建议下“虚实并施来应对”。在既要顾及慈禧对其曾为康党的疑心,又要确保前路粮台职责完成的情势下,当得知商英“借献牛奶救秀才”的真实意图后,他借机“狮子大开口”软硬兼施,要求商英捐款以完成筹措粮饷重任,体现了岑春煊作为官员的八面玲珑。尤其是慈禧在对商英求觐见时疑心重重,担心有行刺之举,提出“有无与康党交往”之问时,岑春煊心理是:“(唱)慈禧她目光犀利非虚传,未见面却已把商氏看穿。一句话问得我涔涔冒汗,该说有或说无我都为难!”于是欲装聋作哑,无奈慈禧紧问不舍,岑春煊“(旁唱)当说无才能过眼前这关”,以觐见换取商英捐资,从而完成筹措粮饷任务。当李莲英建议慈禧将捐银额度提高时,岑春煊在惊愕犹豫之余,转念“(旁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且漫天要价,吓阻秦商氏,免得惹出是非”,于是建议捐五十万。在这一连续变化的心理过程中,凸现了作为朝廷官员代表的岑春煊既要完成职责重任,又要顾及自身安危而明哲保身的复杂心态。
作为总管太监李莲英戏份虽不多,但在有限篇幅中,其心理也得以刻画。其无时无刻不为讨主子欢心而动心思谋划,同时也要暗中助力拜把兄弟之子岑春煊。当慈禧喝上牛奶,李莲英心理是“老佛爷喝一口老泪双流,有几人知道她风霜饱受”,体现了对主子的体谅理解,富有人情味;当慈禧命岑春煊秘密逮捕刘古愚时,他又从旁挤眉弄眼来帮衬,对子侄多有关怀。
剧作家以自身的生命阅历激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但洞烛幽微地开掘出了商英、慈禧、岑春煊、李莲英等人物心灵丰盈的多面向,使其含有别具风采的生命质感,凸显了自身独具只眼的探索眼光与心灵体验,而且还匠心独运地构筑起人物间的心灵冲突角逐,营造出极具张力的戏剧性。
剧中人物整体分两大阵营:一方为商英,一方为慈禧、岑春煊、李莲英,身份、立场各异。因此,剧作家主要构筑了两大阵营间的心灵角逐与冲突。对刘古愚的态度,慈禧是“一提起康与梁我便愤恚,没康党清社稷怎会临危”,视为心头大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商英是“一路上对一事更猜不着,太后为何视古愚为贼蟊”,疑惑不解,全力解救。这一冲突意味颇浓的态度,为全剧的戏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最终走向高潮“双寡夜谈”设置了悬念。
“双寡夜谈”是作者着力经营的心灵角逐最终呈现的一场戏,慈禧将商英捐助之举视为“为国分忧”,而商英的目的乃为营救刘古愚,二人见面的动机判然有别。对于商英,慈禧充满好奇,“(旁唱)二十岁就守寡家业怎创,真令我好惊讶当问端详”;对于慈禧,商英乃平稳情绪,“(旁唱)我把她看作是街坊大娘,莫慌张且从容拉拉家常”,显示了二人的不同心理。在刻画二者心理之异的同时,作者更瞩目于二人的心灵靠拢。随着商英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作为统治者的慈禧遂生同病相怜之感,商英也发出了“太后,你好累呀!”的感触,理国与治家的两位女性的心灵获得了暂时沟通,为最终解救刘古愚提供了转机。
然而,当慈禧得知“胆大包天”的商英乃是为刘古愚求情时,勃然大怒,和缓的剧情陡生波澜,最后全剧解救刘古愚的核心行动最终完成。不难看出,“双寡夜谈”正是编剧构筑心灵冲突策略的精彩体现,也是全剧的“蹲底戏”。
在呈现慈禧与商英心灵冲突外,对于商英与岑春煊的心灵冲突也着意经营。当商英献奶牛后,岑春煊心理是“(唱)鲜奶如及时雨喜出望外”,将商英视为“陕商表率”,为完成供应任务而欣喜不已;商英则是“(唱)他喜悦我要趁机把口开”,借机为投书的于右任脱罪,二人心思截然不同。至商英觐见时,岑春煊心理是“(旁唱)一见她胆已怯我暗高兴”,想让商英铩羽而回,以免惹出乱子,而商英心理则是“(旁唱)安秦堡不扩建款且取尽,为输忱我不惜家产全倾。我此行将心旌稳稳把定,见銮驾怎进言成竹在胸”,意志坚定,胸有成竹,二人心理针锋相对,冲突性更为强烈。
总体可见,剧作家笔力雄健,心细如发,洞烛幽微地对人物心灵进行了丰富而全面的透视,使剧作获得了“内在的人情的真实”[7]。不仅通过人物心灵隔阂冲突营造出内在型的戏剧冲突与富有张力的戏剧性,而且凸现了以“人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戏曲本体特性,使剧作充满了意味浓厚的抒情性,体现了其在历史剧创作中刻画开掘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厚功力,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一剧之本”。
三、醇厚新鲜的戏曲韵味
“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8]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关中晓月》的最终完成要归结于舞台呈现,其表演与舞台设置既遵循了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原则,又凸现了现代观念下传统戏曲艺术的新突破,充满了醇厚且新鲜的戏曲韵味。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9],以优美的程式化表演为其鲜明的美学标志。《关中晓月》虽是一部清装戏,但程式化的表演在其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空间,不仅运用了诸如跪搓、卧鱼、圆场等身段,还利用了马鞭、长绸之类的道具,体现了传统戏曲的程式之美与形式之美。在商英首次亮相时,以一连串的立马鞭、扬马鞭的虚拟动作,结合轻盈优美的圆场身段,展示了商英“催马礼泉访高贤”的行动过程,充分发挥了传统戏曲的虚拟性特质。当刘古愚为救弟子于右任而决定舍身投案时,商英心急如焚,苦苦劝告,以跪搓的步法程式来表现其内心的焦急,使其内在情感得到了外化。在送奶牛进城时,商英坐着小轿,以四位轿夫的虚拟动作来呈现坐轿赶路的过程,灵动优美;当奶牛四下惊散时,以慢卧鱼来表现其心情失落,体现了戏曲“无动不舞”的表演特点。
尤值称道的是,齐爱云自身的戏曲绝活长绸技艺在《关中晓月》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戏剧情境形成了有机结合。在奶牛被惊散之时,齐爱云先后以高飘绸、车轮绸的精湛技艺来调教牛群使其平静,既突出了角儿的技艺,凸现了戏曲绝活的形式美,又渲染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与剧情相得益彰。当商英在幻觉中看见刘古愚被鬼卒追捕时,齐爱云再次以舞动的红绸来凸现其内心的愤愤不平,展现了“小女子”的勇于担当。
如果说戏曲表演充分利用程式,凸现了其作为表现艺术的魅力;那么戏曲表演也注重体验,以便于塑造出内心丰富的人物形象。《关中晓月》的戏剧性更注重于人物的内心冲突以及人物之间的心灵斗争,因此,在表演上除了凸现鲜明的戏曲程式化特征外,还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深度体验,往往借助形体、眼神、声音、表情等,从心灵上把握人物形象,深刻入微地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当商英从李莲英口中得知慈禧对牛奶赞不绝口时,齐爱云以“旁唱”的形式,同时伴以灵机一动、计上心头的面部表情向观者展露其心理,凸现了商英作为商人的机智灵敏。尤其在第五场中对于商英觐见,慈禧、岑春煊、李莲英三人之间各怀心思:岑春煊的谨小慎微,通过面部惊愕不定的眼神、微微晃动的双手来表现;慈禧面如止水,不动声色,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洞若观火;李莲英以丰富的脸部表情,在二人之间来回敷衍。此处通过体验式的表演,细致入微地呈现了三人各怀心事,各说各话的戏剧性场面。整体而言,全剧表演实现了表现与体验的有机结合,避免了话剧加唱的弊病,完成了深层的戏曲化表达。
概而言之,传统戏曲舞台以“一桌二椅”为主,以“虚空”为其鲜明的美学特征,最终追求的是灵动的写意精神。然而,随着物质技术条件的提升,当代戏曲舞台打破了传统“一桌二椅”的固有形式与传统,依剧情需要而设置新式布景。《关中晓月》的舞台以两块颇具关中地域特色和历史沧桑感的青砖砌墙为主,上方楷书浮雕“关中晓月”四字,下方左右有方圆门洞,背面分别镌有慈禧、商英黑白画像与生平简介,与本剧浓郁厚重的文化意蕴正相契合。随着剧情的进展,其犹如魔方一般迁移组合,或左右移动,或一纵一横,或纵向相对,或旋转利用背面,简洁且凝练,变化而统一,与剧情紧密结合,使表演空间具有灵动之气。这与“一桌二椅”的以简驭繁、以少胜多的内在精神相通,符合戏曲舞台时空自由的美学要求,是对传统戏曲写意精神的现代张扬。
结语
如果说郑怀兴的晋剧《傅山进京》被誉为“文人戏的新高度”[10],那么秦腔《关中晓月》既是一部文学与表演相得益彰的成功之作,也标志着剧作家对个人“新高度”的突破。戏曲理论家龚和德曾说:“(戏曲)内容上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对人的心灵的艺术展现达到现代人赞赏的深度,并有利于现代人的心灵建设。形式上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在进行新的综合中达到现代人赞赏的高度整体感,并且含有现代人击节称赏的形式技巧的美。”[11]若以此来审视,秦腔《关中晓月》不仅对人的心灵进行洞烛幽微的透视,而且注重戏曲本体精神的现代舞台转化,毫无疑问是一部传统韵味浓郁且散发着现代精神光芒的难得之作,经得起舞台演出的最终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