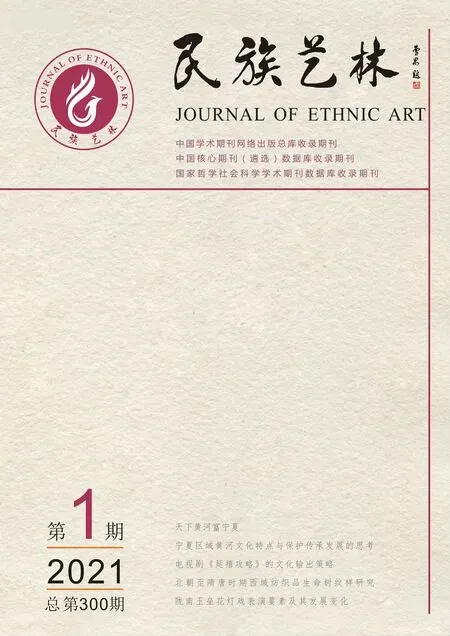多元视角下的内蒙古电影民族文化呈现研究
2021-12-07
(河北地质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四川 成都 610599)
以发展的眼光向历史最深处漫溯,惊然发现内蒙古电影已走过70 余年波澜壮阔、风景如画的辉煌历程。在内蒙古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土地上,一批批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影视创作者得以施展才华,他们创作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册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一部又一部极具草原特色、饱含内蒙古文化、震撼人心的影片征服了无数电影观众。可以说,在辉煌70 余年的经典岁月中,内蒙古电影成为内蒙古文化景观的重要塑造者,无论是描摹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构建民族团结的经典画面,抑或者是探寻民族文化精神之源,内蒙古电影成了传承草原文化精神、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梳理内蒙古电影诞生70 余年来创作的影片,从景观美学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建构,不难发现,故事、音乐、民俗构筑了内蒙古电影的文化景观,三者交融谱写了一曲民族文化景观的电影“协奏曲”!
一、与时代共鸣合拍的故事创作
(一)社会主义认同的建构
从影视人类学的角度讲,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映演。当电影成了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时,它就绝不是简单的娱乐产品,而是履行政治文化职能的文艺产品。要知道国家初建之时百废待兴,而此时的电影就已然成为新中国大规模改造与重建的文化系统,这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电影成了同政治紧密结合、完成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内蒙古电影从诞生之日起便反映时代文化,将意识形态与民族话语进行了巧妙的置换,生活于内蒙古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精神面貌在影像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可以说内蒙古电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描摹。《草原晨曲》讲述的就是内蒙古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故事,影像既有胡合投入到与日寇斗争的光辉革命岁月,又有胡合带领民众如火如荼建设家乡的场面。此后,诸如《东风》《前哨》等反应内蒙古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波澜壮阔地诞生了,可以说内蒙古电影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认同的构建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家国情怀的书写
翻阅早已泛黄的电影史册,不难发现在内蒙古电影70 余年创作艺术史上,家国情怀是其亘古不变、涓涓诉说的永恒话题,正是对家国情怀的描绘让内蒙古电影的文化景观得以别于其他类型电影。在70 余年的历史流脉与复杂的文化形态面前,内蒙古电影因社会思潮的流变而对于家国情怀的表达几经转变。抽丝剥茧般对70 余年来内蒙古电影进行系统梳理不难发现,其对家国情怀的诉说共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是对民族历史的重现与彰显。以塞夫、麦丽丝为代表的内蒙古籍导演创作了诸如《悲情布鲁克》《东归英雄传》《骑士风云》 等刻画民族历史的影片。《东归英雄传》讲述的就是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的顽强意志与向往自由的民族文化,这些从民族历史中取材表现民族文化的影片让“家与国”得到了历史印证。其次是对民族性格与文化的表达。内蒙古电影将个人同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反映出时代文化中内蒙古群众的博爱胸怀。《天上草原》《额吉》《海林都》等电影讲述的都是当下草原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历史事实。对以“抚养三千孤儿”为代表的真实事件的书写,让一个民族敦厚与崇高的品质得到了尽情表达,也让个体、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紧紧相拥,这就构筑了一条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景线。
(三)大时代普通人的描摹
区别于其他电影的“宏大叙事”,内蒙古电影向来以一种“底层叙事”的姿态创作故事,表现大时代背景下草原普通人民的历史沧桑、生存境遇。电影《海林都》是将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与草原三千孤儿将结合,创作出的以草原母亲“都贵玛”为原型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在讲述如此宏大历史事件时,影片不曾拘泥于宏大历史文化,而是将镜头对准阿柔娜与萨仁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通过表现他们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态度,尽显社会现实面貌。除了讲述宏大历史事件,内蒙古电影还将镜头对准了时代背景下的平凡民众,私密化的个人叙事书写了当下内蒙古群众的生存境遇。《片警宝音》作为一部表现英模的影片,却没有书写主人公高超的智慧、独特的破案手法,影片向观众展现的仅仅是调节邻里纠纷、送快递这种“小事情”,在描绘平凡人、平凡事的过程中,草原亲子关系、牧民财产分割以及死亡时刻的宗教仪式等均充分体现在了影片中,这再现了新时代进程中鲜明的内蒙古文化形象,展现了本地区民众生存现状的文化景观,体现出巨大的电影文化价值。
二、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运用
(一)民族乐器的镜像化呈现
从建构民族影像文化的角度来看,内蒙古电影鲜明的影像风格来源于选取的民族符号,而音乐在电影中作为烘托主题、描摹心理的重要手段必定成为塑造文化景观的重要能指。乐器作为人类在生存中所制造的一种传递声音的娱乐产品,其必定承载民族精神、表达民族情感,故此内蒙古电影在塑造民族文化景观时,民族乐器便时常出现在镜头之中。在内蒙古电影中,大众可以时常看到马头琴,马头琴的出现印证内蒙古电影的民族风格,表现着草原民族的风情。从声音角度讲,马头琴琴音圆润,浑厚而低沉,这样的配乐加以内蒙古电影独特主题的书写,为观众谱写了一曲内蒙古群众的独特情感。在电影《嘎达梅林》接近尾声之时,一位艺人手拉马头琴吟唱出了对草原英雄的崇敬之情,这是对内蒙古民族特有历史的一种独特深思缅怀;《东归英雄传》中,面对尸横遍野、白骨淋漓的场面,马头琴的声音再次飘荡在草原上空,马头琴曲调的出现表征的是民族的悲凉和对战争的反感,亦是对土尔扈特部回归故里艰辛不易的写真。可以说,在内蒙古电影中民族特有乐器的出现让影片拥有了生命力,让内蒙古文化景观得到了深层次构建。
(二)歌词文本的民族化体现
在70 余年的创作岁月中,内蒙古电影是以一种多元形态的方式进行创作的,它在保证原生态民族文化表达的基础上,合理化搭载其他民族的文本媒介,构筑出独有的文化抒情样式。音乐的民族性与电影的艺术性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音乐中,原生态的母语曲调、歌词文本并非是它的全部,影像中音乐的歌词大多是以汉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电影作为文化生态产品的必须。在内蒙古电影中,原生态母语的歌曲演唱并不能对影片产生积极影响,故此配乐大多采用了含有民族特质的汉语歌词,曲调则以蒙古族传统曲调为主。例如传承至今的歌曲《草原晨曲》便在歌词文本中凸显了内蒙古文化,“再见吧金色的草原再见吧幸福的家乡啊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这样的文本创作,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这也揭示着内蒙古群众对于建设家乡的奉献。内蒙古电影的音乐在汲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在歌词文本上进行了“跨界”,寻求到了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平和点,造就了内蒙古电影的民族文化景观。
(三)中西结合创新音乐形式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电影市场化的今天极具尴尬色彩,其既得不到市场/票房的高额回报,又不能在普通民众中收获良好的口碑,部分电影直接同市场渐行渐远而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近年来的内蒙古电影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八月》《告别》《心迷宫》等“小投资”的影片在成功地获取了盈利的同时,收获了各大电影节展的青睐,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这被誉为是电影界的“内蒙古”现象。究其原因,是电影界一直在高喊电影要“走出去”时,内蒙古电影却强调“引进来”,其电影中蕴含着丰富的“他者”文化元素,“自我”与“他者”的融合让影片碰撞出了一定的火花,而这种交合则在20 世纪80 年代便在电影音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成吉思汗》(1986)中,电影音乐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内蒙古民族音乐,或者说不再单纯地使用中国乐器,而是创造性地选取了西洋乐队,用西方音乐元素配以中国传统乐器来表现民族风格成为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成吉思汗与勃尔帖新婚之夜的音乐“是由我国民族乐器箫和西洋乐器单簧管、圆号、铝板琴、竖琴及弦乐组演奏的”[1]。中西乐器结合的方式,创造性丰富了内蒙古电影的音乐形式,更加增强了民族音乐的感染力,构筑出了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音乐文化景观。
(四)长调民歌烘托文化韵味
内蒙古电影中最能凸显民族文化的音乐就是长调民歌。长调是蒙古族独有的传统民歌体裁,它曲调浑厚苍凉、高亢悠远,为影片的主题表达与民族文化呈现贡献着自己独特的力量,在内蒙古电影中,长调未曾成为吸引大众目光的猎奇元素,而是成为表现蒙古族人文情怀的重要助动力。在《悲情布鲁克》 中,长调的应用让蒙古族自由洒脱的“马背文化”呈现得淋漓尽致:在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上,草原男儿身骑骏马高声合唱《酒歌》,艳阳高照,醉酒当歌,骏马相逐,歌曲随着马匹的步伐把蒙古族人民的豪放与自由的精神面貌传递给观众,一曲《酒歌》成了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缩影。自然,蒙古长调并非仅仅凸显蒙古族豪放的文化,它还蕴含着蒙古族博爱、温和的感性色彩,诉说着蒙古族人的情绪变动。在以“长调”为主题创作的电影《长调》中,面对母骆驼不下奶,一曲《劝奶歌》荡涤在草原之上,悠扬的曲调最终感化了母骆驼,几近哀求般的音乐曲调让观众看到了蒙古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灵的关爱。可以说,在《长调》中,长调成了主人公消解远离故土的惆怅、表达向往草原的欣喜的叙事载体。蒙古族特有的长调民歌成为蒙古族人民情感抒发的重要介质,在影像的叙事中构筑了一道独有的文化景观。
三、秉承民族精神的信仰呈现
(一)敬畏自然的价值观念塑造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发展急速转轨,昨是今非之场景历历可数。蒙古族文化也遭遇现代文化的大规模冲击,21 世纪以来的内蒙古电影呈现出一种追寻人文关怀精神的趋势。面临大规模的工业文明建设,传统的自然观念、草原文明的平衡圈层受到了致命打击,草场的退化、环境的恶劣,传统的水牧栖息之地遭到了金钱的无情掠夺。“传统的草原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化本就是二元对立的存在”,[2]在这样的视域中,内蒙古电影通过影像诉说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态保护的执拗,它将蒙古族人民生存的命题融入社会发展之中,从悲剧与危机角度描摹人类的生存现状。一方面,内蒙古电影将信仰转化为镜头画面,面临生存危机与环境危机时,蒙古族人民祈求“长生天”的庇佑,《绿草地》《狼图腾》《圣地额济纳》 等等一系列电影中均能看到“长生天”的镜头,而祈求庇佑的基础在于敬畏自然,在于认同万物有灵。另一方面,内蒙古电影通过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传递敬畏自然的价值观,《季风中的马》《狼图腾》等一系列影片均是从这个角度呼吁大众关注自然、保护生态文明。内蒙古电影在“娱乐狂欢”的年代,用自己有限的能力试图唤醒观众理性思考,让社会发展与文明推进得以获得些许探讨。敬畏自然成为内蒙古电影导演的自觉追求,也成为内蒙古电影独有的文化景观。
(二)持守祭祀文化的影像化展演
毫无疑问,电影是一种活动的影像,是一种信息的记载者与传播者。内蒙古电影之所以能够构筑起区别于其他类型电影的风景线,就是因为其对民族特色文化呈现与表达的坚守,而这种民族文化背后承载的就是内蒙古民众的精神实质。几经岁月流变,内蒙古电影中的信仰并未出现退守与漂移之态,而是一以贯之的持守呈现。内蒙古电影中的信仰可以从持守祭祀文化中得到深刻体现。首先是祭祀敖包。在蒙古族自我的民族文化中,祭祀敖包不是对一个终结生命的叹惋,而是祈求上苍保佑的表现。在《嘎达梅林》《悲情布鲁克》《天上草原》等内蒙古电影中祭祀敖包得到了充分展演。以《战神纪》为例,影片中的祭祀敖包就是为了祈求草原和平吉祥,祭祀敖包成为一种祈求降福、保佑人畜两旺的文体礼仪,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对于万物生灵的感恩,是一种宽厚的民族文化观念的体现。其次是“祭火”场景的塑造。“灶火是氏族、部落和家庭的保护神,也是赐予人们一切幸福和财富源泉”[3]。这正如影片《天上草原》中主人公在祭火祷告时说:“火神啊,你给草原带来福气吧,你给畜群带来运气吧,你带给人丁福气吧,免去草原的一切疾病吧。”对于祭祀文化的呈现,表现的是内蒙古群众对文化传承的观念、对民族文化的敬畏与信仰,内蒙古电影鲜明的民族风格正是借助了祭祀文化/文化观念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
在70 余年的时光洪荒流变中,内蒙古电影一以贯之的坚守着自己的风格特征,不低俗、不媚俗、不庸俗,立足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恰到好处地将民族元素融入影像之中。“内蒙古民族电影的价值坚守,是取决于艺术家遴选民族文化资源的明确标准的”[4],可以说,内蒙古电影因为故事、音乐、信仰的独特选取/表达而自成一派,各类文化景观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象征意味,这使得电影成了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表现载体,内蒙古电影70 余年来的创作发展让影像构筑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走出了一条属于自我的创作道路!